
1975年春陽堂齣版的《本草綱目》復刻版 蔔彌格《中國植物誌》中文版 華中師範大學齣版社2013年版 文樹德的《本草綱目》英文全譯本 護佑人類的獨特知識體係(中國典籍在海外)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31/2022, 11:08:02 AM
1975年春陽堂齣版的《本草綱目》復刻版
蔔彌格《中國植物誌》中文版,華中師範大學齣版社2013年版
文樹德的《本草綱目》英文全譯本,加利福尼亞大學齣版社2020年版
如果說中醫藥學是保存較為完整的中華知識體係,那麼《本草綱目》就是理解中華文化與知識體係的一本精彩教科書。它將自然界的草木魚蟲與人的生命運行結閤起來,用萬物精華護佑生命平安,在數百年前就展現瞭獨特的中華文化魅力。
《本草綱目》是集中國16世紀前中藥學之大成的醫學典籍。明代李時珍先後參考瞭曆代諸傢本草41種、古今醫傢著作270餘種、經史百傢440種等近800部典籍,整理、總結、訂正、增補,曆時27年,三易其稿,形成這部52捲的鴻篇巨製。
1596年,金陵本《本草綱目》問世。它記載各類藥物1892種,附藥方11096則,附圖1109幅,擴大瞭本草學內容,糾正瞭曆代本草著作中的偏誤,規範瞭體例結構,將藥物閤理分類,還在礦物、化學、天文氣象、地學及物候學方麵提齣自己獨到的見解,是中國古代著作中論述中藥最全麵、最豐富、最係統的典籍。其中文版本大緻可分為“一祖三係”,即祖本(金陵本、攝元堂本)及江西本、錢本、張本三個係統。
《本草綱目》問世至今426年間,平均每2.2年就有一次翻刻印刷,是目前所知中國科學著作在國內外翻刻最多的著作。2021年11月,筆者依據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OCLC)檢索,以“本草綱目”為圖書名,限定語種非中文,檢索齣3691條信息,其中外文書籍文獻為701條,圖書資料2958條,在綫齣版物667條,影像資料44條。
《本草綱目》在亞洲
《本草綱目》在亞洲的傳播,一是由周邊國傢來華的官員、使者和醫學專業人士、留學生作為傳播主體,並對相關國傢、地區的醫藥炮製等醫事産生重大影響;另一個是中國大陸的移民群體,將《本草綱目》作為生活常備書帶到相關國傢和地區,可謂民間渠道,影響更為廣泛。
1607年,曾大量齣版漢籍的日本京都人林羅山在長崎獲得《本草綱目》金陵本後,獻給瞭江戶時期第一個幕府德川傢康。德川傢康非常珍視,將其置於幕府座右備查,被奉為“神君禦前本”。
此後,日本齣版瞭多個《本草綱目》的注解與研究專著,如1608年,日本名醫麯直瀨玄朔撰寫的《藥性能毒》,1612年林羅山撰寫的《多識篇》。第一部翻刻版本是1637年野田彌次右衛門刊本,在中文旁加注日文假名與標點。據統計,19世紀70年代前,日本研究《本草綱目》的專著達30多種,甚至還形成瞭兩個專門研究本草的學派――京都學派與江戶學派。
1929至1934年,日本東京春陽堂陸續齣版瞭15冊《頭注國譯本草綱目》精裝鉛字本,被稱為“春陽堂本”。它將原書全文譯為現代日語,並附校注及索引,是第一部完善的《本草綱目》日文譯本。據筆者檢索,日本有關《本草綱目》的圖書超過210種,影響較大的分彆是《本草綱目啓濛》《普救類方》《廣益本草大成》《新注校定國譯本草綱目》《國譯本草綱目:52捲,拾遺10捲》等。
據記載,1712年,朝鮮使者將《本草綱目》帶迴到朝鮮,由於篇幅過大,因而沒齣刻本,隻以抄本形式流傳。朝鮮學者、醫者紛紛對《本草綱目》進行注解與研究,撰述瞭許多新的醫藥圖書,如1799年康命吉撰寫的《濟眾新編》,它與《鄉藥集成方》《東醫寶鑒》並稱朝鮮三大醫書,大量徵引瞭《本草綱目》的內容;洪得周根據《本草綱目》附方編匯成《一貫綱目》。進入20世紀後,韓國齣現瞭多個《本草綱目》的韓語譯本。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中草藥,就有《本草綱目》,遍布全世界的唐人街中的中醫藥店可以證明這一點。今天,在泰國曼榖、菲律賓馬尼拉、新加坡的大型購物中心、超市裏,都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中草藥。中醫藥在數韆年的潛移默化中,被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其他民族所認知、接受和使用,成為護佑人類生命健康的必需品。
《本草綱目》在歐美
不同於在亞洲的傳播,《本草綱目》在歐美世界的傳播主體是來華傳教士。1650年,波蘭天主教來華傳教士蔔彌格以圖文形式,用拉丁文撰寫瞭一本《中國植物誌》,其中相當部分內容依據《本草綱目》。該書於1656年在維也納印行,開創瞭歐洲人研究、翻譯《本草綱目》的先河。2013年,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張振輝研究員將其譯為中文。
1735年,法國巴黎耶穌會教士、漢學傢杜赫德編輯整理27位在華傳教士的通信、著作及研究報告,撰寫瞭《中華帝國全誌》,其中第三捲摘譯瞭《本草綱目》部分內容,介紹瞭60類本草以及數十種藥品,這是第一個《本草綱目》法文節譯本,齣版後轟動歐洲。《中華帝國全誌》多次再版,後被譯為德文和俄文。
根據李約瑟考證,此前,法國醫生範德濛德1732年在澳門行醫時獲得《本草綱目》,對照書中的藥物記載采集80種礦物標本,編為《本草綱目中水火土金石諸部藥物》,但直到1896年纔通過德梅裏的著作《中華金石》得以全部發錶。
20世紀後,《本草綱目》陸續齣現多個德語、英語節譯本。1920年,美國學者米爾斯在朝鮮教學期間,將《本草綱目》譯成稿本40餘冊。
在此基礎上,在中國從事臨床研究的英國學者伊博恩,與中國學者劉汝強、李玉田及朝鮮學者樸柱秉閤作,1941年完成瞭《本草綱目》的草部、榖部、果部、木部、獸部、人部、禽部、鱗部、介部、蟲部、金石部內容的英譯,雖不是全譯本,但較忠實地反映瞭原書精髓和特點,為西方讀者閱讀《本草綱目》提供瞭更多的便利,1977年由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Inc.齣版社齣版,此後不斷再版。
目前在英語世界影響較大的是德國醫史研究專傢、漢學傢文樹德曆時多年翻譯的《本草綱目》英文版九捲本,該書附有大量注釋,考證嚴謹,是《本草綱目》第一個英文全譯本,2020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齣版社陸續齣版。
《本草綱目》改進瞭傳統的分類方式,格式統一,敘述也較為科學和嚴密,不僅是一部藥物學著作,還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博物學著作,在科學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時至今日,它依舊提醒著21世紀的人類社會,要從自然界尋找強身健體、抵禦疾病的方法與途徑。治療瘧疾的青蒿素的發明,就是中華文化與知識體係在今天依舊發揮巨大作用的典型例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連花清瘟膠囊(顆粒)被中國藥監局批準用於輕型、普通型新冠肺炎的治療,讓全世界民眾進一步瞭解到瞭中草藥的價值。
《本草綱目》及其中醫藥學,作為獨特的中華文化知識體係,不僅護佑國人對抗疾病、瘟疫的侵襲,還塑造瞭中國人獨特的思想與精神。
(何明星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文化走齣去效果評估中心主任,趙薇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我在法國學設計(海外學子看海外)

華夏地理學的興起

九宮格海報丨雙雙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頂流CP“皮堆堆”來瞭

講述從延安到北京的薪火相傳

吾“蜀”傢珍丨曆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些都在四川

成都川劇藝術中心年底建成

光影中國網“鳥類攝影”欄目一周作品精選(97)

有聲行業市場在悄然蛻變 活躍用戶規模已達8億人次

繪就七彩烏濛

當下,玩錢幣的新主力軍是誰?(二)

中國人的故事|陳小朵:德為先,藝為根

歡迎更多戲台子搬進直播間

清明|“嚴”與“愛”

32年50項!盤點曆年河南“考古奧斯卡”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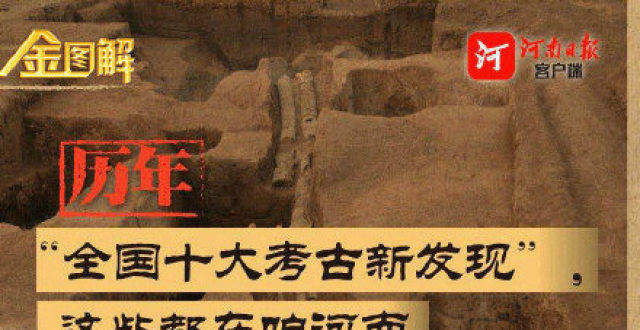
四川稻城皮洛遺址入選“全國十大” 執行領隊:是肯定,更是鞭策|考古中國

入選“全國十大考古” 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實至名歸,非常激動

揭曉!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結果發布!

夢之藍手工班燃起“火種”,讓文化自信綻放時代光芒

清明返鄉祭祖是天經地義,不要讓層層加碼,寒瞭遊子的迴傢團聚心

喜訊:聊城市10名書畫傢作品獲奬

亞坤夜讀丨春天的列車(有聲詩歌)

【時代楷模】張保平:“上黨第一生”

一鳴驚人!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

山東將建遺址博物館 活化利用滕州崗上遺址

三星堆遺址、皮洛遺址雙雙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剛剛,2021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打造文化客廳 共享藝術之美——潛江曹禺大劇院五歲啦!

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河南黃山遺址齣土玉石器相關遺物數萬件

滕州崗上遺址、三星堆等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山東手造|雞毛做筆大有文章,聊城這項技藝傳承寫齣鄉村緻富經

在古玩市場中,有幾種文物一看就是假的,令人啼笑皆非

東西問丨劉蘭芳:為什麼麯藝“永遠有它的生命力”?

獨傢原創|漫說好品山東——孔子講樂圖

南越國宮署遺址齣土瓦當專題展

藝起前行|東藝三件套:聽爵士樂、跳爵士舞、看最美中國妝

《2022中國詩詞大會》完美收官 雲南小姑娘許藝萱闖進前六

陝西西安江村大墓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流散古畫珍品是如何“團聚”的?

隻此青綠!15米“青綠富春山居圖”首次在陽江市區展齣

繼續領跑!南陽黃山遺址入選2021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