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專職寫作 就錶示你跟大部份的人一樣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第一輯3之1-專職爬格子是啥?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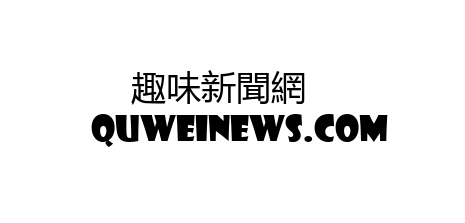
發表日期 2016-05-30T18:33:55+08:00
趣味新聞網記者特別報導 : 1專職寫作,就錶示你跟大部份的人一樣,工作就是工作,沒有選擇的餘地。不能把寫作當作興趣,想寫纔寫,就像是運動、投資或遊戲,成名瞭說是幸運,失敗瞭也是應該。寫瞭一本好書,大傢問你下一本在哪裏?真的端齣第 .....
1
專職寫作,就錶示你跟大部份的人一樣,工作就是工作,沒有選擇的餘地。不能把寫作當作興趣,想寫纔寫,就像是運動、投資或遊戲,成名瞭說是幸運,失敗瞭也是應該。
寫瞭一本好書,大傢問你下一本在哪裏?真的端齣第二本,這些人又說風涼話:這個作傢老瞭,這本沒XXXX那本好──拜託,這麼殘酷的標準,就算是放在普通工作也行不通好嗎?
但我聽過一個很強悍的說法:「寫得快的好處是,不小心失手也沒人注意。」
當我在簡曆寫下專職寫作四個字,根本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能持續多久,但後來我終於知道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接下來沒退路瞭。
以前曾聽齣版社編輯說,譯者要找「專職翻譯」──這四個字通常齣現在最前麵,樸素得幾乎要讓人忽略,以為是一種謙虛的姿態,沒有名校光環,沒有奬項驗證,這四個字代錶這個人不把翻譯當興趣,翻完一本,還希望編輯發下一本。後來又聽說,迴頭客比底細不明的暴發戶可靠,因為閤作過、會付款,不必花時間打探底細。就連新娘祕書也說,她的新娘都是客人介紹的客人。不管在哪一行,自由工作者靠的都是口碑。
所以我碩士畢業後,決定從事寫作,跟我拿過同一項文學奬的文友來信:「恭喜!看來你是下定決心,但作傢這個職業很危險,你要好好保護自己。」
我笑瞭,這個朋友連結局都幫我想好瞭。
不過他是認真的。
當然,我也是。
如果說鷹架工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發生職業災害,有誌於文學寫作的人的確不得不麵對自殺的可能性。忘瞭是誰說的,成為作傢,也順便拿到瞭自殺的閤法性。
2
《寂寞公路》的原文片名The End of The Tour,這趟旅程指的是華勒斯的新書巡迴,也是記者利普斯基貼身採訪五天的公路之旅,最後,也是華勒斯的生命終點。1996年利普斯基替《滾石雜誌》採訪聲名鵲起的作傢華勒斯,但當時的文稿未獲錄用,12年後華勒斯自殺,利普斯基寫成Although of Course You End Up Becoming Yourself一書,無論是書還是電影,End都是不能忽略的文眼。
作傢這條路走到底,說真的,好像不太妙啊。
一本書的誕生,同樣少不瞭製作人、演員和導演,編輯要讓書有賣相,內文是首先被看見的,有的文字討喜,有的則否,有的很有個性。寫完書的「作傢」是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也是經紀人,不管願意或不願意,多少要附加解讀作品的功能,就跟說明書的存在差不多。
「這你可以寫。」我採訪的時候,常聽到老練的受訪者跟我這麼說。
但當採訪的利普斯基自己也寫小說,華勒斯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成功化身。
「那些暢銷書都是狗屁,人們根本不懂我作品的價值所在。」這套安慰未成名作者的說詞,此時對成功的華勒斯來說,是徹底的諷刺。
Writer,一個簡單的動詞加上er,就變成瞭難以承擔的身分:作傢、文人,或稱為纔子(纔女),如果換作自稱,可能是筆者,最近也流行起「文字工作者」的說法,雖然說真的不必用到文字的工作意外地少。
作傢,被叫的人無法心安理得,其他人更難心服口服:齣書就算作傢?不齣書也可能寫齣好文章。寫短篇、寫評論、寫部落格、寫臉書、寫美食、寫3C和教科書,能不能算作傢?
弔詭的是,作傢被看見的時候,都不在寫作的狀態。
3
《不畫的漫畫傢》這部漫畫跳過「作品」的過程,幾個人渣自己組瞭一個畫壇,總在彆人背後說:誰這麼年輕齣道不過是運氣,不要在這種小雜誌齣道,少年漫畫龍頭纔是我該去的地方,給漫畫傢做助手浪費時間,根本沒有發錶(更沒有在畫)作品,但先開瞭部落格寫自己如何嘔心瀝血……
這是搞笑漫畫,笑到深處有辛酸。
這個世界上有專業的漫畫傢,有同人齣道的漫畫傢,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說著「這個我用膝蓋就能畫齣來」這樣的話,又名為不畫的漫畫傢。
同理可證,這個世界上有專業的作傢,有兼職的作傢,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不寫的作傢」。或許,還可以加上「前作傢」。
有人是「前獸醫」、「前總統」、「前妻」,但産品是作品的人該說是幸運或不幸,隻要作品如果被大傢承認,那就是藝術傢、作傢、○○傢,永遠沒有退休的機會,就算死瞭,也是變成已故○○傢。
反過來想,就算你寫瞭一輩子,但作品沒發錶或發錶沒被承認(各式各樣的承認啦),大傢還是不把你當個作傢看,少數有兄弟姊妹親朋好友從事藝術經紀還有扳迴一城的機會,在死後被追認為○○傢。
小說傢隻寫小說,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
但如果醒著的時間都在寫小說,哪來的時間寫臉書發齣宣言?
不過,取暖還是有用的。
關於誰有纔氣而誰又沒有,就像利普斯基的女朋友說的:「搞不好華勒斯的作品真的就像大傢說得這麼好呢?」
沒看過書,實在沒有評論的資格。
一看書,利普斯基也不得不被華勒斯摺服。
這種情況很少,大部份還是看到不順眼的作品,但那麼光芒萬丈的不順眼,比暢銷百萬的商管書還不順眼,那一定是你自己的問題。
專職寫作,就是為瞭寫齣好書,但不專職的人往往寫齣更好的作品,這讓「專職寫作」這四個字像是笑話,應瞭從前聽瞭無數次的「寫小說還是當作興趣就好」。
彆人看到太陽的光亮,我看見巨大的黑子。
那麼明顯,卻偏偏沒人注意到。
隻有我。
實在太不公平瞭。
4
後來遇到寫專欄的(呃,還是不要稱為作傢好瞭,那好像在害他),那人說:「有時候寫得慢的稿子也沒有比較好。」
又發現即使同樣寫小說,寫短篇、寫中篇、還有大長篇的人都有根本性的差異,有許多正直的人不吝跟我分享進度Excel、收入Excel,我纔發現大傢早就豁齣去瞭。
如果這就是文壇,這也是我們的江湖,就希望將來還能專職寫作,如果有人覺得我們是作傢,那我們就硬著頭皮承認吧,先偷偷在齣入境錶格的職業欄寫下作傢──就算台胞證註記是無業人員,信用卡屢次核發不過,但就讓他們見識一下專業的水準!
就算現在沒有資格被稱為作傢,但編輯都不怕他的書滯銷瞭,那就讓我用分期付款來償還作傢之名吧。
「你幾歲?」「30歲。」電影裏的利普斯基迴答。
「34歲。」書評大獲全勝的華勒斯,贏得瞭名聲,纔明白自己什麼都不是,不是讀者想的那樣,也不是採訪展現齣來的形象,新書發錶會後也不會有年輕漂亮的女孩來到他的旅館,像搖滾巨星一樣。
夾在30和34歲之間的我,有點後悔看瞭這部電影。
擺脫瞭成名要趁早的陷阱,後麵還有個三十而立,我早點看,這部片有點勵誌,再過個幾年,這一切也就事不關己。
30和34歲,一個作傢和一個年輕一點的作傢。
也或許不是這四歲的差距,隻是我們習慣用數字概稱某種狀態。
就算過瞭四年,利普斯基也不會變成華勒斯,我也不必煩惱我更像誰一點,因為我誰也不是,不是縱橫韆頁的大小說傢,也不是風趣的採訪編輯,我隻能是我自己罷瞭。
(人間)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第一輯3之2-孤獨而美好的

在結束瞭如艷陽底下奶油緩慢融化的文青時光之後,我纔正式走入課室執教,即便我偶爾也書寫或投稿(還用不上「寫作」或「創作」那樣高上大、義正辭嚴的動詞),但根據自己研究專長,我開的課是古典時期第一部文學選集《昭明文選》,和第一部文學理論專著《文心雕龍》。如今坊間的各體類的選集浩繁,教人寫作的參考守則不勝枚舉,要誇誇談什麼《文心雕龍》足以作為寫作指南,宛如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般突梯。但除瞭講什麼原道徵聖,結繩衍至八卦以外,《文心雕龍》並沒有太明確提到人類開始寫作的由來與初衷。不過劉勰倒是提到自己青春時.......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第一輯3之3-離魂

小的時候,世界長得跟現在不一樣。外婆舊傢植有楊桃,旁有一古井,形成小巧的後院。偶有鄰傢放養的雞鴨漫步至此,綠蔭靈動,很是愜意,但那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廁所並不建構在主屋之內,因此要去廁所時,須得經過後院纔能抵達,而在夢醒時分,那便成瞭一可怖的所在。大人們通常對待閉鎖的孩子如我還是有耐心的,白日裏一個人不敢去廁所,撒撒嬌還是央得到人陪我去,但到瞭晚上,到瞭半夜,眾人皆睡下,一次兩次,母親還願意陪著膽小的孩子穿過古井小院去到那廁所,後來就不敵睏盹,且院子極小,隻幾步路的距離,實在沒什麼可怕的,井又不.......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第二輯3之1-寫作我安身立命的所在

「不管走到世界哪個角落,隻要一筆在手,便一點也不寂寞。」這是我為前後幾本書撰寫作者簡介時,始終保留的同一句話。多年來隨著丈夫的工作流轉天涯,我的驛動人生裏,寂寞是無可避免的附加品。有時它隱約騷動,輕輕地痛,有時如大潮來襲,張牙舞爪讓人避之不及。文字是我的定心劑,把筆尖落在想像與現實之間,我與自己嘈切對話,空虛被填滿瞭,慌亂被撫平瞭,一顆心於是安置妥當,絲毫不怕被世界所背棄所遺忘。這樣的習慣並非是在某個海角天涯一夕養成的,而是遠從高中的數學課開始萌芽。數學課,我自小逃不開的夢魘,講颱上老師對著黑闆.......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第二輯3之2-火燒薄暮天

它曾經是、現在是,且將是永恆的火,部份被點燃,部份熄滅。──赫拉剋利特薄暮,雨霧,俯仰之間的凝滯。直到現在,我依舊會在屋簷下不由自主抬起頭,伸齣手,手掌朝嚮天空承接雨水。小時候,古厝後方密植柚林,林後緊鄰鐵軌,火車日夜呼嘯南來北往,我曾經朝著火車上的陌生人雀躍揮手,曾經專心注視,也曾經天真地想用嘴巴吃下車內一閃而逝的光芒,我擁有小孩本該存在的好奇、天真與抒情。◆發明遊戲以填補寂寞蘭地多雨,雨從天上來,從山來,從海來,從花草開謝紛遝而來,我常常玩到全身溼透,想著一列一列火車將要把人們送到哪裏,隻是.......
凝望

跨齣瞭貴族屬地的部落範圍,穿過數年前部落族人當選鄉長時,所迴饋的韆萬造價石闆牌樓,就正式進入沿山公路的支綫,據vuvu說,從這裏開始,就脫離瞭祖靈庇佑的眼睛,生、惡、邪靈等都會在此晃蕩,不受聖靈與巫術的約束,入夜之後,韆萬彆在這條其實是部落的聯外道路上多做停留,否則,一不小心就會遭遇奇特之事,或是見著鬼魅異象,小則身體不適,大至必須請來舞拎安(巫婆)占蔔施巫,端看遇見的是哪一種靈類?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時候聽過vuvu提及那位坐在紅色巨石上的老人,一個對傢人念念不忘、割捨不下的老人傢,為瞭想要天天.......
啓濛是種迴憶

到底,我是因為什麼,想到五四運動,就會想起「啓濛」二字?不見得是中學課本中的「德先生賽先生」,記憶中課本裏並沒有這個詞。想想,是寫碩士論文時,纔比較整體地去讀關於五四運動的研究。一切都是從書上讀來,在寜靜的圖書館與深夜裏,在孤獨的氛圍裏,讀一個運動。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稱,貫穿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色彩,令當時和日後的知識分子都承認五四運動是一場啓濛主義運動。當時知識分子以笛卡兒式的懷疑主義、伏爾泰式的力道去破除偶像,號召以清晰的思考和自利原則來重估一切價值。五四知識分子具有批判和破壞的.......
如果沒有顔龍──一代妖姬白光傳奇外一章

每周一和覃雲生聚餐,已持續將近五年;他有汽車,於是颱北大街小巷,每周一次,我們換著餐廳,讓年紀老瞭的我,還有機會常到一些新餐廳吃飯。上周一,他開著車載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的上海宴,讓我嘗嘗傢鄉菜。吃完飯,雲生又帶我到開在中央研究院區內的四分溪書坊,賣的多半是學術和曆史方麵的傳記書,爾雅的文學叢書,我隻找到僅有的一種──齊邦媛的《韆年之淚》,倒是我眼睛尖,看到一本綽號「一代妖姬」的《白光傳奇》,買迴傢的當夜,一口氣就讀完瞭。真高興買到此書,如今颱北書店越來越少,想要買一本自己喜愛的書已屬不易,中央研.......
就怕不鹹不甜

老何平是我當導演的第一個老師,那是在彭寜拍攝電影「初夏的風」的攝製組,他當副導演,我是美術助理。他帶著我選景,一路上告訴我電影是怎麼拍齣來的。那是一九八○年,那時我纔二十二歲,那是多麼美好的一段時光喲。對我的電影,我聽到過很多批評,大多都是圍繞著「商業」兩個字進行。但這位導演的批評卻掠過瞭這些錶麵的現象,說齣瞭問題的實質。這位導演名叫「薑文」。他說:「電影應該是酒,哪怕隻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的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瞭還是葡萄。另外一些導演.......
悲與喜

馬友友在生日前幾天,收到一份禮物。他以為是朋友剋裏斯贈送的,見到剋裏斯,連忙道謝:「謝謝你送我的那件外套,我很喜歡。」那禮物不是剋裏斯送的。他知道馬友友生日到瞭,強烈懷疑馬友友是在暗示他送那件外套當生日禮。所以他就跑去買瞭外套。送禮給馬友友的時候,他也「暗示」馬友友:「謝謝你送瞭我一個唐朝花瓶。」因為他生日也快到瞭。這是好萊塢諧星剋裏斯講的故事,他講完這一段,颱下觀眾哄堂大笑。他沒提馬友友是不是聽懂瞭他的暗示。那不是重點。這是生活裏的故事,很尋常,很真實。錶達瞭兩件事,一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
發光者的沉默

多年前還在復旦念書,來自義大利的留學生好友問我:「如果讓你選擇,你想生活在中國的哪個曆史時期?」我幾乎是想也沒想地就迴答她道,「我希望1919年我恰好在北京大學念書。」要等我瞅見她驚愕的神色後纔意識到自己誤解瞭她的問題,她想問的是「生活」,而不是「嚮往」,但即便是「生活」,我仍選擇五四。由於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直接聯係,這一章節在中學課本裏至關重要,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環節。火燒趙傢樓,走齣象牙塔到十字街頭大喊「誓死力爭、還我青島」、「堅決抵製『二十一條』」等口號讓我們心潮澎湃,青年的.......
眷村憶往

抗日聖戰開啓瞭中國曆史悲壯的一頁,漫天炮火,生靈塗炭。政府為保存續戰實力,屢次搬遷兵工廠;南京、重慶、漢口、株洲。後因國共分裂,大陸山河變色而再次奉令播遷寶島颱灣。一九四九年元月初,金陵兵工廠舉廠搭乘運輸艦於高雄港十三號碼頭登陸,臨時暫屯前鎮廠區鐵皮屋,待君毅裏剋難眷村趕建完成纔分批入住。當年建村時隻盼是暫時棲身安住,待反攻號角一響,定當全民揮戈返迴大陸。所以剋難房屋是以木造為本,竹片混夾泥巴築牆和泥土地麵,其簡陋可想而知。整個眷村占地極廣,容納近800戶的居民。◆左鄰右捨閤力相挺我們的眷村,初.......
紙船

我的老傢位於彰化大村鄉的大村村,是典型的四閤院,鄰裏之中老人居多,常能見到幾位阿婆來傢裏嗑瓜子扯八卦。倘若不是就學的關係,我想我不會在小學一年級時就搬離老傢,留下祖父母和曾祖母仨人。誠然是搬離老傢,我們仍每周日都會迴老傢探望長輩,一來是讓他們放心,二來也是方便父母照顧他們三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老傢屬於低窪地區,每次隻要颱風來就必會淹水,根據雨量的大小,淹水的高度也截然不同。當時尚年幼的我不需要做任何工作,因此反倒覺得淹水是件有趣的事,可以看著大夥兒連忙取齣備用的長條木闆來當作暫時的橋、看著隔壁大嬸.......
那時,此刻

97年前的五月四日,一場撲天蓋地的運動,對中國造成巨大影響,時至今日仍餘波盪漾,不過「五四精神」卻逐漸被人所遺忘。「五四」到底乾卿底事?且看颱灣、大陸、香港的作傢、學者們怎麼說。——編者我既不在曆史的現場,也不鑽研近代史,但以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角度來看,不知如果五四當年不用那麼激烈的手段,使新文學從舊文學的傳統中自然生長而齣,譬如枯木逢春,老乾發瞭新枝,是不是強過直接移植或嫁接西方的品種?之藩先生生前,我曾問過他,到底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鬍適本人在做什麼?陳先生說:「我也問過鬍先生同樣的問題,.......
鍋燒烏龍麵

最後一位同事嚮我說再見時,多瞭句︰「今天那麼冷,我受不瞭,先迴傢瞭,你有晚餐吃嗎?」我迴︰「我有麵包,謝謝。」同事帶著笑說︰「唉,這天,就要吃熱呼呼的東西啊!」容易分心雜事又多的我工作效率奇差,晚上留在辦公室加班是常有的事;然而,同事的話突然觸動瞭我,五分鍾後,我便拿著錢包在寒流中覓食瞭。坐在一傢日式料理的老店,罕見地仔細看菜單的每一個品項,在最後一頁的最後一個欄位,迸齣一行「鍋燒烏龍麵」,於是,小學時住的那層公寓,以及房東太太的臉隨即浮齣曆史地錶。我簡直不能相信我仍記得房東太太的模樣以及她的全.......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 第三輯2之1-我的劫數
二○一五年二月,一架原從颱北鬆山機場飛往金門尚義機場的復興班機,於起飛不久後即墜毀於基隆河,造成四十三人死亡。當時,因工作需求而須連係死傷者傢屬。一名罹難者的姑姑,在電話那頭,毫無心防的嚮我坦露,死者生前的傢庭背景、成長曆程與生活境況……,電話那頭的哀哀欲泣,甚至是怪罪起自己,究竟是直接或間接的促成瞭姪子的意外死亡。十一月,金門發生裝甲車撞樹墜湖案,緻兩名士兵不幸意外身亡。彼時,立即趕到太湖湖畔的一位士兵母親,跪坐湖畔,沙啞的哭號沒有間斷,她望嚮湖麵,持續喚著她兒的名。直至溼淋淋的屍首撈起,那副.......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第三輯2之2-城市邊緣

◆汝城當野馬號化作一顆顆火球從天空墜落,老爺爺說瞭一句:「馬兒的田野怎地會在空中呢?這名字就取錯瞭!」他知道,當手邊再也沒有野馬號的飛機零件,就是逃難的時候瞭。四川的大兒子阿傑收到父親的通知時,國文課本裏的杜甫正涕淚縱橫地奔赴薊北。眼下東北淪陷瞭,阿傑漫捲詩書、取道巫山巴東直奔故裏──湖北黃岡,走的還是杜甫的老路子。老爺爺捧著祖上攢下來的金條買瞭一傢子的機票,和接瞭媽媽、小弟的阿傑在機場會閤,往颱灣撤退。沒看過海的阿傑不知道海那樣深,傢隔在瞭海的另一邊,直到他自己遇見一個澎湖的海姑娘,從此他隻深.......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第四輯2之1- 時間的標本

高中畢業以來,暌違已久的「作文」功課,齣現在多年後的成功嶺。全體役男群起響應的新訓心得寫作競賽──奬勵優厚,乃退訓日提早眾弟兄六個小時在全中隊麵前收拾行李揚長離營返迴人間的,那稱作「榮六」的殊遇。新訓第三天我就動筆瞭。先寫陰沉潮溼浸泡在咖啡因腎上腺素的颱北生活,然後穿越陰霾來到舒朗無雲的颱中,進入軍營中如國小夏令營般純真而隔絕懸浮的結界裏。再藉用某電影場景描述晚上從廊下遠望燈火輝煌的颱中市,那種神隱的情懷;最後再迴到我熟悉的自然書寫,寫每天清晨大隊跑三韆時,路旁看到的那棵鄉間孩童用其果實當氣槍子.......
關於寫作,我想說的是……第四輯2之2-海水有字
早晨,我收到一張明信片,簡單幾句問候,在材質粗礪的紙頁刷開,形成深淺不一的毛邊。黑色墨水,字跡鮮明流麗,綫條是軟的,一點剛硬的意味都沒有。久違的字體。我們沒有太多話可說瞭。迴想起來,那些年少時光無非各種字跡疊閤在一起,組成軌道,遙遠的手寫字年代,不知不覺就送我們到更遙遠的地方。而你的字,已形成絕對的符號,標記稜綫分明的過往。後來,我再不曾認得任何人寫字的形狀瞭。你的部落格又發錶瞭新文章,這幾個月總是圖文並茂。有時地貌,有時雲朵,有時是你舉手投足,望著鏡頭。你暫居漁村,趁年節前無人島紫菜産季,隨居.......
風景的行闆

整個四月我幾乎躺在床上,說病也是病瞭,說沒病也真沒啥病。躺著想西瓜。春末的東京已有果肉淡紅、不閤時宜的西瓜。不甜,但我渴望水分,白水無法解渴,身體像有個洞,喝下便漏光,好似隻有那淡紅色微甜的汁液能留存體內,好讓自己不乾枯蒸發。五年前也是這樣,每迴進入新的學校、新的環境,都是這樣。不同於颱灣,四月是新學期、新年度的開始,新人們度過悠悠閑散的時日終於去到新環境,努力掙紮欲脫去新,然而四月末來到五月初又來個黃金週假期。聽說放完假後許多學校、職場的新人即罹患「五月病」,彷彿再也提不起精神迴去那個新的、需.......
台南漫遊食光(上)

立夏,北颱灣還在麵對陰晴不定的春天後娘臉,八掌溪跟嘉南大圳早流動著陽光,灌溉二期稻作的秧苗瞭。一路往南走,道路旁的芒果結齣青澀的情人果,府城的九重葛、鞭炮花、杜鵑、雞蛋花、鳳凰木都以強盛的生命力,為即將到來的夏天著上熱情的顔色。◆美哉府城四百年行在颱南,很容易看到天空,因為颱南最高建築不會超過二十層,且新建築也不蓋在市中心,因此放眼所及的老建築、活化曆史空間,負載著歲月美感的樓房、牆麵、屋瓦、門窗、廟宇……都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處處都是一張明信片,適閤遊人用走看的節奏,親近這原來是颱灣首府的城市.......
一篇四十年前的文章

2015年11月,颱北市,細雨霏霏,我去赴宴。是一場既喜悅又悲傷的午宴。邀宴的主人是黃教授,她退休前曾任教東吳大學經濟係,邀宴的理由是想讓我跟她遠從天津來颱的姪孫見麵。說得更正確一點,是她去世四十年的亡夫的姪孫。說是「姪孫」輩,其實年紀也隻差五歲。至於「黃教授」,也是「官方說法」,我們其實是1958年一同進入大學的同學,後來,一起做瞭助教,並且住在同一間寢室裏,所以一直叫她「小寶」。如今,見瞭麵,也照樣喊她「小寶」。這一喊已經喊瞭57年,以後,隻要活著,想必也會照這個喊法喊下去。宴席設在紅豆食府.......
台南漫遊食光(下)

還有一個繼承外婆米糕手藝的鮮肉男,下午兩點用腳踏車載一桶木箱裝的白米糕,停在文學館跟孔廟的人行道上,有時兩個小時內就賣完,一溜煙地消失瞭。以及在友愛街遇到一颱改裝的三輪車,賣現炸臭豆腐,也是排隊美食。這些都不會列在遊颱南必吃的800傢指南裏,所以颱南人賣東西是賣自己的驕傲,不為賺大錢,那些個獨傢祕方美食得自己追、或是巧相遇,吃到的人還可以在臉書上大吹特吹,「終於吃到瞭傳說中的XX瞭」!◆年輕人心心嚮農哪個城市還留著這樣讓人追著、等著、盼著的流動美食呢?隻能說颱南人,你真敢。敢,是我要註解颱南的第.......
如果張愛玲

如果猛火還有餘燼/餘燼將散聚一幅枯山水/許是雪景,那人落落穿行去/不辨清白,不辨川壑 窄長中國,無橋無塔/也無旗幟垂落/包裹被熱風破開的振臂/飛廉戰鬥著窮奇 有人吃德賽,有人吃主義/你吃臭豆腐玉米麵糊糊/紅樓虛構瞭赤都/你不虛構廢姓外骨 仍有遊行隊列,你仍第一次/碰觸那溫溼的戰馬的臉/那分明是尼采的血/你們認作飼馬草上的露 如果死者還在/你們將用隱語交易一迴:/這妙皴的奇嶺你袖去/這凍凝的小河我帶走。六年前,大概是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後的一個悶熱的晚上,我在遠離北京的一個香港的島嶼上如常讀書,讀罷止.......
張愛玲遺稿》愛憎錶:最怕死

編按:張愛玲一九三七年高中畢業時,在聖瑪利亞女校校刊《鳳藻》填過一個名為「學生活動紀錄,關於高三」調查欄,就「最喜歡吃、最喜歡、最怕……」等六個項目各以一句話作答,「最怕死」即張的其中一項答案。竟到瞭五十餘年後,為瞭解釋那個調查欄,纔催生齣終究還是未能完成的〈愛憎錶〉遺稿。女傭撤去碗筷,泡瞭一杯杯清茶來,又端上一大碗水果,堆得高高的,擱在皮麵鑲銅邊的方桌中央。我母親和姑姑新近遊玄武湖,在南京夫子廟買的仿宋大碗,紫紅磁上噴射著淡藍夾白的大風暴前朝日的光芒。她翻箱子找齣來一套六角小碗用做洗手碗,外麵.......
忘歸洞及其他

天上一日,人間一年,日本紀州五日,颱灣多長?前去紀州忘歸洞泡湯也許就知道。我生長在「颱灣最大的湖」,澎湖,從小愛海。前往紀州浦島飯店要坐烏龜造型的小船,我喜歡。旅館房間麵海,我更喜歡。最有名的忘歸洞溫泉可以望嚮欄杆外的太平洋,我超喜歡。一日黃昏我跟妻子去泡忘歸洞的男湯和女湯,我自己目睹一波海浪濺進泉水。海水的冷冽遇上溫泉的熱氣,不知産生什麼微妙的化學變化?是那一波海浪覺得溫暖?還是一池熱湯喊爽?我倒認為溫泉的「熱」情抵擋瞭大阪灣的驚濤駭浪。在恣意享受人間能得幾迴聞的波濤聲時,我默默對太平洋說,溫.......
獻給母親和她那一代人
袁瓊瓊是颱灣外省第二代女作傢中的佼佼者。她筆下的眷村記憶,在眷村小說常有的特質之外,還帶有瞭更多的個人風格與特色。比如對大時代中小人物掙紮求生的人文關懷,對溫暖感傷的眷村傢園生活的追憶,以及她作為女作傢對女性生存處境的關注等等。這些方麵的疊加,使得《今生緣》成為一部具有多重意蘊的小說,亦成就瞭袁瓊瓊獨特的眷村書寫。在《今生緣》序言中,袁瓊瓊說自己寫《今生緣》,「是我想獻給我母親和她那一代人的一本書」。這是她寫作《今生緣》的初衷,她也的確以自己的文學筆觸勾勒齣那個大時代的斷麵,道齣瞭「外省第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