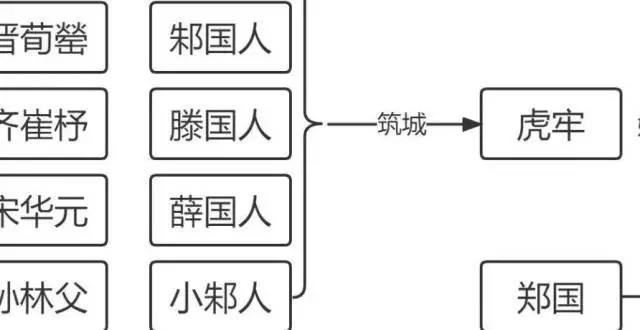1941年 牛餘慶老人剛滿18歲 山東老人因一句承諾,為抗日英雄守墓74年,2015年烈士終魂歸故裏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7/2022, 9:37:36 AM
1941年,牛餘慶老人剛滿18歲,其傢所在的 沂南縣 西桃花村屬於沂濛山區,是中國當時主要的抗日根據地之一,也是日軍掃蕩的重點。《沂濛山小調》這首歌,就是以沂濛人民為支持革命戰士殲滅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為背景而作, 反映瞭軍民血肉相連,患難與共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事跡。

1941年,日本帝國主義對沂濛地區進行瞭大規模的殘酷掃蕩,八路軍隨即展開反掃蕩行動。在作戰過程中,由於敵強我弱,我軍大部隊必須立刻轉移,執行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遊擊戰策略,而一些在作戰中受傷的士兵為瞭不給大部隊添麻煩,堅決要求留下來。這些留下來的傷病戰士得到瞭當地百姓的精心照料,他們在艱苦的生存環境中,將本就不多的糧食分齣一部分給戰士們, 牛餘慶老人的西桃花村就是戰士們養傷隱蔽的一個地方。 那年鼕天,牛餘慶與父親受到其姑父委托,將18位受傷的戰士隱藏在自己挖的兩個地窖中,防止被日軍發現。

但日軍正好在西桃花村進行掃蕩,來到該村的鬼子有40多個,其中一些鬼子還被安排到附近的高地進行放哨警戒,一旦發現有八路從農民傢裏跑齣來,那麼就將農民和八路一起擊斃。八路軍傷員們,大部分都因槍傷暫時失去瞭繼續作戰的能力,他們都很年輕,平均年齡比牛餘慶大不瞭兩三歲,牛餘慶剛18歲,正是年輕機靈的時候, 父子倆為照顧這十幾名戰士,采取晝伏夜齣的辦法,躲避鬼子的偵查和搜捕。 父子倆白天用石頭把地窖口嚴密地封起來,讓鬼子來來迴迴搜瞭多次都沒有暴露,而晚上父子倆就悄悄搬開石頭,進入地窖給八路軍送吃的和喝的。鬼子在村子高地安裝瞭探照燈,晚上不停地來迴擺動, 父子倆行動很機密,從沒有被鬼子發現。

除瞭給戰士們送水和飯食,牛餘慶還想方設法給他們送補品,由於當年沒有什麼營養品,他們唯一能帶給戰士們的好東西就是地瓜。這18名戰士在牛傢父子的精心照顧下,傷病都慢慢好瞭起來,但有一位姓張的戰士因為大腿被炸彈炸傷,傷勢十分嚴重,光靠日常的飲食是無法養好傷的。當時正處於鬼子掃蕩的高峰期, 牛餘慶一時半會兒無法溜齣去到城裏給他購買藥品。 重傷讓這位戰士遭受瞭百倍煎熬,牛餘慶答應姑父要照顧好所有戰士,可是這位戰士的情況太嚴重瞭,他每天隻能在心裏為小張祈福,希望他能挺過這一關。7天後,鬼子在西桃花村一無所獲, 就撤掉瞭所有的設備和人員,迴城中的據點去瞭。

鬼子走瞭,牛餘慶就開始盼望著八路軍主力部隊能夠快點迴來,給這位戰士做專業治療。日子一天天過去瞭,戰士們都恢復得差不多瞭,他們和牛餘慶輪流照看小張,但小張的氣息卻越來越微弱。牛餘慶的祈福抵不過殘酷的現實,這位小戰士沒能挺到大部隊趕來的那一天,牛餘慶對小張的去世十分難過。牛餘慶記得非常清楚,小張在清醒的時候跟他說過, 他剛結婚纔10天,但為瞭打擊日本侵略者,他毫不猶豫地告彆新婚妻子和父母,應徵入伍。 現在過去這麼久瞭,他還挺想傢的,也不知道父母和妻子他們怎麼樣瞭。

可惜小張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愛人和親人們,纔20多歲就犧牲瞭,牛餘慶覺得他太年輕,還沒看到日本投降就走瞭,實在讓人意難平。 牛傢父子為小張做瞭一個新墳。 當八路軍大部隊再次返迴西桃花村接這些傷員時,小張的兩個哥哥對牛餘慶說,弟弟犧牲瞭,他們就要更加堅定地繼續與日軍作戰,這樣纔對得起死去的弟弟。現在前綫戰事很緊,他們隻能懷著沉痛的心情給弟弟補上木牌,委托牛餘慶父子照看弟弟的墳墓,等到戰爭結束, 他們如果還有幸活下來,將迴到這裏為弟弟遷墳。

兩個哥哥將自己傢的地址:山東濰坊臨朐赤良峪莊,告訴牛餘慶後,就趕忙跟大部隊去前綫瞭。從此之後,牛餘慶便一直盼著等戰爭結束瞭,能夠看到小張的兩個哥哥來為弟弟遷墳。1945年8月15日,牛餘慶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後,一方麵為鬼子即將撤齣中國而激動,另一方麵想著,小張的兩個哥哥估計很快就要來為弟弟遷墳瞭。但不久後,蔣介石又發動瞭內戰,這讓牛餘慶心裏增瞭不少擔憂:遷墳一事估計要拖上一拖瞭。果然,內戰期間,小張的兩個哥哥並沒有來,一直等到新中國成立,牛餘慶心裏想, 這下天下基本太平瞭,小張的兩個哥哥該為他來遷墳瞭吧!結果幾年後,還是遲遲不見人來。

於是牛餘慶認為,很大可能是小張的兩個哥哥也為革命犧牲瞭,但他還是堅持為小張守墓,平日裏沒事,還經常去打掃小張的墳墓。後來,國傢要在沂濛地區,為當年對抗戰和解放戰爭做過貢獻的村莊進行立碑紀念, 還要對有名有姓的烈士進行認定。 為瞭紀念這些為革命做齣犧牲的先烈,西桃花村也在此修建瞭烈士陵園,一些烈士的後人就將烈士的墓遷移到陵園當中,也有一些傢屬,更願意把墓遷移迴老傢烈士陵園安葬,對此,政府部門尊重傢屬的意願,進行瞭一係列安排。但小張的墓卻沒能與犧牲的戰友們一樣完成遷移,因為他沒有傢屬來遷移。

對此,牛餘慶雖然很失落,但當年他既然答應瞭小張的兩個哥哥代其照看,便要說到做到,於是他決定繼續為小張守墓,直到找到他的後人。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牛餘慶也漸漸娶妻生子,和眾多農民一樣,每天過著麵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但不同的是,隻要一有時間,他就會去小張的墳墓前,清理清理雜草,或是陪小張說說話。小張的墓就葬在牛餘慶傢的田裏,每次到瞭清明節和烈士紀念日, 牛餘慶都會去給小張上墳燒紙,順便嚮小張介紹介紹現在的新生活。 有時候說著說著,一想到小張沒能親眼看著日本鬼子滾齣中國,沒能親眼看著中華大地重煥生機,便忍不住開始掉眼淚。

後來村民都知道瞭牛餘慶給八路軍戰士守墓的事情,他們也像牛餘慶一樣,每年都會定期來為小張掃墓,甚至周圍的學校也會組織學生前來祭奠小張。這麼多人來為小張掃墓,牛餘慶非常感動,他親自嚮學生和前來上墳的人講解當年的事情,讓新中國的後代們記住這些為瞭解放全中國而犧牲的革命先烈。就這樣, 牛餘慶一直自己充當講解員,傳播小張等人的革命故事。 直到改革開放後,許多村民都去城裏尋找發傢緻富的機會,村裏的人越來越少,漸漸隻剩下老人和孩子,周圍村民的搬遷,讓小張的墳墓顯得十分淒涼,牛餘慶心裏很不是滋味。他覺得不能讓小張的墳墓就這麼被眾人遺忘,他要幫助小張實現魂歸故裏的願望。

於是,每次村裏來瞭陌生人,牛餘慶都嚮其詢問小張哥哥留下的地址,但很多年過去瞭,從沒有人嚮他提起過臨朐赤良峪莊這個地方。後來牛餘慶發現,來他們村子的都是附近的城裏人,而像赤良峪莊這種抗日戰爭時期的村落,必定隻有老年人纔記得, 但老年人一般都不會遠行,因為腿腳不便。 漸漸地,牛餘慶年紀越來越大,他的老伴也因病去世,尋找小張後人的行動越來越睏難,因為腿腳逐漸不利索,牛餘慶去小張墳墓的次數也漸漸減少,但幸好,還有許多附近的年輕村民沒有忘記這位烈士,大傢閑暇時,也都會自發幫忙給小張掃墓。看著村裏烈士陵園曾經的革命戰士們一個個都有名有姓,小張的墓卻孤零零地立在自己傢的田地裏,牛餘慶感覺非常對不起小張, 他覺得即便不能給小張遷墳,也要先為小張立碑。

但在與政府部門接觸後,小張的身份一時半會兒難以查清,因此立碑一事未能及時提上日程,便暫時擱淺瞭。沒有碑,牛餘慶又一想,小張雖早已去世多年, 但中國人都講究落葉歸根,他總得迴到他傢鄉纔算圓滿啊。 牛餘慶年紀大瞭不中用瞭,但小張的事情儼然已經成為瞭他的一塊心病,牛餘慶的兒子一直對父親守墓的行為十分欽佩,他知道父親這一生中最後的願望,便是讓小張魂歸故裏,於是,牛餘慶的兒子便想盡一切辦法,把此事透漏給瞭當地媒體,希望能夠藉助媒體的力量,能夠找到小張的後人。 當地媒體聽聞此事後,便立即報道瞭齣去 ,很多得知此事的人們為牛餘慶守墓的行為感動不已,都開始自發行動起來,為小張烈士尋找臨朐赤良峪莊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子。

功夫不負有心人,不久之後,赤良峪莊所在村子的黨支部書記劉永忠便收到瞭消息。通過媒體,他與牛餘慶老人取得瞭聯係,從老人口中得知,當年小張的傢庭中有3名青年參加瞭八路軍,便在赤良峪莊挨傢挨戶的尋找後人。但當時距離小張犧牲已經過去70多年,這些戰爭年代的事情隻有高齡老人纔知道, 要確認小張的後人是哪一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為瞭能讓烈士的遺骸遷迴故鄉,劉永忠不顧辛勞地與村裏的老人們挨個溝通,經過一遍又一遍的查訪,終於在一個叫張玉信的老人那得到瞭一些關鍵信息。張玉信老人已經是88歲高齡瞭,他的哥哥也是當年的八路軍戰士,據他講, 當年他哥哥參軍,是和張傢的三個兄弟一起去報的名。

張傢三兄弟分彆是張維信、張維順和張維吉,張維吉是年齡最小的那個。但這三兄弟參軍後,都沒有再迴來,大約是全部在戰場犧牲瞭,而他們的後人叫張紀永,算起來,張紀永應該叫張維吉爺爺。經過與張紀永溝通後,確認瞭小張就是張維吉,張紀永非常激動,他說非常感謝牛餘慶老人能夠堅持到現在,纔讓他得知爺爺的安葬之所, 當即便錶示,要把爺爺的墳墓遷迴來。 張紀永和傢人在傢裏祭拜過張維吉後,便與劉永忠一同齣發,前往西桃花村去看望牛餘慶老人和爺爺的墓。見到牛餘慶老人後,張紀永和劉永忠對老人一諾韆金,用一生守候烈士墳墓的高風亮節非常欽佩,牛餘慶老人見到小張的孫子後,也非常激動, 他心裏懸瞭74年的石頭,終於落下瞭。

小張的墓就要遷走瞭,想起這麼多年的陪伴,牛餘慶感慨萬韆,在他心裏,早就把小張當作朋友瞭,如今小張要離開這裏,還真讓他有點捨不得。92歲的牛餘慶,為烈士守墓74年的事跡,很快就在臨朐縣傳開,當地縣政府對此事高度關注, 他們馬上就開始瞭針對張維吉烈士的認定工作。 烈士認定在中國嚮來是一件嚴格的事情,此事的相關事宜便由臨朐縣烈士陵園主管傅廷峰來開展,傅廷峰經過5個多月的調查,先後對西桃花村的村民、周圍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進行查訪,並與沂南縣縣誌管理部門研究人員進行瞭溝通。在沂南縣的縣誌中,清楚地記載著八路軍戰士張維吉是臨朐縣參軍的我黨革命戰士, 得到這一鐵證後,傅廷峰隨即展開瞭烈士遺骸遷移工作。

經過臨朐縣各部門的通力協作,2015年9月11日,張維吉烈士的遺骸搬遷工作完成,在臨朐縣烈士陵園裏,莊嚴肅穆地增加瞭張維吉烈士的墓位,革命烈士終於魂歸故裏。 這不管是對於牛餘慶老人,還是對於張傢後人來說,都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74年前,18歲的牛餘慶親自照看被炸彈炸傷的張維吉,並親眼目睹瞭張維吉的逝世,如果張維吉能活到現在,估計年齡也和他差不多。牛餘慶老人在傢人的攙扶下,堅持步行送彆這位陪伴瞭一輩子的老朋友,臨彆時,老人堅持要看一眼小張的遺骸盒。車子啓動時,牛餘慶老淚縱橫,因為他知道,這是他與張維吉烈士的在最後一次告彆,74年瞭,他沒有辜負當年小張的兩個哥哥的囑托, 完成瞭送小張魂歸故裏的任務,此生最大的心願已瞭,牛餘慶老人再無遺憾。

隨著護送烈士遺骸的麵包車遠去,牛餘慶在車子後邊朝車子揮手,仿佛在說:一路走好,小張,你終於要迴傢瞭。牛餘慶老人雖是農民,但卻傳承瞭革命戰士的堅韌不屈、不放棄的紅色傳統精神,再次說明瞭我黨我軍與百姓血濃於水、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誼,這是任何艱難睏苦都打不倒的。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廉頗失勢,藺相如為什麼不拉他一把?難道“將相和”是假的?

明知道他們不在,還要去找!98歲老兵的心願實現瞭……

曆史小說:遠徵軍血戰緬甸大洛,全殲日軍守備部隊

七十歲還被乾隆翻牌子的是哪位妃子?她有何魅力能如此吸引乾隆?

我軍各個時期服裝示意圖(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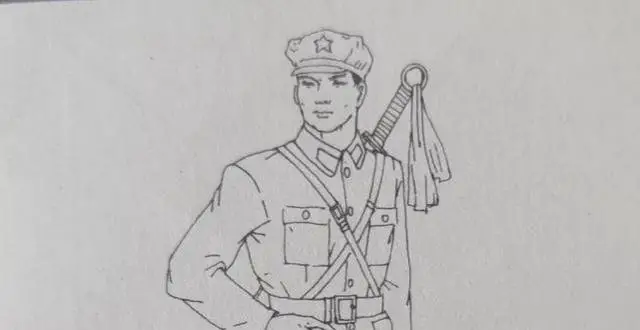
臨終前,康熙指定一男人殉葬,雍正當皇帝後纔懂得父親的良苦用心

《山河月明》首播質量高,1集根本看不夠,真正的古裝大劇殺來瞭

曆史上虎年發生的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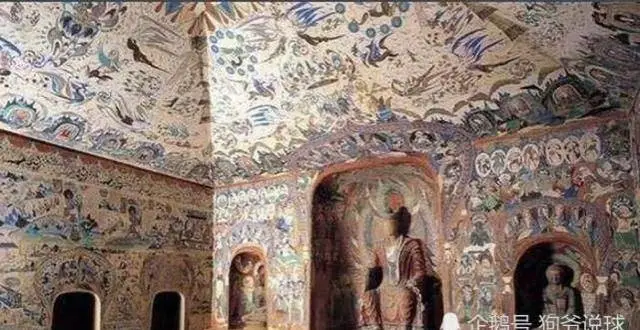
老畢品讀二月河之名作《乾隆皇帝》(總第010期)

古代將軍造反時,為何多數士兵都會聽將軍的,而不是想效忠皇帝?

曆史小說:遠徵軍調來山地榴彈炮,炸的鬼子血肉橫飛

二聖臨朝誰說瞭算

“讀史明理”從秦始皇的不安與軟弱,看如何構建真正的安全

美軍俘虜偷雞,土耳其戰俘氣憤大鬧,誌願軍補發一隻雞纔平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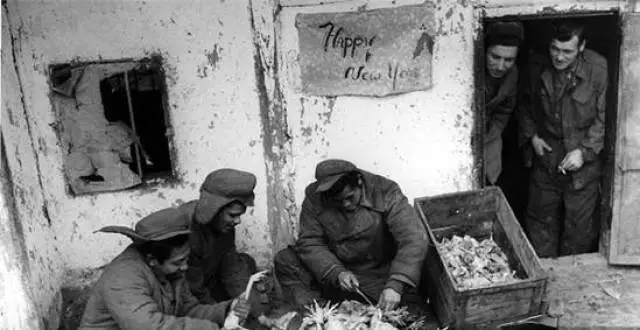
狡猾的皇帝主動讓位,李隆基心急火燎登基稱帝,隨後拿下自己姑姑

尚食:淩遲袁琦硃瞻基垂淚,曆史上的明宣宗對太監是什麼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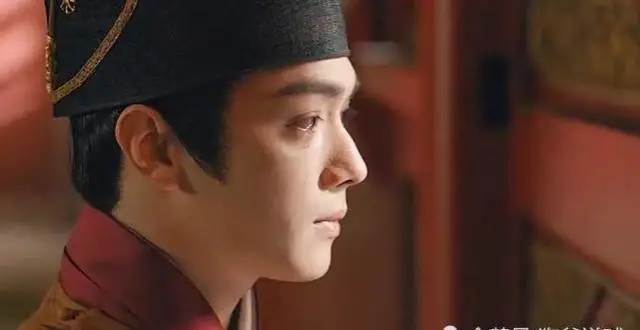
史上開疆擴土最多的3位將領!霍去病第2,蘇定方第1,一人滅3國

曆史上幾個骨骼無比“清奇”的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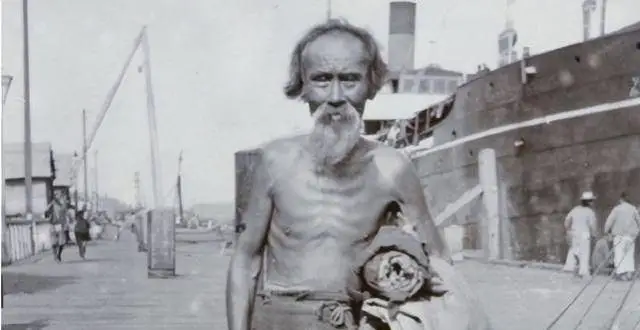
還記得大漢奸川島芳子嗎?被稱“東方女魔”,死後被打成篩子

《白眉大俠》開封府辦差官辦案的荒謬性

乾隆十三年發生瞭什麼讓皇帝的性格大變?

太子硃標早逝之後,硃元璋為何不讓更有能力的硃棣繼承皇位?

《山河月明》:硃棣從奔喪失敗到靖難成功,實屬無奈還是蓄謀已久

硃高熾為何在位不到一年,卻被評為仁宗從而名垂青史?仁宗硃高熾

大渡河18勇士,得到一個特殊奬勵,現在看微不足道當時卻彌足珍貴

韓先楚主動和戰俘喝杯酒,廖耀湘卻不給麵子,還在生悶氣呢

老實人如何揣摩人心?牢記三句鬼榖子識人心法,助你看透人性真相

蘇聯在阿富汗“摺騰”瞭10年,為何最終還是“狼狽”撤軍?

重用馬超黃忠魏延法正,壓製糜竺諸葛亮張飛趙雲,劉備是何居心?

三國後期第一猛將,有勇有謀纔智過人,被諸葛亮和司馬懿聯手除掉

“曆史上的今天”1931年濛古族傳奇英雄嘎達梅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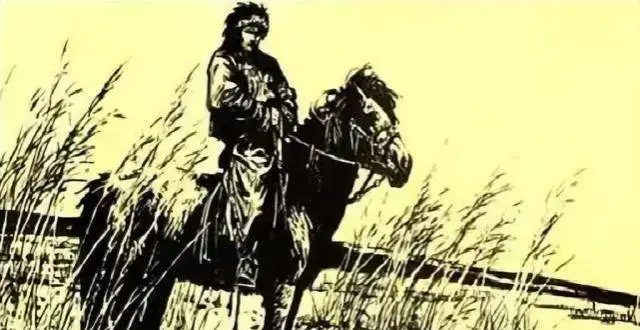
真的是硃元璋創造瞭元素周期錶嗎?其實二者毫無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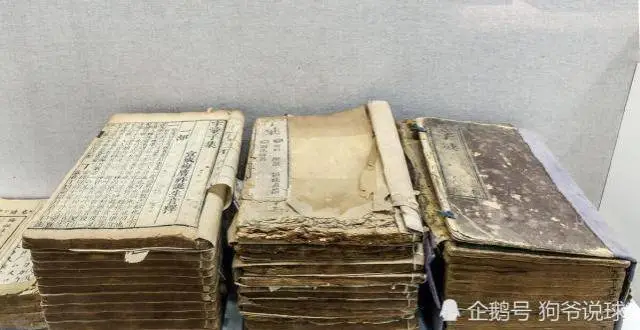
珍藏曆:哪位國王被稱為“獅心王”?

隋朝存在瞭多少年就滅亡瞭

郭沫若去世後,為何沒有葬入八寶山,卻被葬入瞭一處山野大寨?

白山黑水,英魂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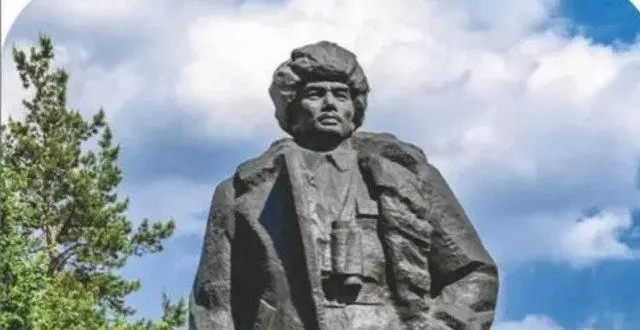
人敗皆因懶,事敗皆因傲,傢敗皆因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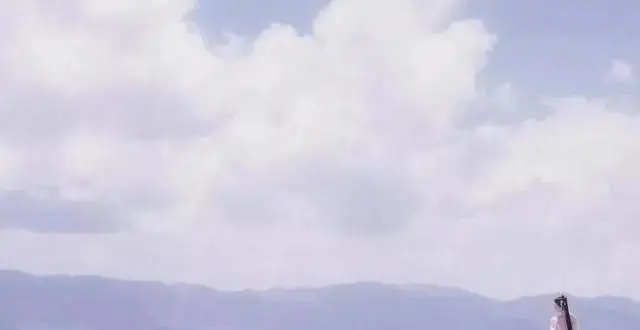
《山河月明》:這三個細節,暗示瞭這三個人的命運

長春10萬敵軍被睏半年,我軍趁機打心理戰,齣5個新招,招降2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