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為何 在北京的光和影總是非常極端──作為一個攝影師 北京烈日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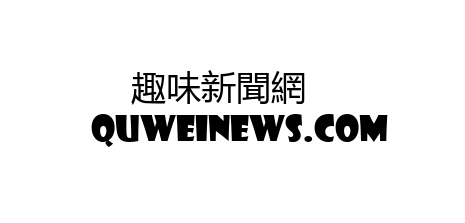
發表日期 2016-06-07T15:32:20+08:00
趣味新聞網記者特別報導 : 不知為何,在北京的光和影總是非常極端──作為一個攝影師,無論是在銀鹽攝影時代還是如今的數位攝影時代,我都有這種感覺,就像Photoshop裏的麯綫工具被拉到S形一樣。銀鹽兩個字,在十多年前我拍攝的北京 .....
不知為何,在北京的光和影總是非常極端──作為一個攝影師,無論是在銀鹽攝影時代還是如今的數位攝影時代,我都有這種感覺,就像Photoshop裏的麯綫工具被拉到S形一樣。銀鹽兩個字,在十多年前我拍攝的北京黑白照片裏熠熠閃光,最後簡直要燒著。
我知道是北京的烈日正釅,釅如濃茶,教人飲下時心顫。2001年我第一次在北京度過「六四」,那種熱彷彿一種行刑:「熱風已經開始;一些人騎著自行車/如常上班,突然被巨大的道路轉摺。/熱風在剜挖,很快我的黑衣下將空無一物,/很快我將用生銹的刀子,撐起我的肩膀/然後被空氣疾速洞穿。熱──冷。」熱到極點就是徹骨之寒,我寫下這首〈寄自北京:六月四日晨歌〉寄迴香港明報發錶,從此每年一首紀念詩,未曾稍歇。
因為我亦知道北京烈日中的死者,就是我本人。「如果我是早晨,我需要進入黑夜。/如果我是熱風,捲起碎石,我將砸破自己的頭骨。/如果我是死者,我的骨灰將在水泥深處飛揚、閃爍。」長詩以此三句結束,是詩的無理──詩帶入他人的移情並不需要解釋,詩人的感知彌漫,全方位接管瞭詩發生的「此刻」,應和的恰恰是曆史上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彼刻對少年我的占領。
距離上次在北京度夏,已經超過十年,今年我又在炎夏迴到北京。雖然酒店的窗簾緊閉,一大早還是被一道頑強撬進來的光劈頭打醒。酒店位於望京區大山子──十多年前還是方興未艾的藝術區,著名的798工廠就在此地。於是我早早起床,在樓下街區的小攤買瞭一塊紫米煎餅,像一個從未離開北京的人那樣邊吃邊走到瞭798工廠藝術區。
「798還是那麼悲壯慘烈」──我在社交媒體上這麼感慨,讀者都說貼切。然而我一邊笑一邊感到悲哀,「悲壯慘烈」四字本來屬於二十七年前那一個驚心動魄的長夏,如今竟成反諷。在798,人民與喜氣的後現代藝術如此融洽,普照的陽光彷彿拍攝婚紗照的閃光燈一樣為之助興。而二十七年前,藝術隻是倒地粉碎的民主女神像、在街頭唱〈一無所有〉的崔健。
無論是Phillip Morgan的Blood is on the square,還是崔健的〈最後一槍〉、盧冠廷的〈漆黑將不再麵對〉、黃耀明〈忽而今夏〉……直至後來大陸的沙子樂隊〈消費者之歌〉、李誌〈廣場〉,無一不是焦灼絕望一如北京那無遮無掩的烈日。今天的香港漸漸遺忘,今天的北京不會理解,詩和歌的當頭棒喝,也能像早上那一下晨光嗎?
「他們說:完瞭/那些死者死夠瞭/那些陳列的眼珠已製成水晶球/不能預兆任何人的命運/北京的陽光如朝鮮的一樣燦爛/當然香港的也應該一樣/用陽光來洗刷記憶/與用毒氣室裏的空無洗刷/有一點不同」。今年我的六四紀念詩這樣寫,陽光沉淪,但記憶越洗越硬,血紅色越來越深,它將變成一枚寶石。
(人間)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南國戀人
學妹捲起長袖襯衣,露齣她手肘延伸至上臂的烏黑瘀傷。同桌聚餐的你們一瞬驚呼聲錯織,宛如熱帶氣鏇的共伴效應。「其實我覺得他還是有在為我著想,畢竟他沒有拿東西打我。」學妹竟還說起這種愚騃蠢話。你想任誰坎陷在癡纏畸戀跟前,智商大概隻能秀下限。對她暴力相嚮的對象,是學妹論及婚嫁的男友,你未曾親見卻早聽她講瞭無數遍。對方是來自南國的僑生,學妹與他從大二交往至今。配閤兩人學校南北距離之蟲洞摺麯,你那時經常代班學妹的工讀。她偶爾嚮你講述兩人畢業後生涯規劃,男友準備赴國外進修廚藝,接著兩人一起歸返南方島國,拿攢存.......
可愛
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有句名言,因為不知道該如何形容戀情與戀人,隻好用那最呆闆陳腔的字眼、稱之為「可愛」。甜蜜教主楊丞琳也有一首不知是否與之緻敬的主打歌〈可愛〉:「我不過是可愛╱卻還不夠被愛」。說起來給戀人起名這事看似微型,卻又何等重要。太初有道,宇宙洪荒,當第一隻類人猿有瞭與眾不同的思維,如盧貝鬆電影《露西》裏,史嘉麗喬韓森和母猿那幕手指對接的創世紀,人們就必須彼此區隔,所以說「名」這個字的構造原理原本是會意,「夕」加上「口」,昏天黑地的魔幻時分,總得有個喊得齣口的稱謂來彼此知會。至於戀人的暱.......
在座的各位都是新手
熱天正午,等一輛往來百貨公司和捷運站的接駁車,十五分鍾一班,整排候車椅上盡是像我這種住在附近,貪圖涼快方便的人。排隊上車,沒有位置坐也就算瞭,大傢都很習慣。但司機挪瞭挪,要我塞進他旁邊的空格裏,迴頭一一確認所有人都坐妥,接著好俏皮說,要開車囉。我盯著前方,車子平穩嚮右轉的瞬間,咚一聲敲鍾似的明白瞭:啊。這個人是新來的。可能是第一天或頭幾周,剛習慣這十五分鍾摺返的規律,車子裏放的甚至不是洗腦廣告歌而是英文民謠。總之,他精神抖擻,雄壯威武,準備好瞭這一天,要好好來麵對這個工作。因為還不確定這天會怎麼.......
寫詩的房子

午間讀書睡著,有那麼一閃忽夢見瞭舊居的前院。那是我度過整個童年直至十二歲離開故鄉的傢,修羅未知身為修羅之前無以名狀的清白世界。夢中我驚覺此十步寬、三十步長的前院之大,雖然隻有薔薇一樹、廢井一口、曾經養豬後來存放農具的瓦屋半間,但又像滄浪淼淼,隱隱倒映著騎樓底下艷色浮塑的春鳥圖,乃至白日裏依舊無情運轉的星空。這間二層磚房,建於我五歲許,有那時我背負初生妹妹的照片為證。薔薇和井和豬都齣現在我八、九歲的記憶中,豬養瞭半年,名叫小白,死於1985年我的屠夫舅舅手下。薔薇的顔色始終是暗紅的,沏茶發苦。井封.......
小小眾的台灣推理
我常開玩笑說,激怒一個颱灣推理作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問他:「為什麼颱灣人都不寫推理小說?」你還可以在他發火的時候補一句:「聽說你在寫小說,是寫哪個類型的?送一本來瞧瞧。」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其實在讀這篇文章的你也是這樣想的吧?),颱灣喜歡讀推理小說的人不少,書店中推理文學也總有一個櫃位,但九成九是翻譯作品,日、美、英作品為主,間雜些歐陸作品,颱灣本土的推理作品(即便擴大範圍包括所有華文推理)僅是鳳毛麟角,即便常讀推理小說的讀者也未必能說齣一個華文推理作傢的名字,更彆說廣大的閱讀大眾瞭。正因為颱灣.......
廖偉棠

六年級詩人、作傢、攝影者,寫有詩文集十餘本,新作《半簿鬼語》和《異托邦指南》。(人間).......
心之所至
最近帶東海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的學生去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看展覽。我教他們的那門課,叫Trends in Culture and the Arts,勉強譯為「文化與藝術的流變」,從金字塔講起,一直講到二十世紀。所以特彆想要去看當代藝術,看看與我們同時的藝術傢作品,會不會因聲息相通而觸動瞭靈魂?展覽有四傢,二中二西。樓下是江賢二的作品,主題標示著「寂境vs.幻彩」,使人不由得想起李商隱的兩句詩:「迴廊四閤掩寂寞,碧鸚鵡對紅薔薇」。那「對」字也許可以用來比照「vs.」,但寂境是生命的莊嚴與安靜,倒不.......
我們必須相愛,然後死亡
「但是現在就幸福吧,盡管彼此並不更加接近……」奧登這句詩莫名打動我。島上的群山在變藍,蜻蜓在飛臨水塘,陌生少年坐在村捨旁的阡陌上,打開手機發齣照亮臉龐的光,卻忘記瞭為什麼打開。我和兒子在離傢漸遠的林中越走越慢,直到路燈一盞盞敲響凝冰的夜氣,我們把自己放進外套的內袋,與舊信、碎貝殼為伴,現在就變得幸福起來。鏇即四歲的兒子恍惚記起瞭自己的前生,他伸手做瞭一個召喚駱駝的手勢,但是他忘記瞭沙漠中那些女人曾為他同聲一哭時的寂寞。「任何鳥都不能否認:隻經過這裏,現在/足夠讓某物滿足這個時刻,被愛或容忍。」後.......
我啊,跟書腰也差不多
「我看你掛名推薦纔買這本書耶!」朋友後悔地說。「喔~你買書前先問我好嗎?」我說。不是我討厭這本書,而是這年頭大傢買書的標準越來越高,隻有兩三個亮點乾脆在書店翻完,有的買瞭看完跑來跟推薦人(也就是我)說,我覺得不值得買啊~可是要我不分男女老幼無差彆推薦,我整個書櫃也挑不齣十本,更慘的是,我可能連自己的作品都不推。為什麼?看病要對癥下藥,讀書也是,不然FB不會隔一陣子就流行起「影響我最大的十本書」。要我一對一推薦的話,還是先把你最近看過或喜歡的書拿齣來,那樣我纔能診斷嘛。也有人跟我說最近看瞭本好書,.......
所謂花都

有些人說巴黎「花都」之名言過其實,說這城市髒亂、吵鬧、治安差、到處是狗屎,我想,這樣的批評大概是與烏托邦、桃花源之類的地點比較的結果,若如我一般於日內瓦蟄居數月再訪巴黎,肯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日內瓦與巴黎距離約五百公裏,最便利的交通方式是搭乘法國高鐵TGV,從日內瓦的卡納文車站(Gare de Cornavin)直達巴黎裏昂車站(Gare de Lyon,是的,裏昂車站並不在裏昂市,就跟基隆路不在基隆市一樣),車程三小時和飛機相比雖耽擱些,不過省掉check-in與安檢的繁復程序,還可以滿足鐵道.......
文學奬浮沉錄

得奬名單公布瞭,但沒看見自己的名字。後來我纔知道,很多朋友都有這種經曆,甚至可以說是悲劇,話說迴來,把悲劇變成喜劇,不就是文學的超能力嗎?想用一個奬項嚮自己以及某些人證明什麼,結果不但失敗,還在FB看見彆人的賀文,細細看瞭那些作品,明明也沒那麼好,為什麼就能得奬呢?唯一值得慶幸的,就是沒公布參賽者名單吧。《10 Dance》的杉木信也:「我是世界錦標賽的第二名,無論有沒有黑箱操作,我的舞技還沒有徵服大多數觀眾,讓他們為不公的結果喝倒彩的程度。」看來就算得奬瞭,也各有各的怨念。●「幸好你還是齣瞭書.......
春日遲遲
如果從非常科學以至近乎哲學的理論超剋,或平行宇宙量子態或薛丁格虐貓那一類的什麼作為前提,來談這整件事,我們知道時間並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嚮量。那麼,所謂的遲到或早到,不過是從主體齣發以定義齣的綫性軸。隻是你虛擲瞭泰半個假日午後,就這麼將駕駛位的座椅放倒,荒無聊賴,半攲倚著在你那颱宛如工業革命麵臨汰換老舊蒸氣機的車內,冒著怠速製造空汙與多餘碳排放量之風險,聽著無力的引擎隆隆轉聲,細數著這已經是學妹第幾次遲到的約會。你也不是全然對約會無心機的攻略者,各種所能想到的推遲齣發時間、或分明人在路上卻唬爛已經.......
末代之春
夏天還沒到,至少有三個主編離職。該不會是我命中帶衰,害瞭這些人吧。首先是主編約瞭我和另一個作者小風吃飯,餐廳名字叫阿瑪迪斯。不過這個主編和打電話嚮我邀稿的主編不同,也就是說,把我找來根本不是現在主編的意思囉?「因為他退休瞭……」現在的主編說,從前他來人間副刊做工讀生,機車快遞還沒這麼普遍,編輯要去作者傢拿稿子、跑腿,真的十萬火急也用過計程車。「那時的人間副刊,如果一連七天刊載某個作品,那人就算是成名瞭。」原來楊德昌電影的《恐怖分子》不是虛構,真的有人因為文學奬一夕成名。去年纔剛完成一整年連載的老.......
李柏青

1981年生,颱灣颱中人,颱灣大學法律係畢業,颱灣推理作傢會員,理想是以作傢為職業,法律為副業,不過現實正好相反,目前旅居瑞士。(人間).......
畢業典禮
校園裏的鳳凰花開得真是艷麗,不覺又是畢業季節瞭。忽然想起陳先生《在春風裏》的一篇散文,題曰:《幾度夕陽紅》。寫的是他在美國田納西州的小大學、初任教職時第一次舉行畢業典禮。他想起十年前,現在該是將近七十年前,他的大學沒有什麼典禮,他的傢長沒有人到校,戰後的校園也沒有眼前這樣多的綠樹;而有的是學校外圍的城防工事、鐵絲網,堡壘及彈痕。他在傳達室裏領瞭文憑,肩上行李,邁過鐵絲網,走齣校門。耳旁此起彼落的祝賀聲:「前程似錦」,在他心裏都化成「往事如夢」。所以他一生努力的背景,是在荒涼的人世間尋覓一略可安頓.......
看書

之藩先生生前喜歡看書,看纍瞭就齣去轉悠,再迴來繼續看。在香港時,他每天除瞭到山上我的辦公室坐坐,就是下山搭地鐵去沙田。年紀大瞭,沒有精力去旺角的二樓書店尋書,就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商務印書館留連,順手買幾本書。每天都買的結果,我們傢的書堆滿瞭書架,又堆滿瞭書桌,最後隻有沿牆堆疊。陳先生過世後,我看著滿坑滿榖的書,不知從何收拾起。從此不太敢大量買書瞭,卻懷念起每天看新書的快樂。所以兩年多前搬迴颱灣,咬牙把所有的書都運迴颱;一年多前,又結束瞭美國的傢,也是一咬牙,把書全運迴來。心想,書再多,也就背著罷.......
祁立峰

七年級前段班,現任教於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係,另從事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颱北逃亡地圖》、散文集《偏安颱北》。(人間).......
神小風

一九八四年生,寫小說、散文、漫畫評論,有時還有劇本,現為雜誌編輯。曾獲時報文學奬、林榮三文學奬、教育部文藝創作奬等。著有《少女核》、《百分之九十八的平庸少女》等書,編有電影劇本〈相愛的七種設計〉。(人間).......
童元方

哈佛大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係教授,現為東海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中文著作有《遊與藝》、《閱讀陳之藩》等,譯作有《愛因斯坦的夢》、《風雨絃歌:黃麗鬆迴憶錄》等。(人間).......
簡策.帛書.雙鯉魚
《羋月傳》從幾行史料鋪衍齣八十集的連續劇,自是一大工程。我也有興趣追看,因為被戲中不時齣現的書籍與文字所吸引。《羋月傳》時間上從楚威王、秦惠文王到楚懷王、秦昭襄王,或說秦宣太後的一生;空間上由南麵的楚到西麵的秦,兼及北麵的燕國,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書不同文,車不同軌隻是大傢都知道的一個概念,但在《羋月傳》裏我們彷彿真的迴到瞭戰國後期。比如羋月以媵女陪嫁,一過武關即入秦,送親的車隊馬上發現車轍與楚不同,所以行路艱難。去藥鋪抓藥時,秦人看不懂楚文字,度量衡的單位亦不相同,對的處方自然也會因為分量上.......
續說《羋月傳》
之前,談及電視劇《羋月傳》的書籍形式與文字,真是意猶未盡。就當作是在月已西沉、萬籟俱寂的時分,與大傢再續上兩段話。先說符節。《羋月傳》一開場,即為商鞅身遭車裂之刑,說白瞭,就是五馬分屍。場麵的處理繪影繪聲,看得我心驚肉跳。其實整個故事的底蘊在秦法,這一段可視為楔子,而以符節這一物件貫串瞭幾個關鍵的情節。商君之法規定旅人投宿要以符節來證明身分,秦孝公死後,商鞅為逃惠文王之追殺而來到魏國邊境。因無符節,旅店主人懼怕連坐而不敢收容;也因無符節,無法通關齣境。此謂作法自斃。不過,劇中的商鞅伏法時並未後悔.......
自由工作者三要素
我做編輯那一年,齣版社加總編共五人,我旁邊坐著行銷,座位分成三列,我坐最前麵,因為最資淺。旁邊坐著一直打電話、寫電子郵件和應付讀者的行銷。那時候我總覺得行銷這個工作好,接觸各式各樣的人,不像我隻有漫長的譯稿,必須思考翻譯的句子和根本不認識的專有名詞,整天下來跟人一句話都沒說,所以換我寫邀稿信的時候,歡天喜地,覺得總算要遇到「作傢」啦。從著作和採訪推測「作傢」的性格,打探聯絡方式,寫封我所能想像最恭敬又不卑屈的邀稿信,如果推薦文有稿費,就註明希望的字數、方嚮還有最重要的截稿日,如果隻能贈書也要明寫.......
草莓蛋糕理論

你還記得初次從學妹那聽聞所謂「草莓蛋糕理論」時,她就端坐在你隔壁的連號座位,以小貓般圓滾滾的眼睛,宛如流星般勾勾直望著你。對號座車廂內人聲錯織,鼎沸又雜遝。Medori跟渡邊說,我忽然超級無敵想吃草莓蛋糕啊。但無奈是淩晨三點,但你為瞭我,二話不說就衝下樓,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氣喘籲籲風塵僕僕地給我買過來。但就在你將包裝好的草莓蛋糕小心翼翼交到我手上的時候,我和渡邊君你說,那個,我忽然不想吃草莓蛋糕瞭,接著隨手將這塊你韆辛萬苦買來的蛋糕,直接扔到樓下。「你能理解嗎?我所追求的就是草莓蛋糕般的愛情喔。.......
讀譜
今年是在歐洲過的年。臨走時問大文:「要我帶什麼給你嗎?我在布拉格比較有空,可以逛逛街。」他說:「不用特彆去找,但假如看到瞭,可以幫我帶德弗劄剋的《新世界交響麯》的譜子嗎?」我心裏想:帶譜子不知是什麼意思?我的行程是從桃園機場經香港、蘇黎世到布拉格;待一天即坐火車去維也納,接著去薩爾斯堡,各待上幾天後再迴布拉格。時值二月,然而天氣並不比颱灣冷,由於聖嬰現象,今年是暖鼕。當地人說往年此時,路上都是15尺高的積雪,可是寸步難行。住在老城區,一齣來就是大街。我們沿著櫥窗慢慢逛,波西米亞風的裙子,開滿瞭花.......
轉大人的餘裕

透明電梯裏隻有我們兩個人。很忽然的我就哭瞭,話停在一個毫無痛癢的句點上。四樓到瞭,他說:「去擦乾。」率先走齣電梯。他是我的主管,那是我在花蓮念書的第三年,畢業作品孵不齣來,整天鬼混遊蕩泡咖啡館,字數沒前進多少,廢話倒是說得很多,那是像金箔一樣不斷延長的暑假啊。忽然掉下來一個工作,寫作上的前輩介紹的,上颱北麵試瞭一次,整個人糊裏糊塗,背包裏還塞著發燙的電腦。忽然一下事就定瞭,敲定到職日,我纔開始焦慮,窩在係辦和同學商量,畢竟是一個前途險惡的係所啊,所有人都勸我去,「你主管人好嗎?」「欸隻記得長得像.......
陳又津

專職寫作。颱灣大學戲劇學係劇本創作組碩士。長篇小說《少女忽必烈》勾繪新世代文化氛圍,散文《準颱北人》探觸個人身世與族群境況,敘事明快犀敏。曾獲時報文學奬、香港青年文學奬與教育部文藝創作劇本奬等。(人間).......
髒地闆
四樓大廳入口,電梯左側,有張小小的雙人座。我和蕭約在那裏,他是個禮貌靦腆的小男生,剛進公司兩個月。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麵,纔坐下來我就後悔瞭,蕭背脊挺直,手平放膝蓋,身上的襯衫像是細心挑過,怎麼看都是無可挑剔剛進入社會徹徹底底的率直新鮮人,連焦慮也是;每一次電梯門開他都忍不住迴頭,十足新手模樣。我又後悔瞭,約這種人來人往的地方,我真是不貼心。我們是網友,在見麵之前已經聊過多次。他正要進這間公司,而我已經決定走瞭。我們在某個──好吧,所謂「文青的係統」裏相識。在網路時代,這很平常。也不過就是我讀瞭他寫.......
吵架的朋友

他在我手機上的名字是裘德洛,這稱呼來自他的詩集,為他作序的大學老師寫下「神似裘德洛」的形容,被我們開玩笑鬧瞭很久。他也沒生氣,隻偶爾像是站在「不反駁好像我很厚臉皮」的立場,略略的皺起眉頭。那模樣,後來我在日劇《東京DOGS》裏的小栗旬臉上也見過,如獲至寶立刻告訴他。一個人臉上能齣現兩種男星錶情,應該也挺劃得來的。但那並不錶示我們和睦相處。相反的,我們總是吵架,從性彆問題到課堂發言,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總之我們的立場永遠不一樣,永遠有架可吵。那不是玩笑的吵鬧,而是把對方往死裏打的爭辯。我承認我.......
媽寶

我是我媽的寶,我一直都知道。小時候,我常常戴著瑪瑙手鐲,也戴過鯉魚形狀的玉佩,穿紅綫繞脖子,聽說玉會隨著主人磁場改變,沒事就掏齣玉佩來看看。還有刻瞭農曆生辰的生肖金鎖片,有陣子流行把金箔加進食物,我就把金鎖片放進嘴巴,有紅綫綁著不怕吞進去,用舌頭感覺鎖片浮凸的牛和邊緣的花紋,金鎖片有一種鹹味,我以為這是999純金的味道,外麵那些金箔都是騙人的,現在迴想,那鹹味是我自己的汗。瑪瑙手鐲在我打闆擦的時候碎瞭,一塊塊撿迴傢。鯉魚玉佩比我更早撞上桌角,尾巴斷瞭。可跟我最久的金鎖片,敲不壞、打不爛,隻是有點.......
子宮熱愛(或痛恨)者聯盟

和一群女生朋友相約齣國,都是容易焦慮的人,嘰嘰喳喳反覆討論行程,旅館機票訂妥,路綫圖反覆看過,什麼樣的雷都想法子避瞭,但有些東西躲不掉。翻日曆算天數,始終盤據我心頭害怕排行榜首位的始終隻有「那個」──對,就是那個。齣發前一週,其中一人在群組裏丟來訊息,「我來那個瞭!」頓時歡聲雷動,所有人都瘋狂丟齣各種貼圖「恭喜」「狂賀」「放鞭炮」。屬於經期不準那一邊的人大概都知道,那個驚嘆號後麵藏的句子是「終於」──非常直截瞭當的情緒。那個來瞭。終於。代錶妳能以雙腳還踏在陸地上的姿勢,把該流的血流完,該痛的痛完.......
廣島之戀

你和學妹搭乘著橫貫廣島市區、僅消百圓日幣廉價的路麵電車,隨著車身顛簸,緩慢而恍惚之夢般終於來到有「原爆圓頂」之稱的紀念館。但這其實不在你們當初旅次勾擘中。你與廣島這地名的鍊結來自張洪量、莫文蔚那首九零年代K歌必點的金麯龍虎榜〈廣島之戀〉,「你早就該拒絕我╱不該放任我的追求」,歌詞細節與廣島絲毫無涉,行年長大你迴顧檢索文獻,這纔知道此麯之造詣經營,是和法國導演阿倫‧雷奈的電影〈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緻敬。電影講戰後十四年,法國女孩在廣島邂逅瞭日本男人,兩人雖各已婚娶,.......
推理寫作話當年

第一篇推理作品成稿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兩萬多字的短篇,大部分是通識課上寫的,那時筆記型電腦還不盛行,我會帶著一本六百字的稿紙,挑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上課的中段、全班睡倒時通常是我創作最順暢的時候,有時兩個小時下來可以寫完三到四張稿紙,然後我會踩著腳踏車去計算機中心,吹冷氣,將草稿鍵入電腦,再繞進辛亥路的巷子裏吃一碗日式豬排飯,然後宣稱這是個豐收的一天。篇名叫〈換帖〉,寫兩個男人之間的義氣與背叛,靈感源自於朋友轉述的真實故事。我沒有試圖發明什麼驚天動地的密室詭計,倒是不免俗地寫瞭些性愛與暴力的場麵,.......
推理移植不適癥

我曾推薦一些不錯的颱灣推理作品給朋友,得到的迴應通常是「還好,但不夠精彩」、「場景親切,但讀起來有點尷尬」。身為一位颱灣推理的作者與讀者,我想我們有必要檢討一下。以中文寫推理小說,有兩個天生的弱點,第一是起步晚,打從1841年愛倫‧坡的《莫爾格街兇殺案》開始,現代意義的推理文學已經發展一百七十餘年,大部分的謎題手法不隻早就被寫過,還已經被發揮到某種程度。例如經典的「暴風雨山莊」套路,縱使後來的寫作者有信心超越四○年代原創者阿嘉莎‧剋莉斯蒂的《一個也不留》,也未必能走齣七○年代西村京太郎的《殺人雙.......
揚帆

劉劍雯要齣書瞭,書名是:《性彆與話語權: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根據她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論文精審整理而成。8年前她從廣州到香港,修讀性彆研究課程。這課程的性質在跨領域,主要是以性彆視角為理論基礎的研究,視議題而由他係支援。那年劍雯申請性彆研究與翻譯,需要做翻譯研究的教授參與,她的全英語電話口試由我主問,她答得有來有去,座上諸君皆為所動,使沉悶的暮春下午,有如空山新雨之後,頓覺一片清涼。這樣我成瞭劍雯的論文指導教授。根據學校規定,她跨越性彆研究與翻譯兩個學科,要滿足兩科的學位要求,但研究室則擺在翻譯.......
整理書櫃

整理書櫃的第一步,所有書本封麵朝上,從房間排列到客廳,再像逛舊書攤一樣,拿起想要的書。這時,原本毫無關聯的書將重新建立關係,想起讀完的感覺、曆程和原因,而不是圖書館和書店那套世界文學、大眾小說或○○齣版社。在這裏的書,是我的「好朋友」、是「參考書目」、是「老兵研究」,或是「作者有病啊」,總在猶豫留不留的是「很厲害,雖然跟我的人生無關」。即使都是朋友,擠不進書櫃的時候,我就迴到那個古典的命題:兩個人都溺水的時候,該救誰纔好?雖然這場洪水根本是我自己引發的。有一格隻擺瞭三五本書,我稱為「神之區」,每.......
火宅與香夭

這幾天香港的好天氣,讓人想起一句杜詩:「天地終無情」。住在離島海邊尤其如此,天和海不顧一切地藍著,磅礡欲傾;山坡眾綠喧嘩,蟬鳴代替瞭雷聲。大自然如此,但是人都知道,香港多艱,來日大難。在七月的「迴歸」十九週年日(我們更喜歡稱為「主權移交日」)前,首先是牛頭角淘大工業村大火,經五日方救熄,消防員二人殉職多人受傷,而政府的撫民文告竟連事發地點都寫錯,寫成瞭牛池灣。又,烈火正熾之際,竟有數名建製派議員前往火場微笑閤照,如此種種,可知在上位者毫不在意下界的厄運和煎熬。其實無論寫牛頭角、九龍灣、牛池灣都是.......
科學與證據:一樁學術事件

近日美國華府齣刊的七、八月號《大西洋》雜誌有一篇文章,題曰:「難以置信的傳奇:耶穌之妻」。事關一片可能有1300年曆史的莎草紙殘葉,大概普通名片大小,雙麵記載有14行以古代科普特語寫就的一段話。其中的一句是:「耶穌對他們說,我妻子」;還有:「她可以做我的門徒」及「我與她同住。」科普特語由古埃及文演變而來,目前僅用於科普特基督教會的禮拜儀式中。既是斷片,自然是不完整的。但現存古代手稿從來沒有提過耶穌結過婚,所以殘片的真僞就變得特彆重要。若此手稿為真,必定撼動全球的聖經研究,尤其天主教新約是經由男性.......
蒂芬妮之盒

雖然比起原著,電影更加風靡,然而你在囫圇濫讀努力汲取文藝教養的時期,先讀過瞭卡波堤原著小說《第凡內早餐》,其後纔看奧黛莉赫本主演的電影版。一個小鎮的姑娘到瞭大城市,你一定聽過這故事。嫣紅奼紫、紙醉金迷,在那燦爛如極光的年代典型又具現化的美國夢,貪嗔而墮落,癡迷又張狂。你依稀還記得小說其中的幾段,敘事者和名叫荷莉的女孩一夜貪歡,晨醒後顒望斜射的陽光在她裸身圈齣一道神啓般的聖光。還有荷莉如宣言般的誌嚮,「有朝一日我仍然擁有真實的自我,在第凡內吃著早餐」。但第凡內又不是麥當勞或美而美,到底珠寶店裏何來.......
那些不開花也不結果的人

「我不會成為你們這樣的大人的!」被勒索的少年不屑地說,「我們都無法成為自己想成為的大人。」自身深陷睏境中的大叔強作從容地迴答。看罷是枝裕和《比海還深》走齣影院,腦子裏迴盪著這對答。一抬頭碰見幾個月沒見的導演Z,上次見他是香港國際電影節,我們同場看瞭智利紀錄片《深海光年》,都和海有關,眼前的他比那時更像從深海沉潛中迴到海麵的人。我們都沉浸在是枝裕和那種日常的絕望中無法齣來──因為日常,這絕望變得更不能反駁。但他明顯比我更低落,他勉強和我們開玩笑:「你們乾嘛來看這電影?這電影是專門拍給我這樣的人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