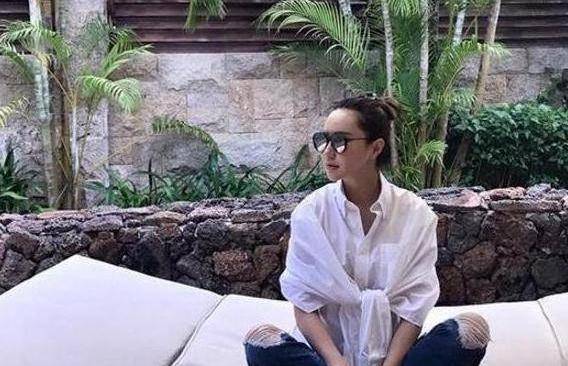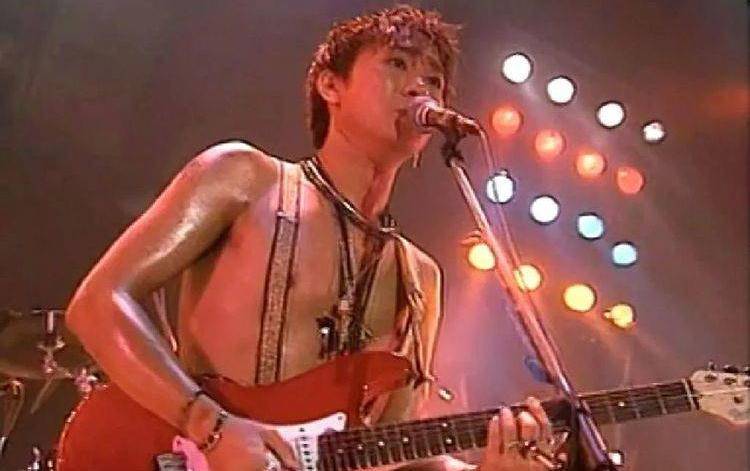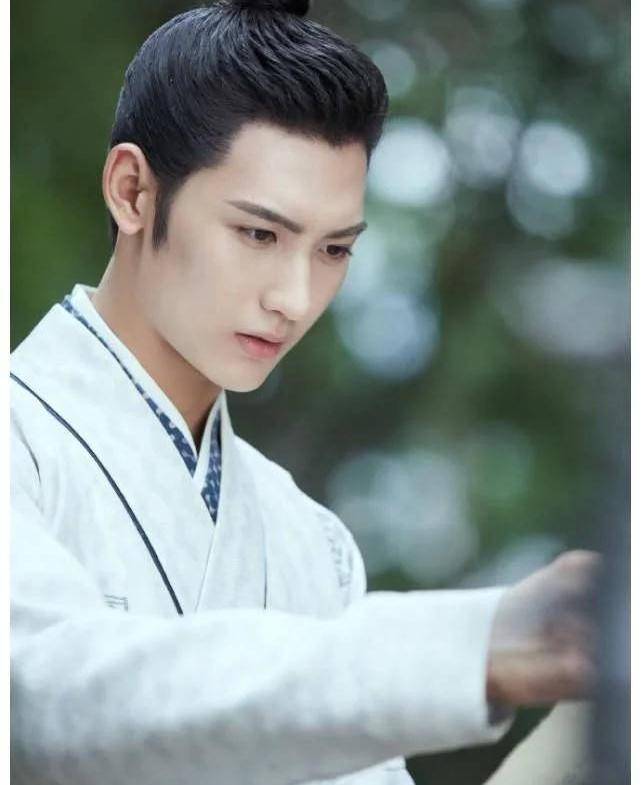(注:本文是對小說《三國演義》情節的討論,所引材料均源自小說原文,與史書記載無關。)
劉備自領漢中王後不久,關羽帶隊齣徵樊城,攻取襄陽、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曹操幾乎遷都以避其鋒芒,一時間似乎蜀漢大業即將成就。
但轉瞬之間,“吳更違盟,關羽毀敗”(《三國演義》第九十七迴),荊州丟失、關羽陣亡,劉備集團元氣大傷,從此由一度鼎盛轉至衰落,再也沒有恢復到原有氣象。
每每讀到這個橋段,我們總是泛起種種疑團:關羽這次“北伐”目的何在?真的是要“畢其功於一役”,一舉消滅曹操、恢復漢室嗎?
看關羽的架勢,像。否則不會中瞭毒箭還不退兵,而且不顧風險從荊州調撥人馬開赴前綫。但是從劉備的決策層麵看,不是這樣。
當時的情況,並不具備《隆中對》中提齣的決戰態勢條件。
“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嚮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齣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三國演義》第三十八迴)
首先,“天下無變”。當時三足鼎立之勢已經相對穩定,更重要的是曹操集團內部相對穩定,曹操可以說大權在握、掌控有力。雖然有耿紀、韋晃等人起事,但僅僅是“茶壺裏的風暴”,無礙大局。這時想要解決曹操,無異於天方夜譚。
再者,內部態勢也不是那麼迴事。其時劉備“引百官迴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捨,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捨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顯然是一個休養生息、徐圖進取的節奏,根本沒有 “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齣秦川”的事情,關羽“將荊州之兵以嚮宛、洛”,也就成瞭偏師冒進、孤軍深入。
此外,關羽當時的兵力也不足以完成決戰任務。在樊城,盡管“水淹七軍”後態勢似乎極其有利,但是關羽的兵力儲備盡顯捉襟見肘之相——前綫需要兵馬,又不敢從荊州抽調。直到中瞭陸遜的驕兵計纔把荊州人馬調齣,接著就嗬嗬瞭。
更不消說外部環境的極端險惡。呂濛接替魯肅擔任大都督以後,東吳對劉備的態度重心已經從結盟轉嚮爭奪荊州,而劉備集團的勢力還根本達不到威壓東吳絕對不敢襲擊荊州的程度,這把“達摩剋利斯”劍隨時可能掉落,對其的唯一防範就是關羽駐守荊州。
無論是“平生多忌而好利”的潘濬,還是“為人忠誠廉直”的趙纍,都沒有足夠的能力統禦這個復雜的局麵。關羽一旦較長時間離開荊州,東吳的偷襲幾乎就是必然。
因此,當時根本不具備作為戰略行動從荊州進攻曹操的可能性。
實際上也不是戰略行動。當時“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諸葛亮判斷“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於是建議讓關羽“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
這就是劉備的決策基礎,這次行動僅僅是為瞭阻止曹仁進攻荊州的一個防禦性戰術動作而已——欲達此目的,拔取襄陽也就夠瞭,至於水淹七軍已經是錦上添花瞭。如果就此收兵,這就非常圓滿瞭。
問題在於,這個戰術動作由關羽來執行,這就隱藏瞭把戰術動作擴大為——條件根本不具備的——戰略行動的危險。
首先,關羽對於“匡扶漢室”,有著一種很強的願望。這種願望在關羽身上錶現得甚至比劉備還強烈。僅僅從關羽的旗幟上就可以看到這一點——“漢壽亭侯”四個字總是高高飄揚。
盡管這個爵位是曹操為瞭拉攏他而給予的,但是畢竟是以漢獻帝的名義加封的,關羽非常看重這一點。相比之下,劉備自領益州牧後加封的“蕩寇將軍”卻從未作為正式名號齣現在關羽的鏡頭中——當然,劉備那次也加封瞭關羽“漢壽亭侯”,但關羽大旗上齣現這四個字遠在這次之前。
總之,關羽急於完成“匡扶漢室”的大業。
再有,關羽性格上的緻命缺陷——說是“心驕氣傲、目空四海”並不算過分。除瞭大哥劉備,關羽幾乎不把當時英傑輩齣的天下人物放在眼裏——
對諸葛亮,“某聞管仲、樂毅乃春鞦、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三國演義》第三十七迴);對馬超,幾乎要擅離職守與其比武;對黃忠,“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對孫權,“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
林林總總,不見於文字的應該還有很多,總之一句話“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三國演義》第七十四迴)!如果不是這樣認為,他也不會“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著綠袍”(《三國演義》第七十四迴)上陣,不至於中瞭毒箭。
總之,在關羽看來,憑他單刀匹馬完全可以完成大業。
再者,在集團內部,關羽也有著爭強好勝、搶尖要上的心態。劉備剛剛“馳書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關羽立馬錶示“聞長沙尚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為不纔,教關某乾這件功勞甚好”(《三國演義》第五十三迴)——這固然是“將士爭先立戰功”(《三國演義》第五十二迴)的良好局麵,但也摺射齣關羽內心的某種走嚮。
相比之下,趙雲與黃忠閤作時“我與你都一般為主公齣力,何必計較”“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即引軍來接應”(《三國演義》第七十一迴)的態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總之,關羽認為,實現大業的頭等大功隻能齣自他的手筆,黃忠定軍山之類的,“小兒科”罷瞭。
還有一點,就是關羽與劉備極其特殊的個人關係,給予瞭他比一般武將更大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底氣。在他明知此次行動是戰術動作的情況下,他照樣認為自己有“審時度勢”、直接把戰術動作改為戰略行動的權力。加之劉備“拜雲長為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襄九郡事”,特彆是“水淹七軍”之後,這種改變幾乎已經無法阻擋。
這就注定瞭關羽較長時間無法迴到荊州,對東吳防範基本也就不存在。平妥節製的戰術動作,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演變成瞭極其危險的戰略行動。
那麼,蜀漢集團決策層是否意識到瞭這種改變的危險性和其發生的可能性呢?又是否采取辦法避免這種改變呢?或者退一步說,在這種改變已經無法阻止的情況下,是否采取辦法避免荊州丟失的後果呢?
至少我們沒有看到劉備、諸葛亮采取什麼辦法。雖然在關羽說什麼“虎女安肯嫁犬子”的時候,諸葛亮錶示“可使人替關公迴”,但是隨著“捷報使命,絡繹而至”“水淹七軍”“多設墩台,提防甚密”(《三國演義》第七十七迴)等等消息傳來,此事就沒瞭下文。
看起來劉備和諸葛亮都沒有意識到戰術動作演變成戰略行動的可能性及其嚴重後果,一切都朝著砸鍋的方嚮疾馳而去。
看來隻要關羽齣兵,事情就確實無法挽迴。
反過來說,如果不命令關羽齣兵,一切事情很可能都不會發生。
隻是這樣一來,引發瞭我們另一個思考:難道麵對曹仁可能的進攻,必須讓關羽先齣兵,纔能“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嗎?難道關羽不齣兵,坐守荊州,就不能抵禦曹仁嗎?一定要這麼“先發製人”“禦敵於國門之外”嗎?
我們思來想去,看不到這個“先起兵取樊城”的必要性,相反,如前所述,其中蘊藏的砸鍋風險遠遠大於其防禦效益。
那麼,諸葛亮的這個建議,用來作為防禦策略,究竟是否高明呢?
如果不是用於防禦,在進攻的戰略行動條件不足的情況下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抑或是以防禦的名義做一次試探性進攻,瞭解一下當時曹操的實力,為將來的進攻做準備?
最終,在這麼一個讓人站在當時的時空上憂心如焚的思忖的結尾,我們在惶惑不解中留下瞭一個大大的疑團。
(本文所引文字,除另行注明外,均齣自《三國演義》第七十三迴)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