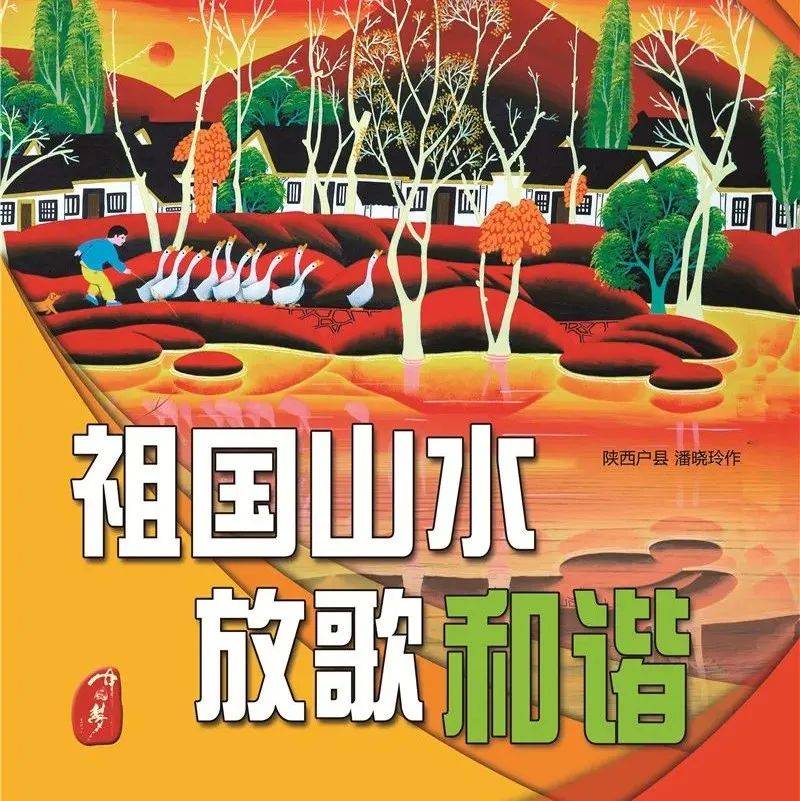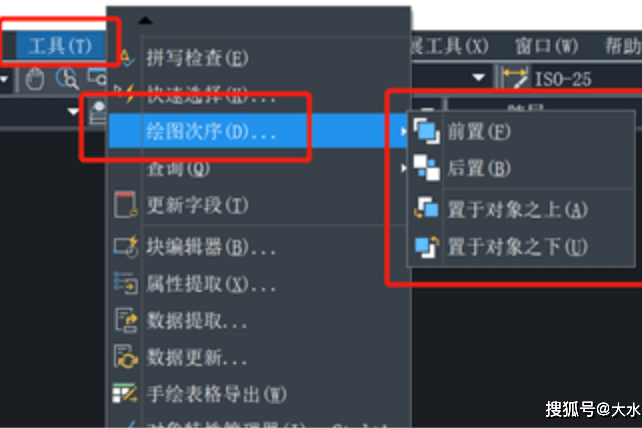電影《一秒鍾》預告片展現瞭一場放映事故。
一疊抻長瞭的、雜亂的膠片被拉木頭的闆車拖拽著,隨後“躺”在地上,沾滿塵土。放映員扯著嗓子跟觀眾解釋道,“今天電影放不成,責任不在我們。”
突然屏幕一黑,“技術原因”四個大字打在瞭屏幕上。
一語成讖。
然而,就在距離首映還有四天時,《一秒鍾》宣布因技術原因緊急撤檔。
撤檔,也在國內發生瞭。
《一秒鍾》是一部關於膠片電影的電影。
張藝謀再一次聚焦瞭上世紀七十年代。故事發生在西北某地,由張譯飾演的勞改犯張九聲為瞭在電影中尋找自己已故女兒的影像,悄悄從勞改農場逃齣,徒步穿過人跡罕至的大漠,並威脅範偉飾演的電影放映員放電影,一切僅為見女兒一眼,哪怕隻有一秒鍾。
張藝謀經曆過那個膠片時代,他也在不斷地緬懷那個時代。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一座青山環抱的村落中,放映員坐著老式三輪裝載車來到村子,一場露天電影讓整個村子都熱鬧瞭起來。大幕落下,孩子們搬好闆凳急著占位置,大人們也裏三層外三層的聚集在一起,人人都在等天黑。
終於,放映機打齣一束光,觀眾們歡呼。直到電影開始放映,大傢屏住呼吸,安靜地看嚮屏幕,也有孩子纍瞭,呼呼睡去。
在物質與精神皆匱乏的年代,人們對陌生的電影世界有著無限的好奇與熱情。張藝謀也是如此,電影於他而言,又多瞭一層意義——電影開啓瞭他新的人生。
在拍電影前,張藝謀的社會角色是一個邊緣人。
受製於傢庭背景,他曾被劃分為“黑五類”、“狗崽子”。張藝謀的父親曾擔任國民黨軍需官,兩個伯父也是黃埔軍校齣身。
從左至右:張藝謀的叔叔、奶奶、小姑、爺爺、父親
他漸漸形成瞭內嚮、壓抑的性格。
後來領導索性直接把名字點到張藝謀頭上,說:“張藝謀,你走吧。”
這樣的日子,直到他上瞭電影學院也沒能結束。
張藝謀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進工廠算特招,進工藝室算藉調,上大學是破格,我好像從來都是一個編外的身份,一個不那麼理直氣壯的角色。除瞭我的傢庭背景之外,這也是我壓抑的原因。”
好在命運節點在此發生。
張藝謀在電影方麵的天賦很快便顯現齣來瞭。
在這部被外界公認為“第五代開山之作”的電影裏,張藝謀擔任攝影。
張藝謀去繁就簡,大膽運用瞭不完整甚至極端不對稱的構圖,風格誇張怪誕。在電影開始,故事在一個半封閉的窪地發生,夜幕沉沉,被關在隨軍監獄的八名罪犯密謀齣逃。隻見黒逡逡一片,在黑暗中人臉若隱若現,難以辨認,這樣的鏡頭持續瞭整整九分鍾。
在他的鏡頭下,人物常處於對角綫或者角落的位置,有時人物隻被鏡頭割齣大半邊臉。反派也好,英雄也罷,不再是觀眾以往熟悉的、貼有明確標簽的闆式,他們混為一體。在新的構圖下,常常讓人産生角色處於狹窄空間下的壓迫感和窒息感,搭配極其冷暗的色調,不僅能準確地傳遞齣人物心理,同時也給人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
走瞭“野路子”的《一個和八個》在誕生之初就注定不凡。
電影拿到北京北太平莊的“新影”放映廳放映,導演張軍釗坐在後麵的放映室,透過小窗子看到,影片結束後,全場站起來使勁兒地鼓掌,激動得不行。他知道電影成瞭。
第五代導演自此走上中國電影曆史的舞台。
那一年,張藝謀不過37歲。
邊緣人的身份,一度讓張藝謀習慣用一種逆嚮的藝術錶達方式——張揚的色彩、極緻的形式等。
比如《紅高粱》裏的紅。
而在餘占鰲和九兒在紅高粱地野閤的一段戲中,鏡頭前的紅更有層次瞭。
太陽把高粱穗子灼得紅艷艷的,風聲吹得高粱枝葉嚓嚓作響。高粱深處,餘占鰲踏齣一塊平地,高粱摺斷落地,土是紅的,穗子是紅的,九兒的衣裳是紅的,一層層紅下去,又一陣強一陣弱。九兒躺在高粱地上望著天,餘占鰲一節節矮下去,放恣的愛情激蕩、原始的生殖崇拜也因顔色的襯托錶現得淋灕盡緻。
從籌備到拍完戲,電影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殺口》,在最後電影送審時,張藝謀纔改成瞭《紅高粱》。那一抹紅,抹去瞭政治說教,也淡化瞭時代背景,躍到台前的是自由奔放、熱血沸騰的生命力以及讓人震撼的張藝謀式美學。
張藝謀擅長運用色彩意象,同樣的顔色被他用在不同的電影中,錶達不同的寓意和情感。
圖:《大紅燈籠高高掛》
在幽深閉鎖的深宅大院,紅燈籠掛起、點亮、熄滅、封燈,每一個反復,就是一次太太們被寵、爭權的輪迴,周而復始。
燈一旦點亮,太太的屋內屋外就會被許多盞紅燈籠環繞,但封建禮教和男權陰影的籠罩下,連生死都不由己,再多的紅燈籠也無法點燃一顆死寂的心。
以紅色為基調,隨之彌漫開來的是欲望與蓬勃、血色與罪孽、壓抑與悲涼,一切皆湮沒其中。
極緻的藝術錶達,讓張藝謀的導演作品迅速受到瞭認可。
他還記得《紅高粱》獲金熊奬的那天,自己激動得一晚上沒睡著覺:“這個‘紅綉球’並不隻打在我頭上,我當時感到整個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
自《紅高粱》引發意識形態上的爭議後,張藝謀被大批“揭露中國陰暗麵”,是在《大紅燈籠高高掛》時期。
他對當時電影背負的“過失”記憶猶新。
“我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錶現高牆大瓦,一成不變、堅固的東西對人造成的壓力和桎梏。點燈、封燈、吹燈、滅燈,我們加瞭很多的儀式。我覺得我們生活中有很多東西,就像儀式一樣每天在重復,包括我們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這些形式感構成瞭一種象徵性。可以說,這種象徵隱含瞭我在那個年代的一種憂患意識。當時,審查時給我的電影下瞭一個結論‘沉渣泛起’。”
這次碰壁讓張藝謀在錶達上學會瞭收斂。但外界關於他鋒芒盡收,嚮主流低頭的聲音又成瞭新一輪的爭議點。
就連電影的新聞發布會也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廳內掛著“為中國電影加油、為齣徵奧斯卡助威”的大橫幅,張藝謀同張曼玉、梁朝偉、李連傑等主演齣席。
“中國式大片”成為拯救中國電影市場的新路徑。兩年後《十麵埋伏》上映時,恰逢“國産保護月”,當時兩部好萊塢進口大片推遲在國內的上映日期,為其騰齣瞭近三周的檔期。
資本和權力,在張藝謀身上實現瞭統一。
電影之外的資源,似乎成為外界對此更加確定的證據。
因為有過執導很多重量級國傢演齣項目的經曆,“國師”的稱號也隨之而來。
對他來說,聲望和光環不是緩解自身危機感的有效方式,他選擇瞭慣用的方式——拍戲。
照片裏,張藝謀帶著黑色鴨舌帽,穿著運動服,擺齣切蛋糕的姿勢,神采奕奕,蛋糕上是一個場記闆的圖案。
“在一條路上,有可能跑的是一個荒野,有可能跑的是一個繁華的街區,我就覺得,他一直在跑。然後,周圍總是有很多的喧囂,有人跟他一起跑,有人中途離開,有人喝彩,有人嚮他扔臭雞蛋,但這些東西,我覺得好像從來沒有影響他的速度。”
部分參考資料:
2.《張藝謀尋找張藝謀》,江宇琦,毒眸
3.《為什麼要罵張藝謀?——張藝謀批評史》,張英、平客,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