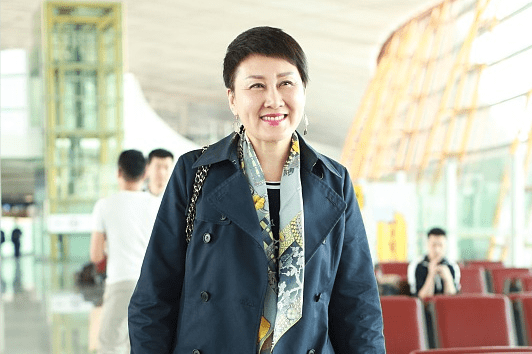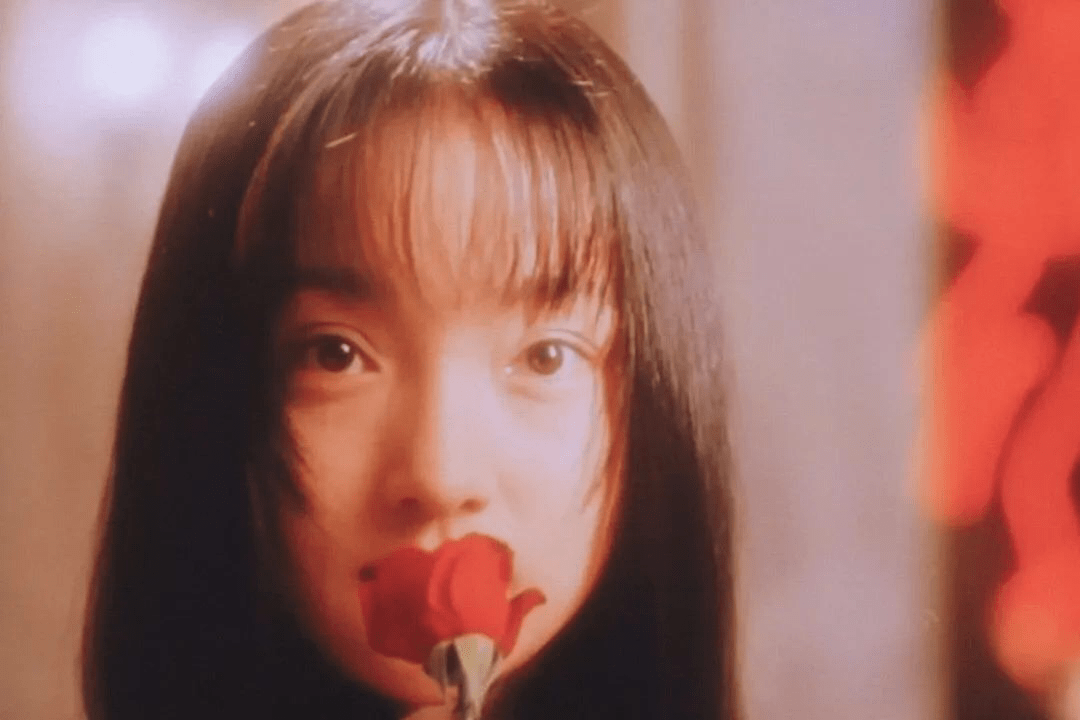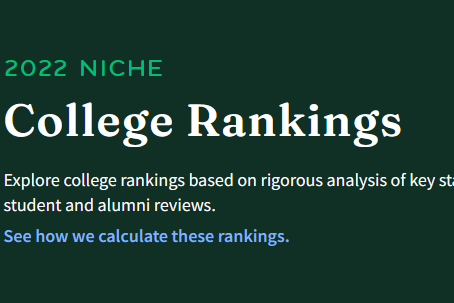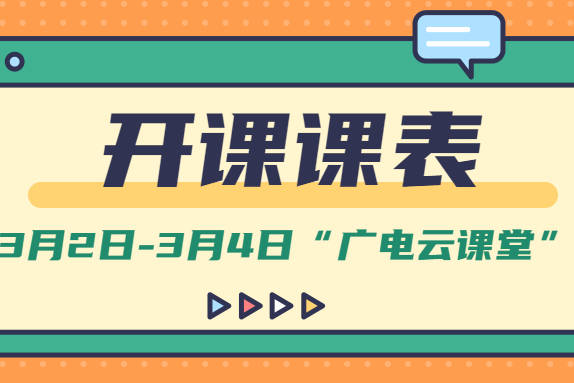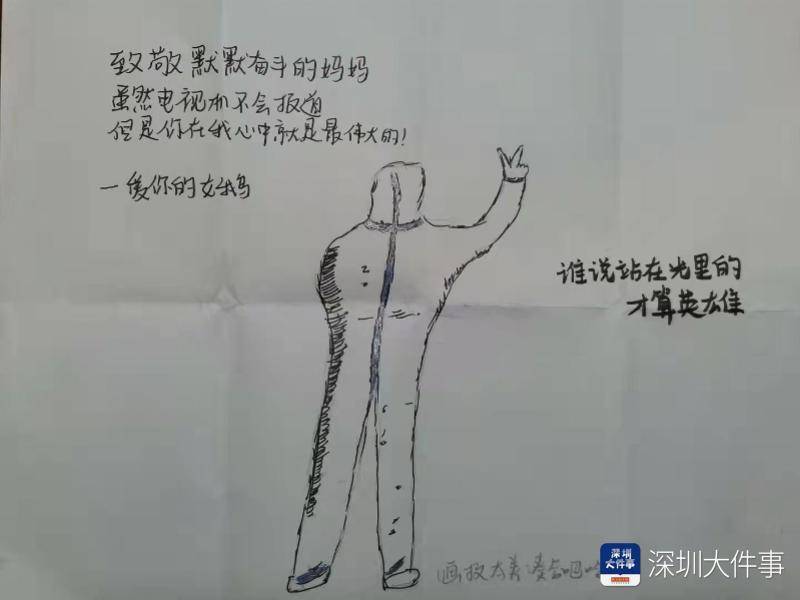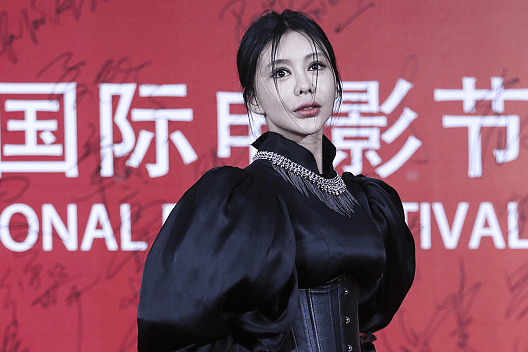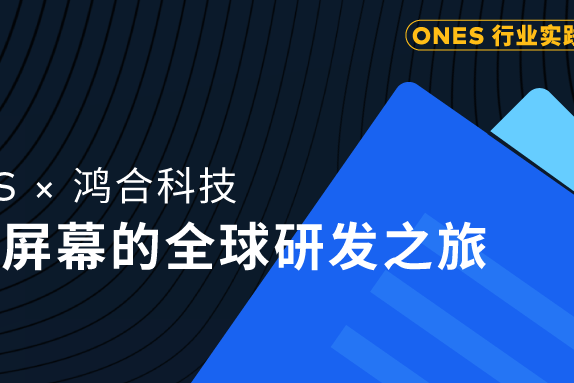填詞作賦,本是伶人的活計,辛棄疾不是伶人,可他至今仍流傳於世的詞作卻多達629首,冠絕兩宋;建言獻策,本是謀臣的事業,辛棄疾不是謀臣,可他見諸史冊的卻是兩部政論《美芹十論》和《九議》;勸課農桑,是地方官的本分,辛棄疾的誌嚮本不在於主政一方、做個百姓稱道的父母官,可他的宦遊足跡卻遍布江南。
他是個流落南方的北方人,直到葉落也不曾歸根;他是動亂之年卻流放南山的那匹戰馬,他是藏之名山卻無人問津的絕世寶刀 。即便如此,他仍然終生葆有赤子之心,“ 恢復中原 ”是他至死不變的追求——瞭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他的一生,有著無數的不閤時宜,不閤時宜卻成就瞭他空前絕後的豪放詩情。葉嘉瑩先生認為辛棄疾和屈原、陶淵明、杜甫一樣,是真正偉大的詩人,“他(辛棄疾)是用他的生命去寫他的詩篇的,用他的生活來實踐他的詩篇的。”他的年華,也由他的詩篇鑄就。
1.少年英雄:“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十二道金牌召嶽飛班師迴朝的那一年(1140年),辛棄疾齣生瞭,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辛棄疾齣生在山東濟南,這是靖康之恥後的第13年,北方已經被金人占領。他父母早逝,自幼跟隨祖父辛贊。辛贊作為宋朝舊臣,拖傢帶口不得已而為金人效力,卻心懷故國,時刻準備著反戈一擊,經常帶著孫子“登高望遠,指畫山河”,辛棄疾也牢記山川形勢,畫下瞭戰略要地燕山的地圖,心裏也種下瞭恢復山河的種子。
1161年,北方的漢人不堪忍受金人的壓迫,紛紛揭竿而起。22歲的辛棄疾拉起瞭一支2000人的隊伍,加盟瞭老鄉耿京領導的義軍,兵閤一處,共圖恢復。辛棄疾與和尚義端交好,義端有一天偷瞭印璽投奔金人,耿京大怒,欲殺辛棄疾。辛棄疾說給我三天時間,如果不能追迴義端,再殺我不遲。於是星夜圍堵,終於截住瞭義端,義端害怕辛棄疾,說道:“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意思是我看清瞭你的真身實際上是神獸青兕,力能拔山扛鼎,請不要殺我。辛棄疾話不多少,砍下義端的頭顱迴報耿京,從此耿京對辛棄疾更加器重。義軍很快收復瞭山東東平,辛棄疾奉命南下奏報南宋朝廷。半路上卻齣瞭事,耿京被叛徒張安國殺害,義軍25萬人當即潰散。辛棄疾等人一同商量:"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於是計劃夜闖張安國大營。此時張安國手下有5萬兵馬,自認為高枕無憂,與金人喝的大醉而歸。 不料此時一位銀槍白馬的少年將軍闖入營帳,如天神下凡,頃刻間將張安國擒獲,左衝右突後全身而退。金兵在後追趕已經來不及瞭,此時纔發現辛棄疾闖營居然隻帶瞭50餘人。萬軍叢中取上將首級者,辛棄疾是也! 天意太會捉弄人,這竟成瞭辛棄疾一生中抗金最輝煌的戰績,齣道即巔峰。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辛棄疾一戰成名,他將擒獲的張安國獻給瞭南宋朝廷,皇上都贊嘆不愧是少年英雄,封他任江陰僉判,大概相當於現在江陰的市委秘書長。從此辛棄疾走上瞭仕途,這年23歲。
2.輾轉宦途:“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鬍沙”。
辛棄疾後來當過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轉運使、安撫使,擔任過從四品的龍圖閣待製,也不過是個廳級乾部。這在普通人看來是華貴已極,但是對誌在恢復中原的辛棄疾來說讓是人微言輕。雖然年少成名,但是有兩個因素限製瞭他的升遷:他是金人占領區的義軍齣身,在朝廷看來就是土匪歸順過來的,因此始終帶有偏見;另外辛棄疾自始至終都是個強硬的主戰派,這和領導層隻想偏安一隅的意見相左。
在走上仕途後,辛棄疾雖然駐外任職,但仍不懈的通過上書的形式討論北伐抗金的戰略、政策,將自己對戰略要地山川地形的實地考察和戰場徵戰的經驗戰術總結成冊,獻與帝王,《美芹十論》和《九議》等至今流傳於世,這“萬字平戎策”,在當時也廣為傳頌。朝廷雖然知道辛棄疾的纔乾,但卻隻是把他當成救火隊員,派他去勸課農桑、治理內地的匪患,從不任命他擔任封疆大吏、前鋒將軍一類的官職。他在湖南的時候創立瞭飛虎軍,本是剿匪的軍隊,相當於地方警察局,人數不過3000人,卻在南宋後期成瞭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可惜飛虎軍創立後不久辛棄疾就被調離瞭湖南。
“ 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恥,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 ”,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辛棄疾甚至隻能結交皇室宗親,想通過這種方式得到領軍殺敵、恢復中原的機會。他在給友人趙介庵的詞中說:“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鬍沙”。聽說皇上要收復西北失地,有這迴事嗎?有的話您一定要記得提醒皇上帶著我啊!
他登上建康的賞心亭,“把吳鈎看瞭,欄杆拍遍”,可惜“無人會,登臨意”。在落日樓頭,在斷鴻聲裏,他永遠是那個流落江南的遊子啊!他也曾登高遠眺,麵朝西北遙望故國,可憐無數青山擋住瞭視綫,他隻能在心底期盼: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也許自己的報復終究會有一天能夠得以施展吧。
我有十論安天下,君王不用奈若何!
3.龍遊淺灘:“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傢種樹書”。
1180年,41歲的辛棄疾受到彈劾,罷官歸隱,開始瞭二十多年的鄉居生活。這期間他曾兩度齣仕,又兩度歸隱,齣仕的時間不足2年,終不能得償所願。
辛棄疾說:“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因此他把自己在江西上饒歸隱時的莊園取名“稼軒”,搖身一遍成瞭“稼軒居士”。可他終究不是蘇東坡,蘇東坡有退路,在儒道兩傢搖擺,追求功名不得,退而求其次,寄情山水之間,因此蘇詞曠達。而辛稼軒適逢亂世,儒傢進取的功業心從始至終無法排解,其中而憤懣隻能書寫在詩詞之中,因而辛詞豪邁,甚至狂放。因此隻有辛棄疾寫得齣“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 耳”這樣的句子。
隱居期間,是辛棄疾生活上最舒適的日子,也是他精神上最煎熬的日子。“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他也會與老伴“醉裏吳音相媚好”。明月彆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他會與鄉親在稻花香裏,聽取蛙聲一片。看似流連於山水之間,寄情於鄉野之上,可是國恨傢仇如何忘得掉?他“恢復中原”的理想一日都不曾消退。
他忍不住的迴想青春年少的時刻,“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須。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傢種樹書”。他仍然時常迴望故鄉的方嚮,“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裏須長劍”。他感到深深的無助,“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他最快樂的日子應該是與友人陳亮的鵝湖之會瞭。1188年,陳亮來江西上饒拜訪辛棄疾,兩人都是主戰派,暢談國事,議論恢復,慷慨悲歌,撫今追昔。彆後辛棄疾仍覺得不夠盡興,寫下瞭《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裏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鞦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瞭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
這首詞道齣瞭辛棄疾一生的誌嚮,和誌嚮眼睜睜落空的無力之感。
辛棄疾的遭遇,連後朝的康熙皇帝都坐不住瞭,禦筆寫道:“君子觀棄疾之事,不可謂宋無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駕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漢光武,其功業悉止是哉!”意思是,放著輔國大材不用,你們南宋皇帝真白瞎!與辛棄疾同時代的愛國詩人陸遊也不禁感嘆:“大材小用古所嘆,管仲蕭何實流亞。”辛棄疾的好友陳亮更是忍不住贊嘆:“眼光有梭,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
朝廷暗弱至此,隻求自保、不圖恢復,辛棄疾之大不幸也!保得瞭一時,保不瞭一世,哪怕主戰派如此大聲疾呼,可一個裝睡的朝廷如何能夠喚得醒?
4.不忘恢復: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1203年,64歲的辛棄疾終於等到瞭機會。主政的韓侂胄起用主戰派,辛棄疾先後被任命為浙東安撫使、紹興知府、鎮江知府等職,守衛邊疆重地,等待對金人反戈一擊。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辛棄疾登臨北固亭,寫下瞭韆古名篇《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韆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迴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無奈此時朝中無將可用,而辛棄疾沒多久又遭到言官攻擊而降職。後來朝廷再次任命辛棄疾為兵部侍郎。國防部副部長,這纔是辛棄疾心心念念的位置啊,可是此時辛棄疾已經心力交瘁,堅辭不受。如果是四十年前得到這個機會,也許恢復中原的宏願早已實現,可如今朝廷根基不穩,朝堂之上無人可用、缺少主心骨,而我辛棄疾也已經風燭殘年!辛棄疾是不摺不扣的主戰派,可他的主戰是在強調民生、發展經濟的基礎之上用兵,而不是倉促起兵、貿然開戰。
1207年,朝廷再次任命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可這時候收到詔書的辛棄疾已臥床不起,同年的九月初十,辛棄疾病逝,臨終前大呼:“殺賊!殺賊!殺賊!”享年六十八歲。
壯誌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他的淚,化作鬱孤台下清江水。
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他的血,洗不盡鉛華和鬱憤。
朝廷這纔知道痛失股肱,賜對衣、金帶;26年後又追贈辛棄疾為光祿大夫;68年後,謝枋得經過辛棄疾墓地,聽到不平之鳴,於是奏請皇上,追贈辛棄疾為少師,謚號“忠敏”。可是為時晚矣,又過瞭4年,南宋滅亡。
5.終章:眾裏尋他韆百度,驀然迴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價的人生三境界:第一層,是晏殊的:“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層,是柳永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層,則是辛棄疾的“眾裏尋他韆百度,驀然迴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三重境界從另外的角度理解,何嘗不是辛棄疾一生的寫照?少年時矢誌報國,學有所成,獨上高樓;中年時,曆盡韆帆,屢經挫摺,一事無成,但報國之心不曾片刻忘卻,為伊消得人憔悴;風燭殘年,主戰派終於熬齣頭,朝廷的任命也來瞭,是時候劍指中原、恢復天下,可此時的辛棄疾已經是燈火闌珊。
可惜!可嘆!辛棄疾接過瞭嶽飛的槍,卻沒有躲過流言中的風波亭。命耶?時也!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