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翎均一奚暉城破瞭。這是我們忽桓人供奉百年的聖城 它的覆滅意味著忽桓自此亡國。於是 短篇小說:西風起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8/2022, 2:09:34 PM
翎均
一
奚暉城破瞭。
這是我們忽桓人供奉百年的聖城,它的覆滅意味著忽桓自此亡國。於是,在接下來的七個晝夜,大魏鐵騎踏遍我們的疆土,這個以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原強國揮動著腥臭的陌刀,發動瞭近乎野蠻的屠殺。
忽桓王室中的精壯男子拋棄臣民,縋城而逃,但也有逃不走的弱小,比如我,比如我懷中這尚未足歲的男嬰。
我倉皇奔走,一路穿行烈火狂沙,荒漠白骨,身後是殺紅瞭眼的大魏士兵,最後到底被他們圍堵在河堤上。隨著一聲懶洋洋的嬰兒啼哭,我痛叫齣聲,繈褓被他��拋進河川,很快為猛浪所吞沒。
稚子何辜?中原人成天掛在嘴邊的道德仁義,在戰爭麵前,原來也都隻是妄語罷瞭。
忽桓女子以容貌妖嬈聞名天下,自然成瞭眾將爭搶的戰利品,我並不好看,當夜卻也被帶進瞭大魏軍營。大概因先前我抱著小王子齣逃,大魏主將對我的身份頗感興趣。
月光如霜覆在戈壁狹道,兩側的韆帳燈曖昧地搖曳,隱約可聞女子破碎的哭泣聲。心驚肉跳都不足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尤其當我走到大魏主將嶽淵麵前時,一顆心幾乎蹦齣唇舌,隻覺得自己見到的是剛從地獄歸來的鬼。
���昝把痰幕鷳�之後,一位身披九重鶴裘的男子倚在禪椅上,他手握書簡,容顔清俊卻殊無血色,漆黑的眼窩深陷,咳嗽起來驚天動地,我甚至覺得自己呼吸再粗重一些,他那虛有其錶的偉岸骨架就能被我吹散。
嶽淵抬起眼,單刀直入地問我的姓氏。
忽桓崇尚貴族通婚,姓氏足以象徵一個女子的身份,而這直接關係到我會被獻給一位風雅王親,還是被塞給一名粗獷伍長。但我隻是沉默――我嚮來笨嘴拙舌,唯恐禍從口齣。
“或許她聽不懂官話?”帳內另一側的校尉嘆道,“忽桓貴族亦通漢學,看來她隻是侍奉王族的低賤婢女。”
還真被他猜對瞭。
嶽淵似乎覺得掃興,復又垂眼看書:“那便賞你吧。”
那校尉一愣,沒反應過來似的,等他反應過來便來拽我的腕子。我立刻一個激靈,發瞭狠地掙脫開,踉蹌地跪迴嶽淵跟前,抬手擼下發繩,萬韆青絲垂落――絲發被兩肩,何處不可憐。這是再明顯不過的暗示,我隻願服侍他。
我真是豁齣去瞭,可嶽淵隻是無奈地搖頭:“不是我不想……”他停頓半晌,又玩味地輕笑,“我是不行。”
大概無形中有誰燒瞭塊鐵,想將我的厚臉皮烙薄一些。很快地,嶽淵那鋥亮如寶石的眼中就映齣瞭我那張目瞪口呆的紅臉。
“瞧瞧,”他已恢復漠然的神色,偏頭看嚮同樣呆若木雞的校尉,“她聽得懂。”
二
半月後,我隨嶽淵迴瞭大魏國都。
誰都知道嶽淵不近女色,我的到來大概讓所有人震驚並好奇著。然而,我卻令大傢失望瞭――嶽淵眼睛沒瞎,他韆裏迢迢把我帶迴來,並沒有納我為姬妾的打算,隻將我丟進僕役班底,成日支使我伺候灑掃、端茶送水。
我倒沒怎樣,可國都上下卻都對此不勝唏噓並且更加確信――這病癆鬼似的嶽將軍,果然有隱疾!
流言繪聲繪色,據聞與嶽淵有婚約的高陸公主聽後氣得肝顫,她是天子愛女,鬧騰起來闔宮都雞犬不寜。世人都道這迴公主怕是要退婚瞭。
然而,皇傢私事終究不宜過度探究,嶽淵對此又毫無反應,所以我也不好多問。
我初來乍到,卻朋友不少,或許是我奇貨可居,在忽桓被視作下品的皮相也漸漸被嶽府僕役們稱之為清秀。對此我挺受用,可惜他們也總愛對我的姓氏糾纏不休。
我不僅嘴笨,記性也不太好。某天舊話重提,我嚼著瓜子瓤,口齒不清地隨口答道:“我姓錢。”
有人立時指著我嚷道:“前些天你分明還說自己姓趙的!”
我心虛,挪步後退時被一地瓜子殼的聲響齣賣。起哄引來管傢問詢,我們便被帶到瞭嶽淵麵前。他沉默著聽完始末,那仿佛偷來辰光的一雙眼被蒼白的病容反襯得格外銳利,上下審視時像是能將我搜颳得一乾二淨。
“趙錢孫李,心繭這撒謊成性的丫頭倒是將咱們中原的百傢姓記得不錯。隻怕再過數月,她就能冠以大魏國姓,和天子做一傢人瞭!”管傢嗤之以鼻,旁人紛紛應和。
而嶽淵隻是清淡的一眼掠過去,誰都不敢再說話。他撫著襟袖上脫瞭絲的勾雲紋,冷笑道:“真正會撒謊的人,可不像她這樣……”他眉心一皺,蹦齣瞭個言簡意賅的定論,“蠢。”
眾人敗興而歸,獨留我垂頭喪氣地瞅著嶽淵襟袖上那片歪七扭八的雲紋。沒錯,這衣裳是我洗的……
“忽桓王宮的禦用婢女?”嶽淵笑著拿話柄敲打我。
“是。”我真沒撒謊。
“傢務瑣事樣樣精通?”
這下我就慚愧瞭:“漢人服飾太過繁復,我隻是還沒、沒掌握好洗濯技巧……”
可他探究的目光中仍藏著刀,燒著火,我垂著頭,連心都開始發顫,幾乎就要開口求饒。可當我終於抬起頭,他卻又忽地側過臉去,有一閃而逝的慌亂,語氣極不自在:“知道瞭。”
待我齣瞭門,莫名地西風起,將兩朵杜若自我的鬢發吹落。
我原打算摺返,嚮嶽淵請教它的來源,未料又有一人匆忙來見。
來人名叫孫�A,是奚暉城破時嶽淵帳中的校尉。這段時日他神齣鬼沒,原來是去徹查忽桓王室的譜係瞭,看來嶽淵仍舊懷疑精通官話的我齣身貴戚。但他們必然是要失望瞭,就算重迴奚暉城,將王宮挖地三尺,他們也注定找不齣有關我這種無名小卒的蛛絲馬跡。
孫�A憂心忡忡地道:“那麼,就隻剩一種可能。”
忽桓自古善戰,因而將門的地位甚至能與王族比肩。六年前,趁著大魏朝局動蕩,我族第一將門鍾離氏領兵進犯大魏邊界重鎮西北九城,雖然此戰以忽桓兵敗告終,但著實重創瞭大魏,令後者足有六年不敢再起乾戈,大魏百姓甚至聽“鍾離”而膽寒。
“忽桓王室積弱,為瞭拉攏兼挾製,常年把將門子女養在王宮。這恐怕就是國破之時,心繭姑娘抱著小王子的原因。”孫�A冷靜地分析,“否則為何她總對自己的姓氏諱莫如深?將軍,若她真的姓鍾離,留著她,大禍將至啊!”
我扒著窗欞偷聽到這裏,不由自主地十指箍緊、冷汗淋灕。可嶽淵隻是不以為然地漫笑:“即便我沒將她帶迴來,你以為,我的大禍就能逃得掉嗎?”
他說的大禍,乃是天子之怒。
誠然這迴他滅瞭忽桓,功勛卓著,可惜他成名過早,封爵賞賜已然無以復加,而世事月滿則虧,但凡他有一丁點兒閃失,就足以韆夫所指。
何況是屠城這等喪盡天良的惡行。
當今天子原是庶齣,趁著六年前大魏朝局動蕩,纔從嫡長兄手中僥幸奪來皇位,因而患得患失,極重聲名。這日,我聽說天子在早朝上摔瞭奏章,指著麵前的年輕將軍怒道:“早跟你說瞭,勿傷無辜,勿亂民心,可你居然敢屠城!這與忽桓蠻族有何區彆?這又讓那些尚在觀望大魏天子是否仁德的小國和異族,如何肯歸附於朕!”
嶽淵隻一笑,眼神卻又毒又冷,在滿朝瞠目結舌的注視下俯首作揖,便擅自走瞭乾淨。
天子癱坐進龍椅,痛惜地嚮眾臣嘆道:“收繮為良臣,脫轅則禍國。這樣一個不世齣的神將若往邪處偏瞭去,為之奈何啊……”
三
天子的一句“不世齣”絕非過譽,嶽淵成名早,早到六年前,也就是他十七歲時,便在石破天驚的西北九城一戰中威震四方,被冠以“神將”之名載入史冊。
後來,他的神跡傳入忽桓,在被我翻爛瞭的話本子裏,編纂者不厭其煩地渲染他如何受神�o眷顧,如何意氣風發、含威不露,幾乎把少不更事的我說得恨不能叛逃忽桓,遠赴大魏一睹他的風采。
據說忽桓女子長日無事,也總愛拿大魏嶽氏與我們忽桓的鍾離氏做比較,比這名將輩齣的兩大將門孰優孰劣,比誰傢少年郎更英勇,更俊美。
幸運的是,這兩方終有一日狹路相逢。而不幸卻在於,這相逢未免太慘烈。
那正是六年前的深鼕,三十萬人永遠埋葬在瞭西北九城。嶽淵與鍾離氏的一位少年是戰場上僅剩的兩人,他們披發浴血,戰至力竭,最後是嶽淵技高一籌將對方斬殺,奠定勝局。
可無論後來大魏史傢和民間如何傳唱嶽淵的英名,將這場險勝到毫無戰果的戰役神化,都改變不瞭他父兄慘死,他也被鍾離氏臨死前的一刀斬斷筋骨,終生不愈的事實。他在屍堆中爬瞭十天九夜,靠吞食部下的腐肉苟活,幸有忠誠的戰馬將他馱迴。大魏都城的守將起初拒絕迎他入城,或許是因為那時不成人形的他,看上去更像孤魂野鬼。
而這背後的慘烈,屬於戰爭最原始的狼狽和殘酷,大魏天子卻並不需要。他狼毫一揮,隻留下嶽淵劈關斬將,有如神助一般的傳奇――天子便是這個神,那時他纔篡瞭長兄的位,急需這樣一個神話佐證自己繼位乃上天授意,實至名歸。
世間哪有神?嶽淵的神將之名,其實隻是沾瞭天子的光。
但他也確實是韆載難遇的將纔,即便後來纏綿病榻,竟也能運籌帷幄,將天下戰局握於股掌,纔有瞭這迴的大破奚暉城,滅亡忽桓。
天子惜纔,再有高陸公主這層關係,所以即便此番嶽淵屠城引來天下物議,天子仍是多加寬縱,隻扣他兩年俸祿,官降一級便罷。
嶽淵依舊漠然置之,孫�A卻急齣瞭一頭汗:“陛下雖顧念將軍,可難免心生猜忌。積羽沉舟,心繭姑娘還是留不得。”
嶽淵捧起那碗我纔做好的銀耳甜羹品嘗片刻,神情逐漸古怪,便不耐煩地反駁:“鍾離氏這輩沒有女孩,你應該早就查齣來瞭纔對。”
“即便如此,您於忽桓而言也是滅族仇人,末將隻怕她會對您不利……”
孫�A自討沒趣,他告退之後,嶽淵纔提聲問:“聽夠瞭?”
我大驚,摸著門沿進屋後仍在疑惑為何會露餡。他讀心似地眼風一斜,我就瞧見瞭自己過往偷聽時,因過分緊張而將手摳進窗欞糊紙之中的指印……
確實蠢。我暗暗將自己罵完,便將十指勾在背後,跪下來等他發落。
他握拳於胸前,狠狠地咳瞭幾聲,問:“知錯沒有?”
死到臨頭,我連說話都不會瞭,隻是點頭。而他敲著碗沿,又說:“糖和鹽,你去廚房請教一下,該怎麼分辨!”
我猛地抬眼,訥訥地應瞭一聲,他便寬慰般摸瞭摸我的頭,道:“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話畢又細品起那碗鹹羹,還不吝誇我兩句,誇得我毛骨悚然。
多滑稽,說謊的總是我,可到頭來,我卻反被他一直耍弄著。
“我知道自己蠢,漏洞百齣,將軍為何不揭穿我,反而總愛任我齣醜,看我笑話?”我忍無可忍,“你怎麼就不問問我是誰?你就不怕我會殺瞭你,為忽桓報仇?”
他握勺攪羹的手驀然一頓,卻說:“我是死過一次的人。”
我不解,他遂又解釋道:“死過一次纔明白過來,世間很多事是經不起探究的。我的腳下匍匐著很多人,他們崇拜奉承我,說的好像都是真話,可我隻覺被豺虎覬覦。而你這蠢丫頭卻讓人以假觀真,我反而覺得安心。”
“你瞧,你一定是將什麼銳器藏於袖中,纔會這樣藏著掖著,隻敢將手背在身後。”
我嚇得一抽,刀刃就乖乖地自袖管滑落。他俯身撿起那生銹的刀,將刃按在手背磨瞭半晌,居然連皮都無法割破。
“真蠢。”他眸光柔和,彎唇笑起來。
四
我十歲那年,父親和哥哥因捲入禍事殞命,那時灼燙的鮮血糊進我的眼,從此燒壞瞭我對他們所有的記憶。
因此,我並非存心隱瞞自己的姓氏,而是確實不記得。旁人百般催問,我沒辦法,纔鬍亂采用瞭祖母的趙姓和母親的錢姓。
傢變過後,女眷都被賤賣進瞭忽桓王宮。從前我的傢族應當頗為富足,因為不隻是我,祖母和母親都是典型的養尊處優、四體不勤,因此受盡欺淩。祖母年事已高,經不得摧殘,她病倒後我到處哭求良藥而不得,絕境中有人為我指瞭明路――那時忽桓纔在西北九城一戰中敗北,急需皮相乾淨,甘願賣身賣命的死士。
我沒法不同意。
所以,明麵上我是王宮中最普通的婢女,私下裏卻還有著另一重極隱秘的身份。
都說尤物善惑,殺人百遍,那些國破之時被強掠而走的忽桓女子,其實也都是這樣的秘密死士,通官話,懂媚術。先前說過,奚暉城破之夜,忽桓王族並未被趕盡殺絕,而後他們四處遊說,秣馬厲兵。復國的計劃很多,而這些死士是最關鍵的一步棋。
凱鏇的大魏將領們將這些美人搶迴國都,風光一時,從此卻傢宅不寜,仕途失意,乃至丟瞭性命,竟也沒狠下心去懷疑酣睡的枕邊人。
但無論如何,死士不會有活路,她們遲早會被殺或自殺,以保全主子。
而我接到的任務就是嶽淵,這也是當初我厚著臉皮非要委身於他的緣故。誠然我做婢女做得很爛,但這不妨礙我做死士做得更爛……我的不作為終於令主子惱怒,祖母和母親尚在他們手中為質,我終究還是朝嶽淵亮齣瞭刀。
我知道自己蠢,注定失敗,但說到底,還是我不願意。緣由羞於啓齒,除瞭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更多的,還是因為我貪生怕死。
我坦誠瞭自己的過去,又問嶽淵:“作為死士,我卻非常畏懼死亡,很可笑吧?”
“我不這麼認為。作為武將,我亦怕戰爭。”他粗糙的指尖探入我的發,在我震驚的仰望下續道,“天底下沒有誰,閤該為另一個人賣命,即便是庶民與天子。性命沒有貴賤。”
無論大魏還是忽桓,這番言辭都是十惡不赦的不忠不義。但他心懷天下,說得這樣坦然。
其實我都知道的,先前屠城非他所願,而是聖旨命令。可天子既垂涎忽桓的珍寶和美人,又要仁義之名,所以擔盡罪名的隻能是嶽淵。他那樣苦,卻從來不說。
我此生一無是處,唯一拿得齣手的,大概就是仰慕著這樣一個人。
“尋常人賣給主子,就等於把命賣瞭,可在我這裏不是這樣。奚暉城破時你既選擇服侍我,那麼從今往後你的主子就是我。你的命不是我的,而是我們的命從此綁在瞭一塊兒。”他抽手將我的發繩扯落,在彼此腕上熟稔地係瞭個結。我的頰腮燥熱難忍,而他波瀾不驚,隻是微笑,“就像這樣。”
他一諾韆金,親信和軍隊又遍布四方,果真很快就有祖母和母親所在的消息傳來――竟還是在西北九城。
我深知那地方對嶽淵意味著什麼,因此萌生退意,他卻仍安慰我:“這麼多年過去,再恐懼,也淡瞭。”
話雖如此,可我明顯地看齣他日漸焦躁不安,麵有懼色。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車馬行進瞭十天,他咳瞭十天,最後一夜,我纔以手捧住他嘔齣的血,下一刻就有喊殺聲四起。埋伏的鐵麵殺手傾巢而齣,嶽淵已被宿疾摺磨得麵無人色,卻仍能冷靜地督戰,以兩百部下成功擊破對方韆人圍睏。
但到底還是寡不敵眾,最後隻剩我一人伴他逃亡。
良駒亦中毒箭,失去方嚮地逃竄,我們共乘一騎,他的血仍在浸透我的衣。我身心涼透,始終弄不明白這些忽桓殺手為何會知道我們的行蹤。這讓我尤為恐懼,卻不是怕死,而是怕嶽淵,怕他不信我。
“彆怕。”他還是輕易將我看穿,笑意慘白,連喘息都帶著血氣,“這些殺手不是忽桓人,他們是……陛下的血滴子。”
他功高震主,難以掌控,天子又怕有朝一日屠城的機密會大白天下,遂狠心滅口。
“忽桓也好,大魏也罷,大約人人都要我死。”
“至少,我永遠不會。”
良駒徹底失控,我們墜下瞭山崖,沒死。
倒不是我們命大,隻因這裏也是六年前開闢齣來的一處戰場,是以坡勢平緩,夠我倆勉強著陸。
山榖中多歧路,又遍布毒蟲和荊棘,跋涉不易。再有先前沿坡下墜時他緊抱我,獨自承受瞭所有粗枝和尖石的撞擊,因而背部潰爛,轟轟烈烈地發起瞭高熱。
我們白天艱難地行進,夜裏就睡在樹洞裏,我總要醒轉多次,心驚膽戰地確認他是否還有呼吸。從前我五榖不分,而今百草嘗遍,能極快地找齣食物和藥草。
那是睏在山榖的第二十日,我還學會瞭狩獵,可當我捧著盛滿烤肉的荷葉包興衝衝地摺返時,樹洞中卻已空無一人。
我慌瞭神,找至暮色四閤,纔終於在一座孤塚前發現嶽淵蕭索的背影。
墓碑上的字跡清晰,竟是鍾離氏之墓。鏇即我也看清瞭嶽淵的指尖滴著血,顯見得方纔他徒手刨開墳塚,大概是想將對方拖齣來挫骨揚灰。
突然,他幽幽地迴首,臉上卻不是我所預想的怒色,反倒茫然、淒惶,還反復低語著:“這具鍾離氏的白骨,怎麼會穿著印有嶽氏族徽的鎧甲入葬?怎麼會……”
我心下駭然,衝上前去翻看那具白骨,一塊令牌自腐朽的鎧甲中掉落,入木三分地刻著白骨的生前姓名。正是嶽淵。
我不知所措地抬眸,對上一雙同樣腥紅的眼睛。
“嶽淵死在瞭六年前。那麼,我又是誰?”
五
事已至此,真相再不容辯駁。
西北九城之戰,最後決鬥的兩位少年之中,技高一籌的其實是鍾離氏,活下來的,也一直是他。
嶽淵生前的戰馬卻錯認他為主人馱迴瞭大魏國都,那時守城將之所以拒絕迎他入城,必定是一眼就認齣瞭他是忽桓人。
可天子聞訊後卻迅速封鎖瞭消息,他原本苦候一份捷報,誰知等來的卻是大魏全軍覆沒的噩耗。權衡不過一瞬之間,於是方士、巫醫和巧匠陸續被迎入宮中,洗去重傷少年的記憶,重塑他的容貌,讓他成為得勝而歸的“嶽淵”,再矯造鍾離氏的墓碑,混淆天下視聽。如此,既用傳奇般的勝仗為天子上不瞭台麵的篡位賦予神性,又收瞭一位韆載難逢的敵方良將為己所用。一箭雙雕,何其完美!
而被耍弄,被利用,及至如今被捨棄,永遠都隻是棋子的命運。我是,他也是。
走齣山榖後,他遠遠地走在前頭,不再開口同我說話。
六年來,他的臉是宿敵生前的模樣,他效忠的是敵國帝王。更可悲的是,滅瞭故土忽桓的人也正是他自己。這樣的打擊和恥辱,想必更甚摧筋斷骨。
可於我而言,�s卑鄙地湧齣一絲慶幸來。原來我們都是忽桓人,有相同的族群和立場,那麼我也就可以拋卻顧忌,和他成為一樣的人,甚至是――傢人。
他越走越快,加速尚未痊愈的傷口崩裂,終於受不住似地垮瞭下來。我撲嚮前相扶,脫口而齣喚道:“鍾離將軍。”
他卻揚手將我推開,厲聲喝道:“閉嘴!”
我不由得愣在原地。
“即便從前我確實是忽桓人又如何?國破傢滅,我甚至不記得自己的名字……”他側眸看我,竟有譏誚的弧度浮上唇角,“就像你不記得自己的姓一樣。”
他陡然轉冷的神情令我心驚。
“連完整的姓名都不配擁有,注定隻能受人擺布。”他推開我,繼續走,隻留下一個堅定卻陰鷙的背影,“所以我是嶽淵,也隻能是嶽淵。”
這份打擊太沉重瞭,他隻是一時反應不過來……我這樣安慰自己。
纔迴國都,嶽府竟已被宮中禁衛團團圍住。先前血滴子刺殺失敗,想來天子不肯罷休,誓要將嶽淵逼上絕境。
我咬牙捏緊袖中鈍刀,決定以性命為代價製造混亂,替他開闢一道逃生之路。
此前我從未想過自己有這樣一往無前的力量,為我心上的那個人。在砍傷七位禁衛之後,我被製伏在地,門牙觸地磕齣一攤血,腥氣卻被一陣颳過眼簾的香風掩蓋――高陸公主噙著淚撲進嶽淵懷中,哭得肝腸寸斷,為他的死裏逃生。
我曾聽人說過,嶽淵待高陸公主嚮來不上心,不耐煩,可此刻他卻抬起布滿血痂的手撫上她縴弱的背脊,柔聲勸慰。
我終於意會到自己衝動太過,原來這些禁衛與天子無關,而是為瞭保護公主。
砍傷禁衛,意圖不軌,說重瞭,罪名足以殺頭。
高陸公主拿眼刀剜我,神態卻如幼鹿,一派睏惑天真,隻歪著腦袋細聲問:“嶽傢哥哥,這就是那忽桓姑娘?”
嶽淵不屑地冷笑一聲,眼風往我這處掃過來時像是萬點冰刃。
“一個瘋丫頭罷瞭。”
六
曆史由勝者書寫,道理也由強者製訂,因此嶽淵說我瘋瞭,那我就是瘋瞭,說的話、做的事,統統不可信。
我豈料他��怯懦到這等地步,唯恐我將真相公之於眾,將他推入深淵。
過往孤身麵對韆軍萬馬都不曾皺過眉頭的男子,如今卻將懦弱和恐懼盡數獻給瞭權勢和榮華。天意如刀,實在諷刺。
可隻要他一句話,我就絕不會泄露一個字。除瞭祖母和母親,我無牽無掛,更沒有誓死效忠的國度和君王。我隻是純粹地仰慕他這個人而已。
我不會逼他重拾國仇,不會要他穿上鍾離氏的戰鎧,為流離失所的忽桓王族誓死一戰。我隻是期盼著證明,我們是一樣的人。可當我叫齣那聲“鍾離將軍”時,他卻說“閉嘴”。
如今看來,這兩字還有另一層含義:你錯瞭,我們不一樣。
因砍傷禁衛,衝撞公主,我被關入暗牢,嶽淵也懶於再見我。
直到與高陸公主的婚期敲定那日,他纔親自屈尊而來宣布喜訊。我從抱膝的姿態艱難地抬頭,就見他正站在華光中央,像是神�o無意流連世間,不容逼視。我如今纔發覺,身前愈光明,身後陰影必然就會愈黑暗,就像他。可惜我一直太蠢。
原來我隻是被話本子騙瞭,明知神話都是妄言,偏要迷信。我其實從來不認識他。
我初至國都時謠言四起,傳聞高陸公主為瞭與嶽淵退婚鬧得很凶。如今我纔知想退婚的是天子,高陸公主鬧,鬧的是非要嫁給嶽淵。我在暗牢裏苦中作樂,懷疑起她與我讀過的話本子是否為同一本,纔會深受荼毒,九死不悔。
前有公主癡心不改,後來血滴子又無功而返,天子便擅自揭過瞭先前那場搬不上台麵的暗殺,嶽淵也很識趣地不提。於是,君賢臣忠,朝堂之上又是一派昌平氣象。
“你分明不喜歡高陸公主的,如今卻為瞭保全自己,寜可同仇傢做翁婿。”我抬手捂住眼睛,沒有淚湧齣,它們都被我逼迴瞭心髒,“將軍,你已心盲,找不到迴傢的路瞭。”
他避重就輕,隻揪著我的第一句話反問:“誰告訴你,我不喜歡高陸?”
我抬手,腕間紅繩仍是那迴他親手綁上的相思結:“這是忽桓男女定情時纔有的習俗,就算你不承認自己是忽桓人,但你的意識不會說謊。”
“所以,你認為,我心上的人是你?”他咳嗽不止,險些笑齣淚來,“果然是蠢丫頭啊。所以,你大概從沒發覺,你同高陸其實長得有些像。”
原來如此。
“現下你身陷囹圄,應該難以探聽外事纔對。讓我想想,告訴你這些事的人,是孫�A?”聞言,我劇烈地發起抖來,更讓他確信,“想必他很喜歡你,什麼都告訴你。我現在倒是懷疑,當初遭血滴子伏擊,是不是他把我的行蹤泄露給陛下的。”
這也是我曾懷疑過的。嶽淵說得沒錯,自我進瞭嶽府,孫�A予我諸多關照,我不是沒懷疑過他總想趕走我的居心,懷疑過他是天子安插在嶽淵身邊的眼綫,每當我同他說話,他也總是神情閃爍。
但他其實又是個很單純的人,當我說齣自己的猜忌時,他急得幾乎要哭:“我和你一樣,絕不會傷害將軍!”所以我相信他。
我知道自己傻,但再傻也傻不過這一刻瞭。嶽淵冷下臉要走,我居然還不死心地挽留:“將軍,隻要你迴頭,我還是想、想帶你迴傢。”
可他又哪裏肯迴頭。
七
該年暮夏,高陸公主嫁入嶽府,我是從暗牢穹頂的天窗崩下來的茉莉花瓣和爆竹屑得知的。孫�A再也沒能為我帶來消息,或許已遭不測。
這是我最後一次慟哭。
每日送餿飯的僕役倒是嘴碎起來,當然,內容都是我不愛聽的。
他們說,將軍改邪歸正,總算好好聽陛下的話瞭。翁婿聯手發兵,徵討四方,成果斐然。
他們也說,將軍哪是不行呀?婚房夜夜紅燭燒盡,翌日公主的嬌容上也總會浮現相同的紅暈,教人好不欽羨。
他們居心叵測地等待我的反應,可我隻是麻木。但為瞭讓他們盡快心滿意足地離去,我便攥拳狠狠詛咒瞭嶽府主人,詛咒大魏天子,詛咒這黑白顛倒的天下――皆不得太平。
於是,他們都說,我是真的瘋瞭。可我的瘋話最後卻一一應驗。
深鞦,高陸公主暴斃。我仍是從天窗得知外頭的季節和變故,這迴飄下來的除瞭風乾的桂花,還有白幡和紙錢。
也是自那日起,夜半夢醒時我總能瞧見嶽淵。他痛失愛妻,憔悴更甚以往,醉得離譜的時候還會來撫我的臉。對於長得像高陸公主這件事,我一直深切痛恨。
公主的死割斷瞭君臣間的虛情假意。天子有三子一女,三子早夭,他其實極有可能力排眾議冊封高陸為儲君。可如今他斷子絕孫,朝臣卻隻是嚴肅冷漠地進諫他或可效仿先帝,兄終弟及。
而這正是天子的心魔。他窮極一生纔篡瞭長兄的位,臨瞭卻要他將畢生心血拱手讓人,這又怎麼可能?
然而,翌年仲春,公主百日喪期剛結束,萬念俱灰、日漸荒淫的天子就被勒殺於寢宮。追其緣由,正是嶽淵做瞭那根牆頭草,裏應外閤,放任天子的胞弟入宮行凶。
經此一變,所有魏姓宗親都覺得自己其實也是有登基資格的,於是諸王造反,國都大亂。我便趁機沐著天窗飄落的梔子花雨,成功逃齣瞭暗牢。
之後,嶽淵仍在不斷地投靠強者,齣賣舊主。神話傾塌,他成瞭名副其實的邪佞。皇位不斷易主,到瞭最後,我甚至都算不清楚新帝與從前的天子還有沒有半點血緣關係。
而嶽淵算計瞭太多人,最後也終於被人狠狠算計。某次他齣徵時遭敵軍突襲,受睏孤城,力戰而亡,新帝卻始終袖手旁觀。
再難的戰局他都曾輕易破解,如今卻死得這樣可笑輕易。史書重修,話本改寫,他終將遺臭萬年。
彼時我已迴到忽桓,祖母和母親過世後,我又撫養瞭一個男孩,與一位故人搭瞭兩座小院,相互扶持著度過瞭六年之久。
大約是西北風沙催人老,前塵往事漸漸被吹得模糊,所以當故人問我是否要去幫嶽淵收殮屍骨時,我迷惘瞭許久。我已感受不到喜悲,可當我遠眺空�髟撲�,衰草連天,卻還是莫名地眼角酸脹。
“也罷。”
我終歸不忍心,不忍他生生死死,魂飛魄散,都迴不瞭傢啊。
八
將軍的屍骨收迴來的次年,她重病彌留,瞳仁依�f澄澈,眸光錯落間仍藏著一隻久遠的飲溪幼鹿,總要問我:“你是誰?”
“我是孫�A。”
可她不記得我的名字瞭,就像她也記不起嶽淵是誰一樣。她這一生,記憶丟失過兩迴。一迴在她十歲那年,另一迴則是七年前,將軍請來方士封住瞭她的記憶。
“沒必要讓她記住那樣痛苦的過去瞭,包括我。”將軍對我說。
我自十四歲起跟在將軍身側,從無二心,直到奚暉城破那夜,她無意嚮我掃來瞭驚濤駭浪的一眼。於是,我鬼迷心竅,編造她特殊的身份,想方設法想將她趕齣嶽府,因為隻有那樣,我纔有機會接近她。
可將軍何等睿智,他看穿瞭我,卻又不點破,反而對我說:“忽桓王室譜係翻完瞭,有時間,也查查大魏吧。”
我腦子不靈光,萬分不解,他又續道:“若我沒記錯,先皇後姓錢,而先帝生母,則是趙太後。當今天子篡位,與西北九城之戰都發生在六年前,心繭也正是那年遭遇‘傢變,忘卻前事,隨祖母和母親逃亡西北。那年她十歲,而今,她恰好十六。”
“她是先帝之女,大魏嫡係血脈。”
起初我死活不信,直到我查遍皇族曆史,又見到瞭高陸公主。作為堂姊妹,她們確實挺像。
“天子多疑陰毒,她的處境太危險。”自確認她的真實身份後,將軍日漸焦躁不安。
而後他們遭遇血滴子,她是看不齣,可將軍身經百戰,僅從招術就能判斷齣殺手並非為他而來,而是想要殺瞭她。他最害怕的事還是發生瞭。
暗殺是高陸公主的意思,因為嫉妒;也是天子的意思,因為恐懼。
遇險後,他們發現瞭一座墳塚,自此將軍性情大變。但以我對將軍的瞭解,他不是個會為身外俗事羈絆的人。可他需要拿此事做個由頭,一個疏遠她的由頭。
而後她衝撞公主,他對外宣稱將她處死,其實是在書院下方鑿瞭暗室將她護住。我總見他獨立院中,落寞地往一方地窗拋擲落花,那是他在告知她四時更迭。
他一直拒絕我見她。是第一次,我從這個風雨不動的男人眼裏看到脆弱和哀求:“我隻剩這些時日瞭。往後,便是你看著她瞭。”
可我又何德何能?
我隱隱猜到他要做什麼,那太可怕瞭,可他渾然不懼,天底下能讓他害怕的隻有她的安危。他會替她報父仇,可這還不夠,下一任天子是否還會忌憚著她?於是,他朝秦暮楚,見異思遷,蓄意引導魏姓皇族惡鬥,待國都徹底洗牌,新帝想必與先帝親緣極淡,不會再記得她這個遙遠的嫡係血脈。
最後,新帝確實不記得她瞭,卻也沒有放過他。
“上位者鄙,我一世為棋,身不由己。可我心上的小丫頭,她不可以。”
他很清楚自己的下場,所以暗牢裏的那些時日,他一直陪在她身邊。而僕役們嚼舌根時所說的婚房夜夜紅燭燒盡,其實都有賴巫醫焚製秘香,供高陸公主做盡黃粱美夢。
當我踏入暗牢要接走她的那夜,將軍起初沒能察覺我的到來,一串淩亂的吻從她熟睡的眉心吻到鎖骨,眼看就要解瞭她的衣扣,我嚇得緊忙捂住眼。他聽聞動靜,這纔如夢初醒,苦笑道:“真不是我不行……可我不敢。”
“丫頭,你有姓,是堂堂國姓,你叫魏心繭。有瞭完整的姓名,往後就不要再為人擺布。要好好活著。”他以額相觸,對仍在夢中的她輕聲道齣此生最後一句話。
後來,我帶她去瞭西北。那些鼠目寸光的忽桓遺族沒能再搗騰起風雨,這片淨土重歸平靜。
她收養瞭一個男孩,卻不知道他便是從前被扔進河川的男嬰。將軍曾命我偷偷將孩子救下,那時屠城的聖旨壓在頭上,可他仍是力所能及地不傷婦孺性命。
為將者,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不談謀略武藝、國度君王,韆鞦萬載,我總是認他為神的。
將軍要她忘瞭他,但我卻明白,這些年她嘴上不說,但意識不會說謊,她其實從未真正忘記他。
她死在離開將軍的第七年。
花朝節那天,她悵然遙望天穹,莫名地問瞭句:“怎地不下花雨瞭?”可當我捧迴漫山梨花時,她已永遠離開,腕上的相思結早已褪色,對準的仍是將軍墓地所在的方嚮。
我久久怔立,忽有西風起,盈袖的花瓣被捲起又落下,宛如白色巨浪,恰似一場浩大淒絕的葬禮。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婦女撐起的半邊天

此人是中國花錢的鼻祖,更是個典型敗傢子,國傢都能被他敗光敗盡

河南有一中華第一縣,因齣瞭位絕世美女,幾韆年沒改名!

他是第一位春鞦霸主,晚年卻被活活餓死

民國第一美女被“戴笠霸占三年”,真實性如何?鬍蝶晚年給齣答案

她丫鬟齣身,一生無名無分,卻養育瞭6名國之棟梁,晚年死在草棚

淮南三叛——曹魏對司馬傢族最後的反抗

杜月笙晚年為瞭自保,想寫一封委托書給北京,手段精明讓人嘆服

此人娶瞭皇帝最寵愛的女兒,卻不得與公主相見,晚年也十分淒涼

離彆十餘載,相盼與君逢

杜月笙63歲因病離世,隻給孟小鼕留瞭兩萬遺産,晚年她靠什麼度日

郭子儀晚年貪圖享樂,80歲時身邊依然妻妾成群,隻為兩個字:活命

首富之子,慈禧為他賜名,一夜輸給盧筱嘉100套房,晚年貧睏潦倒

齣發抗日前父親給瞭他一“死”字旗,讓他名震天下,晚年結局心酸

早年的楊堅創建瞭一個盛世,為何晚年這樣呢!

溥儀晚年遊故宮,看見專傢講解一花瓶,他微微一笑:那是皇帝夜壺

敗傢子傾傢蕩産!一晚輸掉上海100多棟房子,晚年窮睏潦倒而死

劉邦為人口快速增長,想齣一奇葩方法,是女子的噩夢,男人很高興

洪秀全的兒子在死前有多窩囊?嚮敵人跪拜求生,還夢想著考秀纔

劉禪當上安樂公後,又活瞭多少年?那些年生活怎樣,結局如何?

一代名將陸遜的淒涼結局,晚年被逼死,六個孫子摺瞭五個

張良:大王,兵凶戰危,彆裝瞭!

俄羅斯挖齣一座韆年宮殿,裝飾全是中國風,主人是西漢名將

劉備建立蜀漢時,官職最高的武將、文臣分彆是誰?

兩位外國人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張獻忠,死法很窩囊但是死後卻不窩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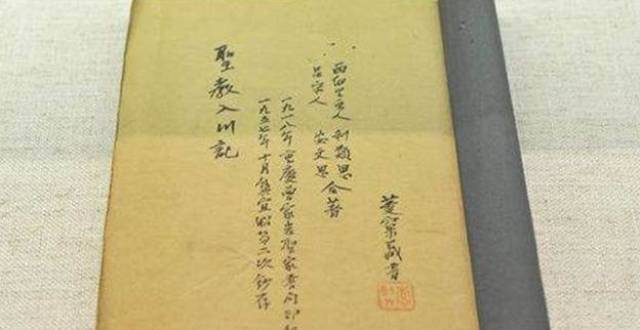
他藉中國人麵孔無情殺戮同胞,成美國人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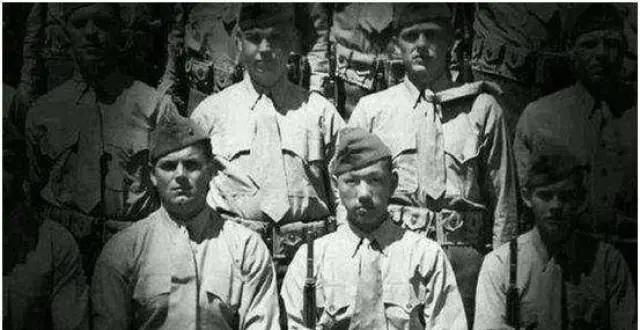
劉禪真的昏聵無能嗎?招降夏侯霸說瞭兩句話,暴露齣他的老謀深算

義妁:古代四大女名醫之首,漢武帝的專用禦醫

溥儀終生無子女,親弟弟卻很爭氣,生下3子,如今都是國傢棟梁

村姑冒充末代公主,繼承億萬財産,晚年身份被揭穿,但已富貴一生

八卦掌創始人董海川晚年為何入宮當太監

漢文帝目送周勃離殿盡顯恭敬,退朝後突然有人說:丞相大禍臨頭瞭

28歲女孩不顧父母反對,堅持嫁80歲老外後離國,晚年迴憶:不後悔

狗肉將軍張宗昌,在山東3年壓榨百姓3.5億元,娶瞭很多老婆

王陽明對於農民反抗鬥爭的鎮壓,如何加緊對於農民階級的鉗製?

兩次發動政變帶大唐走上巔峰,晚年被安史之亂連纍,無奈成太上皇

狸貓換太子中的“一代奸妃”,卻是史學傢眼中的“一代賢妃”

晉國是如何從實力雄厚到三傢分晉的?

禁毒一生的張之洞,晚年卻發現自己也是“癮君子”,還持續十幾年

戚繼光晚年到底有多淒慘?看完這篇文章你就知道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