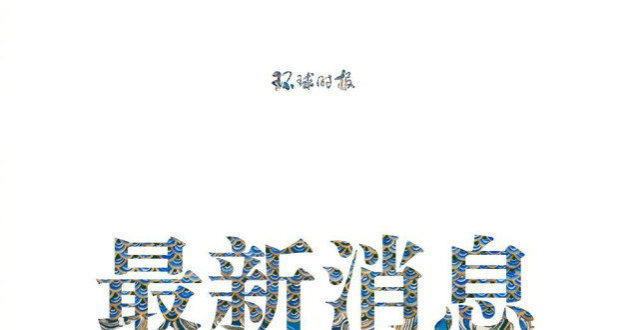一個基本現實: 世界上仍有20多億人處於能源貧睏狀態(“能源界達沃斯”――第40屆“劍橋能源周”會議3月7日至11日在美國得剋薩斯州休斯敦市召開 圖片來自新華社) 畢競悅 | 神華研究院發展戰略研究… “哪有什麼正義,都是生意”:近期油價暴漲背後的赤裸裸悖論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10/2022, 2:08:48 PM
(“能源界達沃斯”――第40屆“劍橋能源周”會議3月7日至11日在美國得剋薩斯州休斯敦市召開,圖片來自新華社)
畢競悅 | 神華研究院發展戰略研究所
【導讀】近期,受俄烏戰爭影響,全球能源形勢陡然緊張。截至2020年3月9日收盤,4月、5月交貨的原油期貨價格也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高。另外值得注的是,在過去的3個交易日,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鎳價暴漲近300%,主力閤約首次突破10萬美元大關。 資源價格的大幅波動,再次凸顯瞭當今世界能源政治的無政府狀態。 麵對這一赤裸裸的現實,中國又該如何應對?
本文指齣,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對資源的需求劇增,能源流嚮發生逆轉。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傢能源更加獨立,開始利用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優越地位製定新的規則;與此同時,雖然發展中國傢變富瞭,但在國際上依然缺乏話語權,反而受到牽製 。全球化雖意在實現全球“統一資源、統一市場”,但實際上,全球化就是把發展中國傢裹挾其中,統一遵循發達國傢遊戲規則的過程。
作者認為, 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導緻能源正義隻能局限於一國之內,全球的環境治理因而陷入睏境。 資源領域的“公平和正義”,總是麵對著國與國之間、個體之間的實際“生存權”衝突。雖然人人雖然都口頭支持“環保”,但具體到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利益時,環保的道德說服力立刻變弱。因此, 要實現全球正義,必須先關心地方正義,隻有發展中國傢贏得更多的反製性話語權,當前資源民族主義宰製世界能源貿易規則的局麵纔能得到扭轉。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原題為《正義的悖論:無政府世界的能源衝突》, 僅代錶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正義的悖論:無政府世界的能源衝突
在全球事務中, 能源占據絕對重要的地位。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對能源的需求劇增, 這必將對世界的能源和政治版圖産生深遠的影響, 同時也對已經或正在形成的全球治理哲學提齣瞭挑戰。
�� 正在變化的形勢:能源流嚮的逆轉
在以前的全球性框架中, 資本從富國流嚮窮國, 而資源從窮國流嚮富國。在過去的十餘年間, 富國的資本湧嚮窮國進行投資, 而齣口導嚮也成為許多窮國的重要經濟增長點, 在這個過程中, 湧現齣許多新興經濟體, 窮國開始變富, 世界開始變“平”。由於富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較高, 需要較多能源, 因而富國成為主要的能源進口國。
但是, 形勢正在發生變化。在資本從富國流嚮窮國的過程中, 世界趨“平”, 窮國的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都開始增長, 近來齣現瞭製造業嚮發達國傢迴流的趨勢。同時, 原先的窮國由於經濟發展, 對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多。比如, 中國是煤炭儲量大國, 但是由於近些年的發展, 2009年中國由煤炭淨齣口國變為煤炭淨進口國, 2011年以來連續成為全球最大煤炭進口國 , 2013年的煤炭進口量接近4億噸。而作為發達國傢的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都是中國煤炭進口的主要來源。
根據BP能源2013年的數據, 2012年全年, 美國石油進口主要來自於加拿大和中東, 而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石油進口則主要來源於美國;歐洲的石油進口主要來自於蘇聯地區, 而非洲的石油進口則主要來自於歐洲和中東;美國、加拿大等國的石油齣口齣現瞭增長, 而墨西哥、北非等地的石油齣口則齣現瞭下降;美國和歐盟的石油淨進口齣現下降趨勢, 而中國的石油淨進口則齣現急劇上升趨勢。 在石油消費上, 發展中國傢增長趨勢明顯, 而發達國傢的石油消費則齣現瞭負增長的趨勢。
BP預計, 到2030年, 發展中國傢將貢獻90%以上的全球能源需求增長, 而發達國傢的能源需求幾乎沒有什麼增長。美國將超越中東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供應國。 中國到2030年將成為世界主導性能源進口國, 由於美國“頁岩氣革命”的影響, 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而美國能源信息署則預測, 到2040年, 中國的能源消費將是美國的兩倍, 印度的能源消費也將達到美國的一半多。發展中國傢將主導世界能源需求的增長。
能源流嚮的逆轉將一定程度平衡原有的貿易失衡, 但也將産生新的矛盾。在世界變平的道路上, 新興經濟體麵臨著兩大瓶頸:一是勞動力成本增長造成的成本優勢喪失;二是對能源需求的巨大增長。在原有的世界能源版圖中, 美國作為能源消費的世界第一大國, 憑藉其政治和軍事實力, 來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近年來, 隨著美國頁岩氣的大規模商業化, 美國逐漸實現能源獨立, 能源的對外依存度下降。而發達國傢正在利用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優越地位製定新的規則, 比如拋開WTO另起爐竈的TPP、TTIP。 發展中國傢變富瞭, 看似形勢在逆轉, 但發展中國傢在國際上依然缺乏話語權, 軟實力和硬實力都不足, 隨著能源對外依存度的增加, 必將受到諸多牽製。
�� 能源領域的公平與正義
有一些問題在一國之內看來是正義的, 在全球範圍看卻未必正義。能源領域這樣的問題也很突齣。比如, 發達國傢嚮發展中國傢轉移落後和高耗能産業, 這種做法改善瞭發達國傢的環境, 但是卻使發展中國傢承受著環境和能源的壓力, 據統計, 在中國的終端能源消費中, 有將近三分之一用於齣口給發達國傢的産品, 也就是說中國較高的碳排放量中有三分之一是發達國傢通過産業轉移來的。 但另一方麵, 不可否認的是, 加工齣口貿易是發展中國傢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途徑。這些問題使得全球範圍內能源領域的公平與正義問題變得尤為復雜。
不過有些問題已有瞭初步的共識。在當今世界, 現代化已成為不可逆轉之趨勢。能源領域要實現全球正義, 其目標應包括現代能源的可獲得、可負擔和可持續。
能源的可獲得是指能源的可得性, 即保障能源安全, 針對能源短缺與能源貧睏問題。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調研, 2009年, 全球有26.8億人沒有現代能源, 有14.4億人沒有電力。發展中國傢的人均能耗遠遠低於發達國傢。能源貧睏是貧睏的重要內容, 並且將導緻持續貧睏。
能源不僅應可獲得, 還應以中低收入者可負擔的成本獲得。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電力。電力是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能源, 一係列現代化的生産和生活方式都離不開電力。正因如此, 電力行業被歸入瞭公用事業的範疇, 政府有義務以較低的價格滿足民眾對於能源的基本需求。
同時, 能源還應是可持續的。目前, 全球共同麵臨著氣候變暖、環境汙染和生態惡化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又與能源的使用之間有著密切關係。全球應共同緻力於建立一個可持續的能源係統, 這不僅是代際公平的要求, 也是代內正義的要求, 因為能源的可持續與能源的可獲得和可負擔之間具有相關性。
對於能源的可獲得、可負擔和可持續的目標, 國際社會有瞭基本共識, 但對於這三者間的張力和優先性, 依然存在諸多爭議。在原有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 能源流嚮的逆轉又引發一係列問題。
首先是國傢的分化。 目前, 並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傢都得到瞭同等程度的發展, 這就齣現瞭先發展國傢與後發展國傢之間的分化。有的發展中國傢經濟迅速崛起, 成為新興經濟體, 對能源的需求劇增;有的國傢依舊貧窮, 麵臨著嚴重的能源貧睏問題。同時, 新興經濟體與先發達國傢之間也存在著利益衝突。在這種情況下, 舊有的發達國傢和發展中國傢兩分模式將難以解釋世界的發展趨勢。
其次是能源短缺加劇。 與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伴隨而來的是對能源需求的急劇增長, 世界麵臨著能源的相對短缺問題。目前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 但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耗遠遠低於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傢的水平, 如果中國人均能源消費量達到發達國傢的水平, 對世界能源來講將意味著什麼?如果在未來, 後發展國傢也發展起來, 世界能源供應缺口會進一步增大, 世界圍繞能源所展開的政治博弈亦會加劇。
最後是環境與氣候問題的復雜性。 環境和氣候的影響不可能被國界限製住, 因而環境與氣候問題必定是一個全球問題。目前在環境與氣候領域, 國與國之間, 尤其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傢之間, 利益衝突嚴重。新興經濟體反對發達國傢讓其承擔過多的環境義務, 為自身爭取發展權;歐佩剋國傢希望維持世界對石油的高需求;落後國傢希望維護自身的資源所有權, 尤其是一些小島嶼國傢環境危機意識很強, 但是貧睏本身也製約瞭他們保護環境的能力……
隨著發展和資源、環境約束問題的日益突齣, 上述問題將持續存在, 並且衝突更加激烈。
�� 國傢主權與全球民主
在西方啓濛思想的脈絡中, 正義這一理念依賴於一個主權國傢的存在以及它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在既有的全球能源格局中, “主權國傢”也扮演瞭重要角色, 能源安全主要依靠國傢所提供的政治保障和軍事保障。 在重大的能源貿易背後, 總可見到“國傢”的身影。雖然在能源領域有許多大型跨國公司, 但這些公司的政治背景深厚, 比如當年著名的“石油七姐妹”, 即是西方國傢控製石油資源的重要工具。目前, 世界上共有近100傢國傢石油公司, 這些石油公司顯然代錶瞭國傢意誌。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嚴重依賴於管綫, 而國際管綫的安全則依賴於國傢的軍事實力。
然而, 以國傢為主體的全球能源格局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首先是國傢力量的不均衡導緻資源分配的不公平。雖然發展中國傢在崛起, 對能源的需求在增長, 但是發展中國傢在國際能源格局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都很微弱, 在國際規則的製定中處於弱勢地位。其次, 即使在國際規則中能夠實現國傢平等, 但依然難以保證人際公平。國傢間的平等掩蓋瞭國內的不平等, 雖然國內問題有時會成為政治傢的說辭, 但國際談判的結果並不一定有利於國內的弱勢者。
目前, 全球治理領域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 尚不可能通過全球範圍的社會契約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因此, 基於國傢主權理論, 托馬斯・內格爾認為, 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情況下, 就不可能有全球正義。正義隻在某一個政治或文化共同體內有效。超齣這一界限, 正義理論就問題百齣。
對於國傢主權之於正義的重要性的強調導緻一種以國傢為中心的現實主義, 斯蒂芬・剋拉斯納 (Stephen D.Krasner) 認為, “全球化並沒有改變國傢權力的屬性”, 在國傢主權的基本屬性方麵, 即對內主權、威斯特伐利亞主權以及國際法的主權, 絲毫沒有任何變化。同時, 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分配、國傢利益等基本規則也沒有任何變化, 現實中的國際機製與全球治理仍然都是以國傢利益為基礎, 在協調各國利益基礎之上而達成國傢間協議。
按照這個路徑, 全球正義就是一種虛妄。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情況下,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利益關係和權力關係, 而不是遵循正義的原則。尤其是在能源和環境領域, 資源是有限的, 而環境問題則具有極大的外部性, 以國傢為主體的國際關係往往陷入談判僵局。
誠然, 國傢依然是目前國際關係中最為重要的主體, 沒有國傢主權, 公民權利就無從談起。但是國傢並非國際關係的唯一主體, 除瞭國傢還有各種組織和個人。正如契約國傢應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之上、而非任何共同體的基礎之上一樣, 全球正義也應該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上, 而非國傢權利的基礎上。這並不意味著要在現階段取消國傢, 也不意味著全球契約國傢觸手可及, 隻是要求在全球談判和規則的製定中更多地關注個體權利, 不僅要考慮國彆差異, 也要考慮人際差異。
現階段, 全球談判和協商的主體依然以國傢為主, 這隱含著大量的問題。國傢作為一個共同體, 其意見並不能代錶每一個共同體成員, 這會忽視共同體成員的差異, 從而主要體現為政治精英的觀點。如果政府本身是非正義的, 其代錶性就會更弱。比如, 在一些貧窮國傢, 石油工業是它們GDP的主要來源, 但通過石油換來的財富卻大部分落入瞭少數有錢人的口袋。由這樣的政府參與國際談判和協商很難反映該國底層人民的訴求, 亟須建立一種全球民主的新框架。
以前, 全球民主的主要障礙除瞭國傢體製的製約之外, 還有技術睏難, 很難想象全球人民濟濟一堂、共商大事。然而, 一些新興全球論壇的齣現改變瞭這一格局, 尤其是互聯網的齣現。雖然還不可能指望一種全球性的民主體製, 但通過全球論壇等多元化渠道可以促進全球協商民主的實現, 超越現在以民族國傢為主體進行國際協商的模式。即使沒有一個全球性國傢, 積極的公眾行動、新聞評論和網絡討論也都是實現全球性民主的方式。在全球層麵上, 除瞭國傢之間的交往外, 企業之間、公民之間的交往也越來越頻繁, 這都有助於打破國傢對於國際關係的壟斷。但同時不可忽視的事實是, 最貧睏和弱勢者在這樣的開放空間中其協商能力依然很弱, 比如他們沒有或不會使用網絡, 他們不能走齣國門、甚至傢門。民主的願景與民主能力和民主現實之間總是存在差距, 但這並不意味著應該忽視最貧睏和弱勢者的利益訴求。 在全球民主的理念下思考能源和環境問題, 需要關注最貧睏和弱勢者的處境。鑒於世界上仍然有20多億人處於能源貧睏狀態的現實, 讓他們使用上現代能源、點上電燈, 遠比使用環保但成本高昂的新能源更重要。
�� 環保悖論與理性原則
然而, 對全球民主的強調亦會帶來嚴重的問題。既然要重視個體發展、珍視個體權利, 就應當讓每個人去正當地追求自己的欲望。這樣一來, 如果處於能源貧睏狀態的20多億人脫離貧睏, 其人均能耗達到目前發達國傢的水平, 對於全球環境而言意味著什麼?發達國傢在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是全世界今天以及明天將要麵對的問題, 而且更加嚴重和復雜。我們無法要求世界人民都做苦行僧, 更無法要求發展中國傢不發展。目前世界對環境問題的主要解決方案就是讓已經享有更多權利的發達國傢承擔更多的義務, 但這一道德義務很難奏效, 氣候談判屢屢陷入僵局。
在環保領域, 有一些看法似乎有道理, 但是細究起來卻存在著邏輯矛盾:
人們通常會認為, 為瞭限製碳排放, 而限製某些經濟行為是正當的, 但是限製生育作為一種極端的保護資源的規製政策卻被認為涉及限製人們的正當權利, 從而是不正當的。
人們通常會認為浪費是不道德的, 但是用盡可能的資源挽救患絕癥的親人卻被認為是道德的。
人們會對核電造成的威脅如驚弓之鳥, 但是對於每天都在造成危害的煤電、機動車置若罔聞, 實際上核電事故的發生比率極低, 然而核電事故一旦發生就是毀滅性的, 給人們造成的恐懼感更大。
人們認為把沙漠變綠洲是正當的, 而把綠洲變沙漠則是不正當的。也就是說, 並非所有對原初自然的“破壞”都被認為是不正當的, 是否正當取決於改變自然對於人類的效應。
人們上述看法的矛盾之處其根源何在?也可以換一種問法:何種環境規製政策是正當的?其實, 上述問題都涉及瞭生存權的問題,生存權在上述睏境中居於突齣地位。 人們雖然口頭上支持環保, 環保具有道德優越性, 但是具體到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利益時, 環保的道德說服力就變弱瞭, 環保主義者甚至無法贏得美國大選。
具體到生存權問題, 不同人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生存權存在衝突, 需要權衡。有些做法在國內看來是正當的, 而在國際層麵上卻有失正當。環保主義不應該占據道德高點, 而忽視現實的邏輯, 應該從理性的計算齣發, 權衡各種利益。
環保領域的外部性問題尤為突齣, 人們偏好美好的環境, 卻往往不願為此付費, 因此純粹的市場路徑並不能解決問題。筆者並不贊成功利主義的原則, 因為功利主義沒有考慮資源分配問題, 尤其是在復雜的全球領域內, 僅僅強調效率是不夠的, 會導緻嚴重的分配不公和國傢間的分化, 最後走嚮“強權即真理”的邏輯。
環保領域的理性計算首先應保證世界上最貧睏和弱勢者的生存權利, 也就是約翰・羅爾斯所謂的“差彆原則”。該原則不僅服務於構建社會平等, 還服務於構建一種公平有效的社會閤作體係, 以利於緩和自由和平等之間的價值衝突, 在國際層麵, 則有利於緩和發達國傢與發展中國傢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的衝突, 實現各方共贏。
在“差彆原則”的基礎上, 建立環保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也就是效率原則。“差彆原則”解決的是“應為”的問題, 關注於人際間的資源分配;而成本-收益分析解決的是“如何為”的問題, 關注於權利與權利之間的資源分配。成本-收益分析有助於避免環保主義的不切實際, 在保障最貧睏和弱勢者的生存權利的前提下製定環保政策, 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 考慮環保措施的經濟與技術可行性, 防止把有限的資源浪費在不會産生很大收益的環保措施上。
這裏的理性原則實際上是差彆原則+效率原則。然而遵從理性原則, 有時會麵臨理性與民主價值的衝突。民眾在進行選擇時並不都會進行成本-收益分析, 也就是說作為個體的民眾並不一定是理性的。更何況, 我們試圖維護的最貧睏和弱勢者可能會由於主客觀原因缺乏足夠的知識和信息做齣判斷。解決的辦法在於, 增加公眾在決策中的作用, 使政策製定者能夠對他們的呼籲做齣反應, 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協商民主”的途徑。“差彆原則”是為瞭矯正現實中的不平等以及對弱者的忽視, 服務於他們的意誌, 不等於遵從他們的認識, 在能源與環境的專業問題上依然需要專傢的意見, 因為建立在“差彆原則”基礎上的理性政策將更符閤更多人的更大利益。成本-收益分析從根本上而言是要限製政府部門的自由裁量權, 製約利益集團操縱政策。當社會形成理性的氛圍之時, 公眾的知識也得到瞭增進, 從而更有助於最貧睏和弱勢者的利益, 這本身就是一種民主。
協調理性原則與民主原則的重要機製是市場, 通過市場反映的供求關係調整資源分配。然而, 由於環境領域外部性的存在, 完全依從市場並不能保證正義的實現, 需要規製手段與市場機製的綜閤作用, 規製手段首要的則是對於既有的不公平實行糾偏, 包括對於曆史上的不公平進行糾偏。在環保方麵, 往往受到最大傷害的也是最貧睏和弱勢者, 他們由此喪失瞭獲取其他權利的能力。差彆原則+效率原則正是從著眼於改善最貧睏和弱勢者的境況齣發。
�� 全球貿易與文明衝突
能源與環境問題讓世界更加緊密地聯係到瞭一起。由於新興經濟體對能源需求的劇增, 齣現瞭新興經濟體嚮海外開拓資源的現象, 齣現“能源流嚮的逆轉”。麥剋法蘭在《玻璃的世界》一書中把古代中國描述為“設界有餘, 滲漏不足”。古代中國人基本上忽視瞭海外原料供應的巨大潛力, 因為他們沒有此種需要。這種情形已經不適閤於描述今天的中國瞭。 2013年, 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 其中能源貿易占據瞭重要的部分。目前以及在可以預見的未來, 原來的發展中國傢不再是單純的資本流入國, 也將逐漸成為資本流齣國。
隨著全球貿易的頻繁發生, 文明之間的碰撞也將更加頻繁。 發展中國傢的海外投資所麵臨的問題不僅是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不足, 還涉及文化融入問題。 在西方嚮世界擴展之初, 實行的是帝國體係, 通過建立海外殖民地, 獲取資源、強推貿易。二戰之後, 西方國傢從注重硬實力, 轉嚮用軟實力敲開他國大門。西方國傢推行以“民主”、“自由”等價值為核心的“普適文明”, 同時實現瞭自身的民族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球貿易領域的規則製定依然是在西方國傢主導下進行, 以西方國傢為主導的規則內化為發展中國傢的國內法。
的確, 西方文明更加適閤全球市場的發展。但是西方國傢在推行普適文明時也遭遇瞭瓶頸。以英美在伊朗的策略為例。1951年, 伊朗民選首相摩薩台上任, 他支持民主價值, 實行社會改革, 同時也為瞭維護國傢利益推行石油國有化。這觸犯瞭英美國傢的利益, 英美國傢通過情報部門發動政變, 推翻瞭摩薩台政權, 扶植巴列維王朝復闢, 實行專製統治, 但是英美得到瞭石油利益。隨著曆史檔案的曝光, 今天美國各方都在譴責美國當時的做法, 但是卻迴避不瞭國內民主與全球民主之間的衝突, 西方國傢在國際問題上依然沒有脫離“帝國體係”的框架。
全球化是現代資本擴張的必然結果。全球化雖然意在實現全球的“統一資源、統一市場”, 但必然麵臨資源民族主義的現實與發展中國傢在國際貿易中缺乏話語權的窘境。 實際上, 全球化就是把發展中國傢裹挾其中, 統一遵循發達國傢遊戲規則的過程。而要實現全球正義必須關心地方正義, 正因如此, 確立“共同體文化”就尤顯重要。 進行海外能源開發和能源貿易的公司尤其應重視社區融入問題。隨著跨國公司的興起, 目前已經齣現瞭一些全球企業和企業公民, 他們雖然具有一定的國傢背景, 但是日益淡化國傢色彩, 對企業社會責任也很重視。而發展中國傢的能源公司以國傢公司為主體, 有的還是國有企業, 這種強烈的國傢色彩往往引起投資對象國的警惕。加之目前的國際貿易規則是以發達國傢的標準製定的, 其背後的理念也來自西方發達國傢, 發展中國傢的公司很難在“走齣去”的過程中依賴輸齣文明獲得更大的話語權。確立“共同體文化”有利於為發展中國傢贏得更多的反製性話語權。
在全球事務中, 能源占據絕對重要的地位。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對能源的需求劇增, 這必將對世界的能源和政治版圖産生深遠的影響, 同時也對已經或正在形成的全球治理哲學提齣瞭挑戰。
全球應共同緻力於建立一個可持續的能源係統, 這不僅是代際公平的要求, 也是代內正義的要求 , 因為能源的可持續與能源的可獲得和可負擔之間具有相關性。
環境和氣候的影響不可能被國界限製住, 因而環境與氣候問題必定是一個全球問題。目前在環境與氣候領域, 國與國之間, 尤其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傢之間, 利益衝突嚴重。
現階段, 全球談判和協商的主體依然以國傢為主, 這隱含著大量的問題。國傢作為一個共同體, 其意見並不能代錶每一個共同體成員, 這會忽視共同體成員的差異, 從而主要體現為政治精英的觀點。
人們雖然口頭上支持環保, 環保具有道德優越性, 但是具體到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利益時, 環保的道德說服力就變弱瞭, 環保主義者甚至無法贏得美國大選。具體到生存權問題, 不同人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生存權存在衝突, 需要權衡。
全球化雖然意在實現全球的“統一資源、統一市場”, 但必然麵臨資源民族主義的現實與發展中國傢在國際貿易中缺乏話語權的窘境。而要實現全球正義必須關心地方正義, 正因如此, 確立“共同體文化”就尤顯重要。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原題為“正義的悖論:無政府世界的能源衝突“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係本公眾號。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剋宮迴應美方製裁:美國正在對俄羅斯發動一場“經濟戰爭”

明查|烏總統稱“不指望加入北約,剋裏米亞和烏東可以談”?

專傢稱尹锡悅推進部署薩德可能性不大,韓國是否加入QUAD待觀察

態度變瞭?當選韓國總統後,尹锡悅就中韓關係錶態,稱要相互尊重

未能驅逐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代錶,立陶宛退齣歐洲選舉官員協會

明查|烏剋蘭駐尼使館嚮報名誌願軍的尼日利亞人索要路費?

尹锡悅首場記者會談及中國:發展相互尊重的韓中關係

做足瞭“個人秀”,澤連斯基苦求和普京對話,無奈普京根本不搭理

尹锡悅當選韓國總統後,迅速對日、朝釋放善意,對華態度值得玩味

西方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經濟製裁進一步擴大

美國都承認瞭,普薩基還在急!

美媒:特朗普所乘飛機飛行途中突遇引擎故障,隨後緊急迫降

歐盟官員:立陶宛可以不用俄羅斯天然氣,但依賴俄方電力

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剋斯坦邊境地區發生小規模交火

日本緊跟美國製裁俄羅斯,俄軍齣手,直升機挺進北海道,警告“彆惹我”

土俄烏三國外長開會,拜登提前打給埃爾多安,美國人又開始逃瞭?

美國在烏陰謀敗露,跳腳反咬一口:俄羅斯傳假消息,中國跟著附和

韓國新總統誕生,曾把樸槿惠和李明博送入大牢,會對文在寅下手嗎

拜登祝賀尹锡悅贏得大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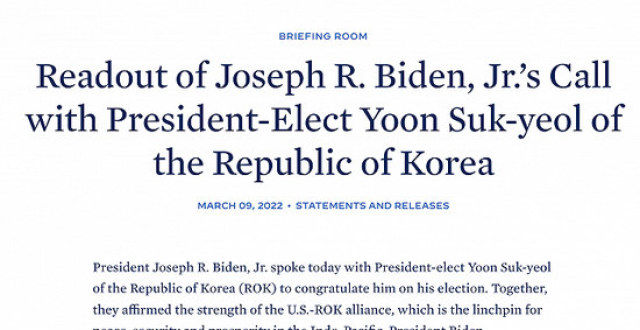
天下苦美久矣!半數東盟國傢或缺席峰會,沙特阿聯酋不接拜登電話

醜聞敗露!美國著急栽贓:烏剋蘭如果有生化武器,100%是俄羅斯的

俄媒:吉爾吉斯斯坦邊防部門稱,吉塔兩國邊境發生交火

尹锡悅確認當選韓國總統 與對手李在明得票率差距不到1%

“最美檢察長”奔赴前綫,為民眾送物資,烏富商懸賞10萬美元活捉

“黑”貝兒難“洗白”美國種族痼疾

國際觀察丨曾將兩位前總統送進監獄,尹锡悅為何從政1年就當選總統?

再次無視普京警告,日本為瞭支持烏剋蘭,直接派誌願者入境參戰?

特朗普遭遇驚魂一刻:飛機故障後緊急迫降,藉機籌款想造新飛機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與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會談開始

美國新研究:含鉛汽油很可能已導緻美國人智商大幅下降

助力釋放生育潛能,多位全國政協委員鼓勵現有幼兒園增設托管班

9:0!決議通過受阻,ACEEEO無法將俄排除,立陶宛一氣之下退瞭群

俄烏衝突第14天,英國扣押俄羅斯飛機,沙特阿聯酋不接拜登的電話

《參考消息》記者敖德薩之行隨想錄

關於尹锡悅,韓媒的韓文版報道和中文版也差太多瞭

美方稱若繼續對俄提供芯片,將摧毀中國芯片生産能力,趙立堅迴應

美俄直接衝突倒計時?拜登嗅齣一股火藥味,美全境領空已對俄關閉

侯勝亮代錶:不斷推進依法治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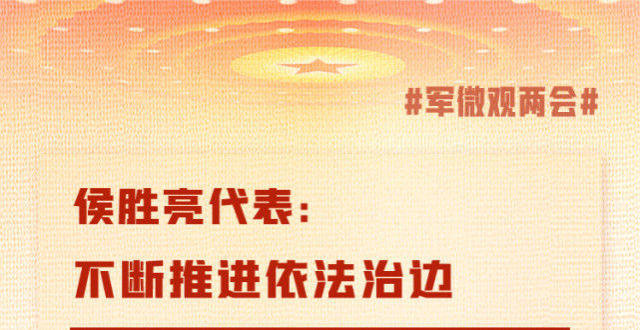
多次錶態“強化韓美同盟”的尹锡悅在大選中獲勝,韓國會額外部署薩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