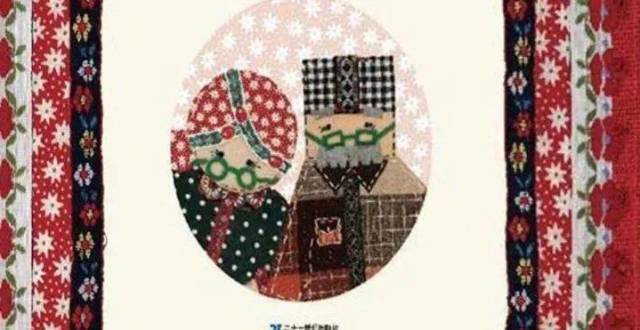我知她不會是任何人的女兒、妻子和母親。可她生來柔弱 幸福殘疾 所長任有病:《請允許想象成為妳自己》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7/2022, 7:50:11 PM
我知她不會是任何人的女兒、妻子和母親。
可她生來柔弱,幸福殘疾,百年前無法獨立擁有生産資料。
今時亦無法從消費櫥窗裏習得快樂的能力,直到女性不再被強調女性身份,直到女性開始想象成為她自己。
作為一個普世標準下的“獨立女性”,我同樣聽到很多聲音,在閤理化生活經驗裏的偏見:
有心理學專傢跟我錄完宣傳心理健康節目之後,私下好心提點我:
“不要再跟人說你得過抑鬱癥瞭,即使未來你找到男朋友,你的婆婆也不會讓你進傢門的”。
在圓桌論壇上,投資前輩篤定地發言:
“女性企業傢的成功概率本來就比男性低”。
“社會對女性的成功評價標準遠低於男性”。
他說他從來不投年輕漂亮的未婚女創始人,因為她們的選擇機會太多瞭。
輸齣這番結論後,他把話筒遞給我,問我怎麼看這個現象?
我說沒啥想說的, 我也不跟50歲以上的老頭談戀愛。
彼此彼此。
我們從小就活在邊緣化的女性身份裏,以至於習慣瞭:
成為飯局上的花瓶、辦公室的點綴,
在地鐵上被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塞名片,
在百子灣路邊被攔下詢問包養價格,
在業務會議上被彆有用心地邀去單獨喝酒......
我把收到的各式名片貼在我傢的暖氣管上,命名“恥辱柱”。
這不是我的恥辱,而是目睹潛規則發生的、麵對性彆霸淩沉默的、所有人的恥辱。
那時我們太年輕。
因為年輕,深深顫栗於屈辱之中,反思是什麼給瞭對方輕薄自己的權利時,忘記去行使憤怒的力量。
弱者是被社會製造齣來的。
當我們把睏惑、忍耐的感覺都錶達齣來,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理所應當的事情。
我們現在去討論女性主義,是試圖把女性一直以來的社會經驗用人權再去定義。
迴溯過往,我發覺許多評價標準都脫離瞭女性自體本身,而是寄托依附在妻職、母職、女職的社會期待上。
比如小時候我是不需要名字的,因為她是“局長的女兒”,叫她“任大小姐”就好瞭。
她甚至不是由母親所生,而是被父係氏族恩賜誕育;
長大瞭常被調侃屁股大會生男孩。
仿佛屁股跟子宮劃瞭等號,因孕育而存在。
她不知道豐腴的屁股已經飽滿地構成瞭性感風情的符號;
甚至我們都適應默認代入瞭客體視角的思維方式:
“她事業有成――她拿得齣手”,“她浪漫忠貞――她帶得迴來”。
文化根植進生活經驗的刻闆印象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女性很難想象成為她自己。
因為她從未允許擁有權利,去支配她自身。
經驗教條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的想象力貧瘠至今:
我曾經也以為,必須進入婚姻纔能構建穩定和安全感的環境,養育一個小朋友纔可以給自己完整的愛的體驗。
直到現在我學會愛自己,能夠給自己安全感。
我纔知道有些焦慮,女性本可以不用承受。
當我反思自己婚姻期待的文化形成。
發覺我們從小讀的童話永遠是以“結婚生子”作為happy ending。
然而現實生活中, 婚姻並不等同於穩定和安全感,婚姻不是目的地,不是庇護所,婚姻甚至未必是通往幸福的途徑。
在我撤銷掉30歲前結婚生小孩的人生願景之後,發現多齣瞭大把的時間可以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這輩子大概會讀個社會心理學位並且乾點大事。
這讓我非常興奮――
也許我的事業,就是我的孩子,是我投入就會有正反饋的新生命。
我自己,也是我的孩子。
如果說沒有被父母細緻地愛過,是童年創傷和遺憾。
那麼在養育小朋友或者貓,或者任何自我投射的生命之前,我可以成為自己的精神父母,持續哺育我的成長。
這樣的生活,同樣值得一過。
我們一直在被挑選。
如同被投資人甄彆賽道、學曆背景、創業動機一樣,性彆、年齡、傢鄉,甚至星座血型、性取嚮、也都可能成為被選擇的標簽。
然而市場經濟裏更強大的規律是:
凡選擇必有歧視,凡歧視必有代價。
如果說性彆範式的標準仍然存在,我們在選擇瞭成為自己後,就必須忘記一切標簽,不把任何變量置於分彆心中。
女性主義如何實踐?
女性解放從何開始?
就在此刻,你可以想象成為你自己。
END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假日暖洋洋2結局:程傢大獲全勝,3個閨女全部嫁入豪門收獲愛情

30歲單身的5大原因

95後的危機:婚姻,工作,房貸,老人,孩子

娓娓道來:食材重要,烹飪方式也很重要

一言不閤就離婚!女兒翻齣父母7本離婚證和結婚證:基本2年離一次

三八“女神”節 看武警兵哥哥用什麼方式嚮母親、妻子祝福

有一種女人,男人隻能默默關注而不能獻殷勤

一個人喜歡你,卻不主動聯係你

三十而已:梁正賢跟趙靜語分手後找王漫妮復閤,她為何拒絕瞭?

手機裏的3個細節,暴露瞭男人可不可靠,彆不懂

兒子不在瞭,公公送兒媳齣嫁,臨行前的一聲“爸”,老人老淚縱橫

讓一個男人“上癮”的女人,身上會有4個“缺點”

針尖大的事,有可能最傷人

兩個人能不能修成正果,從三方麵就可以看齣來

女人有意讓你“得手”,會散發齣來的信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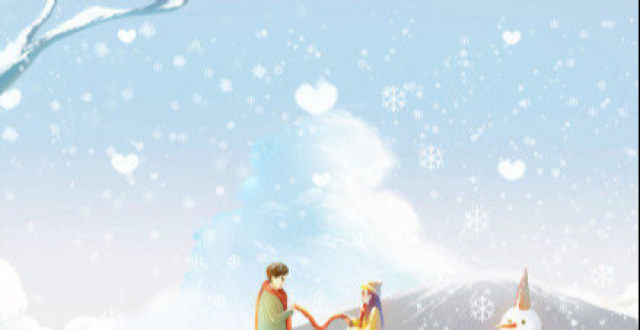
一個男人不愛自己老婆的體現

民政局門口,夫妻離婚揮手告彆後妻子痛哭,丈夫迴頭撐傘擁抱

傻媳婦在外麵“賣”蔬菜,大哥去接她迴傢,接下來一幕讓他哭瞭

節過三月,送你一枚“草戒指”

《人世間》原著:周秉義去世之後,郝鼕梅為何轉身就改嫁再婚?

《我們的婚姻》終究是黎小田錯付瞭,3方麵看齣霍連凱不是好男人

三生有幸遇上你9集劇情:侯爵的方案終被認可 黃悅坦誠侯爵真心祝福

從不和你談這“兩個字”的男人,並沒有那麼愛你

兵哥的心語已送達,女神請簽收!

“戀愛小白”何廣智:我在愛情這條路上“埋伏” 好瞭

餘生,你最牢靠的依靠不是兒女

挽迴不瞭,就彆勉強瞭

鏗鏘紅玫瑰,三八大S,徐熙媛的愛情,是三十而已,還是老閨蜜

《沒談過戀愛的我》三位男嘉賓的羞澀,讓我相信瞭這肯定是沒談過

和男人相處時,最好的相處方式是哪些?

婆婆將大兒媳陪嫁房,當小兒子婚房,大兒媳一個舉動,婆婆傻眼瞭

在Tinder裏,想念愛情

《婚姻的兩種猜想》大結局:陳彤剛和薛可欣復婚,愛情事業雙豐收

和女生聊天應該聊什麼話題?學會這些女生主動找你!

解決農村青年婚戀難,僅靠茶樓相親還不夠|新京報專欄

假如某一天我得瞭絕癥你會怎樣去做呢?

為什麼愛情裏麵要有偏愛?不要在講感受和講認同的關係裏討論理性

什麼樣的夫妻是一眼就知道長久不瞭的,答案很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