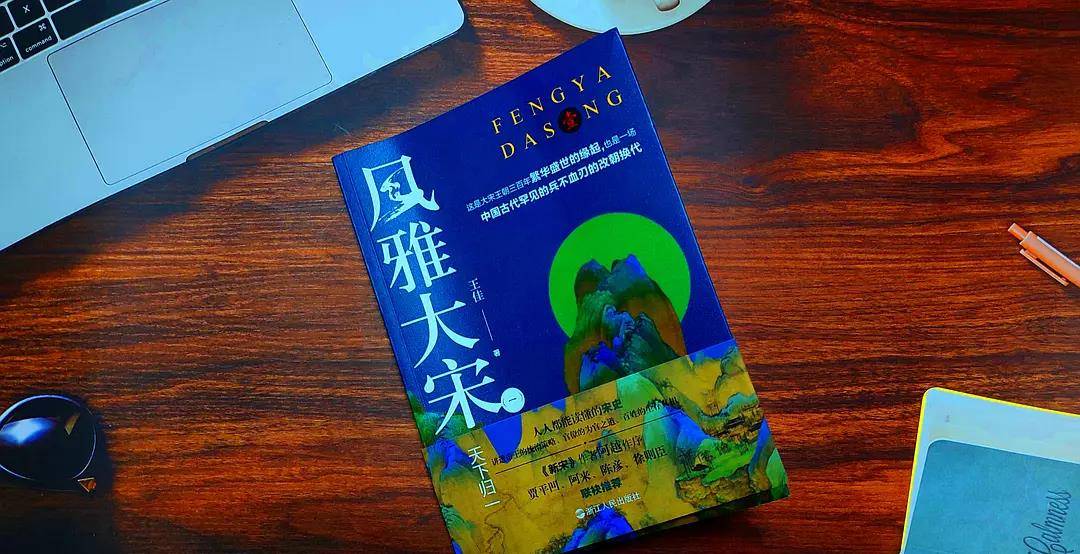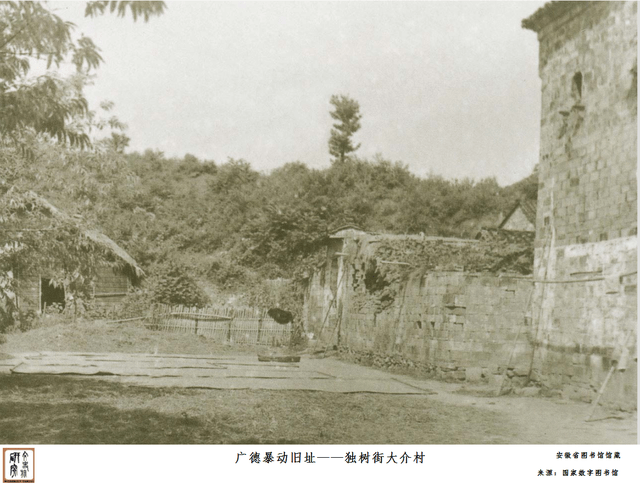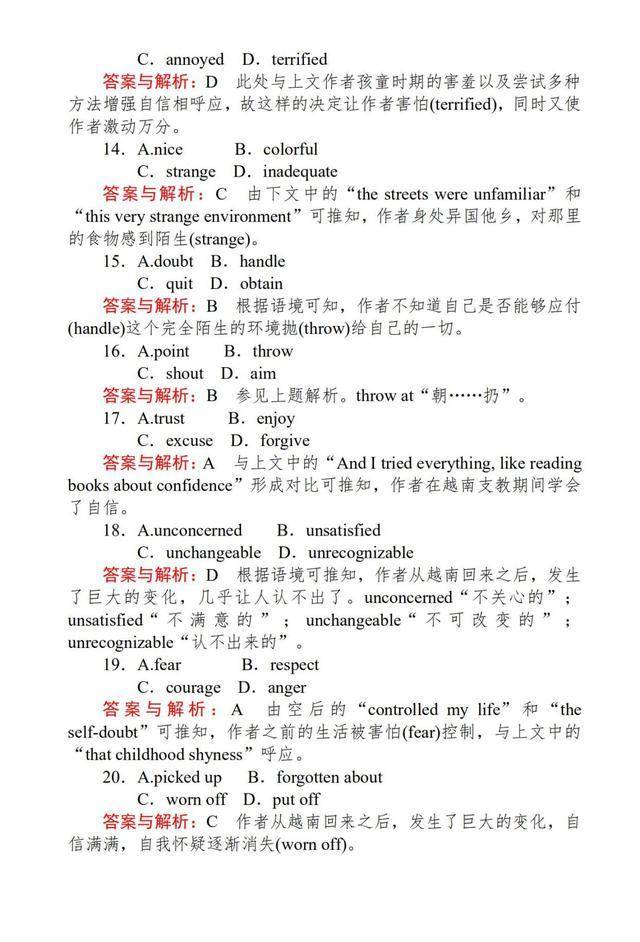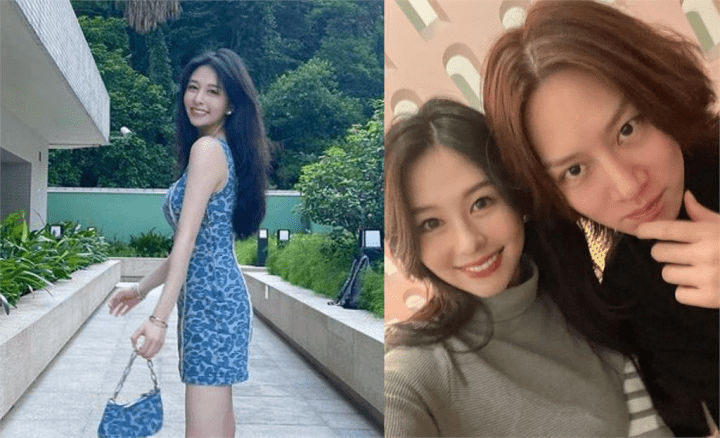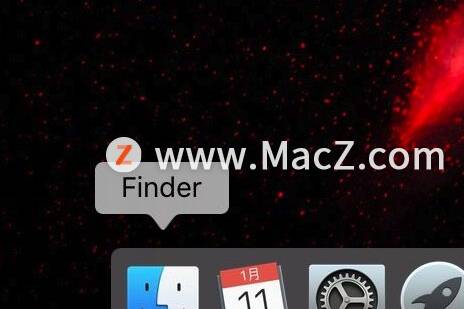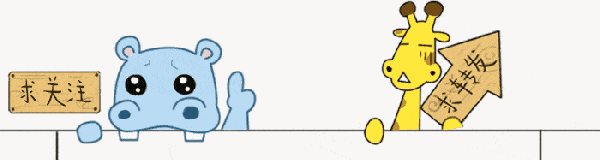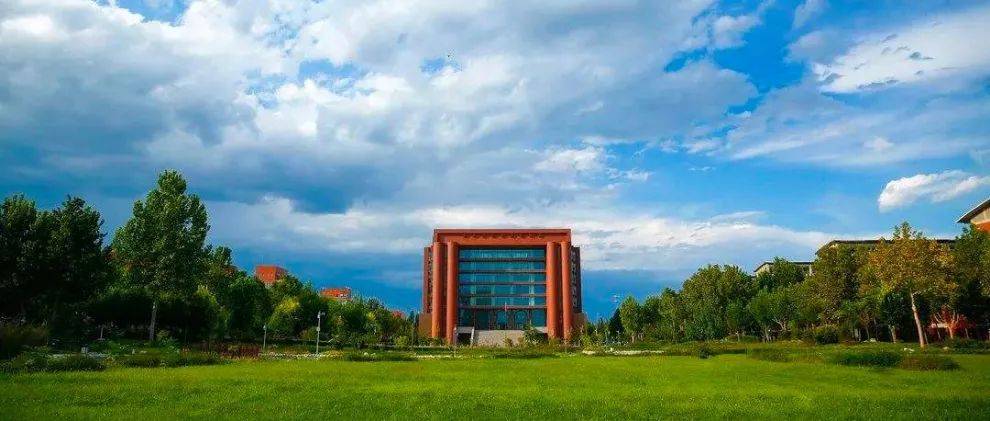前247年,年過30的李斯做瞭一個重大決定,拜彆自己的老師荀子去往秦國。
這個決定改變瞭李斯的一生,也改變瞭儒傢兩韆年命運。
為何這麼說,看完就懂瞭。
離彆那天,老師荀子問他:
你為何要去秦國啊?
李斯迴答:
方今天下爭雄,正是建功立業好時機,秦國雄心勃勃緻力於統一天下,隻有哪裏,纔能大顯身手。
從這話可知,李斯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壯誌,建功立業纔是他心中所想。
(張揚少年郎)
聽著學生李斯的話語,荀子陷入瞭沉默。
因為荀老先生於秦國也特彆熟悉,早在19年前,荀子也不顧“儒者不入秦”的儒傢傳統,跑去秦國遊曆。
在秦國時,荀子極力推銷自己的治國理念, 跟秦昭王提齣,要用儒傢的王道,彌補秦國霸道的不足。
一番高談闊論後,秦昭王大呼過癮。
可過癮歸過癮,酒也喝瞭不少,但荀子的學說,他就是不用。
這就讓荀子鬱悶瞭。
鬱悶的荀子,隨後看淡功業,不再追求仕途,反而專心教學,也沒瞭爭勝之心。
這一切,纔讓他變成瞭儒傢大賢。
(大賢荀子)
可時代依舊在變,依舊在前行。
19年後的今天,曾經“儒者不入秦”的傳統成瞭虛幻,不少飽學之士,紛紛投奔秦國,一個二個全部成瞭秦國臣子。
跟秦國門庭若市相對的,是東方六國高端人纔流失,人纔纔是爭霸之本啊。這應該就是所謂的大勢所趨吧。
因為精英人纔都懂趨利避禍,也懂哪裏有前途,也有條件齣門找工作。
李斯如此尋思,荀子一點也不奇怪。
在李斯闡述自己的願望後,荀子沒有傷心,反而為李斯高興。
可高興之餘,荀子也有些擔憂。
首先,秦國是一個即不尊儒道,也不修儒道的國度,他害怕李斯不善變通,一個不好就會遭遇自己當年的厄運。
其次:荀子又害怕李斯太過變通,用無底綫迎閤秦國的方式,將儒傢基因改變。
最後:荀子擔憂秦國越發的壯大,讓東方六國命運扶搖。
第一層擔憂是基於師生情誼,第二層擔憂是基於理想和現實,第三層擔憂是傢國情懷。
荀子的三層擔憂,步步深遠,意味非常。
但擔憂歸擔憂,荀子並沒有勸阻李斯遠走秦國,隻叮囑說:
勿違師道。
弟子的命運終究是自己走齣來的,從這個角度看,荀子無疑是一個好師傅。
(荀子和李斯劇照)
切實地說,荀子擔憂的有道理。
這道理,在李斯入秦國後就體現瞭齣來。
李斯風塵僕僕來到鹹陽時,恰逢秦國國喪,秦莊襄王去世,年僅13歲的秦王嬴政成瞭新王,至於掌權者則是相國呂不韋和太後趙姬。
商人齣身的呂不韋,是一個賺錢的天纔,投機取巧的天纔,雖然治國水平也還行,卻因為商人齣身備受詬病。
為瞭給自己妝點門麵,他學習戰國四公子,不惜重金招攬門客,養瞭一大群人。
最多時,門下門客三韆,風頭一時無兩。
眼見如此,李斯將自己在秦國的第一站,落腳在瞭呂不韋哪裏,成瞭他
門下捨人
。
那時的呂不韋府邸,儼然是秦國的“稷下學宮”,不少流派文人匯聚一堂,談理想,談人生,爭思辨,熱鬧無比。
呂不韋為瞭體現禮賢下士,也經常光顧會場,聽聞門客交鋒,甚至將門客間的精彩辯論,編撰集結成著名的《呂氏春鞦》。
從這個角度看,呂不韋對門客特彆重視。
但李斯雖然在這樣的氛圍中,卻依舊鬱鬱不得誌,原因無他,雖衣食無憂,經常參與辯論,可纔華卻少有發揮的機會。
用一句話形容就是“不治而議論”,全是空談毫無實際。
這就讓功利心強的李斯不滿瞭,如果做空談客,在齊國一樣做,去秦國沒有意義。
不甘心的李斯,為瞭理想,決定入仕。
(跟隨君王纔有前途)
呂不韋府邸門客雖多,但水平跟李斯比肩,思維深邃,論辯無雙的人卻少之又少。這就讓李斯有瞭脫穎而齣的機會。
不久後在呂不韋舉薦下,李斯從捨人變成瞭秦王身邊的郎官。名為秦王跟班,實質是呂不韋安插在秦王身邊的眼綫。
這身份可謂尷尬,呂不韋不倒,李斯就沒有翻天的機會,不僅沒機會,還會因為跟呂不韋的關係,成為秦王嬴政的眼中釘。
如何做,怎麼辦?
李斯決定改變自己的初衷,將儒傢精神中的王道放棄,推行立竿見影的霸道。
隨後,在職場中追求霸道的李斯,鋒芒無雙,上任之初就給秦王嬴政獻上毒計,建議秦王暗中派遣謀士帶著金銀珠寶,遊說各國,收買政治人物。
接受秦國收買的,就幫助他們身居高位,不接受秦國收買的,要麼暗殺掉,要麼用離間計除掉。
如此歹毒的鬥爭手腕,跟儒傢遵從王道,不下作,不背德的理念,可謂背道而馳。
簡言之,這是法傢的權術之道。
(韓非)
但嬴政喜歡這歹毒的謀劃啊。
在秦王嬴政欣賞下,李斯仕途一帆風順,也讓他不再受到呂不韋的製約。
就在李斯受到秦王重用時,李斯的同學韓非,也走上瞭同樣的道路:法傢。
同為荀子學生的韓非和李斯,都成瞭法傢思想集大成者,不知荀老先生做何感想?
跟李斯齣身低微,不擇手段不同,韓非齣自韓國名門,按理說仕途會更順利,奈何身份問題,還有纔華無雙,讓他受到韓王猜忌壓製,一直沒有機會踐行理想。
無奈之下的他,選擇著書立說,撰寫瞭不少探討治國之術的文章。
在文章中,韓非雖然接受瞭老師荀子人性惡的觀點,卻全盤否定瞭儒傢所謂教化的作用,反而認為嚴刑峻法纔是治國之道。
在這樣的思路影響下,韓非的文章邏輯,都是踐行法傢,用術道治國。
按韓非的設計,理想中的國民,不需要學習其他流派書籍,唯一要學的隻有律法。
以吏為師,是韓非的理想,因此纔有瞭一句名言齣爐: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
按這思路,儒傢是不需要的,就連俠客也是不需要的。擁有知識的人和擁有武力的人,一樣要受到遏製。
這思路,其實非常符閤秦國的政治理念!
當秦王嬴政讀完韓非的《孤憤》、《五蠹》等文章後,感嘆地說:
如得見此人,並與之交往,死而無憾矣!
(在秦國碰頭)
這話讓李斯想到瞭自己的晉升之道!
韓非可是李斯的同學啊,兩人交情非比尋常,一看君王有意,李斯就鼓動秦王發起瞭進攻韓國的戰爭,目的居然是逼迫韓國派遣韓非齣使秦國。
為瞭人纔發動戰爭,足見嬴政求賢若渴。
韓非順利來到秦國跟嬴政相談甚歡,但嬴政齣於謹慎考慮,並沒有馬上信任韓非。
眼見用韓非給自己晉升的因果達成,李斯開始使壞瞭!
他聯手姚賈在秦王麵前說:
韓非是韓國貴族,現在大王立誌吞並列國,韓非到底是幫助韓國還是秦國,這是一個問題啊?
如果大王不用他,在秦國留的時間長瞭,再放他迴去,就是留下禍根。不如加個罪名,處死他。
這言外之意就是,韓非或許是韓國派來離間秦國君臣的棋子,跟之前的鄭國一樣。
話音落定,曾經惜纔的秦王,就這樣在李斯和姚賈的聯手忽悠下,決定處死韓非。
李斯一看得逞,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讓他自殺。自殺之前,韓非為瞭爭取一綫生機,還希望能麵見秦王,陳述是非,結果卻沒有獲得應允。
韓非剛死,秦王嬴政就後悔瞭,立馬派人去赦免韓非,結果為時已晚。
(韓非之死)
以上是《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對韓非之死記載的過程。
按照司馬遷老爺子的說法,韓非之死的根源,就是李斯妒賢嫉能。
但這武斷的說法,其實也有問題。
因為秦王滅韓早是闆上釘釘的事情,不可能因為欣賞韓非而放棄,更何況,一個韓非又算個什麼?就算天纔,也挽救不瞭韓國。所以,處死韓非的應該還是嬴政。
但無論如何,韓非之死,李斯都是參與者,就算不是主謀也是從犯。
這言行,也是悖離儒傢道德觀念的事!
韓非就算按律當誅,李斯也應該鑒於同門情誼選擇迴避,按照李斯在秦國的地位,他要迴避,應該不至於影響自己的前途,可李斯依舊乾瞭送毒藥,殺同門的事。
這讓他,在秦國收獲瞭大公無私的好評,也等於忘記瞭老師荀子的勸誡。
王道在李斯心目中成瞭屁,那一刻李斯唯一的念想就是,如何讓自己仕途更進一步。
那以後的李斯,在霸道之路上一去不復返。韓非雖死瞭,但李斯將韓非的思想拿來,用韓非的思想,武裝自己助力秦國。
(秦滅六國)
一輪輪思想改造後。
前230年秦滅韓,前228年秦滅趙,前225年秦滅魏,前223年秦滅楚國,前222年秦滅燕,前221年秦滅齊。
耗時九年,天下歸一!
統一之後的秦國,按照韓非的思路,在李斯助推下,開始瞭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嘗試。
秦王嬴政成瞭皇帝,自稱秦始皇,隨即廢除瞭謚號製度,禁止瞭百官議論皇帝是非的權力,秦國成瞭一言堂。
為瞭配閤秦始皇的集權訴求,在李斯堅持秦始皇配閤下,郡縣製成瞭秦國政體,文字統一瞭,車軌統一瞭,律法統一瞭,中國兩韆年封建大一統的嘗試,在李斯主持下雛形初現。
李斯也順利地在前213年,登頂秦國丞相,走上瞭人生的最高峰。
跟隨仕途登頂而來的,是李斯這個儒傢子弟,對於儒傢的鞭笞。
也是在那一年的鹹陽酒會上,一群博士,藉著酒興弄瞭一場爭論,爭論的主題是,秦帝國是否應當以史為鑒,修改全麵實行的郡縣製。
這爭論,讓秦始皇非常反感,認為這是儒生藉古諷今,插手朝政。
雖然反感,但為瞭一勞永逸解決問題,秦始皇還是授意李斯,將這個問題在朝會上繼續討論,先說道理,後用強力執行,讓這群人知道自己的決心。
(執法決心)
一看秦始皇態度,李斯那有不明白的道理。
在大廷議時,李斯重點強調瞭一個態度,不能
“薄古厚今”,這言外之意就是,你們彆用古話忽悠今人。
說完這話後,李斯又提齣瞭焚書建議。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傢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不知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四年苦役)。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這段建議的威力,可謂巨大,聽過李斯的話,秦始皇非常高興欣然接受!
那麼焚書令的實質到底是什麼?
答案很簡單,就是遏製打壓知識分子對於法傢的批評,這其中,最喜歡藉古諷今的儒傢,當然是首當其衝。
後世無數人都說,焚書令毀掉瞭先秦古籍,其實並非如此,這焚書令針對的一直是民間藏書而不是宮廷藏書,所有的文獻,在官府都有備份,對於文化典籍的破壞並不大,反而是對於人心的震懾更大。
用焚書之舉,行禁絕思想,毀滅“不治而議論”的士階層,讓曾經的百傢爭鳴失去生存的土壤,纔是目的。
至於終極目的也很好理解,全國都大一統瞭,你們這群鬍思亂想的人,也就沒瞭存在的必要,都跟我學法律去。
秦國滅亡後,除瞭極個彆特彆遵從孔子的漢代儒生,提議恢復儒生議政傳統外,幾韆年來,無人敢於觸碰這帝王逆鱗,就算漢武帝時代獨尊儒術後,儒學雖成瞭唯一顯學,依舊沒恢復到先秦時代的氛圍中。
按這角度看,李斯之後再無真儒,被批駁兩韆年的孔子學說,跟孔子關係不大。
這就是李斯的曆史貢獻,用一己之力,完成瞭對於儒傢的改造。
這也讓他,在臨死之前,特彆的從容。
這從容的背後,是一個儒傢叛逆的悔過,也是一個仕途追求者的自省。
我都成瞭儒傢毀滅者,失去瞭理想,也失去瞭仕途,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如果有,或許也隻有對於養老生活的嚮往吧: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齣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那麼李斯的死冤不冤?
不冤,腰斬其實都便宜瞭!
離彆荀子那一刻,他如果真聽瞭師傅“勿違師道”的話何至於此?
就算不能功成名就,保命依舊是妥妥的,又如何會讓儒傢背鍋韆年?
從這個角度看,荀子擔憂的李斯無底綫迎閤秦國的霸道,是不無道理的,因為做人的原則性,纔是人性的底綫,不能指望一個無底綫的人,乾有情懷的事情啊!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