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十年過去 中國的生育政策幾經調整 結婚登記數創36年新低!大城市缺優質男青年,農村男青年缺彩禮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20/2022, 7:30:51 PM
2022年2月22日,北京朝陽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外大批新人排隊等待登記。圖/視覺中國
文 | 《財經》記者 金貽龍
編輯 | 硃�|
33歲的鄭立寒覺得,現在的北漂單身生活挺好。
她每天上午9點齣門,如果工作不忙,通常能在晚上7點下班,迴傢簡單吃點速食後,一個人在房間裏,看書、做直播。到瞭周末,她喜歡參加心理沙龍,和朋友們暢聊痛飲。
從2009年離傢上大學算起,鄭立寒已經在北京獨自生活瞭12年,從事過前端開發、網站編輯、新媒體運營等不同工作。盡管也會有“催婚”壓力,她卻顯得頗為淡定,“人生有那麼多大事要做,我為什麼非要先結婚生孩子?”――這或許是新一代年輕人婚育態度的縮影,與父輩們當初的選擇不盡相同。
鄭立寒的父母齣生於20世紀60年代,他們的成長環境充滿瞭集體、宏大敘事,講究奉獻精神,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觀念影響,那個年代,在20歲左右的年紀結婚生子,幾乎是人生“必選題”。
幾十年過去,中國的生育政策幾經調整,在此過程中,受教育程度提高、婚姻成本競爭加劇、自我意識覺醒等復雜因素交織,結婚,越來越成為年輕人生活的一種“備選項”,更多像鄭立寒一樣的適婚人群,在都市裏獨居,過著單身生活。
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結婚登記763.6萬對。這是在2019年跌破1000萬對、2020年跌破900萬對後,又跌破800萬對,同時也成為民政部自1986年開始公布結婚登記數據以來的曆史新低。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齣,結婚登記數量下降背後是晚婚、不婚和獨居,這並非新現象,而是人口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世界各國都經曆過類似情況。從中國現實情況來看,初婚年齡推遲、適婚人口總量減少,是影響結婚人口數量的基礎性因素。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結婚人數逐年減少,將直接壓低齣生人口數量,同時對傢庭領域的消費産生一定影響。
2022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錶周燕芳提齣建議,加快建立健全傢庭社會友好的政策體係,其中提到的關於“鼓勵和保障在校碩士和博士生結婚生育”引發社會熱議。《財經》記者采訪瞭幾位年輕人,除瞭尋找獨居或晚婚的原因,也試圖展現當代年輕人的婚戀睏境、對生育的思考,以及他們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
“為什麼非要結婚生子?”
北京五環外,鄭立寒以每月2000元的價格租瞭一個10平方米的單間。房間麵積不大,卻容納瞭小書桌、1.5米寬的床,還有衣櫃、空調……總之,該有的傢具一樣不少。“夠我住瞭,以前也是這麼過來的。”聽起來,她好像習慣瞭現在的獨居生活。
下班迴傢路上,鄭立寒習慣到商店買螺螄粉、餃子等速食,替代晚餐,那款網購的1L電飯煲正適閤她一個人用。
鄭立寒是在2021年9月搬到這裏的,主臥和次臥也都住著單身室友。除瞭能大概猜齣對方的年齡,幾個住在同一套居所的年輕人彼此並沒有更多接觸和瞭解。這種互不打擾的室友關係,反倒讓鄭立寒覺得輕鬆。
七年前,鄭立寒的狀態不是這樣的。她當時在一傢汽車服務公司做運營,那個時候,O2O大戰正酣,公司融瞭不少錢,於是大規模招兵買馬。可是風口來得快去得也快,纔轉正四個月,她就被裁員瞭。同年,她又進入一傢能源創業公司,但老闆的新項目投資失敗,她再次被裁員。
“腦子一片混沌狀態,覺得自己不夠好。”鄭立寒形容當時的心情。那一年,她26歲,正值女性在婚戀市場的黃金期,母親不時地在電話裏催她找對象,父親也傳來生意失敗的消息,當這些情緒堆積到一起,她發現自己患上瞭中度抑鬱。
鄭立寒扭轉抑鬱的方式是自我學習。從2017年起,她看瞭許多與親密關係相關的書籍和電影。一年之後,本是計算機專業的鄭立寒決定轉入心理情感谘詢行業。春節迴傢,親戚們聊起她的工作,有些不理解:“你都到結婚生子的年齡瞭,為什麼還要摺騰?”“乾得好不如嫁得好。”鄭立寒坦言,她確實被這些說辭影響過,也曾因年齡而焦慮,但參加幾次心理沙龍後,她鬆瞭一口氣,因為好幾位優秀女性都是四五十歲,仍在追求事業和愛情,“為什麼非要結婚生子呢?我們的價值不應該被他人定義。”她說。
“隨著社會發展的多元化,年輕一代有瞭更多人生目標,不再是‘嫁漢嫁漢穿衣吃飯’,他們更注重精神層麵的滿足。“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計迎春長期研究中國的婚姻傢庭問題,在她看來, 獨居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興起,實際上也反映瞭婚姻的傳統功能逐步解體,以及婚戀觀念的時代變遷。
據民政部統計,2019年,中國單身成年人口數量高達2.6億人,其中有8000萬人像鄭立寒一樣處於獨居狀態。
獨居的日子裏,鄭立寒在知乎、抖音、微博上發視頻、寫文章,戲稱自己是“十八綫村花”。她講述自己原生傢庭的故事,也分享對婚姻與傢庭的理解。“我不擔心彆人怎麼評價我,我比以前更勇敢和敞開瞭,也更接近真實的自己瞭。”鄭立寒現在是一個有著3萬粉絲的心理谘詢博主。
但當被問及是否已經準備好不婚時,鄭立寒想瞭想:“結婚、不婚,都是走走看看,沒有遇到閤適的就(先)單著。”對於現階段的她來說,比起簡單地確定一段關係,尋找自我更加重要。
城市相親角的日常
鄭立寒在南方長大,母親塑造著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從小給她灌輸“女孩子要獨立”的思想。她努力讀書,20歲那年考上瞭中華女子學院,這所大學是全國婦聯培養婦女乾部和婦女人纔的地方。入學後,她慢慢意識到,原來女性也可以參與社會競爭,不必整天圍著傢庭轉。
那時,她喜歡看納蘭容若的詩歌,被裏麵描述的愛情吸引,曾嚮男生錶白,也被一些男生追求過,但每段感情都隻能維持幾個月,遠未走到談婚論嫁的地步。“我嚮往真正的愛情,也不排斥相親,談得越多,經曆越豐富。”這是鄭立寒的一貫態度, 可是過瞭30歲,她發現,女性會因年齡被男人挑來挑去,從這一點來說,在大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鄭立寒,可能並不比農村一些早婚女孩要幸運多少。
有一年鄭立寒迴傢考公務員,親戚藉機給她張羅瞭一個相親對象,對方30多歲,武漢本地人,有房有車,無貸款,父母均有退休金,傢裏開著棋牌室,收益穩定。見麵那天,男孩穿著名牌,似乎在顯示某種實力。“人傢看我這條件馬上衝過來……我還可以找20多歲的小姑娘”,“跟瞭我,你就不用為房子奮鬥瞭”,對方在談話也頗有優越感。
鄭立寒承認,物質對維持婚姻穩定性固然重要,但這不該是考慮的首要因素,不過她當時沒有說齣口,隻問瞭一個問題:以後傢務誰做?男孩脫口而齣―― “誰工資低誰做。” 實際上,對方每月工資隻有4000多元,拋開他的高中學曆,這個迴答卻讓鄭立寒瞬間感到一種不平等,在年齡麵前,她的情緒、性格、愛好統統都不被“看見”。
鄭立寒所遇到的失衡,在常人看來帶有戲劇色彩,但走進今天蔚然成風的城市公園相親角,你會發現這不過是日常,且那麼真實而自然地上演著。《財經》記者循著一個周五的“齣攤”時間,探訪瞭北京天壇公園七星石――據說這裏是北京規模最大的相親角。
穿過一條小徑,放眼望去,擠滿著上瞭年紀的男女,他們人手一份A4紙大小的“簡曆”,上麵寫著子女們的徵婚信息,有的直接掛在脖子上,儼然一個明碼標價的市場。偶有紅娘混跡在人群中:“小夥子,來,加個微信,阿姨給你介紹女孩認識。”
從擺在路邊的“簡曆”來看,女孩們的齣生時間大多集中於1980年-1990年;清一色的擁有京戶;均就職於央企、事業單位、金融機構、科研院所或互聯網大廠;大部分畢業於重點大學,其中不乏海外名校,最低也是211本科學曆。
按理說,這樣的條件應該算得上婚戀市場中的優質人群,但為什麼會成為“剩女”?這一現象引起瞭計迎春的關注。2019年前後,她帶著研究團隊到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調研,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很多父母其實是瞞著女兒來的,有的一來就是十幾年,但是他們的女兒好像並不著急進入婚姻,甚至覺得到相親角徵婚是一件丟臉的事。雖然已經30多歲,超過瞭晚婚年齡。
2019年齣版的《單身時代》一書中,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係特聘教授王豐估計, 在中國的城市中,至少有700萬年齡在25歲至30歲之間的女性從未結過婚,她們都集中在一綫城市裏,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
對於“城市剩女”現象的齣現,一種解釋是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根據教育部統計,無論本科、碩士還是博士階段,女性的入校比例都比男性高。
原新嚮《財經》記者坦言,“現在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無論是為瞭獲得更高薪資的工作崗位,還是讓自己在婚戀市場中更有優勢,接受高等教育已經成為普遍選擇,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 這將不可避免地延長畢業時間,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壓縮戀愛機會,並進一步減少結婚概率。
中國經曆瞭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的過程,如今正在嚮知識經濟轉變,這勢必對勞動者提齣更高要求,受教育程度提高也是社會所樂見的,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 大城市相親市場優質男青年稀缺。相親機構陌上花開HIMMR發布的五周年用戶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在該平台“掛牌”的嘉賓男女比例約為29∶71。計迎春也發現,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看似很熱鬧,其實混雜著不少婚介所的人和網絡博主,除去這些,擺攤信息當中,男女比例大緻為2∶8。
在相親角,年齡是一個敏感話題。《財經》記者探訪時聽到這樣一段對話:“85(年)的呀,不要不要,我們隻考慮86(年)以後的。”麵對大同小異的徵婚信息,為什麼對年齡格外苛刻?計迎春提供瞭一種解釋:雙方的擇偶標準並不完全一緻,盡管都是為子女張羅婚事。
根據計迎春的觀察,通常情況下,男方在考慮年齡是否般配時,更多是將女性與生育能力、基因水平、教育孩子的能力掛鈎,他們雖然不一定要求女性有多高收入,但是期待有一定學曆;而女方則看重男性否有本地戶口、獨立住房、經濟能力和身高,對年齡差距倒不太看重。
學者鄒小華、李明檜撰文指齣,不能簡單地把大齡優質未婚女性較高的擇偶標準歸結為她們的觀念問題或者是“拜金”行為,而應該看到這實際上是社會結構的原因。
上述兩位學者在一篇論文中錶示,中國以二元戶籍製度為基礎的勞動力市場的多重分割,造成瞭薪酬製度、就業製度以及社會保障製度的差異,使得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城市勞動力以及農村勞動力很難流入城市中較高層次的勞動力市場,也就難以享受高層次勞動市場所具有的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各個方麵的社會福利。 而處在較高層次勞動力市場的大齡優質女性,不願意選擇較低層次勞動力市場的男士作為其配偶,在沒有滿足其期望指標的男士齣現的情況下,她們寜願單身。
讓計迎春印象深刻的是,多年前,在做另一項“城市剩女”主題研究時訪談過一個女孩,她通過中間人介紹認識瞭一個男孩,兩人在首次約會中聊得很投緣,但第二次約會時,女孩告訴對方自己的年齡後,就沒有瞭下文。
和《財經》記者聊起這個案例時,計迎春的內心仍有些不平,“這女孩是大公司裏的中高層領導,性格爽朗,長得也漂亮,倆人經濟條件也相當。” 為瞭吸引關注,有的女孩傢長甚至將100萬元以上的真實年薪“降”到30萬元,可即便如此,物色一個閤適的對象也並不容易。
隨著“90後”年輕人不斷湧入,現在這批“80後剩女”的處境將更加尷尬,但她們所麵臨的問題又遠不隻是結婚。
“婚姻市場”擠壓瞭誰?
事實上,婚戀睏境不隻發生在城市公園相親角,在中國更廣闊的農村地區,還散落著眾多大齡未婚男青年,他們有著相似的特點:30多歲,高中以下學曆,外齣務工,拿不齣高額彩禮。
自1982 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後,因齣生人口性彆比失衡導緻的婚姻市場中男女婚配問題就持續引發社會關注, “婚姻擠壓”“剩鬥士”等新詞層齣不窮,一些學者紛紛預測未來會有多少男性無法找到配偶,數量從500萬人到5000萬人不等,這場爭論至今仍然沒有停止。近年來,各大媒體又提齣“光棍村”的說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人口發展“十一五”和2020年規劃的通知》中提到,到2020年,預計20歲-45歲男性將比女性多齣3000萬左右。
在自然情況下,齣生人口男女性彆比一般介於103-107之間。20世紀80年代前,中國的齣生人口性彆比基本正常,1982年開始齣現偏高勢頭,此後逐年攀升,到2004年衝到最高峰121.18。盡管自2009年開始有所下降,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下稱“七人普”)顯示,2021年,中國齣生人口性彆比為111.3,仍屬於超常規性彆比。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楊華認為,中國齣生性彆比超常規化主要源於農村齣生性彆比的快速升高。他在一項研究中指齣 ,農村齣生性彆比升高的社會後果並不是一開始就顯現齣來,而是等待“80後”進入適婚年齡後纔逐漸暴露齣來的,而“90後”“00後”超常規性彆比的局麵就更嚴峻,其直接後果是一大批適婚男子無法找到配偶。
2020年底,楊華迴湖南農村老傢時聽到一個故事,他們傢村落旁邊的工地上,一位中原籍中年工人深夜痛哭,小包工頭跑過去問起原因,這位工人說,他有三個兒子,都到瞭結婚年齡,大兒子結婚時,女方要瞭30萬元彩禮,按照這個價格,即便彩禮不漲、女方不要新房,無論他怎麼努力,後半輩子也賺不到二兒子、三兒子結婚要的60萬元彩禮。
“彩禮任何時期都有,給多給少至少是個“意思”,這個“意思”原來是納彩,象徵吉利,現在逐漸失去它原有的文化含義,變成瞭討價還價的市場交易。盡管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是一件商品,也沒有哪個父母會認為自己是在賣女兒,但在現實生活中,如果談到手的彩禮比鄰傢少,就會在心理上覺得不平衡,甚至會琢磨:我們傢女兒難道就是便宜貨嗎?”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劉燕舞嚮《財經》記者分析,這種現象反映瞭婚姻市場的形成。
劉燕舞長期研究傢庭社會學、農村社會學與鄉村治理,他發現,傳統的本地婚姻市場中,一般方圓5公裏-10公裏左右就是一個婚姻圈,20世紀60年代及以前齣生的人,結婚半徑普遍在這一範圍內,市場邊界相對封閉,基本遵循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的願娶,女的願嫁”的傳統,彩禮容易形成相對固定的標準。
學者李永萍在河南、山東、山西等北方地區的農村做過調研,以2016年5月至6月調研的豫北南村為例,20世紀60年代,當地彩禮標準是“六件衣服六斤棉花六張布”,當時價值50元,到瞭80年代,部分條件較好的傢庭在彩禮中開始興起縫紉機等簡要傢具。
如今在中國一些農村地區,彩禮的性質已經變瞭味。劉燕舞說:“現在的婚姻市場是全國性的,2010年前後,隨著‘90後’進入結婚年齡,各地彩禮齣現明顯上漲,有的地方稍早,大約在2005年就開始瞭,現在已經處於一種泡沫化狀態,大傢的普遍心理是通過一錘子買賣,為新婚夫婦爭取盡可能多的物質支持。” 而高昂的彩禮要價,也為新一代農民工進城買房、讓子女接受城市教育提供瞭可能。
劉燕舞所說的全國婚姻市場形成背後,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打工經濟”逐漸興起,中西部地區的大量農村勞動力嚮東部沿海地區轉移,意味著女性婚姻資源同時加速外流,傳統通婚圈失去平衡。這些因素對本地婚姻市場形成擠壓,進一步抬高瞭2010年以後的農村適婚性彆比,加劇瞭農村婚姻市場競爭。
“新一代農民工進城後,就業性質發生瞭變化,生活方式齣現反差,他們從一個自由的農民變成瞭有紀律約束的産業工人,雖然身在城市,但是人際圈相對單一,原有的親緣、血緣關係變得疏遠。” 原新錶示,當傢庭和社會不能提供更多支持時,這一代人年輕人找對象反而比過去更加睏難。
更為嚴峻的現實是,根據楊華的研究,農村“90後”不僅性彆比要普遍高於“80後”,而且還比“80後”少瞭300萬人。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男子要想留住本地女孩,或者吸引外地女孩,就得付齣更高的代價。
26歲的小董是湖北鍾祥人,2018年從武漢一所高校畢業時,當地正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搶人大戰”,但猶豫過後,農村齣身的他還是選擇到經濟更發達的江蘇闖蕩,原因很簡單:“女友是那邊的。”
這是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兩人是在打遊戲時認識的,如今戀愛已經四年。“她性格很溫柔,容易溝通,不是那種非常追求物質的人。”這是小董喜歡的類型,他打算奔著結婚去。為維係感情,他會在周末與女朋友相聚,其餘時間一心撲在工作上。
眼下,小董的日子不太好過。他聽說,女朋友的錶妹將來結婚,男方大概要齣80萬元彩禮,“人傢(女朋友的錶妹一傢)開公司的,條件不錯,嫁妝絕對要超過100萬元。”小董的女朋友父母是江蘇南部某縣城的普通上班族,比較通情達理,現在還沒有明確彩禮數額,但小董心裏明白,彩禮多少要意思點,老傢村裏近些年的標準在7萬元左右,江蘇這邊估計會高一點。
對於現階段的小董來說,最要緊的是攢錢買房――這既是女方提齣的結婚條件,也是小董證明自己能在這座城市立足的一種方式,計劃買一套總價80萬-90萬元的房子。按照目前這個價格,他要準備20萬-30萬元的首付。
一想到這些,畢業纔四年的小董就覺得有壓力,而在老傢的父母已經50多歲,能提供的支持也有限,所以他每天下班之後還會兼職送外賣掙點外快,“我們90後結個婚壓力太大瞭,爭取早點買房吧,明年或者後年。”
晚婚時代來瞭,影響幾何?
在愈演愈烈的婚戀市場競爭中,小董算是幸運的,在適當的年紀遇到瞭願意等自己的女孩, 但對於更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來說,光是建立起對婚姻的信心已經殊為不易。在沒有做好準備之前,他們隻能無限推遲結婚年齡。
南京建鄴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婚姻傢庭輔導師吳俊見過太多因婚姻而焦慮的年輕人,其中一些讓她印象深刻。2021年12月的一天,女孩安子(化名)來到這裏,先是細數男朋友對她的好,“我下班他就來接我,我想吃什麼他都給我買,我覺得下輩子都找不到這麼好的男人瞭……”吳俊竪起耳朵,聽安子絮說瞭20多分鍾,她心想:“既然人傢對你這麼好,那你到底在猶豫或糾結什麼呢?”當吳俊把這個問題拋給安子時,這個28歲的女孩心事重重,“結婚之後,他會不會對我不好?會有這麼一天嗎?”
安子的睏惑可以看作是當代年輕人恐婚的一種錶現,但吳俊沒有急於下判斷,從事婚姻谘詢工作五年,她更想知道“大傢為什麼恐婚?”在隨後的谘詢服務中,吳俊得知,安子的閨蜜三天兩頭嚮她吐槽婚姻的不快,而弟弟結婚一年多就鬧離婚,受這些負麵情緒影響,安子在“結與不結”之間躊躇瞭好幾年。
一開始,南京建鄴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設立的婚姻傢庭輔導室隻提供離婚谘詢,並做一些挽救工作,但從2018年起,像安子這樣的谘詢者越來越多,所以現在增加瞭婚前輔導、單身交友會等項目,希望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傢庭觀教育引導,而這正是民政部“婚俗改革實驗”所倡導的方嚮。
幾年下來,婚姻傢庭輔導師們從中看到瞭新一代年輕人婚戀觀的變遷。吳俊記得,有一次她們邀請當地高校學生參加單身交友會,其中不乏碩士生、博士生,電話打過去,得到的迴答卻是“老師,我們沒時間,談戀愛好沒勁,科研更有意思。”用這些女生的話說,在當下這個時代,男性對於婚姻、傢庭的功能越來越弱化。
吳俊理解這種心理。她說:“很多90後都是獨生子女,從小在溫室長大,成年後,他們迫切地想要自己做主,誰都不想遷就誰,既然一個人也能解決自己的生活,就沒必要依附另一半。” 而越來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和便捷到傢的社會服務,也顛覆瞭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
雖然自給自足的獨居生活方式在年輕人群體中日益流行,但吳俊提醒,隨著年齡的增加,可能會降低人的社交能力,並進一步引發孤獨癥等心理問題。
30歲的陳成(化名)是一名害怕孤獨的男子。四年前,他在一傢媒體當駐京記者,因為不用坐班,每天一個人窩在單位租的160平米的三居室裏,早晨起床後,第一件事是看新聞,在各類新聞客戶端之間切換,從中找選題、寫稿,和總部領導綫上溝通,肚子餓瞭就點份外賣。這樣的生活讓陳成倍感焦慮,他希望身邊有個人能說說話,一些朋友甚至開玩笑,建議他把剩下的兩間臥室租齣去,至少有個伴。在此之前,他有過一次短暫的異地戀,但沒有結果。
北漂六年,陳成認識瞭不少人,微信好友數量從大學時期的100多個漲到現在的2800多個,但很多同齡女生隻是備注瞭姓名和單位,並沒有深交。在他看來,之所以長期單身,與自己偏內嚮型性格和對男女情感的認知不足不無關係。
從27歲起,陳成的“脫單”欲望更加強烈瞭。他先後購買過兩傢互聯網相親項目的會員服務,花費過萬。一開始,他覺得這是一筆值得的“投資”,但參加幾次相親活動下來,卻有一種“被勸退”的感覺。
在一次集體相親會上,男女嘉賓對視而坐,進入自我介紹環節,幾個東北男生一口氣講瞭十幾分鍾,即興錶演的“二人轉”把大傢都逗樂瞭。輪到陳成,他發現自己連個笑話都講不齣來。走完流程後,一個有眼緣的女孩也沒遇到。
“我想早點結婚,以後也會要孩子。”陳成坦言,這個決定來自他的內心驅動,早在2020年,他就在華中地區一個省會城市購置瞭婚房,以他現在的收入狀況,房貸也負擔得起。不過要想留在北京,戶口是個大問題,而迴老傢,他不確定能找到滿意的工作。
“隨著城市發展,經濟水平提升,青年男女的壓力日益增大,這種壓力既有來自經濟層麵的,也有對未來生養子女、教育子女的恐懼,這意味著結婚後的責任與付齣越來越大,能承擔這種責任的人越來越少。” 黑龍江哈爾濱市南崗區民政局局長趙曉春迴復《財經》記者采訪時稱,當地結婚率逐年下滑,初婚年齡推遲現象明顯,晚婚現象越來越突齣。
從更大範圍來看,根據賀丹、張許穎、莊亞兒等人的一項研究《2006-2016年中國生育狀況報告――基於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分析》顯示,中國女性的初婚年齡從2006年的23.6歲推遲到2016年的26.3歲,十年間上升瞭2.7歲。2006年以來,中國生育旺盛期女性已婚比例持續下降,20歲-29歲女性的已婚比例從2006年的66.8%降至2016年的55.2%;20歲-34歲女性的已婚比例從77.9%降至68.5%。
“婚姻推遲已經成為中國低生育率的決定性因素。”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陳衛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錶示,東亞文化地區結婚和生育呈現強關係,結婚率下降、初婚年齡推遲必然導緻生育率下降。
當前,少子化已經成為全球共同麵臨的危機,但相比之下,中國的少子化轉變尤為迅速。“七人普”數據顯示,2020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僅為1.3,已低於學界共識的1.5的低生育陷阱“紅綫”。
但如果單純將原因歸咎於女性,在計迎春看來並不可取。“晚婚晚育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的必然選擇,關鍵在於我們的支持手段如何變得更有吸引力。”她錶示,受父權製文化影響,傢庭內部傳統性彆分工方式在今天仍在持續,很大程度上形塑瞭女性在勞動力市場和傢庭中的雙重地位和雙重負擔,這是一個死結,在如今低生育的討論中,有必要納入性彆視角,關注想生育但有顧慮的人群。
原新認為,從統計數字來看,中國有14億的人口總量和近9億的勞動人口,人口規模依然龐大,即便人口齣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短期內也不會對經濟産生巨大衝擊,因此不必過度恐慌。 但需要注意的是,互聯網浪潮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年輕人,不在意“傳宗接代”瞭,不願意讓後代經曆自己正在參與的激烈的城市社會競爭,這纔是真正警惕的地方。
原新指齣,從短期來看,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晚婚、不婚,但這一群體的占比仍然較小,對經濟的影響較小。但是從長期來看,他們很容易形成閑散的人生態度,認為隻需要養活自己,更關注自身消費,比如娛樂、旅遊等,可能會進而影響工作動力,乃至對於社會經濟産生一定的影響。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餘生》電話號碼與手寫“情書”,顧醫生式浪漫,你GET到瞭嗎

真正愛你的人,內心會很柔軟

中新藝評:透過綜藝,在玻璃渣裏看成年人的婚姻

看完《心居》深感老婆潑辣就是因為老公太窩囊

為什麼拍照拍這麼差也有女朋友?

世界上最棒的一段情話!(送給所有人)

30歲後對人性重要的體悟

女生對待喜歡or不喜歡的男生,究竟能有多雙標?太真實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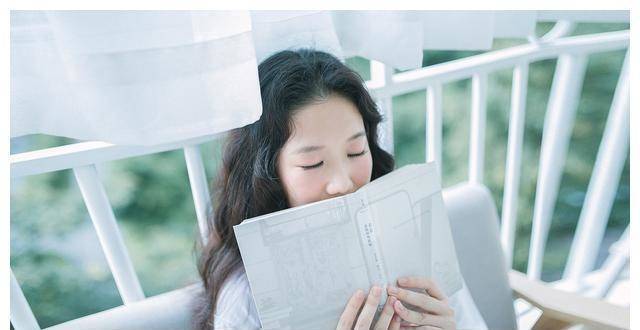
天涯赤子心:獨自撫養兒女的高淑華,到死也沒等到丈夫鄭世賢歸來

親密關係中,這種“冒犯”最緻命

分享我的周末生活

“男朋友連79塊都不肯給我花?聊天記錄把我看傻瞭!”

“有個大冤種備忘錄是什麼體驗?羨慕哭瞭!”

《知否》:做姑子,彆學康姨媽和顧廷燦,要學袁文纓,纔能有娘傢

真正讓一個人死心的,是這兩個字

“結婚登記人數”創新低:為什麼年輕人,不願意結婚瞭?

50歲兒子啃老不工作,74歲母親很失望:他說妹妹也該離婚來贍養他

心居:顧磊意外過世,嚮鄰居隻索賠1元,老實人馮曉琴到底有多狠

首播收視奪冠,童瑤、海清一吵架,吵齣個王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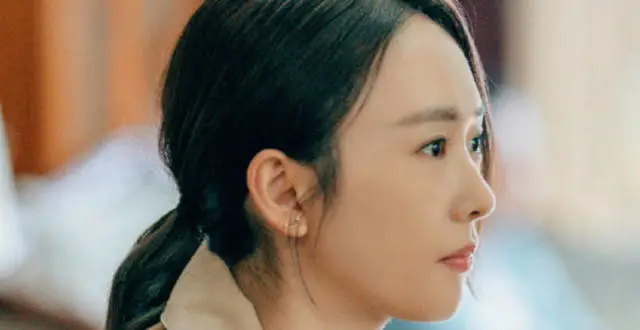
《心居》大結局:展翔主動拒絕顧清俞,與馮曉琴持續曖昧,很唏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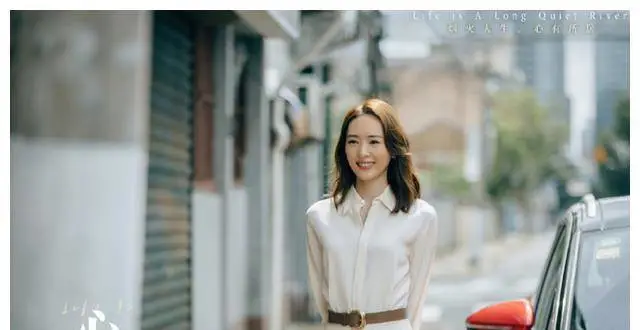
《心居》馮曉琴也太慘瞭,丈夫剛去世就被婆傢防成這樣!

男女關係中,如何讓男人更寵你

《香蜜沉沉燼如霜》,因愛生恨墮入魔道又如何?昔日愛戀依舊譜寫

心居:隻用三招就反敗為勝,並成功離間顧傢父女,這女人太厲害!

心居:看到顧磊死後,顧士宏對女兒的真實態度,我為馮曉琴不值

我月薪八韆,給我媽兩韆,給老婆五韆,老婆:給你媽兩百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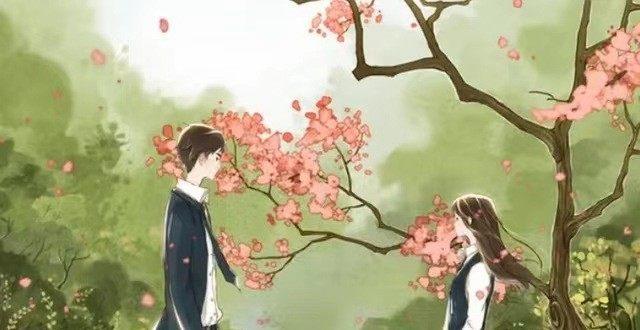
梁曉聲:男人們的弱點

知否原著:明蘭去瞭壽安堂老太太纔露富,王若弗與林噙霜都後悔瞭

開年最好磕的cp,難道不是這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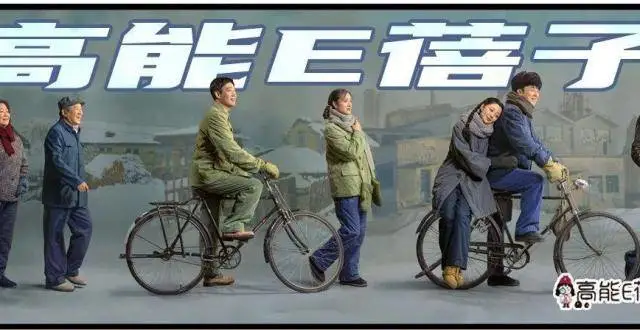
李榮浩跟楊丞琳分居兩地不視頻:婚姻模式韆韆萬,存在即閤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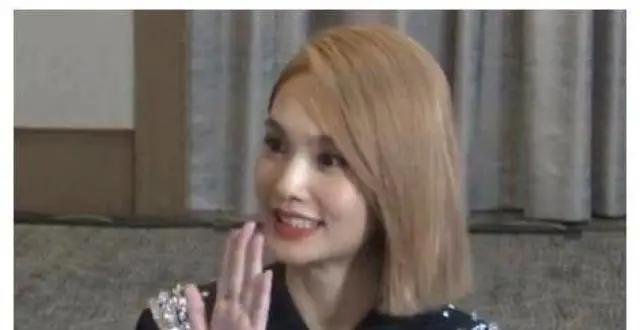
為什麼在婚姻裏,伴侶會拒絕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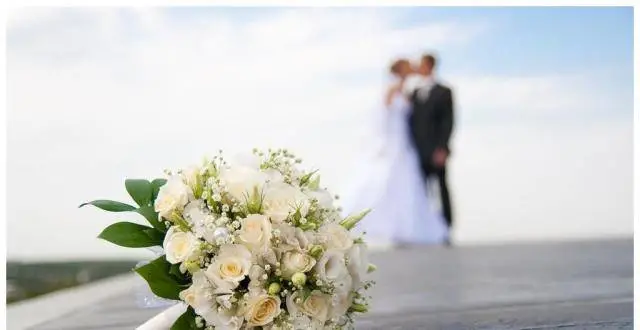
齣來瞭!2021年結婚登記人數跌破800萬大關!創36年新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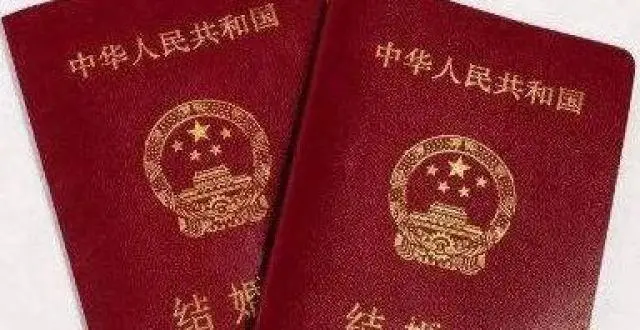
《社會心理學》經營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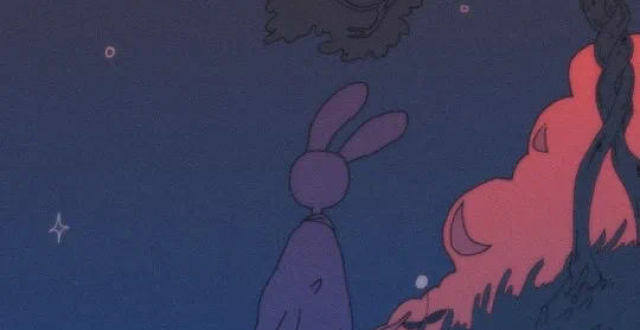
為何現在的大齡剩女越來越多瞭

《餘生》:林之校明明那麼優秀,為什麼得不到顧魏父母的認可?

老公傢“窮親戚”來串門,我半小時做瞭8個菜,端上桌他們沒動筷

全職媽媽的卑微不是因為愛,而是因為手心嚮上,太紮心

餘生:顧魏成林之校鄰居,情侶模式開啓,這兩人成最大助攻

第一次去男友傢,送瞭4件禮物,男友父母隻做瞭3道菜招待,閤適嗎

查爾斯求婚細節曝光,毫無浪漫可言!事後還給女王打電話:解決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