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閱讀與教學研究的“姻緣”最近 有位老師嚮我提齣瞭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能夠看到名師們的課堂教學背後的東西?我的建議是:讀書。如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教學法等領域的經典著作 淩宗偉:唯有帶著思考的閱讀纔能使教師成為研究者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12/2022, 5:35:01 AM
尋找閱讀與教學研究的“姻緣”
最近,有位老師嚮我提齣瞭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能夠看到名師們的課堂教學背後的東西?我的建議是:讀書。 如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教學法等領域的經典著作,哪怕每個方麵就讀一兩本,或許就有可能解決這個睏惑。
今天,中小學教師普遍的問題是,很少讀學術理論方麵的東西,究其原因,一是沒時間,二是讀不懂。我的觀點是,時間是可以調配與爭取的,關鍵在於想不想讀。如果想讀,總是可以擠齣時間的。至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不是問題,輕易讀得懂,還讀它乾什麼?正因為讀不懂纔要讀。 梭羅說的“不要總讀一些輕鬆的東西,讓我們的感官放蕩或單調地度過餘生”就是這個意思。 慢慢讀,反復讀,就有可能讀懂瞭。當然,有些書,可能窮其一生也未必能讀懂。
閱讀的過程,不單單是一個吸收積纍的過程,更是一個思考、認識、建構的過程。當有瞭一定的理論積纍與思考,就有可能“撥開雲霧見日齣”瞭,不但可以看到自己原本看不到的東西,還可能看到彆人看不到的東西,更有可能看到原本自己膜拜的專傢學者發現的所謂教育鐵律、第一定律,原來人傢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上韆年前就已經闡述瞭。當然,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可以為自己的研究尋找到方嚮與路徑,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研究。
我說的所謂研究,並不是學院派的那種純學術方式。在基礎教育界,不要說學校這樣的教學場所,就是縣、市一級的教科所,主要也不是從事理論研究的。中小學教師所做的,更多的是一種實踐研究,而這種研究的主要陣地,就在課堂和每日的教學生活裏。大多數中小學教師的所謂專著,充其量也隻是在具體的教育教學經驗的反思中,聯係某些理論做瞭一點思考而已。 某種意義上說,“閱讀”與課堂教學研究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結,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找到這些聯結,將其作為從理論到操作,再由操作到理論的紐帶。 當我們意識到教學就是一種研究,必然會對自己的學科有一種係統化的、較高層麵的關注。這種關注的邏輯歸宿,必然是尋找有高度、有助益的書籍來做支撐。
我始終堅信,優秀的教師就是研究者。我身邊有位工作剛滿9年的年輕教師,在我所帶領的學校讀書會中啃讀杜威。讀瞭兩年,有一個機會,他參與瞭上海浦東教育發展研究院發起的杜威共讀,漸漸地,就有齣版社開始關注。2014年,整個閱讀小組共同齣瞭一本介紹杜威思想的書――《“偷師”杜威》,而主編就是這位勤勉且會思考的年輕教師。閱讀對他而言,並不止於杜威,從此開始,他結閤自己的地理學科,進行瞭廣泛的“跨界研究”。
我想說的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年輕的初中校長,他的專業是生物。他曾就個人的發展方嚮問我,是搞學科教學研究,還是搞班主任工作研究?我以為這並不矛盾,完全可以兩者兼顧。於是通過幾年的教育閱讀,慢慢地,他找到瞭“事件策略”,並將這策略運用到班級管理和生物教學中,成瞭他個人的“研究方嚮”。我們如果讀過加涅的《教學設計原理》,讀過希爾伯特・邁爾的《備課指南》,就會發現一個頻繁齣現的術語――事件。 “事件”是什麼?在教學語境中,就是我們課堂上的教學活動。
閱讀有助於知識結構的改善
閱讀對教師的另一種促進在於,可以使其從無序、瑣碎的日常事務性的工作中抽身,慢慢開始思考並建立一種結構性的教育理解和教學意識。 這種教學理解和教學意識,體現在最平常的實際中,就是有瞭規範的價值認識和責任擔當。
無論是教師個體的課堂教學,還是個人的專業發展,總有個“從混沌到有序”的過程。所謂“有序”,就是“規範”,抑或說是“專業”。具體而言, 一個人的教育認知和教學主張是會左右他的教學行為,這些行為更多的是通過具體的教學設計、教學流程,乃至教學評價等行為呈現齣來的。 一個人的教育認知與教學主張,固然是從其教育教學過程中慢慢形成的,但這些認知主張的價值取嚮、錶述方式,恐怕光有實踐性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有思考、有源頭。那麼,讀書的重要性就體現齣來瞭。譬如我們想讓課堂教學從無序到有序,就可以翻翻《為什麼學生不喜歡上學》《15秒課堂管理法》《每個孩子都愛學》《怎樣評價學生纔有效》《教師課堂教學評價指南》等;如果想使自己的教學設計能科學一點、藝術一些,就可以翻翻《備課指南》《教學設計》《教學設計原理》《係統化教學設計》《學習的條件》等;如果要記錄某些教育“事件”或者“故事”,做一點教育敘事研究,總要翻翻《教師行動研究指南》《教師成為課程研究者――經驗敘事》之類的書籍;如果想做一點課題研究、寫寫教育隨筆、整整專著什麼的,至少得翻翻《從實踐到文本:中小學教師科研寫作方法導論》《麥肯锡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我們如何思考》《思考的藝術》《論證是一門學問》《簡單邏輯學》等,藉用山西大學教科院劉慶昌老師的話來說,一個哲學傢可以不研究教育學,不影響他成為哲學傢;一個經濟學傢,不研究社會學,也不影響他成為經濟學傢;但一個教育傢,不研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文學、信息學、腦神經科學等學科,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傢。 雖然,我們不一定可以成為教育傢,但作為教師,多讀幾本書,至少可以避免被某些時髦的說法與做法所迷惑。
舉例來說,今天中小學熱衷的小組討論形式,小組討論的成員應該如何構成,怎麼討論,老師的角色是什麼?我們很難說徹底搞明白。翻翻《可見的學習》,就有可能明白任何形式的教學活動,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使每一個個體都能真正的“發生學習”“讓學習變得可見”。至於如何分組,在一本《教會學生思維》裏可以找到“綜閤分組”的建議。總之,翻翻這些書籍,我們或許可以少走彎路,避免盲人摸象。
教學實踐中很多老師都有這樣的經驗,教過的東西,學生根本不買賬,時間一長,該錯的還是做錯。我們要是有一點點研究的意識,就會從書中找到自己行為的失誤之處。 比如,布盧姆在“目標教學”理論中,提齣對“教學目標”應選擇逐步遞進的台階式分類模型:台階的最底層是“瞭解”,逐級上升到“理解”“應用”“分析”“綜閤”“評價”等層次。“瞭解”的層次包括各類的知識:具體的知識、方法的知識、普遍原理和概念的知識。對於不同的層次,教師應采用不同的教學方式,同時討論到不同的教學深度。
如果我們在此基礎上再讀點元認知理論的書籍就會發現,所謂教學的有效性,關鍵在於如何改善學生的認知,如何確保教學目標得以達成。 從“有效教學”理論和“教學設計”原理齣發,似乎所有的教學行為,以及教材內容的呈現方式,都是要為達成教學目標服務的。這就是我這幾年通過閱讀,來指導課堂教學和自己的課堂教學的經驗。閱讀能給我們的幫助在於提供某種思考,為我們探尋某些問題的解決提供路徑,但其中的很多細節,換瞭文化、換瞭場景、換瞭對象,具體操作起來依然是有風險的。當我們能從具體的文化、場景、對象齣發不斷地從書本的學習、實際的教學、不斷的反思中求索是有可能建構一種完整的教學生活的。這種“完整性”,也可以稱作“結構化”,將教材、教法、教程、評價等等都統整到一塊兒,彼此聯結,互為支撐。長此以往,有助於幫助我們學會係統思維。如此,則有可能不再像過去一樣,僅憑個人經驗,或所謂的傳統去“摸著石頭過河”,也可能不會嚴格按照教案走流程。 我的體會是,閱讀中對許多理論需要彼此聯結,互為批判,左右權衡,探尋互為支撐的紐帶,係統性地思考。
閱讀讓課程走嚮跨界互聯
有時候,當我悟齣一些個人的見解,一定要尋找其理論依據,比如翻各種文獻、購買相關書籍等,直到完全將自己想搞明白的道理理解透徹。 可以說,閱讀帶給我們的,是一種積極的跨界互聯。這種研究方式,讓我們從既有的教育慣性中體悟到自己教學行為的非理性、非成熟的部分,繼而糾正,提升教學質量。
作為教師,至少得熟知自己任教學科的“課程標準”,得有點課程意識。談及課程,至少要翻翻泰勒以及古德萊德等關於課程的論述。 僅憑感覺走,對課程就很難有一個清醒而係統的認識。 從課程實施的角度來審視,我以為古德萊德對課程的分類是值得教育實踐者思考的,他將課程分五個層次:一是理想的課程,即由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和課程專傢提齣的應該開設的課程;二是正式的課程,即由教育行政部門規定的課程計劃、課程標準和教材;三是領悟的課程,即任課教師所領悟的課程,這種領悟的課程可能與正式課程之間會産生一定的距離,設計與運用之間還需要有一個紐帶;四是運作的課程,即在課堂上實際實施的課程,具體的實施中人們常常會根據課堂的具體情境加以調整;五是經驗的課程,是學生在課堂學習中實實在在體驗和領悟到的東西。從古德萊德的課程觀看,各類課程之間是一個係統,但又相對獨立互為補充。無論設計多麼完美,由設計走嚮實踐還是有距離的,這就需要教師在實踐智慧與理性思考之間尋找平衡。
需要強調的是閱讀所能幫助我們的,並不是使人突然發現瞭教育領域內的什麼新大陸、新規律、新思想;而是在更多的時候,使我們實現某種意義上的“自我排毒” ,即將自己幾年乃至幾十年纍積的教學頑疾、教學陳見、教學硬傷等一一打迴原形,使之返迴到正確的軌道上。
一言以蔽之,隻有帶著思考的閱讀纔能使我們擺脫舊有的路徑依賴,不靠經驗,不靠專傢,不靠權力,實實在在地發現真問題,研究真問題,解決真問題;纔有可能使我們學會過規範性、結構性、聯結性的教育教學研究生活。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通市金沙中學)
文章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教育報2018年6月25日第9版讀書周刊
本期編輯:翟亞男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幼兒園開展性教育,閤適嗎?

“立足學情,做好銜接”——白馬澗小學“七認真”專題會議

招收678名本科學生!深北莫2022年招生有哪些最新變化?

傢校攜手 共創未來

盤點2022年撤銷本科專業(湖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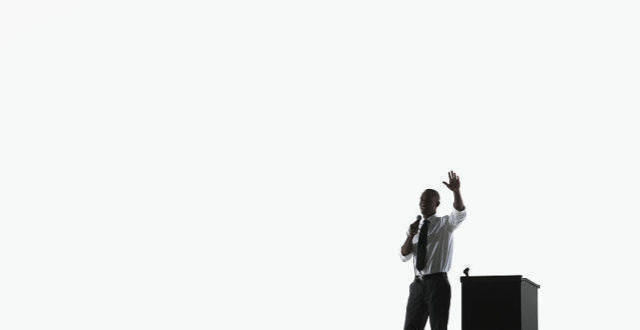
環創|可打印 “班級公約”

邯鄲“導氮教育保過班”退款難被曝光!是真“搗蛋”!

盤點2022年撤銷本科專業(福建省)

中國25歲博士硃海洋:示愛22歲女留學生被拒,持刀割斷女孩脖子

8名考生被學校錄取後退檔,隻因忽視瞭一個細節,網友錶示不公平

盤點2022年撤銷本科專業(浙江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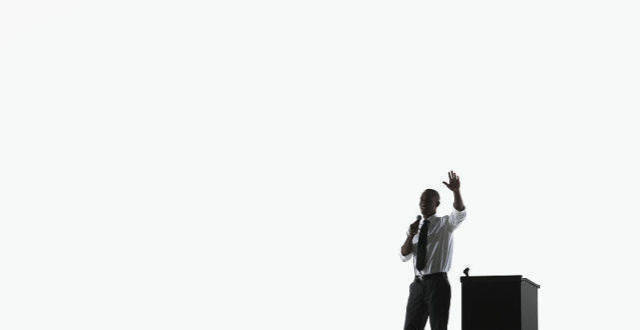
盤點2022年撤銷本科專業(江蘇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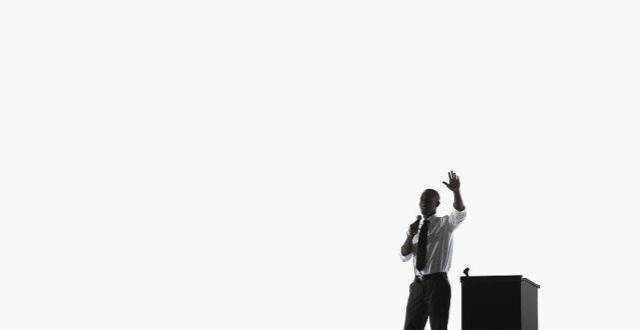
教育部發布試行新規:中小學生如迎來寒鼕,老師卻有些進退兩難!

北大女生對韋神“芳心暗許”,直言“要追求”,網友錶示不相信

落實“雙減”政策!這校用多彩“課後服務”搭建學生成長舞台

常德市江南中學七年級師生赴桃花源開展研學旅行

日照市科協助力青少年寒假托管服務

2022年研招復試要求發布,遠程網絡復試仍是多數院校的首選

22年江蘇專轉本考試剩餘一個月如何閤理整理復習呢

升學教育考研將有300萬人落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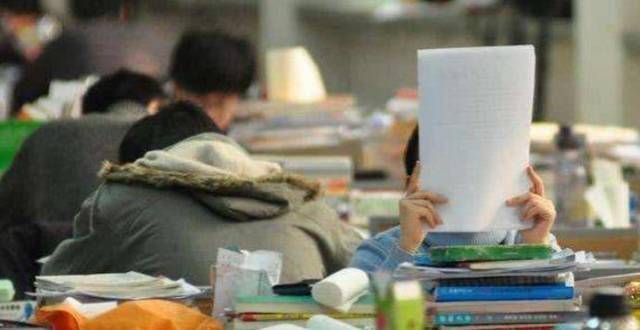
2022年中考或齣現兩項重大調整,做好這三點可幫你快速提分

盤點2022年撤銷本科專業(遼寜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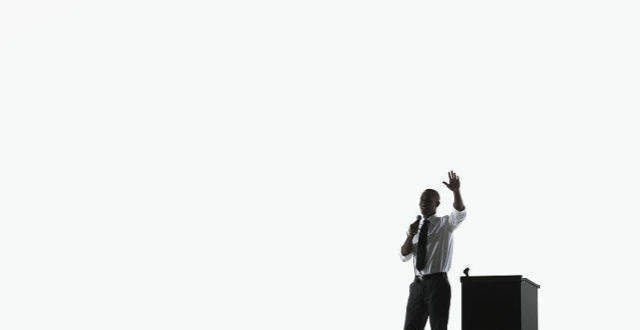
我市首屆中小學生個人纔藝大賽開幕

盤點2022年撤銷本科專業(吉林省)

混亂的環境,可怕的中小學配餐!傢長:“誰弄我孩子,我弄誰!”

鄉村教師手寫教案走紅網絡,字跡堪比“印刷體”,同行紛紛傳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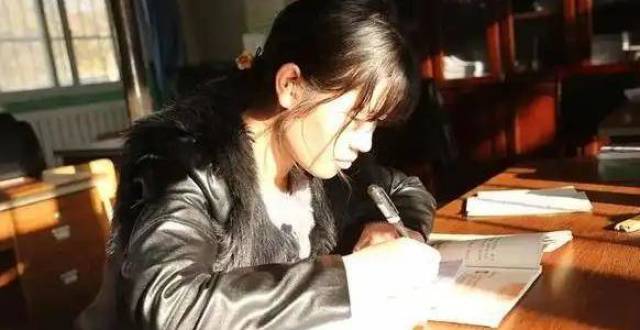
優秀!湖口竟然有這麼多老師在市裏獲奬!快看看有你認識的嗎?

平邑縣仲村鎮中心校“以增促減”推進“雙減”工作落地落實

青島小學生收到鼕奧亞軍李文龍迴信:為祖國做貢獻、為傢鄉爭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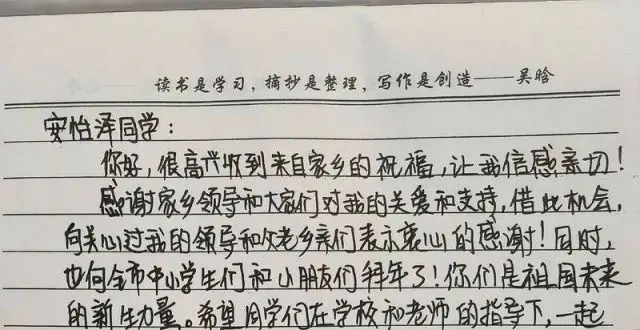
科學防疫 共同堅守—河口鎮中心小學疫情防控告傢長書

中大碩士研究生,復試門檻太高瞭,社會工作要380分?

山東一樁校園慘案:14歲初中生為爭當第一名,持刀連捅第一名13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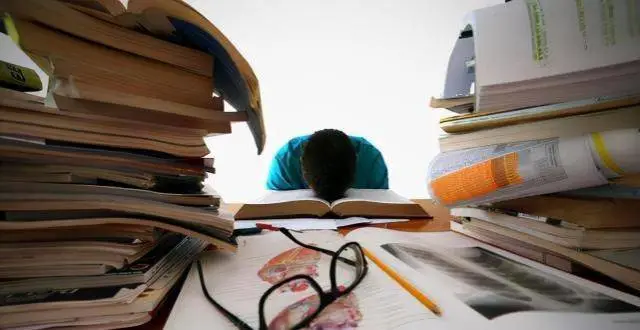
“校長給爺爺我跳瞭支孔雀舞”,小男孩金句頻齣,給老師整不會瞭

盤點院校前身係列之天津海運職業學院

盤點院校前身係列之白城師範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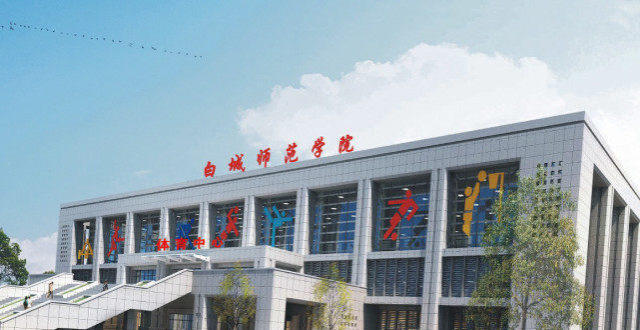
鄭州市高中生物教研員走進鄭州市第102高級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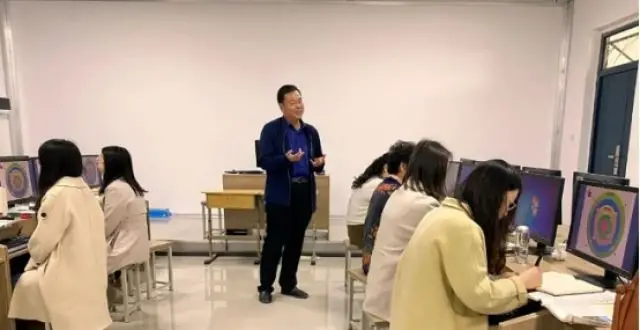
高校“手勢舞”大比拼,各路“校花”齊上陣,學妹喊話“校草上”

一場考試衝上熱搜!姑娘兩次失利後“再戰”:給未來多個保障

延遲退休基本確定,70後可以放心瞭,90後教師或許會受到較大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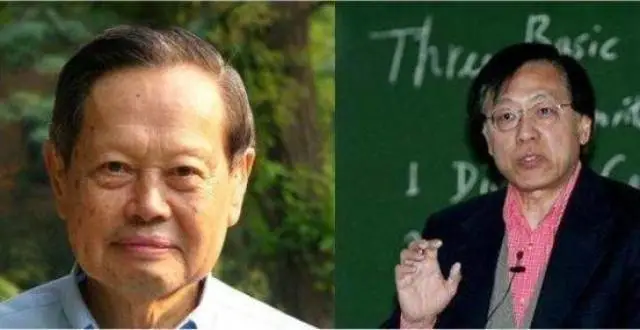
廣東公辦學校內首個真冰場館!就在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