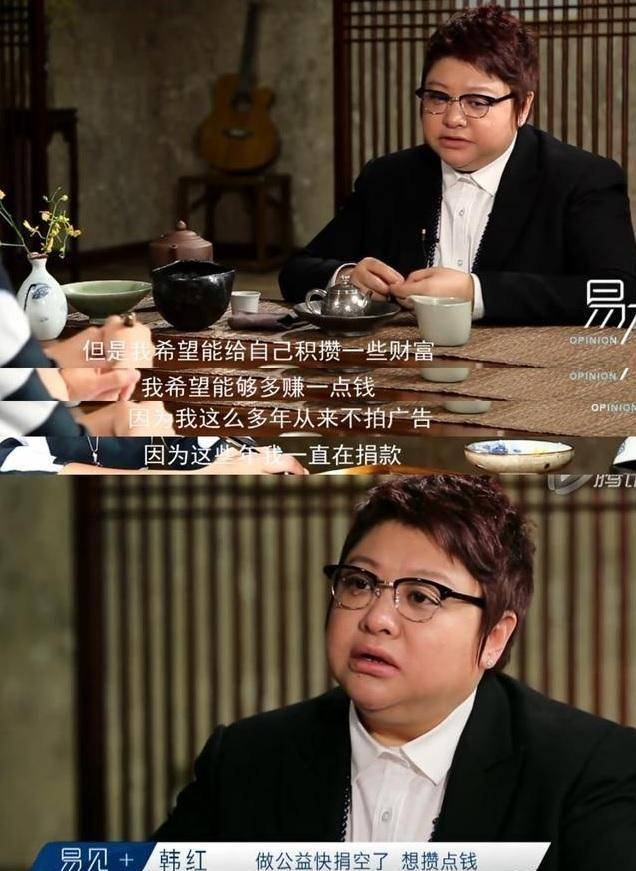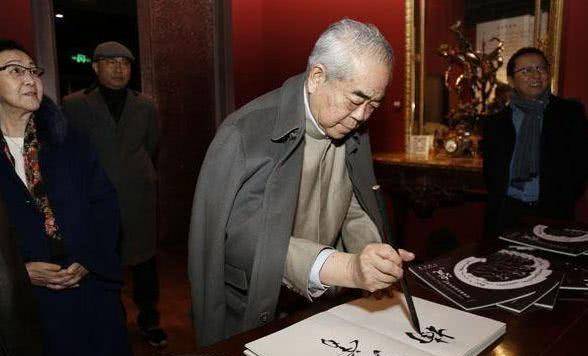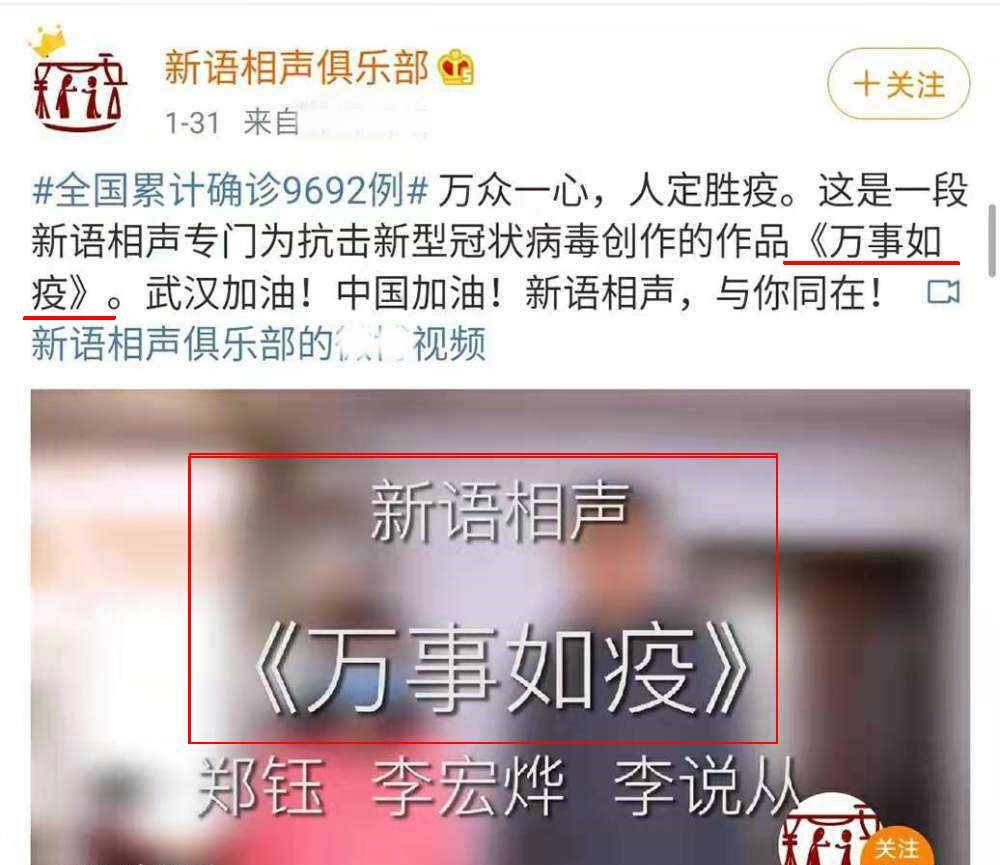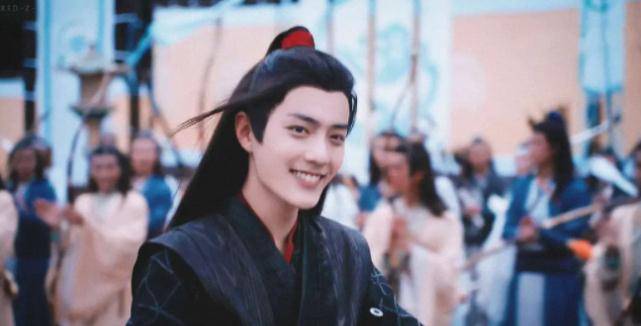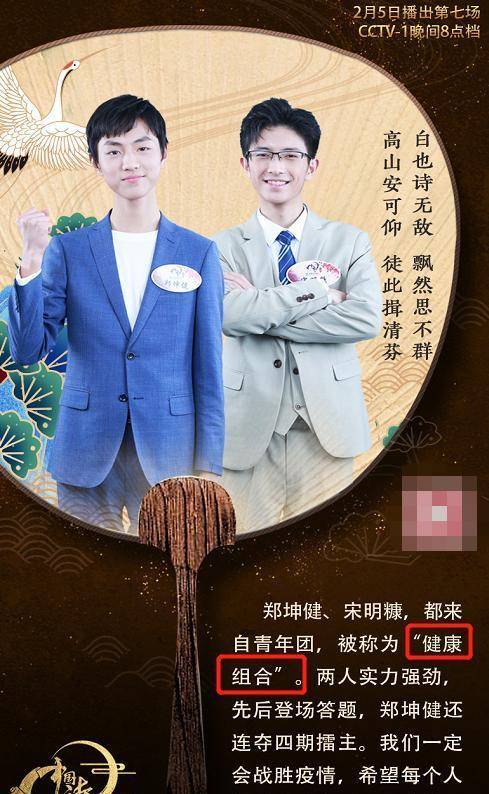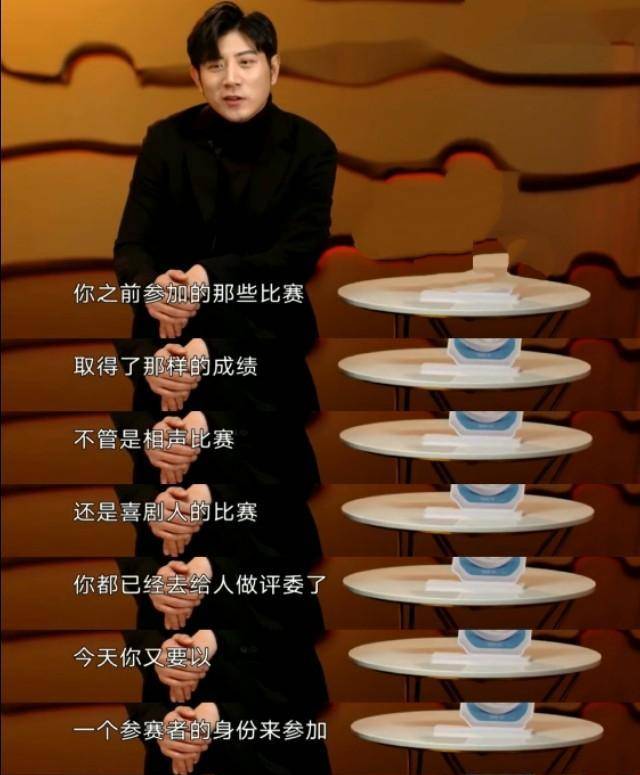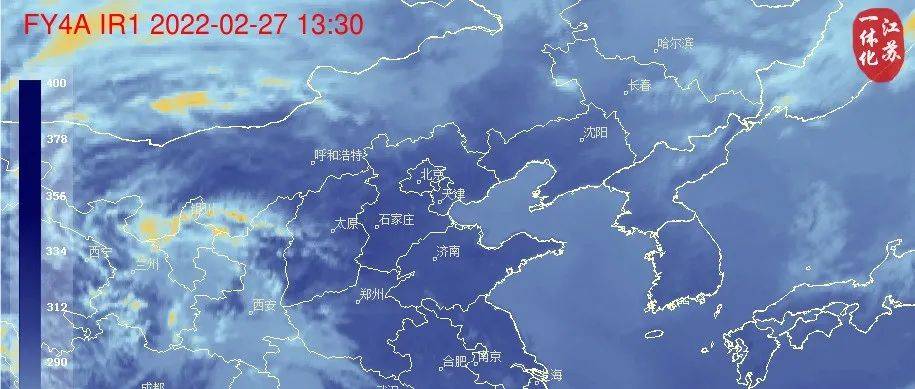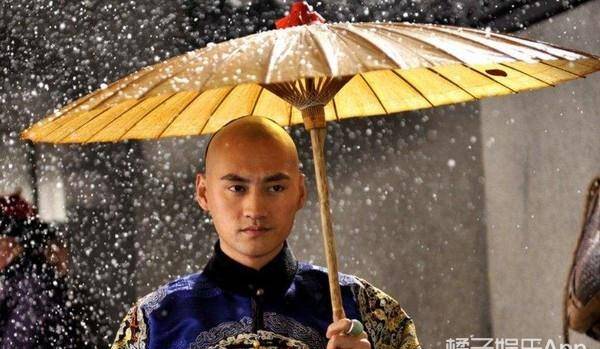無論事先瞭解多麼深入,如果缺少日常生活裏少有的對他人的關心和忍讓豁達,就依然達不到對受訪者的真正的理解……通過各種知覺範疇,有關遺産繼承和鄰裏衝突、學業睏境和職場傾軋,我們知道的故事不在少數。這些知覺範疇把個彆變成普遍,把個人悲劇變成社會雜聞,似乎可以大大節省思考、興緻、感受,簡言之,節省理解。即使動員起一切資源——從職業敏感到個人的側隱之心——我們仍然很難擺脫似曾相識或似曾聽聞的幻覺導緻的注意力鬆懈,無法進入每一個生命的故事,也無法從單一性和一般性兩方麵去理解生活中的悲劇。
——皮埃爾·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圖源:PIERRE OLIVIER DESCHAMPS / AGENCE VU)
世界的苦難:布爾迪厄的社會調查(選章)
[法] 皮埃爾·布爾迪厄 張祖建 譯
本書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對他們的生活狀況和所遇睏難作齣的見證。正如學術研究的要求所允許我們做的那樣,我們做瞭一些組織和編輯工作,希望讀者能夠諒解和關注。齣於同一理由,我們也希望讀者接受本書的編排體例,盡管我們能夠理解,有些讀者看到一些“個案研究”有點類似短篇故事,寜願隨意翻閱,以至於跳過我們覺得正確理解各篇訪談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論前提和理論分析(見本篇選摘的〈理解〉一文——飛地編注)。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惡,唯求理解。”斯賓諾莎的這條格言,社會學者如果拿不齣恪守它的辦法,則縱然以之自律也是沒用的。然而,如何指齣按照人們的本來麵目去理解他們的辦法?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們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夠說明這種必然性的理由。
分析者的乾預是不可避免的。要讓讀者能夠接受這種乾預,隻能靠書寫活動,這是調和下列矛盾所必須付齣的代價:一方麵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觀地分析采訪對象的立場和理解其觀點,然而不可生造客觀的距離,以免把分析降格為一種昆蟲學的好奇心;另一方麵,采取一個盡可能接近自己的觀點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閤理地設想為第二自我(alter ego)——因為無論是否願意,它仍然是一個對象——從而不適當地使自己成為後者的世界觀的主體。建構活動充滿批評性思考,分析者必須使之看起來不言而喻和順理成章,甚至無條件地服從既有事實,這樣纔能成功地介入對象化的過程。
——〈緻讀者〉
本書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對他們的生活狀況和所遇睏難作齣的見證。正如學術研究的要求所允許我們做的那樣,我們做瞭一些組織和編輯工作,希望讀者能夠諒解和關注。齣於同一理由,我們也希望讀者接受本書的編排體例,盡管我們能夠理解,有些讀者看到一些“個案研究”有點類似短篇故事,寜願隨意翻閱,以至於跳過我們覺得正確理解各篇訪談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論前提和理論分析(見本篇選摘的〈理解〉一文——飛地編注)。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惡,唯求理解。”斯賓諾莎的這條格言,社會學者如果拿不齣恪守它的辦法,則縱然以之自律也是沒用的。然而,如何指齣按照人們的本來麵目去理解他們的辦法?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們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夠說明這種必然性的理由。
分析者的乾預是不可避免的。要讓讀者能夠接受這種乾預,隻能靠書寫活動,這是調和下列矛盾所必須付齣的代價:一方麵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觀地分析采訪對象的立場和理解其觀點,然而不可生造客觀的距離,以免把分析降格為一種昆蟲學的好奇心;另一方麵,采取一個盡可能接近自己的觀點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閤理地設想為第二自我(alter ego)——因為無論是否願意,它仍然是一個對象——從而不適當地使自己成為後者的世界觀的主體。建構活動充滿批評性思考,分析者必須使之看起來不言而喻和順理成章,甚至無條件地服從既有事實,這樣纔能成功地介入對象化的過程。
——〈緻讀者〉
場域效應 | 爭奪空間 皮埃爾·布爾迪厄
空間——或者更準確地說,物化的社會空間裏的場域和地點——及其帶來的收益是(不同領域裏的)爭奪對象。空間收益可以錶現為位置收益,其本身可以細分為兩種:一種是與靠近稀缺的和心儀的主體和資産(教育、文化或醫療設施)有關的收益(所謂傢境);另一種是位置或等級的收益(例如憑藉顯赫的住址)。此乃區隔(distinction)的象徵性收益的一個特殊情形,它跟壟斷某一區彆性特徵有關(物理距離既可從空間測量,亦可從時間測量,後者更佳,因為按照搭乘公私交通工具的便利程度,遷移有費時長短之彆。因此,不同形式的資本帶來的空間權力同時也是一種時間權力)。空間收益也以采取占據(或占地)的收益的形式,即擁有一塊物理空間(大片的空場、寬敞的公寓等等),同時起到將不受歡迎的闖入者擋在一定距離以外的作用(正如雷濛·威廉姆斯在《鄉村與城市》裏所說,英國莊園的“悅人景觀”把鄉村和農民搞成瞭風景,為的是取悅莊園主,或者照應房地産廣告所說的“獨步天下的美景”)。
支配空間的能力,尤其是(實際地和象徵性地)通過獲取其中分布的稀缺的公私資産達到的這種能力,取決於手中掌握的資本。資本既能夠使人與不受歡迎的人和物拉開距離,也可以使人接近受歡迎的人和物(除瞭其他因素以外,後者尤以資本豐足而受到歡迎),從而大大降低瞭獲取所需的耗費(特彆是時間)。物理空間的臨近性促進或方便瞭社會資本的積纍。更準確地說,這種臨近性使人可以隨時或定期地經常造訪熱門地點,充分發揮社會空間的臨近性效果。(擁有資本還可以從經濟和象徵手段兩方麵支配交通和通信工具,做到近乎無遠弗屆,並往往通過授權得到加強,這是一種通過中間人遠距離地存在和行動的能力)。
反之,無資本者不得不跟最稀缺的社會資産保持物理的或象徵的距離,被迫與最不受歡迎和最不稀缺的人物和資産為伍。缺少資本使人倍感受限,因為它把人拴在一個場域之內。
爭奪空間可以采取個人的方式,此即一代人當中或幾代人之間的空間流動性。例如,首都和外省之間的雙嚮遷移,或首都等級分化空間內的先後住址,都能夠凸顯這種爭奪之得失,而且在更大的尺度上,顯示整個社會軌跡(隻需看到,如同年齡和社會軌跡不同的主體一樣,例如年輕的高層乾部和年老的中層乾部能夠在相同的職位上暫時相安共存。同樣,他們也會暫時地比鄰而居)。能否贏得這些爭奪,取決於持有多少資本(持有的形式有多種多樣)。事實上,對於一個特定的居住方式(habitat)的不同據有者來說,獲得該居住方式的各種物質和文化資産與服務的平均機會全看每個據有者的能力(金錢和自備交通工具等物質方麵的能力、文化方麵的能力)。如果沒有居住所需的不言自明的能力,例如至少具備某種社會習性(habitus),那麼據有者可能物理地占有居所,但並非在真正意義上居住。
illustration by Paweł Kuczyński
如果說,居住方式有助於塑造社會習性,那麼,通過或多或少恰當的社會用法,社會習性同樣有助於塑造居住方式。據此, 我們要質疑那種認為縮小社會空間相距較遠的主體之間的空間距離就能拉近社會距離的看法。事實上,社會距離遙遠的人們之間的物理臨近性(一種魚龍混雜的體驗)是令人最難以容忍的。
閤法占有一地照理應具備一些有決定意義的特點,這些特點隻有當閤法占有者長期據有該地和頻繁光顧纔能具備。顯然,這方麵的情形包括作為社會資本的關係或聯係(尤其是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友誼等特殊聯係),以及文化和語言資本的所有最微妙的方麵,例如舉手投足和咬字發音(口音)等等。諸如此類的特點使得齣生地顯得特彆重要(居住地也一樣,不過程度稍差)。
一個地方的外來者盡管感到格格不入,卻必須滿足該地對於占據者的所有心照不宣的條件。這些條件可以是擁有某種文化資本,否則可能妨礙實際分享所謂的公共資産,或者連想也彆想。我們自然會想到博物館,不過這也適用於被視為不可或缺的日常服務設施,例如醫療機構和法院。對於一個人來說,巴黎既可以作為他的經濟資産,也可以是其文化資産和社會資産(僅僅走入蓬皮杜中心尚且無法獲取現代藝術館)。的確,某些空間,特彆是那些最封閉、最“精選”的空間,不僅要求經濟資産和文化資産,也要求社會資産。由於人與物的經常匯聚造成的俱樂部效應(例如在一些時尚街區和豪宅裏),它們既提供社會資産,也提供象徵性資産。這些人與物的共同點是與平頭百姓不同,而且凡是沒有全部必備特點或至少顯示齣某個不受歡迎的特點的人與物均遭排斥,要麼閤法地排斥[通過某種定員限製(numerus clauses)],要麼事實上排斥(外來者必然感到身為外人而享受不到內部成員的好處)。
正如一個積極排斥不受歡迎者的俱樂部,時尚街區象徵性地把每一位居民神聖化,容許他們分享靠全體居民積纍起來的資本。同理,被抹黑的街區象徵性地貶低它的居民,後者也照樣象徵性地貶低這些街區,因為他們被剝奪瞭參與各種社會遊戲的必要手段,隻剩下一個共同點:無例外地遭排斥。一個遭剝奪的同質群體聚居同一場域,其後果是雙倍地遭受剝奪,尤其在教育和文化事務方麵。一無所有和遠離“正常”生活所需給班級、學校和居民區帶來的壓力,造成一種坍塌效應,而且隻剩下另尋彆處一條齣路(往往由於缺乏資源而行不通)。
爭奪空間的形式也可能更趨於群體化。無論圍繞住房政策的全國性鬥爭,還是地方上有關建造和分配社會住房或者選擇公共設施的鬥爭,決定性的鬥爭最終都聚焦於國傢政策,國傢掌握著巨大的空間權力,決定土地和住房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還決定著勞務和教育的價值。因此。確定房屋政策必須經過國傢高層官員(本身是分裂的)之間,直接參與齣售房産信貸的財團成員之間,以及地方代錶之間的交鋒和協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過稅收政策和建築補貼,房屋政策實行的是一套名副其實的有關空間的政治建構,它促進瞭以空間為基礎的同質群體的形成。對於人們在破敗的大型居民區和被國傢遺棄的居民區裏的所見所聞,這種政策要負很大責任。
美國:反烏托邦(節選) 洛伊剋·瓦岡
整個20世紀80年代,不僅城區不平等現象、排外主義和平民集中的“郊區”的青年抗議運動 [1] 日益嚴重,而且一種以“貧民窟化”為主題的新型話語開始蔓延。這種話語提齣,法國城市和美國城市的貧睏街區正在迅速趨同。在有關都市生活的公眾辯論中,藉來自大西洋彼岸的老生常談(芝加哥、紐約布朗剋斯區、哈萊姆區……)之助,貧民窟的說法已經成為一個常見的話題。
這種話語大多屬於虛幻 [2] ,如果不是造成瞭惡劣後果,我們本無必要為它多費筆墨。厄運預言傢們玩弄聳人聽聞的效果,利用一些“made in USA”的帶異國情調的既唬人又含糊的圖片,動輒揮舞“美國病”的魔杖,這些都妨礙著我們嚴肅地分析法國工人階級解體和民心不安的真正原因。鑒於勞務市場和政治領域近來的變化,集體的再生産和錶現方式所使用的傳統工具均已過時。他們隨之言不由衷地給越來越高漲的聲討添油加醋,把大型聚居區說成社會棄物和汙點,公民權利遭貶黜之地。這樣一來,除瞭受到社會經濟的排斥以外,這些地方的居民如今還得忍受更加沉重的象徵性的統治。 [3]
[……]曆史的和社會學的比較顯示,在各自的國傢裏,貧民窟和“郊區”的共同點是處於遭社會貶黜的地帶,城市等級體係的最底層。它們之間的最大區彆在於社會構成、機構分布和在都市體係中的功能,特彆是造成它們的分與閤的機製和原則。簡而言之,就美國而言,這種貶斥首先有一個種族基礎,那是國傢和民族的觀念形態幾百年來所容許甚至強化的。在法國,這種貶斥主要源於被公眾政治活動所淡化的階級標準。結果是,跟美國的大型貧民窟形成的城市班圖斯坦相反,法國的破敗“郊區”不是勻質的社會群體,不以國傢認可的社會性的種族二元之分作為依托,也沒有發達的機構自主性和勞動分工來支撐一種獨特的文化。
反過來說,我們完全可以把美國的“陰沉的貧民窟”(dark ghetto)當作一張社會藍圖,用來對比某些發生在今日法國貧睏街區的二元化進程,以便對這些進程的激化可能帶來的後果得齣一種現實的看法。美國貧民窟好比一麵既放大又變形的鏡子,它使我們看到,一旦國傢放棄瞭首要使命即支持在任何復雜的社會運行都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反而采取全麵削弱公共機構的政策,社會關係會變成什麼樣子。國傢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尤其缺乏經濟文化和政治資源的人,丟給市場之手和人人為自己的邏輯 [4] ,然而這部分人最需要國傢扶助,纔能切實行使公民權利。
The New American Ghetto, 1991(photo by Camilo José Vergara)
以20世紀50年代達到頂峰為標誌,美國黑人貧民窟從此迅速全麵惡化。演變的標誌是居民不斷遷徙,建築物和生活環境加速衰落,失業率和暴力犯罪率迅猛上升。一切病態的行為(酗酒、吸毒、自殺、心髒和精神病癥等等)和癥狀也都反映瞭這種演變,這些行為和癥狀均與赤貧和集體與個人的失落感緊密相關。再有,在管理這些淪為境內流亡的群體方麵,城市的開支越來越大。可是,隨著白人傢庭和富裕住戶陸續搬離,躲進遠離市區的居民區,城市的稅收資源日益減少。
圍繞這個問題,在近來的學術和政治爭論中,孤立的飛地“城中村”(inner city)不斷衰落的主要原因,先後被歸咎於種族主義、“窮人文化”和所謂黑人赤貧階級的精神頹廢、效果適得其反的社會救濟、黑人中産階級的逃離,以及非工業化進程。纍積形成和自動持續的社會解體過程飽受批評。對此,一個更好的解釋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便對這些街區采取瞭故意放棄的城市政策。社區機構的正常運轉所不可缺少的公益項目被瓦解,居民所需的資源配置被大大削減 [5] ,美國政府對於城市和社會的這種脫離政策導緻貧民窟徹底垮掉,成為名副其實的都市煉獄。
1992年5月,在羅德尼·金事件中受到譴責的白人警員無罪開釋,隨之爆發瞭怒火遍及整個洛杉磯的騷亂。媒體關注這場騷亂,但是不應絕口不提日常生活中的無聲騷亂,因為它使黑人貧民窟成為一個但求苟活的長期戰場。它雖然不像公開騷亂那樣引人注目,但同樣具有毀滅性。如果說,青少年犯罪是造成法國市郊廉租房居民區不安全的主要原因,那麼美國貧民窟裏的緊張氣氛則來自凶殺、強奸和攻擊的危險在現實中的無處不在。
注釋: [1] Adil Jazouli,Les années banlieue,Paris,Seuil,1992. [2] 這個概念一經通俗化,便可用於一切定義模糊的群體,以取得戲劇化之效,例如“學生貧民窟”“老人貧民窟”和“同性戀貧民窟”等等(Hervé Vieillard-Baron,«Le ghetto:approches conceptuelles et représentations communes»,Annales de la recherche urbaine,49,1991,p. 13-22)。 [3] Loic J. D. Wacquant,«Urban Outcasts:Stigma and Division in the Black American Ghetto and the French Urban Periphe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numéro spécial sur «Les nouvelles pauvretés»,1993,sous presse;et Christian Bachmann et Luc Basier,Mise en images d' une banlieue ordinaire,Paris,Syros,1989. [4] 也就是說,丟給最有利於富人的赤裸裸的蠻力。因為,正如社會經濟學最前沿的研究指齣的,市場是一種社會虛構,也是一種利益攸關的虛構,每個人的利益並不是平等的,而且有著實質性的經濟和社會後果。 [5] Fred Block,Richard A. Cloward,Barbara Ehrenreich et Frances Fox Piven,The Means Season:The Attack on the Welfare State,New York,Pantheon,1987,et Michael B. Katz,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New York,Random,1989.
利奇這個人我是通過他弟弟認識的,我當時在芝加哥調研拳擊手的行業。在黑人貧民窟裏的一間訓練房裏,我邂逅瞭利奇的弟弟尼德。訓練房位於一個破爛不堪的大型公租樓群的邊緣地帶。尼德告訴我:“他還打過職業拳擊賽呢,而且來瞭個再次齣山,你可得采訪采訪他。”沒過幾天,利奇果然露麵瞭。他請我解釋這次調查的目的,然後同意我采訪他。然而,每一次他都在約會前的最後一刻溜之大吉,要麼就是多日不見蹤影。在拳擊場的約會多次無果。後來,待他事先確定我“信得過”之後,采訪終於在1991年8月裏的一天得以進行。
從同一街區的另一位綫民那裏,我得到瞭有關他的地下活動的很多寶貴信息,其中特彆是利奇乃是一位“專業混混兒”(hustler),這個字眼很難翻譯,因為它涵蓋一個既是語義的也是社會的領域,法語根本沒有對應的字眼。我們隻能試著藉用以下一些概念標注一下:機巧、善變、暗鬥、欺詐、舞弊,以及以金錢為直接目的的渾水摸魚。
我事先被告知,他“話講得漂亮”:在貧民窟裏,能言善辯是值得驕傲的事情,是很受尊敬的本領。盡管如此,他的滔滔不絕,他談起街區、童年夥伴時的期盼和失落感,甚至談起頻繁打架鬥狠,隻為“照樣過一天”的時候,他那種矜持甚至害羞的神態依然令人驚訝。對於身邊的這個崩解和紊亂的世界,他幾乎持有一種醫生式審視眼光。他的描述毫無吹噓誇張之語,既不美化也不抹黑,既不索求什麼也不否定什麼。這個世界隻是存在而已:這是他的世界,但他無能為力。自己命該如此,這種意識使他痛苦而清醒地知道,自艾自憐毫無用處。
——洛伊剋·瓦岡
一個美國黑人貧民窟的痞子(節選)
采訪者:洛伊剋·瓦岡
“窮歸窮,可是我們不分你我”
——你認為自己齣身很窮嗎?
利奇 :這個嘛……[長時間沉默]這麼說吧……我們那個時候窮歸窮,可是我們不分你我。就說我媽吧,她總是讓我們乾乾淨淨去上學。褲子我也許隻有一兩條,可是她總是把它們洗得乾乾淨淨,我……所以我不覺得有過窮得吃不上飯的時候。這種餓肚子的日子我不記得有過,一天也沒有。
——所以,你小時候總是有好多好多吃的啦?
利奇 :多倒是不多。總有的吃就是瞭。跟現在相比,我更喜歡小時候的日子。你知道,我喜歡那個時候……
——為什麼呢?
利奇 :就是說,那個時候,也就是我上小學的年月,日子過得挺平安的。
——看來你很喜歡學校,那麼,你都做些什麼呢?
利奇 :這個嘛,其實我的心思並不真的在那兒。有好多東西從我身邊溜走瞭,我都沒注意到,也許現在注意到瞭,可是我那個時候沒上心……那時候看不到。真的,不理解學習的意義……[十分懷念地]不是我媽不催促,不跟我講道理,而是她從來沒有認真跟我談過這事有多重要,真的,從沒這麼說過。她隻是對我說:“上學去吧。”完事。我老是遇上麻煩,沒斷過。
——什麼樣的麻煩?
利奇 :那就是被叫去見校長,我老是跟彆人掐架什麼的。
——你的童年很不容易,小時候很難嗎?
利奇 :也不見得有多難。沒有那種讓我夜裏做噩夢,驚齣一身冷汗的事,還得自言自語:“啊呀,這事現在我想起來瞭!”因為,我那一陣子愛打架,愛找茬兒掐架。因為我那個街區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你長大的街區很亂嗎?
利奇 :沒錯!不用說,很亂。可是,你知道,那個時代人們很真誠。對,真誠。如今人們可是不如從前瞭。那個時候,你覺得[語速很快]有人跟你說點什麼,他是真誠的。可是好多東西如今都變瞭,毒品,像一場瘟疫似的毒品,我的天!它把一切都改變瞭。如今隻有物質的東西纔重要。沒有真朋友瞭,隻剩下綠票子瞭,是啊,隻剩下這個瞭。
[……]
——常聽人說,貧民窟最近十到二十年裏大大衰落。真的是越來越差瞭嗎?
利奇 :是啊,是啊!一點不假。凶殺啊,毒品啊,我的天!你看,毒品這個東西就像瘟疫,我的天!來得真快。說來就來,好像一夜之間,“嘩啦”一聲就來瞭[打個響指],好像生瞭翅膀,你還沒看見它飛過來,就已經到處都是瞭。
——是從哪一年開始的?
利奇 :我記得,大概是從1983年起,直到現在,這段時間毒品真的是……我覺得是打1980年以後,毒品一下子就興起來瞭。注意,這不是說毒品以前沒有,可是[特彆強調]根本沒法跟現在比。我相信,這好像是一個大陰謀,我的天。我們這些老百姓—我是說,我們黑人——那個時候要興旺起來,要進步,擋也擋不住,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可是,毒品他媽的這個玩意兒一來,我的天,嘩啦一下就把我們拉迴50年前去瞭。瞧,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如今是兄弟相爭。隻要我能得到這個東西,我纔不在乎你的死活。那些掙到錢的傢夥[驚訝的口氣]根本不管錢是怎麼來的,他們隻知道買汽車,我的天,買汽車,再弄幾個娘們兒。我的天,就是這樣,沒彆的。總之,我想說,29街和斯戴德大街的拐角,你隻要去那兒看看就知道瞭。還有,一直往下走,到119街,你經過的所有這一大片街區,黑人開的店鋪你找不齣十傢,可是這些全是黑人聚居的地方。這個就讓人琢磨瞭。
[貧民窟的商店曆來都由白人開辦,現在逐漸轉為由亞洲人經營:韓國人、華人、菲律賓人,以及從黎巴嫩和敘利亞來的中東人。]
——這些錢都到哪兒去瞭?總得有人用這些錢乾點什麼吧?
利奇 :這就像我跟你說過的,他們對有些東西感興趣,對男人來說是汽車、娘們兒,我是說,我認識的男人當中,有的人有三四輛汽車呢。可是,說到底[有點氣憤],你一個人能開幾輛車啊?
一個美國黑人貧民窟的痞子(節選)
采訪者:洛伊剋·瓦岡
“窮歸窮,可是我們不分你我”
——你認為自己齣身很窮嗎?
利奇 :這個嘛……[長時間沉默]這麼說吧……我們那個時候窮歸窮,可是我們不分你我。就說我媽吧,她總是讓我們乾乾淨淨去上學。褲子我也許隻有一兩條,可是她總是把它們洗得乾乾淨淨,我……所以我不覺得有過窮得吃不上飯的時候。這種餓肚子的日子我不記得有過,一天也沒有。
——所以,你小時候總是有好多好多吃的啦?
利奇 :多倒是不多。總有的吃就是瞭。跟現在相比,我更喜歡小時候的日子。你知道,我喜歡那個時候……
——為什麼呢?
利奇 :就是說,那個時候,也就是我上小學的年月,日子過得挺平安的。
——看來你很喜歡學校,那麼,你都做些什麼呢?
利奇 :這個嘛,其實我的心思並不真的在那兒。有好多東西從我身邊溜走瞭,我都沒注意到,也許現在注意到瞭,可是我那個時候沒上心……那時候看不到。真的,不理解學習的意義……[十分懷念地]不是我媽不催促,不跟我講道理,而是她從來沒有認真跟我談過這事有多重要,真的,從沒這麼說過。她隻是對我說:“上學去吧。”完事。我老是遇上麻煩,沒斷過。
——什麼樣的麻煩?
利奇 :那就是被叫去見校長,我老是跟彆人掐架什麼的。
——你的童年很不容易,小時候很難嗎?
利奇 :也不見得有多難。沒有那種讓我夜裏做噩夢,驚齣一身冷汗的事,還得自言自語:“啊呀,這事現在我想起來瞭!”因為,我那一陣子愛打架,愛找茬兒掐架。因為我那個街區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你長大的街區很亂嗎?
利奇 :沒錯!不用說,很亂。可是,你知道,那個時代人們很真誠。對,真誠。如今人們可是不如從前瞭。那個時候,你覺得[語速很快]有人跟你說點什麼,他是真誠的。可是好多東西如今都變瞭,毒品,像一場瘟疫似的毒品,我的天!它把一切都改變瞭。如今隻有物質的東西纔重要。沒有真朋友瞭,隻剩下綠票子瞭,是啊,隻剩下這個瞭。
[……]
——常聽人說,貧民窟最近十到二十年裏大大衰落。真的是越來越差瞭嗎?
利奇 :是啊,是啊!一點不假。凶殺啊,毒品啊,我的天!你看,毒品這個東西就像瘟疫,我的天!來得真快。說來就來,好像一夜之間,“嘩啦”一聲就來瞭[打個響指],好像生瞭翅膀,你還沒看見它飛過來,就已經到處都是瞭。
——是從哪一年開始的?
利奇 :我記得,大概是從1983年起,直到現在,這段時間毒品真的是……我覺得是打1980年以後,毒品一下子就興起來瞭。注意,這不是說毒品以前沒有,可是[特彆強調]根本沒法跟現在比。我相信,這好像是一個大陰謀,我的天。我們這些老百姓—我是說,我們黑人——那個時候要興旺起來,要進步,擋也擋不住,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可是,毒品他媽的這個玩意兒一來,我的天,嘩啦一下就把我們拉迴50年前去瞭。瞧,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如今是兄弟相爭。隻要我能得到這個東西,我纔不在乎你的死活。那些掙到錢的傢夥[驚訝的口氣]根本不管錢是怎麼來的,他們隻知道買汽車,我的天,買汽車,再弄幾個娘們兒。我的天,就是這樣,沒彆的。總之,我想說,29街和斯戴德大街的拐角,你隻要去那兒看看就知道瞭。還有,一直往下走,到119街,你經過的所有這一大片街區,黑人開的店鋪你找不齣十傢,可是這些全是黑人聚居的地方。這個就讓人琢磨瞭。
[貧民窟的商店曆來都由白人開辦,現在逐漸轉為由亞洲人經營:韓國人、華人、菲律賓人,以及從黎巴嫩和敘利亞來的中東人。]
——這些錢都到哪兒去瞭?總得有人用這些錢乾點什麼吧?
利奇 :這就像我跟你說過的,他們對有些東西感興趣,對男人來說是汽車、娘們兒,我是說,我認識的男人當中,有的人有三四輛汽車呢。可是,說到底[有點氣憤],你一個人能開幾輛車啊?
Chicago Ghetto On The South Side, 1974(photo by John H. White)
理解(節選) 皮埃爾·布爾迪厄
一場思想活動
不過,為瞭縮短社會距離,我們能夠想到的所有程序和招數都是有限的。訪談筆錄雖然無法顯示口語的快慢緩急,但是隻要連著閱讀幾篇訪談就能看齣,受訪者遠離心照不宣的采訪要求的零碎話語與按照預設的要求調整過(有時會調整過度)的話語之間的不同。
如果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消除或擱置社會距離帶來的不對稱性的社會效應,我們就隻能期待通過不斷建構獲取一些盡可能少受采訪情境影響的迴答。看起來矛盾的是,這種建構工作做得越好,越是帶有“自然的”話語交流的一切跡象(指日常生活裏的傢常話),就越顯得無斧鑿之嫌。
采訪者如果能夠通過講話的語氣,尤其是提問的內容,嚮社會距離與之最遠的受訪者錶明,自己並不是在矯揉造作地消除這種距離(與看不齣個人觀點的民粹派不同),而是設身處地為受訪者著想,就能夠使對方感到,實事求是地錶達自己完全是正當和閤理的。
考慮受訪者的社會地位,設身處地,以此為齣發點提問,以理解對方必然所是,而且在某種意義上站到他的立場上[即弗朗西斯·蓬熱 [1] 所說“事物的立場”],這樣做並不是現象學傢所說的“將自己投射為他人”,而是做到從總體上和源流上理解對方是什麼人,這種理解基於能夠(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把握受訪者由之産生的社會環境;既要把握影響他所隸屬的整個社會類彆(中學生、技術工人、法官等等)的生存條件和社會機製,也要把握與他在社會空間中的地位和特殊軌跡相關的心態和社會環境(二者不可分割)的調整過程。與狄爾泰 [2] 的舊區分相反。我們要說,理解和解釋是一個整體。
這種理解不單單是一種與人為善的態度,它貫穿於既明白易懂又令人安心地介紹、延邀訪談以及引導談話的方式當中,從而使受訪者感到訪談本身和(尤其是)擺齣的議題都有意義。議題及其呼喚的答復都得自一幅對於受訪者所處的生活環境和塑造他的條件的經過核查的圖景。也就是說,隻有對於受訪者有深入的瞭解,采訪者纔可能有機會跟受訪者平起平坐。獲得這種知識有時候要耗費畢生的研究,有時候得事先與受訪者或報吿人晤談。這裏發錶的訪談錄大多隻是很長的一係列交流的一個片斷——當然是受重視的片段。跟缺少專門知識的采訪者匆忙完成的調査的那些有限的、任意的和隨機進行的會麵相比,它們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這種信息隻錶現為否定性的,特彆是它能夠啓迪謹慎而殷切的態度——受訪者能否信任你和加入訪談取決於此——以及提問不為難對方或者偏離議題,采訪者據此也能夠不斷地隨時提齣恰當的冋題。也就是說,憑藉對於受訪者的生成方式的本能的和臨時的理解而做齣的名副其實的設問,能夠鼓勵受訪者更充分地揭示自己。 [3]
無論事先瞭解多麼深入,如果缺少日常生活裏少有的對他人的關心和忍讓豁達,就依然達不到對受訪者的真正的理解,盡管這種瞭解能夠為熟悉的實際知識帶來某種理論對等物。實際上,相比那些有關日常睏苦的多少俗套化瞭的說法,我們對於這些睏苦的關注跟引齣此類說法的問候語“您近來可好?”一樣,大多也是空洞的俗套。通過各種知覺範疇,有關遺産繼承和鄰裏衝突、學業睏境和職場傾軋,我們知道的故事不在少數。這些知覺範疇把個彆變成普遍,把個人悲劇變成社會雜聞,似乎可以大大節省思考、興緻、感受,簡言之,節省理解。即使動員起一切資源——從職業敏感到個人的側隱之心——我們仍然很難擺脫似曾相識或似曾聽聞的幻覺導緻的注意力鬆懈,無法進入每一個生命的故事,也無法從單一性和一般性兩方麵去理解生活中的悲劇。心不在焉和習以為常的即時的一知半解會破壞我們為打破陳詞濫調所付齣的努力。我們每個人都離不開這些陳詞濫調,而且用它們來談論生活中的細瑣難題和大災大難。不定人稱代詞“人們”(on)在哲學上受譴責,在文學上被擯棄,它適用於任何人;而“我”要求最普通的單一性——我們認為指我們自己。相形之下,“人們”因手段極“不可靠”,它要錶達的東西無疑最難聽明白。
[……]
現實的建構活動
采訪者預先做好功課,態度親和,受訪者也有所期待,雙方的配閤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盡管人們有時會有神奇的感覺。真正的實事求是意味著進行建構活動,它基於切實地把握社會邏輯。事實就是依照這種邏輯形成的。以看起來很平常的三個女中學生的談話為例,若想真正聽懂她們在說什麼,就得避免像許多“錄音機社會調查”那樣。把三個活生生的人簡化為三個名字,而是從言談話語裏讀取其求學軌跡與教育製度之間的現在的和過去的客觀關係,進而看到教育製度的整個結構和曆史。關於社會人的獨特性的人格論觀點是幼稚的,與之相反,隻有把局部互動當中的隨機的說法的內在結構揭示齣來,纔能把握構成每一個女孩的特異之處的要素,及其行動和反應的特殊的復雜性。
從這個意義上 [4] 理解,話語分析不僅能夠看到話語互動作為市場的隨機性結構,也能看齣把它組織起來的隱性結構,即以上那個例子中的女孩子們所處的社會空間的結構,以及她們所經曆的不同軌跡所在的學校空間的結構。這些軌跡雖然屬於過去,可是繼續指導著她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的學業,甚至對於她們自己的獨特的看法。
因此,與那種以為取消瞭觀察者便能夠做到不偏不倚的幻覺相反,必須承認,盡管看似矛盾,但所謂“自發性”隻能通過建構纔會有,然而這是一種務實的建構。為瞭使它能夠得到理解,或至少使人感覺到,我想舉齣一件軼事來說明,隻有憑藉對於現實的先期知識做齣建構,研究工作纔能夠揭示它打算記載的現實。我們在調查住房問題期間,為瞭避免人們偏愛的涉及購買和租賃的不現實的抽象問題,我決定請受訪者談談他們先後住過的地方、曾經遇到的居住條件、導緻他們選擇或離開的理由和原因、他們對這些住處做齣的改動等等。在我們看來,如此設計的采訪進行得極為“自然”,受訪者齣乎意料地坦言相告。可是,很久以後,我在地鐵裏完全偶然地聽到瞭兩位40歲上下的婦女之間的對話。其中一人不久前搬進瞭新居,正在述說她先後住過的地方的故事。另一方看起來完全遵循那些我們給自己定下的訪談規則。我把事後憑記憶隨即記錄下來的對白抄在下麵∶
——我這是第一次搬進新公離。真不賴……
——我在巴黎的頭一個住處在布朗西翁大街上,房子很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翻修過,全都一塌期塗,都得重來。還有,天花闆怎麼弄也弄不乾淨,全是黑乎乎的。
——是啊,那真是個大活兒。
——從前,跟父母在一起的時侯,我們住的地方連水也沒有。帶著兩個孩子,能有一間浴室,真是不可思議。
——我父母那兒也是一樣。不過,我們倒沒有弄得那麼髒。話是這麼說,有比沒有還是要方便多瞭。
——從那以後,我們就搬到剋雷代伊(Créteil)去瞭,那棟公寓挺現代化,不過也有十幾年瞭……
——我這是第一次搬進新公離。真不賴……
——我在巴黎的頭一個住處在布朗西翁大街上,房子很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翻修過,全都一塌期塗,都得重來。還有,天花闆怎麼弄也弄不乾淨,全是黑乎乎的。
——是啊,那真是個大活兒。
——從前,跟父母在一起的時侯,我們住的地方連水也沒有。帶著兩個孩子,能有一間浴室,真是不可思議。
——我父母那兒也是一樣。不過,我們倒沒有弄得那麼髒。話是這麼說,有比沒有還是要方便多瞭。
——從那以後,我們就搬到剋雷代伊(Créteil)去瞭,那棟公寓挺現代化,不過也有十幾年瞭……
故事照這樣繼續下去。十分自然,其中穿插著乾預性詞語,要麼以肯定或疑問語氣重復一下前一個句子,簡單地予以“確認接收”,要麼錶明對某個觀點的興趣或認可(“這可不容易,站著工作瞭一整天……”或者“我父母那兒也是一樣……”)。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加入交談,而且藉此也能促使對方參與。采訪者正是在這一點上,為瞭不偏不倚而排除一切個人介入,這種訪談有彆於日常交談和我們所實踐的訪談。
這種催生的辦法跟把議題強加於人有雲泥之彆,後者正是許多幻想能夠“不偏不倚”的民意調查的方法。強人所難和人為拼湊的問題製造齣大量被認為是照實記錄的人工製品——何況是從受訪者親身經驗那兒榨取齣自電視台的意見的電視采訪。 [5] 第一條區彆是在瞭解所謂“公眾輿論”實為變動不居的基礎上具備防範意識:深層次的心態會有各種錶達形式,這一點從預先準備好的答案(封閉式問捲的預定答案,或者現成的政治語言)和相對不同的說法裏便可看齣。這就意味著,把話題強加給對方最方便易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更“自然”的做法。舉幾個例證: 民意調查以一無所知的天真麵目齣現,頻繁地綁架公眾輿論(從而理直氣壯地當作煽情蠱惑的工具);更常見的是,各懷不同信念的鼓動傢總是匆忙肯定一些顯而易見的期待,盡管人們並非總有辦法確定什麼是自己的真實需求。 [6] 強加於人的意見一經發錶就會得到鞏固,同時被賦予一種社會存在。因此,在“不偏不倚”的幌子下,強人所難的危害更大,因為齣版物造成一種民意調查機構已被認可的假象,使之顯得更為可信和可靠。
可以看到,由於嚴謹的知識幾乎總是意味著與廣為接受的信念——即通常所說的常識——發生多少引人注目的決裂,而且顯得立足於某種有待證實的理由或者立場,從而強化瞭學術的經驗主義的錶現方式。事實上,人們之所以會犯錯誤,恰恰是由於袖手旁觀,避免做齣任何乾預和建構,因為這樣就大大方便瞭前期建構和自動生效的社會機製——後者甚至影響到最基本的學術研究(構思和擬定問題,界定代碼的種類,等等)。隻有積極地揭示常識所蘊含的預設條件,纔能抵製談話雙方始終得麵對的所有那些社會現實的錶現方式。我在這裏特指新聞界的錶現方式——文字的,尤其是電視的。它們有時作為現成說法被硬塞給弱勢群體,以解釋後者的親身經驗。
布爾迪厄在1998年的一次失業者示威運動中嚮媒體發言(圖源:Yann Latronche / Getty)
社會主體並非天生就擁有一門有關自己所是與所為的科學,更準確地說,並不一定清楚他們的不滿或煩惱的根源。況且,盡管無意掩蓋什麼,那些最自然的宣稱要錶達的意思可能跟字麵迥異。社會學確信(這一點有彆於民意調查之類無學者參加的學術研究),從提問階段開始,就必須掌握能夠挑戰談話雙方的全部預建構(pré-constructions)和預設條件的辦法。建立調研關係往往全靠談話雙方在潛意識裏就這些東西達成默契。 [7]
社會學同樣確信,一些最自發的,因而看起來也最真實的意見可以滿足調查機構的行事倉促的調研員及其委托方。但這些意見的背後卻是一種心理分析學所闡明的邏輯關係。例如,在沒有跟移民直接打過交道的農民和小店主那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種針對外國人的先入為主的敵視。與基於理解的解讀方式相反,這種敵視以一種置換的形式,為這些收入堪比無産者的有産者的矛盾及其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他們認為後者必須對無法接受的再分配方式負責——提供瞭一條齣路。看到這一層,我們就能超越這種敵視的陰暗和荒謬的外錶。隻有努力發掘埋藏在這些人內心深處的東西,以扭麯的形式呈現的不快和不滿的真實基礎纔會進入意識,即明確的話語。他們雖然對這些東西有親身體驗、卻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在另一種意義上,他們也比誰都清楚。
社會學者猶如接生婆,能夠協助他們做這個工作,但是必須深入瞭解使之成為今日之所是的生存條件和調研關係——包括自己在這種關係當中的位置和基本構想——可能造成的社會效果。不過,作為研究意圖的一部分,發現真相的願望如果不以“工藝”的形式實現,仍然不會有任何實際效用,因為“工藝”是體現所有前期研究的産品,與抽象的和純智能的知識無關。這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求真的習性”(即亞裏士多德在《形而上學》裏說的hexis tou alètheuein)。在采訪中的節點,無論是自薦策略,還是恰當的答辯,抑或是錶示贊同或者適時提問,等等,它隨時都能夠現場發揮作用,從而有助於受訪者道齣真相——另一個更好的說法是,靠道齣真相求得解脫。 [8]
注釋: [1] 弗朗西斯·蓬熱(Francis Ponge,1899—1988),法國詩人。——譯者注 [2] 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德國哲學傢、曆史學傢、社會學傢和心理學傢。——譯者注 [3] 跟彆處一樣,我們可以通過最典型的失誤的例子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失誤的主因都是潛意識或者無知,重自身實效的采訪的某些優點必然無人注意,因為它們主要錶現在一些缺失的地方。 [4] 也就是說,這跟把控製對話方式當作研究對象時的意義是非常不同的,後者如開啓和結束對話的策略,至於參加者的社會和文化特點則另當彆論。 [5] 這裏有必要提到我早前發錶的較為全麵的分析(notamment,«L'opinion publique n'existe pas»,Questions de sociologie,Paris,Minuit,1984,p. 222-250)。 [6] 這些思考尤其針對那些說教者,他們認為民意調查的批評等於民主製度的批評。 [7] 有一份關於政客(德斯坦、希拉剋、馬歇等)的民意調查,完全按照一個中國遊戲設計(假如某人是一棵樹、一隻動物等,那將會怎麼樣?)。我曾經仔細分析過這份調查的答捲。我指齣,受訪者在答捲裏不自覺地運用瞭分類觀念(強弱、剛柔、貴賤等)。同捲的設計者同樣不自覺地將其運用於問題。他們附在公布的統計錶上的評論流於乾癟空洞。說明他們根本沒有弄懂他們自已拿齣來的數據,更不知道這些數據是如何炮製齣來的。(P. Bourdieu,La Distinction,Paris,Minuit,1979,p. 625-640.) [8] 此處不宜全麵分析學術習性的悖論。這種習性一方麵盡力把重要的社會設置說成是有意識的,以便將其淡化或者消除(更好的說法是將其“剝離整體”)。另一方麵——也是動機之一——卻盡量將其加以整閤,即把那些有意地為趁手的不同方法確定的原則說成近乎“無意識”(所謂有意識的“知識”和無意識的“知識”在這裏僅為方便錶達,這組對立其實完全是人為的和荒謬的。事實上,學術實踐的原則能夠既存在於意識當中——依此類實踐的時機和“層次”而有程度的不同——又以閤並設置的形式起到實際的作用。)
選自《世界的苦難:布爾迪厄的社會調查》,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2017.1
/點擊圖片跳轉購買此書/
丨 皮埃爾·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國著名社會學傢、人類學傢和哲學傢。他開創瞭許多調查架構和術語,如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以及慣習、場域或位置,以及象徵暴力等概念,以揭示在社會生活中的動態權力關係。其晚期著作《世界的苦難》傾注瞭對“失範之人”的深切關注。
丨 譯者簡介:張祖建 ,畢業於北京大學和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曾在北京大學、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以及美國多所大學授課,現任美國加州奧剋蘭市萊尼學院外語係長聘教員。2009年憑藉翻譯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麵具之道》獲得首屆傅雷翻譯齣版奬社科類奬項;2017年憑藉翻譯皮埃爾·布爾迪厄的《世界的苦難:布爾迪厄的社會調查》再獲殊榮。
題圖: Pierre Bourdieu, Graffiti by PITR
責編:阿飛、 卓勛 丨排版:鬍桓語(實習)
轉載請聯係後台並注明個人信息
韋伯逝世百年紀念 | 真理正是因為它不美,纔變得神聖
列奧·施特勞斯:如果沒有針對權威的自由,哲學傢將無法追尋真理
我們這一代人覺得自己既是激進人士,又是上流精英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