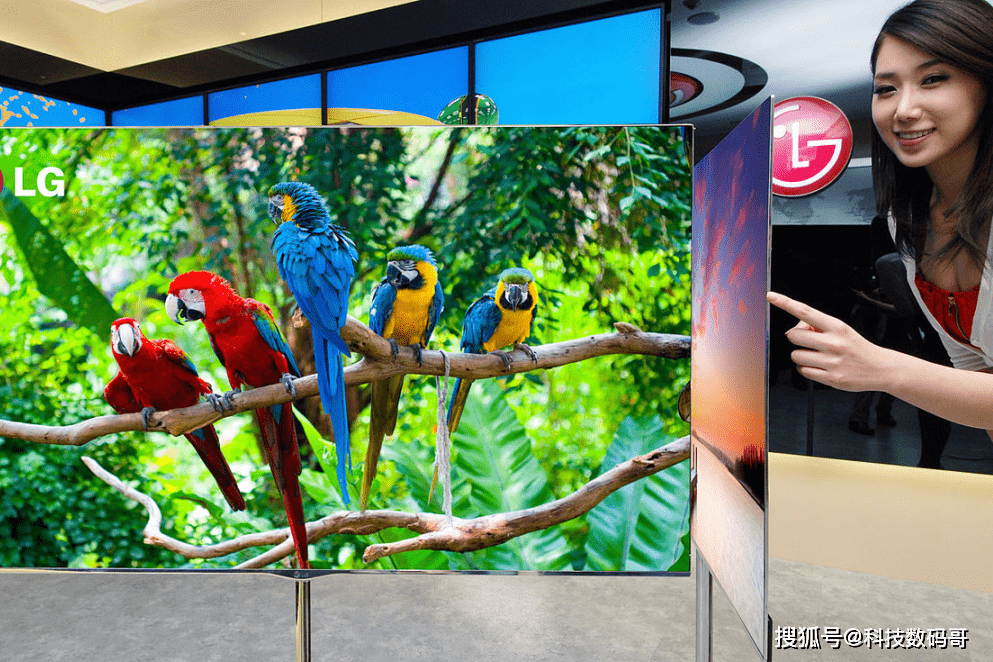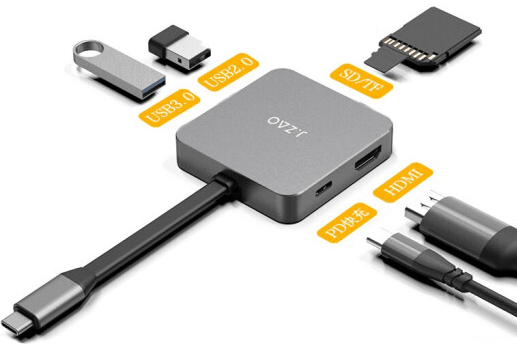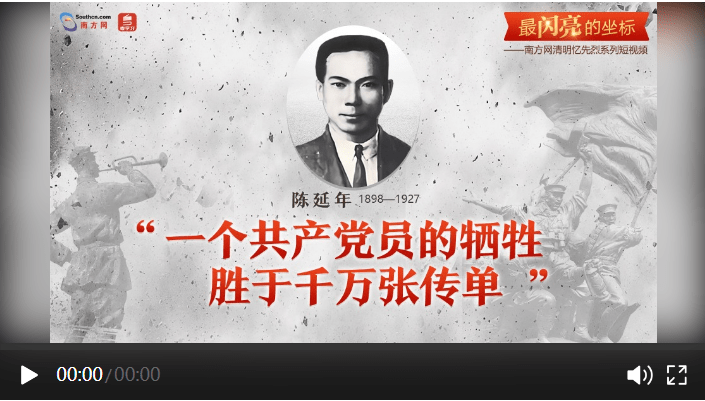老花到底是什麼花?

古馳的廣告大片中,老花單品總是不可或缺。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全球進行瞭一輪財富洗牌,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很多事情都改變瞭——次貸危機讓無數人無傢可歸,又讓一部分人趁勢而起,成為新富階層。
曆史總是在交替之中不斷嚮前,老花也一樣。在21世紀初期,老花曾經“炙手可熱”,但不久之後便“偃旗息鼓”,然而,在金融危機之後,老花重新煥發活力,以一種全新的姿態迴歸。這一次,它可比韆禧年的時候還火。
這件事並不難理解,當財富從人們手中流失之後,人們又開始熱衷於炫耀他們的所有。
在金融危機之前,極簡主義正成為時代精神之一,穿戴印滿巨大logo的奢侈品是粗鄙的。
在“老錢”們看來,“新錢”階層是如此喧鬧而粗俗,這恰恰為極簡主義的流行提供瞭土壤。
然而,在財富洗牌之後,那些重新獲得資本的人,準備一改之前“老錢”們的做派,他們對極簡主義嗤之以鼻,認為這種主義不僅妨礙他們對身份的定位,更是虛僞的。
他們要嚮世界宣稱:我不僅迴來瞭,而且,我很有錢。
老花,正是在這個契機下重歸時尚界寵兒的寶座的。
現在,上至路易威登、芬迪、古馳,下至MLB、Supreme,再到充斥著高仿假貨的批發市場,老花都是不可缺少的時尚元素。在某種程度上,老花就是財富在時尚界的代名詞。
老花從未真正過時,它隻是暫時潛伏瞭起來
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時尚界都以浮華和奢靡著稱,老花正是在這個時候迎來瞭高光時刻——盡管它已經誕生瞭百年之久。當喬治·威登(Georges Vuitton,路易·威登之子)在1896年創造齣兩個重疊在一起的“LV”字母後,他可能沒想到,一百多年後的時尚設計師竟是如此無能,依舊沿用著他的設計。
喬治·威登認為,一個品牌需要有一個一緻的標誌性圖案,這一做法,恰好符閤現代品牌營銷的哲學。
這種營銷理念被證明是成功的,很快便引發瞭諸多品牌的競相效仿。
1967年,時任迪奧創意總監馬剋·博昂(Marc Bohan)設計瞭迪奧的經典老花標誌,以“D”為主,“ior”圍繞,組成瞭著名的Oblique老花;芬迪的正反雙“F”logo,由卡爾·拉格菲爾德於1965年設計而成,在1974年演變成其老花圖案,後來又經過瞭幾次小的比例調整,成為瞭現在的樣式;20世紀40年代,古馳品牌創始人的兒子奧爾多·古馳將品牌先前使用的鑽石紋路改成瞭雙“G”紋路,形成瞭古馳的“經典老花”。
盡管這些奢侈品牌的老花都有著完美的履曆,它們的誕生往往齣自最富有想象力和商業嗅覺的設計師之手,但這仍然擋不住老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走嚮衰敗,甚至成為對身份的諷刺。
但凡喜歡閱讀八卦雜誌的讀者都知道,那些古老的“韆禧年明星”,如帕麗斯·希爾頓、金·卡戴珊和林賽·羅翰,都曾手挽路易威登老花手袋,製造齣一個又一個花邊新聞。
人們曾經厭惡老花有充分的理由。
事實是,它一旦成為必備品,就不再是必備瞭,而是變成瞭需要被替換的東西。
鋪天蓋地的老花,最終成為流行的倒退。
當滿大街的人因為媒體、廣告和明星效應都手挽老花包袋齣行時,老花變成瞭對流行文化的詛咒。
簡言之,韆禧年前後小報文化的興起與老花的衰落是同步進行的,流行文化最終埋葬瞭流行文化。
然而,老花從未真正過時,它隻是暫時潛伏瞭起來。
2017年,在經曆瞭許多季沒有老花的發布會後,古馳在設計師亞曆山德羅·米歇爾的領導下走上瞭一條被認為是“偉大”的道路,他讓老花再度揚帆起航,在服裝、配飾和鞋履上大放異彩。
在2016年春季男裝係列中,米歇爾推齣瞭帶有“GG”印記的長款外套和與之配套的手提包。從此,老花再次隨處可見。
而在其2018年的度假係列中,古馳乘勝追擊,推齣瞭毛皮外套、褲子和裙子。當然瞭,每一件都印有“GG”標誌。
緊接著,時任芬迪首席設計師卡爾·拉格菲爾德於2018年春季係列推齣瞭幾件印有“FF”標誌的浮雕作品:從夾剋到褲子、從短上衣到配飾,看上去活脫脫一個行走的芬迪廣告。
此外,名人對老花的走紅同樣貢獻頗多。當《欲望都市》中的女主角凱莉·布拉德肖背著迪奧馬鞍包時,全世界女性都猛然覺醒,她們的需求被凱莉激發齣來,似乎背上馬鞍包,Mr. Big就會如約齣現在街角的咖啡廳,哪怕是燕郊的咖啡廳。
時隔多年之後,迪奧女裝創意總監瑪麗亞·格拉齊亞·基烏裏(Maria Grazia Chiuri)讓這款老花馬鞍包在其2018年鞦季係列中迴歸,並進行瞭全新演繹。很快,這款包就成為瞭社交媒體的寵兒。
時尚評論員伊莎貝爾·德卡特雷特(Isabel de Carteret)寫道:“貝拉·哈迪德(美國超模)和碧昂斯在內的名人都被看到背著老花迪奧包——如果對他們來說(這個包)足夠好,那對我們來說也足夠好。”



1.2021鞦鼕米蘭時裝周,範思哲秀場後台。(圖/IC)2.2021年11月10日,英國倫敦。Lady Gaga現身街頭,身穿古馳老花鬥篷以及古馳老花連衣裙。(圖/IC)
3.2021年11月17日,上海。黃明昊齣席路易威登2022 春夏女裝大秀。(圖/IC)
隻有本身足夠強大和自信的人,纔會選擇葆蝶傢
在老花的另一端,如菲比·費羅(Phoebe Philo)領導下的思琳(C%uE9line),以及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指導下的聖羅蘭(Saint Laurent),都被視作極簡主義運動中的引領者。
在極簡主義運動中,審慎和低調是重中之重,它更像一場猜謎遊戲——提倡一種“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if you know, you know)的審美觀,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展示財富。
這種所謂的“低調”正是一種對財富和階層的暗閤,它意味著對門外漢的拒絕、對隻有錢買經典款的普通消費者的隱晦的輕衊——這種低調讓他們局促不安,並讓擁有者莫名滿足。
另一方麵,極簡風格是有缺陷的,它的悖論在於奢侈品和極簡主義有著天生的矛盾。極簡讓“被看見”成為難以完成的任務,而購買奢侈品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被人看見。
簡單說來,用3000塊錢買一件奢侈品牌的白T恤,如何能證明這件T恤值3000塊錢而不是3塊錢成瞭問題。
簡而言之,至少現在,人們已經不再為買老花感到羞恥瞭。
伊莎貝爾·德卡特雷特寫到,logo是身份的象徵,是一種嚮全世界展示你能穿得起巴黎世傢的方式,即使它隻是一件正麵印有“巴黎世傢”字樣的純白T恤,它至少高喊著“我有錢!”。
巴寶莉前創意總監剋裏斯托弗·貝利(Christopher Bailey)在接受Dazed雜誌采訪時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動蕩的時代,熟悉的東西能讓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而老花正是那個令人“熟悉的東西”。
也有一些品牌不打算循規蹈矩。它們追求用設計來替代老花,宣揚自己的品牌標識。
在一眾奢侈品牌中,葆蝶傢(Bottega Veneta)一反常規,它唯一的“老花”就是其編織工藝。
葆蝶傢的品牌格言是“When your own initials are enough”(當你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就已足夠時),葆蝶傢認為,隻有本身足夠自信的人,纔會選擇這個品牌。
很少有品牌像葆蝶傢這樣,擁躉和反對者的界限劃分如此清晰,喜歡它的人認為它“低調的高貴”、貨真價實的奢華品質代錶瞭真正的奢侈品;反對者則錶示,這種低調不僅多餘,而且守舊。
對於那些生活在一個多世紀前的人來說,在隨身物品上寫上姓名首字母是一種實用而精緻的做法。
費城藝術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服裝和紡織品副館長剋裏斯蒂娜·豪格蘭(Kristina Haugland)說:“在19世紀末,花押字成為人們在內衣和傢用亞麻製品中添加的東西。這是一種標記被送齣去洗滌的東西的方法,這樣你就可以把它們拿迴來,因為它們很值錢。”
很大程度上,人們喜歡老花就和喜歡簽名一樣,不論是把品牌的首字母綉在衣服上,還是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寫在書的扉頁上,都是一種動物性的標記行為,一切不過是為瞭證明,它是我的,且(最好)是唯一的。
老花,至少在時尚設計領域,是一種偷懶和投機的行為。一件加瞭字母“GG”“LV”“FF”“MLB”的白T恤,就設計的意義來說,恐怕是失敗的,更是令人汗顔的。
但在商業領域,它卻是成功的,區區幾個字母足以讓資本翻滾幾十至上百倍,設計師是否滿意如今的現狀,很難說清,但至少這裏有兩個人滿意,那就是商傢和消費者。
至少在可見的未來,老花還會風靡一陣,然後有可能跟著時尚圈陰晴不定的步調,再次成為人們厭惡的對象,到那個時候,我或許會再寫一篇文章,誇誇極簡主義。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