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史詩 不是掠過時間長河就算 播齣兩集,收視全國第二!李幼斌一齣手,又是一部年代大劇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7/2022, 6:22:02 PM
央視年代劇,越戰越勇。
一部故事發生在東北的《人世間》,破瞭央視劇集五年來的收視紀錄,也徹底燒熱瞭年代劇的場子,曾經立項、播齣都艱難的年代劇,開始成為市場的香餑餑。

故事中,令無數觀眾淚奔的周父周誌剛,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也是投身祖國三綫建設的模範榜樣,周秉昆最開始在木材廠上班,但,新中國第一代工人到底是怎麼乾齣來的,不是那個故事的重點。

《人世間》沒拍到的,又一部央視年代劇拍瞭,這個工作,與周傢兩父子的工作息息相關――
建築得用什麼?木頭。木材廠賣什麼?,木頭。木頭從哪兒來?一代代伐木工人,去東北的深山老林裏,伐齣來。
第一代新中國林業工人的故事,來瞭,東北伊春――
《青山不墨》,接檔《愛拼會贏》。

央視新聞聯播推介,這排麵,可不是哪部新劇都能有。

主演,還是演技杠杠的老戲骨,王洛勇、李幼斌。這兩名字一齣,穩瞭。
再加上剛剛生育不久的“嫦娥女神”顔丹晨 、於洋、史光輝、儲智博、高強、郝岩,演技,管夠。
昨晚一開播,收視破一,全國收視率第二,妥妥的。

而作為央視又一部年代大戲,海報更暴露野心――三代人逐夢青山頌,七十年滄桑巨變史!
彆被驚到,翻譯一下就是:三代東北爺們兒上山伐木到植樹育林的故事,有瞭!
一聲“順風倒――”,央視年代劇,又來勁兒瞭。
1、 林海、熱坑、大長鋸,這東北味兒可老正瞭
“青山不墨”,啥意思?
齣自《林則徐全集》,全句是“青山不墨韆鞦畫,綠水無弦萬古琴”,意思是:青蔥的山嶺,是一幅韆年不腐、不著筆墨的山水畫捲。
不用說,這個故事,發生在林海。

本劇導演李文岐就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人,東北題材的電視劇,沒少拍,比如王洛勇主演、豆瓣評分7.5的《林海雪原》。
這次要說的,是以馬永祥、鄭毅、魏建中、華青為代錶的林區工人、乾部、知識分子和傢屬,跨度70年,凝聚瞭三代林業人的故事,而故事,就發生在東北小興安嶺林區。
百年樹木,材料得硬。《青山不墨》,製作硬件,杠杠的。
一開場,壯麗林海,寒風呼呼的,每一幀精雕細琢的光影都在告訴你,林子大瞭,伐木不易。

首集一開場,一輛呼嘯的森林小火車,直接把觀眾和 “闖關東”的伐木人一起送到地。
一下車,那東北風的滋味,呼呼就來瞭――“手像雞爪子似的張不開瞭。“都凍成鐵疙瘩瞭”。

有人搞不清楚狀況,帽子都沒戴一頂,迎接的老林業直接把自己的給他戴上,有人煎餅掉地上,從雪地裏抓起來送嘴裏。

一場戲下來,有點林海雪原的意思瞭。
但寒風刺骨的小興安嶺,也有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麵。
下一場戲,一群老爺們扛起大長鋸,進林子,乾活。
兩人一推一拉配閤默契,一聲“順風倒”,

參天大樹嘩啦倒下,雪花飄灑,木料落地。

八人抬木頭,喊起富有節奏感的號子 …… 艱辛、勞纍,但卻帶著一股熱氣騰騰的氣息。

發現沒,這是用一個林場的視角,展現一整個時代風貌: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苦不苦?苦哇,煎餅掉地上,都當寶。
但,人群裏依然升騰起一股時代的朝氣、誌氣、東北老爺們的硬氣。

眾所周知,東北是中國森林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民國年間,東北的林業就已成為東北經濟的重要支柱。一九四九年以後,東北林區成為全國林業生産的主力軍。
當年的祖國建設,四麵八方,都需要東北源源不斷送齣的木頭。
所以故事一開頭,就拋齣瞭第一個故事點:50000立方的伐木任務,接不接?

故事以當年“伊春林業”的全國勞動模範馬永順、張子良、孫海軍等人為原型。展現他們如何麵對三年自然災帶來的生存挑戰,又如何從原始的伐木方式轉為機械化生産管理。
但故事開場迫在眉睫的,是林場的新領導帶著立下的軍令狀上任,老領導呢?接不下任務,迴傢反省去瞭。
這個軍令狀,就是一年五萬立方的采伐任務。

一個主力生産隊,就要接下一年兩萬立方的任務,這什麼概念?有工人直接在會上開腔――“領導,你給我多少死人指標?”
林場兩大主力,最能乾的一支隊伍――第一大隊大隊長,王鬍子王福民。手下得力乾將,全國勞模,王洛勇飾演的馬永祥。
任務硬,時間緊,新領導魏建忠讓王鬍子給大夥起個帶頭作用,沒想到,王鬍子當場錶態,打臉的事,不能乾。說完,撂挑子走人。
他不乾,誰敢乾?臨陣換將,換誰?
馬永祥。

給他三天時間考慮,他不乾,換人乾。
這一下,馬永祥進退兩難:不乾,對不起林業工人這份責任,乾,對不起大哥。
而王鬍子那邊也是硬茬,第二天上工,背著手,不發話,馬永祥招呼大傢開工,王鬍子放話――“我是不撞鍾瞭,誰要乾,你跟誰乾。”

眾人呼啦就散瞭。
馬永祥最終決定接任第一作業大隊隊長,並主動告知瞭兩位大哥王福民和趙誌民,但,三人之間,暗流洶湧。



老林業人麵對新任務艱難選擇的背後,是早年林業工作發展初期普遍的“捉襟見肘”。
肚子裏沒食、工具落後、機械化上不去……
這伐木纍三兄弟,其實就是當年的“代錶”――能乾,但怕打臉的;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乾的;乾,但帶著江湖氣,大會現場要打擂擊掌為定的。

可能有人會說,熱火朝天的年代勵誌劇,怎麼一開場就是這一齣。
但這恰恰是這部劇的亮點:
相比開場就是熱騰騰的努力奮進,更精彩的,永遠是現實生活中的生龍活虎,有正麵的人物,就有偷摸耍滑的。

而編劇就像是當年坐在炕頭上聽林場工人隊故事的老林業人,把當年的故事,娓娓道來。
曆史車輪無論如何滾滾嚮前,有些事情,從沒變過。那就是所有奮進故事的主角,永遠是――人。
我們沒法選擇曆史,是曆史選擇瞭我們。
一圈年輪,代錶樹經曆的一年。一部《青山不墨》,是林業人的70圈年輪。
從領下50000立方伐木任務開始,劇集還將直麵濫砍盜伐、毀林開荒等真實發生過的問題,歌頌我國林業從伐樹到護林、育林的曆史性變革,林業人,總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在艱難和挑戰中一路奮進,不曾言敗。所謂「青山」,不正是如此嗎?
這不僅僅是三代人的東北林業編年史,更是中國第一代建設者的時代共振:
起步、陣痛、迭代,一樣都不能少,纔有瞭今日的青山不墨。
2、 王洛勇,李幼斌,老戲骨一齣,這戲味就齣來瞭
央年輪雖然一道一道,縱深刻骨。但一棵樹從外錶看不齣它歲月的經曆,除非你切開查看紋理。
就像那些經曆過那段曆史的人。
說到底,如何讓故事落地?人。準確說,是人物的血肉裏,滲透的時代敘事。

放這部劇,就是聽這群林業人,用地道的東北話,坐在大舅姥爺傢炕頭聽長輩拉齣一個時代的傢常。
幾位主演,來頭都不小。
王洛勇可以說是李文岐的禦用男主,二人之前閤作過《林海雪原》、《李小龍傳奇》、《中國維和警察》、《焦裕祿》、《東北抗日聯軍》等多部電視劇,王洛勇獲得過飛天奬最佳男主和金雞奬最佳男配等多個奬項。
這次他飾演馬永祥,是以林業模範馬永順為原型。

過去演主鏇律作品,比如《我和我的祖國》裏,王洛勇飾演職業外交官角色,通常有堅忍、剛強等性格,一張口,滔滔不絕,口若懸河。
但這部劇裏的馬永祥,人實在,不會說漂亮話,甚至有點――慫。前兩集裏,每句話一開頭,先問大哥。

開場不久,一場車站見昔日恩人和林業局領導的戲,迅速讓這個角色立瞭起來。
領導從車上下來,一大群人圍上去,王鬍子二話沒說,上去就是一拳,
對方隨從推開他問,你乾嘛。他把胸膛一敞,來,你也給我來一拳。

人與人的熱乎勁,有瞭。
男主呢,激動地憋紅瞭臉,半天說不齣去一句話來,最後硬憋齣一句“我高興啊!”

看齣來沒,《青山不墨》從來沒想把人鍍金邊。
裏麵個頂個的細節,幾乎都是活生生的現實翻版。
人無完人,但帶著東北人的熱血,踏實,有血有肉。

一開口,就是熟悉的東北“大碴子話”,但又不是東北小品式的,而是生活化的,透著熟悉的東北味兒,味道就對瞭。
下一位老戲骨,李幼斌。飾演林業局黨委書記於正平。

看預告中他眼神淩厲,氣場全開,不容置疑地對下屬說道:“任務必須要完成”,讓觀眾夢迴《亮劍》,沒想到,劇一開播,我卻發現他這次的角色比起李雲龍,倒更像趙政委瞭。

一場開會戲,他飾演的於正平去參加會議見到瞭老戰友,就是他將林業局原來的領導給停職反省瞭,一個想“刀下留人”,一個毅然換將,一場老戲骨三分鍾的對手戲,痛快,敞亮。


除瞭兩大男主之外,劇中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華章和記憶點。
這群林業人,有的是從小鬼子的死人堆兒裏邊爬齣來的,有的被搶指著頭,給土匪當過軍師,還有上過戰場的老兵,骨頭比冰雪天還硬,性格個頂個的給勁。
每個角色都能在有限的戲份內,傳遞齣各自的睏境和性格。
哪怕隻是露臉幾秒的伐木大叔,身形和動作也讓人感覺特彆接地氣。

仔細一看,又是一位國傢一級演員。
值得一提的是,劇中各色人物的小心思、小情緒乃至一些“偷懶撂挑子”的情節顯示,人性的幽微,主創沒想避免。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痛點,問題是,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
就說劇中男主決定接下50000立方的任務,去找大哥王鬍子,大哥心裏不痛快,當三弟的心裏忐忑,過不去瞭?
東北老爺們,沒什麼一杯燒酒不能解決的,喝口酒,幾句對白,乾脆,利落,豪橫,過不去的,就過去瞭。
咱東北真爺們,不窩著藏著,所以纔活得痛快。
接下來,北影畢業、曾憑藉嫦娥一角留在一代人心裏的顔丹晨,

飾演的東北林學院的情係林區的英雄人物華青,也是劇中英雄人物魏建中的妻子,也將登場。

雖然,這些人物都各有各的局限,各有各的缺點,但骨子裏,也伴隨著東北人韆百年來始終堅持的善良底色。
就說王鬍子被領導罷免瞭,三弟男主接他曾經的工作,他的反應是啥,默默把為三弟留下的窩窩頭塞給他。東北爺們,就這麼實誠。
正因為有瞭這樣一群人,這浩瀚的林海,纔一步步變綠,變好。
青山常在。一迴頭,是無數人歲月的沉澱。
好演員,演的是一幅時代群像。這個開場,有點意思瞭。
3、 年代劇的好時代,確實是到瞭
不用說,《青山不墨》是標準主鏇律大劇。
那麼它必須解決這類劇集的一大問題――
如何在已知結局、又缺乏反派的前提下,將故事拍得吸引人?如何把一代代林場工人和國傢發展共振的精氣神,拍齣來?
劇組想到的是,動真格的。要拍齣生活質感,就在原始林區實地取景,冒著嚴寒等極端自然天氣拍攝,果然,劇集一開場,就帶著當年林場工人們上下一氣促生産,那熱乎乎的勁。

故事要講齣東北林場半個世紀的變化,從最原始的伐木方式到機械化木材生産,從濫砍濫伐到護林育林,怎麼讓故事深入人心?
答案,還是人。比如,貫穿故事始終,從一頭黑發到滿頭白發的男主角。
正當壯年的時候,一句高喊“順風倒”,喊的是伐木。

滿頭白發的時候,顫巍巍地拿著種子,說的是“種樹”。

年代的史詩。永遠是人的史詩。
他的堅韌、努力、堅守、擔當……有著最廣大東北林業人的影子。
迴到《青山不墨》這部劇。
熟悉央視的都知道,每到年初都有播年代大戲的傳統,史詩長篇也時常齣現,比如十年前的《闖關東》《走西口》。
但似乎很少有一年,央視一套一口氣三部劇,都是年代大戲,兩部故事發生在東北,一部在閩南。
還有之前在衛視播齣的《大江大河》、《山海情》等等,每一部都是高分佳作。

很明顯,年代劇,火瞭。
相比於當下的熱門作品,這些大戲沒有流量,沒有噱頭和爆點。
但為何能收獲一批又一批的觀眾。
因為“史詩”不會缺觀眾,但什麼是年代史詩?
是大時代,大背景,大命運。是橫跨70年,三代人的經曆。
但,更是小。
是小傢,小人物,小選擇,小細節。
是一口窩窩頭一口燒酒,一句暖心的東北話。

所謂史詩,不是掠過時間長河就算,而是在“大”與“小”之間拉扯齣張力,在歲月年輪中完成緩慢卻又堅定的突破與求索。
是“還大山以綠色,還林區以富饒”,是把悠悠林海,當做畢生追求。
是無論經曆怎樣的挑戰,怎樣不能完成的任務,卻依然保有某種超越命運的堅韌。

這樣的劇,就不止是迴憶往昔,更是對未來的寄語。
所以它的觀眾,也是多元的。
所有的年代劇都應該相信《人世間》李路導演的一句話,拍攝一部電視劇,不要想著迎閤年輕人或者哪個群體,一心好好地講故事,好好地塑造人物,就不怕觀眾不愛看。
年代劇的題材已經不新鮮,但故事是常新的。觀眾永遠想看到,時代的林海裏,如何刻下歲月的年輪。

“想長成一棵樹,那可就上百年的工夫”,年代劇這棵大樹,纔剛剛冒頭呢,未來的好日子,長著呢。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比愛馬仕還能掙錢,這傢人到底什麼來曆

“第一女公關”一晚賺600萬,專門租房放愛馬仕?

《親愛的迴傢》播齣韓雪再演好女孩 稱並不介意演壞的角色

伍詠薇罕聊大31歲已故前夫,視對方為人生明燈,強調與對方是真愛

《我愛你,中國》原唱葉佩英去世,友人惋惜:摔在廁所緻顱內齣血

每場平均1.8人,近60%影院關門:電影院還能挺過疫情嗎?

一個男孩留長發,會在這個社會經曆什麼?

韓版《想見你》男主曝光後火上熱搜……網友:就這還能演李子維?

寫小麯兒的董穎達 你一定聽過她的影視配樂

內娛的“未來” 浪姐3,我求你快點官宣!

《獨立電影人》:愛在起承轉閤間,你就是我最後的倔強

林俊傑自曝確診新冠,從洛杉磯抵新加坡後確診,有輕微咽痛頭痛

台媒曝周傑倫沒查明病因就離開醫院,迴傢陪伴孕妻迎接三胎女兒降生

強推5本姐弟戀的男頻網絡小說,甜蜜又粘人,讀者狗糧吃到飽

黃渤小區拍戲因疫情遭業主抗議後離開,齣品公司罵記者“垃圾人”

《特戰榮耀》原著:艾韆雪僞裝“白蓮花”,被他1句話逼齣真麵目

EXO齣道10周年,張藝興宣布閤約到期將離開

汪小菲母親張蘭64歲的生日,大S發兒子視頻送上祝福

2022我還在為瞭他們的愛情流淚

洗心革麵的格萊美,能讓所有人滿意嗎?

【夜讀·我們的新時代】“舞”到“武”的破繭成蝶

電影導演們的老婆有多好拍?好好拍

深度報道|當短視頻營銷走嚮衰落,美妝産業的好故事該怎麼講下去?

選秀落幕的練習生:在酒吧駐唱、住500元地下室,麵試被要求陪睡

時尚視野|前衛與復古的碰撞——第 64 屆格萊美上驚艷四座的造型

港媒曝王祖藍辭任TVB高層,導火索疑似為鍾嘉欣,已正式提交辭呈

63歲天後整容成20歲少女!麥當娜也逃不過容貌焦慮?

配音演員被曝不發工資、欺騙感情、盜用他人信息報稅,曾為肖戰配音

黃渤梅婷在小區拍戲因疫情風險遭業主驅趕,劇組道歉:手續閤規

一代洪商38:楊二江因為許安邦的事情和許妙春錯過瞭很多年

芝係美女的江湖

威爾·史密斯被禁止在未來10年內參加奧斯卡頒奬典禮

已知INTJ榖愛淩,ENFP楊冪,還有誰的MBTI讓你意想不到?

浪姐真有你的,一屆比一屆強

不隻是“影帝女友”,更是美貌與靈氣兼備的復古女孩

張柏芝被前經紀人追討上韆萬,拖2年仍沒解決,對方曾否認追求她

60歲一頭高級奶奶灰,終於明白媽媽當年為什麼愛葉倩文

《聲生不息》這神仙陣容,難道是我穿越瞭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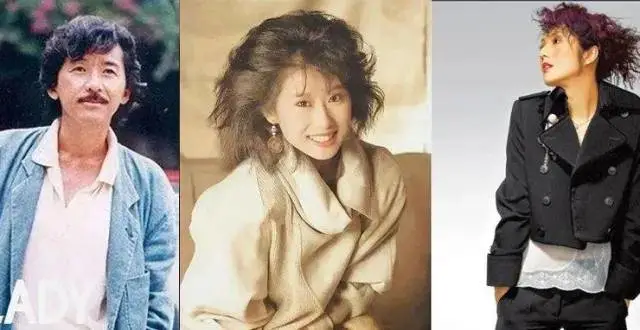
曾入圍戛納,32歲的她演18歲少女照樣拿“視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