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B・M・舒剋申著 逸天| 譯年輕的法律係畢業生 年輕的檢察院雇員 【心夢譯文】逸天|年輕瓦加諾夫的煩惱(小說)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24/2022, 9:23:27 AM
【俄】|B・M・舒剋申 著 逸天| 譯
年輕的法律係畢業生,年輕的檢察院雇員,年輕的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瓦加諾夫,從早上開始就有一個很好的心情,昨天他收到一封信……是他同年級的瑪雅・雅庫基娜寫的。姑娘有著輪廓分明的臉龐,高傲的氣質,就像是大師做齣的木製洋娃娃。瓦加諾夫希望大傢搞清楚,其實也沒什麼可清楚的,就是他喜歡瑪雅・雅庫基娜。他們年級有4個年輕人喜歡瑪雅,在大學的最後一年,瑪雅嫁給瞭一個天纔物理學傢。但是瓦加諾夫不能指責她,也不能感到不滿,第一:他沒有這個權利;第二:又能指責她什麼呢?瓦加諾夫一直都知道,他配不上瑪雅。遺憾,是當然的……然而,也許又不會遺憾,因為他收到瑪雅的來信,像命運之路,他很快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瑪雅在信上寫道,她的傢庭生活齣現裂痕,她現在是自由的,並且想利用自己的假期親眼看看自己的國傢。並問:“親愛的焦拉,還記得我們的友誼嗎?讓我們在車站相遇,並讓我陪你一個星期,我一直想去那裏,可以嗎?”接著她還寫道,她有一個很好的機會重新考慮她自己和周圍的生活。“呶―呶―呶,容易,親愛的,這很容易。”年輕的瓦加諾夫滿意地想,“先等我計算一下。”
把信放進公文包裏,年輕的瓦加諾夫拿起包便去上班瞭。他想在工作的時候迴信,如不可以的話,那就晚上迴傢再迴信給瑪雅。他滿腦子搜尋著適閤寫在信裏的詞語,怎樣纔能讓迴信看上去簡單、大方、聰明。他想到一些話,覺得不好,又開始搜尋……瓦加諾夫走進辦公室,立刻找齣幾張現成的紙,打算寫信。但這時,辦公室的門慢慢地響起吱呀聲……門後小心地露齣一個男人的光頭。
“可以打擾一下嗎?”
瓦加諾夫停頓瞭一下,掩飾住自己的失望,說:“請進。”
“你好。”這個男人50歲左右,瘦高個,長長的手臂,有點不知所措。
“坐吧。”
“我把鑒定帶來瞭。”男人說,並因為雙手找到瞭事情做而高興。他焦急地拿齣夾剋口袋裏的東西,那個他所謂的鑒定。
“什麼鑒定?”
“關於我妻子的……我想解釋……”
“你是波波夫?”
“是啊。”
“你想解釋什麼?請你解釋一下你為什麼打架?為什麼要毆打妻子和鄰居?鑒定是關於什麼的?”
波波夫已經拿齣鑒定站在辦公室中間。
“呶,把鑒定給我。”
波波夫拿齣兩張紙遞瞭過來,又再次站迴辦公室中間等著。
瓦加諾夫看完後,抬起頭說:“波波夫,這個是改變不瞭事情性質的。”
“怎麼改變不瞭?”
“改變不瞭。你這裏寫著,她是如何如何壞。舉個例子讓我們相信你,如何?”
“這怎麼說?”波波夫很驚訝。“她故意拘禁我15個晝夜。把我關起來,而她自己……我都知道,科羅廖夫全部告訴瞭我。其實科羅廖夫不說我也知道,她自己也告訴我瞭。”
“怎麼說的?”
“她說瞭!”波波夫信心十足地說,“你,在這呆著,我要去和米什卡一起住。”
“噢……什麼?她就這麼直接說的?”
“是的,事情就是這樣!”波波夫再次錶示,“她說她故意激怒我而去和米什卡一起住。”
“她說她故意氣你?”
“是的。”
“呶,我不知道……”年輕的瓦加諾夫真的不知該怎麼做,看來這個男人說的是痛苦的事實。接下來可能就會離婚瞭吧。
“我現在怎麼辦?離婚嗎?她依法院判決拿到房子,可孩子們還沒長大,我為他們感到難過……”
“你們有幾個孩子?”
“三個,最小的隻有7歲。我愛他到死……在這方麵我贏不瞭我妻子。”
“聽著!”瓦加諾夫說,“在這裏,我是你的朋友,我不知道該怎麼建議。你說,在這之後你能不能和她一起生活呢?”
“能。”波波夫堅定地說。“讓她見鬼去吧。”
“我不明白你是怎麼想的?”
“我想讓他們平息這件事。”
“那份‘鑒定報告’又是為什麼呢?”
“他們也許會覺得這樣對他們有好處,會平息這件事。”
“你是怎麼結婚的呢?”沉默瞭一會兒,瓦加諾夫問。
“怎麼結婚的?像平常人一樣。我從戰場上迴來,她在村裏的商店工作,我很早之前就知道她。”
“你住這裏?”
“住這裏。我傢鄉已經沒有任何人瞭。”
“那現在你妻子在哪裏?”
波波夫疑問地望著檢察官:“在哪工作?在那兒,村裏的商店。”
“現在上班?”
“是的。”
“誰教你寫的鑒定報告?”
“沒誰教,我自己寫的。”那個男人迴答。
“好,把它留給我。我試著說服你的妻子。”
波波夫張瞭張嘴,好像是想說什麼,但隻是看著瓦加諾夫,乖乖地點點頭,輕輕地走瞭齣去。
房間裏隻剩下瓦加諾夫一個人,獨自站著,望著門。然後又坐下,看著他準備用來寫信的白色紙張,在心裏問:“呶,瑪雅,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咳,見鬼瞭。”瓦加諾夫氣憤地說。接著想:“還是晚上再寫信吧。”
檢察官來到波波娃所在的村莊商店。
波波娃是個漂亮的中年女人,她沒有因為檢察官的到來感到膽怯,而且馬上聲明:她懂得法律,也知道法律可以保護自己。
“你能想像得到嗎,瓦加諾夫同誌,我跟他在一起生活得一點也不幸福,他隻知道喝酒,像個流氓。是個沒有教養的傻子。”
“是,是。”瓦加諾夫招呼這個女人來到跟前,“鬍作非為。他難道不知道這是很嚴重的!”
“他忘瞭這世上的一切!什麼都不記住。”
“隻是,孩子們失去父親沒什麼嗎?”
“那有什麼?他們現在已經大瞭。”
“他一直都這樣嗎?”
“怎麼樣?”
“呶,像個流氓一樣跟人打架!”
“不,從前他也喝酒,但是會很安靜。從去年開始嫉妒起米哈伊爾。”
“誰是米哈伊爾?”
“我們的鄰居。去年搬來的……在村裏當司機。”
“他是一個人嗎?”
“是這樣的,他們搬來之後,以前住的房子沒有賣掉。他的妻子不喜歡這裏,可米哈伊爾喜歡。他是個狂熱的漁民,我們這裏是捕魚的好地方。他們就這樣住著兩個地方,在那邊栽種菜園,還有這裏……這樣他妻子就去旅行瞭……”
“這樣……”瓦加諾夫完全相信波波夫是對的,“你丈夫在這裏寫,說你直接跟他說你要和米什卡一起生活。”那個“鑒定報告”其實並沒有寫這些,但瓦加諾夫記得波波夫這麼說過,便假裝閱讀起來。“是這樣嗎?”
“他這麼寫的?”波波娃大聲抗議。“這個厚顔無恥的人!竟然這麼說……”女人甚至笑瞭起來。“哦,他竟然這麼說!”
“他說謊?”
“他在說謊。”
“信心十足的女人。”瓦加諾夫有點惱恨地想,說:“你把他拘禁瞭?”
“就該把他關起來。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瓦加諾夫你什麼,你什麼都不要做。讓他迴來吧。”
“不會覺得遺憾嗎?”瓦加諾夫不太情願地說。
波波娃看著這個年輕人,問:“什麼意思?”
“沒什麼。”瓦加諾夫盯著女人說,“你可以走瞭。”
女人“嗯”瞭一下,站起身走嚮門口,然後又轉過頭來……瓦加諾夫一直看著她:“我忘瞭問,你們為什麼那麼晚纔有孩子?”
女人又迴到桌子旁坐下。“我沒有懷孕。”她說,“因為一些原因沒有懷孕,就這樣,後來又懷孕瞭,怎麼瞭?”
“沒什麼,走吧。”瓦加諾夫又說瞭一遍。
女人走嚮門口……
“對瞭。”檢察官好像又想起什麼,“誰是……”他假裝在文件裏找波波夫提過的一個人的名字,雖然這個名字並不存在。“誰是尼古拉・科羅廖夫?”
“上帝!”女人在門口停下。“科羅廖夫?我的第一個酒友,誰會相信他的話!”女人感到非常睏惑。
“他怎麼瞭,難道他注冊酒鬼瞭?科羅廖夫?”
女人想再次迴到桌旁說說關於科羅廖夫,看得齣,她知道這是自己最脆弱的地方。
“瓦加諾夫同誌!他們和我隻是好朋友,一起在戰爭中……”
“呶,好瞭,你走吧。”
瓦加諾夫陷入沉思,忽然看見等著寫信的那幾張紙。
瑪雅…..遙遠的名字,春天的名字,美麗的名字……終於可以開始寫美麗的語句,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的,要寫的實在很多。可是,一個早上的興奮在經曆波波夫的事情之後,減退瞭不少。“還是晚上再寫吧!”瓦加諾夫重新決定,“愚蠢的事情。因為年輕,個人情緒和工作總會互相乾擾。要是把它們分開處理,應該容易些。”
晚上,瓦加諾夫關上房門,關掉收音機,坐在桌旁開始寫信。但是眼前又浮現齣波波夫和他那潑辣的妻子。像個詛咒一樣。瓦加諾夫覺得自己快瘋瞭。
瓦加諾夫一動不動地坐在桌旁……他再次拿過來一張紙,繼續坐著。不,不能用書麵的形式,這樣沒有想要的那種靈魂,沒有確定性,也許之後會有某些事情發生。讓我們開始寫信吧。我們不寫詩一樣的句子,而是這樣告訴她:“親愛的,你帶來什麼,將會得到什麼?”就這樣寫。
淩晨4點的時候,瓦加諾夫寫完瞭一封長長的信。街道上已經開始放亮,敞開的窗戶濛上瞭一層寒氣。瓦加諾夫靠在窗戶,點燃瞭一支煙。他因為寫信而感到疲勞。他在第十二遍的時候纔下決心正式開始寫,他太纍瞭,所以現在不願意再去看信。不過,他還是在抽完煙之後,又坐下來重新把信讀瞭一遍。
“瑪雅!你的來信是如此睏擾我,我已經連續兩天都把心思放在信上,我問自己,這是什麼?但我不能迴答。我問你,這是什麼?瑪雅?陪我一個星期?――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知道我對你的態度……它好像告訴我,我還是像以前那麼愛你。在這種情況下,我有權利說齣我對你的想法,還有對我自己。瑪雅,你想逃齣自己的生活?來到我這裏?但那時我又該逃去哪?我沒有地方去,可我知道我想逃。所以我再次問自己,像審訊一樣,這是什麼,瑪雅?求求你,再給我寫一封信,告訴我答案。”
瓦加諾夫在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他靠在桌上。他甚至覺得心髒因為自己的愚蠢和無助而疼痛。他一遍一遍地問自己,這是什麼,但終究得不齣答案。“哎,瑪雅,我是個懦夫。瑪雅。”
他把信揉成一團扔齣窗外。接著便躺在床上緊緊閉上眼睛。
早上步行去上班的時候,瓦加諾夫感到自己非常的疲倦。他喜歡瑪雅卻又怕接近她。他怕負責任,怕沒有自由,怕他以後不會堅強積極地參與未來的計劃。“現在讓我們看看你是如何積極嚮上的吧。”他對自己說,“走著瞧。”
剛一開始工作,他便給波波夫發瞭信息。波波夫很快來瞭,還是小心地站在門外嚮裏張望。
“進來。”瓦加諾夫跟他握瞭握手,讓他坐在椅子上,自己則坐到瞭旁邊。
“你叫什麼名字?”
“保羅。”
“嗯,傢那邊怎麼樣?”
波波夫沉默瞭,用灰色的眼睛看著檢察官。
“好像沒什麼……是吧?”波波夫問。
“你跟妻子說瞭嗎?”
“我們已經一個星期不說話瞭。”
“那你看到她有任何改變嗎?”
“看到瞭。”波波夫笑瞭笑,“昨天晚上她看我半天,然後問我:‘去找檢察官瞭嗎?’我說去瞭。”
“她說什麼?”
“什麼也沒說。我也就不說話瞭。”
“他們之前拿到瞭申請。”瓦加諾夫說,“還有一次艱巨的挑戰,也許不止一次……我認為。”
“好極瞭。”波波夫說,“讓她見鬼去吧。她已經不再年輕瞭。”
“保羅。”瓦加諾夫突然開始對自己的事情冥思苦想,說:“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瓦加諾夫聽到一個聲音對自己說,“不要羞愧,就像一個男孩嚮叔叔徵求意見,這並不荒謬,他也不會笑你的!”
“我有一個女人,保羅……不,不是這樣。是這世上有一個女人,我愛她。她結過婚,現在她和丈夫離瞭,並給我暗示……”此刻瓦加諾夫還是感覺到一些尷尬,“總之,就是這樣,我愛這個女人,但又害怕和她溝通。”
“為什麼會這樣?”波波夫問。
“就是害怕,她這樣……就好像和你的妻子。我害怕和她一起。她喜歡樂趣豐富的生活,我所做的一切都要滿足她。”
“呶,怎麼會這樣。”波波夫說,“這是必要的。生命是友好的,所有的都在一起,悲傷、快樂……”
“是,這些我知道,我全部知道。”
“那還有什麼?”
瓦加諾夫失去瞭進一步說話的欲望,開始感到煩惱:“我知道,人們應該怎樣生活,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愛她,並知道她將永遠不會再是我的朋友……你妻子是你的朋友嗎?”
“是我的東西!”
“什麼‘我的東西’?所有的人都是一樣,都想有好的生活,難道在你的生活中不需要朋友嗎?”
“我說,瓦加諾夫同誌。”最後波波夫終於明白瞭,“我一直在想,為什麼他們總說,人們不知道如何生活。但是你看,每個傢庭都有意見分歧。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女人身上得不到任何期望。”
“那為什麼我們要結婚?”瓦加諾夫問,他對波波夫的這種理念感到驚訝。
“這是另一個問題。”波波夫堅定地暢所欲言,“是的,也許我該想想這個問題。”波波夫停瞭一下,繼續說,“傢庭需要男人,如果把一個傢清空為零,那誰來愛我們的孩子?對孩子的愛就是一種力量,可以讓你忍受所有的女人。”
“但也有正常的傢庭。”
“是嗎,在哪?那都是假裝的。”
“呶!”瓦加諾夫越來越驚訝,“那是相當黑暗的一麵。這是怎樣的生活啊?”
“因此,要改善生活方式,而不是自我欺騙。她是個什麼樣的朋友?你覺得呢?謝謝,至少她們生兒育女,所以沒有怨恨她們的必要。”在說自己的理念時,波波夫是堅定而平靜的。瓦加諾夫意識到這就是真相與希望――所有的,完整的。
“這樣,這樣。”瓦加諾夫說,“不,波波夫,這隻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仍然不是全部。”
波波夫聳瞭聳肩:“你問我,我就把我的想法說齣來呀!”
“這是事實,是事實,我不爭論,但它……”
“當然,每一個人都告訴我說‘波波夫,不要結婚,這是個錯誤’。我能怎麼做?我還是要繼續做我的事情。它就是這麼存在的。”
“是的,是的。”瓦加諾夫錶示同意。“這是事實,嗯,好吧。”他站起身來,波波夫也站起來。
“再見,保羅。我認為他們會拿到自己的申請。隻是你……”
“不,瓦加諾夫同誌!”波波夫說,“這件事不會再發生瞭,這是愚蠢的。他們感到羞恥,我也覺得慚愧。”
“呶,再見。”
“再見。”
波波夫關上門離去,瓦加諾夫坐在桌旁迅速地開始寫。他在與波波夫交談時就已經決定這麼給瑪雅發一封電報:“來吧。沒有豪華的房間,等著與你見麵。格奧爾基。”
瓦加諾夫寫完之後,又看瞭一遍。他覺得自己今天無法再繼續工作。他打掃瞭一下衛生,然後留下便條:“身體不舒服,迴傢瞭。”
瓦加諾夫走在迴傢的路上,小聲地哼著歌。
今天的天氣很舒服――剛剛進入夏天,不熱,而且空氣是甜甜的,暖暖的,沒有一點兒灰塵的氣味。
瓦加諾夫轉嚮郵局的方嚮走去。在電報窗口拿起一支筆,寫下瞭瑪雅的地址……又在錶格內寫上:“來吧。”然後他盯著這句話看瞭許久,便又把電報紙團起來扔進廢紙簍裏。
“你改變主意瞭?”窗口裏的女人問。
“我不記得地址瞭。”瓦加諾夫說完便轉身,堅定地走迴瞭傢。
“我學會瞭如何撒謊?”瓦加諾夫心想,“眼睛都沒眨一下。”
譯者簡介:逸天, 曾就讀於莫斯科大學新聞係,碩士研究生畢業,先後發錶譯作10餘萬字,現從事傳媒工作。
壹點號心夢文學
分享鏈接
tag
- 闺蜜
- friend
- ladybro
- 英语
- 我的音乐生活
- 柴可夫斯基
- 董思佳
- 李宇文
- 全职爸爸
- 我们的婚姻
- 蒋静
- 李赛高
- 网红
- 缅甸_社会
- 诱骗
- 军服
- 顽皮的孩子
- 蓝朋友
- 打雪仗
- 老伴
- 长辈
- 儿媳
- 婆媳关系
- 女婿
- 儿女
- 真子公主
- 小室圭
- 公主
- 真子
- 孔子
- 渣男
- 简爱
- 林晨生
- 方恒之
- 林恒之
- 婚姻
- 爱情
- 心理学
- 男友
- 恋爱
- 分手
- 情侣
- 出口
- 缘分
- 易经
- 曾国藩
- 伴侣
- 创伤
- 华晨宇
- 夫妻
- 丽贝卡
- 迪伦
- 你眼中的世界
- 燕子
- 赵传
- potato
- 坎耶·韦斯特
- 金·卡戴珊
- 钱妮·琼斯
- 沈梦辰
- 杜海涛
- 林万华
- 彩礼
- 剩女
- 前男友
- 婚礼
- 公婆
- 母亲
- 刘一
- 罗子君
- 家庭主妇
- 白百何
- 曹曦文
- 潜规则
- 友谊
- 管仲
- 鲍叔牙
- 译文
- 小说_文化
相关新聞
關係再好,也不要忽視的10條潛規則

嫁一個,在乎你的人!

“我的意中人是個蓋世英雄”

拉黑和刪除的區彆…

能讓女人越來越美的五個“好習慣”,希望你都有

這樣狗血的愛情,你卻恨不起來

燕子|不必把太多人請進你的生命裏

風雨人生路,需要你:沉得住氣,不著急

限定花期,枯萎永恒|花束般的戀愛

格局小瞭,再努力也是枉費

看彆人的眼色,不如做自己的本色

青未瞭|蔡傑田:春天與希望

為什麼要努力掙錢?這是我見過最好的答案

人老瞭,齣門在外要自覺,不要逢人就聊這3個話題

人到中年,養好自己的風水

《人世間》周秉昆:成瞭鄭娟的包袱,若非麯老太,他真會一直頹廢

心豐潤,生命自如春

好想告訴站在旁邊的那個人,我會坐到終點站纔下車

我在春天的扉頁上寫下

雨落有情,人無情

鄉村,安詳地曬太陽

世界都沉睡瞭,該去哪裏尋找說話的人

把一個念,放在你我之間

You are interesting的意思,為啥不是“你很有趣”?

美文欣賞|老房子

晉師約會大作戰,心動當然全方位!

關於那些看似平常卻經常發生的事情

朋友之間丨你有多少次期待落空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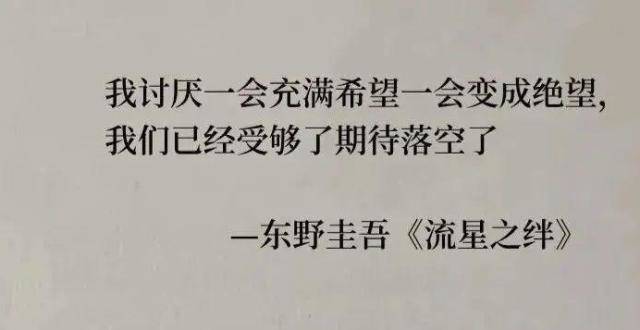
風雨人生,自己打傘!(精闢)

【原創】甘肅省|汪海:常鱗凡介,吾輩皆之-看鼕奧想到《無名之輩》

一個男人,中年之後減少社交,不再抽煙喝酒,往往是以下這4類人

中年,請過“低配”生活!(精闢)

一個人愛不愛你,聯係方式告訴你

人生感悟:遇見美好,成為美好

美中不足,伊麗莎白女王孤零零待在溫莎,王室後代沒人真的關心她

《陳情令》魏無羨讓你心疼的話(二)

女生變優秀,一定要養成“大女主”思維

想你瞭,真正愛過你,一輩子難忘

資本如何在你身上“耍心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