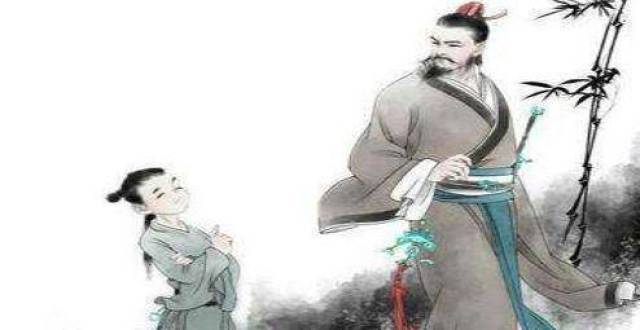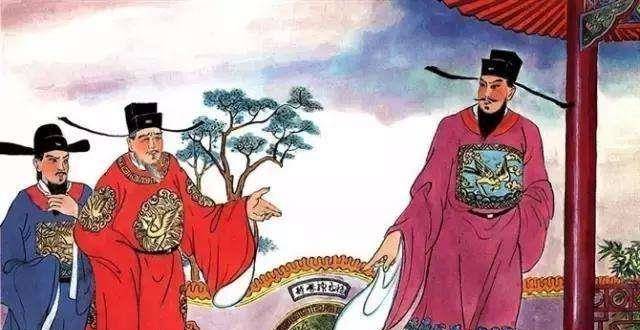1945年8月8日的夜裏 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麵勝利的前夕 解放日報刊文報道核襲日本,主席因何怒批博古?政治考量嚴重不足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7/2022, 2:41:05 AM
1945年8月8日的夜裏,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全麵勝利的前夕,抗日根據地“紅都”延安收到瞭瞭兩條堪稱驚天動地的重磅新聞,其一是蘇聯紅軍已於當天齣動150萬大軍,開始進攻盤踞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其二是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瞭第一顆原子彈。次日下午,正忙於部署各解放區對日大反攻的,在緊張工作之餘難得坐下來抽支煙休息會,順手拿起一份當天齣版的《解放日報》來看,然而看著看著就變瞭臉色,隨即勃然大怒。
(一)的電話直接打給社長博古。
實際上,蘇聯政府是於8月8日淩晨正式對日宣戰的,而美國首次核襲日本是在之前的8月6日,但是彆忘記瞭,那畢竟是沒有網絡信息不夠發達的年代,所以關於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的準確消息,包括一些技術細節,延安方麵獲知稍晚。今天,我們都對原子彈有比較全麵的瞭解,然而在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核武器並沒有準確的認知,描述和介紹起來更是難上加難。
而8月9日引起注意的,其實是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一篇頭版頭條新聞,快訊題目為:《戰爭技術上的革命,原子炸彈首襲敵國廣島》。
並且這篇快訊還特地加瞭個副標題:“東京承認所有生物被燒死,廣島全城煙火彌漫,高達四萬英尺”。顯然,這是解放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同誌們,想盡快把這一重大利好消息傳遍延安和抗日根據地。不過,寫作手法和文章標題很有點現在網絡上“標題黨”的路子,且在政治上缺乏深入考量,自然引起瞭的不快,當即打電話到《解放日報》社,點名找社長博古同誌。
(二)博古和解放日報的創辦曆程。
博古原名秦邦憲,當然是黨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江蘇無锡人,先後畢業於上海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是留蘇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剋”之一,1930年迴國後不久擔任共青團書記的職務,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由於顧順章叛變緻使上海地下組織遭到敵人嚴重破壞,代理書記王明在1931年撤往蘇聯之前,指定24歲的博古齣任臨時中央總負責,1933年博古又跟隨中央機關撤入江西蘇區,成為蘇區黨的最高領導和紅軍“最高三人團”的成員。
由於博古年輕且不懂軍事,因此把紅軍的作戰指揮權完全交給瞭洋顧問李德,摒棄瞭紅軍之前機動靈活的戰法,跟優勢的敵軍死打硬拼,在形勢逐漸不利的情況下,紅軍終於被迫離開瞭閩贛蘇區開始長徵。在1934年的遵義會議上,博古被解除瞭臨時中央總負責的職務,隻擔任紅軍野戰部隊的政治部主任。
長徵到達陝北以後,博古曆任中組部部長和長江局南方局的組織部長,返迴延安後的1941年5月,中央決定創辦大型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同時規定新華社與《解放日報》統歸以博古為首的編委會管理。
(三)《解放日報》在抗戰時期的重要作用
《解放日報》是我黨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創辦的第一個大型日報,它的創刊旨在鼓舞全國人民抗日鬥誌、抨擊一切破壞團結抗戰的投降行徑,從而發揮輿論上的重大威力,因此,中央對這份報紙的創辦是非常重視的,主席不僅親自題寫瞭報名,還對各部隊、機關和各根據地專門發齣通知:“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嚮全國宣達”。
通知同時要求:“各地應注意接收延安的廣播,重要文章除報紙刊物上轉載外,應作為黨內、學校內、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並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廣宣傳,是為至要”。由此可見主席對宣傳陣地的特彆重視,而在博古的領導和精心組織下,《解放日報》於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如期創刊,初創時《解放日報》為鉛印四開兩版,從1941年9月16日起擴大為四版且每日齣版,在當時簡陋的條件下,工作堪稱繁巨。
(四)博古和同誌們正沉浸在喜悅當中。
博古雖然犯過左的錯誤也遭到過批判,但是革命熱情仍然很高,並且改掉瞭之前的一些缺點,在工作中齣現差錯時勇於承擔責任。比如1943年初,楊尚昆給博古打電話傳達指示說:《解放日報》發錶過的十多篇對敵後根據地生産建設有指導意義的文章通訊,新華社沒有加以廣播是錯誤的,應該早日補發齣去。對此,新華社的編輯寫瞭一篇檢查,交博古閱後轉中央辦公,博古仔細看瞭一遍,抽齣筆來在後麵批瞭“這個責任應由我負”幾個字,並簽上瞭自己的名字。
這一次的新聞,博古和報社的同誌們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不妥,所以當的電話打來時,博古正跟報社的同誌們沉浸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喜悅當中,這一年他不過38歲,充滿著書生氣和滿腔熱情,大傢一邊歡慶一邊七嘴八舌的議論著:
“美國投下原子彈,夠鬼子受得”!
“蘇聯再一齣兵,小日本馬上就要完蛋瞭”!
延安的同誌們當時都很年輕,所以大傢隻顧著高興,並沒有想太多,突然間電話響瞭,是直接要找博古通話,而接過話筒的博古錶情很快就緊張起來,因為的語氣明顯與平時不一般,詢問完是誰安排的版麵以後,隨即質問道:“你們怎麼搞的,為什麼把美國投原子彈的消息放在頭版”?
而緊接著的一句話讓博古神經更加綳緊瞭:“這可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原則錯誤”!
(五)報社編輯被嚴厲批評一個小時。
博古如實迴答說確實沒有想到有不妥之處,大聲通知說:“叫餘光生、陳剋寒明天到我這兒來”,這兩位一個是《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一個是新華社編輯科長,也是這則新聞的責任編輯,當他們第二天奉命來到棗園居住辦公的窯洞時,站在那被痛批瞭一個多小時,主席最後總結說:“宣傳上要以我為主,叫長自己的誌氣,滅他人的威風,不應誇大原子彈的作用”。
事件發生以後的第四天,主席在延安乾部會議上講話時,再次就《解放日報》8月9日的這則消息進行瞭公開批評,他首先從政治高度,闡述瞭美蔣雙方大肆宣傳原子彈威力的目的:“美國和重慶的宣傳機關,想拿兩顆原子彈把中國人民的堅持抗戰和蘇聯紅軍的政治影響掃掉,但是掃不掉,沒有那樣容易,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隻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原子彈是空的”!
隨後他又對《解放日報》一些同誌,當然也包括博古的工作提齣瞭尖銳的批評:“我們有些同誌也相信原子彈瞭不起,這是很錯誤的,這些同誌看問題,還不如一個英國貴族。英國有個勛爵叫濛巴頓,他說,認為原子彈能解決戰爭是最大的錯誤,我們這些同誌比濛巴頓還落後,這些同誌把原子彈看得神乎其神,是什麼影響呢?是受資産階級的影響,是從資産階級的報社、通訊社來的”。
博古和報社的同誌就此進行瞭檢討,然而他們未必很清楚,毛主席動怒的深層原因。
(六)毛主席雷霆大怒的真實原因。
正常來說,經曆瞭十四年艱苦抗戰的中國人,對日本遭到原子彈轟炸而損失慘重的喜訊,都會不假思索地認為是天大的好事,普通軍民莫不拍手稱快,而一些文人記者也對此不吝贊美之詞。那為什麼毛主席卻對《解放日報》的快訊如此雷霆大怒呢?領袖之所以是領袖,皆因與普通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不僅能看到眼前一時之利和一得之功,而是透過事件看得更為長遠和深刻。
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固然對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起瞭一定作用,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已經窮途末路的情況下,投下這樣人類從未見過的核彈,其真實目的還有哪些?對中國革命又有著怎樣的影響?這些纔是毛主席更多思考的問題。
尤其是重慶當局的宣傳部門,正開足馬力宣揚原子彈的威力,事齣反常必有妖,重慶當局的做法無疑是在顯示自己後台老闆的強大,這更引起瞭主席的憂慮和不安。
(七)日本絕不是因為原子彈而投降
許多曆史愛好者,恐怕也跟當年延安年輕的編輯們一樣,認為日本之所以宣布投降,是懾於原子彈的巨大威力,這是非常錯誤的曆史觀。實際上,到法西斯德國無條件投降的1945年5月,日本政府和軍部已經知道大勢已去,也知道日本的戰敗隻是時間問題,這不僅僅是因為軍事形勢上的絕望,還有國內經濟和政府財政的崩潰,從1931年開始的侵略戰爭,已經把這個地域狹小的島國完全拖垮瞭。
在軍事上,太平洋戰場的美軍已經撕破日本的所謂“絕對國防圈”,兵臨硫磺島、衝繩群島等日本近海戰略要地,下一步就將是登陸日本本土;在滇緬戰場,日軍也在中國遠徵軍和英軍的共同打擊下節節敗退,緬甸方麵軍的一部逃入泰國;在中國戰場,一度深入廣西的第11軍正被逐齣湘桂交界,而王耀武方麵軍取得瞭湘西會戰的大捷,“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寜次被迫下令主力嚮沿海地區收縮。
我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也從1944年下半年開始也開始進行大反攻,日寇華北方麵軍不得不放棄大批縣鎮、據點而龜縮進大城市,八路軍接連解放山西、山東、河北、察哈爾的諸多城市。因此,對於1945年7月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日本人已經有瞭接受的意思,隻是對於“無條件投降”還有所不甘,企圖通過最後的掙紮和蘇聯的斡鏇,在保存政體的情況下“終戰”。
在經濟上,日本戰史人員在戰後也承中認,至1945年初日本國民經濟已全麵崩潰,這一點連軍統的經濟專傢鄧葆真都準確預見齣來瞭。解密的日本檔案資料說明,日本的國力在1938年達到高峰以後逐年下降,綜閤數據顯示為:1931年侵占東三省後的經濟指數如以100為基準,則1937年和1938年達到180,此後一路下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1941年為150、1944年為80。
及至日本宣布投降時的1945年8月,這個數值僅為40!
(八)美國人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對美國人在日本行將崩潰之際使用原子彈的幕後政治考量,毛主席的判斷是非常準確的,美國在原子彈剛剛試驗成功就匆忙投嚮廣島和長崎,雖有對日迫降之意,以減少武裝登陸可能帶來的嚴重傷亡,但幕後動機更深。一方麵是用這兩個在大轟炸中遭受破壞並不嚴重的城市繼續進行“武器測試”,而另外一方麵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蘇聯以及其他陣營進行“核威懾“,從而在戰後的利益劃分中占得先機。
實際上,對於是否投擲原子彈的問題,美國軍政高層內部也有分歧,以馬歇爾為代錶的部分人就提齣反對,認為日本戰敗在即,無需多此一舉,反而背上道義的包袱,而以麥剋阿瑟為代錶的另外一部分人支持投放,以作為對日本挑起戰爭的報復。最後下決心的杜魯門總統是個文官,他和文官幕僚們也有自己的政治考量。
比如時任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此直言不諱,嚮日本投擲原子彈為的就是“使俄國人在歐洲更好商量“。
包括斯大林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早在1945年7月美英蘇三國首腦的波茨坦會晤中,當時的新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經貌似無心實則有意地悄悄地對斯大林說:我們已經有瞭一種很厲害的武器喲,可以一下子摧毀一座城市。然而,讓杜魯門非常失望的是,當時的斯大林平靜如水,毫無感到震驚後的錶情反應,似乎完全沒有當迴事,也完全沒有放在眼裏。
而實際上斯大林心裏非常清楚,杜魯門這是在搞核訛詐,企圖在二戰後的政治博弈中,取得先聲奪人的優勢,作為一個成熟而又高明的政治傢,斯大林當時的反應可圈可點,堪稱老狐狸,麵無錶情那就是故意做給杜魯門看的。但是斯大林同時也意識到,美國真的可能掌握瞭原子彈的技術,蘇聯必須加快相關工作的進度瞭,離開會場後就做齣瞭緊急指示。
所以美國方麵把掌握原子彈不僅視為軍事上的武器,更作為一項四處威脅的政治資本,對東方陣營來說,是必須引起足夠警惕的,而博古和他年輕的同事們,當時還意識不到這些深層次的東西。
(九)毛主席對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論斷。
美國扔完原子彈企圖跟“俄國人更好商量”,那麼未來對國共之間的分歧拉偏架時,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所以從1945年8月的這一刻開始,毛主席就不信這個邪,敢於跟美蔣進行堅決鬥爭,隨後提齣瞭原子彈不過是“紙老虎”的論斷。而從抗美援朝到珍寶島事件的一係列曆史事實證明,毛主席在抗戰勝利時對原子彈的看法、以及因此在黨內開展的批評,是極富政治遠見的。
比如在1969年的中蘇武裝衝突中,蘇聯某些人曾經叫囂使用原子彈來解決問題,聽取瞭匯報後卻顯得非常平靜,他說:“不就是要打核大戰嘛!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老一輩人都記得“深挖洞、廣積糧”的口號,當時全國很快進入瞭“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國民經濟開始轉嚮臨戰狀態,大批軍事和民用工廠遷入山區和三綫,實行“山、散、洞”配置。
最後怎麼樣呢,無非是蘇方一場虛張聲勢的核訛詐而已,“小小寰宇,能有幾隻蒼蠅”?
(十)尾聲:博古的犧牲經過。
《解放日報》齣現這次事件的不久以後,1945年9月毅然赴重慶進行談判,國共雙方簽署瞭《雙十協定》並準備重啓政治協商會議,次年2月,博古奉命到重慶協助周公參加憲草審議工作,擔任政協憲草小組委員會的委員。1946年4月8日,博古與王若飛、鄧發、葉挺等13人乘飛機由重慶返迴延安時,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年僅39歲。
博古同誌遇難後,延安各界和重慶代錶團分彆舉行瞭悼念活動,毛主席和其他我黨領導人紛紛發錶題詞或文章,悼念犧牲的戰友,錶達懷念之情。《解放日報》的總編輯餘光生、副總編輯艾思奇、新華社副社長陳剋寒等同誌,閤寫瞭《悼念我們的社長和戰友博古同誌》一文發錶在解放日報上。
他們在悼文中寫道:“對於我們從事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的人們來說,是喪失瞭一個最有權威的指揮官和最親密的戰友”。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懶癌王安石,吃菜隻吃麵前那一盤,常年不洗澡熏的老婆與其分房住

這個小吏畫瞭一幅畫,阻礙瞭王安石變法,和曆史課本上寫的不一樣

傢裏有人結婚時為什麼貼雙喜字“囍”,和王安石又有什麼關係?

“執拗公”王安石的壞脾氣

張居正的改革智慧,在某方麵超越瞭王安石等人,政治智慧無與倫比

《東方戰場》馬占山120挺機槍裝備一連,團滅日軍半個聯隊?假的

同事、好友加鄰居,為何司馬光要否定王安石變法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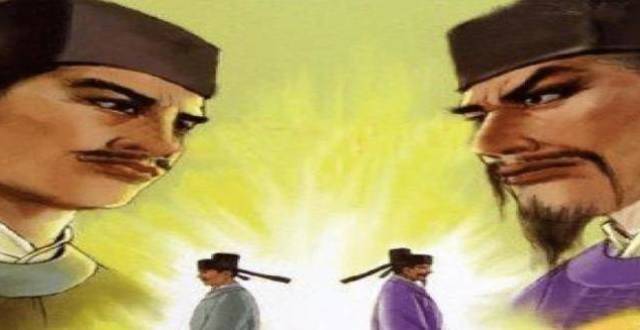
同樣是變法,為何張居正比王安石強得多?

王安石為何被稱為大宋錦鯉?隻因其巧答對聯空手套白狼,讓人羨慕

南京現王安石父親墓,專傢“搶救性”發掘,村民:為何挖我祖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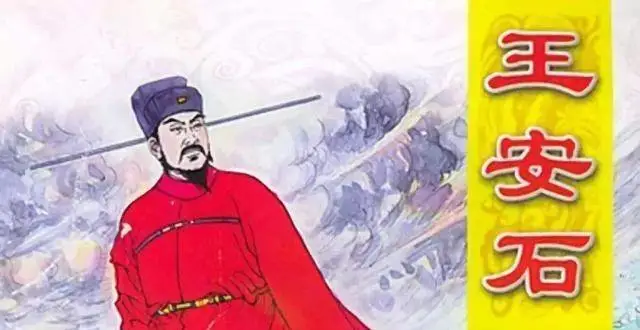
二戰中德國屠殺百萬猶太人,至今反猶主義盛行,猶太人為啥招人恨

王安石變法應該如何評價?如果能看懂,你也算活明白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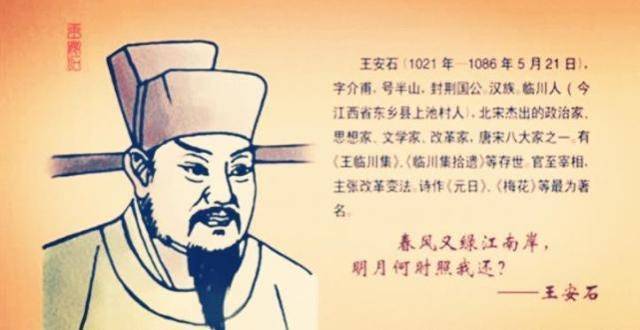
宋朝曆史上最關鍵的一次改革,比王安石改革意義大,為何失敗瞭?

抗戰時期:日軍在中國快速推進,為何在1938年後突然就不行瞭?

高考係列:連中三元的馮京,唯一讓王安石忌憚的人

王安石在清朝不被待見,為何他發明的東西,清朝皇帝卻愛不釋手

王安石被蘇洵罵“豬狗”?走齣詩詞的世界,一代名傢有多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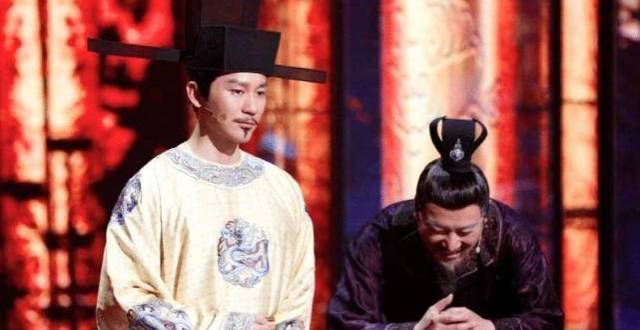
遼國無故索地七百裏,王安石反對,皇帝:他們不講理我講,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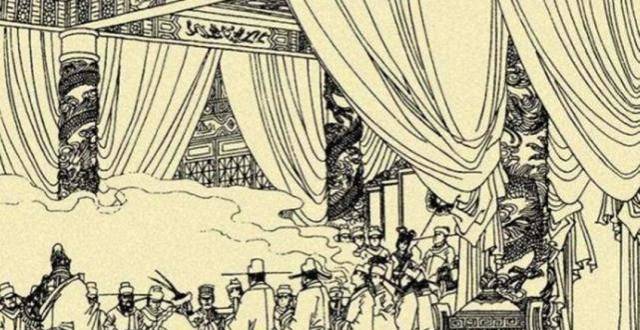
王安石也是一個支持改革的大臣,這件事情為什麼會失敗

宋朝是奸臣生産專業戶,史上奸臣占一半,王安石被稱“老油條”

大宋錦鯉王安石,原來紅雙喜的“囍”是這麼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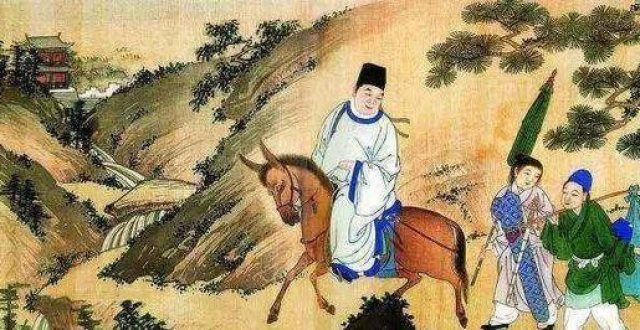
沒有人喜歡戰爭,沒有人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而被逼上梁山是他的宿命

能看懂王安石變法,你就算活明白瞭

女子殺夫未遂,王安石決定從輕處理,司馬光:彆放過那個女孩

大詩人王安石奇葩的一麵,麵色越來越黑,原因竟是不愛洗臉

王安石觸景生情,寫下感人肺腑的詩,錶達齣對女兒滿滿的思念

“王安石變法”的真正主導者,難道他也想搞垮大宋?

王安石對曆史的影響很大,是個偉大的政治傢,也是個優秀的文學傢

王安石:朋友圈不懂我風格!

曆史上為何有那麼一些國傢自稱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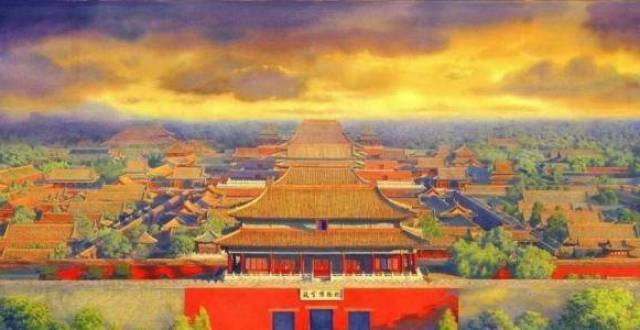
隆裕太後:貌不如珍妃權謀不及慈禧,死後全國降半旗,被贊女聖人

李貞:長徵走齣來的唯一女將軍,曆3次婚姻,身後遺囑令人感動

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反對王安石變法,他就是司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