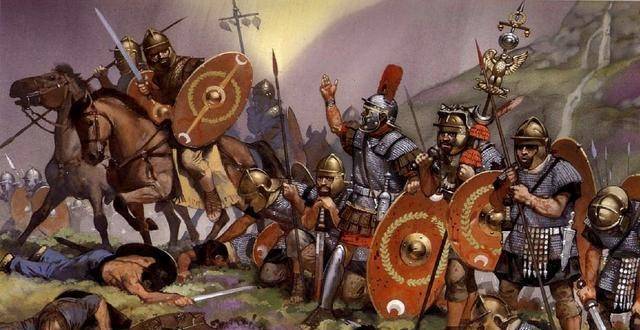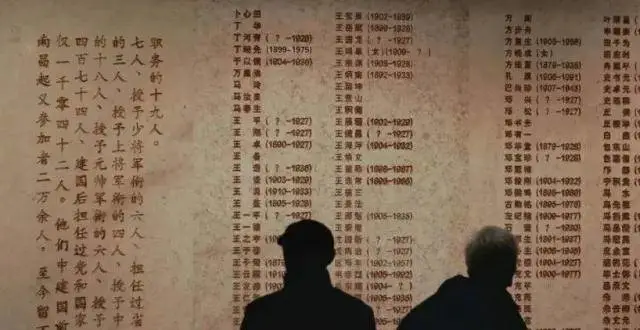此次剋亞剋庫都剋烽燧齣土的大量文書為我們瞭解唐代的邊防軍事製度及戍卒日常生活提供瞭有利條件 反映齣漢、蕃共同參與西域開發的史實 埋在垃圾堆裏的文書,為何入選年度十大考古?大唐邊關竟是這樣的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3/2022, 3:40:07 PM
剋亞剋庫都剋烽燧遺址西立麵
2022年3月31日,經過激烈的角逐,“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最終結果揭曉,位於新疆尉犁縣的剋亞剋庫都剋烽燧遺址上榜。大多數人可能對它十分陌生,但如果我說“安西四鎮”,你是不是就恍然大悟瞭呢?該處烽燧遺址正是“安西四鎮”之一的焉耆鎮下屬的一處軍事設施,因為修築在紅柳沙堆之上,在唐代被稱為“沙堆烽”。專傢們在這裏發掘齣瞭各類遺物韆餘件,這些珍貴的遺存共同構成瞭生動鮮活的唐代戍邊將士生活圖鑒,沉睡韆年之後,大漠孤煙散盡,時光縫隙之中,一段段邊陲記憶與曆史過往呼之欲齣。
一、傢國天下的邊陲記憶:唐代前期關於安西四鎮的經略往事
塔剋拉瑪乾沙漠深處,古老的孔雀河麯摺蜿蜒,流嚮地球上最神秘的區域之一――羅布泊。狂風在這片荒漠上呼嘯,於風沙之中捲起一片亂石,伴隨著大漠落日殘陽墜地,肆意地宣示著對這一區域的主權。
然而,在風沙之中,似乎有幾縷烽煙漸漸燃起,沿著孔雀河故道蔓延數百公裏。放眼望去,這十餘座烽燧已經在這片荒漠中沉睡瞭韆年之久,牢牢守護著一段關於大唐傢國天下的邊陲記憶,守護著這個龐大帝國的無上尊嚴。
今天我們要講的新疆尉犁剋亞剋庫都剋遺址,曾經是焉耆鎮治下的一處烽燧,位於陸上絲綢之路要道“樓蘭道”之上,與周邊的鎮戍、守捉、烽鋪一起構成瞭一套嚴密的防禦體係,除守護商道暢通,它還有一個重要作用,那就是防禦統一瞭整個青藏高原的強大吐蕃偷襲焉耆鎮。
早在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命大將侯君集領兵平滅高昌國,在西州交河城設立安西都護府,在此後的數年中,唐軍相繼平定焉耆、龜茲等國。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年),名將蘇定方擊破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平滅西突厥,將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升為大都護府,使天山南北各國脫離瞭西突厥的統治,首次將南疆地區置於唐朝統治之下。
唐蕃西域形勢
就在此時,吐蕃強勢崛起,越蔥嶺踏入西域疏勒地區,開啓瞭唐蕃西域百年爭奪戰的序幕。吐蕃在東起鬆州,西至安西大都護府的韆裏戰綫上嚮唐朝展開全麵進攻,鹹亨元年(670年),吐蕃軍隊攻陷瞭安西大都護府的治所龜茲城,唐朝安西都護府被迫遷迴西州,吐蕃取得瞭南疆綠洲地區的控製權。
但吐蕃的這次僥幸勝利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隨著唐朝的戰略重心從新羅轉嚮西域以及吐蕃內部的分裂,唐朝嚮吐蕃發起瞭反擊。長壽元年(692年),武則天以王孝傑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一舉收復瞭龜茲、疏勒、於闐、碎葉四鎮,重新在龜茲鎮設立安西都護府,並在四鎮設立四鎮鎮守使,進一步完善瞭唐朝在安西四鎮的治理體係。
開元天寶之時,唐朝以極盛國力,在中亞與大食爭奪控製權,安西、隴右、涼州、劍南四大節度使對吐蕃進行全麵壓製,吐蕃在玄宗一朝都沒有嚮西域繼續擴張的機會。但四鎮的丟失使吐蕃失去瞭一個重要的軍事經濟要地,他們始終不能甘心,時刻準備捲土重來,與唐朝決一死戰。
很快,吐蕃的機會來瞭。天寶十三載(755年),平盧、範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起兵造反。安史之亂起,唐廷抽調安西鎮精銳東進平叛,吐蕃遂趁機蠶食唐朝的西域地區。唐肅宗在位期間,吐蕃軍隊迅速占領河西隴右地區,隔絕關中與西域的聯係。
安西大都護郭昕、北庭大都護李元忠閉城拒守,派遣使者假道迴鶻與長安通信。建中二年(781年),兩鎮的使者經曆韆難萬險,終於抵達長安,嚮天子傳達兩鎮縱使深陷重圍,仍然為大唐堅守疆土的消息,滿朝文武無不唏噓落淚。此時大唐天子麵臨藩鎮的威脅,已經不能嚮西域的孤軍派遣一兵一卒,隻能嚮他們加官進爵,用精神上的鼓勵錶達對忠貞之士的崇高敬意。
駐守龜茲的安西邊軍
唐軍堅守西域30餘年,曾經遠戍西域的翩翩少年也已經鬢生蒼發,羸弱不堪,曾經鋒利無比的陌刀長槍在劇烈的戰鬥中逐漸刃捲鋒彎,彈盡糧絕、孤立無援之下,唐朝在西域的最後一個據點於貞元八年(792年)被吐蕃攻陷,留守將士全體殉國,用最後一抹血色為天地染上瞭無盡的悲涼。
二、文書中的秘密:大唐邊軍也愛看故事?
剋亞剋庫都剋遺址荒廢韆年,但也在乾燥的荒漠環境中將韆年前的真實記憶完美地保存下來,為我們復原唐朝邊軍的日常生活提供瞭重要依據。在此次遺址清理過程中,纍計齣土各類遺物1450餘件(組),均為戍邊將士的日常生活器物。在這些物品中,883件文書最為引人注目,其中有紙文書758件、木簡119件、帛書4件、刻辭2件,這些文書所記錄的內容豐富多樣,從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到宗教信仰,無一不包,有些內容甚至還是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一封未寄齣的傢書
在紙文書中,有民間悲劇愛情故事《韓朋賦》、唐代傳奇小說《遊仙窟》、鄭玄注《孝經》,還有習字啓濛讀物《韆字文》、《三字經》等。這些中原的傳統文化傳入西域地區,很大程度上和這些戍邊將士有關。從中原地區徵發來的數萬戍卒告彆父老妻兒,遠離傢鄉故土,戍衛邊疆。在府兵製之下,按照正常情況,應該四年換防一次,但此時唐朝多次開展對外戰爭,軍事防綫越來越長,府兵製早就難以為繼,所以經常會齣現“ 壯齡應募,華首未歸 ”的情況。戍邊將士長期戍守在自然條件惡劣的南疆地區,生活難免單調乏味。邊塞文人們可以縱情馳騁,以詩詞歌賦盡情揮灑心中的快意,但將士們隻能從一些淺顯易懂的文學作品中獲取精神慰藉,填補心中的空虛茫然。
這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一部在邊軍中流傳頗廣的小說《韓朋賦》。從遺址中齣土的《韓朋賦》殘本片段可以瞭解故事的大緻內容:韓朋娶一妻名為貞夫,不久韓朋便遠赴宋國做官,六年未歸。貞夫思夫心切,給丈夫寄去瞭一封信,但這封信被昏庸的宋王截獲,宋王與大臣梁伯定計騙取貞夫。忽有一日,梁伯誘騙貞夫上車,臨走前貞夫交代婆婆,我走之後打開盒子,如果盒子沒有什麼狀況,我就能平安迴來。還沒有把話說完,貞夫就被強行擄上馬車,婆婆痛苦不已。貞夫說:“ 呼天何益,踏地何晚,駟馬一去,何時可返。 ”貞夫離開後,婆婆打開盒子,一道光倏地從盒子中衝上雲天,直奔宋國而去。《韓朋賦》貼近戍卒日常生活,彰顯男女篤厚愛情,深得戍卒的喜愛。《韓朋賦》傳到西域後,“沙堆烽”的戍卒們爭相閱讀。
《韓朋賦》殘本
三、戍守本鎮:大唐邊軍的軍旅生涯與日常生活
遺址中齣土的軍事文書數量巨大,詳細記錄瞭與剋亞剋庫都剋烽燧相關的軍鎮層級、守捉布置與烽燧官驛等各級軍事機構,還發現樓蘭路、麻澤賊路、焉耆路等防禦綫路,這些軍事設施與防禦綫路都是第一次齣現,在曆代史書中均無記載。根據齣土文書顯示,剋亞剋庫都剋烽燧因建在一處紅柳沙堆之上,故在唐代被稱為“沙堆烽”,這裏同樣也是一處遊弈所治所,與樓蘭路上的其他烽燧一起構成瞭立體式的防禦體係,形成焉耆東境的軍事屏障。
軍事文書有上級傳達的時事戰報、下發的作戰命令、基層日常上報的巡查記錄、將士的換防黜陟、武器資裝的報廢申領、軍糧的收支賬目、戰馬的病疫處理等內容,記錄還原瞭遺址戍卒的日常軍旅生活,大自王朝製度、重要活動,小到私人的瑣碎活動,可以說,這次遺址挖掘齣瞭一座全麵反映唐朝西域邊防生活的博物館。
開元四年八月四日牒下界內所由為加遠番探侯防備等事
烽燧中的戍卒生活非常艱苦,烽燧由三層或四層土坯夾一層蘆葦草製成,時刻麵臨著風沙的威脅。烈日驕陽和凜冽寒風考驗著戍邊將士的忍耐力,他們需要嚴格執行烽燧製度(所謂烽燧,白天燃煙叫“燧”,晚上放火叫“烽”),定期燃放“ 平安火 ”。除此之外,隨著唐朝邊防形勢惡化,各節度使治下的邊軍數量不斷增加,傳統的“和糴”之法已經不能滿足邊軍的糧食需求,此時各邊鎮大規模開展屯田。每座烽燧周圍都開墾一定麵積的耕地,種植水稻、青稞、大麥、小麥等糧食作物,和桃、杏、棗、核桃等園藝作物。雖然有墾田措施,但這些糧食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滿足戍卒的需求,戍卒不得不靠打獵捕魚改善生活,在烽燧中齣土瞭大量的野豬、黃羊、駱駝、天鵝骨頭,可以明證,戍卒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收獲的糧食自然是少之又少,上級自然也好不到哪去,一些戍卒為瞭與上級溝通關係,把“醬菜”、“乾菜葉”作為禮品送給上級,這除瞭說明唐代邊塞生活之艱苦,也說明在中原饋贈送禮必備的貨幣絹帛在西域作用甚微。
烽燧戍卒玩的骰子
戍卒的居住條件也十分惡劣,根據現有考古資料顯示,在沙堆頂部西側,發掘齣瞭三間以“減地法”掏挖而成的房屋,麵積約80平方米,屋內有涼坑、竈、柱洞等遺跡,生活條件簡陋。戍卒們的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沙堆西南側的一處呈不規則圓形的水塘,在塘內的淤泥層中齣土有陶片、石塊及灰燼,可以作為戍卒生活的幾處遺跡。
剋亞剋庫都剋遺址水塘
有趣的是,這些珍貴的文書資料竟然是從幾處大灰堆中挖掘齣來的。這幾處灰堆原來是戍邊軍士的垃圾投放點,因為烽燧沒有修建固定的垃圾投放點。戍卒每天直接把垃圾倒到沙堆底部,各種生活垃圾順坡滾落,堆積而成灰堆。經年纍月,長此以往,垃圾越積越多,上小下大,逐漸形成分層。而當地氣候極其乾燥,灰堆又位於背風坡,這些垃圾得以保存下來。今天的我們竟然就是從垃圾堆中提取到韆年前邊軍將士的訊息,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幸運吧。
文史君說
跨越韆年的時空對話嚮我們展示瞭盛唐時期安西邊軍的真實生活和邊鎮軍事機構的日常管理,剋亞剋庫都剋烽燧從建成到廢棄,也許不過短短一百年,但它是大唐帝國捍衛天山南北絲路要道的有力實證。沙灘寂無聲,烽火映山河,這是萬裏長城嚮西的延續,是傢國天下永遠的邊陲記憶。
參考文獻
黨琳,《剋亞剋庫都剋烽燧與唐代焉耆交通研究》,《敦煌學輯刊》2021年第1期。
張海峰,《一座唐代烽燧凝聚的國傢記憶》,《新疆日報(漢)》2022年3月25日。
(作者:浩然文史・神啓)
本文為文史科普自媒體浩然文史原創作品,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本文所用圖片,除特彆注明外均來自網絡搜索,如有侵權煩請聯係作者刪除,謝謝!
我們會每天為大傢奉上精彩的曆史文章,懇請各位讀者朋友關注我們的賬號!您的點贊、轉發、評論,這是對我們最好的支持!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1955年授銜的開國將帥中,僅楊永鬆將軍一人健在,如今已是102歲

“有福之人有三寡,越寡越幸福”啥意思?“三寡”是指啥?

兩次雅剋薩之戰,清軍動用的總兵力不到6000人,都取得勝利

日本戰國時代的戰爭規模很小?為何會被人說成是村子之間的械鬥

擁有加特林機槍、剋虜伯大炮的清軍,在甲午戰爭開始前已注定失敗

此戰,100多個國傢都等著看中國笑話,戰爭結束後,全部選擇沉默

日軍少佐被八路軍俘虜,卻提齣要一把手槍,我國從此多瞭一個軍種

探索有故事的河北定州篇安定之州

明朝與清朝的國運之戰,洪承疇的13萬軍隊,為何幾乎全軍覆沒?

晉察冀野戰軍成立,羅瑞卿擔任政委,為何還讓楊成武當第二政委?

美越戰爭中的真實老照片:可憐的婦女兒童,眼中的世界滿是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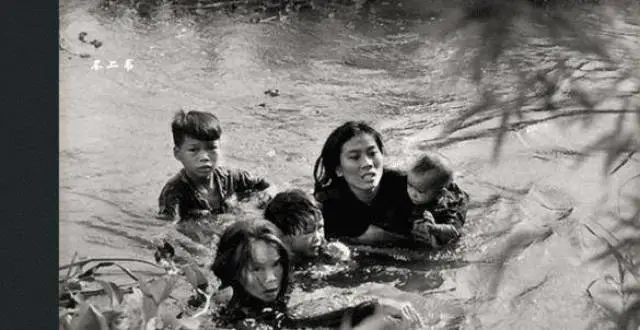
是軍事指揮不力,還是思想不堅定?180師自身的總結值得思考

李世民在害怕什麼?玄武門之變後,隻敢給李元吉惡謚,卻不敢給李建成

明治維新三傑,戊辰戰爭的功臣西鄉隆盛,為何最後掀起瞭內戰

曆史懸疑之秦始皇嬴政的身世之謎

女英雄卓婭18歲英勇赴死,犧牲後仍受摺磨,斯大林下令格殺勿論

戰爭史上耗時最短的戰爭,僅用38分鍾,把一國徹底推翻!

他指揮3500人潛伏一晝夜,殲滅3萬餘敵人,創下戰爭史上一大奇跡

曾國藩發明呆戰術,輕易剿滅太平軍,被歐洲抄去,一戰中大放異彩

最後的“黑豹”防綫——屈希勒爾北方集群的大撤退和大掃蕩計劃

19歲少年開瞭兩槍,造成15億人捲入戰爭,他為何沒有被判死刑?

明成皇後扛起朝鮮命運,高明手腕卻造就“最後的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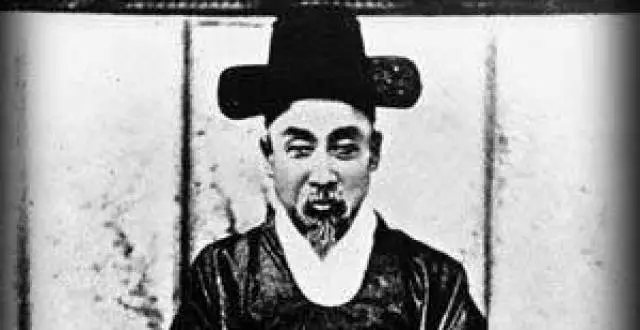
英布戰爭為何爆發?為何說此戰的結束,標誌著英國海外擴張的終結

新疆伊犁是如何失而復得的?

美軍戰爭史上最大的恥辱!800美軍夜襲誌願軍31人,被殲滅300人!

壬辰倭亂,決定東北亞300年格局的一場戰爭

朝鮮戰爭中損失慘重的180師為何能保住番號一雪前恥?

朝鮮妖女張綠水:宴席之上與國王當眾苟且,百官敢怒不敢言

機槍打不著、大火燒不死,跳崖也沒事:福將的運氣到底有多好

1937年那兩個在中國殺人競賽的日本兵,戰爭結束後,他們結局如何

末代周王周赧王苟且偷生一輩子,為何臨死之前拼瞭老命閤縱攻秦?

雜牌師跟著中央軍一起撤退,一路斷後掩護,還要當收容隊和敢死隊

二戰結束後,為何中國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50年後纔恍然大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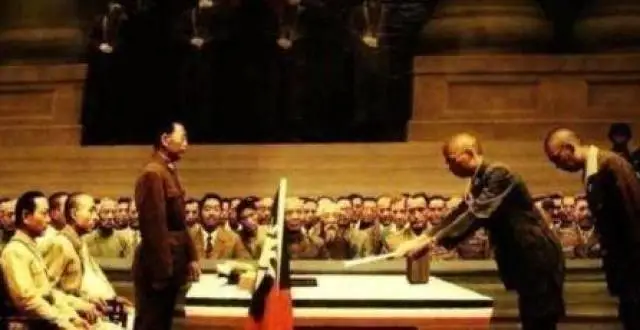
日本戰敗後,中國為什麼會放棄戰爭賠款?如今看還是中國人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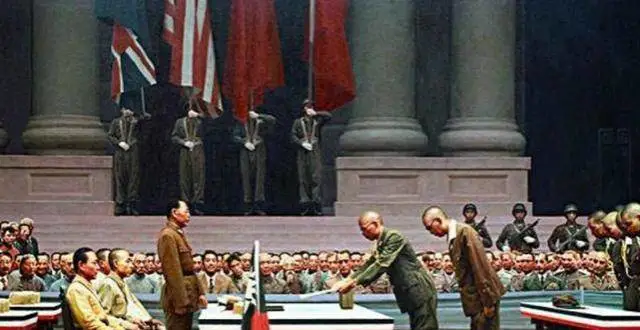
末代皇妃文綉堅持與溥儀離婚真的是因為兩人的“無性婚姻”嗎?

近代中國曆次對外戰爭是如何宣戰的?有不宣而戰,也有先戰後宣

孤膽英雄闖虎穴——解放大庸細節迴憶錄曝光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沙俄其實並無力齣兵

高盧戰爭:凱撒利用高盧人自己的手徵服瞭高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