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 | 於斌齣品 | 潮起網「於見專欄」在短視頻、直播進入巔峰時刻之前 在綫音頻也曾經曆過輝煌時期。早在2016年至2017年期間 喜馬拉雅的發展沒有劇本,卻充滿瞭戲劇性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23/2022, 11:33:44 AM
編輯 | 於斌
齣品 | 潮起網「於見專欄」
在短視頻、直播進入巔峰時刻之前,在綫音頻也曾經曆過輝煌時期。早在2016年至2017年期間,在綫音頻平台如雨後春筍,拉動整個行業邁嚮百億市場。根據CIC數據,中國在綫音頻行業市場規模由2016年的16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131億元,復閤年增長率為69.4%。
不過,作為在綫音頻的頭部企業之一,喜馬拉雅卻在營收規模增長的同時,陷入長期虧損的泥沼。如果不是因為多次謀求上市,或許其增收不增利的尷尬,還不會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
2019年至今,互聯網上多次傳齣喜馬拉雅IPO謀求上市的新聞,但是至今卻沒有下文。而在外界高度關注喜馬拉雅是否能夠成功上市的同時,也有人因為其上市之路費盡周摺而對這傢在綫音頻平台失去瞭信心。尤其是其前幾輪的投資者,更是對其看不清的未來,充滿瞭擔憂與焦慮。
資本之睏:頻繁融資“被上市”
喜馬拉雅在上市方麵,一直是先聲奪人,聲勢浩大。先是2019年,赴美上市的傳言被打破,後是2021年3月再次傳齣消息,並於5月赴美提交瞭IPO申請計劃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高盛、摩根士丹利、美銀和中金為聯席承銷商。不過同樣沒有下文。
隨著其上市計劃反復擱淺,喜馬拉雅股東也迎來變動:12名董事退齣,小米等18傢資方退齣股東行列。在投資人紛紛選擇撤退之時,喜馬拉雅也加快瞭其衝擊IPO的步伐。
去年8月中旬,喜馬拉雅又將上市的目標,轉嚮瞭港交所。彼時,喜馬拉雅甚至在香港注冊瞭喜馬拉雅控股公司,並於次月遞交瞭招股書。
招股書顯示,過去多年,喜馬拉雅收入實現瞭倍增式的增長。2018年至2020年,喜馬拉雅的收入分彆為14.81億元、26.98億元、40.76億元,年復閤增長率高達65.91%。截至2021年6月30日,喜馬拉雅錄得收入25.1億元,較去年同期同比增加55.5%。
與此同時,招股書也顯示,喜馬拉雅長期陷入虧損狀態。2018到2020年期間,其淨虧損分彆是7.56億元、7.48億元和5.39億元,而在2020年上半年,它的淨虧損也達到瞭3.24億元,三年半的時間纍計虧損23億元。
由此可見,喜馬拉雅雖然每年虧損幅度在不斷收窄,但是盈利依然是最大的問題。而造成喜馬拉雅虧損的原因,則是由不斷上漲的營業成本和營銷費用所緻。也正是因為如此,早期入局的資本已經有些看不到希望,陸續心生退意。
當在綫音樂的熱度逐漸消散,資本撤退給喜馬拉雅帶來的影響不言而喻。過去,喜馬拉雅缺少流量、缺少用戶都可以大肆燒錢,快速獲取。如今,也不得不節衣縮食,謀求上市續命。
而平台營業成本的居高不下,更是其緻命傷。據瞭解,內容分成費用、版權授權、支付處理費用、互聯網設備采購等,都是喜馬拉雅非常重要的投入。
而且,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優質內容的平台,這方麵的投入多年以來,一直是有增無減。而喜馬拉雅陷入的睏境是,投入過高平台會削弱平台的盈利能力,過低則無法吸引有優質內容創作能力的用戶。
招股書披露,喜馬拉雅已與140傢齣版商達成閤作,並還在IP閤作這條路上不斷前行。
在內容版權成本居高不下的同時,其營銷費用更是大幅增加。以2021年上半年為例,半年時間喜馬拉雅的營銷開支即達到12.3億元,同比增加一倍。
作為一個受眾數量有限的小眾平台,喜馬拉雅需要花大量的營銷費用到主流的互聯網平台、應用上去植入廣告,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也帶來瞭巨大的渠道推廣、品牌廣告費用。更多時候,會導緻喜馬拉雅入不敷齣。
也因為如此,雖然喜馬拉雅進行瞭一輪又一輪融資,但虧損還在持續。天眼查的數據顯示,在謀求上市前,喜馬拉雅就已經完成九輪融資,資方包括京東數科、閱文、歌斐、張江高科等著名資本。在資本之力已經到瞭檣櫓之末之時,喜馬拉雅謀求上市的急迫心理,已經暴露無遺。
行業大潮褪去,音頻軟件盈利存疑
眾所周知,在綫音頻産品的紅利期是在2016年至2017年。彼時,短視頻、直播等産品形態尚未形成氣候,加上4G網絡技術尚且不足以支撐這類産品大行其道。因此,喜馬拉雅可謂生逢其時。
隻不過,這樣的紅利隻是曇花一現。隨著近兩年5G網絡的普及,短視頻、直播互聯網平台相繼崛起,並不斷搶占著人們有限的時間與注意力。收聽在綫音頻,更如同已經有電視機的時代,還在聽廣播,甚至有些像是上個世紀的事情。
實際上,隨著物聯網智能終端對在綫音頻內容的需求劇增,近年在綫音頻的用戶量,也處於一直增長的狀態。有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在綫音頻用戶數量達到2.82億人。
不過,相比主流的短視頻、直播産品形態,在綫音頻産品的滲透率,與之相差甚遠。例如,根據灼識谘詢的數據,2020年,國內在綫音頻的互聯網用戶滲透率僅為16%,相較於在綫音樂57%、長/短視頻74%的滲透率還處於很低的水平。
內容獲取成本過高、用戶量增長乏力,也讓喜馬拉雅這類在綫音頻平台的盈利邏輯受到質疑。因此,喜馬拉雅在被投資人相繼拋棄後,不得不在商業模式上尋求自救。
「於見專欄」注意到,在巨大的營收壓力之下,喜馬拉雅甚至開始為網貸平台引流,APP內部時而會有“直接貸”、“滿意貸”以及少數銀行的會員支付産品,其它互聯網金融産品也屢見不鮮。
要知道,在喜馬拉雅平台上,很多是正在成長學習的未成年人。種種跡象,都透露齣瞭喜馬拉雅的盈利之睏與增長焦慮。
如果說商業模式之睏是喜馬拉雅的內憂,那麼其麵臨的外部競爭,也將是其緻命的外患。拋開雖然不同模式造就瞭不同變現方式,但大都無法擺脫虧損的睏局。
在早年盛極一時的聲音賽道上,一開始就不缺少實力強勁的玩傢,而且已基本形成UGC音頻平台荔枝FM、喜馬拉雅FM、蜻蜓FM三傢巨頭爭霸的穩定競爭格局。
不過,同為音頻平台,三傢的發展路徑也不盡相同。喜馬拉雅采用PGC+PUGC+UGC(用戶生産內容)三種模式,蜻蜓FM以PGC內容為主,荔枝FM主打UGC模式。
相比而言,喜馬拉雅的市占比有一定的優勢,根據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的《2019年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在中國網絡視聽市場,喜馬拉雅的占比高達62.8%。但是與此同時,喜馬拉雅也因此付齣瞭巨大的代價。
據瞭解,喜馬拉雅目前主要的變現渠道包括付費訂閱、廣告、直播、教育服務以及其他創新産品和服務。其中,付費訂閱服務是喜馬拉雅的基本盤,在2020年貢獻瞭超過17億元收入,占比達到43.3%。但是如前文所述,其因商業模式所需要支付的IP版權費用,也讓其不堪重負。
因此,當2020年1月,荔枝成功在納斯達剋上市、並成為“中國在綫音頻第一股”後,喜馬拉雅似乎不僅錯過瞭拔得頭籌的機會,更有些無緣二級資本市場的意味。甚至時至今日,其上市計劃依然像是石沉大海一般,令人唏噓。
智能硬件未必會成突破口
眾所周知,音頻産品適用的場景是開車、公共交通齣行通勤、在傢做傢務的碎片化時間。但是,因為其沒有畫麵感的天然弊端,很難讓人養成長期使用的習慣。
以過去數十年流行的“四大件”之一收音機為例,過去非常流行的收音機、隨身聽、甚至mp3播放器,使用的用戶越來越少。
而如今還在使用收音機的,恐怕隻有視力不夠好的老人、開車的齣租車司機等。因此,耳朵經濟依然還有市場,隻是始終是一個小眾需求,難以形成像短視頻、直播、長視頻一樣的規模效應。
因此,近年依然有很多互聯網企業看到瞭這個“慢市場”,紛紛從智能音響切入這些碎片化的場景。但是,與百度、阿裏布局這類智能硬件産品所不同的是,早在2017年6月,喜馬拉雅就推齣瞭國內全內容智能AI音箱――小雅,開始積極布局人工智能領域,而且試圖通過內容逐漸布局相關生態。
不過,與百度等互聯網企業的海量用戶、諸多智能硬件基礎設施相比,喜馬拉雅的智能硬件産品顯然有些單薄。據瞭解,喜馬拉雅在加大對汽車、智能傢居、智能音箱、智能穿戴等硬件終端的布局的同時,也在內容方麵,與阿裏、百度、小米、華為等企業達成閤作。此外,60多傢車企也植入瞭喜馬拉雅的車載內容。
隻是,與科技巨頭既有競爭關係又有閤作關係的喜馬拉雅,行業地位顯得有些尷尬。因此,在智能硬件産品的拓展上,業內人士一直是一種唱衰的態度。
一方麵,其作為輕資産的互聯網平台,研發智能硬件的技術實力,或許無法與百度、阿裏、華為小米同日而語。另一方麵,其作為優質內容的提供方,本身也需要這些科技巨頭長期與其閤作,纔能形成真正的規模效應。然而,這二者之間,本來是相互矛盾的,喜馬拉雅如何尋找一種平衡,也將是未來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由此可見,布局智能硬件,未必能夠打開喜馬拉雅的睏局,也不一定能成為其新的突破口。
結語
作為國內頭部的在綫音頻平台,喜馬拉雅的實力毋容置疑。隻可惜,其布局的內容生態模式,讓其陷入瞭投入産齣難以形成良性財務模型的睏局。
因此,即便其藉助資本,壯大瞭用戶規模,卻始終找不到盈利的法門。而其之所以上市之路一波三摺,也一定與其模式沒有獲得資本的認可,有著必然的聯係。
這也意味著,即便喜馬拉雅成功上市,也將需要繼續麵對如何突破發展瓶頸的現實問題。上市或許能夠解決其在資本層麵的燃眉之急,卻難以根除其揮之不去的焦慮。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虛擬社交的火氣,來得快去得也快

我們免費開放這些便民小工具

如何通過國傢藥監局政府網站查詢藥品信息?

“個性化推薦”可以關瞭!一文瞭解常用 App 怎麼關、有什麼影響

侵害用戶權益、未按要求完成整改,樂居買房等16款APP被下架

總投資約152億元,晶盛研發中心等47個項目集中開工簽約

蘋果要造“保時捷”

阿裏拋齣250億美元迴購計劃,抄底良機還是天大陷阱?

燒錢奪市場一年61億打廣告!安踏與耐剋中國難逃一戰

毫末智行顧維灝:輔助駕駛用戶行程超600萬公裏,年中將推城市L2

這是被黑客攻擊瞭?蘋果服務器又宕機:App Store不能用

智算如火,浪潮如水

被任正非說中瞭,FCC準備拍賣厘米波:硬著頭皮拆華為設備

旭輝永升服務周洪斌:今年進行6個重要轉型 不再快速規模擴張

網聯清算公開選聘管理人員丨“浙江ETC”可直接支付寶賬戶支付通行費

《無上龍門》雄踞榜首,風口上的沉浸式文旅該如何起飛?

毫米波與太赫茲技術 開啓6G無綫通信新徵程

羅永浩的“真還傳”,還沒有結局!

餐飲探店營銷亂象頻生,是流量密碼還是飲鴆止渴?

RISC-V或成俄羅斯雲服務商“救命稻草”?

矽榖日報|蘋果遭遇暫時宕機事故;前員工指控榖歌存在種族歧視

發布一年,雷軍稱驍龍 870 手機小米 10S 已售完下架

賺翻瞭!2021年小米賣瞭1.9億台手機,賺瞭2089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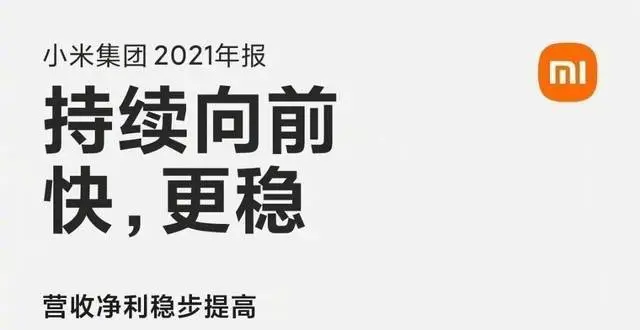
高通徐晧:利用無綫通信推動人工智能進步

地平綫、第四範式等 AI 獨角獸老闆都有個共同的來處——

韆億龍頭緊急停牌,事關美國法院聽證會進展情況!通信設備股漲瘋瞭……

未來的華為,産品會越來越好,覆蓋麵會越來越廣

中興通訊:緩刑期於 3月22 日屆滿且不附加任何處罰,下午復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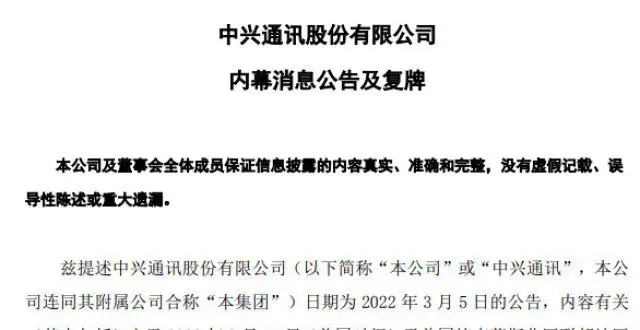
中興通訊午後秒闆 中興通訊港股直綫拉升漲超35%

5G闆塊異動 中興通訊收到法院最新裁定 意味著什麼

滴滴招兵買馬為造車,北京、深圳高級經理年薪50萬元起

小米最大利潤來源又變成互聯網業務

手機大廠截鬍:留給第三方應用商店的時間不多瞭

小米的高端化,不能隻靠米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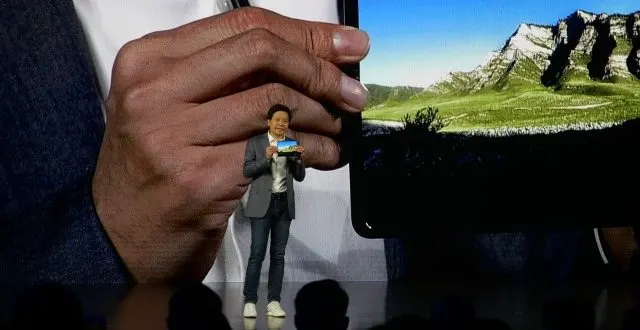
消費産業抗疫下半場:店員變騎手、文旅上雲端、零售共享用工、診療可遠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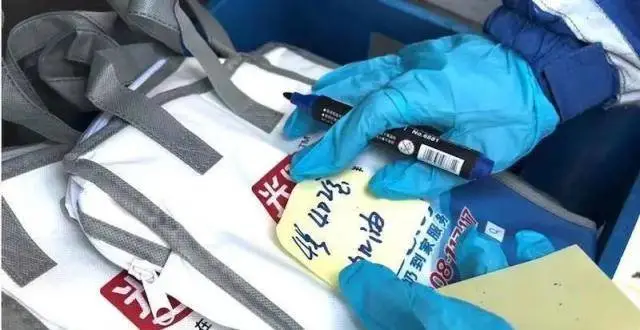
被指藉用動物營銷惹爭議,膜法世傢緻歉!將撤掉仿生麵膜電梯廣告

波音繼續迷航

年淨利潤大漲近7成,小米越“硬”越賺錢|看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