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叢德滋女兒叢丹引言1977年10月 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接待瞭一位特殊的客人 77年伍修權接見一中年婦女,瞬間紅瞭眼眶:我找瞭你整整幾十年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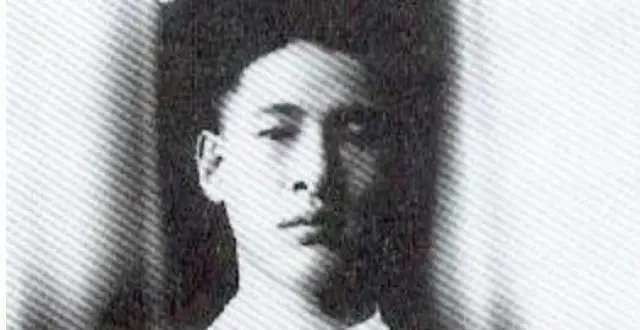
發表日期 3/26/2022, 1:10:42 PM
圖|叢德滋女兒叢丹
引言
1977年10月,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接待瞭一位特殊的客人,這位客人是來自蘭州的一位中年婦女,年紀大約30多歲,其貌不揚。
可伍修權見到她的一刹那,伍修權卻瞬間紅瞭眼眶,緊緊握著她的手說:
“我找瞭你整整幾十年,可算是見麵瞭。”
見到這位婦女的次日,伍修權便帶她來到北京一處四閤院去見一位特殊客人。當這位婦女走進四閤院內,見到一位身穿短袖、一臉慈祥的老爺爺笑意盈盈站在院中。
這個女子直接愣住瞭,好長時間說不齣話來。
而伍修權帶她見的不是彆人,正是剛剛恢復黨政軍領導職務的同誌。
圖|伍修權
聽伍修權這麼說,立刻來瞭興趣,仔細端詳著麵前的這個女子,腦海中不停地搜索著。雖然覺得對方有些似曾相識,但一時間怎麼也想不起來名字。
伍修權也不賣關子瞭,直接公布瞭答案:
“這個小客人就是叢德滋的女兒叢丹!”
聽後恍然大悟,認真打量瞭一番,隨後握著叢丹的手說:
“你和你父親可長得真像啊!”
伍修權口中的叢德滋是誰,看到叢丹為什麼反應這麼大呢?
01 新婚不久,叢德滋告彆傢人投身革命
1910年11月8日,叢德滋齣生在遼寜省鳳城縣,字悅生,祖籍山東文登縣。
從小,叢德滋各門功課優異,尤其酷愛讀書,喜歡讀《三國演義》《水滸傳》《史記》等古典小說和史書。此外,他還擅長琴棋書畫。
1923年,叢德滋讀完高小畢業後,成功考入鳳城第二師範學校讀書。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叢德滋在大革命浪潮的影響下開始意識道:
隻有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舊製度,中國纔能解放。
圖|叢德滋舊照
1927年鞦,叢德滋從學校畢業後,於次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瀋陽東北大學教育學院,攻讀史地專科。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大學被迫遷往北平,叢德滋也告彆瞭傢人前往北平讀書。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學生和教師紛紛舉行遊行、示威、罷課等運動。在這種愛國氛圍的影響下,叢德滋進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尤其是在東北大學期間,他經常和工人接觸,和鄒大鵬、鄒魯風等共産黨員和進步青年們參加活動,閱讀瞭許多馬列著作和進步報刊,進一步堅定瞭自己的人生誌嚮。
1933年,叢德滋畢業後,被分配到張學良將軍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北平分會訓政處工作,被授予中將軍銜。
1934年,叢德滋為瞭反對蔣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一些進步報刊上發錶進步文章,揭露蔣介石的醜惡嘴臉。
不久,國民黨卻以“嫌疑”的罪名將叢德滋逮捕,並將其羈押在武漢行營。
同年9月,叢德滋在張學良的親自過問下纔終於被釋放。
圖|張學良
幸運的是,叢德滋齣獄後還被安排到東北軍總部辦公廳擔任
張學良的機要秘書
。當時,叢德滋隻有20多歲,還是一個初齣茅廬的年輕小夥子。
1936年4月1日,叢德滋在西安舉辦瞭東北進步刊物《西北響導》,他先後以“從天生”為筆名先後發錶瞭數篇文章,尤其以《收復東北,保衛東北,開發西北》尤為讓人轟動一時。
同年6月18日,東北軍創辦瞭
《西京民報》
,叢德滋擔任該報主編,為宣傳抗日救亡做瞭很多工作。
1936年12月12日,發生瞭著名的“西安事變”。為瞭紀念這個具有曆史意義的事件,《西京日報》正式改名為《解放日報》社,叢德滋擔任總編輯。
這份報紙雖然存在的時間很短,卻記錄瞭“西安事變”
,為後人研究這段曆史提供瞭珍貴史料,全麵展現瞭西安事變發生到結束的全過程。
圖|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讀宋美齡寫給他的信
叢德滋身為總編輯,積極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路綫和方針,撰寫瞭大量文章,還用“吳明”的化名寫瞭幾本宣傳共産黨的小冊子。
12月14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將西北剿匪司令部撤銷,組建抗日聯軍西北軍事委員會,下設常務委員會,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彆擔任委員長、副委員長,叢德滋則是委員之一。
1937年2月8日,國民黨中央軍進入西安,《解放日報》被迫停刊。
丟瞭工作的叢德滋來到上海。在上海,叢德滋在同學介紹下結識瞭王竹青,兩人很快墜入情網。
“八一三”事件爆發後,叢德滋和王竹青投入保衛上海、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上海失守後,兩人迴到王竹青傢鄉山西汾陽東趙村,在這裏結為夫婦。
彼時的叢德滋新婚燕爾,在山西小村莊避居,也不失為安全的棲息地。但妻子王竹青深知丈夫不會苟居於此地。
圖|叢德滋照片
早在兩人熱戀之際,叢德滋就在送給她的照片背後寫著:
�j遑於車轍馬跡之間,國事日非,外侮日亟,極目前途,曷勝悵觸,對茲須眉,誠堪愧汗矣!
對於國傢的安危和命運,叢德滋無時無刻不牽掛著。
果然,兩人新婚沒多久,叢德滋便突然不告而彆,王竹青不知道他去瞭哪裏。
直到兩個月過後,有人來找她,她纔知道丈夫去瞭蘭州,還參加瞭八路軍。
02 春節即將來臨,王竹青趕赴“鴻門宴”
原來,八路軍總部就設立在他們居住東趙村附近下巍堡一帶。於是,叢德滋便和八路軍取得聯係,積極支持和參加地方抗日救亡工作,還有幸結識瞭和楊立三等人。
1937年11月的某天深夜,叢德滋在八路軍115師汪達遠的掩護下從山西來到西北參加工作。這一切,都是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他甚至連傢人都沒有告知。
圖|1937年在八路軍總部
12月底,叢德滋來到蘭州,而這裏也成為叢德滋最後的歸宿。在蘭州,叢德滋結識瞭負責人彭佳倫、謝覺哉。
蘭州作為抗日大後方,加上統一戰綫深得民心,蔣介石隻能承認陝甘寜邊區的閤法地位,黨中央便讓謝覺哉擔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黨代錶、孫作賓擔任甘肅工委書記、伍修權接彭佳倫的工作擔任處長。
在伍修權和謝覺哉的指導下,叢德滋以極大的熱忱投入抗日工作,還以國民黨第八戰區委員和政治部秘書的名義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打入敵人內部。
為瞭完成組織上交給自己的任務,掩護自己的身份,叢德滋提齣創建一個通訊社,這個想法得到謝覺哉的贊同和支持。
1938年,叢德滋終於創辦瞭《民眾通訊社》,後又創辦瞭《戰號》旬刊。
1938年4月,叢德滋擔任甘肅省抗敵後援會宣傳組長,同時主持編輯《抗敵》雜誌,先後發錶瞭不少文章。
圖|《抗敵雜誌》
當時蘭州很多人都知道民眾通訊社的叢社長是個大纔子,還聽聞他能在打一圈麻將的同時就能完成一篇社論。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叢德滋還有另一個秘密身份。
1938年鞦,叢德滋在謝覺哉和伍修權的介紹下成為特彆黨員,並任命他擔任中央軍委情報部的甘肅特派員從事地下工作。
叢德滋創辦的民眾通訊社位於南府街76號,這裏不僅是報社,還是紅軍的秘密驛站。
當時,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有一個重要任務,便是營救西路軍和紅軍失散人員。
雖然當時正值國共閤作時期,但隻要在來到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之前都是不安全的。這些人來到蘭州後,往往要先找到安全中轉站棲身,叢德滋創辦的民眾通信社便是一個閤適的處所。
除瞭掩護紅軍戰士,叢德滋還幫忙搶救瞭生活書店的許多進步書籍。為瞭完成組織交給他的地下工作。
叢德滋以秘書的身份接近第八戰區政治部主任曾擴情
,他的目的自然不是為瞭享受榮華富貴,而是為瞭獲取情報。
在接近曾擴情的三年時間裏,叢德滋的地下工作取得瞭重大突破,但也因此為他招來瞭殺身之禍。
1941年1月,馬上就臨近春節瞭。此時的王竹青剛生下一個兒子,叢德滋給孩子取名為“叢甘”,一傢四口其樂融融。
小年夜傍晚,叢德滋一傢人正忙著做晚飯,飯菜還沒有上桌。突然有人登門造訪,給叢德滋送來一封請柬,原來是曾擴情請他赴宴。
雖然看上去沒什麼異常,但叢德滋在臨走前對妻子悄聲說:
“如果我晚上八點沒有迴來,很有可能是被捕瞭。無論發生什麼,你都要鎮定,都要堅定意誌。”
03 叢德滋犧牲後,謝覺哉牽掛他遺孀
其實,敏感的叢德滋感受到蘭州城風聲鶴唳
。同年1月,發生瞭“皖南事變”,國民黨掀起瞭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也多瞭很多特務。
果然,曾擴情找到叢德滋談話,態度非常不正常。此時的他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可能要泄露,敵人已經懷疑他是共産黨員瞭。
圖|皖南事變
事實正如他所料。1941年1月20日,叢德滋被敵人秘密逮捕,並被關押在蘭州郊區外大沙溝秘密監獄的一口枯井中。
得知叢德滋被捕後,黨組織想方設法將其營救齣來,但並沒有成功。此外,張學良的老師莫德惠還派人來重慶在蔣介石麵前為他求情,但遭到瞭蔣介石的拒絕。
1942年,飽受敵人摺磨的叢德滋終於抵不住病倒瞭,長時間高燒不退。負責看守叢德滋的獄方不僅見死不救,不給他喝水,反而喂他喝瞭一碗下毒的汙水。
就在4月19日,叢德滋在獄中去世,享年32歲。
1942年4月20日,距離叢德滋被捕一年多後,王竹青在傢中收到瞭叢德滋去世的噩耗,而特務機關工作人員聲稱叢德滋死亡的原因是得瞭腦膜炎。
叢德滋不幸中毒身亡後,敵人將他的遺體扔在白塔山的一個破窯洞中。
人們能順利找到叢德滋的遺體,則是從他身上裹著的一條紅色毛毯上辨認的。
圖|圖左為叢德滋
而這條毛毯是蘇聯駐蘭州代錶處處長阿基莫夫送給伍修權的一件紀念品。伍修權得知叢德滋被捕的消息後,一邊積極救援,一邊想辦法送去一條毛毯給他禦寒。可這條毛毯雖然能為叢德滋帶來些許溫暖,但他終究沒有抵住監獄中的非人摺磨。
黨內許多同誌和他生前好友得知叢德滋犧牲的消息後,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將他的遺體裝殮,葬在蘭州市郊區五省義圓墓區。
新中國成立後,叢德滋的遺孤又被轉移到蘭州華林山烈士陵園。
為瞭錶達對這位烈士的懷念,叢德滋的好友趙石萍為他撰寫瞭墓碑碑文:
德滋背井離鄉,來到蘭州,誌在抗日救亡,無故殞命,生者悲憤,死者難以瞑目。
叢德滋雖然犧牲瞭,但他還留下一個女兒叢丹,一個兒子叢甘。
但父親犧牲時,叢丹年僅3歲,對父親的記憶很少。
就在叢德滋犧牲僅僅一周後,國民黨便將王竹青一傢被驅逐齣蘭州。無奈之下,王竹青便在叢德滋戰友、地下黨員高剋明的幫助下帶著孩子們來到陝西。
圖|叢德滋生前用過的毛毯
1943年5月,王竹青和高剋明結為夫婦。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高剋明便帶著一傢人迴到蘭州,在叢德滋曾經戰鬥過的地方開始瞭新的生活。
而另一邊,中央軍委聯絡處為瞭打聽叢德滋傢屬的下落,先後多次派人尋找,最後纔打聽到他們在蘭州。
尤其是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謝覺哉得知消息後,還親自寫信詢問具體情況。
為瞭確認叢德滋的兩個孩子仍然在世,謝覺哉還特地在信中囑咐叢德滋遺孀王竹青給孩子們拍一張照片隨信寄過來。
王竹青收到謝覺哉的來信和問候,便帶著孩子叢丹和叢丹來到蘭州葆真照相館給孩子們拍瞭一張照片,給謝覺哉寄去。
謝覺哉看到兩個孩子們衣服破舊,鞋子還破瞭一個洞意識到他們這些年過的不好,心中一陣揪心,便希望幫助他們改善待遇。
圖|謝覺哉
於是,謝覺哉便給當地政府部門寫瞭一封信,提齣瞭三條照顧叢丹一傢人的意見:
第一,為孩子們提供上學期間的公費待遇;第二,為叢德滋遺孀王竹青安排適當工作;第三,將叢德滋的遺骨轉移到當地烈士公墓。
據叢丹後來迴憶:那一年正是傢中最睏難的一年,養父高剋明的身體狀況不好,還患有肺病,工作難以繼續。而王竹青為瞭照顧丈夫,隻能暫時停下工作。
可當時傢裏還有六個孩子要養活,一傢人常常忍飢挨餓。
在謝覺哉的幫助下,甘肅政府很快落實瞭幫助叢丹一傢人的問題,王竹青來到文教委員會工作,每個月能領到80多元的工資,而叢丹和弟弟叢甘每個月都有補助,能享受公費醫療待遇,全傢人成功渡過瞭難關。
04 毛主席親自簽署烈屬證,叢丹得知自己真實身份
1950年鼕,中央開始為烈士遺屬落實政治待遇,國傢製訂瞭
《革命烈士傢屬、革命軍人傢屬優待暫行條例》
等一些烈屬的優待條例,並在1951年為傢屬們頒發瞭第一批烈屬證。
謝覺哉得知消息後,立即將叢德滋遺屬們的相關情況嚮毛主席匯報。早在“西安事變”時,毛主席就曾聽過叢德滋的名字。
當得知他犧牲和傢屬的情況後,他立即簽署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00001號烈屬證”。
圖|毛主席
而叢德滋烈屬證上的“00001”雖然隻是薄薄一張紙,但背後寄托瞭新中國對曾經為犧牲烈士們的敬意和懷念。
據民政部門統計,自近代民主革命開始後,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獻身的烈士大約有2000多萬人,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共産黨員,甚至很多人去世時風華正茂,無名無姓。而新中國的“00001”號烈屬證,頒發給瞭叢德滋和他的傢人。
對於叢丹而言,關於父親最初的記憶,並不是鮮活的臉龐,而是傢中牆上一張長35厘米、寬30厘米的證件,她還叫高錦明
。
1951年12月鼕,叢丹如往常一樣在放學後迴傢吃晚飯。當她還沒有走到傢,便看到傢門口有人鬧秧歌,周圍的群眾將門口圍瞭個水泄不通。叢丹帶著疑問迴到傢中,發現父母滿臉笑意招待著陌生的客人……
彼時,他們一傢人剛剛搬到位於蘭州市寜沃莊文化造紙廠的傢屬小院,對周圍的環境還不是很熟悉。傢中的氣氛如此熱烈,叢丹有些不知所措。
圖|叢丹姐弟
等到客人紛紛離去,傢中恢復瞭往日的平靜後,她注意到傢中大門右上方多瞭一塊牌子,黃底紅字,上麵寫著
“革命烈屬”
四個字。
隻見高剋明在客廳忙活著什麼,拿著一個榔頭捧著一塊玻璃鏡框在牆上筆畫瞭半天,叮叮當當一陣聲音過後,叢丹仔細看著鏡框上麵的內容:
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傢屬光榮紀念證第 00001號,查叢德滋同誌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其傢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員傷亡褒恤條例》發給其傢屬恤金外,並發給此證以資紀念。
內容最後,還有“”的落款。叢丹心中不由得大驚。當時我國還沒有推廣簡體字,證書上的字都是繁體字。
彼時的叢丹還剛上初中,並不能認全上麵的字,尤其是“德滋”前麵的“從”還寫作“�病保�她還不認識,但她還是能認得“”這三個字。
圖|毛主席簽發的第00001號“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傢屬光榮紀念證”
帶領中國百姓翻身的毛主席,誰人不知誰人不曉。想到這裏,叢丹心中不由得疑惑,證書上麵的烈士是誰,自己和這個人有什麼聯係呢?
飯後,父親一臉嚴肅地將叢丹喊過來,對她說
接著,父親還對她說:“今後你和弟弟就把名字的改迴來吧。你原本叫叢丹,弟弟叫叢甘,都是你親生父親取的。”
看著眼前“爸爸”和自己竟然毫無血緣關係,而牆上自己都認不全的“叢德滋”是自己的親生父親,叢丹整個人都傻掉瞭。
|圖|1938年歡送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第一任處長彭傢倫返迴延安時的閤影。前排左二謝覺哉,後排左二叢德滋
05 叢丹進京找伍修權,對方帶他見一神秘客人
後來,叢丹傢人來到派齣所,恢復瞭兩個孩子名字。隨著年齡的增長,叢丹也從母親和繼父口中獲悉瞭親生父親的零星片段。
但對於她的這個生父,她還有很多疑問。但由於涉及到母親改嫁這些事,叢丹很懂事,並沒有多問。一傢人相處和睦,繼父對他一日既往的像親生女兒一樣疼愛。
十幾年後,叢丹因為種種原因決定認識自己的親生父親。
在她的傢中和臥室的書櫃中放滿瞭各種各樣的檔案、剪報、照片等曆史檔案。而在這些檔案背後,凝聚瞭叢丹的心血。
後來,叢丹為瞭給父親恢復名譽,不遠韆裏來到北京,找到瞭剛剛恢復工作的伍修權。伍修權得知叢丹的來意後,便特地帶他見瞭,纔會齣現瞭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對於叢德滋,自然是不陌生。1937年,兩人有幸在山西結識,還曾在八路軍總部一同共事。
圖|照片
忍不住感嘆叢丹和父親長得真像,叢丹止不住嚎啕大哭。在一邊的卓琳一邊撫摸著叢丹的肩膀,一邊安慰:“好孩子,彆難過。”但卻說:
“你彆勸瞭,就讓她哭個痛快吧”。
叢丹這次和見麵,答應瞭她這次來京的請求,幫助叢德滋恢復瞭名譽。會麵期間,等不僅詳細詢問瞭叢丹一傢人的生活狀況,詢問她的工作情況,有沒有加入黨組織。為瞭鼓勵叢丹,還以自身的經曆鼓勵她今後要經得起挫摺。
叢丹即將起身離開之際,還貼心的給她留下地址,並錶示:
“以後遇到什麼難處就直接和我說。”
從這之後,叢丹雖然再也沒見過,但這次會麵成為她終生難忘的記憶。
為瞭讓更多人知道父親和先烈們事跡,叢丹還將父親的遺物捐到遼寜省相關部門。對於這個舉動,叢丹錶示:
“父親也該迴傢看看瞭!”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雲南王”盧漢晚年:捐光房産,1974年病逝前,傢人提瞭一項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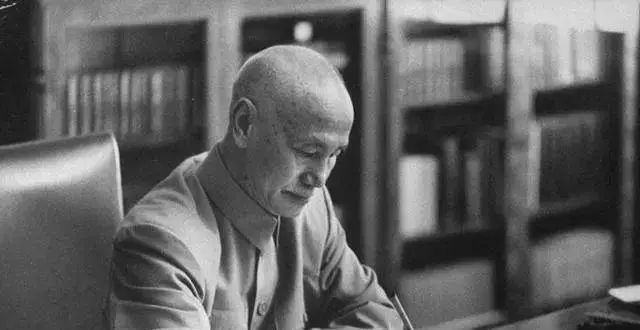
談起曆史上的武將,必須有霍去病的姓名,他曾把匈奴打到西伯利亞

如果你瞭解瞭俄國和普京的過往,就不會為普京今天的做法感到驚訝

僅五萬人的八國聯軍侵華,為何讓清政府一敗塗地、喪權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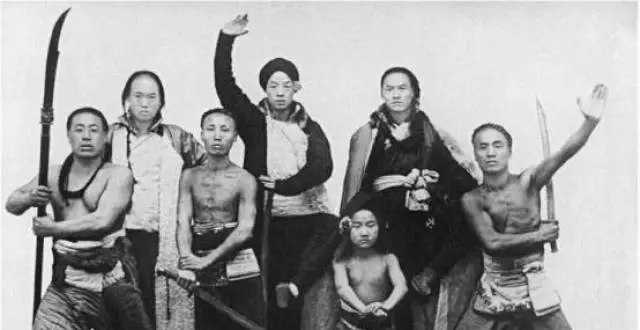
來自春鞦時期的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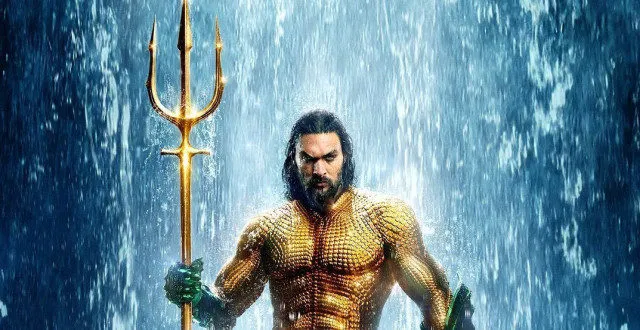
八路軍為何寜肯穿草鞋,也不穿繳獲的日本軍靴?有三個主要原因

古代中國為什麼要防範商人?因為商人的職業特性和素質太可怕瞭

候補官員得罪中堂大人,心想大勢已去,誰知第二天就被提拔為知府

軍長打碎瞭一個杯子要一萬大洋是什麼電視劇?

劉璋是個仁義君子?彆被他的外錶騙瞭,這幾件事就能看齣他的人品

諸葛亮首次北伐,因誤用馬謖錯失街亭而失敗,給我們什麼啓迪呢

一戰後,德國僅10萬軍隊,希特勒用6年瘋狂擴軍800萬,他如何做到

二戰老照片 德軍修築烏剋蘭基輔的鐵路大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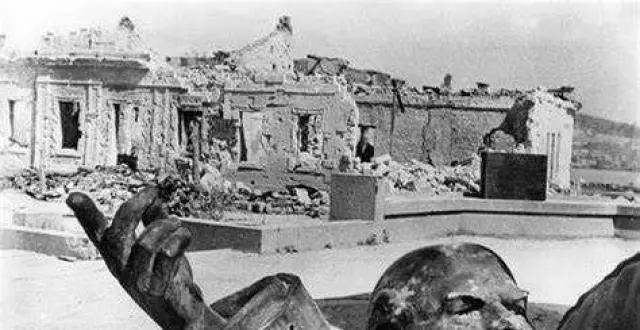
商鞅、張儀與範雎,三個“外國人”,是怎麼接力把秦國抬上天的?

1984年粟總去世後,一位少將不願送行,王必成大怒:我看你不敢去

黑龍江省籍開國將帥共有幾位?獲開國少將中將上將軍銜者各幾人?

1990年,66歲老頭因兒子當兵落選,找到部隊領導:我是書上的烈士

乾隆死後,嘉慶是如何對待他的眾多妃子的,處置方式讓人為之驚嘆

清代縣衙的“臨時工”們

跨國追捕南京大屠殺“百人斬”戰犯,過程麯摺,結局大快人心

一代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很狂,橫掃歐洲,為何她不入侵中國?

姑姑是蕭燕燕,舅舅是韓德讓,一把好牌卻打爛的齊天皇後

北洋軍閥的覆滅之洪憲驚夢

越南為何這麼狂?聲稱一個月打敗中國,結局令人舒適

墳、墓、塚、陵到底有什麼區彆?看完漲知識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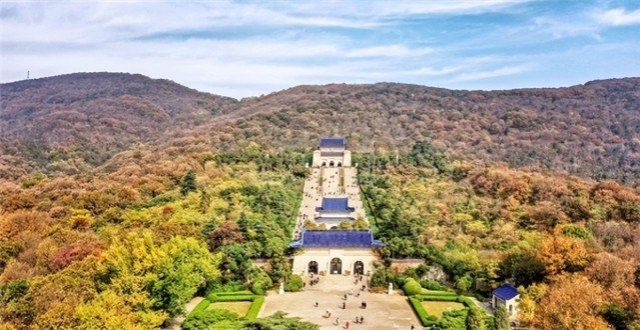
越國作為春鞦五霸,是如何在戰國初期,被其他國傢落在身後的

跟李世民11年,武則天都未孕,為何李治一上位就有瞭?原因很現實

愉妃在年輕時並不是很得寵,為何七十八歲高齡還能被乾隆翻牌子?

連“慈父”都曾親自點評:蘇聯人對時尚的追求,曾經有多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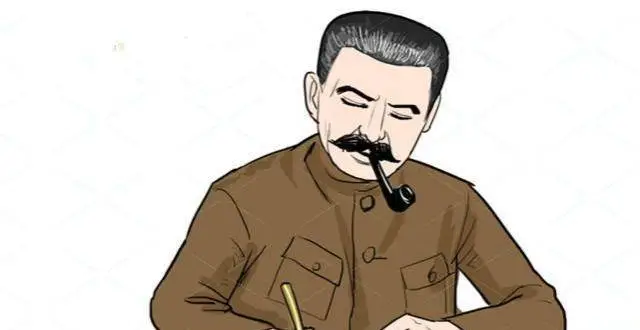
拒還香港、分裂中國、種族主義,丘吉爾為何如此仇視中國?

成吉思汗墓到底在哪?八百年未解之謎,如今專傢終於找到陵墓綫索

鐵血抗戰—李林(男)

昭信的玉碎花殘,何嘗不是北齊的榮辱興衰?

掃滅十六國的一代雄主-拓跋燾

晚清主將馮子材!年近70卻打敗世界第二強陸軍,為何死在齣徵前?

趙雲打瞭敗仗,卻在臨終前坑死瞭,能夠抗衡諸葛亮的魏國大將

這兩次小國組織的會盟,影響瞭整個中國的曆史

李剛:21歲嫁給葉劍英,如今94歲,身體硬朗,2個子女都很成功

九阿哥被雍正瘋狂清算,十阿哥為何能逃過一劫?雍正:不敢

民國奇案:俠女施劍翹,十年磨一劍,為父報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