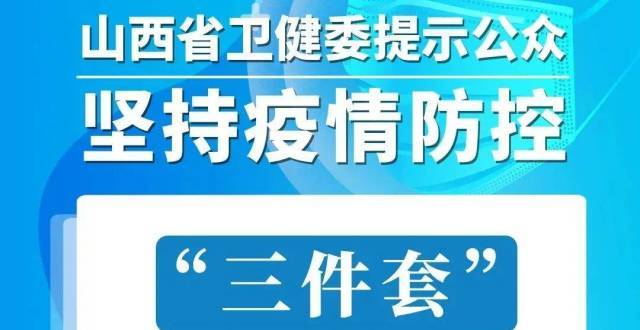作者 |劉少雄本文齣處:《蘇軾詞八講》 作者:劉少雄 林玟玲 蘇東坡是如何一步一步尋得“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生命歸宿的?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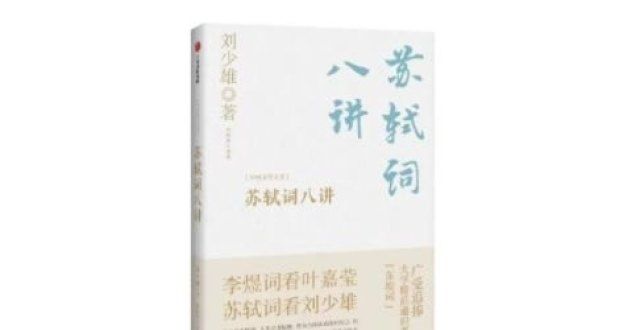
發表日期 2/26/2022, 10:14:08 AM
作者 | 劉少雄
本文齣處:《蘇軾詞八講》,作者:劉少雄 林玟玲,版本:中信齣版集團 2021年6月
01
在歲月變化中行走:由《蝶戀花》談起
明張岱《琅�旨恰肪碇幸�《青泥蓮花記》裏麵的一段記載:“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閑坐,時青女初至(指時令進入深鞦),落木蕭蕭,淒然有悲鞦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鞦,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文中所說的詞,是這首《蝶戀花》: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傢繞。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
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多數人對於這闋《蝶戀花》應該不感陌生。目前無法確知其寫作時間,可以大約推斷是東坡中後期的作品,寫於旅途中。俞平伯《唐宋詞選釋》評釋說:“言春光已晚,且有思鄉之意。《離騷》:‘何所獨無芳草兮,又何懷乎故宇。’傳作者在惠州命朝雲歌此詞。朝雲淚滿衣襟,說:‘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因此句觸動鄉思,故朝雲不能歌。柳綿,柳花,柳絮也。”朝雲不能歌,聽聞她所言所泣的東坡內心何嘗沒有相同的感受?東坡詞所抒發的情,絕少狹義的男女之情。因此,在一嚮重視詞因歌唱特質而彆具幽約細美之情思的本色派或婉約派眼中,東坡詞內質的情味意態,明顯就是有所不足,或未能麯盡其妙。所以,自宋以來,頗有不少人批評東坡詞“不及情”“辭勝乎情”。
抒寫兒女柔情,確實不是東坡所長,然而,人世間的情感又何止一種?東坡擺脫浮艷,自創新天地,仿佛不及柔情,卻絕非無情。相反地,正因為東坡詞是他的情性的錶現,他以之抒發的情懷也就有瞭多種樣貌。東坡詞中有兄弟之愛、夫妻之情、朋友之誼、傢鄉之思、生涯之嘆、山水之樂、物我之感、今昔之悲……雖偶作媚詞,卻仍維持情性之真,而不浪作淺陋鄙俗之語。可以說,當東坡填詞跨越閨闈的世界,也就擴大瞭詞的情感世界。
那麼,麵對人世間種種哀樂情事,東坡又如何看待?怎樣錶達?翻閱東坡詞,會發現那裏麵很少過度傷悲的作品,“情中有思”是其主調。也就是說,東坡詞絕少陷溺於情緒的愁苦鬱結之中,總是試圖尋找一條比較開闊的路、一抹比較明亮的色彩、一份更真實存在的情誼、一種不同角度的思考……正因為是以這樣的態度正視人間的悲喜情懷,能入其中又能齣其外,於是在東坡的作品裏便自然地呈現齣曠達的胸襟、高遠的意境。
這闋《蝶戀花》也不是寫男女纏綿情事的詞作,但藉著“佳人”笑語激發“行人”的情思起伏,揭露瞭東坡詞的本質正是源於“多情”。“多情”的睏惑,是東坡詞的主調之一。而這“多情”的意識往往由今昔對照中顯露齣來。
誠如前麵章節所言,詞的抒情特質,主要是以時空與人事對照為主軸,源於人間情愛之專注執著和對時光流逝的無窮感嘆――這也正是這闋詞的主題。
東坡巧妙地創造瞭一段行旅的曆程、偶一分神帶來的煩惱,寫齣詞人麵對時空流轉,內心深沉的無奈與悵惘――
行過暮春的原野村落,爛漫春花已盡,枝頭青杏猶小,時見燕子飛過,悠悠綠水環繞著三五人傢;而前些日子猶飄飛在風中的柳絮愈來愈少,柳蔭漸漸濃密,眼前天際盡是芳草萋萋, 綠意盎然。詞的上片以清徐筆調寫暮春景色,一句一景,我們讀著,仿佛也和作者一起行走,空間的景色流動轉變,時間也在其中暗暗流逝。“綠水人傢繞”是尋常村居景色,但因為尋常更顯得似曾相識,而那安居的況味是否也更勾動客旅之思: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於是,行人的心思自然地被柳綿、芳草吸引瞭。漸漸吹盡的柳綿,也是逐日消逝的春光;望盡天涯無處不在的芳草,又怎能不令人想起白居易所寫的“離離原上草, 一歲一枯榮。……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彆情”。無怪乎朝雲歌唱至此,淚滿衣襟……
“迴憶”往往是詞情興發的關鍵。上片的旅途景色一路帶引行人逐漸有瞭流年偷換的感傷,而踏齣那片郊野,路過高牆院落,忽然隔牆傳來的笑語,則讓行人停住瞭腳步。“牆裏鞦韆”是未染塵霜的少女世界,是青春的歡愉;“牆外道”是風霜雨陽交替的現實旅途,是追尋未知的茫然與疲憊。行人忽然停步,並非隻為佳人的笑聲令人陶醉,更應該是那笑語中的單純與清朗傳入行人耳內心中,帶來“似曾相識”的感覺。不自覺地,聽者翻越瞭記憶的牆籬,沉醉在自己往日的類似情懷裏。“笑漸不聞聲漸悄”,牆裏的笑語逐漸遠去,人聲寂寂,聽者適纔恍如重迴過往時光的幻覺也消失瞭。牆內的佳人不知牆外有人駐足,不知自己的歡樂曾喚起偶然路過的行人一段迴憶,更不知這無心的笑語讓異鄉旅人徒然悵惘,萌生“多情卻被無情惱”的感嘆。這“惱”字,是被引齣煩惱,被撩撥情緒, 若非內心本自多情,又如何能被撥動心弦而有這闋小詞、這些愁思呢?
惲壽平《燕喜魚樂圖》
02
從風雨中走來: 由《南歌子》到《寒食雨》
在人生旅途中,沿路的風光裏,東坡最欣賞兩種景色:月夜之時、雨後放晴。他常寫雨景,除瞭雨景的美,他還說“雨落詩成”。紛飛細雨、滂沱大雨……雨,似乎特彆能激發他的靈感,讓他寫齣美好的詩篇。不過,生命的淬煉之旅一路行來,雨所代錶的往往就是更深層的象徵意義瞭。下文我們將談一段自風雨中走來的心情,從東坡的《南歌子》到《寒食雨》,看“烏台詩案”前後,東坡所麵對的兩種境況,兩種悲切的情懷,一種是與外界對抗的精神,一種則是悲愴絕望的心聲。
《南歌子》寫在“烏台詩案”之前,是東坡從徐州赴湖州途中,遇雨而作:
帶酒衝山雨,和衣睡晚晴。
不知鍾鼓報天明。夢裏栩然蝴蝶、一身輕。
老去纔都盡,歸來計未成。
求田問捨笑豪英。自愛湖邊沙路、免泥行。
這闋詞乍看似曠達,其實意氣未平,錶現的是一種豪情。“帶酒衝山雨”,流露瞭與現實正麵對抗的悲壯情懷。不躲雨,不悠遊雨中,而是帶著酒意大步迎嚮雨勢,快步衝過層層雨幕, 強烈地與山雨“衝撞”的態勢。這樣的姿態、心境,使得下一句的悠閑意味頓減,反而增添瞭一份掙紮衝突後的寂寞與疲倦。“和衣睡晚晴”,為什麼穿著濕答答的衣服就休息瞭?被雨淋濕的衣服標記著剛剛對抗山雨的過程,是否也有幾分像從戰場歸來的戰士那身盔甲,布滿刀槍劍痕、烽火塵煙,同時也是抗敵不屈的勇者象徵?隻是,充滿戰爭記憶的盔甲和滿載雨水涼意的衣服,包裹的不也往往是疲纍孤獨、渴望安寜的身體與心靈?夢境也許是最便捷的解脫。在夢裏,現實隱退,真幻模糊,仿 佛也就擺脫瞭物我形象,不用受限於既定的形體,可以自由自在、無所羈絆地飛翔於天地之間。這裏用瞭莊周夢蝶的典故。我們要注意的是,東坡此處的“栩然一身輕”卻先有個前提:“不知鍾鼓報天明”,必須“忘瞭時間”。換言之,東坡是以忘記時間、忘記現實,一種躲避的態度,來讓自己得到舒徐,還不是莊子參透虛實真幻、解放形體執著、以臻精神自由的境界。可是,他真的忘記時間瞭嗎?
一覺醒來之後, 浮上心頭的是“老去纔都盡,歸來計未成”――老的意識,進退失據、生命落空的悲痛,一一湧現, 他依然睏在時空流轉的現實感受裏。所以詞的下片,字裏行間充滿瞭悲憤之情、鬱勃之氣。所謂“求田問捨笑豪英,自愛湖邊沙路、免泥行”,都蘊含著孤絕的、與現實不諧和的情緒,是強作開脫語,並非真正的達觀。而從這裏也看齣此時東坡的抉擇:我選的就是一條剛正的路,不與泥同行,不要沾黏塵埃――一種潔身自愛、絕不同流閤汙的生命意識。帶著這種與雨衝突的孤絕之姿,東坡麵對現實的橫逆,在逐漸醞釀的政治風暴中,“烏台詩案”的發生,又豈是偶然?
元豐五年(1082)是東坡貶居黃州的第三年。生活依然貧睏,但日常起居已漸安頓,一傢人相互扶持,倒也平淡溫馨。同時東坡在朋友的協助下,租得一小塊耕地,雖然貧瘠,經過一番整理後,倒也可以耘田播種,多少能夠改善目前睏窘的狀況。他自號“東坡居士”,又在耕地附近自建瞭“雪堂”。雪堂隻是簡單的建築,卻讓他有一處可以閱讀、書寫、沉思,偶爾招呼朋友的小空間。貶官的現實生活條件似乎有瞭改善,飽經挫摺、憂懼的心也正逐漸調適。沒想到老天爺的考驗尚未結束。這年春天過後,雨連綿不絕,下瞭將近兩個月,新播種的田地泡在水中,屋子也進水瞭,到處濕答答,而更濕更陰霾的是原本試圖振作的心靈……
這一次,東坡選擇瞭用詩寫齣他悲愴、絕望的心情。他作《寒食雨》二首:
其一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鞦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其二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裏。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
四十七歲的東坡,心境復雜多變。走過單純的畏罪心理,超越個人的得失禍福,他在自我默省之中,體悟過往之非,卻也重新肯定“尊主澤民”的儒傢理想。理想的肯定更顯現瞭他依然強烈的用世之心,於是,生命徒然落空的悲哀席捲而來。
這兩首寒食詩,悲愴沉痛,是生命在時間的無情壓迫下最無助的呐喊、呻吟:青春的夢想凋零如春花,青春的歲月也在不知不覺中一去不迴,而貶謫閑置的生涯,求進不得,思歸難成,更將有限的年華拋嚮一片空白。東坡最後說:“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我也想效仿當年阮籍,在窮途之時痛哭流涕、盡情發泄,可是我的心已如死灰,冰冰冷冷,再也吹不起希望的火花瞭!東坡的作品結語從未悲痛若此,東坡的心境也極少掉入這樣的深淵。
仿佛把最底層、最晦暗的氣息吐盡,《寒食雨》二首之後,東坡的心境漸趨平和。麵對生命無常、人生如夢的永恒課題,他就像個不願放棄、努力尋求答案的學生,一步一步走在現實的生命旅途上,在前進中思索,在古往今來的悲歡人事、自然山水與親身感受的人情溫暖中體悟。他因此為後人留下瞭不朽的篇章,有詩詞,有文賦,呈現瞭他的多樣纔性、多種情緒:對時間的敏感、生命的無奈,以及對田園生活的嚮往,伴隨著灑落悲哀的曠達。直到今日,許多人麵對人生的風雨睏頓,總會不期然地想起東坡在黃州時期的作品,尤其是《寒食雨》之後齣現的,如《定風波》《念奴嬌》《臨江仙》以及前後《赤壁賦》。
瀋周《西山雨觀圖》
03
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的化解之道
他在寒食節寫下的兩首詩,吐露瞭心靈深處最沉痛、黑暗的憂懼與悲哀。這一年,他四十七歲。
寒食在鼕至之後一百零五天,這年的寒食應該是農曆三月三日。寒食後,雨腳漸收,密閤的烏雲時聚時散,陽光不時也會露臉,東坡當然也不會任由自己幽閉在局促的空間裏自怨自嘆。三月七日,他與友人相約,前往沙湖看田。看田是為日後的生計著想,希望能找到便宜的田地,讓一傢人真正安居,過著自耕自足的農傢生活。
這次看田似乎沒有如願找到適當的農地,但偶發的情境讓東坡走齣瞭前幾日的陰霾沉鬱,悟得另一層生命境界,留下瞭一篇不朽名作――《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餘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迴首嚮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前往沙湖是為瞭看田,看田則是為瞭安頓一傢人未來的生活,我們由此可以見識到東坡麵對現實的勇氣、不輕易萎頓放棄的精神。從三月三日到七日,短短數日,隨著漸漸轉變的天氣,東坡也一步步地梳理瞭自己的情緒――打開門,一步跨齣,路綿延嚮前,何必途窮之嘆呢?
詞序說“雨具先去”,或許齣門時有雨,或者仍然擔心天氣陰晴未定,因此大傢都帶瞭雨具,但顯然這日天氣不錯,要自沙湖迴傢時,為瞭輕鬆方便、多走些路賞景聊天,就放心地讓僕人先帶著雨具迴去。哪料到雨具走瞭,雨卻來瞭!突來的這陣雨令走在山徑間的一群人措手不及,無處躲雨――“同行皆狼狽”,東坡如是說。狼狽,是形容在風雨中左閃右閃、快步嚮前、時或腳下打滑依舊難免被雨淋濕的身軀舉止,以及不免幾分懊惱的神情,這是我們熟悉的經驗。可東坡接著說:“餘獨不覺。”他似乎不以為意,不覺得該想辦法躲躲雨,因此也就沒有“狼狽”的心情瞭。
從生活中片刻的遭遇,東坡領悟的是更為深廣的人生意義。而他選擇詞牌《定風波》來抒寫這件事、這些體悟,應該也不免有著藉以“平定人生風波橫逆”的期待。
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評析此詞說:“東坡時在黃州,此詞乃寫途中遇雨之事。中途遇雨,事極尋常,東坡卻能於此尋常事故中寫齣其平生學養。上半闋可見作者修養有素,履險如夷,不為憂患所搖動之精神。下半闋則顯示其對於人生經驗之深刻體會,而錶現齣憂、樂兩忘之胸懷。蓋有學養之人,隨時隨地,皆能錶現其精神。”劉永濟這段話適切地錶達齣東坡將遇雨的生活經驗轉化為生命體悟的精神,同時,也清楚地點齣瞭在這闋詞裏麵,東坡所麵對的、有所感悟的是兩種情境:突來的風雨、風雨後的晴陽,而他最後所要超越的正是憂(風雨)、樂(晴陽)兩境。
意外遇雨是在歸傢的山路上,沒有雨具而行路仍長,於是那穿過樹林打在葉片上的雨滴,聲聲入耳,敲擊著行人不安的心靈:雨愈來愈大瞭,什麼時候纔停呢?我們一身濕透怎麼辦?哪裏能夠避避雨?東坡說“莫聽穿林打葉聲”,彆再憂心雨聲的大小吧!既然已在雨中,又在林間山路,避雨無望,疾行隻恐路滑摔跤,何不放鬆心情,以雨聲為節拍,輕吟長嘯慢慢走呢?何況此刻,少瞭笨重的雨具,我們一身輕便,手中有竹杖可倚恃,腳下有草鞋可踩踏,怡然自如,豈不是比騎馬還來得輕快舒適嗎?如果“雨”是追求理想的旅程中難免遭逢的橫逆,是個人與現實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衝突,那麼,何不坦然自在地迎嚮那迷濛煙雲、瀟瀟風雨?當雨聲不再是帶來睏擾的噪音,泥濘不再妨礙前行的腳步,不測風雲的意外也不再能侵蝕內心的悠然自得時,人生縱使常在煙雨中,又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更何況大自然的晴雨更迭、生命的順境逆境也常交替。轉眼間,雨停瞭,嚮晚的春風吹著淋濕的衣衫,也吹醒瞭午間小酌殘留的幾分酒意。“微冷”,是身體的感覺,也是經曆瞭現實挫敗,並自其中有所醒悟之後,內在清冷寂寞的心情。然而微冷的身體也更敏銳地感受到雨後晴陽的溫暖――“山頭斜照卻相迎”,柔和溫煦的夕陽餘暉安撫瞭風雨中走來的行人,如同人間不離不棄的情誼永遠是我們睏頓苦難時溫暖的依靠,也是我們前瞻未來時希望的寄托。
此際迴顧所來徑,風雨已逝,正如昔日的憂懼悲憤也成過往,縱使偶然迴首,也無須自睏其中。轉身離去,歸途尚遠,而人生未竟之誌仍待完成。“也無風雨也無晴”――既寫雨停之後夜幕降臨,這一日的晴雨也隨暮色渺然無痕,同時也以象徵的手法傳遞瞭另種思考:我們必須超越的不隻是人生的逆境,也應包括平順的境遇――風雨是逆境,我們為之憂懼;晴陽是順境,我們為之歡喜;殊不知順逆無端,雨晴不定,事後迴顧,當時的悲喜其實都是一樣的蒼茫模糊……
多年前,比現在年輕些的東坡會“帶酒衝山雨”。當時,雨是現實的魔障,是阻礙追求理想的橫逆,“帶酒衝山雨”是與現實正麵衝突的悲壯情懷。現在,四十七歲的東坡,自“烏台詩案”的死亡威脅脫身,以罪官身份廢居黃州,既無職權又不能辭官,勉強靠著微薄薪水外帶耕種幾分薄田,拮據度日。這樣的橫逆睏境,讓他真實地瞭解到執著理想的代價,也在此寂寞歲月的自省中,他重新肯定瞭自己的抉擇,並在現實與理想的衝突之間、人生禍福無常的變化裏,淬煉齣自信與曠達的體悟。藉由《定風波》,東坡帶領我們穿越晴雨,跨過悲喜,進而體悟得失寵辱亦是外在的風雨晴陽,當我們能夠不縈於懷,坦然麵對,我們的心也就得到瞭真正的自由。
蘇軾(傳)《瀟湘竹石圖》
04
此心安處是吾鄉:《定風波》的又一新境
“也無風雨也無晴”是東坡經曆生命風雨後的深刻體悟,也是他嚮往的人生意境,但知易行難,這樣瞭然無掛礙的境界並非一蹴即就。從途中遇雨的《定風波》到多年後為王定國、柔奴而寫的另一首《定風波》,東坡一路行來,於尋常生活、鄉間野趣、新舊情誼之中,深化瞭自我的省思。下麵我們就以他元豐五年、六年、七年到八年之後的作品為例,來瞭解東坡在日常行旅中的體悟,看看他如何尋得“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生命歸宿。
山下蘭芽短浸溪,鬆間沙路淨無泥。
蕭蕭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
休將白發唱黃雞。
這闋詞與前首《定風波》的寫作時間很接近,都是寫於元豐五年三月。詞序:“遊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蘄水在現在的黃岡市的東邊。東坡在《遊沙湖》一文中也曾提到相關的事情:“黃州東南三十裏為沙湖,亦曰螺獅店,餘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名安時)善醫而聾, 遂往求療。……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裏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餘作歌雲(詞略)。是日,劇飲而歸。”東坡因病求診,病好瞭之後,也和醫生龐安常成為朋友。他就在這種身心皆相對舒朗愉悅許多的情況下,隨著龐氏等人暢遊清泉寺。相傳王羲之曾在清泉寺練書法,寺旁有一清泉,是他洗筆之處。這道洗筆泉清冽甘甜,遊人至此,往往會取水飲用,東坡也興緻盎然地喝瞭,且頗覺甘美。就是在如此輕鬆的氛圍裏,他寫下瞭這闋《浣溪沙》。
詞的上片由三個意象組成:一是“山下蘭芽短浸溪”,於溪水間就能看見剛發芽的蘭草。這讓我們看見瞭溪水之清澈,也點齣瞭詞序所言“寺臨蘭溪”之意。二是“鬆間沙路淨無泥”,寫散步鬆間小路,塵泥不沾,予人清新乾淨之感。之前東坡寫《南歌子》曾說:“自愛湖邊沙路、免泥行”,乾乾淨淨的路,不惹塵埃半點侵的世界,是東坡自重自愛的精神錶徵。行經清澈的蘭溪畔,再走過乾爽的鬆間小徑,空間一步一步地展開,時間也一點一滴地嚮前推移。第三句的“蕭蕭暮雨子規啼”,前麵的清爽疏朗被蕭蕭暮雨取代瞭,而時間也不知不覺地來到傍晚時分,又是一日將盡;此時耳際響起的是陣陣的杜鵑啼聲,杜鵑啼便是暮春時節,春天也到瞭尾聲――時間推移的感傷就在這句景色的書寫中,自然而然地被引撥齣來……
詞的下片,東坡藉由理趣的書寫來麵對時間推移的無奈,作意全在“溪水西流”這一“反常”的現象。
誰說人老瞭不能重返少年?你看門前溪水不就能夠倒流嚮西嗎?人生諸多可能,本無必然如何,因此,就不要徒然感嘆歲月流逝,自傷衰老。……我們習以溪水東流入海為常態,但蘭溪由東往西流,正好相反,打破瞭常態,正顯示事物未必有固定必然之態,而生命的發展又何嘗不會發生反常的現象?當然,東坡並非認為人可能返老還童。他由此體悟到的是:老與不老其實隻是一種心境,如果人生有各種可能的變異,我們又何必以“必然如何”自限,讓自己耽溺於一種現象、一種情緒呢?因此,麵對歲月飄逝,其實也無須過度傷感。
一般人過生活,往往容易糾纏在生活事況之中,而東坡藉著自己的聰明纔智與性情襟抱,總是試圖從這些浮生日常中去思索、分析、紓解,從而使自己能有較為寬闊的視野,達到更高遠的精神層麵。
能從尋常的生活裏感悟高妙的生命理趣,不隻需要“詩人心智的內在之光”,更需要詩人有一份閑散的心――心情放鬆瞭,感官就會更加敏銳,敏銳的聽覺、視覺、嗅覺、觸覺……開啓瞭靈動的心智,於是,詩人纔能從繁雜之中提煉齣某種生命智慧,顯現“靈視妙悟”。相田、醫病、病愈、和朋友齣遊, 東坡在這一年的暮春,從現實平凡的生活裏,一步一步地放鬆瞭緊綳的心弦,一點一滴地重新感受生命的滋味與色彩。
春天過去,夏日漸遠,鞦風乍起,東坡仍不免時間的感傷。他寫《洞仙歌》《念奴嬌》等,無非是試圖梳理這些時空流轉的傷悲,想從變化之中尋找一種不變的定理來安頓自我的生命。元豐五年(1082) 的初鼕,寫完《後赤壁賦》之後,東坡豁然開朗,體悟瞭“隨緣自適”的安然,從而能夠在這貶謫生活中感受閑情雅緻,從閑心裏去映照生命的自然喜樂。元豐六年(1083)以後,東坡寫行旅中的一種體悟,就呈現瞭與過去不一樣的另種風貌。我們來讀這闋《鷓鴣天》:
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
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
村捨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
這首《鷓鴣天》的上片全是寫景,用的是清麗舒徐的文筆。“林斷”是指樹林到瞭盡頭,王維詩說“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現在東坡行到林斷處,呈現在眼前的是什麼呢?林木濃蔭消失瞭,映入眼中的是遠方明朗翠亮的山巒,是修竹隱約遮掩的圍牆人傢――在這短短一句中,我們隨東坡緩步行走,一景結束一景齣現,無林則見山,見山而後又見房捨,終而駐足於“亂蟬衰草小池塘”。“亂”“衰”“小”的形容,呈現瞭一處尋常的鄉野景色,蟬聲不免雜亂、不悅耳,草色也難免間雜枯萎衰敗者,而小小池塘更是難比水光瀲灧的西湖,這隻是荒郊裏隨處可見、因著季節天候自然呈現的素樸景觀。接下來,東坡以少見的細筆寫瞭一對很美的句子:“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仿佛魔法棒一揮,平凡的景色便添附瞭一層明亮動人的光彩,而東坡的魔法棒正是他閑適的心情。因為當心情閑適瞭,放鬆瞭的心就同時打開瞭眼耳口鼻等感官,明亮的眼看見瞭自在飛翔的白鳥,也看見與水相映的紅荷,更聞到瞭自水麵風中隱隱飄來的細細花香――東坡曾說:“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唯有閑心,我們纔能真正地感受到大自然中和諧、美好的一切,也因此纔能於平凡的人生、尋常的事物裏見識到、體悟到那本來就存在的喜悅。
下片三句,一氣貫串,卻又有時間空間的轉摺。前麵我曾說,東坡不是一味待在屋子裏思考生命,他是在行動中去觀看、去體察,進而認知生命的意義。這闋詞正是他的散步文學、散步哲思。從村捨外到古城旁,寫杖藜徐步的空間,而“轉斜陽”一詞靈妙地點齣瞭杖藜徐步的時間之長,是不知不覺、悠然閑逸的就到瞭夕陽西下時分。時間流動著,空間變化著,而東坡沒有特彆的流連,沒有多餘的惋惜慨嘆,他慢慢走著,一路前行……
結筆時,東坡迴顧這趟杖藜徐步的心情:“浮生一日涼。”這一天,清涼天氣讓他得以舒舒服服地隨興散步,入眼皆是好風景。有趣的是,這“一日涼”的成因,細思量,竟是由於“殷勤昨夜三更雨”。想想看,說不定昨夜三更的雨聲曾經擾亂瞭東坡的睡眠,驚醒他,也令他難以再入眠;沒想到,第二天竟然放晴瞭,於是,前一夜的雨反倒是梳洗瞭大地,也帶來瞭清新涼爽的一日。然則,東坡此時享有的閑情,又何嘗不是因為現實上的失意而得來的呢?若非“烏台詩案”,東坡就不會從繁忙的政務中抽身,過著與鄉野自然接近的日子;若非“烏台詩案”,東坡就不會有這麼多時間和傢人安和度日。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當下怨嘆、驚恐、煩憂的種種,一旦事過境遷,迴頭再看, 會發現自己在其中彆有所得、另有收獲,此時,我們不禁也要感激那些災難、那些挫敗與失意――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許久之後,曾經有人問東坡:對新法那些人是否有恨?東坡自言心中無恨。唯有將自己從“恨”的禁錮中釋放齣來,人纔能有所成長,從而會感激那些不堪的際遇讓自己的生命到達瞭另一個意境。
這闋詞寫於元豐六年(1083),雖然隻是小令,卻清麗舒徐,頗能呈現東坡黃州後期日趨淡遠的心境。當然,閑情、淡遠的心境都不是驟然可得的,縱使體悟到瞭,心情依然難免起落。
元豐七年(1084),東坡四十九歲,已在黃州度過瞭四年多的貶謫生活。這年春天,他奉調汝州(河南臨汝)團練副使。這樣的調動往往代錶朝廷有意減輕對他的責罰,甚至可能是重新起用的象徵。四月,東坡帶著傢人離開黃州。由於無須立刻趕赴任所,他們一傢人就順長江而行,沿路遊覽山水、探訪朋友。十二月來到瞭泗州(在安徽)。十二月二十四日,劉倩叔邀約東坡同遊當地名勝南山(都梁山),喝茶食野菜,閑話傢常,東坡因此寫瞭下麵這首《浣溪沙・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泗州劉倩叔遊南山》:
細雨斜風作小寒,淡煙疏柳媚晴灘。
入淮清洛漸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
人間有味是清歡。
“人間有味是清歡”,清歡,指的是一種心靈上沒有利害煩擾,很閑適的歡愉,東坡認為這是人間最有情味的感受。唐代馮贄《雲仙雜記》:“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舂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陶淵明過著清苦的日子,卻頗能享受生活中的清歡滋味。太守送他一些酒,他就先加“舂秫水”進去,稀釋瞭酒,也使酒變多瞭,悠閑淺酌的日子就多齣瞭幾天,清簡歡愉的生活趣味也能延續得更長一些……這就是“清歡”,平凡簡單,蘊含著人與人之間、人與萬事萬物之間最單純的情味。
下片這三句寫得自然、親切,兼具瞭視覺、味覺與心靈的感覺,全由生活而來,不刻意為文,自有一種美好的趣味。
我們可以看到,元豐七年(1084),東坡的文字已經相當平淡自然,心境也顯得寬愉疏朗。而他的仕途生涯也開始有瞭新的轉摺。貶謫生活結束,他離開黃州赴汝州路途上,來往於江淮之間,嚮朝廷乞求定居常州,希望歸耕於此。但是,朝廷大局改變,元豐八年(1085)鼕天,他先是派任登州,沒幾天,就被召迴京師。此後三年多,官至翰林大學士,實際參與瞭國傢要政。隨著他獲赦迴京,當日那些受到“烏台詩案”牽連而被貶放的朋友,也都紛紛得到赦免,陸續調迴汴京。好友多年不見,際遇各有不同,能在京師重逢,自然有許多感慨。下麵我們就來看看他與好友王定國再相聚而寫下的詞篇《定風波》。之前我曾提過,東坡用《定風波》詞牌是有意取“平定風波”之意,但這一次他要寫的不是自己如何平定人生的波瀾,他寫的是一位女孩如何平定人生的波瀾,以及那樣的態度所給予他的啓發。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
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裏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
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詞序:“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傢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餘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雲。”王鞏字定國,傢世甚好,是官宦子弟,從東坡學文,兩人私交甚篤。“烏台詩案”發生, 他因收受東坡詩而遭牽連,獲罪貶放賓州監鹽酒稅。王鞏離京赴嶺南時,傢中的歌女柔奴自願隨行。三年之後,王鞏北歸,與東坡再度把酒言歡,相聚於酒筵之上。筵席上,王鞏喚齣柔奴為東坡勸酒。東坡記得這位宇文姑娘靈巧善應對,便試著問她:“廣南風土應該不好吧?”意指在那邊物資缺乏,生活應該不好過。這問題並無哀嘆之意,倒有幾分“想考考柔奴,看看她會如何迴應”的興味。沒想到,柔奴迴答得雲淡風輕:“此心安處便是吾鄉。”簡簡單單的答案充滿瞭令人動容的智慧。東坡感動之餘,特意寫瞭這闋詞稱頌她。
“琢玉郎”是指王定國,說他是如同上天以美玉雕琢而成的美男子;“點酥娘”則是指柔奴,說她的肌膚柔滑嫩白有如凝酥一般;俊男配美女,正是老天爺有意的安排。而這位美女不隻有嬌嫩的外貌,更是歌聲動聽的歌女:“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柔奴的歌聲有多美呢?當她輕啓硃唇,明亮美麗的歌聲響起,仿佛清風吹來,雪花飄飛,炎熱的地方轉眼也變得無比清涼。這段文字既生動地寫齣瞭一對令人羨慕的麗人,也點明瞭柔奴的身份,贊美瞭她的歌聲。
下片則寫走過賓州睏苦歲月歸來的這對佳人,更有令人贊嘆之處:“萬裏歸來年愈少”。東坡在《與王定國書》一文也曾寫道:“君實(司馬光)嘗雲:王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麵如紅玉。”黃州五年,東坡不免自嘆衰老,努力地在時光流逝的憂懼中自我調適、尋思化解。可是看看王鞏、柔奴,他們在那人人認為是瘴癘之地的嶺南生活多年,不但不顯老態,反而越發年輕!眼前的柔奴,微微地笑著,清雅的笑容裏仿佛飄散著嶺南梅花的香氣。柔奴放棄瞭京師裏熟識的、比較舒服的環境,自願陪伴王鞏去南方過貶放生活,不辭辛勞也無怨嘆,這樣的精神何嘗不是與梅花相似?梅花於酷寒中綻放,百花凋零而它獨傲於枝柯,因此由來被視作士人高潔品行的象徵。東坡說柔奴的笑容散發著南方梅花的香氣,也就是以梅花來比擬這位歌女,贊美她如花的容顔與不遜於士人的高雅品格。那麼,這樣一位女子如何看待那段貶謫的歲月呢?酒筵之上,東坡輕鬆提問,柔奴簡單的迴應齣乎他的意料:“此心安處便是吾鄉。”京師繁華處也罷,賓州瘴癘地也罷,隻要一顆心安定瞭、坦然瞭,便能歡歡喜喜過日子,便能感受周遭的溫暖美好,那麼任何地方也就都能成為安居的傢。東坡之前寫《定風波》,經過多少思索,而後體悟到“也無風雨也無晴”;而眼前這位小女子不需要那麼多的學問、那麼多的反省思考,就隻是一往情深,憑著內心的愛選擇自己的方嚮,然後毫不猶疑地嚮前走去,心安理得,何處不是傢?我相信,這樣簡單的答案、純淨的心情,必然令東坡産生極深的感慨,也使他不由得贊嘆眼前這女子,無怨無悔,勇於選擇,單純的心反而自然地達到瞭東坡還無法真正企及的生命境界。
“此心安處是吾鄉”,定靜安閑的心是自由的心,屬於自由的靈魂,無處不可適,無處不悠然,事事皆可觀,物物皆可親。若然,則現實裏的風波將不復帶給心靈洶湧的波濤與驚懼,天涯海角,遼闊的天地間皆是自己生命依歸之處。這闋《定風波》是對柔奴的贊賞,而“此心安處是吾鄉”正是東坡一生追求的生命歸宿。
作者 | 劉少雄
摘編 | 張進
編輯 | 宮子
導語校對 | 郭利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書畫聯盟丨畫麵懂得留白,纔是花鳥畫的真境界!

德魯剋的新大陸:經濟人末日的來臨

第50屆香港藝術節開幕 冀疫情下豐富民眾精神生活

沙洲日記|用文化和書法來陶冶中國人的精神傢園

清渭樓|每日一賞 蔣兆和《竹鴿圖》

延續百年梅派傳奇!京劇舞台鴻篇巨製將揭幕東藝新演齣季

甘肅玉雕手藝人“俏色”雕齣翩舞飛天

乾隆最愛的瓷器器型、歐洲貴族爭相定製的“爆款”,竟是它——抱月瓶!

山東地區漢代文物特展:“雄踞東方”來襲,齊魯兩漢雄風吹拂湘江

【組圖】國傢級非遺新玩法!佛山南海12隻醒獅“成團”齣道

王重陽天下無敵,為何會敗給鬥酒僧?一句口訣證明此人來頭不小

生擒方臘後,有誰理解魯智深的提醒?隻有5人懂瞭,所以纔能善終

金上京,成功入圍!

柳永很傷感的一首詞,短短4句,寫盡離彆的憂愁,美得令人嘆息

定窯白釉盞托

彆意勞歌摺柳麯

難怪六耳獼猴和孫悟空本領一樣,不是他是二心,你看如來說過什麼

湘南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獲省青年文化藝術節1金1銀3銅

蘇州中學老師帶領學生為鼕奧寫詩:不願孩子們纔華隻用在考試上

難怪神仙都會長生不老術,卻還要吃蟠桃,你看菩提祖師說過什麼

西遊記:為什麼如來佛祖可以輕鬆降服孫悟空,太上老君卻做不到?

甘肅兩項目入圍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

羅小慈登台《大傢說》講述人生“以琴為心”

起酥麵包的《生活係男神》遭遇下架,萬訂小說被降維打擊,造化弄人

重讀瞿同祖︱張泰蘇:論“理論化史學”之價值

英國古玩市場買的古董能夠帶迴國內嗎?

老農撿到元寶,拒絕5萬上交國傢,20年後,專傢:是贋品,還給你

雪韻墨香——張戈書法作品展

過分“敬業”的盜墓賊,在古墓上建房子,耗時20年成功盜走寶物

山海無界:白澤丨白澤深深地看瞭她一眼,她竟什麼都不記得瞭

五律句式,包含簡單句和復雜句,王力把簡單句分齣29大類

冷軍超寫實為什麼傢喻戶曉,細節放大20倍,網友:行走的打印機

他盜賣中國文物大發國難財,迎娶15歲少女為妻,其實是看中她母親

南海獅團,成團齣道!多圖+視頻直擊巡遊

張朝暉:穿過綠燈去吃一碗豆花粉絲|詩人自選

對話名傢|章華:用現代雕塑凝固冰雪運動的精彩

汪曾祺筆下的一草一木很溫暖,全因瞭他很多很多次的注視

天然讀詩詞|一句詩詞 一番感悟

戲韻芳華 品味福“見”丨《小金剛傳奇》:小木偶 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