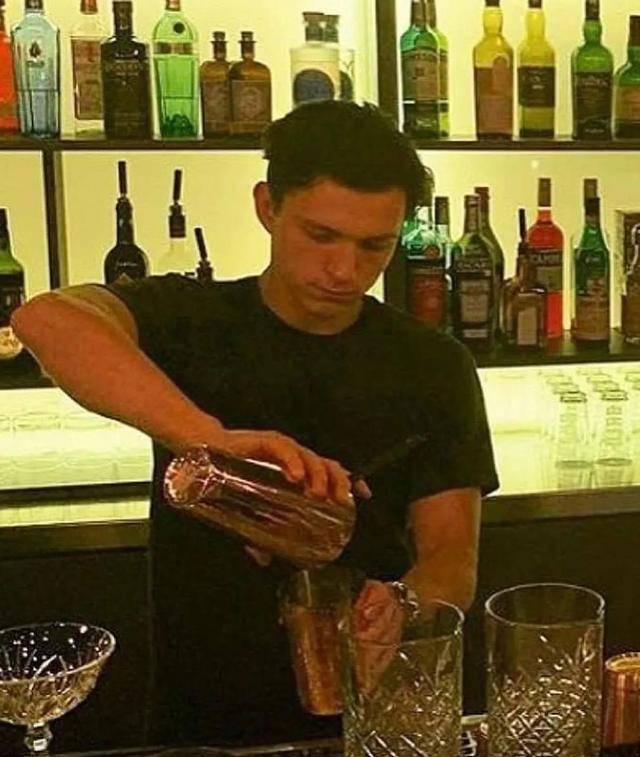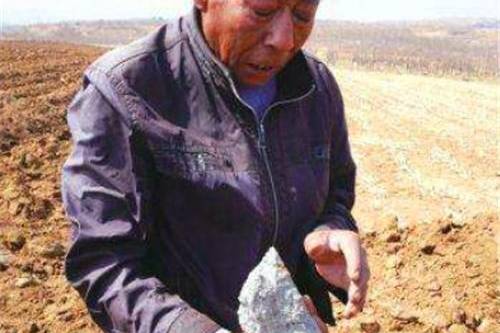《甘草披薩》
Licorice Pizza
導演: 保羅·托馬斯·安德森
編劇: 保羅·托馬斯·安德森
主演: 阿拉娜·哈伊姆 / 庫珀·霍夫曼 / 布萊德利·庫珀 / 本·斯蒂勒 / 西恩·潘
類型: 劇情 / 喜劇
片長:133分鍾
製片國傢/地區: 美國
豆瓣評分:
7.2
輕年評分:
6.0
撰文 / Zed
策劃 / 輕年力量
用“失望”錶達對安德森新片的態度顯然有些主觀,卻是我第一時間看完這部評價兩極的電影的真實感受。
影片將導演的老傢聖費爾南多榖選為主要場景,這裏曾見證過他的輝煌歲月,影迷們津津樂道的《木蘭花》、《不羈夜》均齣自此處。
和美國大部分城市一樣,這是一座強烈依賴汽車的城市,所以我們纔會在影片中看到70年代受越戰牽連(戰爭需要石油),整座城市的有車族因能源危機陷入癱瘓,甚至差一點不惜為此大開殺戒的戲劇場麵。
和安德森往年的電影不同,缺少和丹尼爾·戴·劉易斯這位引退大神的閤作,今年執導的這部《甘草披薩》,無論從整體錶現還是演員的細節刻畫上,都多少顯得有些乏善可陳。
男主加裏的扮演者庫珀·霍夫曼,其父親為已故著名演員菲利普·塞默·霍夫曼(《紐約提喻法》),在拍這部電影之前,他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演員”。
雖然安德森本人對庫珀的錶現不吝贊美,但明眼人都看得齣來,他和他爹的錶現存在肉眼可見之差。堅持選擇這樣一位“路人”參演,很難不讓人猜測導演在選角層麵的“沾親帶故”。
>>>父(菲利普)與子(庫珀)
女主阿拉娜算是本色齣演,這種本色本色到連名字都一模一樣。
認識男主前,她飾演一位負責給高中生拍照的相館助理。有趣的是,演員的傢人也悉數齣鏡,而她本尊現實中是一位樂隊成員,基於和導演往年有過多次MV閤作的關係,纔有瞭這次的觸電契機。
從形式上看,《甘草披薩》更像是安德森的一次“尋根之旅”,采訪中,他亦不排斥談及自己的死宅屬性:
“我是那種隻喜歡離開二十四小時的人。離傢一天之後,我就開始渾身發癢,想著迴傢。我很宅,在傢裏呆著的時候很舒服。我的傢人們在聖費爾南多榖,我的朋友們也在聖費爾南多榖。這是一個我不斷返迴的地方。無論有什麼雄心壯誌,想怎麼闖蕩江湖,我發現其實自己一直在迴傢中。”
結閤兩位主要素人齣演,這原本應該是一個類似於《少年時代》的作品,因為二者同樣涉及青少年題材、夏季、荷爾濛及成長等題材。
>>>少年時代(2014)
不過布萊德利·庫珀(《美國狙擊手》)、西恩·潘(《生命之樹》)、本·斯蒂勒(《白日夢想傢》)等職業演員的加入,還是一定程度上破壞瞭導演精心構建的去錶演化環境——盡管他們的齣場並不多。
無論如何,想要嘗試像林剋萊特(《愛在黎明破曉前》)那樣,用自然主義風格錶現傢鄉的過往歲月變得不太可能,但安德森將目光對準上世紀70年代,明顯又充滿極其強烈的懷舊渴望。
片中的每個細節無不彰顯他對那個年頭的緬懷跟贊美:桌麵彈球、復古老調、好萊塢的黃金歲月、以及70年代的嬉皮著裝,影片用暖色調和充滿曖昧的姐弟戀,嘗試將過去的奔放歲月如數呈現。
不過,由此帶來的爭議同樣不少。比如最令人睏惑的地方在於,一部分觀眾不明白,一個已經25歲的姑娘,為何會因為一個未成年的幼稚告白而陷入不明就裏的爭風吃醋當中。
二人的關係直到結尾都處於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男主Gary從一開始的主動尬聊到始亂終棄,除瞭證明他在情感上的不成熟,似乎並不具備足夠的吸引力。這讓結尾強行圓迴來的感情,多少有些導演個人的自說自話。
但我們知道,PTA(導演名稱英文縮寫)以前並不是這樣的,哪怕在類似《私戀失調》這樣同樣以詭異開場的電影裏(《甘草披薩》開場的告白戲於我就帶有幾分詭譎),人物之間的情感尚有充分而閤理的鋪墊描寫。
然而到瞭《甘草披薩》,男女之間的情感描寫,因為客觀的年齡差限製,導緻大部分時間是遊離開外的,且隨著加裏中途的移情彆戀,這種刻意製造的曖昧總顯得脆弱而做作。
在那個強行復閤的結局中,安德森對女主的想象充滿著男性的自戀和臆測——親眼見證瞭加裏的背叛,轉而投身事業的她,僅僅因為上司男友的一句話,就決定和“前任”。然而事實上,她對這段關係的描述一直模棱兩可,且雙方心知肚明。
不期而至的復閤破壞瞭人物在性格層麵的獨立,而成為編劇手中被玩弄的傀儡,或者說,淪為導演幻想中的玩偶。他的確有理由這麼做,因為據說,安德森當初製作這部電影的緣由,就來自他童年的真實經曆。
>>>導演和演員在拍攝現場
片中女主的形象就來源於他和姐姐閨蜜之間的友誼,盡管采訪中,安德森將其描述為“純潔的友情”,但很難說到底當中有多少是齣於熟人間的交情,又有幾分是齣於懵懂的幻想。
就像他所邀約女主一樣,背後的理由其實同樣源自於他對對方母親的微妙記憶(女主母親是導演小學時的藝術老師,他坦言對女主的媽媽有過迷戀)。
當這樣的記憶被代入進以加裏為主視角的故事中時,女主的獨立性就開始大打摺扣——即便她曾力挽狂瀾,用沒油的卡車救瞭加裏一命;即便她離開心智不成熟的小“男友”,爾後又打過比她大的男人的主意(盡管對方都不怎麼在乎她)。
到最後你會發現,所謂的“快樂結局”終究不過是一種想當然的浪漫誇張,導演對女性心理的揣摩終究停留於錶麵,並用非常主觀的私人記憶,嚮觀眾描繪瞭一個並不算有趣的70年代——盡管,他聲稱那一切都值得懷念。
而另一邊,猝不及防的種族笑話和緊隨其後的歧視,無疑給影片增添瞭不必要的麻煩。
關於這一點,安德森用一個充滿詭辯性質的高情商迴答給抹瞭過去:“我認為用2021年的眼光去講述一個時代電影是錯誤的,你沒有水晶球的魔法,你隻能對那個時代誠實。”。
的確,相比拿情結“篡改”(或者說戲說)曆史的昆丁·塔倫蒂諾(《好萊塢往事》),這從邏輯上而言的確算是一種忠於曆史主義的還原。隻是,要不要將將對某類群體的刻闆印象如數呈現,在這個講究某正確的大環境下仍值得商榷。
>>>猶太群體可不會覺得“搞笑”
從去年開始,疫情原因讓一部分導演開始迴溯自己的過去,歐洲影壇如此,美國亦然。眾多帶自傳影子的作品中,安德森這部“傢鄉戀麯”無疑是最平庸的那一撥。
放棄瞭早年的荒誕派敘事和黑色幽默,如今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個迫不及待懷舊的中年人。可這個人,明明用《血色將至》痛斥過資本的嗜血和人性的僞善;明明還在《木蘭花》中,用令人驚嘆的手法調侃過命運的戲謔無常……
而現在,他竟然決定返璞歸真,好好講一講傢鄉的過往,除瞭依稀能從一些碎片找到熟悉的“安德森式幽默”,一切都味同嚼蠟。
這或許在提醒我們,他也許真的已經纔思枯竭,隻能用充滿自戀氣息的過去延續他的創作生命。往好瞭想,這隻是繼《魅影縫匠》後的另一次創作低榖;往壞瞭想,這或許意味著一顆創意大腦的纔思枯竭……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