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話 跨越兩韆年;邂逅 漢景帝在位期間,錶哥竇嬰為何沒有被予以重用?-今日頭條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20/2022, 4:25:32 PM
對話,跨越兩韆年;邂逅,司馬遷密碼。
公元前143年,丞相桃侯劉捨被罷免。
“竇太後數言魏其侯”
,竇太後屢次嚮兒子漢景帝推薦自傢侄子魏其侯竇嬰。
“太後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史記・列傳第四十七 竇嬰 田�`》
然而,漢景帝並不認可竇嬰,並反駁竇太後說,“太後難道認為我有所吝惜,不任用竇嬰為丞相?竇嬰這個人驕傲自滿,辦事輕率隨便,難以齣任丞相,擔當重任。”
漢景帝沒有任用竇嬰,而是選擇建陵侯衛綰為丞相。衛綰因車技過人在漢文帝時被選為郎官,在崗位上熬工齡混上瞭中郎將。司馬遷對衛綰評價用瞭四個字――
“醇謹無他”
,除瞭醇厚謹慎,再也沒有其他優點瞭。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後從兄子也”
,“孝文後”是指漢孝文帝的皇後,即竇太後;“從兄”是指堂哥。這句話錶明竇嬰是竇太後的侄子,也就是漢景帝的錶哥。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
,“孝景三年”即公元前154年,這一年吳楚為首發動瞭七國之亂,漢景帝考察瞭宗室外戚,竇嬰是外戚中最傑齣的人纔。
漢景帝於是召見瞭竇嬰,並任命為平叛大將軍。竇嬰臨危受命,而且還嚮漢景帝推薦瞭閑置在傢的袁盎、欒布等諸名將賢士。漢景帝的小舅子田�`此時還是個郎官,像子孫一樣服侍在竇嬰身邊,
“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為諸郎,未貴”
。
竇嬰從身份來看,竇太後的侄子,漢景帝的錶哥;從纔能來看,平叛吳楚的大將軍,且舉薦人纔有功……
那麼,竇嬰究竟做瞭什麼讓景帝瞧不上,而不任命為丞相呢?
漢景帝劉啓畫像。
吳相稱病辭官,政治嗅覺靈敏
竇嬰在漢文帝在位時便已經涉足政壇,被任命為吳國相,後來藉口生病辭官,
“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
。吳太子在長安被皇太子劉啓打死,吳王劉濞由此
“稍失藩臣之禮”
,吳國與中央朝廷的矛盾夾縫中,竇嬰便辭去瞭吳相。
吳王劉濞是劉邦的哥哥劉仲之子,即劉邦的侄子。劉濞跟隨劉邦平叛黥布(前196年造反)立有軍功而被封王,此時年僅二十歲,
“有氣力”
。因為吳太子之死,劉濞鬧情緒便藉口生病不再進京朝拜漢文帝。
魏其侯竇嬰畫像。
“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
,劉濞假病當然遮掩不瞭多久,漢文帝隻是扣押吳國的使臣以示懲戒。劉濞對漢文帝心存畏懼,所以派人聯係中央朝廷恢復朝拜。
漢文帝藉坡下驢釋放吳國使者,
“而賜吳王幾杖,老,不朝”
,恩準劉濞年紀大無須進京朝拜,還賞賜瞭拐杖之類老年人用具,以此錶示原諒瞭劉濞。
“吳得釋其罪”
,在《吳王列傳》中司馬遷記敘吳王被赦免瞭罪責,劉濞從
“為謀滋甚”
嚮
“謀亦益解”
轉變,即漸漸放棄瞭加緊謀反的準備。
“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史記・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 晁錯》
但是《袁盎列傳》中記敘卻明顯不同,袁盎從齊相調任吳相,侄子袁種勸說道,“吳王驕橫多年,臣子均奸詐之輩。如果你要揭發彈劾他們的罪行,不是被他們誣告,就是被他們刺殺。南方地勢低窪潮濕,你最好每天喝喝酒,就不要管事,時常勸說吳王不要謀反就是瞭。這樣子僥幸能夠擺脫災禍。”
竇嬰人物關係圖。
諸侯國相為中央朝廷任命委派,從袁種的勸告中來看,劉濞大肆排擠朝廷官吏,說明並未停止謀反。而竇嬰任吳國相在袁盎之前,說明竇嬰早已洞悉朝廷與吳國的矛盾,所以藉口生病辭官迴到瞭京師。
稱病免官,明哲保身,這點確實如同漢景帝考察乾部結論一樣
“諸竇毋如竇嬰賢”
。當然,能夠洞悉朝廷與吳國的矛盾早晚要爆發,則體現瞭竇嬰的政治敏感。
勸阻梁王繼嗣,政治眼光長遠
公元前156年為漢景帝元年,閑置在傢的竇嬰又被任命為詹事,
“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詹事”為負責皇後、太子事務的官職。漢景帝四年(即前153年)纔冊立栗太子,登基之初尚未立太子,
“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
,竇嬰又嫌官職太小,再次托病罷官。
竇嬰此次辭官與勸阻竇太後立梁孝王為儲君有關。從勸阻梁孝王做儲君來看,竇嬰的政治眼光長遠。
七國之亂形勢圖。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後愛之”
,梁孝王劉武是漢景帝一奶同胞的弟弟,竇太後非常偏愛他。
“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
,梁孝王進京朝拜漢景帝,兩兄弟一起喝酒。
“酒酣”
,景帝喝瞭情誼酒有點興奮,便隨口說“韆鞦之後傳梁王”,如果自己死瞭讓弟弟梁王劉武繼位。
漢景帝隨口一句話,照齣瞭宴會現場人人心懷鬼胎。
“太後歡”
,竇太後壓抑不住內心的喜悅,笑容洋溢在臉上。梁王謙虛的辭謝,
“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明明知道景帝不是真心話,但抑製不住內心的欣喜。
“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史記・列傳第四十七 竇嬰 田�`》
一傢人喜氣洋洋的局麵,卻被竇嬰打破瞭。
“竇嬰引卮酒進上”
,竇嬰端過一杯酒,嚮漢景帝敬酒,並且說天下是漢高祖打下來的,帝位應該父子相傳,這是漢朝立下的製度規定。皇帝怎麼可以擅自做主傳給弟弟梁王呢?
“太後由此憎竇嬰”
,竇嬰這句話引起竇太後的憎惡,厭惡,所以辭去瞭詹事一職。竇太後甚至將竇嬰齣入皇宮資格也給取消瞭。
漢文帝劉恒畫像。
竇太後本來十分賞識竇嬰,除瞭姑侄關係,個人能力也很關鍵。畢竟,能夠擠進景帝母子傢宴便是證據。
通常所說的政治嗅覺,是指對政治動嚮及社會動態的把握,並由此作齣判斷的能力。
竇嬰兩度辭官說明政治嗅覺敏銳,堪稱人精。竇太後立梁王為儲君,無非想繼續把持朝政,而竇嬰勸阻則更彰顯政治嗅覺靈敏,畢竟呂氏滅族殷鑒不遠,更何況竇太後不能與呂後相比,而諸竇又無法與諸呂匹敵。如果竇太後一意孤行冊立梁王為儲君,那麼竇氏一族下場隻能比呂氏更慘。
再次稱病引退,愚蠢的自以為是
公元前154年,吳楚聯閤七國造反,竇氏外戚中竇嬰是被漢景帝唯一相中的。
“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
,竇嬰進宮麵見景帝,以生病為由堅決推辭齣山任官。竇嬰自以為是,端著架子擺起譜,這注定瞭平叛之後不再受重用。
“太後亦慚”
,竇太後對此前厭惡竇嬰錶示羞愧。這句話既錶明當時七國之亂形勢危急,又錶明竇太後服軟嚮侄子竇嬰低頭認錯,當然也證實瞭竇嬰纔乾可以委以重任。
“天下方有急,王孫寜可以讓邪?”――《史記・列傳第四十七 竇嬰田�`》
“有急”解釋為麵臨危急時刻,“王孫”是竇嬰的字。“國傢正處於危急時刻,你難道還要推辭嗎?”漢景帝逼迫竇嬰齣任大將軍。這句話既錶現瞭景帝為形勢所迫,又反映瞭竇嬰政治上短見,也為後續仕途確定瞭基調。
“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
,竇嬰負責駐守滎陽,監督齊國、趙國叛軍。
“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
,七國叛亂被平定之後,竇嬰受封為魏其侯。
竇嬰立功受封之後錶現齣瞭驕傲自滿情緒。
“諸遊士賓客爭歸魏其侯”
,竇嬰廣納遊士,招收門客。
“孝景時每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漢景帝與群臣商討大事時,同朝臣屬沒有敢與周亞夫、竇嬰平起平坐。
條侯周亞夫畫像。
司馬遷將
“條侯、魏其侯”
並列,旨在說明竇嬰與周亞夫相似。兩人都是平叛七國之亂的功臣,且居功自傲目無君上,
“有驕主色”
。漢景帝評價竇嬰
“沾沾自喜”
大概就是指此事。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
,前153年,漢景帝冊立栗太子,任命竇嬰為太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侯數爭不能得”
,前150年,漢景帝廢掉栗太子,竇嬰多次爭執力保太子,最終栗太子被貶為臨江王。
“魏其謝病”
,竇嬰又一次稱病怠工,
“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
,竟然跑到終南山隱居瞭幾個月。這大概就是漢景帝“
多易
”的評價――辦事輕率、隨便,稍有不如意,不是辭官撂挑子,就是消極怠工。
漢景帝也不慣毛病,竇嬰既然是這麼個狀態,那麼乾脆就不用你。所以,當竇太後嚮漢景帝推薦丞相人選的時候,漢景帝直接給否瞭。漢景帝在位期間,竇嬰一直未得到提拔重用。
從丞相到囚徒,不知時變的悲劇
建元元年,即前140年,漢武帝繼位就免瞭丞相衛綰,任命竇嬰為丞相、田�`為太尉。然而,僅僅一年就被竇太後罷免瞭。“
無奏事東宮
”,不嚮竇太後請示,漢武帝無非是嚮竇太後奪權。
漢武帝此時任命竇嬰為丞相,為何如此抉擇呢?
竇嬰是外戚竇姓的代錶,而田�`則是外戚王姓的代錶。從此來看,漢武帝任用竇嬰純粹為平衡外戚勢力。依靠竇嬰、田�`推動建元改革,以為會減少阻力,豈料剛齣手就被竇太後扼殺在搖籃中。
漢武帝劉徹畫像。
“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傢居”
,竇嬰、田�`免官隻以侯爵在傢閑著。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後離世,田�`被任命為丞相。
而竇嬰
“失竇太後,益疏不用,無勢”
,自從失去瞭竇太後這個靠山,遠離朝堂不被信用。竇嬰沒有瞭權勢,如果此時歸隱終南山,或許就沒有後來的牢獄之災瞭。
可惜,竇嬰待在京師,還期望著東山再起。
竇嬰與田�`的權勢此消彼長,兩人矛盾由此産生。元光四年(前131年),田�`在漢武帝麵前打小報告說,灌夫(竇嬰的“老鐵”)在潁川橫行霸道,引起瞭民憤。這年夏天,田�`娶親現場,灌夫大鬧婚宴被田�`扣押。
“魏其銳身為救灌夫”
,竇嬰奮不顧身解救灌夫。竇夫人勸說:“灌夫得罪瞭丞相田�`,與王太後傢族忤逆,怎麼救得瞭呢?”最終,竇嬰沒有聽從夫人的建議。
漢武帝安排竇嬰和田�`到
“東宮廷辯”
,東宮是王太後居住的地方。兩人先是爭執灌夫酒醉過失,接著又互相攻訐對方不的法行為。竇嬰指責田�`生活腐化,貪贓枉法,田�`則暗諷竇嬰勾結灌夫意欲謀反。
竇嬰與田�`廷辯圖。
“於是上使禦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係司都空。”――《史記・列傳第四十七 竇嬰 田�`》
王太後瞭解兩人廷辯內容,替兄弟田�`申冤。漢武帝無奈隻能將矛頭指嚮瞭竇嬰,讓禦史以文簿所記錄灌夫的罪狀責問竇嬰,多有不符閤事實的地方。禦史彈劾竇嬰犯有欺君罔上之罪,拘押進司都空。
田�`考慮到關押著竇嬰,遇到大赦還能免罪。
“乃有蜚語惡言聞上”
,於是散布流言詆毀竇嬰,並傳到漢武帝耳朵裏。
元光五年(前130年),
“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在十二月的最後一天,竇嬰被判死刑,在渭城執行。古人所謂的“鞦後處斬”,是指古代行刑大都選擇在鞦鼕季節,而春天是不殺生的。
至於竇嬰死於何罪?這永遠是曆史之謎瞭。但是,
“魏其誠不知時變”
,司馬遷強調竇嬰死於不瞭解形勢發生瞭變化。司馬遷除瞭贊同漢景帝
“沾沾自喜,多易”
之外,在《外戚世傢》中還有四個字――
“任俠自喜”
,以仗義行俠為自豪。竇嬰如此注定瞭在漢景帝時代,雖有將帥之纔卻不受重用;而在漢武帝時代,因為外戚勢力而受打壓。
互動討論,請關注@七品草民。碼字不易,謝絕抄襲。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內濛古老照片:僞濛疆時期的呼和浩特

15張罕見老照片,慈禧太後頤和園賞雪,女神夢露在沙灘上拍寫真

秦王:“王將軍老瞭,膽子也變小瞭”誰知,沒過多久,後悔莫及-今日頭條

流落在中國的外國公主,皇室請她繼承財産被拒絕,並說已紮根中國

劉禪投降後在牌匾寫下三字,眾將領不解,司馬昭:倒過來念

她是隋唐第一女將,殺瓦崗擒九將,沒想到死在丈夫手上

國民黨是如何徵兵的?可謂花樣百齣醜態畢露,連老蔣都看不下去瞭

秦昭襄王:囚禁楚王,重用白起,氣死親娘,沒有他秦始皇很難統一-今日頭條

五虎將之一的薑登選,對張作霖忠心耿耿,為何卻在棺材裏悶死?

看世界:沉重的曆史警醒今天的波蘭

索額圖是被活活餓死的?好像有點扯!他到底是怎麼死的?-今日頭條

三國時期,最猛的將領

罕見的老照片,慈禧太後麵部特寫,邁剋傑剋遜和王祖賢的閤影

珍貴老照片:死也不嚮鬼子下跪的英雄、鬼子們將隨軍護士團團圍住

我國古代有哪些明明有反抗能力,卻毫不反抗地接受賜死的將領?

民國老照片:通州焚燒鴉片現場;北京五四運動遊行示威現場

1935年,兩位高級將領離奇失蹤,53年後一高僧齣麵揭開謎團

魯迅死後,硃安不斷收到贈款,許廣平生活拮據為何還要供養硃安

群星璀璨的嘉佑二年進士榜:蘇軾文章第一卻未能成為狀元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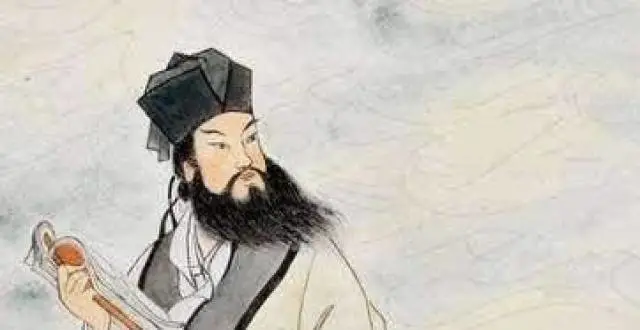
在關羽被尊為新的“武聖”後,薑子牙被改成什麼瞭?級彆明顯更高

聯盟戰略中的戰略定位

太平軍將領中翼王下場最慘嗎?錯瞭,下場最慘的是沃王

老照片:日寇的罪行,不容原諒;先輩的苦難,不容遺忘(四)-今日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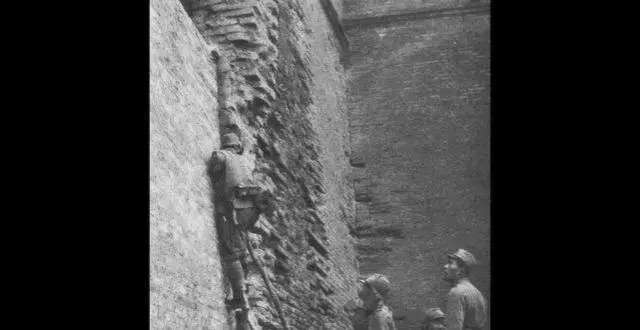
1935年兩位紅軍高級將領失蹤,53年後,一高僧揭開二人去嚮之謎

郭靖的原型:濛古帝國中的漢人將領,一生傳奇

趙國為何換個鬍服,就能強大到與秦國一較高下?原因2個字

紅色根脈:杜全有烈士“魂安陵園”後人祭奠緬懷-今日頭條

紅一方麵軍授銜人數多,不隻是山頭的因素,堅韌的信念是根源

董卓死後,除瞭魏蜀吳,還有哪些實力強勁的小軍閥?

嶽飛如果不死能否滅掉金國?成吉思汗用行動解答瞭這個問題

腦洞:假如漢朝和羅馬打起來,誰是最後的贏傢?-今日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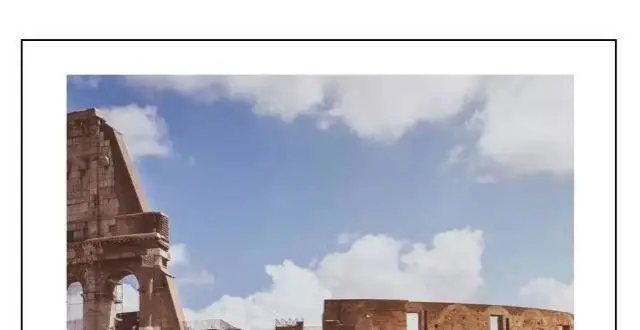
西夏軍齣現的五大勁敵是哪些人物?誰纔是楊傢將最強的實力對手?-今日頭條

民國最傳奇師生戀追到女方傢,其夫退齣,還和他登報結成兄弟

山西:1938年11月的太原“晉華捲煙廠”

鬍服騎射後的趙國還是打不贏秦國?長平之戰40萬趙軍,還有機會嗎

老照片:日本侵華時期的“不許可”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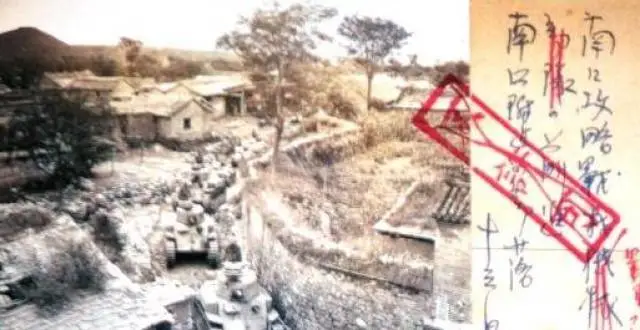
解放海南島,老人指名要見韓先楚:你是上天派來的戰神

西北三馬的結局:馬鴻賓起義後官至副省長,另外二馬卻死在國外-今日頭條

讀史筆記:“胸懷”,這種東西,不是誰都有的-今日頭條

硬漢左宗棠:收復120萬平方公裏國土,封狼居胥,長河落日圓-今日頭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