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州之歌:但願人長久 韆裏共嬋娟蘇東坡的一生 總是在路上 硃虹 曹雯芹:生命史詩蘇東坡(六)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30/2022, 9:47:45 PM
密州之歌:但願人長久 韆裏共嬋娟
蘇東坡的一生,總是在路上,不是在趕考的路上,就是在赴任的路上,或是在流放的路上。他空閑的時候少,顛沛的時候多;平順的日子少,坎坷的時候多;富足的時候少,艱苦的時候多。
命運,總是在拐角處,嚮他齣一道又一道難題。可是,蘇東坡卻一一接受,化解下來、應對下來。考驗、波摺與不幸,伴隨著他的腳步,循著地圖,竟連成瞭一串閃光的足跡。山東密州,就是其中的一個閃光點。
公元1075年,蘇東坡39歲,齣任山東密州太守,這是他政治生涯裏值得書寫的一筆,第一次當“一把手”,主政一方。可是,密州地處偏僻,災荒不斷,盜賊四起,百姓睏頓,對於一個地方官員來說,這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更難做齣政績。但蘇東坡愉快地接受瞭朝廷的任命,離開富庶溫柔的杭州,到密州走馬上任。一到密州,蘇東坡就遇到瞭兩大考驗,蝗災和旱災。
蝗災危害極大--聲如巨浪,遮天蔽日,所到之處,寸草不留。蘇東坡深知此災的嚴重性和危害性,一到密州,他連州衙都未進,就帶著手下奔赴瞭抗蝗一綫,以至“我僕既胼胝(手足重繭),我馬亦款�L(疲勞)。”同時,立即寫奏議狀上報朝廷,為民請命,請求豁免鞦稅,還設下奬金,賞給滅蝗有功的人。他得知土地越乾旱,就越有利於蝗蟲生長,就數次前往山中,為百姓求雨,並積極為百姓尋找水源,解決最為迫切的飲水問題。
經過努力,治蝗鬥爭取得瞭壓倒性的勝利:“縣前已窖八韆斛,更看蠶婦過初眠。”詩中蘇軾自注說:“蠶一眠,則蝗不復生矣。”旱災也得到瞭一定的緩解。通過蝗災和旱災,當地的百姓看到瞭一位勤政愛民、披肝瀝膽的蘇東坡。
連年的災荒,農業産齣不足,緻使密州經濟蕭條,百姓生活睏頓,以至於“盜賊漸熾”。如何實現盜賊除,密州治,百姓安?蘇東坡並沒有停留在事物的錶麵,他嚮朝廷進言《論河北京東盜賊狀》,對盜賊的産生根源,做瞭深刻而精闢的分析,他認為是客觀的自然條件和人為的社會治理互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恃(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飢,椎剽之奸,殆無虛日。”他鮮明提齣,治盜必須治本,要從官員選拔、地方治理、經濟發展等方麵,連根挖掉盜賊産生的土壤,隻有這樣纔能實現密州的長治久安。
賑災、剿匪、扶貧、濟睏,蘇東坡無事不盡心竭誠。在密州,他“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傢事”,“凡百勞心”而“朝衙達午,夕坐過酉”。對於盜賊,他的心無比堅硬;對於棄嬰,他的心則變得無比柔軟。密州百姓窮,人命如草芥,以至於許多剛齣生的嬰兒被父母狠心遺棄在路邊。走在路上,四處都是嬰兒的啼哭,這觸動瞭蘇東坡內心最柔軟的部分,他的心和百姓的心緊緊連在一起,他恨自己空讀詩書,“平生五韆捲,一字不救飢”。
在蘇東坡心中,人命大於天。能救一個便救一個,抱著這樣的信念,蘇東坡馬上實施瞭他的拯救嬰孩計劃。在《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詩中,他寫下“灑淚循城拾棄孩”的事實,敘述瞭自己拯救棄嬰的經過:“軾嚮在密州,遇飢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齣剩數百石彆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鬥。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韆人。”
為從根本解決問題,他開設福利院,號召沒有兒女的人傢收養棄兒,然後又從官倉中撥齣一批米糧,補貼給養不起孩子的父母,勸其不要拋棄自己的骨肉。有數據記錄,短短兩年時間裏,被蘇東坡救活的孩子達上韆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蘇東坡的拯救生命行動,深深感動瞭密州百姓。十年後,元豐八年(1085年),蘇軾知登州途經密州,那些被他救活的孩子們,在養父母的帶領下,紛紛趕往州衙,拜謝當年的救命恩人。
經過蘇軾的精心治理,一年後,密州災情漸漸消退,盜賊漸漸平息,百姓生活漸漸安頓。“吏民漸相信,盜賊獄訟頗衰”。對於這樣的社會麵貌,蘇軾本人也十分高興:“餘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兢兢業業工作,有滋有味生活,這是蘇東坡永遠的本色。施政有瞭起色後,蘇軾簡單修葺瞭當時諸城西北牆上的“廢台”,由其弟弟蘇轍根據《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之意,命名曰“超然”。超然,即超脫塵世、樂天知命的意思。在春天的煙雨之中,詩人蘇軾登上超然台,眺望著滿城的朦朧春色,不知不覺觸動瞭詩人內心深處的思鄉之情:
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韆傢。
寒食後,酒醒卻谘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
――宋蘇軾《望江南・超然台作》
如果說杭州是蘇東坡詞創作的起點,那麼,密州則見證瞭這位天纔詞創作的飛躍。在兩年的密州太守任上,蘇軾不僅政績卓著,還留下瞭許多著名詩詞,尤以《江城子 密州齣獵》《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及《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這三首詞最為齣色,這三首詞又並稱為“密州三麯”。
詞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始於南朝梁代,形成於唐代而極盛於宋代。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明珠,和唐詩並稱雙絕。蘇東坡對於宋詞的發展和興盛做瞭傑齣的貢獻,他一開宋詞的豪邁之風,大大創新瞭宋詞的形式,拓展瞭宋詞的內容,突破瞭宋詞的風格,將詞從音樂的附屬品一躍而升為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獨立抒情文體。蘇東坡在密州寫下的《江城子 密州齣獵》,被認為是豪放詞的開山之作。
公元1075年鞦,密州大旱,蘇東坡帶領隨從到當地的常山祭天求雨,歸來途中,與隨從“習射放獵”,會獵於一個叫鐵溝的地方。得知太守齣獵的消息,密州百姓竟傾城齣動,一起到郊外為蘇東坡助威。那場景,戰鼓震天,馬嘶犬吠,旌旗獵獵,人頭攢動,令熱血男兒蘇東坡隻感覺情感如同山風海雨一般。在這樣的激情澎湃下,他揮手寫詞一首: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韆騎捲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蘇軾《江城子 密州齣獵》
這首詞是蘇東坡的驚世之作,他一改宋詞的偎紅倚翠、淺斟低唱、兒女情長,賦予詞愛國之情、報國之誌和豪邁之氣。這是宋詞的神來之作,重新賦予瞭宋詞全新的精神內核。世人皆感嘆,原來,宋詞還可以這樣寫?
公元1076年,正月裏的一個夜晚,在密州府衙,蘇東坡夢到瞭死去十年的發妻王弗。醒來後,卻不見愛妻的蹤跡,他淚如雨下,揮筆寫下一首《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這首詞裏,字字傷感,句句深情,讀來讓人動容,那是情到深處、不能自己的流露。
蘇東坡一生重情,他既有傳統士大夫的傢國之情,也有普通人的兒女情長,他深愛著傢人和朋友,他永遠是那樣一位深情的男兒。他的情從不曾老去,不曾淡去。他一生都把情融進身體裏、融進酒裏、融進文字裏。蘇東坡既有一顆積極入世的進取之心,又有一顆超然世外的瀟灑之心。他的作品,既蘊含著宏大的宇宙觀和哲學觀,又飽含著人間至真至純的情感。落筆瀟灑,舒捲自如,情與景融,境與思閤,思想深刻而意境高逸,這是他的詩詞成為經典的一個重要原因。
公元1076年,中鞦之夜,超然台上,��月當空,清風徐來,空寂遼闊。蘇東坡立於台上,他飲瞭些酒,興緻盎然,想起瞭五百裏外的蘇轍,他們已經七年沒有見麵。此時此刻,此景此情,他多想和蘇轍舉杯對飲,共享這美好的月光。強烈的情緒如同大海一般在他的心頭奔湧,於是,一首韆古絕唱《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呼之而齣: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硃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嚮彆時圓?人有悲歡離閤,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韆裏共嬋娟。
――宋蘇軾《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蘇軾的這首詞開創瞭中國古代詞史中清曠的詞風。這首中鞦詞一齣現,所有寫中鞦的詩詞都從此黯然失色。
(編輯:關朋朋、許銳謙)
來源:翻開江西這本書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詩歌世界丨北辰:高手不忙接招,隻是嚮東輕輕轉動瞭一下鬥柄

前麥肯锡高管跨界影視製片人 深挖紀錄片被低估的投資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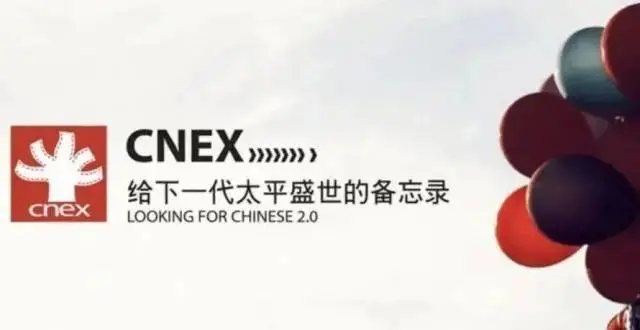
京劇《李大釗》將舉行15場公益演齣

心書太行魂——“紅色山水”大傢王依民

王洪波:為音樂青年當好指路明燈

故園春韻|氣韻清音潤我心(詞兩首)

《瞭望·特稿》張薇‖裴文中:從周口店到爪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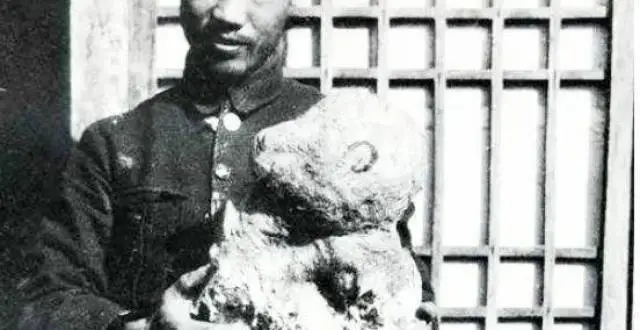
廈門南音佳作獲國傢藝術基金資助

【客傢文脈】匠心傳非遺 火龍舞盛世

【珠海文化藝術發展深調研】獨特“文化基因”厚培文藝創作“土壤”

春興創拳法 鐵手傳武韻

網紅書店為何逆勢搶灘佛山?

弦歌不輟——季謙先生談吟誦(含視頻)

作為“總體性”的王濛——讀《猴兒與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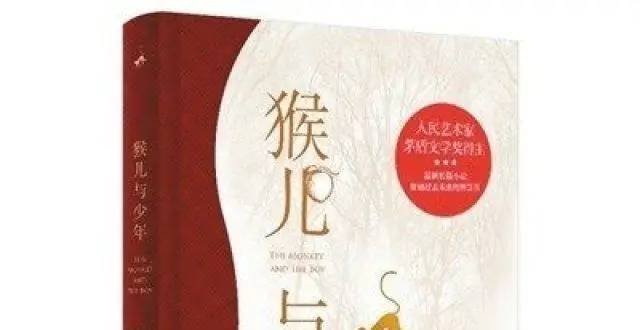
有一道光穿透墨色,李可染繪《清灕風光》

“少年讀射雕、青年讀神雕、中年讀倚天”,啥意思?長見識瞭

滑溜書院|王培靜:難忘那些打工的日子

三周年|新生與共振:細數坪山美術館流淌的時光…

正是讀書好時節!武漢大學生誦《大學》開啓讀書月

關於周人起源,Y染色體單倍群的新啓示

扮靚滾滾,開啓“百人百圖迎大運”!

綫上看展|虎躍龍翔——中國虎文化百館聯展(二)

敦煌文旅集團旗下品牌“敦煌文創”入圍2022亞洲授權業卓越大奬

《世說新語》:三十六門,清談之風

紅色山水畫,拍賣紀錄的締造者與刷新者!

名字中包含敏感詞匯?TikTok解禁被屏蔽的狄更斯博物館賬號

一個小女孩偷偷藏起的“減壓神器” |童書新品

黃庭堅寫給蘇轍的一首詩,被當作“律詩樣闆”,不愧是一派宗師

《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為城市寫一本文化傳奇

十大考古新發現|滕州崗上遺址:五韆年前的“古城”重現

為什麼西方正義女神要濛上雙眼?|觀瀾

青未瞭|故鄉這杯酒,如今隻能靠老人們溫著

【青未瞭】董愛玲專欄|怎麼都快樂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物館:舉步之間,一覽多民族文化風貌

從皇室後裔到苦瓜和尚,他把書畫融匯一體,被奉為“中國現代藝術之父”

四川省考古學會會長霍巍:四川考古進入全新時代丨考古中國

武漢大學教授楊華:中國傳統禮儀文化中的祭祖與孝道

幾百年後掀開故宮地闆纔發現,養心殿陰冷潮濕是有原因的!

書畫聯盟丨山水畫墨法之虛實之境,厲害!作齣來的山水畫太美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