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哲學中有一類被稱為“知識論”的問題 這類問題研究諸如“人類的知識從哪裏來?”、“我們的知識可靠嗎?”等問題。哲學知識當然也是一種知識 你也能讀懂休謨——談談休謨對於因果關係的考察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2/2022, 12:36:09 AM
引言
哲學中有一類被稱為“知識論”的問題,這類問題研究諸如“人類的知識從哪裏來?”、“我們的知識可靠嗎?”等問題。哲學知識當然也是一種知識,因此也存在上述問題。所以知識論在哲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是對於哲學知識,對於人類的一切知識,包括曆史知識、日常生活知識、科學知識等等,我們都可以提齣這樣的問題:這些知識是從哪裏來的?它們可靠嗎?
休謨是英國(準確的說是蘇格蘭)18世紀著名的哲學傢,今天他被認為是曆史上最重要的哲學傢之一,是哲學界的大Boss、大魔王。他對於哲學所做的貢獻之中,最重要也是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對於知識論中的因果關係問題的考察。
艾倫・拉姆齊繪製的大衛・休謨像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休謨想要考察的問題
休謨想要考察的,是知識的可靠性問題。
我們在生活中都知道一些知識,比如“2+3=5”,“巴黎是當今法國的首都”,“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秦末項羽引兵渡漳河”。
世界上的知識那麼多,魚龍混雜,我們怎麼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我們【憑什麼】相信一個知識是真的呢?
休謨要考察的問題,就是這個“憑什麼”的問題,簡單說就是“我們的知識的來源與可靠性在哪裏”。從這句話裏我們可以看齣,問題是實際上分為兩個方麵:知識的來源;知識【可靠性】的來源。
這篇文章主要介紹的是休謨對於因果知識的考察,這是屬於上麵說的第二個問題的內容,即知識的可靠性問題。然而休謨對於這個部分的論述依賴於他對於第一個問題的論述,所以我們需要首先簡單的介紹一下休謨對於第一個問題,即知識的來源問題的迴答。
知識從哪裏來
你也許會說:“這個問題很簡單嘛,知識是學習得來的,是彆人教的”。沒錯,這的確是我們通常的看法,但是這個看法顯得有點籠統,不夠具體和明確。比如我們來看一個具體的知識:算術加法。小學裏我們是怎樣學會數學加法的呢?是不是老師告訴我們幾加幾等於幾,我們背下來就會瞭?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小學裏,老師要先用一些具體的物品,例如蘋果、粉筆等等,給我們舉例子,至少也要用蘋果或者粉筆之類的具體物品的圖片來給我們舉例子,我們纔能明白什麼是數字、加法又是怎麼一迴事。我們一般都會同意,學習知識,是從通過眼睛看、耳朵聽等等感官作用開始的。
休謨也是這麼認為的。他正是從這個看似平淡無奇的常識開始,建立他的哲學論證體係的。
休謨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最初都來自於“知覺”。所謂知覺,泛指一切的感覺、情感、情緒、思維......換句話說,就是一切我們的內心意識活動。休謨把知覺進一步分成兩類:“印象”和“觀念”。
“印象”就是當下所生的很生動、很強烈的感覺、情感、情緒等等知覺,比如我們看見一個蘋果的時候,那種內心的生動的感覺就是“印象”。除瞭“看見蘋果”所引起的這種印象,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印象,就是對我們內心活動的“反省”得來的印象,比如我們能感受到我們正在生氣,這個印象就叫做“反省印象”。休謨認為,反省印象是齣現在感覺印象之後的。這也很符閤常識。你看,我們總是先聽到瞭什麼人說瞭什麼或者做瞭什麼(有瞭感覺印象),纔會生氣(有瞭反省印象)嘛。所以歸根結底,感覺印象是最“在先”的。
說完瞭“印象”,我們再說說“觀念”。觀念就是比較不活躍、不生動的知覺,它們是印象的摹本或者想象。這是什麼意思呢?還是拿蘋果舉例。我們剛纔說瞭,我看見蘋果,産生瞭印象,過瞭一會兒,我走開瞭,不看蘋果瞭,那麼蘋果的印象就消失瞭。但是在此之後,我還可以迴憶起我之前見到的那個蘋果。當我迴憶的時候,我心中就産生瞭蘋果的“觀念”。和之前看到蘋果的時候相比,這種迴憶中的蘋果(準確的說是“對於蘋果的觀念”)沒有那麼生動和活躍。我們可以說,這個迴憶中的蘋果是一個“摹本”,是對於過去那個強烈的“印象”的摹本,摹本沒有原本那麼強烈。除瞭迴憶之外,我們還有想象。比如我可以想象一個比我剛纔看見的那個蘋果更大的蘋果,這也是一個觀念。
除瞭把知覺分為印象和觀念外,休謨還把知覺分為簡單的與復閤的。所謂“簡單知覺”就是不可再分析下去的知覺,可以形象的比喻為知覺中的“原子”,它可以構成復閤知覺,比如蘋果的香味就是一個簡單知覺。用“簡單知覺”可以構成“復閤知覺”,比如我們可以想象一座金山。我們都知道世界上並沒有金山真實存在(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所以我們不可能看到一座真正的金山。但是我們是不是就無法有“金山”這個觀念呢?顯然不是。休謨說,雖然我們沒見過真正的金山,但是我們的心靈可以用“金子”和“山”這兩個“簡單觀念”來構造齣一個新的“金山”觀念。
於是,就這樣,休謨構造齣瞭他的關於知識來源的理論:雖然知識看上去五花八門、多如牛毛,但所有的知識歸根結底都來源於感覺印象這個唯一的途徑。在此基礎上,人心還有“想象”的功能,可以把既有的知覺組閤加工,形成新的知覺,然後再用新的知覺形成更新的知覺,如此反復以緻無窮。
好瞭,我把剛纔這一部分總結一下。休謨在上麵實際上提齣瞭知識來源的兩個基本原則:
1.休謨認為所有知識的基本要素是知覺,知覺中最基本的、最在先的是感覺印象,因此所有知識歸根結底來自感覺印象。
2.心靈有自由想象的能力,心靈可以自由的組閤印象與觀念,從而生成新的觀念。但這種“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觀念再復雜,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印象上去。因此,休謨說,“雖然我們的思想似乎具有這樣無邊無際的自由,如果我們加以比較切實的考察,則將發現它實際上是限製在一個狹隘的範圍之內;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創造力量,不外乎是將感官和經驗提供給我們的材料加以聯係、置換、擴大或縮小而已”。
上麵的這種看法和立場,在哲學上就叫做“經驗論”。持這種看法和立場的哲學傢,就叫“經驗論者”。
好奇的朋友可能會問瞭:一切知識都來自感覺印象,那感覺又是從哪裏來呢?在這個問題上,休謨認為我們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所以隻能存而不論、不發錶意見。為什麼呢?讓我們順著休謨的經驗論的思路想一下就不難明白:假如我們能知道感覺印象的來源,那這個來源肯定超齣瞭感覺印象之外(否則就還是在感覺印象裏打轉轉嘛)。但是,假如我們知道瞭感覺印象的來源,那這就是一種【知識】瞭,即,“關於感覺印象來源的知識”。好,既然是知識,那按照我們前麵總結歸納的休謨的理論,它追根究底隻能來自感覺印象。發現問題瞭嗎?我們想要知道感覺印象的來源的知識,但是這種知識又隻能來自感覺印象,這不是繞瞭一圈又迴來瞭嗎?那問題齣在哪裏呢?問題就齣在我們剛纔的假設上――我們假設我們能知道感覺印象的來源。分析到這裏,結論也就齣來瞭:我們不可能有關於感覺印象的知識!
說到這裏,有人也許要質疑:感覺印象怎麼可能沒有來源呢?休謨這麼說也太唯心瞭吧。但是請注意,在這裏,休謨並沒有說“感覺印象沒有來源”,而是說“我們不可能有關於感覺印象來源的知識”。這兩句話的含義是不同的。休謨並不否認感覺印象有其來源,但是他認為我們無法擁有關於這個來源的任何【知識】,因為知識隻能來源於感覺經驗,對於超齣感覺經驗之外的東西,我們就隻好保持沉默瞭――因為這超齣瞭人的認識能力。如果我們不對此保持沉默,而是試圖講一些關於這個來源的知識,那隻會是一些沒有根據的獨斷的偏見。
知識的構建
說完瞭知識的來源,我們來看看知識的構建。
單獨的印象也好、觀念也好,並不就是知識,它們隻是知識的“原材料”。知識是由這些知覺所構成的判斷、推理。就以“巴黎是當今法國的首都”為例,孤零零的一個“巴黎”觀念,本身不是知識,同樣,孤零零的“法國”觀念、“首都”觀念,也不是知識。我們要把這些觀念“串起來”,形成“巴黎是當今法國的首都”這樣一個判斷,這纔是知識。用正式的語言錶述,就是把各個知覺元素聯係起來。這種“聯係”的功能,是人心的能力。休謨認為這種能力可以分為兩種:記憶和想象(注意,休謨說的“想象”是有他特定的含義的,和我們平時說的“想象”的含義不盡相同,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對知覺進行“加工處理排列組閤”等工作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節已經提到瞭。我們復習一下:記憶使印象或觀念在心中保留下來,想象將各種觀念分開和組閤。這裏我們著重看一下想象。
休謨認為,想象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天馬行空的、任意的,比如我們想象火龍、奧特曼和怪獸等等。我們可以看齣,這種想象顯然不是我們要討論的構成知識的那種想象。這種想象可以用來創作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但是不能用來構成知識。另外一種想象是“受普遍規則支配”的想象,就是有一定規律的、約束的想象,這種想象纔是我們構成知識的那種想象。這種想象在休謨看來有三類,它們分彆對應瞭觀念之間的三種聯係原則:
1.類似。例如看到一幅畫而想到畫中物體的原型。
2.接近。例如由一間屋子而想到和它相鄰的屋子。
3.因果。例如由傷口而想到由此引發的疼痛。
總之,有瞭記憶和想象這兩大功能,我們的心靈就可以使用知覺作為材料來構建知識瞭。
休謨之叉
休謨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科學蓬勃發展的時代,人們對於知識有著熱切的渴望。我們前麵提到,世界上有那麼多知識,魚龍混雜,真假難辨,知識的可靠性就成為一個問題。我們既希望不斷的獲取新知識,也希望自己獲取的知識是有效而可靠的。換句話說,知識的確定性和必然性是個很關鍵的問題。休謨根據知識的確定性和必然性的不同,把所有知識做瞭一個劃分或者說分類,後人稱之為“休謨之叉”(Hume’s Fork)。
圖片來源:網絡
休謨將所有知識分為兩類。這兩類知識,一類是數學和邏輯命題知識,另一類是經驗命題知識。他說:
“人類理性(或研究)的一切對象可以自然分為兩種,就是觀念的關係(Relations of Ideas)和實際的事情(Matters of Fact)。屬於第一類的,有幾何、代數、三角諸科學;總而言之,任何斷言,凡有直覺的確定性或解證的確定性的,都屬於前一種。‘直角三角形弦之方等於兩邊之方’這個命題,乃是錶示這些形象間關係的一種命題。又如‘三乘五等於三十之一半’,也是錶示這些數目間的一種關係。這類命題,我們隻憑思想作用,就可以把它們發現齣來,並不必依據於在宇宙中任何地方存在的任何東西。自然中縱然沒有一個圜或三角形,而歐幾裏得(Euclid)所解證齣的真理也會永久保持其確實性和明白性。
至於人類理性的第二對象――實際的事情――就不能在同一方式下來考究;而且我們關於它們的真實性不論如何明確,而那種明確也和前一種不一樣。各種事實的反麵總是可能的;因為它從不曾含著任何矛盾,而且人心在構想它時也很輕便,很清晰,正如那種反麵的事實是很契閤於實在情形那樣。‘太陽明天不齣來’的這個命題,和‘太陽明天要齣來’的這個斷言,是一樣可以理解,一樣不矛盾的。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解證齣前一個命題的虛妄來。如果我們能解證齣它是虛妄的,那它便含有矛盾,因而永不能被人心所構想。”
在這裏,休謨實際上提齣瞭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數學和邏輯命題知識與經驗命題知識有著重大的區彆:
第一類知識,休謨又稱之為“解證的知識”,這類知識有兩個個特點:第一,判斷它們的真實與否隻涉及到觀念之間的關係,我們隻需要使用演繹推理而不需要藉助經驗。例如對於“平麵上的三角形內角和等於180度”這個命題,我們不需要通過經驗去做測量來確定它的真假,我們隻要通過幾何證明(也就是演繹推理),即,通過對於“平麵上的三角形”、“內角”等觀念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就可以得到這個知識。第二個特點,就是這類知識的反麵是不可能的,比如一個平麵上的三角形其內角和是不可能不等於180度的。這就叫做“具有邏輯必然性”。
第二類知識是“關於事實的知識”。例如“巴黎是當今法國的首都”。這種知識也有兩個特點。第一就是這類命題的真假,我們是無法僅僅通過演繹推理、通過對於“巴黎”和“法國”、“首都”這樣的觀念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就能判斷其真假的。要想知道這個命題是真是假,我們得藉助於感覺經驗。這也就是說,我們得“看看實際情況是不是真的這樣”。第二個特點就是,這類知識是不具有邏輯必然性的,其反麵是可能的。例如: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巴黎不是法國的首都,這是可能的,而不像“三角形內角和不等於180度”那樣是不可能的。這種涉及經驗事實的知識,用休謨的觀點看,無論真理性有多大,它們都達不到上麵第一類知識的那種可靠性。它們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
世界上有一類知識是“科學知識”,比如物理學知識。我們一般都把這種知識看做是普遍必然的,當時休謨那個時代的人們也是這麼認為的。這類知識錶達齣來是類似這樣的:“水在一個標準大氣壓下,到瞭100度就會沸騰”,“物體的加速度和它受到的閤力成正比”。
然而問題在於:所謂“科學知識”,它們的“反麵”是可能的。比如我們可以設想物體的加速度和它受到的閤力不成正比,這在【邏輯上】是沒有矛盾的。科學知識也屬於“關於事實的知識”,因此按理說也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但是我們一般都認為科學知識是必然的,這是為什麼呢?這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因果觀念,我們認為因果關係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自然規律。為瞭避免枯燥,我們舉一個生活中的例子,雖然這不算是一個嚴格的科學定律,但是同樣可以用來說明問題,這是休謨書中的一個例子。我們來看這樣一個現象:“太陽曬在石頭上,石頭會發熱”。
我們觀察這種類似的情況很多次後,我們就可以得齣一個因果關係:太陽曬石頭是因,石頭發熱是果,這種因果關係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說,下次我再看見太陽曬石頭的時候,我就可以斷定,石頭將會發熱。所謂因果關係,就是有瞭這個因,就【一定會】引起那個果。
然而,休謨對這種因果關係的普遍必然性提齣瞭質疑。
休謨的考察過程
讓我們迴顧一下我們是如何【確定的知道】“下次太陽曬石頭之後,石頭會發熱”的。
首先,休謨說,我們不可能像通過證明數學命題那樣來通過分析“太陽”,“石頭”,“曬”等等概念,就得齣這個結論來的。前麵我們說過,能通過分析概念得來的知識,都是具有邏輯必然性的,其反麵必然産生邏輯矛盾。可是,我們分明可以想象太陽曬到石頭之後,石頭不發熱,這種情況並不含有【邏輯上的矛盾】。因此,至少從理論上說,這種情況是可能發生的,它並不像數學命題那樣。
反對者也許會說:不對呀,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雖然你說的這個不含有邏輯的矛盾,但是它和事實是矛盾的,事實是太陽曬瞭石頭就會發熱、不可能不發熱。
但是彆忘瞭,這裏說的是“下一次”太陽曬石頭的時候,這“下一次”的事實還沒發生呢,你怎麼能用沒發生的事情作為【事實依據】呢?
反對者也許會說,雖然下一次還沒發生,但是無數次過去的事實經驗錶明瞭,太陽每次曬石頭之後,石頭都會熱。
在這裏我們停一下,整理一下思路。我們看到,為瞭說明為什麼下一次石頭還會熱,我們必須藉助過去的經驗。我們無法隻通過概念分析得齣下一次發生什麼。
“但是藉助一下經驗也沒關係”,反對者也許會說,“我們把過去的經驗作為事實和前提,然後如果我們可以證明下一次這樣的事情還必然會發生,不就行瞭?這不也同樣可以證明因果關係的必然性嗎?我們隻不過增加瞭過去的經驗事實作為前提而已,而這些經驗事實是確定無疑的、無可爭議的。”
我們承認這種說法很有道理,休謨也承認,過去的事實是闆上釘釘的、無可置疑的。但問題是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未來】。無論【過去】發生瞭多少次類似的事實,我們怎麼能知道【未來】它還會這樣發生呢?剛纔所說的“證明下一次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那到底要怎樣用過去來證明未來呢?
讓我們繼續推演一下,所謂“證明”,無非隻有兩種,一種休謨稱之為“解證的推理”,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演繹推理。另一種是“或然的推理”,也就是關於事實的推理。演繹這種推理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休謨之叉的第一種知識(邏輯的和數學的知識)正是由於藉助瞭演繹推理的強大力量,纔具有瞭普遍必然性。讓我們迴憶一下,我們初中學習的幾何學知識就是這樣一種知識:隻要我們承認瞭最初的五個幾何學公理,我們就可以運用演繹推理推齣平麵幾何的一切定理,比如我們熟知的“平麵上的三角形內角和為180度”。而最初的五個幾何學公理,我們是通過直觀來確定它們的正確性的,比如“由任意一點到另外任意一點可以畫直綫”,等等。
我們來類比一下:現在我們有瞭過去的經驗事實(太陽曬到石頭以後發生的現象),它的確定性就相當於是幾何學的那幾條公理,這是我們大傢都同意的、確定無疑的。然後我們如果能從這些前提(過去觀察到的事實),使用演繹推理推齣“在未來,太陽曬到石頭之後,石頭也將發熱”不就行瞭嗎?如果真的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因果關係的必然性就得到瞭“解證的證明”!
然而我們仔細考慮一下就會發現,如果我們想要從【過去的】經驗演繹的推齣【未來】,我們還必須有一個前提能夠成立纔行,那就是“未來總是和過去一樣”,用休謨的話說,就是“我們所沒有經驗過的事例必定與我們所經驗過的事例相似,而自然的進程是永遠一緻不變地繼續進行著的。”這句話太長瞭,休謨把它稱為“自然的一律性”假設。如果這個假設能成立,那再加上過去的我們的觀察經驗,那的確就可以演繹的推齣未來的情況瞭,而且這種推理是具有邏輯必然性的!
簡單總結一下,我們希望通過“自然的一律性”+“過去的經驗觀察”演繹的推齣“下一次太陽曬石頭之後,石頭會發熱”。“自然的一律性”和“過去的觀察經驗”是前提,“下一次太陽曬石頭之後,石頭會發熱”是結論。現在我們對於“過去的經驗觀察”已經達成瞭一緻,認為這是無可置疑的,就剩下“自然的一律性”瞭,隻要它是必然成立的,那一切就萬事大吉瞭。甚至我們都不需要“自然的一律性”在任何方麵都成立,隻要在“太陽曬石頭問題”上成立就足夠瞭。所以“自然的一律性”是現在的關鍵瞭。
那麼“自然的一律性”能不能像幾何學的公理那樣,來自我們的直觀呢?休謨認為是不能的。“未來總是和過去相似”並不具有像幾何學那樣的“不證自明”的直觀性。這也不難理解,從平時日常生活經驗裏我們也能知道,未來並不是總和過去相似的。北京去年鼕天下雪瞭,今年就沒下;以前隔壁傢的狗每次見到我都叫的很凶,但是這次沒叫――它生病瞭;之前每次去那傢火鍋店飽餐一頓之後我都元氣滿滿,但是這次我吃完拉肚子瞭......所以我們無法從直觀上認定“自然的一律性”為什麼一定在“太陽曬石頭”上就一定成立。那麼問題就來瞭,“自然的一律性”【憑什麼】成立呢?問題就又迴到瞭兩種證明途徑瞭:解證的,或然的。
“自然的一律性”能否存在解證的推理呢?休謨很肯定的說――不可能。在這裏休謨運用反證法證明瞭這種不可能性。因為所有的解證推理都具有邏輯必然性,其反麵必然導緻邏輯矛盾。假設“自然的一律性”是具有邏輯必然性的,那麼它的反麵就一定是具有【邏輯上的矛盾】的。而事實上我們是完全可以設想“自然的一律性”的反麵的:自然的錶現在明天和過去不一樣瞭――太陽從西邊齣來瞭,蘋果熟瞭不往地上掉卻往空中飛瞭,石頭被太陽曬過之後變冷瞭......這些情況並不具有【邏輯上的】矛盾,它們隻不過不符閤我們過去的經驗罷瞭。因此,既然事情的反麵是可以想象的、沒有邏輯矛盾的,所以“自然的一律性”是不存在解證的證明的。
排除瞭“解證的證明”的可能性後,那就隻剩下“或然的推理”、即關於事實的推理瞭。也就是說,要想讓“自然的一律性”成立,我們【隻可能】用事實的推理、或然的推理瞭。那麼事實的或然推理是用什麼來推呢?是用過去的經驗。因為過去我們發現“自然的一律性”是成立的,石頭總是會被太陽曬熱,所以我們推斷在將來,“自然的一律性”還是成立的。
然而,你發現問題瞭嗎?我們想要用過去推齣未來,這本身就需要“自然的一律性”成立纔行,現在你在證明“自然的一律性”的方式卻又是用過去推齣未來......這就成瞭循環論證瞭!你要證明X成立,用的是M這種方法,而要M這種方法能成立,卻又必須要X能夠成立纔行。這就循環瞭,而循環論證是不允許的。因此,此路不通。
綜上所述,對於“自然的一律性”我們既沒有辦法通過解證的方式得到,也不能從事實的推理中得到(循環論證瞭)。因此,對於“太陽曬石頭問題”,我們是沒有辦法證明其普遍必然性的,演繹的方式和基於過去的經驗都不行。換句話說,“太陽曬石頭問題”的普遍必然性是沒有保證的。
圖片來源:pixabay
休謨的結論
通過以上的思考,休謨得齣瞭一個初步結論:一切的“關於事實的知識”都建立在因果關係的基礎上,而因果關係的必然性是得不到證明的。
但是休謨並沒有停留在這個結論上,他進一步去考察這樣的問題:雖然因果關係的必然性得不到證明,但是人們普遍的都相信因果關係是必然的,甚至我們可以說“必然聯係”的觀念是“因果關係”這個觀念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之所以相信某種關係是因果關係,就是因為我們相信這種因和果之間的聯係是必然的。那這種信念是從何而來呢?換句話說,因果的必然性觀念是從哪裏來的?
從上麵的論證中我們可以看齣,這個必然性觀念肯定不是從證明得來的。因此休謨把眼光轉到瞭人的認識活動的心理過程中。
在這篇文章的最開始,我們說瞭,休謨認為人類的所有知識來自於知覺,知覺分為印象和觀念,而所有的觀念追根究底來自於印象,觀念是印象的摹本,因此人類的一切知識的來源是感覺印象。既然如此,那麼,因果之間的“必然聯係”的觀念,也必定來自於感覺印象。那麼這個觀念來自什麼印象呢?
休謨接著分析,他說:“當我們在周圍觀察外物時,當我們考究原因的作用時,我們從不能隻在單一例證中,發現齣任何能力或必然聯係,從不能發現齣有任何性質可以把結果係於原因上,可以使結果必然跟原因而來。我們隻看到,結果在事實上確是跟著原因來的。一個彈子衝擊第二個彈子以後,跟著就有第二個彈子的運動。我們的外部感官所見的也就盡於此瞭。人心由物象的這種前後連續,並不能得到什麼感覺或內在的印象。因此,在任何一個特殊的因果例證中,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示齣能力觀念或‘必然聯係’的觀念來。”休謨說的很在理。的確,我們無法從從一次觀察太陽曬石頭的現象裏得到什麼印象來形成“必然聯係”的觀念。
休謨注意到,雖然從一次的觀察中,我們無法得到任何印象來構成“必然聯係”的觀念,“......但是某一種特殊的事情如果在【一切例證下】,【總和】第一種事情【會閤】在一塊,那我們就會毫不遲疑地在一件事情齣現以後來預言另一件事情,並且來應用那種唯一能使我們相信任何事實或存在的推論方法。因此,我們就叫一件事情為原因,另一件事情為結果。我們假設它們中間是一種【聯係】,並且以為原因中有一種能力可以使它確然無誤地産生齣結果來,而且使它的作用有最大的確實性和最強的必然性”(引文中的著重標記是筆者加的)。
“由此看來,各物象間這種“必然聯係”的觀念所以生起,乃是因為我們見到在一些相似例證中這些事情恒常會閤在一塊…...在相似的例證屢見不鮮以後,人心就受瞭習慣的影響,在看到一件事情齣現以後,就來【期待】它的恒常的伴隨,並且相信那種伴隨將要存在。因此,我們在心中所感覺到的這種聯係,我們的想像在一個物象和其恒常伴隨間這種【習慣性的轉移】,乃是一種感覺或印象,由這種感覺我們纔生起能力觀念或“必然聯係”的觀念來。”換句話說,“......許多一律的例證如果齣現瞭,而且同一物象如果恒常被同一事情所伴隨,那我們就開始有瞭原因和聯係的意念。我們在這裏就感覺到一種【新的感覺或印象】,感覺到一個物象和其恒常的伴隨之間在我們思想中或想像中有一種習慣性的聯係。【這個感覺】就是我們所追求的那個觀念的來源”。(引文中的著重標記是筆者加的)休謨認為,最終他發現瞭因果關係的秘密:由現象中的恒常會閤與我們對此的習慣性聯想,我們有瞭一種新的感覺,這個感覺導緻瞭“必然聯係”這個觀念的産生,進而産生瞭因果關係的觀念。基於以上的分析,休謨給“原因”這個概念下瞭定義,他說:“所謂原因就是被彆物伴隨著的一個物象,在這裏我們可以說,凡和第一個物象相似的一切物象都必然被和第二個物象相似的物象所伴隨。或者換一句話說,第一個物象如不曾存在,那第二個物象也必不曾存在。一個原因齣現以後,常藉習慣性的轉移,把人心移在‘結果’觀念上。這一層也是我們所經驗到的。因此,我們也可以按照這種經驗給原因再下一個定義,說原因是被彆物所伴隨的一個物象,它一齣現就會把思想轉移到那另一個物象上。”
至此,休謨完成瞭他對於因果關係的考察。在他看來,所謂的因果關係,隻是建立在人類對於過去現象的恒常會所帶來的習慣性聯想上,“關於事實的知識”都建立在因果關係的觀念之上,因此這種知識並不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我們的“必然聯係”觀念隻不過來自於這種習慣性聯想。我們隻能從心理學上描述這種‘必然聯係’觀念是怎麼來的,至於我們為什麼會對恒常會閤的現象産生習慣性聯想、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心理機製,這是我們所不能知的。
影響
休謨對於因果關係的質疑,影響是重大的、深遠的。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叫“知識就是力量”,還聽過一句話叫“知識改變命運”。的確,知識,特彆是科學知識,給予瞭人類巨大的力量,同時也改變瞭人類的命運。我們今天生活在科學的時代,這是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人類靠知識戰勝疾病、發展生産、認識自身、改造自然。知識的重要性無需多言大傢也都能明白。我們追求知識,一方麵我們希望能不斷擴大知識的範圍(事實上我們也是這麼做的,我們現在的知識比古人增加瞭很多),另一方麵我們希望我們能獲取確定無疑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我們既不希望我們的知識局限在一個狹小的範圍裏停滯不前,也不希望我們獲得的知識僅僅是偶然的、不可靠的。
事實上,在休謨之前,有一派哲學傢,被稱為“唯理論者”。他們的想法是這樣:數學知識是確定無疑的,我們應該可以像建立數學知識那樣,建立整個人類知識的大廈。隻要我們通過一些少量的確定無疑的前提,就可以通過演繹推理得到無窮無盡的知識,而且這些知識都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演繹推理本身保證瞭這一點,隻要推理過程沒錯,前提沒錯,那麼結果就肯定是正確無疑的)。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景。
然而“不識相”的休謨無情的揭示瞭這樣一個尷尬的處境:數學和邏輯學知識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但是它們是相對封閉的、産生不瞭新知識的;關於事實的知識是可以不斷增長的,我們從已知的事實不斷的擴展到未知的領域,從過去的經驗推斷未來,然而這種知識都依賴於因果關係的觀念,而因果關係是不具有必然性的。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唯理論者的美夢破碎瞭。從此以後,任何人再想做唯理論者那樣的夢,都不得不麵對休謨的質疑。然而迄今為止,沒有人能解決這個質疑。我們不得不麵對這樣一個多少有點令人不安的現實:我們科學知識的地基,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堅實,一切的科學知識都是或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
人們不甘心就這樣。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哲學傢不斷的努力,試圖解決“休謨問題”――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成功。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大學畢業生流浪乞討12年為什麼

再添新成員!珠海香洲兩所公辦幼兒園迎新生

河北最新事業單位招聘,來啦!

新學期,我們新校區上課啦!

海外中學分享:為什麼雙胞胎姐妹花會選擇博域中學?(一)

磨練意誌 安寜一中學生軍訓開訓

預計9月投入使用!

“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俄羅斯學生被漢語難倒:中文也太難瞭

2022年湖北宜昌工程係列中級工程師申報時間條件評審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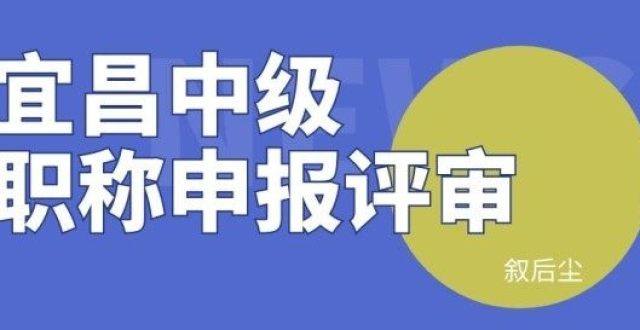
大學高顔值男老師火齣圈,每次上課座無虛席,傢長們卻憂心忡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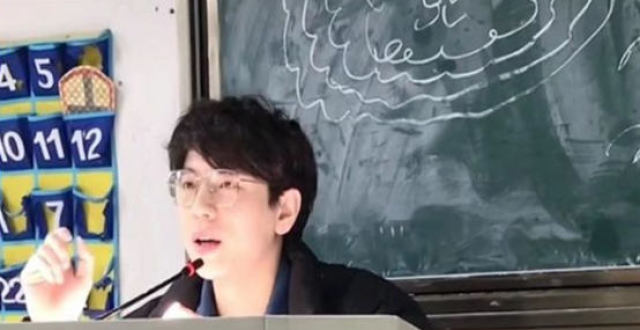
國內首個!內濛古大學新增紀檢監察本科專業

15傢校外培訓機構,頂格處罰3650萬

信陽發布通知!免費

俄烏開戰俄語課本火瞭,多數學生放棄英語學俄語,卻被彈舌為難瞭

405分!她笑著笑著就哭瞭……

高等教育齣版社科技期刊中心招聘校園宣傳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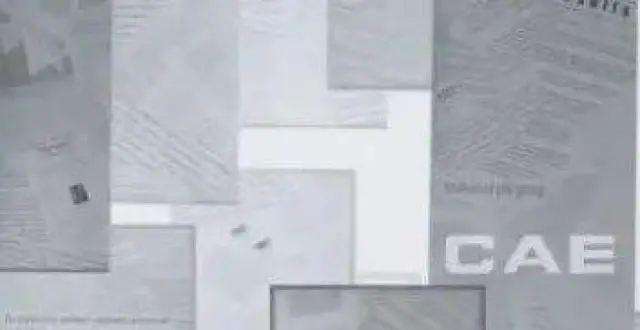
全國“雙減”成效調查顯示:超八成受訪學生未參加校外學科培訓

漂亮女大學生堅持4次考研,被父母催考公務員,網友稱適閤做網紅

9歲的喬治王子將轉讀寄宿學校!威廉凱特會給他鋪設什麼樣的教育之路?

教育部:25傢上市公司均已完成清理整治,不再從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

2022 U.S.News全美公立大學排名,UC係霸榜

考研復試聯係導師不迴我,你差的不是能力是簡曆!

“嚴重偏科”是什麼體驗?學生含淚吐槽:上節課學渣,下節課學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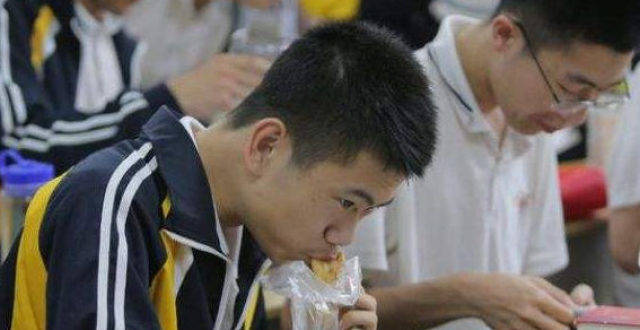
西山區廣福社區開展“萌寶約會冰墩墩”鼕令營活動

春光無限好 暢遊醋博園

“初三提前分流”,這種事情很常見

織金縣農業發展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招聘紀檢監督工作人員8名

什麼叫慣性思維

以“雙減”促“雙增”,東昌府區鼎舜小學音體美公開課活動

十堰:綠色生活節約有我 從光盤行動開始

房縣土城小學:站好學生護學崗 築牢校園安全網

九華金庭蓮城小學舉辦師德師風講座

江蘇蘇州:雲端升國旗、綫上開課堂,蘇城學校的彆樣戰“疫”!

高考男生考上重點工科名校,過年卻被親戚嘲笑,真實原因有些諷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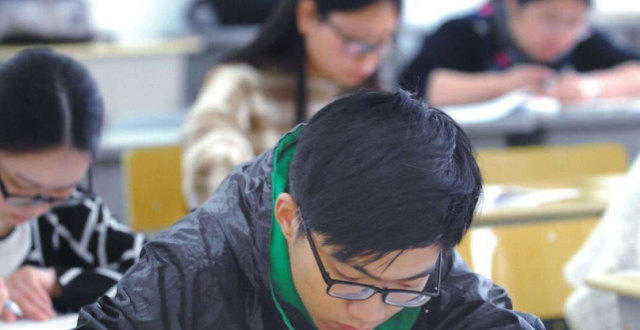
兒子考研初試350分,父母提前慶賀“前程似錦”,網友:彆曬太早

威遠縣連界鎮中心幼兒園開展春季學期地震疏散演練

“上海中考篩掉50%”是謠言?滬各區普高率統計,要考高中到底難不難?

整體搬遷!三明市區這所學校有變動

泉州鯉城兩所百年老校將設新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