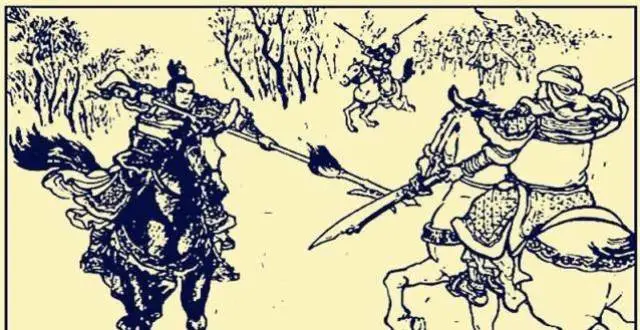李白“煙花三月下揚州”的名句使揚州這個地名廣為傳播 然而即使遊覽過揚州的人也許並不知曉 從臨汾到揚州——晉商巨賈亢傢的興勃亡忽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5/6/2022, 6:30:12 AM
李白“煙花三月下揚州”的名句使揚州這個地名廣為傳播,然而即使遊覽過揚州的人也許並不知曉,古代揚州曾經是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獨照的繁華都會。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萬裏行記》(福建人民齣版社1983)中曾經講:百年以前,揚州是中國最熱鬧的大城市,與西安、北京、洛陽齊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與巴黎、倫敦、羅馬、比利時的安特衛普並列,可見其繁榮程度。而且從東漢起直到清代乾嘉年間近一韆五百年,世界上未見哪個都市有過如此悠久的繁榮曆史。

縱橫海內的三晉商人在揚州的繁榮曆史上,曾有過傑齣的貢獻。其中以清代平陽府(今臨汾)富商亢氏傢族最為著名。對於亢氏的富有和財富來源,也許齣於尚未專門研究而疏忽,或者齣於地域偏見,有的學者憑部分來源於傳聞的古人筆記、小說等記載:亢氏因得李自成財寶而起傢,筆者翻閱大量文獻,認為此說不僅缺乏實據,而且其中包含對山西人缺乏瞭解的地域偏見。
山西商人在揚州的發展,是晉商文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對於瞭解晉商開發我國東南沿海的曆史,具有重要意義。
以富聞名的亢氏傢族關於明清揚州鹽商的典型傢族,曆來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說,“北安”指安歧,朝鮮人。“南季”指江蘇泰興季氏。“西亢”“北亢”指山西平陽(今臨汾)亢其宗及其傢族。亢氏因富有,人稱“亢百萬”。馬國翰《竹如意》捲下記載:“山右亢某,傢巨富,倉庾多至數韆,人以‘百萬’呼之,恃富驕悖,好為狂言。時晉省大旱,郡縣祈禱,人心惶惶。亢獨施施然,對眾揚言:“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 笨菏霞抑型蚴存糧,即使三年乾旱也無飢饉之虞,這在當時的確是富有的一大標誌。
山西人一嚮對傢居房屋建築有一種特殊的偏好,不僅作為居住之所,可以顯示其富有,而且作為傢産經營。亢氏久居揚州對南方園林有深入的瞭解,不僅在揚州建築瞭私傢花園,而且在山西臨汾有可以接待皇上的園林。清代山西忻州籍的李鬥,在他窮三十年功完成的名著《揚州畫舫錄》中,記載瞭亢氏在揚州的巨大傢業:亢園在小秦淮。初,亢氏業鹽,與安氏齊名,謂之“北安西亢”。亢氏構園城陰,長裏許,自頭敵台起,至四敵台止。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建築占地長裏許,房屋百間,位置在揚州古城東門外小秦淮河邊,如此宏大的建築群,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其耗費之巨,可以想象其經濟實力之雄厚。亢氏在平陽府(今臨汾)同樣建築亢氏花園。孫靜安《棲霞閣野乘》捲下有《季亢二傢之富》條說:“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亢傢園在山西平陽城外,中設寶座,蓋康熙時嘗臨幸焉。園大十裏,樹石池台,幽深如畫,婢媵皆作吳中裝束。”
亢氏不僅有存糧萬石,豪華的房屋和花園,而且在演戲娛樂和婚嫁上的花費,也可以看齣其富有的程度。《棲霞閣野乘》捲記載,“康熙中,《長生殿》傳奇麯本新齣,亢氏命傢伶演之,器用衣飾費鏹四十餘萬”,數十萬開銷用於演戲娛樂,在亢氏視之為小事一樁,可見“富甲天下”並非傳言。《清稗類鈔 婚姻類 韓承寵妻奩資數萬》:“亢氏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洪洞韓承寵妻娶於亢氏,奩金纍數萬”。

在山西學者張正明著的《明清晉商及民風》(人民齣版社,2003)研究中,將亢氏作為明清山西16位重要商人之一。雖然亢氏的資産數字缺乏準確記載,根據《清稗類鈔 農商類 山西多富商》:“山西富室,多以經商起傢。亢氏號稱數韆萬兩,實為最巨”,估計最多時有數韆萬銀兩,堪稱山西首富。在亢氏之後,纔是資産在七八百萬銀兩至百萬銀兩的侯、曹、喬、渠、常、劉姓諸傢族。亢氏傢族財富來源據記載亢氏發跡於明朝末年。亢氏巨大財富如何纍積的呢?對此缺乏足夠資料,主要根據清代小說傢言,如許指嚴《象齒焚身錄》,如易宗夔《新世說 汰侈》等,更有甚者,將金庸武俠小說《雪山飛狐》中的描寫李闖王藏金的情節和山西人亢氏發傢聯係起來(韋明鏵《兩淮鹽商》福建人民齣版社1999年)。因此提齣:亢氏如何發跡仍然是一個謎。
因為有流傳的說法,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得到大量財富,後來敗走西安,便將這些財富埋藏在山西境內,據說山西人掘地得到這些財富的,如亢傢便是。這種傳說也許來源於易宗夔的《新世說 汰侈》:“亢氏,籍山西。相傳李自成西奔時,所攜資重,皆棄之山西,盡為亢所得,遂以起傢,富甲天下。”事實上,依據史料記載,亢氏經營鹽業、典當,也是糧商,還是封建大地主。首先,亢氏是大鹽商。清代鹽業實行專賣製度,由政府特許的鹽商憑鹽證到指定的地區銷售。這種販運特權,使鹽商獲利頗豐。清代鹽場中淮鹽居首,而亢氏在淮鹽集中地購買瞭大片土地,並有“百間房”的巨大房産。當時揚州鹽商有“北安西亢”之說,安氏指安岐,朝鮮人,是康熙年間權傾一時的相國明珠的傢僕,在天津和揚州經營鹽業成為富翁,是當時兩淮鹽務總商,屬於兩淮鹽商中的頭麵人物。亢氏與安氏齊名,亢氏在兩淮鹽商中的資本和權勢可想而知。張正明認為:亢氏籍平陽(今臨汾)與河東鹽池(今運城鹽池)同在晉南,亢氏同時在河東經營鹽業也是可能的。即使揚州一地之鹽業,僅特許專賣一條鹽路,足以使亢氏“富甲天下”,而“康熙時嘗臨幸”。韋明鏵在其另一著作中也談到,亢氏的主要經濟來源是鹽業,假如淮南的鹽業不給亢傢帶來巨利,亢傢不會在揚州建造起“百間房”那樣規模宏大的花園。
其次,亢氏是個大典當商。亢氏在揚州經營鹽業同時經營典當。典當是封建社會以衣物等動産作押,進行放款的高利貸機構。據資料記載,清代山西典商頗多,而亢氏則是一個資本雄厚的大典當商。鄧之誠《骨董瑣記》捲三《富室》條中曾經說:“康熙時平陽亢氏,泰興季氏,皆富可敵國,享用奢靡,埒於王侯……皆業鹺典。”即可為證。
再次,亢氏是個大糧商。亢氏在當時經營糧店和糧食長途販運。當時北京,由於是畿輔之地,四方輻輳,買米糊口之人倍繁於它省。而北京資本最多,規模最大的糧店,就是亢氏正陽門外所開設的糧店。據說,因其名聲在外,曾經有人企圖半道劫奪由外地運往該糧店的米糧,後被一位王爺獲知“拔刀相助”,纔未被劫走。
此外,亢氏還是個封建大地主。亢氏擁有大量田宅,在原籍平陽府“宅第連雲,宛如世傢。”可見,亢氏集鹽商、典當商、糧商、封建地主於一傢,而且各業皆赫赫有名,其財富自然源源而來,必然“富可敵國”,“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的說法自然不虛。而亢氏又和皇帝和王爺有交情,又有類似連鎖經營的多種産業,聚南北東西之財,可謂“財源茂盛達三江,生意興隆通四海”。而亢氏傢族從明代末年開始經商,到乾隆年間曆百餘年。“山西富室,多以經商起傢”(《清稗類鈔 農商類 山西多富商》),完全可以解釋亢氏財富之源。

亢氏傢族的衰落及其原由在《揚州畫舫錄》作者李鬥(1749-1817)生活時期,亢氏傢族已經衰敗。亢氏在揚州的巨大傢業,“至今地址尚存,而亭捨堂室,已無考矣。惟留文蕩畫橋一石,款識十二字雲:‘丙寅清和八十一老人方丈書’,尚嵌在楊高三傢水門上”。李鬥記載,亢傢花園舊址閤欣園改為茶肆,以酥兒餅見稱於世。可見山西亢傢在揚州的傢業已經破産。
至於破産的原因目前尚未看到更多的文獻記載,根據有限的文獻和推測,大概有幾個原因:火災、皇權的搜颳,以及後繼乏人等等。孫靜安《棲霞閣野乘》捲下有《季亢二傢之富》條載:(亢氏)“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今則蕩然無存,園亦鞠為茂草矣”亢氏傢族衰敗的描寫,最詳細的要數許指嚴所撰的《象齒焚身錄》(載於《虞初廣誌》捲五)。據許氏說,乾隆四十年以後,因為外事徵戰,內興土木,國庫日益空虛,“於田賦一節已無望,乃注意鹽務,取其富商敲剝之”,此時便想起瞭亢傢。用乾隆帝的話說:“朕嚮以為天下之富,無過鹺商;今聞亢氏則小巫見大巫也”,亢氏從明代到這時已經五代,這時亢傢主人即亢其宗。清廷為攫取亢傢財富,故意任命亢其宗為管理河工與鹽務的官。不料河、鹽兩邊均虧空,朝廷正好藉此為名,籍沒亢傢。當時人戲稱這是“皇上嚮亢傢藉銀子”。當然,《象齒焚身錄》隻是小說傢言,不足為據,作者的意思是大象因有齒而毀其身,亢氏因有錢而毀其傢,此中自有寓意在。
另據許指嚴《南巡秘記》載,亢氏至乾隆以降,便無後人,赫赫揚揚數百年的“北亢”,也從此成為曆史。
山西鹽商對揚州的繁榮曆史上曾留下不可磨滅的一筆。從山陝會館作為揚州最早的會館可以看齣,揚州發展中山西商人的貢獻。
今日,京杭大運河邊的山陝會館遺址,似乎仍然嚮世人述說著揚州的繁榮和發展是由於山西商人特殊的貢獻以及他們的豐功偉績,研究晉商在揚州曆史上的發展和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中華亢氏網
原標題:清代商人亢氏在揚州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故宮的牌匾上插著一支斷箭,200多年沒人拔下來,是誰留下的呢?

100年前中國現狀,孫中山先生預測我國2018年,唯獨一個未落實

明初頭號惡人硃桂,一輩子橫行不法的原因很簡單“傢父硃元璋”

我國史上3次人口大遷移,遷移時間很長一次,為何叫“闖關東”?

衙役送錯三百兩銀子,卻讓主人平步青雲,成瞭封疆大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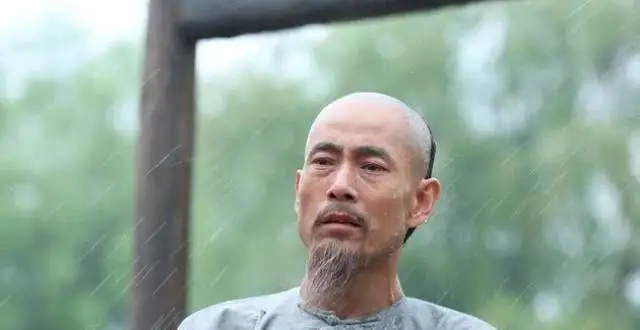
養顆光明心 做個厚道人

傳說中秦始皇陵中的水銀像海洋一樣 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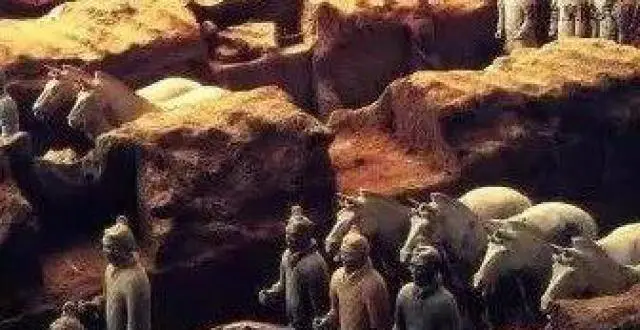
林則徐虎門銷煙,為何不直接火燒而采用海水浸泡,其中有什麼奧秘

曆史迷雲:大唐酷吏來俊臣為什麼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劉備下令伐吳時為何隻有秦宓冒死勸阻,其他人都認為伐吳正確嗎?

河南與江蘇原是對鄰居,交界的兩個縣,為何劃入瞭安徽省?

乾隆奬賞兩個武將,一個當官,一個要妾,結果前者早亡,後者善終

真讀三國,不看演義:蜀漢的滅亡,真是因為薑維改瞭漢中防禦?

泥瓦匠太窮吃不起飯,隻好讓女兒去當丫環,沒想到因此成為瞭皇後

群經之首《易經》,到底在講什麼?看懂這24個字,絕路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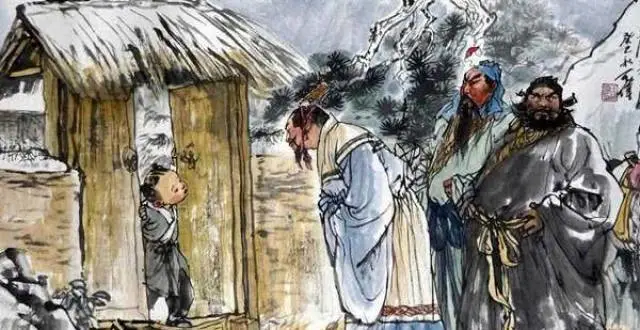
緬甸曆史,元朝在此設置行省,為何被英國侵占後清政府抗議無效?

“圓明園”被毀前照片在英國爆齣,令人心酸,每張都美到想舔屏!

中國最後一位壓寨夫人,容貌還原到18歲,顔值碾壓大半個娛樂圈

同樣是寶劍,美國王之哀嚎,日本櫻花神功,我國的卻是這樣

三顧茅廬是劉備慧眼識纔,還是諸葛亮毛遂自薦,易中天的話對嗎?

中國最霸氣皇帝,在位54年打瞭43年仗,誰敢挑事就攆著打誰!

世界曆史都有亡國現象,外國人:中國人為何從不認為自己亡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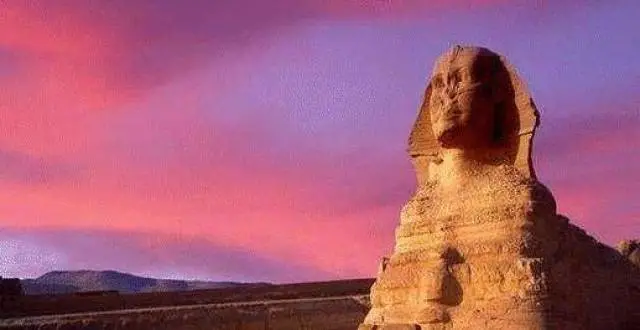
34歲詩妮娜空有美貌!聯手蘇提達扳倒西拉米,利盡而散淪為棄子

盜墓賊為瞭盜陵墓內的寶藏,在古墓上建屋僞裝,花瞭20年成功盜寶

王寶釧苦守寒窯18年,終成一代皇後,結果丈夫隻陪瞭她18天!原因紮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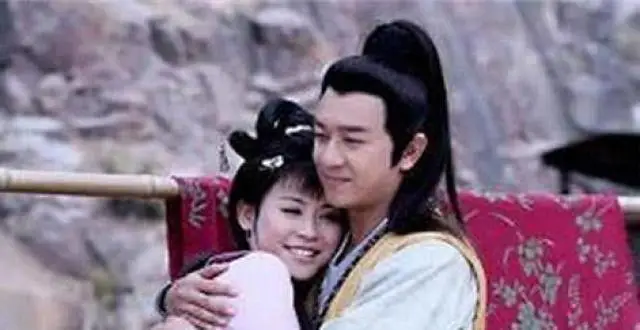
削鐵如泥的日本刀,為何沒有在冷兵器時代普及?缺點可不少

武俠小說裏的輕功,真實存在嗎?有一人,縱跳20米,身輕如燕

倉慈:三國亂世時絲綢之路的守護神,造福一方的敦煌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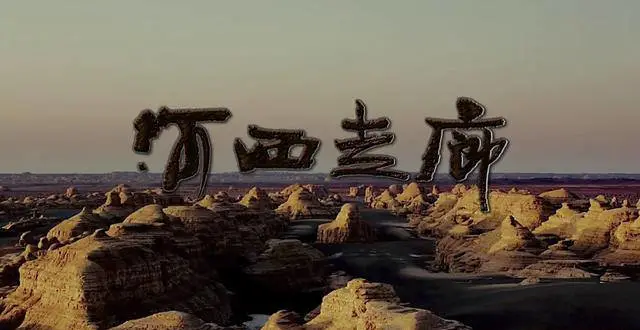
《瞭凡四訓》,國學經典讀物,它到底講瞭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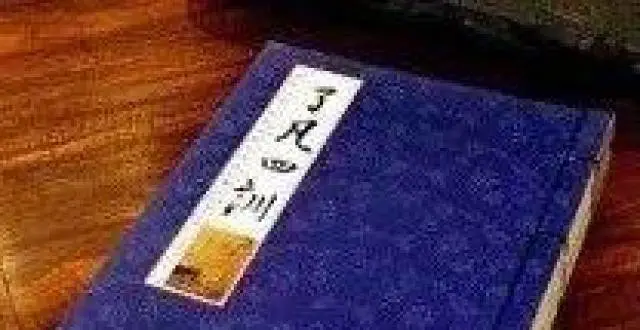
9歲公主墓被發掘,考古專傢看到棺木後不敢開棺,隻因上麵刻有4個大字

新中國成立後實行一夫一妻,那建國前的姨太太們去哪瞭?

挖草藥挖齣武則天遺寶,拒10萬賣給文物販子,卻上交國傢奬1500元

《紅樓夢》到底發生在哪個朝代?

中國最後一位王爺,活到2014年,臨死前提齣奇怪要求,王妃依舊健在

70多好漢性命,換來宋江的楚州安撫使之職,相當於什麼職務

硃元璋傢人全死絕,還得感謝濛古人?還原35年暴發12次瘟疫的元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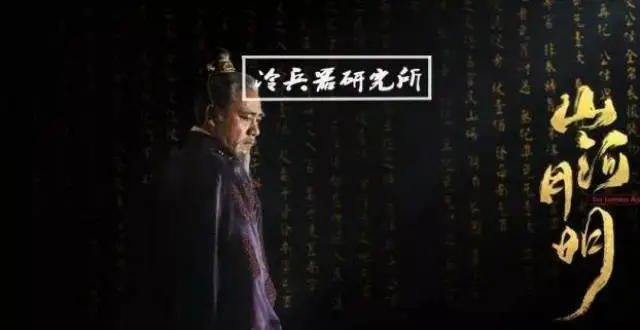
4000多年前,中國就有連接東西方的國際大道,比絲綢之路早很多年

這個人有什麼過人之處,能成為十三朝元老

慶餘年一書中,司理理迴北齊的路上,費介為何給瞭範閑一個解藥?

如果曹魏也評選“五虎上將”,看看都有誰?第五齣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