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西方來說契約是個貫穿生活始終的東西 建立瞭契約就要按照約定去完成。但是西方人對待契約的態度和東方人對於“守信”的看法並不全然一緻。例如全知全能的上帝為什麼要和柔弱無力的人類立約而不是直接降下神諭… 契約精神是怎麼來的,它又是如何成為西方社會的基礎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1/2022, 6:03:58 AM
對於西方來說契約是個貫穿生活始終的東西,建立瞭契約就要按照約定去完成。但是西方人對待契約的態度和東方人對於“守信”的看法並不全然一緻。例如全知全能的上帝為什麼要和柔弱無力的人類立約而不是直接降下神諭;為什麼浮士德與撒旦立約後,上帝也無法乾涉並撕毀……
某種程度上,西方人將契約視為人不可或缺的一種精神信仰。
西方的契約最早誕生於古希臘時期。希臘特有的地理環境 -- 多山丘、少平原,而且土地貧瘠,所以古希臘諸城邦並沒有發展農業文明的自然條件,不過希臘人為什麼又沒變成通過掠搶來補充自身需求的遊牧民族呢?
一個重要原因是海洋。
地中海雖然是個內海,風浪無法與外洋相提並論。但是在生産水平和能力極低的古典時代,這也不是人類可以隨意穿行的池塘。換句話說從成本上古希臘人就不具備以掠搶來維持自身生存的條件。
因此為瞭更為有效地獲取所需的資源,希臘就發展齣瞭依托手工業和地中海沿岸國傢貿易換取資源的古典工商業文明。但是依靠什麼來維持貿易的穩定呢?
這個時候武力反而成瞭障礙,因為強大者可以保證自己每次交易都最大獲利,但是他不能保證被交易者不逃跑老老實實等著他來再次交易。
哲學傢亞裏士多德提齣瞭一個理念 �C 交換正義 。亞裏士多德認為在交換中除瞭需要誠信之外,還要確保所有參與主體的利益。實現這一點的基礎就是交換過程中不損人利己,這種平等的貿易可以保證交換的持續。
由此基於 交換正義 的契約拉平瞭交易者之間實力的差異,從而讓交易各方能主動且自發的參與貿易,也讓平等理念開始成為一種思想被人們所接受。
這種平等為基礎的契約給希臘工商業文明帶來的興盛,也讓契約在整個地中海區域被普遍接受並盛行開來。在這種環境下摩西在西奈山代錶以色列人與上帝建立永久的契約,而不是跪接上帝恩賜的法旨就不是什麼不能理解的事情瞭。
羅馬徵服整個地中海地區後,由於廣泛的和平,讓各地區之間的貿易發展到瞭一個全新的高度。為瞭加強內部的管理、快速處理糾紛,以及應對律法無法將各類情況都一一羅列,羅馬將契約融入進瞭法律。
羅馬人認為契約是 由於雙方意見一緻而産生相互之間法律關係的一種約定 。從而將遵守契約從守信的道德要求,更進一步提升為必須遵守的律法要求。另外由於羅馬的徵服,基督教也在整個地中海地區發展壯大,並逐步代替羅馬多神教,最終成為羅馬的國教。
基督教原本脫胎於猶太教,所以基督教也繼承瞭猶太教的基礎,神和人之間的契約關係。《聖經》分為《舊約》和《新約》兩大部分,雖然曆史上相關的版本無數,具體內容也互有差異,但是其中的“約”是契約這個意思一直未變。
因此隨著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推廣和盛行,契約觀念也進一步地滲入西方人的行為和生活。
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方步入黑暗的中世紀。由於再無一個勢力能像羅馬一樣建立起大一統的帝國,分裂以及戰亂導緻社會經濟實際上是在倒退。為瞭在低經濟水平下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土地,西方進入以“采邑製”為政治主體的封建時代。
“采邑製”是領主(君主)把土地分封給手下的貴族,貴族再將土地嚮下分封給自己手下的貴族或傢臣,而獲取封地的封臣可以基於血緣將自己的封地傳承予自己的後代繼承。這樣一級級的分封直到最底層的農民為止。
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次分封土地實際都是訂下契約,封臣在獲取土地利益的同時也意味著他接受對應的義務。封臣必須按照約定嚮領主繳納稅款、上繳貢物,在戰爭時期響應領主的徵召等等。
封臣如果不遵守契約,領主可以懲罰封臣或者沒收封臣的領地。同樣在封臣遵守契約的情況下,領主則無權直接乾涉封臣對其領地以及臣民的治理。更重要的是封臣可以正當地迴絕領主提齣的契約之外的要求。這也是西方的君主們在威權上一直弱於同方的同行的原因。
維係這一製度穩定的關鍵就是彼此對於契約的遵守,因為此時血緣隻能決定某個人將會繼承何種權力,但是血緣無法讓這個權力被保障。
為瞭維護社會關係的穩定,這時de 契約又被賦予瞭新的含義。
托馬斯・阿奎那等思想傢為古希臘的德性思想增加瞭一層神性意義,提齣瞭全新的“德性論”。這種新思想中,守約不但是一個人的道德義務和這個人為自己定下的法律,它也是每個人在人間遵從上帝的約定,踐行上帝的觀念。因此每個人隻有履行自己的承諾,纔符閤正義的德性,纔能真正稱為上帝的子民。
油畫 聖托馬斯阿奎那的典範
在中世紀那個神學統治、約束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時代,這種“德性論”將宗教融入進瞭契約,在普通的道德和法律之外,為契約增加瞭更高層次的道德約束。宗教的加持,讓是否遵守契約成為判斷一個人德性的重要依據,也讓契約精神更加地深入人心。可以說中世紀的社會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契約來維係的。
注:這個有些類似我們古代,一個人倘若“不孝”無論他能力如何,做過什麼,都會被整個社會所不容以及排斥。
這也是為什麼西方曆史以及傳說裏有很多王室血脈隔瞭幾代還能復國、遺腹子復仇重新獲取爵位的故事,而東方自戰國以後就不再有類似的事跡瞭。
歐洲文藝復興結束黑暗的中世紀後,宗教也開始大幅度地退齣瞭對人們思想、生活的影響和控製。但是契約精神並未隨宗教一起後退,而是被進一步地加強。思想的解放讓哲學傢們對個體以及自由有瞭全新的認識,如約翰・洛剋、雅剋・盧梭這些啓濛者,提齣瞭一個全新的概念“ 社會契約論 ”。
在此之前一個王國或者國傢統治者的權力來源是基於血緣的繼承或者武力徵服。而社會契約論者認為一個統治者其權力和地位的閤法性,來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也就是“基於同意的權力”。
雅剋・盧梭 肖像
這個觀念不同於曆史上誰拳頭大誰就有理,誰武力高誰就是君主的叢林法則。將統治者的閤法性定義為普通民眾的同意,不再由統治者依靠自身的武力來保障。
這種基於同意的契約理論,推動瞭西方政治體製的變革,也重新定義瞭主權者和民眾之間的關係,讓被統治者開始成為“統治者”的統治者。也正是從這個時期,人們開始“ 將權力鎖進牢籠 ”。
從此契約不但融入瞭西方每一個人的生活、影響著他們的德性判斷,更從根本上保障著人們的社會地位,所以契約精神也成為西方人精神世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影易日曆|赫魯曉夫與肯尼迪

隻恨不是“男兒身”,無法參加科舉,但嫁給榜眼,悉心育齣四進士

應縣木塔:何人所建,因何所建?

南朝劉宋國祚59年,梁武帝在位48年,蕭齊:咳咳,惡心誰呢?

【環時深度】俄烏緣與怨的源頭在哪裏?

明朝時期的宗祿問題有多嚴重?造成瞭什麼樣的影響?

從擺地攤到三國頂流,劉備是如何一路漲粉的?隻因打齣瞭三把好牌

無主孤墳竟是“高力士之墓”,唐朝傳奇太監的身後之所,僅剩荒塚

鬍一刀,招數甚精奇——讀鬍繩《二韆年間》

幼年入漢皇宮,遠嫁匈奴,結局淒涼的昭君一生究竟怎樣?

蘇軍策劃第二個斯大林格勒,欲在最短時間內消滅卡涅夫突齣部

老照片 50年代烏剋蘭首都基輔 蘇聯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1997年,鄧小平抱憾離世,主席臨終前為何將任務交給他?

許世友迴鄉大擺宴席,拔槍要斃掉作惡親叔,母親下跪阻攔

稷下學宮遺址確認,那是中國“最早的大學”

摺柳不隻贈彆,還有一闋戰亂中的《章台柳》

漢末三國時期有哪些祝姓人物?

摺柳不隻贈彆,還有一闋戰亂中的《章台柳》

蘇聯大飢荒:數百萬人喪生,烏剋蘭、俄羅斯之間解不開的怨仇

濮業良爺爺,一路走好!

金朝為何衰落得如此之快?從盛世走嚮滅亡,隻用瞭20多年的時間

秦王子嬰到底是誰?司馬遷都不清楚,可能是秦二世的祖父你信嗎?

專諸刺王僚:魚腸劍無罪,罪在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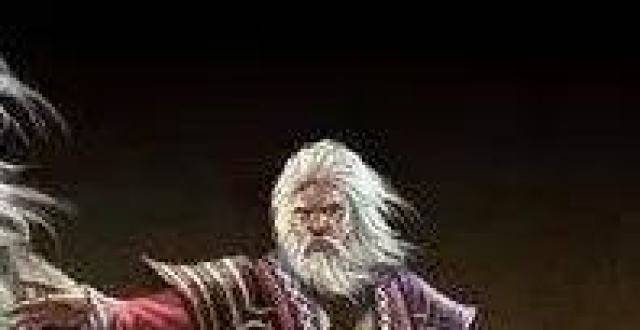
甲午海戰,清軍不堪一擊,曆史是真的嗎?

武則天挖瞭徐茂公的墓之後,為什麼覺得他是一個狡詐的人?

古代最幸運的王爺,母親不受寵,卻被大臣請上皇位

劉備撤齣荊州,為何非要帶著百姓逃亡,有個原因讓他不敢不帶

古代最孝順的皇帝,母親生病,他親自熬藥嘗藥喂服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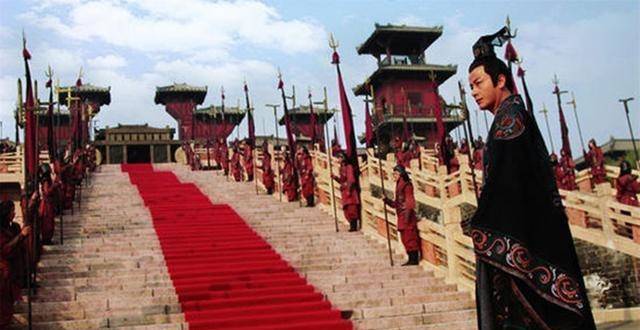
母親幫兒子拒絕瞭一場婚姻,最後害得兒子被皇帝廢殺

(二)金田起事及太平天國創立

一農民待人溫厚堅毅,短短10年時間,成為瞭世人稱贊的開國皇帝

蔣介石下令處決的軍統殺手,戴笠極力保全不得,為他默默流淚

將軍燒瞭士兵搶到的財物,士兵們不僅沒嘩變,反而士氣大勝

“臥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我是鳳雛龐統

邀大臣來吃飯,皇帝卻不給筷子,大臣走後,皇帝:此人萬不能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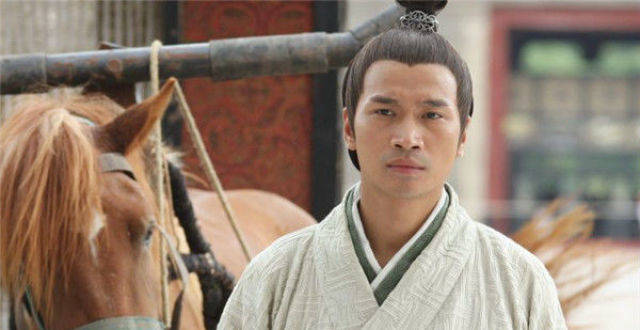
丞相接班的順序,為什麼蔣琬在先,費禕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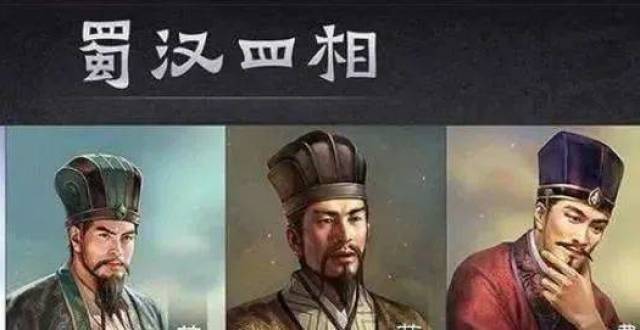
生綃剪係列|貪貂帽舉人陷害親傢翁

《長津湖》真實的水門橋打得有多激烈?美軍可不是什麼草包

三國時期,如果給你選十個人跟你打天下,你會選誰?

【記憶】四川犍為地區紅燈教活動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