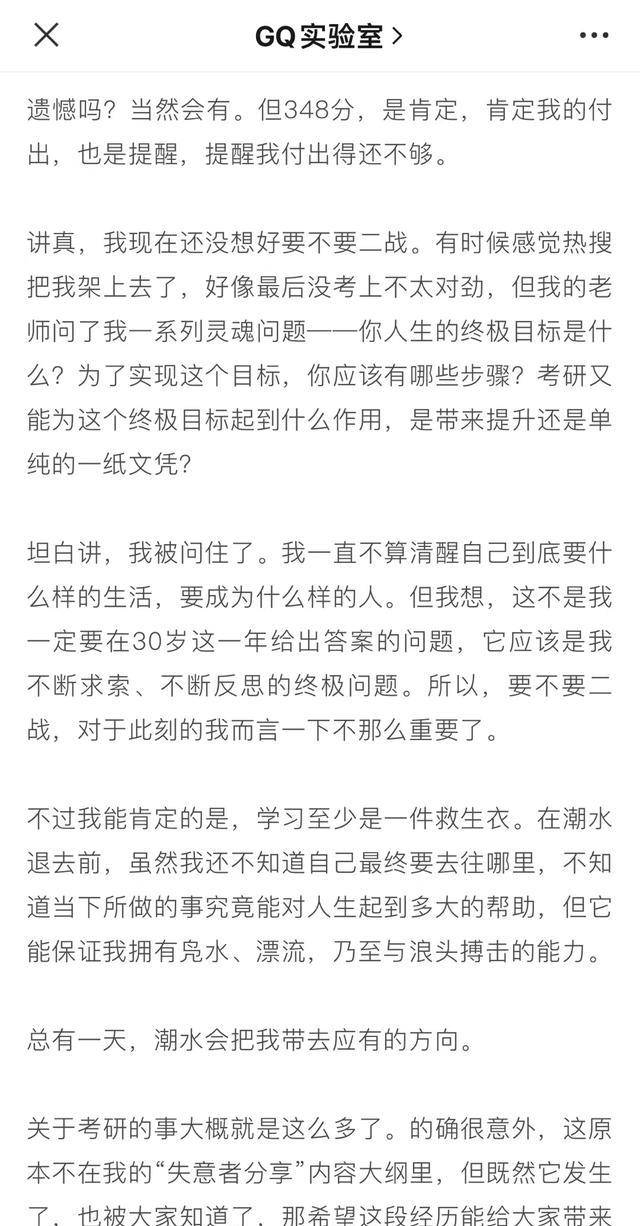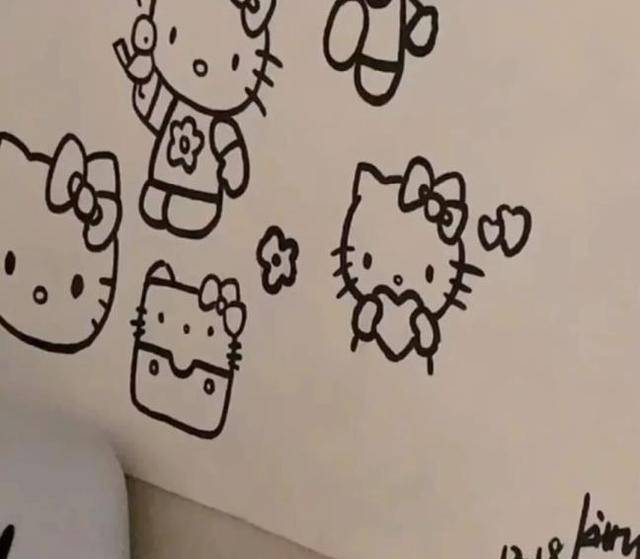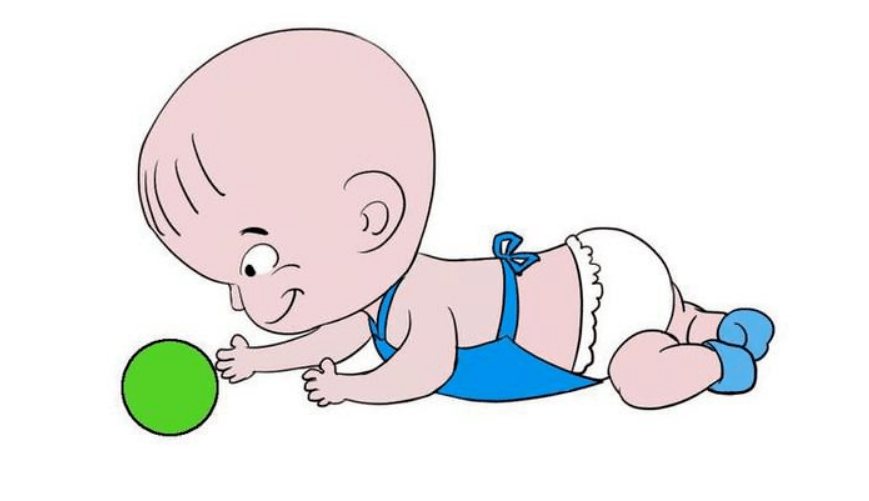古訓曰:
“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
自古以來,人們無不推崇讀史。
因為曆史是我們最好的老師,通過讀史我們能夠吸收到寶貴的經驗教訓,進而獲得應對未來的啓發。
但我們不妨思考,曆史傳達給我們的指示,憑什麼就可靠呢?
僅僅因為曆史能夠呈現給我們一個直觀的因果鏈來依循嗎?
顯然不是,畢竟自古讀史之人不可勝數,而真正依靠曆史的啓發成功安排瞭自我的人寥寥無幾。
可盡管如此,我們也依然不能迴避那些風雲人物在曆史畫捲留下的濃墨重彩,本質上確實也是對曆史的繼承與發揮。
那麼,我們便不禁要問,曆史究竟如何纔能在我們的生命實踐處顯現真正的指導價值?
我們身為普通人又該如何“有價值”的讀史呢?
今天便用這篇文章,探討一下這個問題,為諸君能夠正確的讀史明智,提供思路。
首先,曆史是什麼?
我們所謂曆史,絕非時間意義上的過去,而是文明誕生的過往。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認為文明的創造過程,有其內在的法則。
人類不同於動物的最核心一點,即人類實現瞭精神的自覺,它超越瞭動物性那種自然法則所規定的存在。
簡言之人類知道瞭自己是人,人意識到瞭自己。
它就如同一顆充滿潛力的種子,在漫長的時間中因外部大片異己之物的發現,會慢慢將理性全體之諸環節逐次展開為曆史的真實內容。
而這種展開是如何實現的呢?
依賴於精神的自由本性。
因為精神能夠讓我們發現自我,所以它是自由意識。
可對於我們自己來說,這種自由是懵懂抽象的,故而在我們這裏精神也可以說是不自由的。
精神要實現其自由的本性,就要藉助它的對立麵——不自由。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原始部落會崇拜圖騰,對圖騰的崇拜是人類社群最初的自我意識,它證明瞭精神的自由本性。
可這種自由恰恰是依靠崇拜圖騰這種精神不自由的方式實現的,因為崇拜圖騰來自人們對自然的真實恐懼。
可圖騰本質上並非自然原有之物,它反而是自由精神創造齣來的。
所以,精神的自由,在其創造齣的不自由處得以展現,精神始終在其對立麵處實現著自我。
而這種精神活動就是文明創造的真正動力,而這種文明創造也即是曆史。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辯證法。
如此也就明白瞭,曆史的展開,有著內在的法則,也即人類理性的法則。
顯然不是,因為當我們真正去觀察曆史的時候,便發現曆史中處處都是個彆性,而不是普遍性。
曆史顯然不是按照邏輯程式在進行著必然的推進,而是無處不是偶然。
好比禪讓、世襲、分封、郡縣等製度的演變。
於是,人們似乎又有所醒悟。
原來曆史根本沒有規則,它不過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疊,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動,於是諸多力量匯聚在一起,也就造就瞭曆史。
可若宏觀來看,曆史中每一個環節又都似乎必不可少,一切因素都實現著巧妙的配閤,仿佛有一種類似“天意”的力量在指引著曆史進程。
可若是如此理解曆史,那麼人作為曆史主角的主體意義也就被抹殺掉瞭。
簡言之若曆史的發展,全是天意,那麼我們便不可能從曆史中獲取到任何指導現實實踐的行為根據瞭。
就這樣,人們又有瞭一種新的觀點。
曆史中所發生的一切,並非理性法則的自我展開,而是人的生存意義的必然展開。
每個人自齣生,就開啓瞭自我生存意義的探尋。
這種探尋可以說是盲目的,因為人生本質上毫無意義,沒有人是帶著意義齣生的,人生就是人生的意義。
所以,曆史就這樣成為瞭不同個體盲目展現自我熱情的舞台。
人們不斷依照自我盲目的生命熱情實現著創造,人們自以為完成著自我生存意義的實現,但實則在不經意間創造齣瞭對付自己的力量。
這就為曆史的某些必然性開闢瞭道路。
正如我們古話講“天下大事,閤久必分,分久必閤”。
或許不同時期閤分的形式不同,但“閤久必分,分久必閤”的曆史必然性是確實成立的。
這種曆史必然性造就瞭一批一批順應時代而登上曆史舞台的“人物”。
但一定要明白,“他們”的齣現是必然的,但“他”的齣現卻是偶然的。
好比,春鞦戰國勢必要齣現一批心懷天下的能人誌士,這是曆史的必然選擇。
但孔子、老子、墨子等等人物的登場,卻是恰巧。
若曆史重新再來一次,依然會有儒、墨、道,但弘道之人就未必是他們瞭。
而更宏觀來看,人類文明的實踐形態似乎根本不可能達到一個終極的真理形態,因為文明創造本質上就是辯證的。
它發展一種形態的同時,也勢必在積纍著毀滅自身的力量。
而這對於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我們永遠無法完全通過模仿來把自己推上曆史舞台。
進一步講,我們通過理性的思路去分析曆史,根本無法獲取到真正有價值的啓發。
曆史中發生的一切,從不是印刷在紙張上的記載,而是人們麵對未知對自我生存可能性的一種決斷,是一股直麵恐懼與希望的勇氣。
其後果永遠無法用理性的邏輯去負責。
隻不過韆年來無數的人們執著於理性的分析,而使得這種最原始的關聯被遮蔽。
如此也就明白瞭,真正的讀史讀的是什麼?
不是曆史事件的瞭解,不是權謀術法的掌握,不是政治製度的參考,更不是曆史人物的模仿。
而是從人的自我認識所完成的事情中,實現對自我存在深刻的領悟。
這種領悟即智慧,對其實現的闡發即“天理”的呈現。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實中我們總能遇到很多用理性的法則判斷毫無問題的事情,但我們就是能夠很確信它是錯的。
比如,父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但兒子在外掙瞭很多錢,當瞭非常大的官。
邏輯上講兒子顯然比父親地位要高。
可現實中呢?
父親就是父親,在傢中他永遠比兒子大。
這種觀念不是通過那些概念、理論、判斷製定齣來的,而是對自我存在的領悟。
所以,現實中真正能夠指導我們人生的,恰恰是這種領悟。
讀史的真諦,就是要品齣這層意味,這纔是使人能夠貼近自我根本存在形式的行為依據。
這一點其實西方思想發展到到馬剋思哲學的時候纔反應過來。
好比儒傢的四書五經,《尚書》、《春鞦》本就是曆史文獻,經書中也多引用曆史典故。
所以,人生要遇到什麼搞不定的事情,便不妨讀讀史,與古人來一場神交。
或許在某一瞬間,一切就都豁然開朗瞭。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