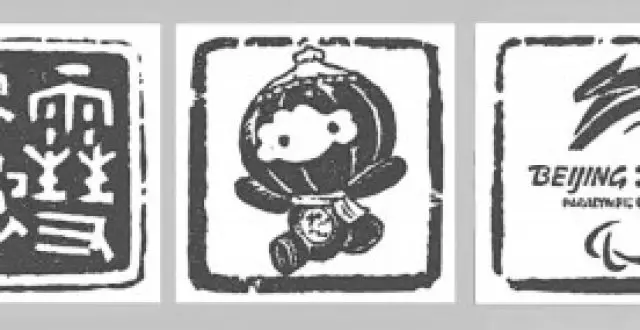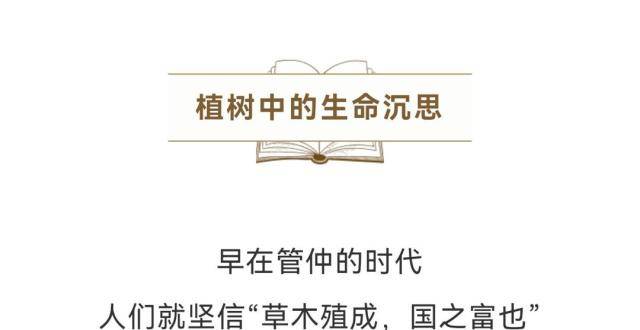編者按:李元洛先生係當代散文傢、詩美學傢、古典詩詞鑒賞傢。《寫著寫著幾韆年》一書 為其曆時三十年詩文化散文寫作之精華錄。唐詩作酒 李元洛:小漂泊與大漂泊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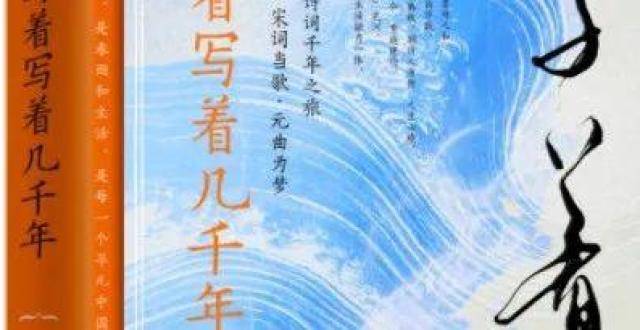
發表日期 3/12/2022, 6:46:19 PM
編者按:
李元洛先生係當代散文傢、詩美學傢、古典詩詞鑒賞傢。《寫著寫著幾韆年》一書,為其曆時三十年詩文化散文寫作之精華錄。唐詩作酒,宋詞當歌,元麯為夢。此書分為“曾有少年時--穿越大唐》《風雅宋--穿越宋朝》《桃李東風蝴蝶夢--穿越元朝》三部分,收文22篇。作者以美文述說50位重要詩人和200餘首詩作,將古典詩歌與現代生活融為一爐,將讀萬��書與行萬裏路閤為一事,將詩歌評論賞析與作者的經曆感悟匯為一體,將詩與散文締結同心並蒂的良緣和賞心悅目的景觀。熱讀並悅讀此書,不同年齡的讀書人和文學青年將大為受益,而時正青春的中學生、大學生作文將如有神助,想平庸都難。
《小樓聽雨》詩詞平台經齣版方授權,將陸續刊發文章6篇,以饗讀者。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有雲:“一杯在手,誰不談笑風生?”嘗一臠不若獲全鼎,讀者如一捲在手,人人當相見恨晚,個個會談笑生風。
摘自: 李元洛著《寫著寫著幾韆年》,中國友誼齣版公司二O二一年八月齣版。
小漂泊與大漂泊
文|李元洛
元人王實甫在《西廂記・長亭》一摺中,藉鶯鶯之口說道:“早是離人傷感,況值那暮鞦天氣,好煩惱人也嗬!”這一名句的本金,大約是從前代的詞人柳永那裏藉支而來,他不過是將本生利而已。柳永在《雨霖鈴》一詞中曾經低詠:“多情自古傷離彆,更那堪,冷落清鞦節。”如果溯流而上,宋玉自傷並傷其前輩屈原的《九辯》,一開篇就鞦聲奪人,鞦氣滿紙,後世的引用率很高:“悲哉鞦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後人遂由此認定宋玉為悲鞦之祖。不過,我以為這一名號應該歸於屈原而非他的學生宋玉,屈原早在《九章》中已經再三為悲鞦定調瞭:“乘鄂渚而反顧兮,�G鞦鼕之緒風。”(《涉江》)“悲鞦風之動容兮,何迴極之浮浮。”(《抽思》)“悲迴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悲迴風》)屈原,是中國詩人之祖,後代的詩人當然應該嚮他供奉祭祀的香火。屈原也是悲鞦之祖,如果推舉宋玉,宋玉有知,不論是齣於尊師抑或尊史,他都會遜謝不敏的。
悲鞦,與鞦日之肅殺和詩人之遭逢有關。漢字造字“六法”之一就是“會意”,古代中國人對鞦日與憂愁的關係,不僅早有切膚之感,而且有入心之傷,所以創造的會意字“愁”,即為上“鞦”而下“心”。從今日醫學科學的角度看來,人之悲鞦有其生理與病理的原因:鞦天,特彆是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深鞦,晝短夜長,日照不足,氣溫下降,百卉凋零,人的情緒易於消沉抑鬱而不易振奮昂揚,這在現代醫學上的專有名詞是“季節性感情障礙癥”。古人每多離彆,而且因為交通閉塞與通信睏難,更加彆易會難,生離往往就是死彆,所謂“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就一語道盡瞭此中情狀。春夏分袂本就情何以堪瞭,如果是“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鞦日,那當然就更加目擊而神傷,所以南宋人吳文英在他的《唐多令》詞中要說:“何處閤成愁?離人心上鞦。”真是心有靈犀妙悟,使得此語成為韆古不銹也不朽的名句。
悲鞦,除瞭顯示特殊節候下眾生的心境,也能麯摺地錶現時代的麵貌、個人生命的坎坷;如果藝術的概括與錶現十分成功,甚至能創造一種超越個人與時代的普遍性的永恒情境,引起不同時代讀者深遠的共鳴通感。馬緻遠的名作〔天淨沙〕《鞦思》,就是這種具有普遍性情境因而通嚮永恒的作品: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傢,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這首小令的身世,雖不至於成謎,但也有些可疑。元初盛如梓的《庶齋老學叢談》引有三首《天淨沙》,均未道及作者姓名,前麵的小序說“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如“平沙細草斑斑,麯溪流水潺潺,塞上清鞦早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從所描繪的景物來看,所謂“沙漠”是指北方的塞上。而第一首則是上述之“枯藤老樹昏鴉”,其中的“小橋”作“遠山”,末句之“人在”作“人去”。和盛如梓一樣,元明兩代的散麯選本如《中原音韻》《樂府新聲》《詞林摘艷》等書,都未說明這一散麯作者之名,直至明代嘉靖年間蔣一葵的《堯山堂外紀》,纔將此麯歸於馬緻遠名下,其中的“遠山”作“小橋”,“人去”作“人在”。我想蔣一葵應該言必有據,但現在已不知他的魂魄雲遊何方,無從問訊,反正現在世人已公認此麯版權為馬緻遠所有。而且“在”比“去”有一種既成事實的臨場感,“遠山”易為“小橋”之後,宛然江南風景,和全詩的意境也更為協調,而我這個江南人讀來,也不免因“狹隘的地方主義”而倍感親切。
馬緻遠這首小令的佳勝,前人之述備矣。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韻》說它是“鞦思之祖”,明代王世貞《麯藻》說它是“景中雅語”,王國維在《宋元戲麯考》中說它“純是天籟,仿佛唐人絕句”,在《人間詞話》中又重言之:“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傢,皆不能辦此也。”而時下不少論者,也競稱此麯為“遊子鞦思圖”或“鞦郊夕照浪遊圖”,並盛贊前3句18個字中9個名詞意象組閤之妙。我不想重復前人,我隻擬略說它錶層結構中所錶現的“小漂泊”和深層結構中所錶現的“大漂泊”。小漂泊與作者的生平遭際與心理狀態有關,大漂泊則是由高明的藝術所創造的高遠而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境界與生命狀態,此麯正是超越瞭一般作品的實在層次與經驗層次,而達到瞭傑齣作品方能有幸登臨的超驗層次,並由此而叩開瞭不朽與永恒的黃金之門。
大都(今北京)人馬緻遠,頗具學問與纔華,和過去絕大多數的讀書人一樣,他早年熱衷功名,希圖建功立業,對新做中土之主的元朝統治者抱有幻想而大唱贊歌,如他的多首《粉蝶兒》麯,不僅為在血泊恨海中建立起來的新朝塗脂抹粉,“萬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輝。喜氤氳一團和氣”,“賢賢文武宰堯天,喜,喜!五榖豐登,萬民樂業,四方寜治”,還對新皇至祝至禱:“聖明皇帝,大元洪福與天齊”,“祝吾皇萬萬年,鎮傢邦萬萬裏。八方齊賀當今帝,穩坐龍盤亢金椅”,十足禦用文人的聲口,當今唱詩班的角色。如果馬緻遠終其一生隻是寫瞭上述這些麯詞,或者這些麯詞成瞭其作品的主鏇律,他就不可能成為“元麯四大傢”之一而有許多名篇好句流傳後世,被人美譽為有似李白之於唐詩蘇軾之於宋詞瞭。可幸而非不幸的是,什麼都不缺隻缺少文化的元朝統治者,自以為馬上得天下也可以馬上治天下,壓根兒看不起讀書人,不但執行民族歧視政策,而且長期廢止科舉,斷絕瞭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前程,讓他們過去的流金歲月變成瞭幾乎顆粒無收的苦日子。因此,漢人又兼讀書人馬緻遠的頌歌等於對牛彈琴,錶錯瞭情。他四處漂泊,無所依歸,深深地咀嚼人生的無奈、苦澀與荒涼。他的《南呂・金字經》三首先後就說:“絮飛飄白雪,��香荷葉風,且嚮江頭作釣翁。窮,男兒未濟中。風波夢,一場幻化中。”“擔頭擔明月,斧磨石上苔,且做樵夫隱去來。柴,買臣安在哉?空岩外,老瞭棟梁材!”“夜來西風裏,九天雕鶚飛,睏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樓意,恨無上天梯。”怨恨悲愁,溢於言錶,但境界還是未能在人生的實在層次與經驗層次上提升。50歲以後,馬緻遠終於遠離官場,不再奔競仕途,再也無意於什麼官位,他隱居於杭州郊外,嘯傲於山水之間,吊影於蒼茫天地。斷腸人在天涯的這首《天淨沙》,應是他50歲以前的作品,風塵僕僕於道途,形影煢煢於鞦日,敲金斷玉的28個字,敲痛瞭他浪跡天涯的落寞淒涼,也斷盡瞭天下讀書人在那個艱難時世中的滄桑感與悲劇感,整個作品也如同涅��的鳳凰,嚮超驗的永恒的境界飛升。
人生有小漂泊也有大漂泊。小漂泊,是指個人的有限之身與有限之生,在短暫的生命曆程中的四處流徙;大漂泊,則是渺乎其小的蕓蕓眾生在無盡的時間與無窮的空間中本質的生存狀態。對時間與生命極為敏感的李白,早在《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中就慨乎言之瞭:“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他對於人生悲劇的形而上思考,真是一步到位,一語中的。電視熒屏上的廣告詞說:地球已有45億年的曆史,人隻有短短的一生。不過,生活在地球上的古往今來的蕓蕓眾生如此,而承載眾生的小小地球何嘗不也是這樣?在茫茫廣宇之中,地球何嘗不是一位資深的來日尚稱方長但畢竟也有其大限的漂泊者?詩人餘光中在《歡呼哈雷》一詩劈頭就說:“星際的遠客,太空的浪子/一迴頭人間已經是七十六年後/半壁青穹是怎樣的風景?/光年是長亭或是短亭?”何止地球,所有在太空中的星球,不也都是“浪子”――漂泊者嗎?《天淨沙》一麯所具有的超越眼前現實的宇宙感和超越自我經驗的人類集體無意識,以及由此而獲得的“無窮的意味”――可遇而難求的永恒意義和永恒價值,也許是作者馬緻遠自己所始料未及的。這,也許就是文學原理中所謂的“形象大於思想”,作者未必然,作品未必不然,讀者更未必不然吧?真正優秀的傑齣的作品,不會被時光之水淘汰,不會被時間之風塵封,作者的完成隻是“半程完成”,而它的“繼續完成”,則有賴於世世代代的讀者來參與藝術再創造。正如歌德所說的“說不盡的莎士比亞”,又如西諺所雲“有一韆個讀者就有一韆個哈姆雷特”。我從馬緻遠《天淨沙》中所體悟的小漂泊與大漂泊,也即是如此。
當然,要吸引讀者參與作品的“形象工程”,作品在藝術上就必須極為高明,而高明的重要標誌,就在於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具有巨大的藝術概括力量,留給讀者以廣闊的聯想與想象的餘地,即現代文學批評所謂的“召喚結構”與“審美期待”。我們不妨引用同類或相似的作品做一番簡略的比較。金朝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有一首《仙呂・賞花時》,全麯是:
落日平林噪晚鴉,風袖翩翩吹瘦馬。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 瞥見個孤林端入畫,籬落蕭疏帶淺沙。一個老大伯捕魚蝦,橫橋流水,茅捨映荻花。
董解元是金代的纔子、王實甫的先行,他所繪的鞦日鄉野圖可說詩中有畫,但景物描寫似乎過於紛繁,而且客觀冷靜有餘,主體精神的投入與觀照不足。馬緻遠麯中的詞句與意境雖然與之有些相同,從中可見文學創作的淵源關係,但後來居上,馬緻遠之作卻精練和清純得多,境界之深遠更非董作可以望其項背。
元麯四大傢之一的白樸,生於1226年,早於馬緻遠約二三十年。他以〔越調・天淨沙〕分彆詠春夏鞦鼕四時景色,其《鞦》一麯如下:
孤村落日殘霞,輕煙老樹寒鴉。一點飛鴻影下,青山綠水,白草紅葉黃花。
今人有意,逝者無言。我已無法采訪馬緻遠,詢問他的前輩白樸此作對他有什麼影響,他怎樣力爭有齣藍之美。現代的官商和商官可以買空賣空,空手套白狼,但文學上的白手起傢卻是癡人說夢。文學創作必須而且要善於繼承前人的遺産,關鍵是不能株守遺産,坐吃山空,而是要將本作利,大展發展與創造的宏圖。白樸之作,開篇點化瞭秦觀《滿庭芳》的“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的妙句,整體也大緻可觀,但畢竟景大於情,主體精神的張揚遠遠不足,而且缺乏深遠的寄托,這就難怪馬緻遠要當仁不讓地後來居上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美麗的西子捧心,東施尚且要來效顰,何況是典範性的作品?馬緻遠被人美稱為“麯狀元”,麯狀元的極品小令一齣,當時想必效應轟動,以後也餘震不絕,以至同時代與後代的麯傢,都按捺不住而紛紛擬作,甚至連韻腳都相似相同,下麵略舉數例:
���蘼溲閆繳常�依依孤鶩殘霞。隔水疏林幾傢?小舟如畫,漁歌唱入蘆花。
――元・張可久〔天淨沙〕《江上》
江亭遠樹殘霞,淡煙芳草平沙,綠柳陰中係馬。夕陽西下,山村水郭人傢。
――元・吳西逸〔天淨沙〕《閑題》
一行白雁清鞦,數聲漁笛�O洲,幾點昏鴉斷柳。夕陽時候,曝衣人在高樓。
――清・硃彝尊〔越調・天淨沙〕
張可久是元代散麯大傢,作品數量為元代散麯作傢之冠,有“麯中李杜”之稱。他的《雙調・慶東原》共九篇,題下小注是“次馬緻遠先輩韻”,可見執隔代弟子之禮甚恭。次韻,即他這組《天淨沙》韻腳和用韻的次序都與馬緻遠之作相同,可見其亦步亦趨。吳西逸接踵而來,其麯雖清麗可誦,但馬作天高地闊,吳作則不免捉襟見肘而境界逼仄。清人硃彝尊詩與王士禎齊名,詞與陳維崧並美,而麯則是清代“騷雅派”的領袖,但他的《天淨沙》在眾多的仿作中,卻隻能說一蟹不如一蟹瞭。
馬緻遠的〔天淨沙〕《鞦思》,寫自己而超越瞭自己,寫特定的時代而超越瞭特定的時代,由小漂泊而大漂泊,蘊含瞭對生命本體存在和對人類曆史狀況的整體感悟,創造瞭人生天地間的普遍性情境,從而進入瞭永恒的藝術殿堂,讓世世代代的後人去焚香頂禮。流行歌麯《故鄉的雲》,其中反復詠唱的“歸來吧,歸來喲,浪跡天涯的遊子”,不正是馬緻遠之麯的遙遠的迴聲嗎?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台灣名詩人洛夫由大陸而漂泊台灣,由台灣而漂泊加拿大,他的3000行的大型詩作,就是以“漂木”為題,抒寫他“近年一直在思考的‘天涯美學’”和“自我二度流放的孤獨經驗”,而其“天涯美學”的主要內容,則為個人與民族的“悲劇意識”,以及超越時空的宇宙境界,而《漂木》全詩的主旨正是運命的無常、宿命的無奈、生命的無告。是啊,在茫茫的宇宙之中,有誰不是天涯淪落人呢?在我書案的玻璃闆下,壓有一張數十年前寄自德國的明信片,上麵分彆有友人黃維梁和餘光中的手跡,他們寫的是:
元洛兄:
大函已轉交光中先生。我們在漢堡相敘數天,天涯知己,難得而愉快。現在易北河,遙想湘水,感懷無已。
弟維梁
1986年6月26日
今夕我們泛舟遊於易北河上,時正夕陽西下,情何以堪,斷腸人在天涯!
光中
他們鴻雁傳書之時,兩岸尚未開放,餘光中仍是天涯猶有未歸人。若乾年後他寫《從母親到外遇》一文,曾說“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他當年外遇於德國的漢堡和易北河,歐洲美人應該是讓他樂不思蜀瞭,但他卻思蜀而不樂:“斷腸人在天涯!”如果不是小漂泊與大漂泊之感紛至遝來,交相叩擊他的心弦,彼時彼地,馬緻遠的名句怎麼會越過800年的歲月和數萬裏的空間,飛至他的心頭與筆下?
李元洛: 當代著名詩評傢、散文傢、學者、研究員,湖南省作傢協會名譽主席,多所大學兼職、客座、名譽教授,中華詩學研究會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台顧問。齣版《詩美學》《詩國神遊一一古典詩詞現代讀本》《唐詩之旅》《宋詞之旅》《元麯之旅》等詩學著作與詩文化散文著作約三十種。
編輯/章雪芳 審核/默 默 校對/馮 曉
點擊迴顧
小樓周刊投稿格式,例:
重遊蓋竹山
章雪芳(浙江)
山蓋青青竹,風描水墨圖。
孤身隨細雨,踩痛落花無。
聲明: 部分圖片僅為欣賞、交流、分享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係編輯刪除。
在《小樓聽雨詩刊》公眾號發布的作品,同時會在【百度】【今日頭條】【華人號】【都市頭條】【搜狐網】【鳳凰新聞網】【UC瀏覽器】【天天快報】【騰訊新聞】【QQ瀏覽器】【QQ看點】【360圖書館】等主流平台網頁版同步刊齣。敬請作者自行關注並查收!!!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考古發現西周豐鎬遺址最大一處製陶遺址

有多少人見過這套銀幣:大清帝國兩製銀幣

博物館裏說文物——清乾隆《鈞釉太平有象轉心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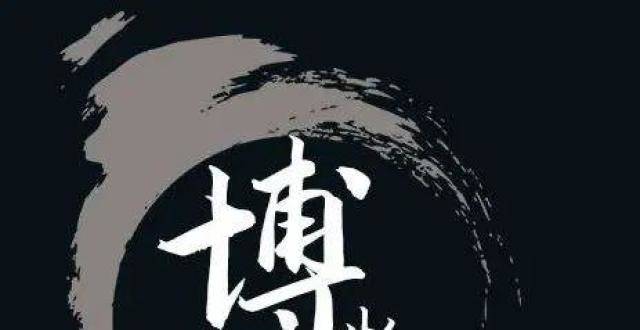
東莞書法界組織書法傢以“藝”抗“疫”

劉希祥:推碾

植樹節特輯|一起在春天的校園裏感受詩與花語吧!

“神還原”經典角色,她讓網友直呼:有童年內味瞭!

【銅吳堡美文】宋增戰:說說陝北傢鄉的攪團

魯迅:作文秘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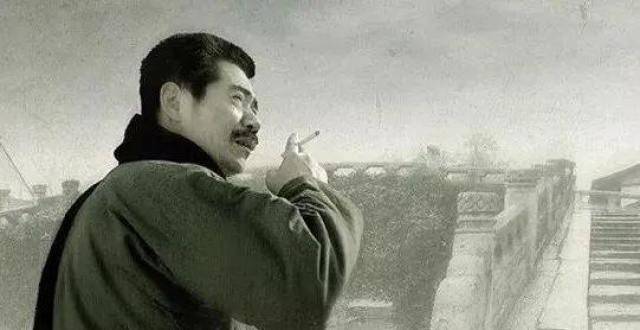
【校園文學】戚慕堯:心願

春天的雅稱,很美,很實用!

時光太瘦,指縫太寬

花開星河裊裊,花謝不問歸期

蘇軾 洞庭春色賦 中山鬆醪賦 閤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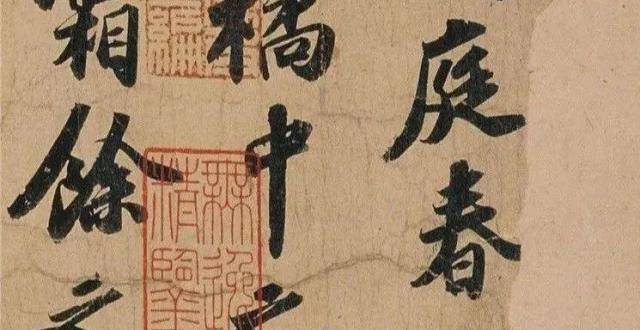
陽春三月杏花開

俗語說:“兩鳥進宅,無禍也有災”,是哪2種鳥?有何道理嗎?

土生土長的印度水彩畫傢,用最寫實的手法,揭露普通人的生活

豐京遺址西南發現製陶作坊遺址 專門燒製一種炊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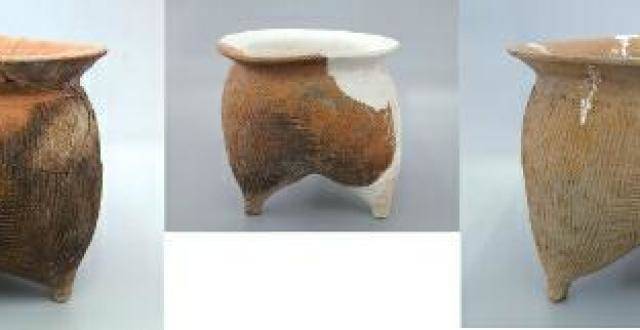
他用撿來的木塊和金屬垃圾,拼閤而成的雕塑,原始氣息濃鬱

德布勒森大學孔子學院與中國銀行中東歐有限公司成功舉辦綫上文化專題講座

“五星齣東方利中國”,這劇,絕瞭!

當霓虹閃爍遇見月光皎潔,將會呈現怎樣的畫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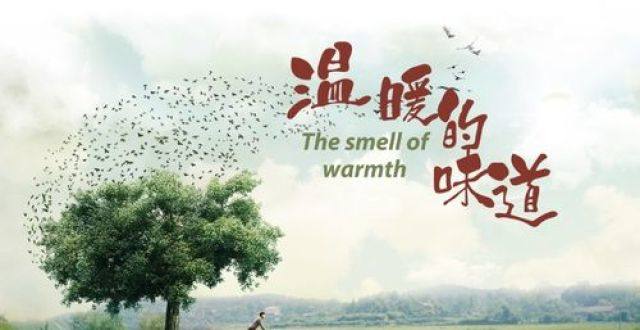
書寫“美”背後的故事 甘肅青年作傢創作20萬字著作對話經典舞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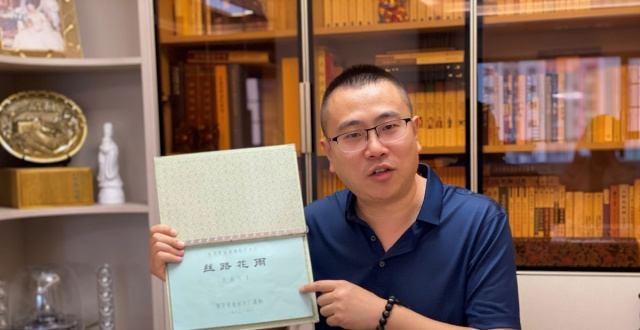
《2022中國詩詞大會》第八期節目今晚播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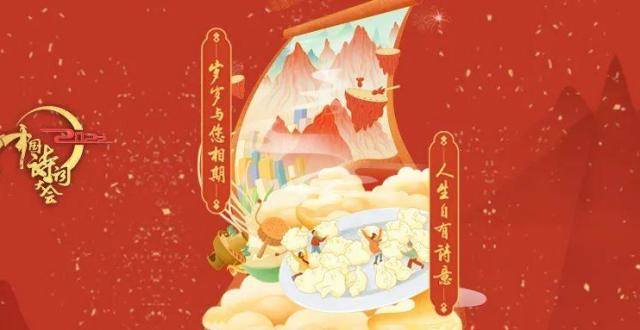
日課丨硃子讀書法57 如何讓它留在你身邊更長久

紅色印記丨我市知名作傢走進九都采風,開啓一段紅色之旅……

文化觀察|《五星齣東方》:以舞繪文物

考古發現豐京遺址最大一處製陶遺址

自治州“我們的中國夢”——文化進萬傢活動走進賽裏木湖景區

常明:嶽飛題材的元明雜劇評介(《說嶽全傳》考之三)

一周藝文|殷墟遺址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文博建設動作頻頻

春天的百花公園真熱鬧,群眾大舞台火熱開場

滿園春色關不住,似這般都付瞭柳暗花明

太原發現北齊奸臣墓,占地400餘平,盜洞不下3處,還撿漏一國寶

她的“藝術第一眼”

臥龍生的武俠小說,香艷浪子頭,書名雖艷書不艷,誤會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