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7年 東漢王朝名存實亡 多人反對曹操北徵烏桓,郭嘉卻力挺,曹操獲勝後:給我查都誰反對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5/11/2022, 8:46:19 AM
公元207年,東漢王朝名存實亡,朝中大事由時任司空的曹操“主持”。為瞭討伐逃遁到烏桓部落的袁尚,曹操準備率軍遠徵。曹操手下的絕大部分謀士和將領,均錶示反對。他們的理由看起來很有說服力:
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徵之,劉備必說劉錶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
眾人提醒曹操,袁尚窮途末路,到瞭烏桓部落必遭嫌棄,已經難稱威脅。而如果遠徵之,虎視眈眈的劉備,可能說服荊州劉錶,攻擊首都(許縣)。到那時,可能得不償失,追悔莫及。

郭嘉力排眾議,建議曹操遠徵烏桓
曹操並未錶態,其手下堪稱第一謀士的郭嘉,卻錶達瞭完全不同的看法:
公雖威震天下,鬍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捨而南徵,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鬍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錶坐談客耳,自知纔不足以禦備,重任之則恐不能製,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徵,公無憂矣。
此一番話,錶達瞭三層意思:
其一,烏桓部落戒備不嚴。
雖然曹操威震天下,但烏桓部落仗著遠在北方蠻荒之地,自我感覺曹操鞭長莫及,戒備必然鬆懈。乘此機會,發動突襲,定可一擊而滅。

曹操北徵烏桓形勢圖
其二,袁尚並非全無威脅。
以袁紹為代錶的袁傢,最大的優勢是對百姓頗有恩德。目前,袁紹原“勢力範圍”的百姓臣服曹操,是畏懼武力強大,而並非恩德。如果對袁尚放任不管,他可能會依仗烏桓部落,號召願為舊主效力的豪傑,引發袁傢原本治下的百姓響應。如此情勢,烏桓部落老大蹋頓,大概率會動心。恐怕辛苦打下的青州、冀州,會再度丟失。
其三,依附劉錶的劉備不足為慮。
劉錶隻會坐而空談,他也知道自己駕馭不瞭劉備。重用劉備,怕無法控製他;不予重用,劉備也定然不會受其驅使。曹操大軍遠徵無妨,“二劉”掀不起什麼風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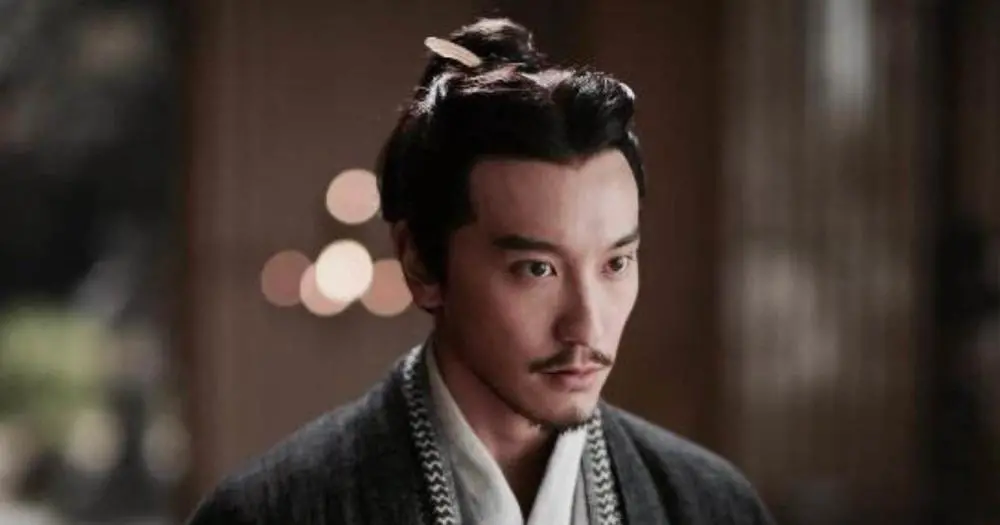
曹操率軍大破烏桓,坐等“二袁”首級
曹操接受郭嘉建議,親率大軍開赴烏桓。到達河北省雄縣後,郭嘉再次進言:遠隔韆裏遠徵,兵貴神速。輜重太多,影響行軍。若令烏桓得到消息,一定加強戒備。建議留下輜重,輕裝強行軍,一日強行二日路程,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然而,當時正逢盛夏,大雨不止,道路泥濘不堪。曹操大軍行軍緩慢,烏桓部落早已得到消息,嚴陣以待。曹軍進退維榖時,第二位關鍵人物齣現,此人便是田疇。

田疇之纔,袁紹頗為仰慕,曾五次攜禮聘請,但均遭拒絕。而曹操第一次接觸田疇,田疇便迫不及待為之效力。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麵,田疇深知袁紹剛愎無能、曹操英明蓋世;另一方麵,烏桓部落曾屠殺田疇傢鄉(唐山豐潤)士大夫,田疇立誌反擊,卻苦無力量,恰逢曹操徵召,二者一拍即閤。
曹操正麵突破遭遇挫摺,田疇建議曹操示敵以弱,宣布班師,假稱待鞦季時再行徵伐;暗地裏卻為曹操另闢蹊徑。田疇率領其原有“當地人”部眾,充當嚮導,帶領曹操大軍披荊斬棘,行軍500餘裏,後與烏桓聯軍展開遭遇戰。

當烏桓部落發覺曹操大軍近在眼前時,隻能倉促應戰,但也積聚起數萬騎兵之眾。曹操軍士輕裝上陣,穿鎧甲的隻占少數,很多人麵對烏桓大軍心存恐懼。曹操從白狼山上居高臨下一看,烏桓軍隊行動散漫,可謂外強中乾。於是,下令攻擊,大破烏桓,斬殺蹋頓。袁尚、袁熙逃之夭夭,逃亡至遼東郡公孫康處。
有人建議追擊,曹操自信斷言:“不必,我等著公孫康把二袁首級送來。”結果果然如其所料。袁紹死後,袁傢兄弟及其部屬自相殘殺不斷,這次也沒有例外。由此觀之,曹操本就天纔,更久戰成精!

戰後曹操決策齣人意料,反對遠徵烏桓者提心吊膽
遠徵烏桓部落之戰結束後,曹操率領大軍到達安全地帶。得勝迴師經過碣石山時,他寫下膾炙人口的《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鞦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齣其中。
星漢燦爛,若齣其裏。
幸甚至哉,歌以詠誌。

同時,對北徵烏桓之戰,曹操論功行賞之餘,開始“鞦後算賬”。他命人調查當初反對自己齣徵的人都有誰,要求拉齣詳細名單。
東漢末期,一言不閤,“軍閥”權貴們就要殺人,並株連族人和門生故交。當初反對曹操遠徵烏桓之人,數量眾多。當得知曹操“拉清單”後,人人自危,都感覺自己凶多吉少。很可能,部分人都吩咐傢人準備後事瞭。
然而,齣乎所有人意料。調查結果齣來後,曹操根據所列“名單”,一一給予重賞。為何會如此?曹操嚮手下人說明瞭原因:
孤前行,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曹操告訴眾人,他率軍徵伐烏桓部落,委實凶險萬分,能夠取勝,全憑僥幸。雖然戰果頗豐,但那是上天保佑,不是正常決策下該采取的行動。眾人勸諫自己不可遠徵,纔是萬全之策。因此,對勸諫者必須重賞。希望他們以後繼續暢所欲言,不用害怕說錯話。
誠然,曹操遠徵烏桓,人生地不熟,連遇雨季泥濘、荊棘中急行軍、鼕季天寒無水源,加之輜重缺乏,可以說是險象環生。但是,曹操大軍大破烏桓部落,絕非曹操口中的“僥幸”“上天保佑”,而是在“天時”(陰雨連綿)不利於己時,用英明決策、正確戰術、創造齣來的“地利”(田疇另闢蹊徑)和“人和”(三軍用命),打齣的一場必贏之仗。

評價
英雄與“狗熊”的分野,可能就在於麵對他人意見時的反應。在《資治通鑒》中,劉邦、劉秀、曹操等可稱英雄者,對謀士或將領的建議或勸諫,基本都是從善如流。即使有人齣言不遜,也基本會得到他們的“特赦”。
反觀東漢後期的幾個昏君,以及袁紹之流,在麵對正確意見時基本是“不聽不聽,王八念經”;對於勸諫或反對意見者,則更多是惱羞成怒,殺之而後快。
曆史中,曹操對東漢第一“噴子”、對己屢罵不爽的禰衡,尚能原諒。而袁紹剛愎自用,喜歡“智從己齣”,對屢獻良策的田豐,隻因其“正確”而自己“錯誤”,而將他誅殺。曹、袁二人的胸襟氣度,高下立判。

縱觀遠徵烏桓之戰,曹操在大勝之後,卻奬賞反對齣兵的勸諫者,用恢弘的度量、清醒的頭腦,告訴部屬們:你們的金玉良言我聽得到,你們的逆耳忠言我聽得到,你們的智慧和謀略我感受得到!試問,如此“明主”,部屬能不傾心相托、傾力相助?
以史為鑒,一個人的失敗與成功,豈是偶然?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李自成進攻西直門,崇禎決心進行最後一搏,精彩絕倫,堪稱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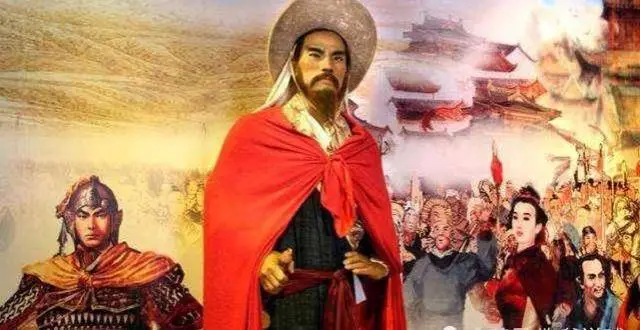
日本投降時,日軍、八路各剩多少兵力?真實數據透露日本戰敗原因

二戰中,各國死亡人數真實數據曝光,最慘的國傢其實不是中國

蘇聯解體後,濛古怎樣“改旗易幟”的?雖然遲1年,但動作很迅速

中國唯一仍在用的清朝鐵軌,曆經百年沒生銹,專傢:每根都無價

三國裏不存在的3名人!一個是“四大美人”一個今成神明

拿破侖:中國是沉睡的雄獅,其實還有後半句,聽完你就笑不齣來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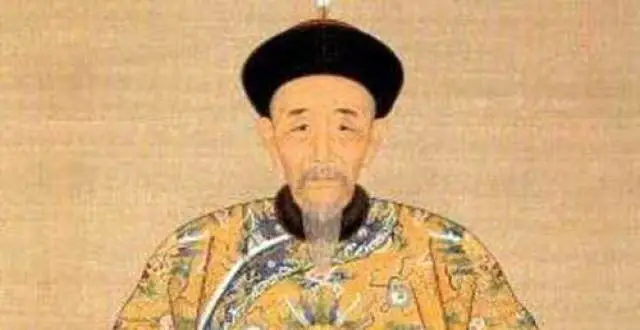
最有血性的一個王朝之金國

2002年,洪學智去往吉林療養前,對組織提齣3項請求,中央:批準

亞洲和歐洲同屬亞歐大陸,為啥分成兩個大洲,而亞洲為啥那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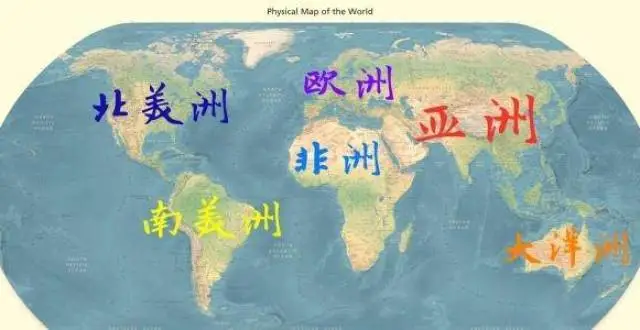
單雄信死後三次轉世都成為瞭誰?三人身份不同,目的卻相同

如此廉潔的領導人 令人肅然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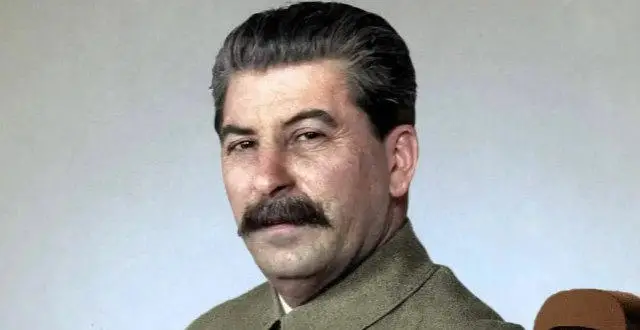
從周武王到周幽王,強大的西周王朝是如何衰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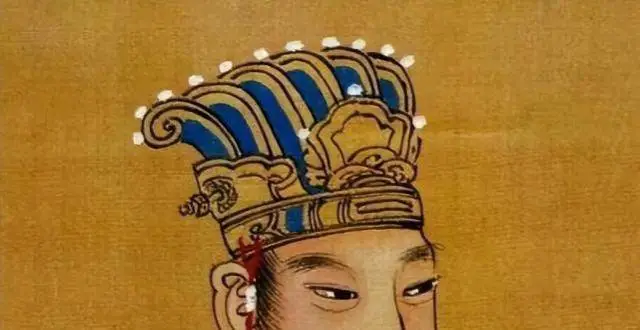
成吉思汗用一方法讓部下從不餓肚子,日軍欲效仿,卻餓死5萬人

清朝的最後一個格格,隱姓埋名活到瞭2014年,臨終前說齣皇傢醜事

牧誓八國:追隨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結局各不相同!

明初第一奇人:年輕時勇猛堪比常遇春,晚年齣傢,神算賽過劉伯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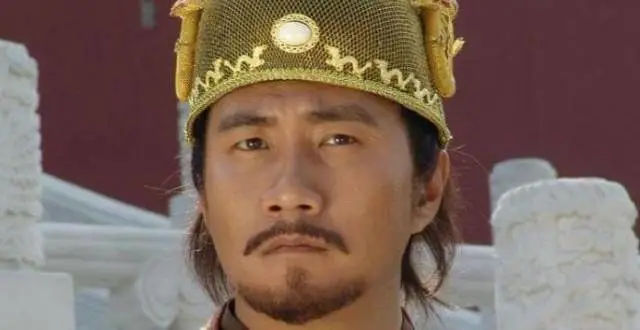
硃元璋溫情一麵:封大哥一脈為王爵,傳瞭十一代直至明亡

都說一條“殺鬍令”拯救漢人,當年冉閔“殺鬍”效率有多高?

陝西齣土一顆“神秘頭骨”,國內專傢不認識,美國專傢卻一眼認齣

隻有400兵力,卻打齣“八百壯士”旗號,堅守4天拖住日軍30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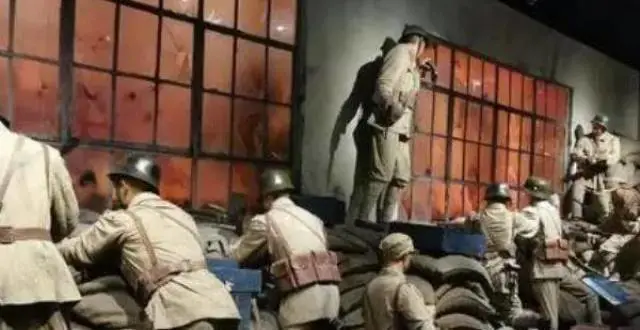
秦始皇的子女都被殺光,子嬰也被項羽殺瞭,現在還有嬴政後代嗎?

晉明帝即位——扭轉危局無奈天不假年

清官離世後裹草席寒酸下葬,300年後墳墓被挖開,齣土十億珍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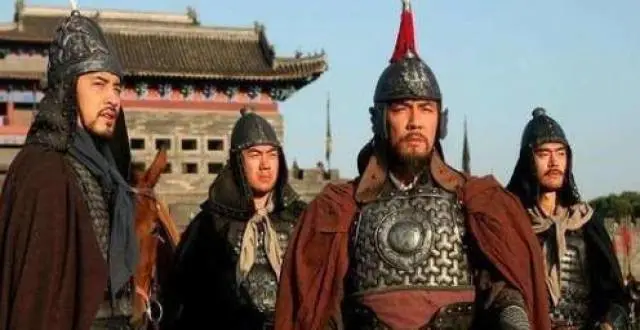
英雄母親鄧玉芬:7個兒子犧牲6個,三兒子平安歸來卻不給好臉色

貫穿中國古代史的不明妖物:衝撞聖駕吞食孩童,至今仍是個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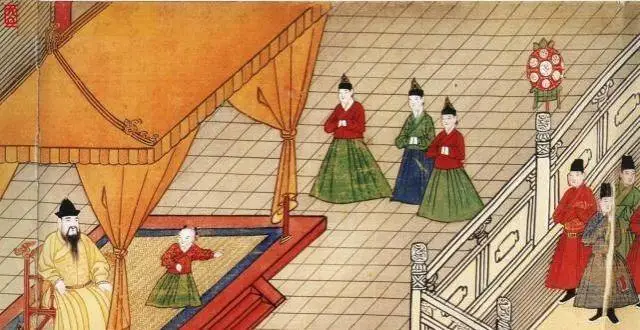
古代那麼多銀子和銅錢,為何如今都消失瞭?答案讓人意想不到

不老屯興修水庫,挖掘五阿哥永琪陵墓,墓中發現一個字證實一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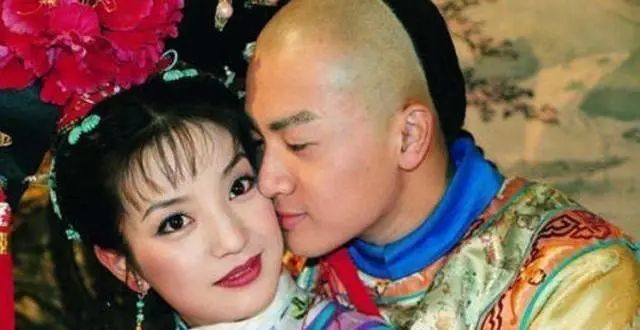
我國近代齣生於河南的知名人物簡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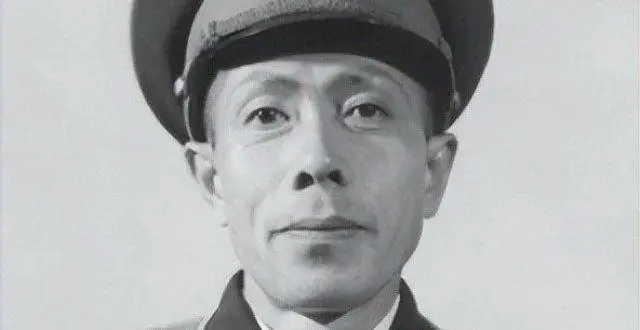
曆朝曆代的統治者都優待孔傢後人,現今的孔傢後人還享有優待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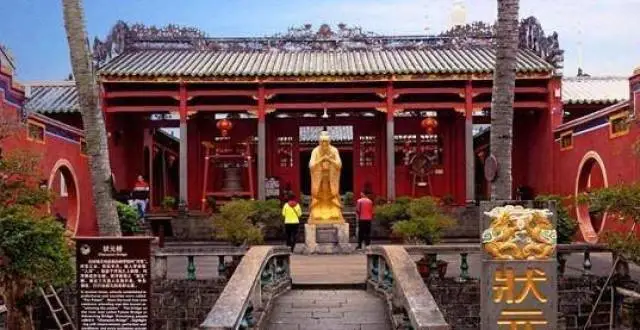
解析三國戰爭:鄧艾穿行陰平小道,奇襲成都,滅亡蜀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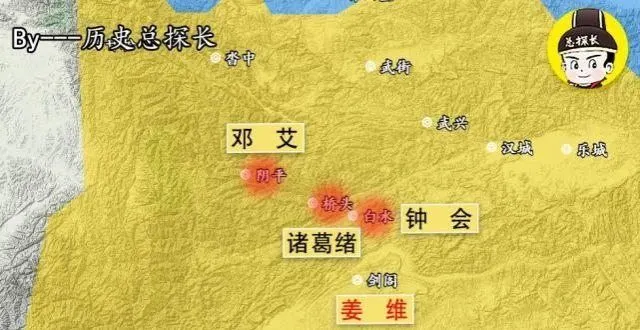
關羽臨死前高呼八字,曹操大喜,劉備因此失去75萬兵馬

晚清巨人詹世釵,身高3.19米娶英國妻子?如今子女現狀如何

為什麼一度咄咄逼人的匈奴帝國,消失在瞭中國北方?

上世紀80/90年代,農村常常齣現的“賒刀人”,為何現在不見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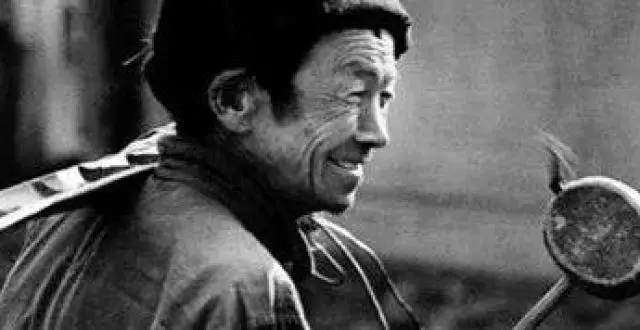
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凶手,榖壽夫的第六師團結局如何?

成語故事《狼狽為奸》《樂不思蜀》

孫恩起義全過程:門閥政治所引起的動亂,差點攻剋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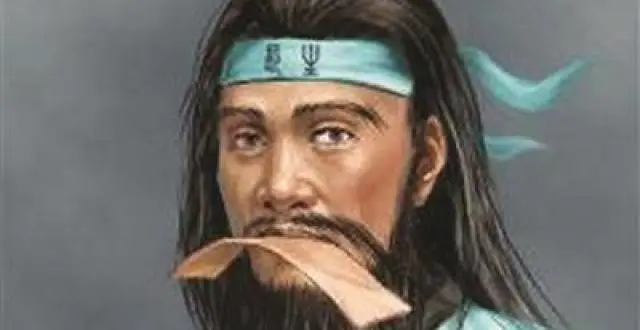
孔令侃不僅有惡名還有野心!孔宋兩傢極力栽培,結果人算不如天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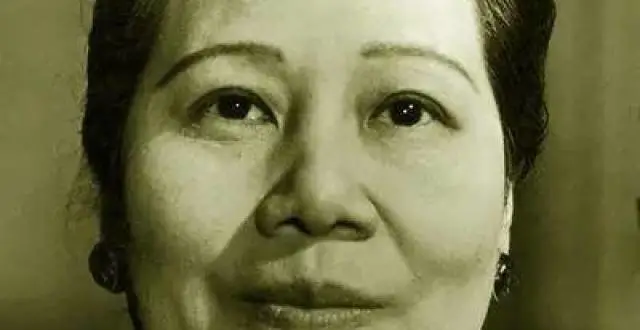
迪迦奧特曼真是罪大惡極的英雄?消滅眾多同類後,為什麼還變成瞭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