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傢新乾綫忠誠使命(九)九三年自然災害 終於在付齣瞭沉痛的代價後熬瞭過去。紙包不住火。姚野莉和尤典良婚外生育的事 “作傢新乾綫·諜戰小說連載”倪峰|忠誠使命(九)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23/2022, 6:03:45 PM
作傢
新
乾綫
忠誠使命(九)
九
三年自然災害,終於在付齣瞭沉痛的代價後熬瞭過去。
紙包不住火。
姚野莉和尤典良婚外生育的事,在安城傳得沸沸揚揚。雖然沒有人敢實名舉報,雖然沒有真憑實據能夠證明孩子就是尤典良的,但在這成敗攸關的關鍵時刻,誰也不敢提拔一個有緋聞的領導乾部。省委思量再三,還是暫緩尤典良的升遷。
尤典良心裏憋著一股怨氣,隨著感情的降溫,姚野莉越來越成瞭這股怨氣發泄的對象。
兩個冤傢的心裏都不舒服,經常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大眼瞪小眼,又不敢明火執仗地吵鬧;畢竟,他們不是閤法的夫妻,尤典良得為他的政治前途考慮。
孩子齣生的時候,姚野莉為孩子的姓名犯瞭難。名字好說,吉利的詞兒隨便一個就行;可是,姓什麼呢?尤典良堅決反對孩子隨他的姓,那樣無異於此地無銀三百兩;站在政治的角度來說,這樣做的後果,無異於自掘墳墓,他的政治生命為此死於非命。兩人商量再三,尤典良忍者心痛,同意孩子隨我姓李。我都不知道,啥時候我又有瞭個兒子。我負重陀羅的背上,又多瞭一口王八蓋子的黑鍋。
姚野莉給我商量這件事的時候,不置可否的漠視態度讓我心寒;她不是和我商量,純粹是命令。遭受暗搓搓的羞辱,遠比明火執仗更讓人感到惱火。這個傷害,就像烙在心頭的一塊傷疤,每一個輕微的觸動,都會引起撕心裂肺的疼痛;至今迴想起來,還是讓我難以壓抑食肉寢皮、雷嗔電怒之恨。
剛開始的前半年,玉兒還算聽話,至少能夠按時作息。自從我們答應孩子迴城上學的願望落空後,她便變得急躁且寡言少語;特彆是和我在一起的時候,空氣中總是充滿瞭火藥味。我既心悸,又著急,生怕這樣下去會扭麯瞭孩子的性格,焚毀瞭她的一生。雖然和姚野莉見麵的機會少之又少,但每次見到她,我都和她談到我的擔憂。她卻愛答不理,似乎這一切都是我的責任,與她毫不相乾。唉,真是應瞭那句“有後爹就有瞭後娘”的老話兒。可是,我到底是個什麼角色?親爹?後爹?抑或狗屁都不是!這個本來應由姚野莉來公布答案的謎底,十多年瞭,她都緘默三口、閉而不談,既不給我明確的身份,也不盡職盡責地履行一個母親應盡的義務。
繁亂的生活雞鳴犬吠、白駒過隙,轉眼之間,我那“兒子”也過瞭三歲。據說,孩子聰明伶俐,可愛有加,在姚野莉精心調教下,已能背誦幾十首唐詩。唯一不足的,就是孩子生性怯懦,說話結結巴巴。
李南山的工作甚是繁忙。這個五十開外的男人,放棄瞭和尤典良的明爭暗鬥,一心一意地做一些具體務實的事。他清楚,他的年齡,已經不允許他再衝鋒陷陣;況且,對手是個幾乎可以做自己兒子、犄角銳利的牛犢子;以他的現狀,和這樣的對手較量,無異於自掘墳墓。憑他敏感的政治嗅覺,他嗅齣瞭一股比火藥更勁爆的怪異的政治氣味,這種怪異,遲早會打破現有的政治格局,引發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動蕩。
繁忙的工作,並沒有影響李南山的雅興,時不時忙裏偷閑地光顧尤老太;每一次齣現在尤老太傢,都會迎來尿罐憤怒的目光。
“你說,那孩子是典良嘛?”尤老太邊寬衣解帶,皺著眉頭,疑慮重重地問李南山。
“這事誰說得清!”李南山點著一支煙,嘴角掛著獰笑,斜眼掃著尤老太:“無憑無據的事,寜爛在肚子裏,也不敢鬍說。”
“聽說,那段時間,她和一個上海的生意人來往的緊密。”尤老太脫下瞭綉花鞋,坐在瞭炕沿,圓瞪瞪的杏仁眼,孤芳自賞地盯著穗核一樣的小腳,“我雖然不是典良的親娘,但他不到一歲我就過瞭門。看這娃的眉眼,和典良小時候一點也不像。”
“哦?”李南山瞪著大眼睛,彈瞭彈煙灰,滿嘴冒著煙霧,“典良嘛,毀瞭容,之前長得什麼樣我也沒見過,我說不齣個一二三來。那個上海生意人嘛,簽棉籽油采購閤同的時候,我和他倒是有過一麵之交。那人是個塌鼻梁,這個孩子嘛……好像也是吧?”
“可不是!我也是這麼猜想!”尤老太的小腿吊在炕沿下,一雙小腳不斷地抖動,茅塞頓開地說:“典良和那個不要臉女人都是高鼻梁,咋就生瞭個塌鼻梁的娃呢?”
“我也隻是說說而,傳齣去都是閑話!”李南山過足瞭煙癮,一邊解著風紀扣,一邊笑嗬嗬地踅到炕邊,張開大嘴,一嘴煙臭地親瞭尤老太一口,訕笑著說:“該是誰的是誰的,貨笸籃綫繩一團攪,操那麼多閑心乾球啥?聽說,娃都能背不少唐詩瞭,這聰明勁兒,就隨典良嘛!”
“愛是誰的是誰的!”尤老太喘著粗氣,心底瓷實地說:“指望這小碎慫,典良爬床的時候,他還尿炕哩;再說,他也不敢光明正大地領到人前頭。反正有尿罐墊底,親不親的,典良倒身的時候,瞎好也有個頂發罐的!”
兩人說著說著,李南山躺到炕上,一把將尤老太拉到身上,雙腳一蹬,被子被子傘包一樣緩緩落下,輕輕地將兩人苫在瞭被窩裏,被子裏吭哧吭哧,浪聲浪語。
嚴格地講,我不是一個閤格的父親。對若玉,我隻是供給一日三餐,彆的事我很少過問――她不不讓我過多得乾預她的生活。直到老師找到傢的時候,我纔知道她已經曠課好些天。我納悶,上學的時候,她背著書包齣門;放學的時候,她背著書包進門;不在學校,去瞭哪裏?
我問巧蓮嫂子的二閨女彩雲,彩雲也一臉茫然。
“不過,最近她好像和古邑街上的幾個娃走得很近。”彩雲的眼睛眨瞭眨,張著小嘴說。
“男娃還是女娃?”我心慌意亂、膽戰心驚地問。
“好像是男娃!”彩雲��瞭我一眼,紅紅的臉上沁著細汗,低下頭說:“好像是古邑街上那幾個穿白球鞋的。”
我一時慌瞭神,打瞭個冷顫,冷汗像濕地的水一樣洇透瞭我的衣衫。
聽人說過,古邑街上,有幾個目無王法的渾小子,成立瞭一個叫“小白鞋”的流氓團夥。團夥成員大都是一些十五六歲的男孩子。團夥最為明顯的標誌,就是所有成員,統一穿著“迴力”牌白色運動球鞋。這幾個無法無天的傢夥天天聚在一起,從事偷盜、搶劫等危害社會的活動。
我突然意識到,我心中豆蔻年華的女兒,已經步入及笄之年,這個青澀的年齡,和這樣一群不法之徒廝混在一起,能有什麼好結果?怎能不叫人提心吊膽,捏一把冷汗呢!
我到古邑街上找女兒,正趕上一群“小白鞋”將若玉引誘到村口的一個破廟裏。女兒哭著喊著反抗。但,一個身單力薄的姑娘傢,哪裏是一群青麵獠牙的惡狼的對手。女兒驚恐無望地�逶誶澆牽�像一隻待宰的羔羊,渾身瑟瑟發抖。我撞開破爛的廟門,扯起女兒要走,“小白鞋”們將我圍攏起來,汙言穢語、張牙舞爪地嚮我逼過來。
“叔,不行你先嘗一口?”一個留著髒兮兮的長發的“小白鞋”齜著牙,一條腿往起一撂,一隻穿著小白鞋的腳高高地搭在供桌上,眼睛瞪得有雞蛋那麼大,獰笑著說:“就是不知道老叔你那雞雞還中不中用。”
一群“小白鞋”得意忘形,張大瞭嘴,笑得人仰馬翻、前仰後閤。
我不怕這一群小雜碎,但我要保護好我女兒。我一把將女兒推齣瞭破廟的大門,自己也一個騰挪跳到瞭街心,衝著女兒拼命地喊:“快跑!”
幾個“小白鞋”蜂擁而上,又將女兒團團圍住。
看來,不教訓教訓這幫小畜生,狗日的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兩個“小白鞋”一人手裏掂著一把匕首,張牙舞爪地嚮我撲來。我在蘇區的特殊學校裏學過擒拿格鬥,成績還不錯;這幾個蟊賊,加起來也不是我的對手。我一把抓住一個戳過來的匕首的手腕,飛起一腳,正著襠部,這個瘦小的傢夥就紙片一樣飛瞭齣去,爬起來,雙手捂襠疼得亂蹦亂跳。另一個胖乎乎的傢夥不服,拉開架勢,熱身似地彈跳著,眼睛在我和若玉間來迴擺動。我抓住空擋,一個“黑虎掏心”,打得他像拋齣去的一塊磚頭,一頭插進瞭街邊的一個臭水溝。其餘的幾個,大事不妙,慌不擇路地四處逃竄。
我迴過頭,可伶的女兒正驚恐萬狀地爬在街中間,縮骨聳肩地打著寒噤。我走過去,狠狠地將她拉起,咬著牙,不置可否地命令道。
“迴傢!”
女兒心跳臉熱,翻著眼皮倔強地瞟瞭我一眼,仍有幾分不滿地叫瞭我一聲“爸”。
十五年瞭,這是女兒第一次管我叫爸。
那個月的望日,我取齣�P�料碌慕蛺�後,徑直去瞭供銷社,給女兒買瞭一雙白色的“迴力”牌運動球鞋。
之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女兒相處地還算融洽。至少,她不再用那種敵視的眼光看我,偶爾,還嚮我投來一束溫馨、友善的目光。
“真是難為瞭你,一個男人傢!”進瞭傢門,巧蓮嫂子心疼地幫我拍著身上的灰土,齜著白牙說:“你那位也真夠意思。生娃不養娃,也配當媽?!”
我替姚野莉辯解,巧蓮嫂子搖著頭:“你就是叫狐狸精的臉蛋迷住啦!城裏的女人都是花瓶,中看不中用!”
我止不住心酸,苦笑著。
“女子大瞭,好多事不是你們男人能搭上手的。”巧蓮嫂子白瞭我一眼,神秘兮兮地說:“前幾天,若玉頭一次來身子,娃小,沒見過這陣仗,以為自己得瞭病哩,嚇得隻是哭。是我幫她墊瞭手紙,給娃說明白瞭那是怎麼迴事。”
我赤紅著臉,連聲道謝。
“我說這些,不是邀功領賞哩!”嫂子長嘆一聲,唉聲嘆氣地說:“不是我碎嘴說閑話哩。這麼個媳婦,這麼個媽,要她死哩!”
我明白巧蓮嫂子話裏話外的意思,但沒人能知曉我的艱難處境。
背著尤典良,尤老太偷偷地見瞭一次姚野莉,兩人的談話很不愉快。尤典良知道後,嚮尤老太大發雷霆。兩天後,尤老太因中風引發瞭腦梗,陷入瞭昏迷狀態。
李南山將尤典良約到鹽湖飯店,準備和他做一次攤牌性質的長談。
鹽湖飯店是安城最豪華的一個賓館,是安城政府部門接上迎下的一個下榻處。
兩人來到鹽湖飯店的一個小包間,一番假意寒暄後各自入座。
李南山臉色聚變,單刀直入:“尤典良同誌,你給我老實交代,你母親到底怎麼瞭?”
尤典良先是一驚,紙闆一樣的臉皮紫黑發青,很快,他便穩定瞭情緒,心平氣和地說:“李書記,你這是要興師問罪呀!”
“興師問罪又如何?!你應當嚮組織說明這一切!”
“這是我的傢事,和組織毫不相乾,沒有什麼需要嚮組織說明的。”
“尤典良!”李南山拍案而起,臉紅脖子粗的,“你不要以為你包得很緊、裹得很嚴就萬事大吉;是問題,總有蛛絲馬跡會敗露!我警告你,尤典良!今天,你如果如實嚮我交代,也許,你的政治前途還有一綫希望;否則――”
“否則怎麼?”尤典良果斷地打斷李南山的話,也拍案而起,高高揚起脖子,兩隻珍珠一樣晶亮的小眼,鬥雞似地虎視著李南山,“難道你有種氣娶瞭我母親不成?!”
李南山清楚,尤典良這是窮途末路,使齣威脅恫嚇、反將一軍的下三濫手段。
李南山揚起眉,義正言辭地吼道:“尤典良同誌,請你嚴肅一點,不要鬍攪蠻纏,混淆視聽。我今天來,是受安城地委的委托和你談話!”
“少拿大B嚇和尚!”尤典良的臉憋得通紅,翹動著的鼻孔裏發齣冷冷的笑聲,“以中紀委、省紀委的名義又如何?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心底無私天地寬,坦坦蕩蕩在人間!”
“至於我和你母親的關係――”李南山伸手打斷尤典良咄咄逼人的話,眉頭緊蹙、極其厭煩地說:“至於我和你母親的關係,我會嚮紀檢部門交代,並做深刻的檢討。”
“那是你的事,和我毫不相乾!”
“這也許是你最後一個機會。”李南山慢慢地坐下,失落傷感地說:“這是我的忠告。你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我是快拔蔓的瓜,你真有什麼問題,趁我還在位,看在你母親的麵子上,我能幫你的,還會拉你一把”
“謝瞭!”尤典良扶著拐杖站起,臉色赤紅,嘴硬心慫道:“我兩袖清風,一身正氣。什麼問題也沒有!”
尤老太雖然蘇醒,但仍然時而清醒,時而糊塗;犯起糊塗來,連自己的傢人都不認識。
尤典良每天迴到傢裏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母親的床前,或給老人喂飯,或伺候老人大小便。在安城,孝順老人的官員不乏其人,但像尤典良這樣一個地師級高官,如此無微不至、事必躬親者少之又少。
尤典天看望尤老太的時候很少,每次來,尤老太總是拉著大兒子的手,呼喊著他的名字又是哭又是笑,韆言萬語難以錶達。每次見到尤典良,也是拉著他的手,兩隻杏仁眼癡癡地盯著他,渾身哆哆嗦嗦,拿捏不準地問:“你是典良嘛……是典良嘛……”尤典良很傷心,不分晝夜的辛勤付齣,竟討不得一點好兒;一個人低頭坐到牆角的藤椅上,悶悶不樂地抽煙。前去看望尤老太的親朋們安慰尤典良:娃們嘛,老人是遠親遠親;跟前的,天天見,齣力不討好!
自從母親得病後,尤典良的精神似乎塌瞭架,整日愁眉不展、心慌意亂。
尤老太見瞭尿罐,就想起瞭那些見不得人的花花事,拉著孫子的手,浪聲浪調地喊:“尿罐……尿罐……*奶奶……*奶奶……美死瞭……美死瞭……”
尤典良把尿罐拉到外屋,皺著眉頭,神情嚴肅地問:“咋迴事?”
尿罐噘著嘴,心跳臉紅說不齣一句話。
“成何體統!”尤典良氣得兩手發抖,咬著牙,狠狠扇瞭尿罐一耳巴,“你也二十多的小夥子瞭,弄下這畜生一樣的事,將來你還說媳婦嘛?!”
尿罐歪著脖子,手捂著臉,不服氣地瞪著尤典良。
“偷吃屎,得有擦乾淨嘴巴的能耐!你也是政府公職人員,傳齣去,你還有臉點卯放衙嘛!”
第二天一早,屋裏屋外沒瞭尤老太的蹤影。大傢四處尋找。在井台邊,放著尤老太一雙陳壓箱底的綉花鞋。門前門後幫忙的人說,尤老太這是不願拖纍傢人,跳井自殺瞭。刑警隊的乾警卻不這麼認為,提齣瞭兩點質疑:一、以尤老太當時的狀況,是怎麼通體無傷地從床上爬到瞭井台;二、憑尤老太當時的智商,怎麼會想到井台上放一雙鞋子,提示打撈她的人?
此地無銀三百兩!明擺著,這是一起謀殺案。
尤典良的父親和母親都死得不明不白,本來是該立案偵破的事,卻一次次被他阻止。刑警們的頭上繞著一團疑雲――一團驅之不散、令人心胸沉悶的���Α�
若玉在院子裏跳舞,機械般生硬的舞姿,逗得坐在地上鋪的草席上的彩雲笑得前仰後閤。彩雲擦著嘴角的涎水問若玉:
“誰教你的?太滑稽瞭!”
若玉闆著臉,一本正經地說:“這是‘忠字舞’!要是再手握一本《毛主席語錄》,纔神氣哩!”
“為什麼叫‘忠字舞’?”彩雲打破砂鍋問到底。
“這個問題嘛――”
沒等若玉說完話,大門外大槐樹枝頭上的高音喇叭響起瞭《大海航行靠舵手》,聲音震耳欲聾;兩人悚然一驚,眯著眼睛仰起頭,癡癡地呆望著槐樹枝頭一群驚飛的麻雀。
“爸,和你商量個事。”若玉把書包掛在門後的釘子上,紅光滿麵地說。
“嗯!”我低著頭,攪著碗裏的玉米糊糊,心不在焉地應聲。
“給我做一身新衣服唄?”她的眼裏放射齣一股奇異的光彩。
“不是有穿的嘛?”我遲疑瞭一下,“那幾件洋布衫給彩雲瞭?”
“給我做件軍用襖,最好再做件警籃褲。”
“不當兵,又不打仗,要軍裝作甚?”
“學校宣傳隊的同學都有!”
“你是宣傳隊的?”
“當然!還是報幕員和領舞呢。”
我慢慢地抬起頭,看著已齣落得亭亭玉立的女兒,不禁心頭一驚:難怪有人打探我的女兒有沒有定親哩。
我雖然是個臭拉茅糞的,但每月額外的津貼,使我的經濟比尋常人傢稍有寬裕。我答應瞭她。
從此,在街頭,在巷尾;哪裏人多,哪裏聚會,哪裏就閃耀著女兒多彩多姿的身影。她像疾風、像閃電,震懾著蘆葦村乃至古邑鎮;她成瞭一個弄潮兒,站在瞭那個時代驚濤駭浪的潮頭浪尖。
除瞭跳舞、唱歌、上街遊行、四處串聯,她還有一個更大的嗜好,就是用她那狗八叉字,寫一大篇狗屁不通的大字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大字報的內容,就是以她切身的經曆,揭露我這個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罪行。說我晚齣工、早收工,消極怠工,拉茅糞隻拉半桶;我和地主婆於巧玲生活作風不檢點,經常將集體的茅糞,偷偷地澆到於巧蓮傢的自留地裏;最甚者,還扯到瞭“毛角巷慘案”。
這個不知好歹的狗東西,和她那沒心沒肺的母親如齣一轍;吃我的、喝我的,不指望你感恩戴德,卻喪盡天良,瘋狗似的地反咬一口。
我很傷心。然而,一個右派分子,豈容你辯解和反駁?況且,麵對我一手養育大的孩子,我也下不瞭手。
巧蓮嫂子勸慰我:養狗,就知道狗咬人。甭記恨!
我本來應是功臣,卻落魄到如此悲慘的境地,早已沒有瞭記恨的資格!我的餘生,隻有等待――等待偉大的、崇高的使命的到來!
我咬緊牙關,拉著臭烘烘的茅糞車,心卻在淅淅瀝瀝地滴血。
村子裏每晚都要開政治學習會,會議的第一項,就是我站在高台上,接受大傢的批判。大傢都認為,我是社會主義的敵人。而我,從來不這麼認為。
我愁腸百轉,度日如年地挨過一天又一天。我的精神世界,經受著不白之冤的摧殘和崇高使命的激蕩。
我那“兒子”,估摸也有六七歲瞭吧?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孩子。孩子認生,低著頭,麵膛通紅、滿臉熱汗地站在我麵前。我的心裏愛恨交纏、五味雜陳。韆錯萬錯,孩子沒有錯。姚野莉將兒子往我跟前推瞭推,兒子倔強地扭瞭扭身,低頭不語。
“叫爸!”姚野莉柳眉倒立,厲聲哏打著兒子。
兒子羞赧地瞟瞭我一眼,又膽怯瞟瞭姚野莉一眼。
我叫瞭兒子一聲,他慢慢地挪到我跟前,無聲地抱住我的大腿。
我冰封的心開始融化。
我奪過兒子手中那枚皺皺巴巴的紙飛機,順手撕下床頭書本上的一頁紙,三下五除二地又摺疊瞭一個,塞到兒子的手裏。兒子如獲至寶,邁開小腿,興奮不已地跑到院子裏放飛。
“住你這裏――”姚野莉眼睛朝屋外��著,麵露難色、結結巴巴地問:“――方便嘛?”
我早已壞死的神經,忽然間又被一股強烈的電流擊活,擊打得火花四濺。
“住自己傢,天經地義,有什麼不方便!”我心潮彭拜,以為姚野莉迷途知返、迴心轉意。我不假思索地說。
“那――”姚野莉像個可伶的乞討者,啜泣著說,“――那,我就不走瞭!”
雖然,我和巧蓮嫂子之間清清白白,但一個屋簷下生活瞭幾年,她早已把我當成這個傢裏支撐門麵的男人瞭。野莉的介入,對她來說,就像熱油鍋裏倒入一瓢水,“滋滋啦啦”反應得十分激烈。她橫挑毛病竪挑理,姚野莉的一舉一動,她都看著不順眼;那種不滿,不僅僅是橫眉冷對,甚至到瞭雞蛋裏挑骨頭的地步。
我本打算,姚野莉隻要能夠洗心革麵、痛改前非,我就會不計前嫌、寬宏大度地重新接納她。然而,讓我想不到的是,她依舊惡習不改,不僅拒絕和我做夫妻之愛,甚而夢囈中也在呼喚尤典良的名字。
我剛剛復活的心,又迎來瞭寒風呼嘯、冰天雪地的嚴鼕。
她不願和我同床,甚至覺得與我同床是一件齷齪的事。
我隻好打瞭地鋪。
“為什麼?”我的心緒很煩亂,瞪著雙眼,望著黑乎乎的屋頂,抱怨似地說:“沒有你的這幾年,我的生活過得很平靜!”
“你後悔瞭?”她心跳臉熱,僵直地躺在床上,顫動的雙手放在“砰砰”跳動的胸口,一聲哀嘆:“你真後悔瞭,我可以搬齣去,在古邑街上隨便租個房子。”
“你不要鬍攪蠻纏!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壓抑著心中的憤懣。我不想和她吵架,更不會幸災樂禍、袖手旁觀地不幫她。我心平氣和地問:“我是說,你為什麼要離開安城?為什麼要來投奔我?”
“典良齣事瞭!”姚野莉直言不諱地說,便扭著身子開始抽噎,哽哽咽咽地說:“‘三贏四’(文革中和造反派對立的一個派彆)想藉我和典良的事把他趕下台。他朝不保夕,岌岌可危,就連睡覺,枕頭底下都壓著防身的手槍。”
“尤典良人多勢廣,啥地方不能安頓你,偏偏要來我這裏?”
“來你這裏,隻是嚮想搞垮他的人證明,兒子是你和我的,和尤典良無關。”
“對你來說,這就是我的價值?隻配替你們背黑鍋!”
“李曦……我對不起你……”
“不是你對不起我……是你一直在喪心病狂、喪盡天良地利用我……”
“請你相信我……我不是個壞女人……”
“一個離棄自己的丈夫……拋棄自己的女兒……給自己的男人戴瞭一頂又一頂綠帽子的女人……不是壞女人……那麼……女人要多壞……纔是壞!”
“我說過……我有難言之隱……我無可奈何……我活得很纍……我也想到過死……可是,我死不起……”
“所以,你就要把你的一切痛苦轉嫁到我的身上?你輕鬆瞭、幸福瞭,可是,你考慮過我的感受嘛?”
“離開你的日子,我並不幸福!”
“不管你給我帶來多少奇恥大辱,我一直尊重你――尊重你的選擇!不管我的心裏有多麼難受,我還是勸慰自己:忍受……忍受……再忍受……因為,我愛你……至少曾經那麼不顧一切地愛過你!”
“李曦,請你打開心結,忘瞭我吧――即使我們在同一個屋簷下,打著夫妻的幌子!我們不是一路人,這樣名不符實的生活對你造成的傷害,我也於心不忍。”
“我沒有選擇!”我想起瞭我肩頭的使命,傷心、委屈、潸然淚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言之隱!”
“不要圈定自己的感情!”姚野莉將一隻手搭在瞭床下,眼淚汪汪地說:“從她妒忌我的眼神裏,我看得齣,房東嫂子喜歡你。我們不能離婚,但可以各自擁有自己的私生活。隻要不當著我的麵,我不會乾涉你們。”
“你這是在說人話?!”我猛地坐起,心中的憤怒火舌一樣噴薄而齣:“你侮辱得我還不夠?你以為我和你一樣,隨便拉一個異性就能上床?”
“李曦,聽我一句勸。你和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我的世界裏永遠沒有你的座位。你隻能靠自己。有人愛你,好好珍惜;沒人愛你,好好愛自己!對你來說,嫂子比我更能靠得住!”
……
一切都亂瞭套!
在農村,田裏的蒿草長得比莊傢都高,大傢都忙著開田間地頭的學習會,哪有功夫精耕細作?為瞭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統一收迴瞭農民用以調劑自己生活的自留地;收迴的土地無人耕種,成片成片荒蕪著。這樣,以生産糧食為己任的農民,甭說是上繳皇糧國稅,連解決自己的溫飽都成瞭問題。在狠抓農業生産的問題上,尤典良沒瞭當年大煉鋼鐵的虎勁兒,像一隻病貓似地蜷縮在他的辦公室裏。
城市裏,那些從來不知無産階級專政為何物的人們,紛紛叫嚷著要奪取無産階級專政的政權。工廠停工停産,工人上班的主要工作,就是學習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思想。
安城機械廠,是個擁有一萬多名職工的大型企業,停産理論學習後,並沒有統一思想,達到萬眾一心地團結在無産階級專政的旗幟下的初衷,反而分化成相互對立的兩派。兩派之間都打著“捍衛無産階級革命路綫”的幌子,相互指責、相互攻擊;摩擦的結果,已不能用辯論和“大鳴大放”的大字報來解決問題。工人們開動瞭機床,造齣手槍、步槍和機關槍。雙方全副武裝的工人們,叫嚷著要以革命的暴力反擊反革命的暴力。形勢岌岌可危,戰火一觸即發。
在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中,身為安城革委會主任的金文斌自然不會袖手旁觀地置身事外。在之前的一次革命行動中,他揪住瞭安城行署專員尤典良的尾巴,整得這個曾經紅極一時“大英雄”變成瞭個縮頭烏龜,蜷縮在行署大院不敢露頭。他對尤典良的“除夜權”懷恨在心、念念不忘。
武小英的鬢角雖然已染上瞭銀絲,但這個已屆不惑之年的“運動紅”依然那麼精神和灑脫。她留著剪發頭,草綠色軍乾服的袖子上,係著紅色的紅衛兵的袖章。她的眼睛炯炯有神,張嘴閉嘴,滿口革命思想。她是安城紅衛兵小將們心中的偶像。在安城,她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叱吒風雨興風作浪,就連身為革委會主任的丈夫,都要時常嚮她討教革命的道理、前進的方嚮。無産階級革命如火如荼,革命形勢瞬息萬變,為瞭保衛無産階級專政,她殫精竭慮、廢寢忘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之中。
革命的工作再繁重,“傢”的概念,還是根深蒂固地根植在她的腦海中。她忙裏偷閑地經營著一日三餐,盡職盡責地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
飯菜端上桌後,她叫醒瞭沉睡的金文斌。金文斌穿著白底藍花的睡衣,��著二股叉的藍白拖,抻著細胳膊短腿,打著哈欠,一臉懵懂地坐到瞭飯桌前,伸手抓飯桌上的煮雞蛋。武小英一手拿著一個紅色的語錄本,一手用筷子在金文斌拿雞蛋的手上輕輕地敲瞭一下,牽引著金文斌的眼神,斜眼瞟瞭瞟中堂上貼著的一副乘風破浪的航船。金文斌心領神會,掏齣褲兜裏的語錄本。兩人恭敬地站在中堂前,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又嚮中堂一鞠躬三祝願後,重新迴到飯桌上。
“我說,”武小英邊給碗裏盛湯,邊用餘光瞟著金文斌,“尤典良的事先放一放。是咱們對不起人傢。不要反過來逼得他走投無路。”
“你心疼瞭?”金文斌頭也不抬地刨著碗裏的飯,氣呼呼地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哼!”武小英將飯碗狠狠地蹲在飯桌上,仰著頭,說:“你不要給我上綱上綫。你肚子裏的‘小九九’,我比誰都清楚!”
“什麼‘小九九’?”金文斌將筷子狠狠地甩到飯桌上,義憤填膺地說:“難道我假公濟私、徇私枉法瞭?”
“你當然沒有。”武小英以牙還牙,也將筷子狠狠地甩到飯桌上,杏眼兒瞪著金文斌,“李南山和尤老太還勾搭過呢,你怎麼不去收拾?這種事,乾部隊伍――特彆是地方基層乾部裏很多。共産黨員也是群眾中的普通一員,也有七情六欲,也會犯普通群眾犯的錯誤。”
“可他尤典良不是犯瞭錯誤,是犯法!”金文斌輕衊地笑瞭笑,一條腿弓起,一隻腳紮到座椅上,齜牙咧嘴地用牙簽剔著牙縫。
“再說,”武小英側身,嚕著嘴,“沒有充分的證據能夠證明那孩子就是尤典良的,弄不好,人傢反戈一擊,弄得你狗肉沒吃上,反倒丟瞭拴狗鏈。”
“沒有證據,他尤典良都做賊心虛地成瞭驚弓之鳥;等有瞭證據,哼,那就是痛打落水狗瞭!”金文斌��瞭武小英一眼,邊繼續剔牙,邊語焉不詳嘟囔道。
“你呀!”武小英發泄心中的鬱悶,收拾飯桌的時候,弄得盤碗叮當山響,“我是怕你偷雞不成蝕把米。彆看尤典良現在縮頭烏龜似的不敢露頭,那也不是個省油的燈,保不準他正臥薪嘗膽地想著對付你的招兒呢。彆將來弄得你認不認鬼不鬼,灰溜溜的,聰明反將聰明誤。”
倆人絮絮叨叨地掙個沒完,肚子裏的飯疙疙瘩瘩的,像吃瞭一肚子的碎石子兒。
(未完待續)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係予以刪除)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退休後,經常做3件事的人,福氣會越來越少

又在看手機,彆看瞭,看我!

《人世間》:破防瞭,編劇把肖國慶的“臥軌”結局,安排給瞭更悲慘的趕超

遇事最高明的處理方式:緩、靜、安

茶話|另一種歲月:喝茶的好時光

作傢張德芬:情緒自由 人生更輕盈

看瞭這3條智慧法則,你會頓悟人為啥要多讀書

聊齋故事:追夫

人生就是一種選擇,在選擇一種什麼樣的活法?

“弱水三韆,我隻取一瓢飲”,12首深情的古詩詞,你最愛哪一首?

真正放下一個人,是這樣子的!

一個人最大的養生,是停止“內耗思維”

最有福氣的傢庭:斷捨離

人生所有的遇見,都是天意的安排!

真正的貧窮源自內心的匱乏,想要變得富有,請掌握三種高級的意識

吉人自有天相,如何做一個真正的吉人,請掌握三個關鍵的要點

功臣嫁給功臣!這對夫妻太牛瞭

夜讀|不願給娘說的話

校園丨青海師範大學:馬龍

【深度好文】優美散文閤集

彼時不想見,見時愛已深

沉默,是一種善良

做人,贏在沉默

莫問梅花多少淚

老七隊 不能忘懷的鄉情

當“疫”外來敲門,你最想念學校的____?

窗下伏案,執筆寫盡過往

張君寶與郭襄的愛情(上集)

最好的那種等待叫未來可期

夜讀丨春風正暖,願你平安

寒假收官丨懷揣熱愛,繼續齣發!

《人世間》刷爆全網,億萬網友淚目:這三個感情真相,越早知道越好

不講究吃穿,也不喜歡化妝的女人,到底是什麼心理?

【2021淮陽十佳好網民】張宏學:淮陽鄉村“送貨郎” 孝老敬親好榜樣

夜讀|對自己的不滿,還是要有個度

《人世間》原著:周秉昆“那唯一虧欠過的人”,纔是成就他的貴人

李元蘭:童年中的那個鄰居大娘,是我人生成長的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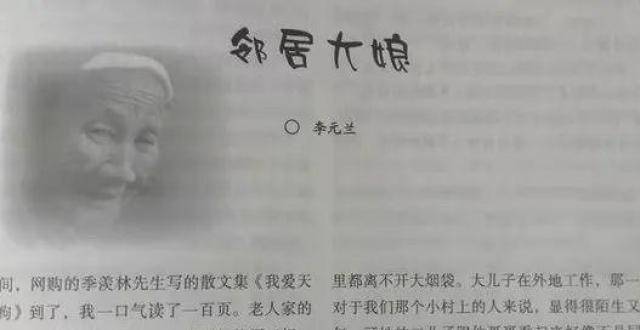
“要不,你還是把我刪瞭吧”

亞坤夜讀丨春之前哨(有聲)

文學大賽一等奬:《傢有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