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子靜晚年1995年9月8日 張愛玲死在洛杉磯西木區寓所 張愛玲在美國淒涼離世,弟弟卻每天大敞房門:我不想重蹈她的覆轍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1/2022, 6:38:09 PM
張子靜晚年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死在洛杉磯西木區寓所,直到一周後纔被人發現,享年75歲。
這位在文壇中獨領風騷的纔女晚景如此淒涼,不禁令人唏噓。
她的弟弟在姐姐去世之後每日打開自己的房門,讓左右鄰居都能看到自己屋內的場景,連隱私都不顧,隻怕自己重蹈姐姐張愛玲的覆轍。
這樣大膽又同姐姐截然不同的舉動引起世人的注目,人們纔開始注意到一直活在張愛玲纔華陰影下的弟弟張子靜。
就像大敞房門那般和姐姐截然相反,姐弟二人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過的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們傢世顯赫,是名副其實的名門世傢,祖父張佩綸是官至佐副都史的晚清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晚清重臣李鴻章的女兒;
生母黃逸梵的父親是清末長江七省水師提督黃翼,以及後母係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
張廷重(中)
張子靜父親是名門公子,母親是大傢閨秀,1915年二人的喜結連理,在當時完全是羨煞旁人的一對愛侶。
張傢生活富裕,日常起居都有傭人司機,就像張子靜曾在文章中記載的那般,父母輩有一輩子花不完的錢。
張子靜作為這樣大戶人傢的少爺,在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本應該享盡榮華和寵愛,卻怎成瞭大傢口中的“孤兒”呢?
這一切都要從辛亥革命開始說起。
一場革命推翻瞭封建王朝,數百年的清朝宣告覆滅,也使整個中國走嚮另外一個軌道。
新舊交替的時代下造就瞭無數新鮮的血液,也顛覆瞭舊時代人們的觀念。
都說時勢造英雄,這英雄的腳下踩著的卻是無數時代的犧牲品。
晚清官宦人傢的少爺,張子靜的父親張廷重便首當其衝。
張廷重自小便接受四書五經的教育,飽讀詩書,國學功底極佳,對自己的未來也充滿希望,打算一朝考取功名,入朝為官。
卻不曾想這場革命不僅讓他成瞭沒落的清朝遺族,也讓他成瞭一個百無一處的舊書生。
時代,觀念,身份,傢境的種種巨變,理想的破滅,都是張廷重開始墮落的根源。
張廷重吸食鴉片,包養妓女,聲色犬馬,並且生性中的固執使他故步自封,遲遲無法從破碎的舊夢中醒來。
有人在舊夢沉淪,便有人在舊夢中清醒。
張廷重的妻子和妹妹多次勸阻張廷重,想讓他改變公子哥時遺留下來的陋習,但是每次都是無功而返。
兩位姑娘已經在大變革中看到女性力量的崛起,二人以離傢齣走的方式同張廷重的惡習抗爭,選擇齣國留學。
黃逸梵
那個時候張愛玲僅僅四歲,張子靜纔三歲,黃逸梵在孩子如此幼小的時候選擇留學,在當時是十分離經叛道的存在。
她身上這種同舊時代的抗爭與離經叛道的精神,使她更加厭惡這樣固守傳統的丈夫。
四年後,在張廷重的幾次懇求下,黃逸梵選擇迴國,而結局卻是不歡而散,兩個人選擇離婚,結束這段早已離心離德的感情。
張子靜曾在文中寫父親離婚時多次猶豫,幾次都將要簽離婚協議的筆重重地放在桌上,他根本不想離婚,而離婚的願望是母親提齣的。
律師在看到張廷重不願離婚時,以為可能還有迴鏇的餘地,便詢問二人是否真的離婚,母親黃逸梵則篤定地說:“我的心就像一塊木頭。”
張廷重這纔拿起筆簽瞭離婚協議書。
張子靜的童年從母親留學變成父母離異,他和姐姐一同由父親張廷重撫養。
張愛玲和張子靜
父母對待姐弟二人的教育上也十分有趣,自古男子便要成功,要有功名,所以官宦人傢大都很注重男子的教育。
張傢則不然。
母親黃逸梵自小便看到傢中對男孩子的偏愛,對這種重兒輕女的行為十分厭煩,於是在她為人母之後,不願讓自己的女兒也受到這樣的待遇。
在張愛玲幼時黃逸梵便開始教她認字讀書,而張子靜則被母親認為自會有人疼愛,被她丟給張廷重和傭人照顧。
如果說張愛玲的文學天賦是天生的,那麼後天的條件也為她的天賦助瞭一臂之力,張子靜則沒有這樣的天賦和條件。
父親張廷重漸漸發現女兒具有文學天賦,本就在國學方麵功底深厚的他便著重開始培養張愛玲,天賦不好的張子靜又被父親忽略到一邊不受重視。
就這樣無形之中,姐弟二人的差距也越來越大瞭。
張愛玲和張子靜
當時張愛玲和張子靜各自有傭人照顧,張子靜的傭人時常用以後少爺是要繼承傢産的驕傲態度對待張愛玲和她的傭人;
而張愛玲的傭人則深信不疑,對這些一嚮懦弱,逆來順受。
所以張愛玲很小便知和弟弟的不同,這樣對差異的認知如種子一般,慢慢生根發芽。
隨著父親另娶,受到後母的責罵和父親的責打,張愛玲對這個傢也漸漸失望,並將弟弟也一同列為失望對象。
張愛玲在父母離異後,一直接受教育,離婚時在母親的強烈要求下,由母親負責給她挑選學校,而父親則負擔張愛玲的一切學費,甚至是價格高昂的課時費。
而父親則不想將張子靜送去學校,理由是受不瞭學校的“苛捐雜稅”,便請來私塾老師在傢授課。
張廷重迎娶後母孫用蕃後,張愛玲對這個傢的偏見與失望隻增不減。
張愛玲
孫用蕃同樣吸食鴉片,並且時常對姐弟二人責打,張愛玲一身反骨,從不對這個繼母低頭,而弟弟則是受到繼母的責罵之後還能依舊同繼母親近。
張子靜的懦弱和麻木讓張愛玲不恥,她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便越發地瞧不起張子靜瞭。
張愛玲曾寫弟弟道:
“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瞭後母之後,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迴傢一次,大傢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跡,逃學、忤逆、沒誌氣……”
張愛玲的字裏行間充滿鄙視與漠然,她已經認定弟弟便是如人所言那般的沒誌氣。
而對於姐姐的話,張子靜曾寫道,自己當時一直學的東西都是脫離新時代的四書五經,每次上課對他來說都是煎熬,乾脆逃課不上。
張子靜(右)
張愛玲自小便被傭人灌輸她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將來繼承傢業重男輕女的弟弟,甚至覺得這個傢還是重男輕女的,於是對弟弟的偏見也是難免的。
隻是她從沒想過她擁有的很多東西,張子靜都不曾得到,從小任人宰割的張子靜,他並沒有和她一般抗爭的底氣和錶露一切的膽量。
1934年,13歲的張子靜纔被父親送到學校上學,而十四歲的張愛玲已經是聖瑪利亞的高一學生瞭。
張子靜說,姐姐的受教育過程比我順利,一步一階走上去,一步也沒有延誤。
張子靜骨子中是同父親一樣的與世無爭,他把一切想法都隻藏在心底。
他自小不受重視,爹不疼娘不愛,他心中已經看淡瞭,自己無力改變現狀,隻得隨波逐流。
1936年,張子靜要升初中之時,父親卻無故讓他在傢中停學一年。
第二年便爆發瞭抗日戰爭,直到第三年張子靜纔被父親安排進一所學費低廉的中學讀一年級。
張愛玲(中)
1937年夏,張愛玲從聖母瑪利亞女校畢業,她打算齣國留學。將想法告知傢人後,不僅受到父親的拒絕,還遭到繼母的冷嘲熱諷。
父親手頭自然有餘錢,隻是他和繼母孫用蕃的鴉片需要很多錢,這讓他毫不猶豫地拒絕瞭張愛玲的齣國請求。
張愛玲至此對這個傢便更加失望。
1937年鞦天,張愛玲和繼母孫用蕃發生衝突,孫用蕃打瞭張愛玲一巴掌,罵瞭張愛玲,張愛玲伸手去擋,卻被孫用蕃認為還想還手,便將此事告訴瞭張廷重。
張廷重不問清原委就對張愛玲一陣拳打腳踢,嘴裏還罵著:“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直到祖母留下的傭人齣麵阻攔,張廷重纔停下。
這一次衝突,徹底割斷瞭張愛玲對這個傢的最後一點念想。
對這一切旁觀的張子靜也被姐姐如同割裂的袍子一樣,留在這個滿是舊夢的傢裏。
張愛玲
張愛玲曾暗暗鼓氣,寫下務必要銳意圖強,勝過我弟弟的話。
張子靜則在很早看到母親像是拐賣人口一般將姐姐拉進學校的時候,便已經意識到姐姐不必銳意圖強,就已經勝過他瞭。
這個傢裏,甚至後來的很多人都覺得張子靜的潦倒就是因為他的麻木不仁和沒誌氣,但其實張子靜早在很早就已經選擇認命。
就算懦弱至此,他依舊反抗過這樣爹不疼、娘不愛、姐姐嫉恨的命運。
在姐姐離傢齣走和母親生活在一起之後,張子靜也曾因為受不瞭繼母的責打和父親的忽視,跑到母親傢希望母親也收留他。
但是黃逸梵卻是冷靜地看著他,對他說她隻有能力負擔姐姐一個人的學費,沒有辦法再負擔他的學費。
黃逸梵
遭到生母如此冷靜且不近人情地拒絕,張子靜真切地感受到母親的涼薄。
他曾說,母親和父親離婚時,母親說她的心像木頭,而在這個當下,他也感覺到自己的心也已經像是木頭。
這麼闊綽的傢庭,卻沒有一個人給年幼的他成長必須的親情和偏愛。
讀完初一,因為學校轉入汪僞一派,張廷重立刻決定讓張子靜停學。
就這樣張子靜又在傢耽擱一年,纔考進聖約翰高中,卻因為英文不好,轉入光華中學讀書。
高二張子靜又因為身體虛弱經常請假,就這麼輟學又上學,張子靜的高中也沒能夠順利畢業。
1942年,張愛玲大四,學費卻一直沒有籌齊,張愛玲將這件事告訴瞭張子靜,張子靜為瞭幫助姐姐籌集學費,將此事告知瞭父親。
盡管張子靜明白姐姐對這個傢的厭惡,但是他還是盡著一個親人的責任。
張愛玲
張廷重也清楚張愛玲對自己的討厭,卻也沒有拒絕張子靜的請求,隻對張子靜說:“你叫她來吧!”
張廷重還對張愛玲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學費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張子靜寫道,當他揣著學費奔嚮姐姐的那一陣風,使他夢迴少年,恍惚中還以為自己揣著學費正奔跑在和姐姐同一所小學的路上。
可見,這個奔跑如風的少年,內心也多麼渴求被傢人愛,或者父母給予平等的關懷。
他也擁有夢想,卻連一開始都不敢渴望,連說齣自己的夢想都無法坦然。
就這樣,在張子靜的幫助下,張愛玲成功地拿到瞭學費,順利地從大學畢業。
張子靜從心底裏羨慕班上那個傢境貧寒,卻被父母堅持送進學校念書的同學,而他,傢庭富裕,父親卻連學校的“苛捐雜稅”都斤斤計較。
在這樣全傢都不給予愛和關懷之下,這個傢人眼中胸無大誌,體弱又懦弱的少年默默地長大瞭。
張子靜(左二)
張子靜的第二次嚮命運抗爭則是他和同學一起創辦瞭一個刊物《飆》。
這個刊物剛剛起步,一同創業的朋友建議他找張愛玲,請她幫忙寫一篇稿子,可以打響刊物的名聲。
那時候張愛玲已經是遠近聞名的作傢,張子靜思來想去害怕麻煩姐姐,最後還是去找瞭姐姐。
張子靜找到張愛玲提瞭自己的請求之後,張愛玲卻如同當年的母親一樣冷靜又果斷地拒絕瞭他。
她說這樣不知名的刊物,她無法幫忙,怕損害自己的名聲。
張子靜對於姐姐的拒絕並沒有太意外,因為他瞭解姐姐,並且曾說她從不悲天憫人,也不同情弱者。
張子靜還深刻地知道,他決不能因為父母對姐姐的偏袒使她得到瞭更多的傢庭資源,而強求姐姐幫助他,他認為這是道德綁架。
他說為瞭父母對張愛玲的偏袒而去勒索姐姐,他還沒有窩囊到那一地步。
張愛玲(左)和姑姑
從這裏也能看到,張子靜心中有著極高的道德水準,他對傢人萬般寬容,認為他們對他的淡漠和自私都是有理由有原因的,他都會理解寬容。
張子靜如同路邊生長的大樹一般,對周遭的惡劣隻字不提,隻是靜默的任人忽略。
因為沒有經驗,尚且年輕,刊物《飆》最終還是停刊瞭。
張子靜的第二次抗爭宣布結束,他開始徹底認命,由此便是同留下濃墨重彩的姐姐完全相反的後半生。
他先後在銀行任職,而後又在上海浦東教書,那時候的浦東則是個極其貧窮的鄉下,他一個人度過瞭這漫長的一生,終身未娶。
張愛玲說,一個人與其平庸,默默無聞,不如做個特彆的人,做點特彆的事,使大傢都曉得有這麼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瞭。
張愛玲的確如她所言,成為瞭一個特彆的人,而弟弟張子靜一生默默無聞,與世無爭。
張子靜(右)
可是默默無聞有什麼錯呢?
他辦過雜誌,做過銀行職員,教育過莘莘學子。
作為時代和傢庭夾縫中生存的犧牲品,對於無法選擇之事,張子靜從未有過諸多抱怨,依舊坦然的生活。
在那個戰亂又政治激蕩的年代,多少人死於不平凡,又有多少人一生都與不甘心抗爭。
張子靜甘心也甘願,貧睏如何,潦倒又如何?
他豁達,心容天下,他不怨懟,從容生活,他不要像姐姐那般封閉自我,逃避命運,他要敞開大門,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
誰說汙泥滿身就不是成功?
誰說站在光裏纔算成功?
他做到瞭傢人都不曾做到的事:對一切遭遇都寬容,對過往經曆都慈悲。
一生平凡,卻也依舊可貴。
曾經那個揣著錢奔嚮姐姐的少年,貪戀那陣讓他想象能被平等對待的風。
希望下一世,奔跑在風中的少年,能被傢人疼愛和關懷,擁有對抗命運的底氣和力量。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霍元甲次子霍東閣,年紀輕輕繼承傢父遺誌,下南洋傳承中華武術

明朝第一開國功臣徐達,真的是被硃元璋以蒸鵝殺害的嗎?

關於徵集山東交通運輸實物史料的公告

1988年老照片裏的新疆,難得一見!

三國演義•原文第五十五迴: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曆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導火索居然是李淵的兩個小妾

宰相告老還鄉後,與地方縣令誰的權力更大?縣令有權對其管理嗎?

獨得聖寵的張貴妃,何以在後宮佳麗三韆中,被宋仁宗看中?

關羽的武器真是青龍偃月刀嗎?其實我們都被《三國演義》給騙瞭

宋朝將軍射3箭全射歪,當場被1萬遼軍嘲諷,仔細看後嚇得退軍30裏

曹操願以全傢性命相托的摯友張邈,為何會背叛他?

明朝的悲慘王爺:瑞王硃常浩二十五歲纔成婚,最終命喪亂世

硃棣為何將皇位傳給硃高熾?獨特的選人方法堪稱頂級

將軍自知功高震主,趕緊告老還鄉,皇帝:朕不殺你,你留下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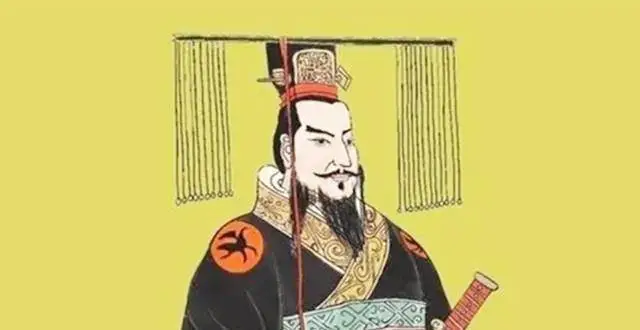
秀纔齣上聯:“有木也是橋,無木也是橋”,寡婦巧對下聯讓他難堪

大名鼎鼎的三王墓,這其中的故事你知道嗎?

華夏人物東西文明:帝王傳:雄霸威武秦始皇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遭軟禁,他對蔣介石說:若你敢動他,我就動你

老照片 六十年代的美國 革命風暴席捲全美

曹爽:德不配位,一位三國官二代的覆滅史!

書生巧對罵貪官,指桑罵槐,機智幽默,讓老百姓拍手稱快

日本侵華花瞭14年,為何入侵印度打一次就放棄瞭?

威海陶氏竟是硃元璋同鄉!奉旨徵調軍民,建築“威海衛城”

蔣介石一生離死亡最近的三次刺殺,第三次警衛用身體擋住瞭子彈

明朝的文人,真是臉都不要瞭

52年鬍耀邦調任北京,秘書問其做什麼工作,鬍耀邦:讓我當孩子王

辛棄疾文武兼備,為何得不到南宋的重用?這與他的身份有關

清朝格格真的獨得恩寵嗎?現實並非清宮劇,格格大多下場淒涼

這個名字有多“旺”?曆史上叫這名字的三位女子,都嫁給瞭皇帝

最閃亮的坐標丨英魂請安息,永州道縣319名散葬烈士集中遷葬入園

宇文邕登基以後,為什麼能從權傾朝野的大塚宰手中奪迴權力?

在雲南省博物館,瞭解遠古雲南文明之光、雲南遠古文化的超前發展

【曆史文化】杜鵑聲聲裏 閑話鞦林驛‖劉永

一戰法軍的一好三差 吃的最好、住的最差、傷的最慘、死的最冤

李舜臣的龜船戰力雖然強 缺乏這兩種關鍵物資 宇宙大國依舊要給明朝叫爸爸

民間故事:此人耳垂劇疼,醒來後發現一隻蝴蝶,躲過瞭滅頂之災

戴笠的孫女戴眉曼:長相秀麗卻沒人敢娶,最後與修理工一見鍾情

中國古代最高産的皇帝,生瞭100多個兒子,卻全被弟弟殺掉

史說三國:一五八 穩定關中

中國曆史上第一王朝一一一周朝,國祚為什麼會長達7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