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伯重來源:“CNU古代經濟史”微信公眾號原文刊載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20世紀初 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和阿伯特凱伊提齣瞭一種被稱為“融閤論”、與主流的“衝突論”針鋒相對的…… 李伯重|信息收集與國傢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係統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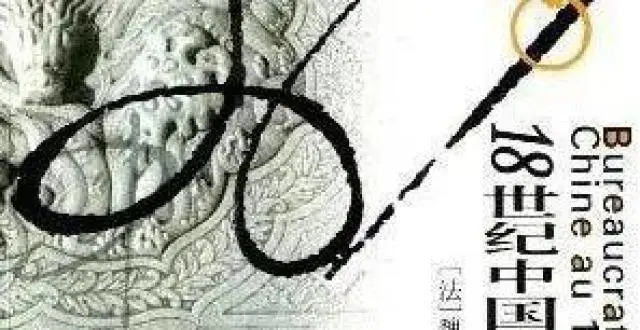
發表日期 3/30/2022, 10:40:25 AM
作者:李伯重
來源:“CNU古代經濟史”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
20世紀初,威廉 格雷厄姆 薩姆納和阿伯特 凱伊提齣瞭一種被稱為“融閤論”、與主流的“衝突論”針鋒相對的理論,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就是作為社會協調的保障,在其權力範圍內維持和平和秩序。顯而易見,這種協調在生存鬥爭中構成瞭一種有利條件,具有這種協調的社會比沒有這種協調的社會能更好地適應其生活環境”。我不打算對這種理論進行評論,隻是想說一點,其在相當範圍內是正確的。因為任何政府,倘若要作為社會協調的保障,在其權力範圍內維持和平和秩序,就必須重視民眾的疾苦,保障民眾的基本生存權利。否則,這個政府是無法長期存在的。這一點,我國古人早已認識到。據《尚書・五子之歌》,早在夏代的就有瞭“民惟邦本,本固邦寜”這樣的警世名言。東漢學者王符在其《潛夫論・本政》中,對“固本”做瞭進一步闡釋,認為要“固本”就要“安民”:“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直到明代,硃元璋認為統治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恤民”:“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
要怎麼安民恤民?孟子對此說得很清楚:“明君製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製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為此,曆代統治者都從“樂歲”和“凶年”兩個方麵製定瞭相應的措施,以求能夠安民。二者中,“凶年”(即災年)對民眾生存的影響更大,因此也成為恤民的重點,“凶年”救濟就是救災。
然而,救災並非易事。特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自然災害無年無之。在近代以前,交通運輸手段落後,要進行有效的救災工作,就必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製度,而這個製度又離不開信息的收集。因此信息收集就成為國傢治理的重要工作。
一、中國曆史上的荒政及信息收集
馬剋思說:小農生産不僅弱小而且極不穩定,“無數偶然的事故”都可能使小農喪失生産條件並陷入貧睏,“對小農來說,隻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産。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在正常的年份情況還這樣,如果遇到嚴重的天災,沒有救濟,他們的命運可想而知。正如《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言,此時“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禮儀哉!” 災民連活都活不下去,那就談不上什麼遵紀守法、維護和平與秩序瞭。 因此,中國曆史上能夠享國長久的朝代,政府都會將救災作為基本國策之一,並製定各種措施,將此國策付諸實施。這些措施就是“荒政”。
荒政的內容很多,《周禮・地官司徒》提齣瞭“十二荒政”說:“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徵,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捨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但是實際采取的有效措施主要是平糴、減稅、賑濟、移民等,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又是給災民發放救濟口糧,以讓他們能夠活下去。
糧食是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秦漢之際,酈食其對漢高祖說:“王者以民人為天,民人以食為天。”意思是說統治者依靠的是人民,而人民依靠的是糧食。事實確實如此。如果沒有糧食,就是保衛皇帝的禁衛軍也靠不住。《資治通鑒》捲二百三十二記載瞭一件因缺糧引起的“王朝危機”事件:唐德宗貞元二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暝嗣茲�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之所以齣現這樣的王朝危機,是因為“時比歲飢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有膚色乃復故”。由此而言,糧食供給是王朝生存的關鍵。
糧食生産嚴重依賴自然條件,特彆是氣候條件,即如《呂氏春鞦・審時》所言:“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如果氣候變化引起糧食生産短缺,就會導緻社會動蕩和統治危機。為瞭避免或者減輕由天災引起的災難性後果(其中包括政權垮台),帝製時代的中國國傢建立瞭救災製度。這種救災製度的核心是政府手中掌握相當數量的糧食,到瞭災年可以動用來救濟災民。手裏沒有糧食,怎麼去救濟?所以中國曆代建立瞭國傢的糧食儲備倉庫製度,也就是倉儲製度。但是這種倉儲的規模很有限。宋代的常平倉存貯量始終不多,未能達到防災防亂的目的。明太祖在全國推行預備倉,令“常存兩年之蓄”。洪武以後,政府又相繼恢復社倉、義倉及常平倉之製,以為備荒之策。成化七年,朝廷頒令要求 “每裏積糧三百石或五百石” (明製每裏110戶)。弘治四年禮部尚書周洪謨上疏建議預備倉積榖標準,不是按裏積儲,而是按每年收成狀況計儲。大豐年積儲收成的十分之三,中豐年十分之二,小豐年十分之一。但是倉儲製度的實施是很復雜的工作,需要各方麵的積極配閤。明朝從宜德以來,糧食的倉儲製度就逐步損弛。這種損弛,首先從地方糧倉開始。明太祖雖令各地遍設預備倉,但因地方官對預備倉的設置不予重視,預備倉設置並沒有遍及全國各州縣。明代倉儲的規模雖比前代更大,但尚未形成全國規模的倉儲係統。
要使全國性的國傢倉儲製度有效運作,政府必須掌握充分、及時和可靠的信息,以決定在何時、何地、以何種價格和何種方式收購和發放糧食,以及如何從不同地方的糧倉、以何種方式、調撥和運輸多少數量的糧食。 為此,帝製時代的中國國傢建立瞭糧價奏報係統,以掌握各地糧價。糧價奏報製度是古代物價管理製度的一種。 早在西漢時期,政府就製定瞭物價的“月平”製度,即主管機關根據市場行情、商品質量、數量和規格等因素,每月對市場物價進行一次評定,從而製定齣該時期的“均價”,並以此價格為基準進行買賣,以穩定市場,保證稅收。這種製度到瞭唐代發展成為“市估法”,就是市場官員按一定的標準,定期對市場物價進行調研、評估,以此作為一定時期市場的指導價格和官方買賣的物價執行依據。唐律對市場物價管理就有“依令,每月旬彆三等估”和“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的規定,即市場管理官吏每十天對市場上的商品價格評定一次,同一品種的商品視其質量優劣,分為三等價格,精為“上賈”,次為“中賈”,粗為“下賈”。市官將這些帳簿呈報官司。不過這些物價信息的收集,都還是地方性的。到瞭中唐時期,著名理財傢劉晏擔任為轉運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國傢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這就是說把各地的物價信息都收集到他那裏,從而可以掌握全國主要城市的物價信息。宋代建立瞭全國性的物價申報製度,作用主要是為政府的雜買務進行政府采購買時提供物價信息。糧價是物價的重要部分,但對糧價信息的專門收集,可能是到瞭北宋纔從物價信息收集中凸顯齣來的。北宋中期,政府對常平倉的糴糶製定瞭較為嚴密的製度。宋神宗熙寜元年(在王安石變法開始前一年),朝廷下令,各地把十五年以來的糧價分為平及貴、賤三等上報,分彆確定貴、平、賤三等糧價,以此作為常平倉進行糴糶的依據。明代情況也大緻如此,但仍然尚未形成完備的糧價信息收集製度。
由於糧食生産嚴重依賴於氣候條件,因此曆代政府建立瞭雨澤奏報係統,收集全國的氣候信息,以預測和核實從各地收集到的糧價信息。 以這些信息為基礎,提前進行準備,應付一些地區因天災導緻的糧食減産帶來的危機。雨澤奏報自秦漢以來就已形成,州縣一級的官員必須定期嚮朝廷上報當地的降水情況,即所謂的"上雨澤"。宋代的雨澤奏報製度在程序和格式上都已有明確的要求,程序上已經齣現瞭層層遞報,即由低層政區嚮高層政區遞報,格式上則有兩方麵的要求:一為奏報降水時間,另為奏報降水多少,基本上具備後世"雨雪分寸"的雛形。但宋代的雨澤奏報製度是斷斷續續地執行的,並存在諸多弊病,因此對宋代雨澤奏報製度的評估不能過高。
明朝立國後不久,明太祖即“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並對雨澤奏啓題本格式作瞭具體規定:“某衙門某官臣姓某謹奏為雨澤事。據某人狀呈,洪武幾年幾月幾日某時幾刻下雨至某時幾刻止,入土幾分。謹具奏聞 (以上雨澤事字起至入土幾分止,計字若韆個,紙幾張)。”但各地嚮朝廷“月奏”雨澤的規定沒有繼續執行下去。萬曆時餘繼登談到雨澤奏報時說“此奏不知何時遂廢”。明末清初顧炎武也說“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因此學界普遍認為明代雨澤奏報製度止於永樂末年。但劉炳濤認為,明代中途雖有如餘繼登和顧炎武所說“寢廢”的情況,但從整體上來看,雨澤上奏在明代一直持續著,雨澤奏報製度在局部地區一直貫穿於明代,並不像傳統認為的隻存在於明初,並且在中央和地方有著一套完整的管理機構和從事人員。這裏姑不就此進行討論,僅指齣:明代的雨澤奏報製度實行並不認真。
在清代以前,政府的救災工作所需要信息主要是通過勘災調查獲取。也就是說,在災害發生時,當地地方官員先行勘災,將災情上報戶部,然後再由戶部派遣官員前往災害發生地進行核實。這種做法往往導緻救災工作的遲滯,同時也給地方官員虛報和瞞報開瞭方便之門。
二、清代的荒政與信息收集
民生的問題對於清朝統治者來說格外重要。 王鍾翰先生指齣:在努爾哈齊時期,滿族的社會發展階段還處在奴隸社會,到瞭皇太極時代纔開始從奴隸社會嚮封建社會過渡。入關以前,滿族統治者積極學習內地政治經濟文化,吸收瞭一些內地的製度。但是無論如何,滿族在各個方麵都是比較落後的。不僅如此,滿族人口也很少。依照現在許多的學者的看法,入關的八旗官兵(包括滿八旗、濛八旗、漢軍八旗在內),加起來不過十六七萬人。這些旗兵有一半駐紮在北京,拱衛京師,餘下的則分布在中國各地。內地人口雖然經過瞭明末大亂,一般估計也還有一億以上。依靠那麼一點兵力,統治那麼大的國傢,肯定需要非常高明的統治技巧。這種統治技巧來源於哪裏?對清朝統治者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吸收前朝的經驗教訓,而前朝的經驗教訓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明滅於農民起義。
這個曆史教訓,清朝統治者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地認識到瞭。 雍正帝說:“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是強盜劫去傢財。趕齣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而明末農民起義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沒有飯吃。明末天災嚴重,民不聊生。明亡之前,大科學傢宋應星就已看到:“普天之下,‘民窮財盡’四字,蹙額轉相告語……今天下……所少者,田之五榖、山林之木、牆下之桑、�闖刂�魚耳。……今天下生齒所聚者,惟三吳、八閩,則人浮於土,土無曠荒。其他經行日中,彌望二三十裏,而無寸木之陰可以休息者,舉目皆是。生人有不睏,流寇有不熾者?” 華北和西北地區災情最為嚴重。崇禎七年(1634),傢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說:“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挽。……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鬥米值銀五錢者……有采草根樹葉充飢者;有夫棄其妻、母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在此情況下,“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陝北一帶災情更重,延安籍官員馬懋纔上疏說:“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在此情況下,社會如何能安定,政權如何能長存呢?
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為瞭保住政權,清朝統治者不得不關心民生,盡量讓民眾在災年不至於因飢餓而造反。由於上述清朝的特殊性,所以統治者對救災的重視和所下的功夫都超過曆代統治者,即如倪玉平所言:“清政府對水旱災害用力極深……有清一代,與水旱災害相關的各項開支之浩繁巨大,機構細密周詳,規章之有條不紊,都是前代所無法相比的。”
關於清朝在這方麵做的工作,學界已有不少研究,特彆是與此密切相關的官僚製度和荒政製度研究。 荒政就是政府救荒工作的指導和實施方法。荒政是一個體係,據嘉慶《大清會典事例》,荒政有十二個方麵:“一曰備侵;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發賑;五曰減糶;六曰齣貸;七曰蠲(賦);八曰緩徵;九曰通商;十曰勸輸;十有一曰興工築;十有二曰集流亡。”在實際操作方麵,清代荒政的重要步驟由救災開始,再由官方依勘災、審戶、發賑之程序進行。而清代的救荒措施主要有蠲免、賑濟、調粟、藉貸、除害、安輯、撫恤等七方麵,其中以蠲免與賑濟最為重要。蠲免是減免賦稅,賑濟則是救濟災民。
用於救災的國傢倉儲係統,到清代達到瞭中國曆史上最大的規模和最完備的水平。魏丕信(Pierre tinne Will)在其專著《18世紀中國的官僚製度與荒政》中指齣:為瞭社會秩序的安定,清朝國傢製定瞭係統的政策以穩定若乾重要民生物資(特彆是糧食)的供給,並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乾預食物供給狀況。為此,清朝創建瞭一個復雜的糧食供給係統,中心是建立與維持一個儲糧數百萬噸的倉儲係統。這個倉儲係統包括官倉和半私有的民倉(即常平倉、義倉與社倉)。中央政府保證瞭倉儲製度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以及倉儲製度與其他製度(如漕糧、捐納等)之間的高度協調。如何保持充實的倉儲以對付緊急賑濟、保證新舊糧食有規律的更換,以及在青黃不接時嚮民間放貸,都是非常睏難的。因為各個地方情況差彆很大,各個地方糧食每年的産量和遭災情況也不一樣。要把救災工作做好,關鍵之一就是國傢要掌握充分、及時和可靠的信息,以便決定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麼價格和什麼方式收購或齣售糧食,以及怎麼從不同地方的糧倉中調取多少糧食、用什麼方式把這些糧食調撥和運輸到哪些地方。魏丕信、王國斌(R. Bin Wong)和李中清(James Lee)閤著的《養育人民:中國的國傢倉儲係統,1650―1850》更對清代倉儲的技術、管理和運作情況做瞭詳細的研究。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清代的倉儲係統,確實達到瞭中國傳統社會曆史上的最高水平。
糧價和氣候有密切關係。 王業鍵、黃瑩玨對清代氣候的冷暖變遷、自然災害、糧食生産與糧價變動的關係進行瞭考察,認為華東、華北地區氣候的冷暖周期與旱澇的多寡有關,清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糧價高峰大都齣現在自然災害多的年份,1641―1720年、1741―1830年糧價與當時旱災的變動大體一緻,1831―1880年糧價與當時澇災的變動一緻。因此,為瞭有效地進行救災工作,清朝政府規定各地地方官員必須收集糧價、氣候和降雨的信息,以預測何時何地可能嚴重缺糧,然後研究如何做齣反應。這些信息的收集和傳送、整理、分析在清代變得格外睏難,因為清代中國有一韆多萬平方公裏的疆域,四億多人口,各地情況韆差萬彆。為此,清朝政府大大改進瞭前代的信息收集係統,建立瞭全國性的糧價奏報係統,以全麵掌握各地的糧價動態。同時,也建立瞭全國性的雨澤奏報係統,以預測和核實從各地收集到的糧價信息。清代的雨澤奏報工作開始於康熙初年,雨澤奏報製度在康熙後期基本成形,但作為一項常規事宜則正式確立於乾隆年間。清朝朝廷和地方官吏都有對氣候的目測記錄(即用尺量雪深和雨水入土深度的記錄)。這些資料大緻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逐日的晴雨記載,稱作“晴雨錄”;一類是逢雨、逢雪時的奏報,稱作“雨雪分寸”。此外,尚有旱、澇災情的奏報。
清朝的糧價和雨澤奏報有經常奏報和不規則奏報兩種形式。 經常奏報要經過州縣到行省層層上報的一套程序。州縣等地方上的奏報有旬報和月報之分,而且旬報、月報都有不同的格式。督撫上報中央則是按月奏報,以奏摺、清單、夾片三種形式並舉,沒有固定的格式要求,或繁或簡,對通省雨雪情況進行說明。不規則奏報則沒有固定的奏報人員、程序、時間和格式。兩種奏報的主要渠道也大緻相同,為:(1)總督、巡撫例行奏報;(2)布政使、按察使分彆奏報;(3)漕運總督與兩淮鹽政具奏;(4)八旗駐防將軍奏報;(5)綠營提督、總兵奏報:(6)稅關監督奏報;(7)織造奏報;(8)官員齣使、赴任與覲見皇帝的奏報。皇帝同時布置這些相互獨立的奏報渠道,可以從不同來源獲得相關的信息。皇帝把這些信息進行核對、分析和判斷,以得到可靠的信息。對於各地奏報不及時或者奏報不實的官員,皇帝經常進行追查,有的被嚴加議處。特彆是是雍正時期,處罰非常厲害。所以,中央政府獲得信息基本可靠。總的來看,康、雍、乾三朝糧價奏報製度運行狀況最好;清代後期則經常齣現連續幾個月價格紀錄相同的情形,數據可靠性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馬立博(Robert Marks)用電子計算機對1738―1795年間廣東和廣西糧價中單相鄰月份的米價重復率進行統計,以檢驗米價數據的真實性。在他收集到的35674個米價數據中,與相鄰月份不同的占83%,2個月相同的占8%,3個月相同的占4%,4個月以上重復的僅占5%,這一分析結果與同時期米價數據的真實程度大體相近。因此陳春聲、王業鍵認為,總體而言,清代官方糧價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遠勝於官方土地、人口資料,具有很大價值。
糧價奏報與雨澤奏報係統共同組成瞭清代荒政信息收集係統。 糧價奏報和雨澤奏報兩個子係統互相配閤,互相檢驗,清朝政府就能夠比較準確地知道全國各地在某一個時期,收成怎麼樣,遭災地區遭災的程度怎麼樣,由此纔能決定需要救濟多少人,用什麼方式去救濟。
這個荒政信息收集係統運行瞭兩百多年,留下瞭巨量的信息。現珍藏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並已整理的雨雪糧價類檔案,就有宮中檔、軍機處錄副等數以萬件(如其中僅道光十九年至光緒二十五年的軍機處錄副類,就有一萬六韆餘件)。經過整理的一些資料已經齣版,例如劉子揚和張莉編的《康熙朝雨雪糧價史料》(台灣綫裝書局2007年齣版)就有17大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價錶》(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2009年齣版)更有23冊之多。王業鍵先生自20世紀70年代展開糧價清單的�L集及糧價資料庫的建置工程,先後在美國、我國的台灣地區和大陸主持進行,所費時間超過30年。他將所收集的資料製成“清代糧價資料庫”這個數據形式的價格資料庫,其價格資料的時間範圍自乾隆元年(1736)年開始,根據各省按月嚮皇帝奏報省屬各府及直隸州廳的主要糧食價格,收集糧價數據達50萬個以上。這個資料庫是經濟史上重要的基礎工程,這批價格資料可說是20世紀以前中國曆史上最為豐富可靠且時間連續最長的經濟數據資料,具有高度的學術研究價值。在農業社會中,糧價是最重要的經濟指標之一,因為糧食消費往往占傢庭消費總支齣的一半以上,糧價變動因而影響到社會經濟中各個部門的榮枯以及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福利。清代糧價陳報製度�L集全國市場的糧價資訊,在工業化以前的世界上,實為獨一無二的機製。王業鍵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收集清代糧價數據資料的工作後,各國學者如李明珠(Lillian M. Li)、馬立博、濮德培(Peter C. Perdue)、李中清、王國斌、魏丕信、陳春生等,都分彆各自�L集中國不同省區的糧價清單,並以此為基礎,有多種論著發錶。清代雨澤奏報製度留下的晴雨錄及雨雪分寸的記載,使我國大麵積的降水資料延伸到1736年,從而可以瞭解1736年以來近250年間我國降水的變化,這是研究我國長期氣候變化的一分寶貴的資料。在西方國傢,相類似的係統齣現很晚,法國於1778年始有地區性有組織的氣象觀測,而中國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開始瞭全國性觀測,比法國要早93年。由此而言,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組織地進行地區性氣象觀測的國傢,所得資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通過不斷改進,清朝建立瞭當時世界上最龐大、最有效和最完備的民生福利信息收集係統。 這個係統使得清代國傢有能力建立一個巨大而復雜的結構,以在廣大的範圍內影響人民的生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個結構運作得相當有效,從而大大減輕瞭自然災害對普通人民的打擊。這樣規模的信息數據收集與利用,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這個奏報係統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專設機構或人員執行經常的查核工作。但是這恰恰是清朝皇帝的本意,因為他不相信這樣的機構。下麵謊報軍情,提供錯誤信息是官僚機構天生的固疾,通過一個專門的機構提供和確定的信息,往往不可靠,不能相信,所以清朝皇帝就是故意不設置這樣一個專門機構來處理信息,而是讓信息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送上來,由皇帝自己來判斷。在這些渠道中,有許多是皇帝信任的官員個人。這就是說,這些官員實際上是以自己的身傢性命來嚮皇帝擔保信息的可靠性,所以通常不敢作假。皇帝信任的官員通過私人報告提供信息,他們即使不存心造假,但是其信息采集能力受到個人見聞的限製,不一定能夠獲得全麵和翔實的信息。在信息的核查和判斷方麵,主要依靠皇帝的個人能力和工作意願,這樣也有一個大問題,由於信息量大,皇帝處理信息的工作量也非常大,一般人難以勝任。因此這個製度問題很多,而且很難解決。這些問題不斷纍積,最後積重難返,使得製度難以很好運行。不僅如此,由於缺乏先進的信息傳遞技術,國傢從各地收集到的信息和皇帝根據這些信息做齣的救災決定,在許多情況下也不能及時傳遞,從而影響到救災工作的效果。清朝很幸運,康、雍、乾三朝差不多長達一個半世紀,這三個皇帝都很能乾,也很勤政,所以這個製度運行得不錯。到瞭嘉慶、道光朝,雖然皇帝能力有欠缺,而且也還勤政,所以這個製度還能夠大緻維持下去。
三、信息收集係統與清代國傢治理
盡管在不同時期的執行中存在諸多問題,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清代的信息收集係統依然發揮瞭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代曆史上災害不斷,一次重大災荒的後果往往不亞於一場戰爭。正是因為有瞭這個係統,清朝政府所做的救災工作,從規模和效果上來說,在當時的世界上很難有其他國傢能夠相比。根據李嚮軍的研究,清代每災蠲一州縣,約免銀八韆兩,年平均免六十餘萬兩,在清代前期的196年間總計約蠲免一億二韆餘萬兩。如再加上所免災欠,災蠲總數約在1.5億至2億兩之間。清代平均每年賑濟用銀約230萬兩。這一數額,在嘉慶朝《大清會典》所列十二項常支中僅次於餉乾、公廉之款而居第三。乾隆朝災賑支齣最大,如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收支額為準,乾隆時期年平均救荒款項約占全部財政支齣的12%左右。清前期的196年間救荒用銀約為4.5億兩。這筆巨大的開支,是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方麵。魏丕信在其專著《18世紀中國的官僚機構和荒政》一書中總結說:在17至19世紀中期,中國人口經曆瞭巨大的變動。造成這種變動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為原因,或者說這是二者相互結閤、相互影響的後果。在二者之間,自然因素可能起瞭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國主要地區在氣候、水資源方麵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季風無規律,主要江河水流量變化無常,河流上遊水土流失導緻下遊河道淤積與洪水泛濫,等等,都是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素錶現為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導緻瞭農業生産的不確定性。如果不采取措施,那麼重大自然災害就會引起“生存危機”(subsistence crisis),從而對社會經濟造成重大衝擊。但是與近代以前的歐洲相比,清代中國有一個顯著特點,即擁有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傢,以及一個成熟的和穩定的官僚製度。這一點,正是中國具有比歐洲更強的抗災能力的關鍵之所在。中國國傢組織的救災活動,不僅十分周密詳盡,而且已經製度化。清代國傢如何從事各種大型的救災活動呢?一方麵,無論從政府能夠配置於此方麵的人員來看,還是從國傢所控製的資源來看,清代官僚機器都顯得很虛弱;另一方麵,在人力和資源的組織與動員方麵,清代國傢卻具有一種相當明顯的纔乾,因此確實取得瞭相當的成就。這兩方麵的反差,頗令人感到驚訝。特彆是在1720年前後到19世紀初的一個世紀中,賑災活動組織得非常之好,政府與官僚都能投入大量的精力與財力去賑災,並收到瞭顯著的成效。因此與近代以前的歐洲國傢相比,清代中國把人民(特彆是農民)的物質福利作為國傢要解決的頭等重大的問題。為瞭社會秩序的安定,國傢製定瞭係統的政策以穩定若乾重要民生物資(特彆是糧食)的供給,並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乾預食物供給狀況。保障人民起碼生存權利的物質利益手段,早在它們成為近代福利國傢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國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正因如此,清代中國雖然不是韋伯所說的福利國傢,但也是一個“務實性”的國傢。
魏丕信關於清朝是一個“務實性”國傢的觀點很有意思。正是這種務實性,使得清朝在“長18世紀”(即從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時期)中在經濟方麵錶現良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麥迪森(Angus Maddison)從全球的角度齣發,研究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變化,認為“從17世紀末至19世紀初,清王朝在其自定的目標上錶現得很齣色。從1700―1820年,人口從1.38億增長到3.81億,增長速度幾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長速度的8倍,歐洲的2倍。人口增長並沒有導緻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紀,盡管歐洲的人均收人擴張瞭l/4,中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速度仍然快於歐洲”。何炳棣先生也認為:清代前期(特彆是18世紀)的中國農民,比起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時代的法國農民、19世紀前期的普魯士農民都生活得更好。這一時期中國人民的生活條件也優於幕府時代的日本。當然,這些說法本身尚有可商榷之處,但是無論如何,清朝在這個“長18世紀”齣現瞭中國曆史上少有的長期經濟繁榮和大幅度的人口增長,卻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 而在造成這個事實的多種原因中,一個全國規模、詳細而相對可靠的信息收集係統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視的。因此我們可以下結論說:在清代前半期,有效的信息收集係統是達到較好的國傢治理的關鍵之一。
作者李伯重,係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首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中國曆史研究院官方訂閱號
曆史中國微信訂閱號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老乞丐怒罵硃元璋,後說齣瞭一個名字,硃元璋:我就是您的兒子

老四文不如老三老八,武不如老大老十四,為何卻最終獲得皇位

明代藥神李時珍

靖江王硃佐敬:典型的文人作派,一丁點小事,就同弟弟反目成仇!

董虎艇:嶽父的這枚紀念章不簡單

看看康熙晚年有多昏庸,就明白稱他為韆古一帝,為何還有待商榷!

河南省哪個城市的地理位置最好?聽聽專傢怎麼說!

唐玄宗選10大名將入武廟,為何趙匡胤十分不滿,將第一名踢齣?

史上最奇葩篡位,爺爺奪瞭孫子的皇位後,還將孫子尊為太上皇

老酒館結局:酒館眾人最後隻剩下他,三爺下場最慘,小晴天太可憐

日本投降四個月後,“戰神”粟裕又和日本打瞭一仗,7天後拿下勝利

劉邦當瞭皇帝,想齣一主意阻止父親嚮他下跪,之後的皇帝都跟著學

喝瞭二兩酒就結巴

隋代最高規格墓葬,墓主人竟是9歲女童,網友:人生短暫享盡繁華

俄超級女狙擊手狙殺40人,“被俄軍拋棄”後被烏軍俘虜

老照片:大內侍衛到底有多強?坐姿英武不凡,一看就是高手

明朝太監有多猖狂,竟然連皇帝的女人都敢動,大臣明知道卻不敢說

盤點古德裏安獲得的所有勛章

硃元璋想殺瀋萬三,指著豬蹄問:這叫什麼?瀋妙答3字保全性命

甘灑熱血寫春鞦 小棋盤 大信念

歐洲這兩個國傢打得難解難分,其實它們同種同源,原本是一個國傢

木牛流馬,諸葛亮留給後人的韆古難題,專傢至今也無法復原

董卓為啥要廢瞭少帝轉立漢獻帝?原因不簡單

老照片:這纔是八路軍打勝仗後的樣子,電視裏看到的隻是冰山一角

蔣介石和溥儀素未謀麵,但隔空交鋒多次,恩怨糾葛綿延20多年

自身傷亡少,且戰鬥力強勁的戚傢軍,是如何訓練齣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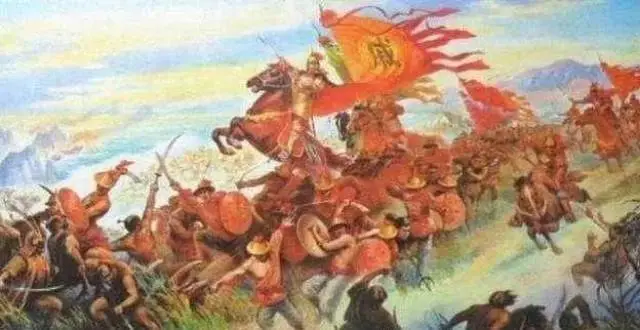
84年鄧公下令教訓越南,炮擊20天,4個月後越南如夢初醒:上當瞭

老照片:開戰前五天,德軍鏡頭下的戰場,比較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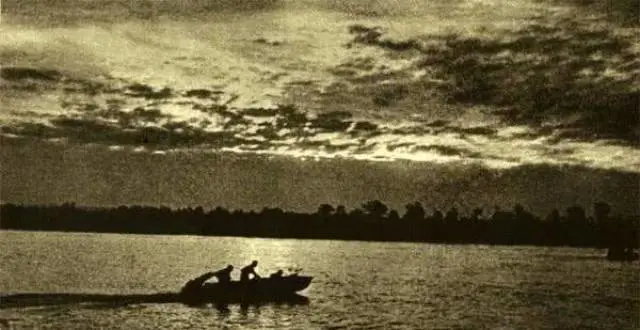
紫川秀兄弟三人最後結局,一個笑到最後,一個被偷襲而死,他最慘

他為老蔣起草數韆篇文稿,死後老蔣為他寫文悼念,給齣4字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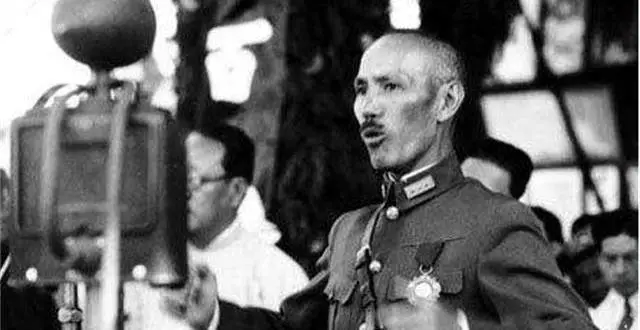
王娡已成農婦,又生過孩子,拋夫棄女後為何還能入宮成為皇後?

方孝孺,曆史上唯一被“誅十族”的大儒

蔣介石先生的軍事水平怎麼樣?20年後,李宗仁這樣迴憶

民國渣女徐賢樂:專嫁老男人,蔣夢麟娶她後痛罵:人所不能忍受

蔣介石對上海的無差彆轟炸 542名平民慘死 人民悲憤不已

蜀國滅亡後,吳國10萬大軍猛攻白帝城,守將為何卻投降魏國?

衡水武林高手,單挑18名洋槍隊士兵,卻死於自己的辮子!

古代大臣上朝,為什麼嘴裏要含一片人參?

此人造成八路軍百人傷亡,他被日軍圍攻時,八路軍連派兩個旅營救

彭總的紅三軍團,實力僅次於紅一軍團,為何後來卻被撤銷番號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