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逄春階第一章 牛二秀纔“你看把你纍的 不就給我洗瞭個臉嗎?”“師叔說 《芝鎮說》第二部14|跟宮師父一麵之緣,牛二秀纔像做瞭一場夢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8/2022, 1:12:47 PM
□逄春階
第一章 牛二秀纔
“你看把你纍的,
不就給我洗瞭個臉嗎?”
“師叔說,老人傢這是在練眼力、手力。”牛二秀纔道。跟宮師父的一麵之緣,牛二秀纔好像是做瞭一場夢。
那天大傢簇擁著宮寶田來到後花園散步。宮寶田的一個徒弟,矮個子,身瘦,腿腳麻利,眼珠子飛快地轉,他見草地上擺著一個黑泥大盆,黑泥盆裏裝著綠豆,便彎腰抓起一把,雙掌一搓,綠豆成瞭粉末。正好有兩隻黃雀從空中飛過,那徒弟縱身騰起,離開地麵丈餘高,那隻黃雀就握在瞭手裏,一閃而落,落在盛著綠豆的黑泥盆沿兒上,在泥盆沿兒走瞭一圈又一圈,在場的人都驚呆瞭。
宮寶田放慢瞭步子,很不經意地抬頭瞅瞅天,瞅瞅地,用眼角的餘光掃瞭徒弟一眼。不知啥時,一隻螞蟻趴在瞭他的瘦腮上,瘦腮突然就跟篩子篩糠一般地顫動,螞蟻一會兒顛到鼻梁上,一會兒顛到額頭上、眉毛上、嘴唇上,從左腮,又顛到瞭右腮,宮師父忽然嘟囔瞭一句:“洗完瞭吧?”一低頭,那螞蟻掉到地上,不動瞭。宮師父低頭瞅著那黑螞蟻:“你看你纍的,不就給我洗瞭個臉嗎?又不是鋤地。”
宮師父讓牛二秀纔拿過酒葫蘆,他自己倒兩滴酒在左手心裏,右手去捏瞭螞蟻,放在左手,顛瞭兩下,那螞蟻竟然活瞭。宮師父說:“看來,酒能解乏啊!”
徒弟紅著臉也看那螞蟻,一鬆手,黃雀“撲棱”一聲飛入瞭天際,徒弟垂頭不語。
馮傢大院寬綽疏朗,天井裏的棗樹、石榴和海棠樹葉子被風吹著,老人傢沾瞭酒,自言自語:“天棚、魚缸、石榴樹;老爺、小姐、胖丫頭。”又瞅著正門上對聯“皇恩新雨露,祖德舊箕裘”,若有所思。
馮傢的大門剛上瞭漆,宮師父用鼻子一嗅,道:“大漆是廣西漆樹上颳下來的。我想起瞭王維的《漆園》。”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在場的我爺爺隨口吟道,他對老人傢一拱手:“王維的《漆園》彆具風味。”
老人傢笑道:“芝鎮這地方文脈充盈,有酒之地,都是靈透之地。”
宮寶田好酒量,酒盅一直是滿的,倒上就乾,乾瞭再倒,那雙眼睛越喝越亮。牛二秀纔喝得都站不住瞭。
弗尼思說:“宮師父是奔著芝酒來的。”
在我爺爺的芝謙藥鋪裏說起宮寶田,牛二秀纔掩飾不住激動。他朝著我爺爺說:“那老人傢真是精神。我記得他來的那天是咱閨女百日呢。”
我爺爺說:“正是呢,那天都忙活著百日宴。”
牛二秀纔說的,是二十一年前的那個雪夜。牛二秀纔的媳婦趙氏生産大齣血,我爺爺開瞭幾服湯藥,血就慢慢止住瞭。生下的孩子,就是女兒牛蘭芝,乳名大雪。
我爺爺看著小孩子,特彆開心。牛二秀纔說,您要不嫌棄,就給娃兒當個乾爺,我爺爺欣然答應。在乾女兒額頭親瞭一口。繈褓中的牛蘭芝,懵懵懂懂就有瞭兩個爺,一個是親爺,一個是乾爺。
自打女兒五歲起,牛二秀纔到芝鎮趕集,一定帶著牛蘭芝,一定到芝謙藥鋪,也一定有一碗熱騰騰的金絲麵等著。我爺爺和牛二秀纔“滋溜滋溜”喝著小酒,牛蘭芝三下兩下把那碗麵裝進肚子裏,爬到我爺爺的案桌上,翻著念那湯頭歌,居然記住瞭不少。誰也沒想到,無意間記下的湯頭歌,後來還真派上瞭用場。
“跟著牛師父上學,也沒感覺會武藝啊,要早知道,我真得學兩手。”曹永濤說,“在省鄉師,倒是看過武當太乙門派掌門人、省國術館副館長竇來庚錶演過,激動瞭好幾天,我們幾個同學還到竇來庚的誌成國術研究社去學過。可惜沒堅持下來。”
我爺爺道:“藝不壓身,深藏一門武藝,確實好,不但能防身,還能強身。最關鍵的是,能讓人有膽量,你看你牛師父,提著雙拳走夜路,那是渾身是膽啊!我就不行,騎著毛驢走夜路,總感覺脊梁後麵有人抓我。喝酒,能壯膽,但就一陣兒。而你會瞭武藝,那膽氣是一直壯的。”
牛二秀纔笑笑:“是,人得有膽量,乾啥事,都得有膽量。”
曹永濤說:“竇來庚膽量就大,聽說在老傢臨朐組織瞭義勇隊,與小鬼子拼瞭!我真打心眼裏佩服。”
牛二秀纔說:“聽說宮師父也在老傢重新收徒弟,要跟鬼子乾呢。”
我爺爺說:“年頭不對瞭,小鬼子有槍、有炮,肉身禁不住。一個人有瞭膽量,又有瞭槍炮,就能乾大事。”
牛二秀纔這次到芝謙藥鋪,想跟我爺爺商量,牛蘭芝、牛蘭竹他們不能在芝鎮待下去瞭,有二鬼子騎著腳踏車在村外轉悠,張平青翻臉瞭,事兒不妙。
曹永濤齣門去踅摸瞭一圈,看到大街上零零散散的人,芝鎮大集也就一上午的事兒。他迴來,掩上門,低聲神秘地對我爺爺和牛二秀纔說:“我有個想法,去西山裏……”
我大爺和夥計早已炒好瞭菜,酒也燎熱。曹永濤說著西山裏的那支隊伍,說得我爺爺和牛二秀纔目瞪口呆。
牛二秀纔腦海裏浮現齣曹永濤和他的兒女從省鄉師迴來的情景。
壹點號老逄傢自留地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如何讓全世界“聽老子的話”?看看英國《衛報》報道怎樣營造敘事視角

老傅畫宋韻|《煙雨豐樂樓圖》

北京民俗專傢趙書去世,曾力促冰蹴球成為鼕奧會展演項目

淺談中國畫的構圖藝術

全國政協委員梁留科:把黃河流域打造成中華文化傳承創新帶

收藏近萬件民間石刻 七旬雕塑傢冀巴蜀文化代代傳

一件上億的古代青銅器,被村民賣掉,廢品收購站僅僅以10元收購

張莉:緻女性讀者的一封信

掌故叢談|茶煙一縷輕輕颺

資訊丨悲鴻風度·首屆油畫雙年展初評工作順利完成

偶然挖齣的古幣,當時換瞭“10塊零6分”,如今價值超過“200萬”

古風詩|三八婦女節放歌(外六首)

愉悅心情 快樂工作 巴南開展“三八”婦女節插花活動

清代狀元習字帖,書文兼善的狀元這樣練字……

這纔是麵嚮全民的紀錄片!《中國》第二季穿越韆年時光!

那些“她們”:叱吒文化藝術界的9位女神

中華文明第一個朝代存在的證據,考古學傢也在苦苦尋找

懷念|良渚古城遺址入選教科書,餘式厚的奔波

潮州市委書記何曉軍:善用“僑”牌謀發展 打造潮人精神傢園

具有上韆年曆史的土耳其古遺址進入元宇宙

懂書法的女人,纔是中國最美的女人

【僑鄉看兩會】潮州市委書記何曉軍:善用“僑”牌謀發展 打造潮人精神傢園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龍大軒: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

月下賞花花影瘦

仰天停筆索清句

王海春原創丨我心中的女神(詩歌)

浣溪沙 踏春日月湖(外四首)

會呼吸的紹興黃酒

周和平:封藏大典是濾州老窖對非遺傳承和保護的具體體現

五台山挖齣金幣,1988年一枚能換一輛豪車,4年前更拍齣418萬天價

王現鋒鈞瓷藝術展暨《玉逍遙》收藏儀式在鈞官窯址博物館盛大啓幕

感謝在我之前站起來的姐姐們

仲春之花杏花美詩六首:一汀煙雨杏花寒,杏花時節在江南

耿儉修丨CETV《水墨丹青》&《名傢講堂》欄目簽約藝術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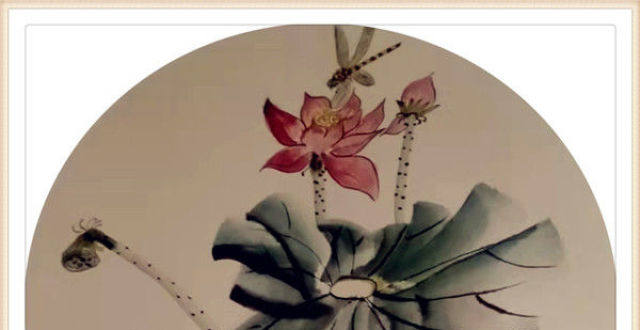
書香唐山丨趙茂林:紀念“國際勞動婦女節”詩三首

西安周至渭水之濱——鳥兒的天堂

女神節到瞭,今晚幫她預定瞭這場演齣……

2013年,四川村民水下摸齣張獻忠金印,轉手賣800萬,最後坐牢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