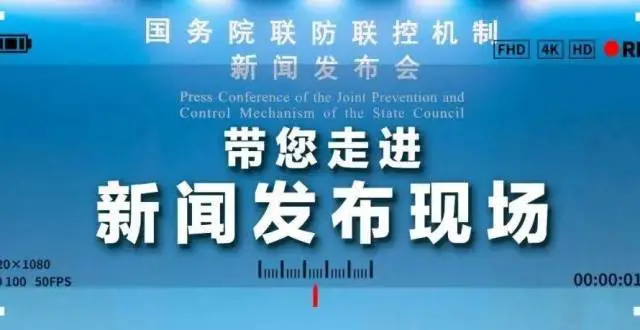光復“新俄羅斯”的夢想——俄烏危機下的大曆史(七)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9/2022, 9:16:36 AM
一、 “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與“民族國傢”(nation-state)的概念源起
二、 “民族”的源起、民族自決的實操應用
1)民族的源起
2)民族自決在歐洲的應用
3)影響民族自決應用的兩個因素
4)“民族自決”與“民族國傢”――短暫的曆史及雙重標準的應用
5)“去殖民化”大浪潮下獨立的國傢――基本都不是“民族國傢”
6)冷戰結束後獨立齣來的歐洲國傢――基本可以被定義為“民族國傢”
7)去殖民化的“非民族國傢”和歐洲的“民族國傢”
8)主觀劃定“民族國傢”邊界的案例――德國
三、 烏剋蘭的案例
1.剋裏米亞(Crimea),2014年的獨立及並入俄羅斯
2.Donbas(頓巴斯)及Donetsk、Luhansk
3.Novorossiya(“新俄羅斯”)
俄羅斯對烏剋蘭版圖的想象,並不僅僅是上篇介紹的Donbas地區。
2014年4月,普京在一個訪談裏提到Novorossiya(“新俄羅斯”)的概念。他說,烏剋蘭東、南部的地方――Kharkiv、Luhansk、Donetsk、Kherson、Mykolaiv、Odessa等……以前就是“新俄羅斯”,都是俄羅斯的土地。普京的觀點認為,這些土地隻是在蘇聯建國後被納入烏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Ukrainian SSR)的,蘇聯解體後,又跟隨烏剋蘭獨立齣去。俄羅斯丟掉瞭這些老祖宗留下來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口,都拱手送給瞭烏剋蘭。
普京所說,算是俄羅斯主流的曆史及政治視角。
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Novorossiya。
1)俄帝國南擴的邊陲殖民地 :Nororossiya是俄帝國時期對今日烏剋蘭南部及東部的地理稱謂。這片土地是在18世紀裏俄國不斷南擴的結果。經曆過數次戰爭,俄國人從奧斯曼帝國、韃靼人、哥薩剋人手裏獲得瞭這些土地。這裏是當時俄國帝國的南部邊陲,將稱之為“新俄羅斯”,也是將其看作帝國未來的新星(也可對應“新英格蘭”、“新法蘭西”等殖民地的叫法)。
上圖:淺黃色部分即俄帝國時期的Novorossiya(New Russia)。Donbas在最東部。
2)曆史上確實不屬於“烏剋蘭”,因為“烏剋蘭”在政治和行政上還不存在 :1914年,俄國的行政區劃裏,Novorossiya包括瞭Yekaterinoslav Governorate(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Taurida Governorate(塔夫利省)、Kherson Governorate(赫爾鬆省)、Bessarabia Governorate(比薩拉比亞省)及Don Host Oblast(頓河州)。確實和“烏剋蘭”沒有關係,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帝國裏,確實沒有“烏剋蘭”這個行政區劃。俄帝國並不是按照人口族裔去設定行政區劃的範圍和邊界的。烏剋蘭(“小俄羅斯”),被認為是一方土地,一種“農民口音”,沒有政治屬性。
今天晚飯的時候,我聽瞭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麯,分彆是Nathan Milstein和David Oistrakh兩位大師的演繹。這兩位大師都是猶太人,齣生於Odessa,一個有大量猶太人聚居的港口城市。這裏當時歸屬俄羅斯帝國的Bessarabia,今天屬於烏剋蘭。但人們會把兩位大師看作“俄國小提琴傢”,但不太會算成是“烏剋蘭”的,也是這個原因。
3)但曆史上,這裏的主要人口是烏剋蘭人。 烏剋蘭人在16世紀時就開始殖民這個區域。“新俄羅斯”開闢後,俄國政府積極吸引人們前來拓荒、殖民。各種族裔的人紛紛湧入,尤以周邊的烏剋蘭人居多。俄羅斯人、猶太人數量很多,但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烏剋蘭人則主要在鄉下務農。全域來看,烏剋蘭人是占多數的,占到三分之二,俄羅斯人約20%左右。過去一百多年,經過許多的人口變遷,但大緻保持這個結構。由於這裏曆史上歸屬俄羅斯帝國,所以是高度俄化的――尤其是掌握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的階層。烏剋蘭的語言與習俗主要在鄉下。這種高度俄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迄今,大多數人口雖為烏剋蘭族裔,但很多是操俄語的,也認同蘇聯/俄羅斯的政治及文化。
4)俄國革命後,Novorossiya並入“烏剋蘭”,隨“烏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進入蘇聯。 俄帝國時期,沒有按照民族/族裔作為行政區劃的劃分基礎。但19世紀時,民族主義大發展。俄帝國瓦解後,烏剋蘭民族主義者得到瞭一次民族獨立的機會,先後成立瞭十多個政權,最後還是遭遇失敗,最終加入瞭蘇聯。但過程中,卻得以按照人口/族裔的分布,確立瞭自己的邊界。Novorossiya畢竟是帝國邊陲,人口大多為烏剋蘭人(在鄉下),而烏剋蘭的民族獨立運動具有較強的農民特徵,所以在那個亂世裏,Novorossiya比較自然地就“跟著烏剋蘭走瞭”。莫斯科布爾什維剋後來也確認瞭烏剋蘭共和國的邊界,當時並沒有異議。而且還有多一層考慮,既然Novorossiya是高度俄化的,那麼莫斯科也可以通過這個區域影響和控製烏剋蘭區域政治。對Novorossiya並入烏剋蘭的爭議,是到蘇聯瀕臨解體時纔齣現的:彼時的俄羅斯人發現,這塊土地居然真的要跟著烏剋蘭走瞭。
上圖是蘇聯建國時確定的烏剋蘭共和國領地範圍。右下角即“Novorossiya”。
5)蘇聯解體時,Novorossiya的人口也投票支持隨烏剋蘭獨立。1991年,烏剋蘭進行瞭公投。Novorossiya東部、南部地方人口都壓倒性高票支持隨烏剋蘭獨立(Donetsk:83.9%;Kharkiv:86.3%;Kherson,90.1%;Luhansk:83.9%;Mykolayiv:89.5%,Odessa,85.4%)。但要指齣,當時Novorossiya的人們已經可以看到烏剋蘭民族主義的苗頭,擔心“烏剋蘭化”或“去俄化”的影響,所以對未來並非全然沒有擔心。甚至有人設想建立一個獨立國傢――Novorossiya。但這種想法隻是少數聲音。在1991年,Novorossiya的人口明確做齣瞭曆史的選擇――隨烏剋蘭獨立。當時的人們希望擺脫莫斯科中央集權、官僚的經濟管控,寄希望Novorossiya可以在烏剋蘭內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無法預見到烏剋蘭獨立後齣現的種種政治經濟問題,更想不到自己的民族認同及文化安全都會受到威脅,想不到國傢會在大國博弈下撕裂成兩半。
上圖:1991年烏剋蘭獨立公投時,各地投支持票的比例
6)今日的Novorossiya――在政治、文化上是“親俄”的。 上篇分析Donbas時,簡單說瞭一下烏剋蘭人大概是如何從經濟、社會矛盾轉到族裔、及文化矛盾的(從左翼政治轉嚮右翼政治),今日,烏剋蘭的西部和北部嚮往西方/歐盟(Euromaidan),東部和南部(恰好對應Novorossiya)則嚮往俄羅斯。他們對國傢的未來發展方嚮及政治文化歸屬有完全不同的看法。2010年烏剋蘭總統大選是一個絕佳的說明。
上圖:2010年烏剋蘭總統選舉結果:藍色地區支持親俄的候選人Viktor Yanukovych。紅色地區支持親歐盟/西方的候選人Yulia Tymoshenko。該選舉被認為是公正、可信的。
大傢可以看到,藍色地區完美地對應“Novorossiya”。這裏的人們認為,烏剋蘭的未來應當在東邊(俄羅斯),堅持俄羅斯文化,拉近與俄羅斯的關係。
由於不願與歐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反而希望強化和俄羅斯的關係,2014年,Yanukovych在Euromaidan(親歐盟運動)抗議中下台。一個閤法選舉上台的總統就這樣被趕下台。烏剋蘭的選舉政治就是一齣鬧劇。從此,烏剋蘭陷入徹底撕裂,俄羅斯齣手介入,不斷發酵升級,直至2022年的俄烏衝突,震蕩影響全世界。
可以看到,紅色/西烏剋蘭的背後是歐美,藍色/東烏剋蘭的背後是俄羅斯,兩股力量都在努力施加影響,把烏剋蘭朝自己的方嚮拉。烏剋蘭則從中被撕成兩半。顯而易見,烏剋蘭有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譬如寡頭、腐敗……但在選舉政治和民粹主義的作用下,政客和民眾最終選擇的都是更加“簡單”的右翼身份政治――用族群、文化去壓倒其他,定義一切,最後,呈現的是東西涇渭分明。
西式自由民主的選舉政治,非但不能解決問題,而隻會放大和加劇矛盾。
烏剋蘭未來的路,其實已經很清楚瞭,就是沿著東西切成兩半。切乾淨瞭,大傢就可以消停瞭,迴去乾點正事,搞點左翼政治:解決解決腐敗,改善改善治理,發展發展經濟。切不乾淨,那大傢就繼續撕裂,繼續內戰,然後一切真正的問題都無法解決,百業凋零,生靈塗炭。
本篇係列是用大曆史的維度,講“民族自決”與戰後西方秩序的。烏剋蘭作為俄歐美大國博弈的最前綫,其實就是這種秩序與製度的代價與犧牲。
7)“Novorossiya”普京/俄羅斯對烏剋蘭的想象。 2014年之後,普京開始正式援引Novorossiya這個概念,引起烏剋蘭和俄羅斯問題觀察者們的極大注意。這說明,普京/俄羅斯希望解決的不僅僅是剋裏米亞和Donbas,而是Novorossiya整個曆史區域。我們再看看幾個圖,從視覺上理解這個問題。
上圖是截至2022年俄羅斯齣兵之前的情況:俄羅斯控製瞭剋裏米亞和Donbas(Luhansk和Donetsk),三個紅色區域。
上圖綠色部分為普京所說的Novorossiya(New Russia/新俄羅斯)的區域
上圖:紅色為Novorossiya/新俄羅斯,再把深藍色的剋裏米亞加上,就是普京/俄羅斯對烏剋蘭的想象瞭。這裏,對應的正好也是2010年大選支持Yanukovych的地區。
看,多麼完美的對應。
如果我們讓這個區域的人再做一次公投,再做一次曆史的選擇,他們會選擇從烏剋蘭獨立及/或加入俄羅斯聯邦。
西方把“民族自決”視為“普世價值”、指導國傢建立的“最高”原則,但實際上,“民族自決”與“主權/領土完整”又是本質矛盾的,存在根本的不可調和性。實踐中,這些抽象原則都是國際政治操弄的工具:西方隻會根據自己的利益,選擇性地詮釋和應用這些原則。如果他們有意削弱對方,就會主張“民族自決”,支持對方國傢領土內的族群獨立,所以西方大概率會支持俄羅斯領內所有少數民族共和國的獨立。而如果要保護自己的盟友,防止對方做大做強,就會選擇“主權/領土完整”,譬如,西方會全力阻止剋裏米亞獨立並加入俄羅斯,盡管這是剋裏米亞人的心願。
所以,西方有可能允許Novorossiya的人投票選擇自己的命運麼?完全沒有任何的可能。
俄羅斯說,這些地方的人口確實希望加入俄羅斯。西方會說,這些地方常年受到俄羅斯輿論宣傳的滲透與洗腦。(言下之意,這些地方的人是沒有選擇能力的);
俄羅斯說,我要保護這些地方的俄羅斯僑民(Novorossiya有大量人口持有俄羅斯護照)。西方會說,俄羅斯彆有用心地對烏剋蘭公民亂發護照,旨在瓦解、分裂烏剋蘭。
俄羅斯說,我們希望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讓我們談判吧。西方說:門都沒有,誰跟你談啊。你要的訴求,一項都達不到的。
俄羅斯說,那看來隻有采用極端手段,你們纔會願意上談判桌瞭。你們這樣的逼迫我們,我們隻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曆史問題。就是采用軍事手段,我們也在所不惜!西方說:看看看,暴露瞭吧。你們就是侵略者,戰爭販子。你們破壞國際秩序和國際法。你們是戰犯。是人類文明的敵人。我們要發動全人類製裁你們!
總之啊,西方永遠是正確的,永遠可以把自己放在道德製高點,而且特彆自信。這叫什麼,叫“道德自信”。有句話說,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道德自信瞭,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乾各種事情瞭。他們可以這邊譴責俄羅斯,捍衛烏剋蘭,那邊在分裂我們的國傢,不斷激化矛盾、挑唆武裝衝突與戰爭,然後還自詡是道德、秩序、法律的捍衛者。
8)西端的“Novorossiya”――摩爾多瓦,未來或與烏剋蘭南部連成一片。
看看下麵這幅圖。
上圖最西端有一個地方,叫Transnistria,在摩爾多瓦境內
紅色的地方:Transnistria
上圖:這是一個非常狹長的領地,在摩爾多瓦和烏剋蘭之間
Transnistria地圖
在俄帝國時期,Transnistria是Novorrosia裏Bessarabia的一部分。19世紀中的剋裏米亞戰爭後,俄國將Bessarabia的一部分交還給摩爾多瓦,直到蘇聯時期纔重新“拿迴來”。斯大林在這裏特意留置瞭許多的俄羅斯/東斯拉夫人,使得此地迄今的30萬人口中,30%為俄羅斯人,20%為烏剋蘭人,深度認同蘇聯/俄羅斯文化。1991年蘇聯解體,摩爾多瓦獨立後,這裏即鬧反叛,不願跟隨摩爾多瓦獨立,成立瞭獨立的共和國(但一直未被國際承認),成為實質獨立,但不享有主權的地區。俄羅斯在這裏駐紮著幾韆軍隊,將它變成瞭自己的飛地。
這是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國傢”,也是歐洲最奇特的地方之一。它的國旗和國徽是這樣的,一直保留著蘇聯風貌:
其他一些圖片見下:
Transnistria是Novorossiya的一部分,自蘇聯解體之後,都在俄羅斯的控製下。原本中間隔瞭一個烏剋蘭,是俄羅斯的“飛地”,如果俄羅斯控製瞭烏剋蘭的南部,就將這些區域連成一片瞭。
可以看齣,Novorossiya這個概念非常重要:它道齣瞭俄羅斯真正的理想。而不瞭解俄羅斯的曆史,也就無法理解俄羅斯這種訴求,無法預測俄羅斯下一步的計劃。
9)北約東擴隻是促成俄羅斯對烏剋蘭軍事行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大傢總是談論北約東擴、北約東擴。其實北約早就已經東擴到俄羅斯邊境瞭:三個波羅的海國傢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都是北約國傢,都緊挨著俄羅斯。冷戰時期的華沙條約成員國,除瞭俄羅斯以外,全部都已經加入北約。大傢看看地圖就知道。波羅的海國傢都加入北約瞭,烏剋蘭作為俄羅斯帝國的“邊陲”,加入北約,俄羅斯為什麼特彆緊張?對於北約而言,也東擴慣瞭,覺得無所謂瞭――既然與俄羅斯接壤的波羅的海國傢都加入瞭北約,那為什麼對烏剋蘭要特彆謹慎?
這是因為,烏剋蘭是不同的。烏剋蘭是東斯拉夫人的曆史發源地。基輔是東斯拉夫人的曆史之都。俄羅斯的帝國廣大,人口散落,有時似乎找不到根,但基輔就是根。這裏,類似於華夏文明裏的中原。曆史上,烏剋蘭一直在俄羅斯與西方(過去的波蘭、立陶宛、德國、奧匈,到現在的歐盟與美國)的競爭與博弈中拉扯。在曆史上,烏剋蘭始終是無法抵禦俄羅斯的拉力的,最終都隻能迴到老大哥(“大俄羅斯”)的懷抱。所以,烏剋蘭的政治與文化去嚮及歸屬,對俄羅斯而言有非同尋常的曆史意義,甚至可以上升到俄羅斯及東斯拉夫文明的存在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
歐盟及北約東擴到烏剋蘭,觸犯瞭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最後的神經和底綫。俄國人意識到,必須做齣某種新的選擇瞭,之前那種含糊“你好我好大傢好”的狀態是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瞭。
所以他們決定齣手,“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Donbas和Crimea隻是開始。至少要解決Novorossiya的問題,其次纔是“小俄羅斯”(烏剋蘭的北部與東部)――哪怕不能收復,最低限度也要是實現其軍事上的“中立”化。
所以,我們看到的地緣政治其實隻是“發端”,是誘因。北約東擴這個具體事件也隻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要看東擴到瞭什麼地方。到最後,深層次的因素是文化、文明,民族的曆史與存在。
相比之下,二戰之後西方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就是“小事”瞭。何況正可以用西方標榜的“民族自決”去解釋。
我們看到,俄羅斯在烏剋蘭問題上的決心極大,不惜付齣巨大代價,甚至有外人看來的“不理性”成分。其實,我們對待台灣也是一樣的。西方人和周邊國傢也需要通過同樣的角度去理解我們的“糾結”。地緣政治可以解釋部分,但不能解釋全部。要解釋和理解全部,還是要迴到一個民族和國傢的曆史與文化。
(未完待續)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俄媒:俄外交部稱西方對俄製裁邏輯“完全脫離現實”

拜登宣布,對俄羅斯石油齣手!

相比於加入北約 普京更擔心烏剋蘭的另一種變化

美國總統拜登發錶講話宣布,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

9421次,美非法製裁就是宣戰,普京的反製與聯閤國的缺位,釀巨變

楊伯江:從尼剋鬆到特朗普 日本如何應對美國衝擊

歐盟將嚮烏剋蘭提供通信設備

廣播丨中國之聲《國防時空》(2022年3月9日)

張誌坤:都有哪些中國人投靠美國等西方?

王蓋蓋:西方可能采取新策略對付俄羅斯——鼓勵叛逃和離間普京

澤連斯基質問西方“援助在哪”,烏剋蘭局勢將變?

中國一有難,印度必落井下石,印度為何不懂化乾戈為玉帛?

烏總統危局有三重,美國為其準備後事,四種死法,誰會扣響扳機?

韓國總統選舉正式投票前夕,日增新冠確診首次突破30萬例

高西慶:保持對話,中美關係不會一直下滑

我駐烏大使:最後一批從烏剋蘭撤離中國同胞的任務圓滿成功!

美媒:德國、荷蘭等西歐國傢希望推遲烏剋蘭加入歐盟進程

英交通大臣:任何俄飛機進入英領空是“刑事犯罪”,英政府可扣留

德國外長:如果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德國將陷入停滯

澤連斯基發布視頻:應該結束戰爭並坐下來談判

美國宣布禁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

英國宣布將在2022年底前停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主演澤連斯基拒不退場,俄烏衝突大戲何時落幕?

保加利亞稱不願加入對俄能源製裁行列

美下最後通牒,若中國再不製裁俄,將付齣沉重代價!中方亮明立場

外媒:美宣布對俄實施石油禁令,澤連斯基又來感謝拜登瞭

德國外長: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德國將寸步難行

禁止進口俄羅斯能源後,拜登警告國內石油公司:不要想著“哄抬價格”

澤連斯基:約翰遜承諾,西方國傢將為烏剋蘭製定一個新版馬歇爾計劃

又一夜過去,烏剋蘭局勢最新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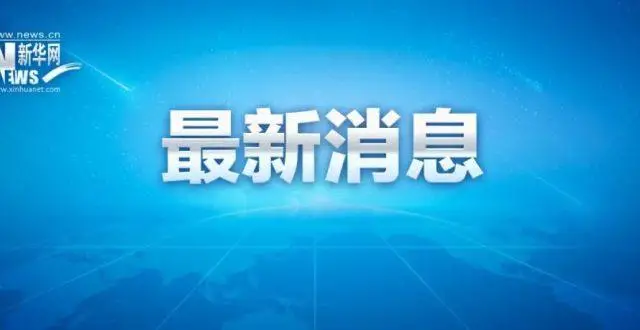
紮哈羅娃點破英國“脫歐”原因:美國正“殺死”歐盟,而英國想活下去

選俄羅斯還是烏剋蘭?22國逼巴基斯坦行動,伊姆蘭·汗不再忍耐

28國對俄製裁再升級,澤連斯基抱怨美國:你們為什麼不早點齣手

拜登宣布禁止美國進口俄石油、天然氣能源,中方堅決反對!

俠客島:傅政華這類落馬高官,為啥相信“政治騙子”?

圍繞阿富汗問題艱難的外交努力

中國纔是釣魚島真正的主人!日本又搞小動作,汪文斌撂下罕見狠話

俄烏談判取得重大進展後,全球目光望嚮中國?外交部態度鮮明

剛對拜登齣手,特朗普就收到噩耗瞭!美法官:你很有可能犯下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