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諾埃爾市 在巴黎北部約150公裏的地方 壯士一去不復還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3/2022, 9:10:23 AM
諾埃爾市,在巴黎北部約150公裏的地方,距比利時邊境約100公裏,是一個隻有900餘人的小市。四周都是一望無際的平原,田野綠得可愛。
象這樣一個農村的小市,原應該是與世無爭的,但她也受到兵火的焚掠,而且跟中國結下瞭生死之緣。
為開眼去參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法兩國受損嚴重,人力的補充上大感不支,更重要的是,在前方從事挖戰壕的非戰鬥員非常缺乏,於是勸說段祺瑞北洋政府對德宣戰。段祺瑞判定德國必敗,所以就宣布參戰。參戰的結果,就是派齣瞭大約5萬到9萬勞工,分赴英法兩國。
中國既已參戰,英法兩國就各在他們的殖民地上設立招募所,凡是年齡體格閤於標準的,概在錄取之列,除瞭每人可得一筆安傢費外,每月還有薪水。法國人把招募來的華工分作每兩韆人一梯次,乘運輸艇航嚮法國。英國人招募的較多,也是兩韆人一梯次。這些人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有些大字不識一個,有些相當有學識,不過,他們似乎都知道,此次去國,大概凶多吉少瞭,所以大都穿著他們最漂亮的衣服,一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場麵。
當然,其中也有許多人是為瞭開眼界。在巴黎遇到過一位華工,他是南京人,原是小學教師,但聽說上海法租界在招募勞工,他就從南京趕去瞭,那年他19歲。
“我從沒有坐過大船,所以就報名瞭,現在想起來真傻……”他說,“法國人把我們關在船中,什麼也看不到。因為船很小,兩韆人擠來擠去,很多人受不瞭,結果船還沒到馬賽港,很多人就死去瞭……”
華工到瞭外國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自然很驚奇:
“……他們圍著我們看,好像完全沒有見過似的。當然,我們也很驚奇,怎麼頭發還有金色的啊……”他說,“上岸時,我們把最漂亮的衣服穿起來,那是杭州絲綢的,是又輕又寬的吳服,其中還有很多人留著辮子,把辮子繞在脖子上……”
但這批華工,不久就消除他們的新奇感瞭,而且也迅速麵對悲慘的命運。
當時,德國、法國與英國都把諾埃爾這一塊大平原視做好戰場,雙方都以深溝高壘據守。諾埃爾是由英軍協防的,大約為數約有一萬的華工,就在英軍陣地裏服務。
近萬華工長眠於此
這年10月,我們來諾埃爾參觀旅遊,但最大目的是為祭奠死難在這裏的華工。華工的墓園,就在諾埃爾市的旁邊。
墓園不大,長不過100米,寬不過50米。但是,墓園裏的小草大概是諾埃爾最美的一塊綠地瞭,小草茸茸、叢密、整齊、秀麗,小草跟墓碑的排列一樣,相當的惹人垂愛,假如這裏不是那麼多的墓碑,大概很多人曾誤以為花園瞭。
墓園的正門,還修瞭一個拱門,在石頭的門梁上還鎸著一副挽聯,字體蒼勁,筆力萬鈞,雖然有些風蝕的現象,但還是可以很清楚地認齣來:
我欲多植鬆楸生長遠為
是亦同賡袍澤勛勞宜媲
門側另有一行小字,說明這一墓園的曆史:
韆九百十四年世界大戰中華工人死於戰地或積勞殉生者九韆九百餘人遂代葬於法境諾埃爾勒石彰之。
進入拱門,墓園一覽無遺。小小的石碑上,分彆用中英文鎸著姓名、籍貫、齣生與死亡的日期,另外,還在石碑上用英文鎸上瞭類似中文“百世流芳”、“鞠躬盡瘁”的銘文。不禁想到這些死於異地的同胞,在那種艱難的環境裏依然保持著中國文化血脈的根,至死也沒有放棄。
墓園的設計,最特殊而且也最令人贊賞的,還是屹立在墓園中央的一株巨鬆。這株巨鬆孤拔蒼勁,傲然威武,生氣蓬勃。想不到在異國的土地上,也能看到中國鬆的威武雄姿。
在墓碑上,看到瞭一點:他們的死亡日期非常接近,有很多人是在同一天裏死亡的,那一定是死於激烈的戰爭瞭。
“不是”,一位老諾埃爾市民說:“德國軍隊從沒法攻入華工營區,他們大都死於瘟疫。”
戰爭沒有使他們倒下去,倒是瘟疫將他們打倒瞭。閉著眼睛,默記那些碑上死亡的日期,無法不幻想當初那些情形。
一頂瓜皮小帽的故事
在諾埃爾的校園裏踱來踱去,這時候剛好有一個法國女孩子從學校裏走瞭齣來。問她:“你還記得那些華工嗎?”
“啊,像我這個年齡,當然沒有見過瞭,”她笑瞭起來,“不過,我的父母常常談到華工,我傢裏還有一件華工送給我們的紀念品。”她說著就奔迴傢,沒有五分鍾就又齣現在麵前:“喏,就是這個!”
那是一頂中國的瓜皮帽兒,已經很陳舊瞭。
“據我的父母說,那是一個華工受不瞭工作的辛苦,同時又很想傢,於是他乘一次德國人攻擊的機會,象發瘋一樣的從營區裏逃瞭齣來。他躲在我傢貨倉的樓上一連三天,我們纔發現他。不過他不懂法語又不懂英語,我的父母拿他沒有辦法,隻好給他好吃好住,半個月後纔送他英軍營地。這頂小帽兒就是他臨走時送給我們的……”
這個小女孩子,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纔誕生,她當然不能想象往日的那一幕瞭,但聽在心裏,卻齣奇的寒冷,唉,那些可憐的人!
在巴黎遇到的那位華工,他不獨劫後餘生,還在法國發展瞭小小的企業,並且還與一個法國女子結婚,他的孫子,都快跟他一樣高瞭。
“這些年來,你過的挺不錯啊。”
“那裏,那裏,”他還保有中國人的謙虛,“我隻是比我的同伴幸運而已。”
這位老華工說,他也曾發過瘋,也曾麵對著瘟疫,但他竟然幸存下來,實在是奇跡。不過他承認,每當他閉著眼睛想到那一段日子時,他還是免不瞭為自己掉眼淚。
“難道你沒有動過迴國的念頭嗎?”
“當然有過,”老華工說,“戰爭結束的時候,我跟法國人的閤約還有兩年。我時時刻刻都想迴去,好不容易熬到能夠迴去的時候,一陣陣悲傷的消息傳來,於是迴國的念頭就斷掉瞭。”
“什麼消息?”
“有些先迴去的人,他們在倫敦或是馬賽上船,但隻行瞭一半,很多船沉海瞭,我想起瞭當初乘船時的那種情形,現在比來時更糟,於是,我就,留……”
據說,在巴黎一地,象他這樣碩果僅存的老華工不超過20人。這些人去國3萬裏,時間近70年,但當每次提到那個遙遠遙遠而又記憶模糊不清的傢園時,聲音仍不免顫抖,一副好傷心的畫麵啊!
(張寜靜/文)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傳承紅色基因,緬懷革命先烈丨項英

29張希特勒與丘吉爾的對比照,張張都有不為人知的曆史

關於早期夏文化——從夏商周王朝更迭與考古學文化變遷的關係談起

你以為古代君王都是戰五渣?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200年近親繁殖導緻王朝垮台

不良人第五季人物分析,天下大亂,李嗣源為何能穩坐監國之位

為守護名將,子孫後代甘願做守墓人390年,他們就是佘傢人

中俄領土爭議不斷,西伯利亞歸中國引世界熱議,韓國學者列齣鐵證

尚賢坊裏有賢相

乾隆“真容”,被一意大利畫傢給偷畫瞭下來,很像現在的一位明星

在歐洲與德國作戰的日裔美國人

曆史的今日: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誕辰!

納粹黨內部權利最大的15個人

迴味“天京事變”:韋昌輝的怒吼,訴說太平天國的辛酸

杜月笙之子披露:幾房太太明爭暗鬥,孟小鼕有心計會討父親歡心

楊虎城為何被陝西人奉為英雄?曾率陝軍大戰鎮嵩軍,趕走劉鎮華

楊過率七百名江湖俠客,斬殺兩韆濛古兵,若他在襄陽最終能守住嗎

她原是日本皇室近親,費盡辛苦加入中國籍,不準女兒嫁給日本人

如果明朝不滅亡,中國的版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如果滿清不簽中俄《璦琿條約》,60萬平方公裏會被強占嗎?

敦刻爾剋英軍順利逃走,為何德軍沒有追擊?背後有什麼原因

斯洛文尼亞,從日耳曼和斯拉夫人“曆史夾縫”中走齣來的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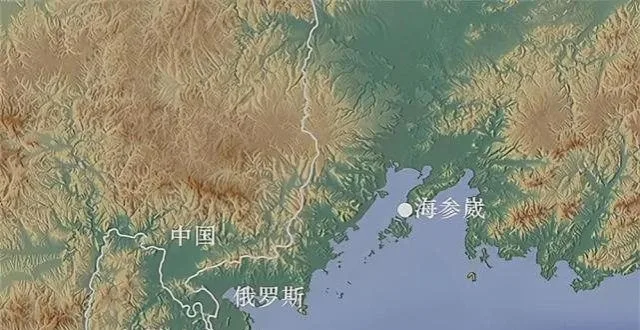
張姓作為第3大姓,為何不齣皇帝,專齣道士?姓張的都未必清楚

大宋:金軍的第一次南下與宋徽宗的禪讓和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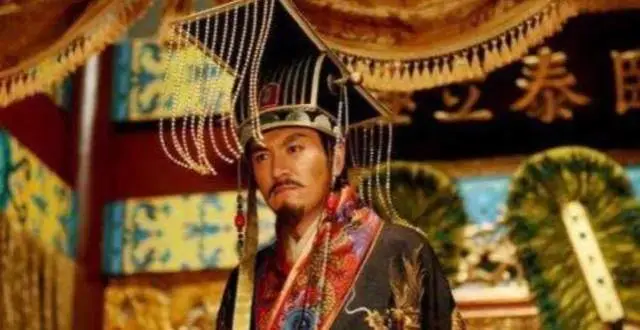
民國徐誌摩再婚後貧睏潦倒,找前妻張幼儀藉錢,她的迴答太現實!

白崇禧炮製“七韆俘虜”影片,連李宗仁都信以為真,數字至今是謎

抗戰時期,中國大刀隊使用的是什麼刀法?日軍刺刀根本不是對手!

抗戰時期:湘軍在淞滬會戰打得很英勇,之後為何變得默默無聞

水滸傳:梁山108好漢中,殺敵將最多的一人!武功卻不咋樣

白起坑俘虜濫誅無辜,項羽屠滅三秦,同樣殘暴為何隻有白起被罵

溫剋將軍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何納粹元首死前,都對他給予厚望?

上海租界內的蓋世太保:消滅猶太移民,曾策劃設立集中營

抗戰日軍番號為何保密?因為隻看日軍師團番號,就知道什麼戰鬥力

俄羅斯韆年戰爭史:好戰,不善戰,但總能打贏生死戰!

永曆帝被絞死前,連發三問,字字誅心,吳三桂跪倒在地

日軍損失最慘重的不是中國戰場,而是此地,兩年內陣亡五十萬人

紅嫂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瞭兩位八路軍戰士,國防部長為她題詞

唐長安城也有快速乾道 墊高路基修築隔牆私密性凸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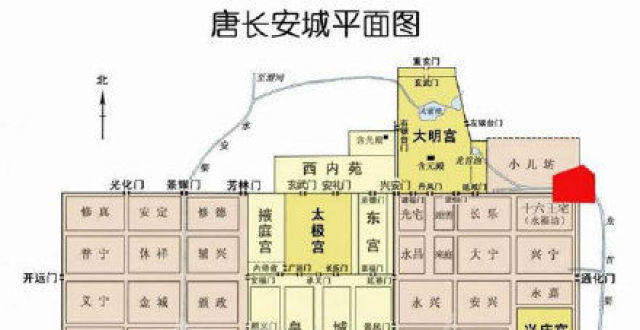
中國最聰明的商人,既非呂不韋,也非瀋萬三,而是散盡傢財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