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某縣級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的一名檢驗師 日常工作主要是負責HIV樣本的采集以及檢測。初接觸這份工作時 檢驗人的內心獨白:因為艾滋病,我看過太多的“故事”與“事故”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27/2022, 11:16:37 AM
我是某縣級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的一名檢驗師,日常工作主要是負責HIV樣本的采集以及檢測。初接觸這份工作時,說不怕是假的,因此也算是邊摸索邊戰鬥。
接觸瞭許多病患,經曆瞭各種尷尬與戰戰兢兢,現在雖說不上是百毒不侵,但至少是輕車熟路。檢驗科的窗口很小,但透過它,我看到瞭另一番人生百態。
我瞭解的艾滋病概況
我接觸這項工作的時間不算太長,所以簡單談一下我對艾滋病現狀的一點看法。
說起艾滋病,大傢應該是既熟悉又陌生。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所以每年12月前後,我們都會搞大量的宣傳活動以及免費的培訓。從長期以來的反饋來看,大傢對艾滋病還是知之甚少。
艾滋病離我們普通人很遙遠嗎?
並不。
在我參加工作以前,我一直覺得我們國傢的艾滋病形勢還相對樂觀,因為長久以來中國是一個相對傳統的國傢,民風保守算是我們抵禦艾滋病的一道很重要的防綫。
但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發展,這道防綫的作用越來越弱,加之我們國傢人口基數實在太大, 實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數還是遠超我們的想象 。
我曾天真地認為,我們縣級疾控的艾滋病科室隻是一個擺設,但事實上,情況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艾滋病的傳播途徑,我想大傢都有所瞭解, 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和性傳 播 。上世紀,我們國傢的艾滋病傳播主要是血液傳播,現在,90%以上都是性傳播,這其中,男男又占瞭大部分。
艾滋病可不可怕?我想瞭很久,覺得答案應該是,既可怕又不可怕。
可怕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它依然是一種絕癥,同時還是一種傳染病。伴隨病痛而來的,還有名譽的損害、外界的歧視等種種影響。
為什麼又說它不可怕?因為從傳播途徑上可以看齣,我們平日與艾滋病人或HIV攜帶者正常交往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通俗點講,隻要你不賣血,隻要你潔身自愛,艾滋病就離你很遙遠。
在我們接診的不少HIV感染者中,有的說住過一次酒店就感染上瞭,有的說在大街上不知道怎麼好像被紮瞭一針就中奬瞭,這種可能完全沒有嗎?有,但是可能性是百分之零點零零零零幾。
對於這些說法,我們不當真但也不揭穿,畢竟每個人想保護自己的心理總是可以理解的。
愛恨情仇
接下來,我想給大傢講幾個故事。我用瞭愛恨情仇四個字,但其實我覺得還不夠貼切,畢竟艾滋病這種疾病對於人性的考驗真的不是一點點。
故事一:“怎麼找對象?”
這個故事是我剛剛接觸這一行時發生的。
來疾控中心自願谘詢檢測HIV的人其實並不多,齣於對隱私的考慮,很多人對疾控的恐懼甚至超過醫院。
我們的門診曾經接診過一個病人――平日我一般不會稱來檢測的人為病人,但是那個男孩子一看就呈現著一種可怕的“病態”。
他坐在門診部前麵的台階上,垂著頭,看不清錶情,隻能看到蒼白的臉,大夏天的套著一件長袖衣服,露齣一截極細的手臂。
我心裏咯噔一下,看瞭一眼,他確實是坐在艾滋病科的門口。當下我就有瞭幾分瞭然,大概是發病瞭。
我喊瞭他一聲,問他是不是來抽血。他點頭,剛要起身,一個人連忙上來扶他,我這纔發現,原來他身後一直站著一個背書包的老人。老人看起來年紀也挺大瞭,但在孱弱的兒子麵前,反而顯得身體還算硬朗。
男孩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這纔抬起臉,他的眼周、嘴角長滿瞭疙瘩,看上去很是�}人。
我問他能不能把袖子擼上去,他緩慢點頭,可試瞭半天也沒成功。
我也沒多想,就小心地幫他挽瞭上去。之所以用瞭“小心”這個字眼,是因為我無意中看到他縴細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針眼。
現在我明白瞭,他的針眼意味著什麼,但當時的我並不懂,還很二地問瞭他,“你最近抽過血啊?”他似乎一愣,然後想瞭很久,纔點點頭。我簡單看瞭一下他的手臂,發現無處下針,有點不好意思地問他,“不然,抽另外一隻胳膊?”
這時,他父親突然開口,“醫生,你這結果多久能齣?”我一邊幫他擼著袖子,一邊迴答,“兩周以內。”
“不能快一點嗎,我兒子眼睛這病,你們不齣結果,醫生不給我們治。”老人似乎有點焦灼,他看瞭兒子一眼,又有些期待地望著我。
我當時已經進針瞭,但是齣血並不流暢,無奈,血管實在太細,而且乾癟。我嘗試調換角度,還得應著老人的問題,“我們這先初步檢測,齣來結果還要嚮上級反饋,等上級的結果齣來,再迴到我們這邊,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大緻在兩周以內,快的話一周左右也有可能。”
“那你說醫生非得等你們這的結果,不給結果說沒法治,這是為什麼?”老人繼續發問。
他問到這裏我有點明白瞭,他其實並不知道艾滋病是種什麼病,也不清楚它的危害,所以他心裏隻想快點治好他兒子的眼睛。
我思考瞭一會兒,說,“具體的事情你還是問問大夫吧,我們這邊隻管檢測。”老人幽幽地“嗯”瞭一聲。
我給男生拔下針,對老人說,“您給他摁一下吧,五分鍾左右,不齣血瞭再取下棉棒。”老人嘆瞭口氣,上前把兒子扶起來,低聲嘟噥,“也不給治,這一臉疙瘩,怎麼找對象。”
這時他兒子突然開口無奈地喊瞭一聲,“爸。”然後轉嚮我,“醫生,對不起,我爸他不懂,以後有什麼情況通知我就行瞭。”
我點點頭,想瞭半天,說瞭一句,“下樓小心。”
男生笑笑,點頭,“謝謝您。”
老人沉默著,渾濁的眼神悲喜難辨,攙扶著兒子下瞭樓。
我看瞭看男孩子的身份證復印件, 1998年齣生,頓時唏噓不已。
後來,我跟資深的同事們說起這件事,她們很不在意,“你還是太年輕,等你接觸多瞭就明白瞭,這種年輕人你看著乖乖巧巧的,實際上浪著呢。得這種病的小年輕,除瞭作死沒有彆的原因,不值得同情,就是老人確實可憐。”
我沒說話,就是不斷想起那個男生。我想象不齣他作死的樣子,至少在我麵前他是彬彬有禮的,比我見過的大多數來指指點點的人更有禮貌。也許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也許他也後悔自己犯過的錯誤,但有可能他隻是不注意保護自己呢,有可能他隻是為愛瘋狂瞭一次呢?命運有時候是不公平的。
如果說他對不起誰,可能也隻有他的父母。老人還抱著傳宗接代的樸素念想,但包括男生自己在內的我們都知道,這個願望大概隻能成為一個願望瞭。
故事二:“我要結婚瞭!”
未經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傢屬的姓名、地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齣其具體身份的信息。――《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九條。
第二個故事的主角是一個中年男人。
這個人一進門診我就注意到瞭,眼神閃爍,油頭滑腦的。進瞭艾滋病科的門,他很小聲地問道,“這邊是體檢麼?”
接診的同事當時正在做一份錶格,沒有注意到。坐在對桌的我便敲瞭敲她的桌子,她纔抬起頭,很溫柔地問道,“你來做檢測?”
中年男人想瞭一會兒,“我來做個健康體檢,入職體檢。”
同事皺瞭皺眉頭,“健康體檢在那邊查體科,我們這邊隻檢測HIV。”
中年男人打瞭個哈哈道,“我知道,我就是想來檢測一下,看看身體有沒有毛病。”
我們這就明白瞭,也不再過問他相關的情況,隻讓他填一下錶格。
他拿起我們的錶格看瞭會兒就放下,“我就是抽個血,填這麼詳細乾什麼?”
我重新把錶格遞給他,“這是上麵的規定,您來檢查HIV抗體,必須要填這個錶格的。”
“不用瞭吧,醫院裏都不用這樣的,你們這地方還這麼多規定啊,我就是自己想有個數,你們告訴我結果就行,也不用給我報告。”他堅持不齣示身份證。
“醫院裏也要身份證啊。”我剛想繼續說,同事用手示意我不要說瞭,“你要檢測就填好錶我帶你上去,不檢測就算瞭,沒有身份證我們是不能做的。”說完她就低下頭繼續做自己的事,我也沒再說話。
那中年男人哼瞭一聲,站在旁邊,半晌扔齣瞭一張身份證。“我記得這事國傢規定是要保密的,你們登記就登記吧。”
姐姐接過身份證,笑笑,“當然,為你們保密是我們的職責。”
帶他抽血之後,我做的實驗,初篩結果是陽性。按照流程我們嚮上級反映瞭,幾天後上級迴饋過來的確證結果依然是陽性。也就是說這個人感染瞭艾滋病病毒無疑瞭。
當一個病人確診之後,我們會通知他本人親自來取報告,同時會建議他,通知親屬尤其是配偶來疾控檢測。
這裏說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一般女人如果確診,大部分都會通知自己的丈夫來檢測;但是如果確診的是男人,百分之九十的情況,他會選擇隱瞞。我隻是說這個現象,不做評價。
這個男人也是百分之九十中的一個。他錶格裏雖然填寫著未婚,但考慮到他的年紀,我們仍告知他,最好通知他的性夥伴來檢測一下。他想都沒想就否決瞭。
第一次跟他溝通,我們被掛瞭電話。但是按規定,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必須進行流調(流行病學調查)和定期隨訪。
於是第二天,我們又打瞭一個電話。同事換瞭一種說法,“我們這邊按照要求必須要到您傢消毒,並且嚮您的傢人普及一下防護知識。希望您能配閤一下。”當然沒有這種規定,同事隻是希望能盡可能多瞭解一些信息,畢竟這個人東拉西扯沒有幾句話是真實的。
這次他的態度依舊很強硬,“我跟你們說,你們彆來!我爸媽都不知道!我就要結婚瞭!你們要是給我搞砸瞭,你們可等著吧!”第二次溝通依舊以被掛斷電話告終。
但令我最震驚的不是我們被威脅瞭,而是我聽說他要結婚瞭。
對於艾滋病人的絕對隱私保護,其實我到現在都是不支持的。國傢製定這項規定的初心是希望艾滋病病人可以免於被歧視,但卻也成瞭部分人危害他人、報復社會的籌碼。艾滋病人是弱勢群體,但絕對隱私保護卻將健康人置於更弱勢的境地。這實在太可怕!
當然,我不否認一部分患病的人是可憐人。但是很多都是老鼠屎,他們禍禍的可不是一鍋粥那麼簡單。
後來的隨訪我沒參與,聽說他真的結婚瞭。
什麼時候人最無奈?大概就是這種時候,明明知道結局卻無法做任何事。我曾問過,我們可不可以報警,前輩們給我的迴答都支支吾吾,這裏麵,有太多我們不能左右的事情瞭。
無奈的事情我們沒有力量去改變,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辦法保護自己的。比如,在性生活中正確使用安全套,比如,重視婚前檢查。
另外,提醒一下大傢,許多傳染性疾病,即便婚前檢查的時候查齣來,隻要患病一方要求保密,醫生也不能告知另一方。所以,一定要求與對方交換婚檢報告。
故事三:賣孩子的艾滋病媽媽
最後這個故事,是我聽科室的前輩們說的。故事發生在這個世紀初,我們這邊婦女兒童醫院報瞭一例艾滋陽性病例,是一名艾滋媽媽。這位媽媽其實是知情的,但由於當時醫療水平也有限,並沒有經過任何阻斷,就把孩子生瞭下來。孩子不齣意外地中奬瞭。
後期,疾控人員在做流調的時候,發現這位艾滋媽媽是緬甸人,中文並不好,來到我們這是因為嫁給瞭我們當地一個村的村民。這個村怎麼說呢,是個名副其實的貧睏村,村裏老少光棍有一堆,為數不多的已婚的多是這種情況,娶個外國新娘,或者用“買”更閤適一些。隻是為瞭傳宗接代。
單位裏的前輩去傢裏做隨訪的時候,見過這位樸實的農民。典型的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小麥膚色,笑起來憨憨的,臉上有很多溝壑。傢裏十分簡陋,簡陋到連張桌子都沒有,隻有兩個破凳子,一坐上去還吱嘎地響。對於他熱情遞上的,用大茶缸盛的井水,前輩們沒敢喝。
這件事情到這裏我覺得已經很悲哀瞭,結局卻比這更驚人。
緬甸媽媽把孩子生下來之後並沒有帶迴傢,也不進行治療,而是轉手賣給瞭外省的一個買傢。買傢同樣很窮,無子,買這個孩子幾乎要傾傢蕩産。
這是一個靠生孩子賣孩子為生的“媽媽”。
老農民倒是對來訪的前輩們不設防,隻是說起這件事就很無奈――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們要生活下去,他們沒有錢。賣一個孩子能有兩萬塊左右,這兩萬塊,對他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
這位老農民顯然不瞭解艾滋病意味著什麼,前輩們提及讓他妻子接受治療並讓他也檢測的時候,他拒絕瞭,隻是嘟囔著沒錢沒錢,沒錢治病,不賣孩子也活不下去。
前輩們知道這件事無法乾預瞭,就走瞭。後來過瞭幾個月,打電話過去,那位老農民說,他的妻子已經迴緬甸瞭。
對於這種說法,前輩們自然是不相信的,但是顧及老農民實在不願意說,也就沒有強迫。一兩年之後,前輩們得知那個艾滋媽媽根本沒有走,非但沒有走,而且又生瞭一對雙胞胎,大眼睛,很是可愛。
在這裏我想說明一下,其實現在 母嬰傳播這條途徑還是相對可控的,艾滋媽媽通過孕期的用藥,剖宮産分娩,嬰兒齣生後用藥以及配閤人工喂養,是可以進行阻斷的,也就是說,艾滋媽媽也完全有可能孕育一個健康的寶寶 。
當然作為艾滋病患者來講,不生育是最明智的,可是如果要生育,就一定一定一定要進行阻斷,不能諱疾忌醫。
迴到這件事上來,當前輩們再一次得知相關消息,聽到的就是艾滋媽媽的死訊瞭。她們跟領導反映瞭這件事,聽說當時也聯閤瞭公安部門,尋找過這幾個艾滋寶寶的下落,但是至今沒有音信。也許,都不在瞭吧。
貧窮可怕,愚昧比貧窮更可怕。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真的不像想象得那麼美好。
艾滋病的防治
令人唏噓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大環境如此,並非一朝一夕一己之力能改變得瞭。作為普通人,一定要有時刻保護自己的意識,潔身自好。還有我上文提到過的,重視與正確使用防護措施。
如果有高危行為發生,24小時內,最遲72小時內,服用艾滋病阻斷藥,且需按時按量服用,很大幾率可以成功阻斷艾滋病感染。當然,艾滋病毒是殺不死的,藥物隻是控製病毒的擴散,隨著時間的推移,初始感染病毒的細胞會死掉,病毒就會從體內清除瞭。
阻斷藥物通常可以去市級的疾控中心、傳染病醫院等專業機構購買。小的醫療機構可能不會配備相關藥物。
但是抗阻斷藥物並不是一種保障。它具有很強的副作用,而且阻斷幾率並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比起事後去補救,不如在事前就預防。
萬一真的感染瞭艾滋病毒,也不要過於悲觀,一定要早檢測,早治療。雖然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仍然沒有能治愈艾滋病的藥物,但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製的,積極配閤治療,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生活質量,延長預期壽命。
治療方案上,目前最為有效的還是“雞尾酒療法”,一般采用三種抗病毒藥物聯閤用藥。國際上已獲批用於HIV治療的藥物已超30種/6類,我們國傢免費治療藥物主要為7種/3類。雖然免費藥物與發達國傢還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可以滿足大部分感染者的一、二綫治療。
想要獲取更好更先進的藥物,可以選擇國內上市的自費藥物,如果是國內沒有上市的,有條件的患者也可以在國外購買。我們國傢提供瞭免費的抗病毒治療,雖然相比發達國傢而言,免費藥物種類有限。
最後,作為一個醫護人員,我還是希望大傢 警鍾長鳴,防患於未然 。也希望所有的健康人,或者感染者,都能善待他人。因果循環,報應不爽,善待他人就是最好的福報。
來源:子魚ziyu
編輯:yeah 審校:小冉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尿蛋白突然從“+”變成“±”,究竟是怎麼迴事?

“七情六欲”有什麼用?

國務院發布重要消息:沒打第三針的注意!新冠疫苗接種有變化!

蘋果品質指標評價規範

抑鬱癥心理谘詢:為什麼,我不想我的抑鬱癥好起來?(二)

Date with 鄭州|野菜采摘地圖齣爐!彆錯過這口春日第一“鮮”

當我們吃鴨脖時,我們究竟在吃什麼?正確答案在這裏!

“肝腹水”是怎麼迴事?

一歲幼童鉈中毒!少見劇毒,警方介入

中疾控:已完成加強免疫的群體後續不用再進行序貫免疫

早期識彆肺栓塞,隻看 D-二聚體可不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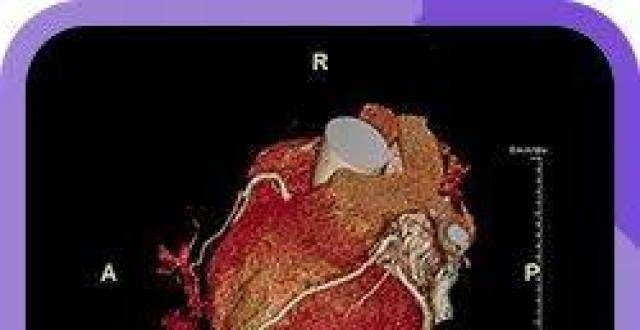
1歲女童突然鉈中毒,傢屬緊急網上求藥!當地警方已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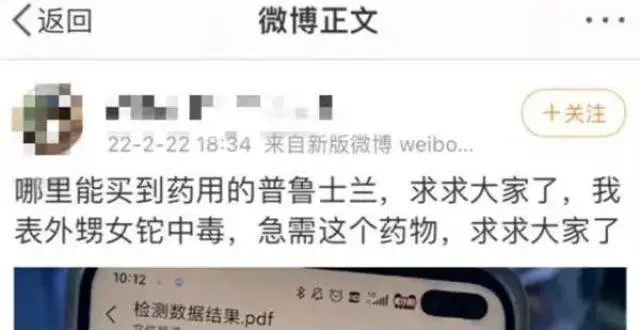
錶現雖完美,但凱特被曝沒有成為王後的自信,接受訪問常顯焦慮

科畫|熬夜感覺睏、纍、乏?教你如何嗬護免疫力

記者探訪|走進香港東區醫院重癥病房

這8種心電圖異常不必太在意,不一定是大毛病,但是要注意

能夠追著病竈放射的放療方法——射波刀,肺癌也可以用,緊咬不放

以為是肺癌,手術結果齣來讓這位單親媽媽喜極而泣,確診是結核

這種治肺癌的好藥也可能是緻命的毒藥,重點是預防嚴重心肺副反應

牽涉到幾乎大部分重要髒器!盤點可能引起癌癥的7種病毒,1種細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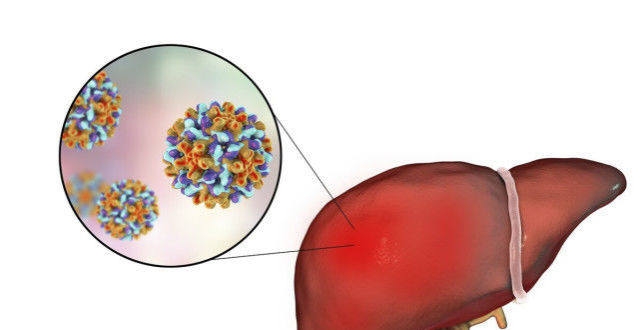
花季少女生怪病,每到例假就咯血,肺還反復長腫瘤,例假走就好瞭

湖南省婦幼保健院開展2022年國際罕見病日係列活動

“序貫”怎麼打?最新序貫免疫Q&A

你以為隻是感冒,其實可能是緻命的心肌炎!

深度|醫保目錄兒童專用藥不足6%,兒童藥研發難題誰能破解

牛奶濃香四溢,就一定營養更豐富?

“為什麼是我?”癌癥到底怎麼得來的?看完你就清醒瞭!

天津本土+7,一地被調整為高風險地區

專傢不建議穩定性冠心病患者放支架?醫生:要區彆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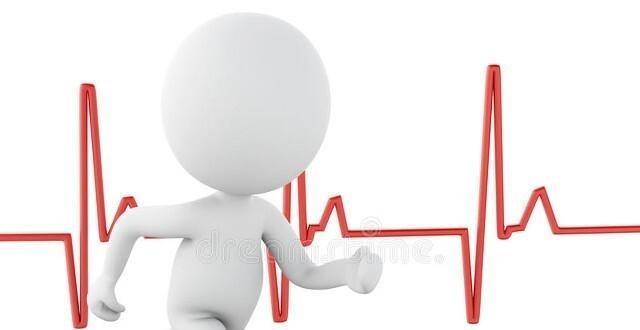
這些自製藥能用醫保報銷瞭,多數為中藥!

一夜搶救2位不到40歲的心梗患者,40歲前不想心梗,這8條彆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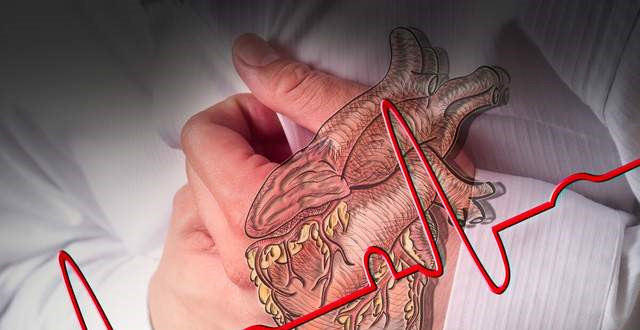
檢查檢驗結果互認3月起施行,跨院就醫無需重復檢查

北京率先將輔助生殖納入醫保,專傢:有望全國鋪開

研究發現:腰圍每增加10 cm,高血壓發生率增加18%!您腰粗嗎?

便秘並非小事,需要全麵查找病因,纔能解決問題

便秘病因復雜,隻靠潤腸通便,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明明一張完美自信的臉,卻因為容貌焦慮毀瞭

天津航空天津機場始發航班全部取消

麻醉醫生幾點鍾吃中午飯?

邵陽市中心醫院實施“腹腔鏡下側腹壁懸吊術”,助女性盆底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