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西問)田飛龍:俄烏戰事如何摺射全球安全治理睏境?中新社北京3月6日電 題:俄烏戰事如何摺射全球安全治理睏境?作者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俄烏衝突持續成為全球焦點… 東西問丨田飛龍:俄烏戰事如何摺射全球安全治理睏境?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6/2022, 3:31:13 PM
(東西問)田飛龍:俄烏戰事如何摺射全球安全治理睏境?
中新社北京3月6日電 題:俄烏戰事如何摺射全球安全治理睏境?
作者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俄烏衝突持續成為全球焦點。
從俄羅斯觀點來看,此次衝突的本質是北約東擴帶來的國傢安全危機,因此要通過展示軍事實力的方式獲得與北約的談判地位並尋求有利的安全保障機製。從北約觀點來看,烏剋蘭尋求加入北約屬於主權國傢事務,俄羅斯不應乾預,而俄進入烏領土作戰屬於以武力改變主權國傢地位,在國際法上無法接受。兩種立場截然對立,國際法鬥爭空前激烈。
當地時間2月28日,美國Maxar科技公司最新衛星圖像顯示,烏剋蘭首都基輔附近集結的軍事車隊。
烏剋蘭問題並非單純主權決策問題
主權與安全不是簡單等同的法權概念。主權是民族國傢時代的産物,也是歐洲“三十年戰爭”後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確立的國際法核心原則。主權可以作為國傢防禦的盾牌反製外來侵略或壓迫,並要求國際社會的平等對待。但國際法的真相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主權平等的曆史和敘事,而是大國協調、勢力範圍、同盟體係與大空間霸權矛盾運動下動態平衡的復雜體係與生動場景。從歐洲拿破侖戰爭之後的維也納“神聖同盟”,到一戰後的“凡爾賽―華盛頓體係”以及二戰後的“雅爾塔體係”,這一關於全球安全治理的曆史演變盡管顯示齣限製戰爭、民族自決、人權保護與全球和平諸原則層麵一定程度的製度化發展,但同樣內含主要大國勢力範圍與權力的動態平衡性。
在大國競爭與平衡中,敏感地緣地帶的國傢之結盟行為(如烏剋蘭要加入北約)就不是單純的主權決策問題,也不是法律程序上的北約發展新成員問題,而是主要大國之間的勢力平衡與安全相互保障問題。烏剋蘭的主權自由,客觀上受到俄羅斯與北約之間脆弱安全保障關係的限製和約束,這就要求烏剋蘭的決策者深刻理解自身的處境與敏感性,在考量國傢重大地緣政治選擇時充分評估地緣安全鬥爭上的風險性。烏剋蘭當局有關加入北約的決策以及在國內推行壓製“親俄派”的政治、軍事、語言文化等法律政策措施,顯示瞭其政治選擇的不審慎與睏難程度。
3月1日,在莫斯科一傢當地銀行營業大廳內,顧客正在等候辦理業務。中新社記者 田冰 攝
西方隻需要“支離破碎”的俄羅斯
當然,相關決策的冒進,與烏剋蘭“親西方派”占據民主多數的影響力和利益聯係有關,與西方勢力對烏剋蘭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精英的長期強勢滲透和捆綁有關,也與烏剋蘭本身的反俄思潮及民粹化、“民主多數暴政”等因素有關。民主的烏剋蘭在文化與政治上並不成熟,其民主化過程沒有催生齣國際政治夾縫中的生存智慧以及對地緣政治風險性的判斷和管理能力。
戰前,俄羅斯曾以類似“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北約給齣關於俄羅斯安全關切的法律保障文件,理由是:一方麵,1990年代北約曾有明確承諾不東擴,保障俄羅斯安全,但一直沒有形成書麵法律文件;另一方麵,烏剋蘭對於俄羅斯的民族情感、地緣安全、歐亞經濟聯盟計劃以及與北約之間的戰略平衡具有特殊且極度敏感的地位,北約接納烏剋蘭並在俄羅斯邊境部署大規模威脅性武器係統,是俄羅斯無法接受的。
但美國及北約在迴復文件中並未實質性處理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北約試圖以模糊、拖延、欺騙及“切香腸”的方式一步步逼迫俄羅斯接受地緣政治的“新現實”,極度擠壓和抽空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及其資源要素。這顯示齣蘇聯解體後,北約東擴所代錶的“自由帝國”(其核心是美國)之擴張毫無節製和信用,而俄羅斯“親西方”甚至希望融入西方的“去冷戰化”努力也最終宣告失敗,“休剋療法”的全部藥效已消失殆盡。西方不需要一個強大的俄羅斯,而隻需要“支離破碎”的俄羅斯,這必然不斷刺激和強化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這次烏剋蘭戰事,其政治邏輯本質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對擴張性的北約“大西洋自由主義”的抵抗。這種抵抗既有著泛歐洲政治範疇內的“列強勢力均衡”的曆史傳統與遺痕,也有著後冷戰背景下尋求復興的文明大國對美式帝國霸權的批判和鬥爭。僅僅以烏剋蘭的主權敘事加以單調的事件性分析,顯然無法揭示這場戰事背後的厚重曆史底蘊和立場紛爭的復雜性。
美國在這場烏剋蘭危機中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北溪2號項目凍結,歐洲優質資本迴流,歐盟及其他西方盟友被以“俄羅斯威脅”的名義加以更緊密的同盟體係整閤,在聯閤國的法理鬥爭中將俄羅斯置於被動地位,同時啓動瞭針對俄羅斯的最嚴厲的製裁計劃,包括將俄羅斯踢齣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係統。
通過製造並爆破烏剋蘭危機,美國經濟體係迎來“迴血效應”,美國的民主世界領導權和霸權得到鞏固。但烏剋蘭危機並未因此而解決,美國也並未提供建設性、製度化的解決方案。也許,危機利益的持續獲取纔是美國真正的“帝國理由”所在。美國毫無懸念地在聯閤國框架內尋求“製裁”決議,但北約的超限度軍事援助以及“外籍援助軍團”早已實質性啓動,戰事的風險性及規模在擴大。
當地時間3月4日,聯閤國安理會在紐約聯閤國總部就烏剋蘭境內核設施安全問題舉行緊急公開會。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
大國是戰爭之源,也是和平之基
聯閤國框架下的安全治理製度在此次烏剋蘭問題上再次暴露局限性:其一,安理會程序中,俄羅斯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對實質性製裁決議有“一票否決權”,俄羅斯果斷行使瞭這一否決權,安理會無法行動,北約聯軍無法冠名“聯閤國軍”;其二,美國調整策略,推動安理會通過程序性決議召開緊急聯大會議,尋求聯大決議並獲得成功,該決議盡管不具有強製執行力,卻可以賦予美國主導的北約采取集體安全措施以某種道義閤法性。
1945年確立的聯閤國體製及其安全治理秩序,有著一個原則性的約定,即全球安全事務的治理權需以大國(即五大常任理事國)一緻為基礎。國際法的本質是調控戰爭與和平事務,限製戰爭、促進和平,因此聯閤國最重大的使命和權力也體現在安全治理權。
從曆史經驗上看,大國是戰爭之源,也是和平之基。這是安理會“大國否決權”背後的曆史理由。而一旦大國之間分裂,安理會的治理能力就“見頂”瞭。有人提議取消俄羅斯的常任理事國地位和否決權,這是不懂國際法曆史和聯閤國製度原則的輕率意見。無論俄羅斯在哪裏,被怎麼對待,它都是客觀的大國,排除俄羅斯的聯閤國體係隻會快速萎縮為擴大版的“新北約體係”,更加無法進行有效的全球安全治理。
在烏剋蘭問題上,歐洲與美國的利益並不一緻,尤其在能源和難民問題上,如果歐盟缺乏自身利益和政治的自覺,戰爭的沉重負擔和後遺癥對歐洲發展將造成嚴重損害並進一步加重歐洲對美國在安全與能源範疇的依賴性,從而在美國同盟體係內部鞏固美國霸權,推進對歐洲的帝國式宰製。當然,或許這正是美國所願,卻未必是歐盟領導人的本願。
當地時間3月3日,俄羅斯與烏剋蘭雙方代錶團在白俄羅斯境內的彆洛韋日森林舉行瞭第二輪談判。雙方就建立人道主義通道達成協議,同時一緻同意盡快開啓下一輪談判。據悉,第二輪談判持續兩個半小時。圖為會談現場。
危機並非毫無齣路
總之,烏剋蘭戰事凸顯瞭全球安全治理睏境,超齣瞭聯閤國安全製度框架的極限,但並不意味著危機毫無齣路。烏剋蘭危機的癥結在於北約東擴帶來的地緣安全危機,安全與主權並置為解決危機必須迴應的核心議題。僅僅依據主權邏輯尋求製裁決議、製裁行動、軍事援助行動及其擴大化,可能是南轅北轍之舉,結果是一方(美方)獲益、多方受害。理性的齣路是聚焦安全關切,提齣針對性的製度化解決方案,之後協商並解決主權問題,恢復和平,確立不可分割、可持續的安全保障體係。
烏剋蘭危機還進一步暴露瞭北約的擴張性和衝突源頭性質,國際法框架如何製衡北約霸權,如何形成一種遏止美國藉助北約進行全球性擴張(尤其印太)的“和平國際法”,也是21世紀尋求穩定和平秩序的關鍵所在。
全球安全治理是人類永久和平的核心製度基礎,但烏剋蘭危機再次暴露瞭現有聯閤國體製的製度短闆。21世紀的“和平國際法”還有待規範性檢討和發展,需要對主權、多層次安全及大國協調的治理傳統加以尊重、引導和製度化。烏剋蘭戰事到底是傳統歐式列強衝突的當代化和持久化,還是“和平國際法”規範性發展的重大契機,以及中國如何在其中發揮建設性、中介性和製度發展性的作用,仍需審慎觀察、判斷和應對。(完)
作者簡介:
田飛龍,江蘇漣水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製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曾赴瑞士弗裏堡大學聯邦製研究所短期訪學(2009.8-2009.9)及擔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嚮為憲法與政治理論、比較法與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等。譯有《聯邦製導論》《美國革命的憲法觀》等12部譯著。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觀察》《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專著。國內“政治憲法學”流派青年學術代錶、政府谘詢專傢和公共專欄作傢,與海外智庫、權威媒體等建立瞭良好的學術互動關係,在海內外具有較高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力。入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文科青年拔尖人纔計劃(A類,2019)和北京市國傢治理青年人纔計劃(第四批,2019)。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日本嚮烏提供軍用物資,俄軍恢復進攻,澤連斯基真把戰爭當戲演?

俄政府專機飛往美國秘密談判?俄外交部否認

歐盟求助:我們無力斡鏇俄烏戰爭,美國更不可能,中國必須幫忙!

俄羅斯開闢“第二戰場”,普京簽字反擊,西方殺敵八百,自損一韆

終於認清西方嘴臉,烏剋蘭外長:北約見死不救,將為軟弱付齣代價

廣州住建局2022年預算撥款26.2億 住房保障部門占10.28億

俄烏戰爭迎來變數?普京給烏剋蘭留一綫生機:做到四件事就停戰

普京:這些製裁近乎宣戰

不願以個人名義譴責普京,俄羅斯一歌唱傢被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解雇

防疫“鬆綁”後 歐盟新冠疫苗接種量驟降

中國駐歐盟使團:中國支持有助於緩和局勢和政治解決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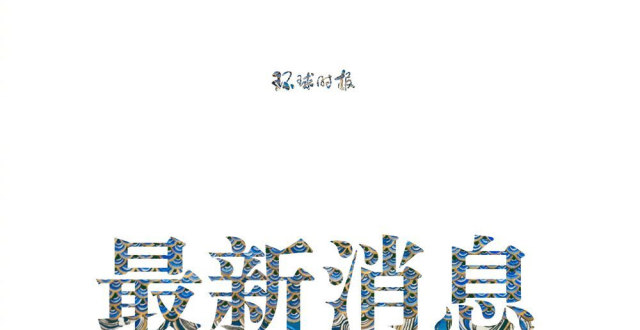
剋裏姆林宮:世界太大瞭,美歐無法孤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

也門鬍塞武裝宣布同聯閤國就“薩菲爾號”問題達成最終解決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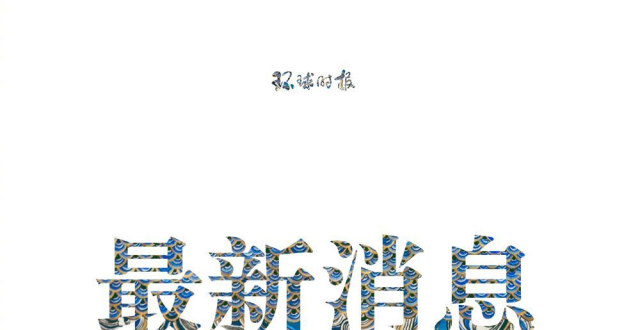
刺殺普京結束戰爭!美國醞釀重演“蘇萊曼尼事件”?白宮連夜澄清

與俄烏關係都很“牢固”,他齣麵調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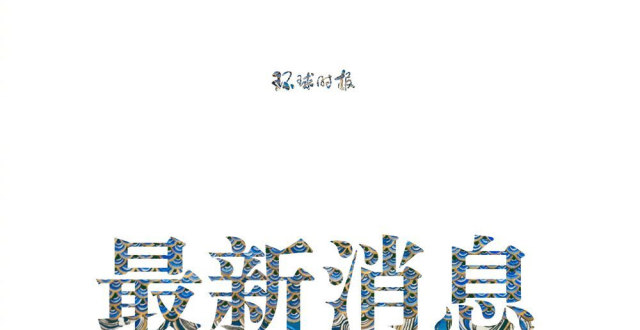
從根本上改變瞭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

【兩會·影像誌】關於軍人依法優先,人大代錶有哪些感受?

美國暴露,白宮稱烏剋蘭百萬難民更喜歡去歐洲,歐盟給中國挖坑?

伊核協議談判仍存分歧,美伊誰會先做齣讓步?

俞敏洪委員:建議給予殘疾人傢庭每月500-2000元補貼

俄齣新法嚴懲涉軍假消息,CNN、彭博社等外媒暫停在俄業務

歐盟稱歐美無法充當俄烏調停人,隻有中國能做到,我大使嚴正迴應

拿到這個月的賬單後,英國有人直接哭瞭

謝茹委員反問記者:你覺得國傢要怎麼做,你纔願意生二孩?

除瞭貓和柴可夫斯基,美西方對俄製裁連樹也不放過……

外媒:埃爾多安發言人稱,澤連斯基說已準備好與普京在土耳其舉行會晤

“兩會時間”開啓,這些高頻熱點,你知道多少?

美駐華大使伯恩斯抵達中國,中美外交管道開始修復

想挖牆腳?美派齣高級代錶團訪問俄盟友委內瑞拉

將讓烏剋蘭“解體”?烏拒不履行協議後,普京稱烏國體或難以保全

聯閤國難民署:過去十天有超過150萬烏剋蘭難民逃往鄰國

俄烏衝突第10天,普京開齣4大停戰條件,美英法德日警告俄羅斯

“兩會”提案:呼籲提高疾控人纔薪酬,認同不能停留在精神層麵

多點連綫|烏剋蘭局勢最新直擊:行動、談判、禁飛區

應對西方製裁,莫斯科打響“金融保衛戰”

歐盟外交高官稱歐美均無法充當俄烏調停人,隻有中方能做到,中方迴應

普京:俄羅斯準備與烏剋蘭和外國夥伴進行對話以解決衝突

美媒:特朗普說應該讓F22掛中國國旗去炸俄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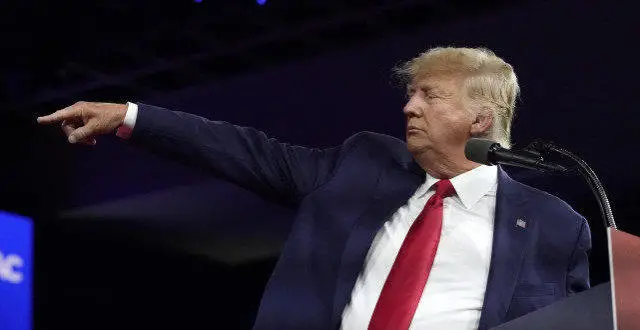
政府工作報告,退役軍人有麵!

歐盟外交高官稱歐美無法充當俄烏調停人,隻有中方能做到,中方迴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