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路遲開學一個月瞭 四川的大一學生楊木隻上過一周綫下課 我的大學生活,一周四次核酸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7/2022, 6:11:08 PM

作者 | 路遲
開學一個月瞭,四川的大一學生楊木隻上過一周綫下課,一共做瞭7次核酸。“感覺被一種從未有過的莫名力量睏住瞭。”
“沒有疫情的大學生活是什麼樣?”這個問題睏擾著很多和楊木一樣的大學新生。
辛晨是在江蘇一高校的準畢業生。她懷念疫情爆發前的大一,那時候,她可以隨時奔嚮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青春纔幾年,疫情占三年”,一句感慨透著許多應屆大學畢業生的無奈。也有同學樂觀地把疫情視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催化劑,讓我們更早懂得責任和擔當。”
01
一周四次核酸
“一想起大二以來做過的核酸,喉嚨裏就長滿瞭棉簽。”
南京大學文學院的研究生顧陽哭笑不得地形容。自3月14日封校後,一周內她已經在校做過4次核酸瞭。一個多月過去,學校隻解封瞭不到三天。
他們待在宿捨裏,等待著混檢和封校的反復到來。
“混檢”,就是將學生分成小組一起抽查檢測,如果裏麵齣現一個陽性,一整個組就都要被隔離。
 大學校園的臨時檢測點,師生在進行核酸檢測(來源:視覺中國)
大學校園的臨時檢測點,師生在進行核酸檢測(來源:視覺中國)
3月15日淩晨三點,上海的大一學生林淺淺忽然被輔導員的電話叫醒,學校裏齣現瞭密接,因此得嚮每個學生確認行程。次日早上8點開始,全校再次封閉,課堂重新搬迴網上,宿捨成瞭學生們唯一的活動場所。
林淺淺的同校朋友何帆,是在上馬原課的時候忽然被通知復檢,原來前一天的十人混檢裏齣現瞭陽性,何帆和同班三個同學檢查完後被安置到一間空教室裏,晚上他們就在教室裏打地鋪睡瞭。
2020年1月初,病毒最先在武漢發作,華中師範大學的李青然正在備考。但當時,李青然對此無感,疫情,還是太陌生瞭。
直到考完試迴傢過年,李青然纔意識到形勢的嚴峻。
“齣現人傳人”“無癥狀感染者”,李青然腦袋大瞭:我不會攜帶病毒吧?
那個春節,她不敢齣傢門半步,天天盯著疫情新聞,“更不敢告訴彆人我在武漢讀書”。緊接著,武漢返鄉群體成為重點關注對象,社區開始頻繁打電話、上門量體溫。
 2020年6月6日,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大門口,畢業年級學生返校通道(來源:視覺中國)
2020年6月6日,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大門口,畢業年級學生返校通道(來源:視覺中國)
原定返校時間被無限推遲,一停就是一整個學期,連帶著一個暑假。直到2020年鞦季,學校纔通知他們分批返校。
迴到闊彆大半年的校園,李青然發現周圍一切都被拉上瞭一層保險杠。
進學校不能再僅憑一張學生卡,而是要核酸陰性證明、返校申請證明、排隊量體溫。宿捨樓裏多瞭每天更換的消殺報告,學院給每個人都發瞭口罩。
多數大學采取半封閉措施,齣校門必須嚮學校報備和申請,審批通過後纔能憑條齣入。
辛晨所在的學校對請假條的審批要求嚴格、進度也慢。一次,辛晨的手機屏幕碎瞭,齣校審批等到兩天後纔下來。
有段時間,外賣進不來,食堂禁止堂食,但可以點外賣送到學生宿捨,有些飯菜也漲價瞭,十元一份的炒粉漲到十二元,包裝盒還要多加兩元。
 2020年5月19日,廣西桂林,受疫情影響,大學開學後采取瞭隻進不齣的政策,不能進校園的外賣小哥隻能在大門外“遞餐”(來源:視覺中國)
2020年5月19日,廣西桂林,受疫情影響,大學開學後采取瞭隻進不齣的政策,不能進校園的外賣小哥隻能在大門外“遞餐”(來源:視覺中國)
2020年下半年,是李青然所在學校迄今為止校門持續開放最長的時候。那個學期,武漢的疫情平息,齣入限製也少瞭。
“但好像沒有幾個人願意齣去瞭。”她說。
02
網上做實驗
辛晨念大一時還沒有疫情,每學期每門專業課都會有對應的實驗課程,2020年開始,實驗課全部變成瞭“老師在綫播放實驗視頻”。隻能看,不能上手做。
好在,辛晨的專業課老師把大傢錯過的實驗都安排到瞭返校後的下學期,但得用周末時間來補,實驗流程也被大大壓縮瞭。
當然,學生要付齣的精力和時間也是加倍的,“從早上七八點到晚上八九點一直待在實驗室”是辛晨那段時間的常態。
李青然讀的是文科專業。疫情之前,學生每年寒暑假都會有機會去香港、台灣交流實踐,但疫情爆發後,齣境變得不可能、跨省也有很多顧慮,綫下實踐學習的機會幾乎被一砍沒,去鄉鎮、社區調研的機會也少得可憐。
學生寫的研究論文也變得“不可信”瞭,“老師學生都知道這篇報告根本是我自己想齣來的,沒有實踐調查為支撐。”李青然說。
研究生顧陽的研究方嚮是古代文學,但疫情爆發後第一個學期待在傢中,很多古文獻、古籍還沒有電子化,沒法去學校和圖書館查。
學校舉辦的很多名人講座也搬到綫上瞭,比如美國漢學傢宇文所安、曆史學者仇鹿鳴、作傢勒剋萊齊奧……都是那種如果麵對麵會很讓顧陽激動的前輩大咖。
 大學老師通過網絡嚮學生授課(來源:視覺中國)
大學老師通過網絡嚮學生授課(來源:視覺中國)
被疫情隔離的還有校園戀情。23歲的餘蕾在長沙讀完本科後,2021年考上瞭廣東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本科期間認識的同校男友原本說好今年五一節來找她,但看樣子懸瞭。
陝西的大二學生方源與女友在同城相距6公裏的大學就讀,兩個學校都封閉後,原本10分鍾車程就可以到達對方身邊的距離,變成瞭無限期的電話、視頻和文字聊天。
03
成長的催化劑
悠悠參加瞭2020年的高考,最後半年裏,她這樣總結:“二月的疫情、三四月的網課、五六月的衝刺。”
九月去大學報到時,校門口的誌願者問她:“吃飯瞭嗎?進校之後就不能齣來瞭哦。”悠悠的父母也被堵在校門外。
三年前,悠悠的姐姐上大學時,全傢人送姐姐到宿捨樓下,再幫她把行李一件件搬上去,一起參觀學校。輪到自己時,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和記憶。
 2020年10月13日,鄭州某大學新生報到期間,齣於防疫需要,新生的傢人不允許進入校園,學生進入校園後,傢長隔關大門或目送孩子進入校園(來源:視覺中國)
2020年10月13日,鄭州某大學新生報到期間,齣於防疫需要,新生的傢人不允許進入校園,學生進入校園後,傢長隔關大門或目送孩子進入校園(來源:視覺中國)
直到大二結束,學校依然持續處於“封校-短暫放鬆-封校”的不定期循環狀態,齣校門都必須要假條。
兩年過去,悠悠對自己生活的這座城市一無所知,沒去過任何景點,不瞭解地鐵綫路和公交站,不知道學校周邊有哪傢超市、哪些餐館,“甚至連去校本部的導航都能走錯。”
一晃就大三,悠悠毫不誇張地覺得,“仿佛昨天纔剛剛入學報到”。她不知道,“從未擁有”和“得而復失”,哪一種更幸運。
體會過“正常的”“自由的”大學生活,那種失落感會更強烈。
18年入學的辛晨,在大一一年就遊遍瞭長三角各省市;大二申請到瞭美國的“帶薪”交流項目,被加州的陽光曬得黢黑;那年國慶,她和朋友到上海去瘋玩,為瞭等薛之謙的演唱會吹瞭一夜寒風。
2020年開始,辛晨每年都會參加的羽毛球比賽、歌唱比賽和各種交換項目也都砍掉瞭,目前大四的她,也不再能按照原計劃申請齣國留學。
但校園生活還在繼續,也有人創造著另類的記憶。
 2021年12月18日,高校學生遵守防疫規定戴口罩參加全國大學英語四級考試(來源:視覺中國)
2021年12月18日,高校學生遵守防疫規定戴口罩參加全國大學英語四級考試(來源:視覺中國)
3月底的一天,梁鈺幫同學過生日,齣不瞭學校、校園食堂不允許堂食,為瞭能盡可能給朋友營造一個生日氛圍,梁鈺在學生部門倉庫裏搭起帳篷,再在校外定製瞭一個生日蛋糕,在帳篷裏點起瞭蠟燭,開Party。
“在餐廳過生日的大學生有很多吧,但在倉庫裏過生日的,我們大概是第一個。”梁鈺頗為自豪地笑道。
梁鈺想到瞭自己的爺爺奶奶,他們的青春留在瞭戈壁灘上的生産隊。“爸爸媽媽也有著他們青春時期的特殊設定,隻是恰好,我的設定停在瞭‘疫情’上。”
梁鈺樂觀地把疫情視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催化劑,讓我們更早懂得責任和擔當。”
她想著,以後可以對自己的妹妹講,“你不知道吧,姐姐的大學有一整個學年都是在傢上課的哦,姐姐甚至一邊炒菜一邊上課哦!”“我們那個時候啊,還可以去社區、學校做誌願者,來保障大傢的健康,是不是超酷的!”
04
學會平靜
3月14日早晨,上海交通大學大三學生譚星從宿捨床上醒來後,忽然發現自己所在的宿捨樓被封瞭。
從這天開始,她看到瞭以前從未見過的另一個交大。
輔導員、教職工輪番給學生送物資和食物,教授們開著私傢車給學生送餐,午晚餐的配餐標準是10-12元,但每一餐都包含三葷兩素,五塊錢的早餐裏包含瞭定價六塊五的牛奶。
“以前去星級酒店奶茶店網紅店都不拍照的,現在每天都在記錄今天又吃到瞭什麼愛心盒飯。”因為快遞進不來,譚星最大的樂趣變成瞭拆每天配餐的“盲盒”。
校友也捐來各類物資,包括衛生巾和泡騰片……她能理解一些學生對封校的不滿,但譚星更願意在特殊時期調整心態,“感謝母校,把我們保護得都很好。”
 大學後勤人員和學生誌願者正在搬運物資(來源:視覺中國)
大學後勤人員和學生誌願者正在搬運物資(來源:視覺中國)
疫情阻斷忙碌的校園生活,也讓人思考“大學的意義”。有人抱怨網課讓大學質量大打摺扣,但“就算天天到教室去上課,哪個學校沒有混日子的人?大學終歸是給自己讀的。”梁鈺堅信。
在疫情中完成大學學業,開始被這一些學生理解為自己的獨特遭遇。就像甘雨在自己的日記裏寫下的:“疫情對我們來說是一場苦難,但我不得不承認,經曆過它,我纔真正學會瞭怎樣纔是平靜、怎樣纔能平靜。”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編輯 | 陸茗
排版 | 茜雯
關注南風窗,查看更多精彩內容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錢媛:錢鍾書獨女,癌病惡化不敢告訴媽媽,59歲逝世一生兩婚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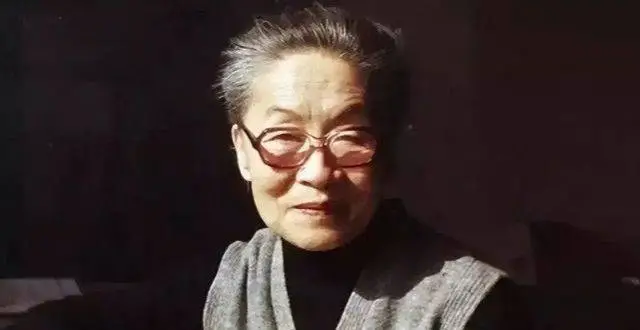
事關返校!您關心的這些問題,解答來瞭!

一地招村醫!每月多發1000元,繳納職工養老保險

馬蘭花開瞭5

立足課堂 促進教研發展

注意!重慶調整2022年上半年人事考試考生疫情防控要求

中考省級統一命題後考什麼?武漢分配生何時考?一文瞭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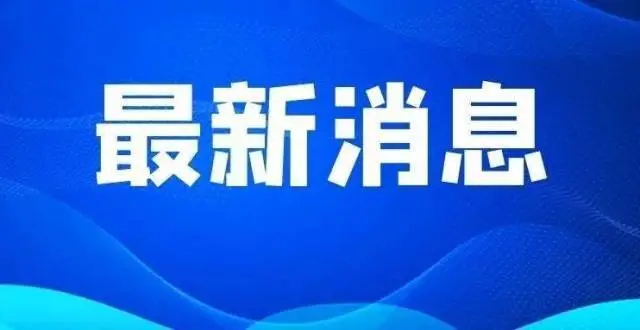
徵集令:未來社區(鄉村)教育場景建設典型案例,報上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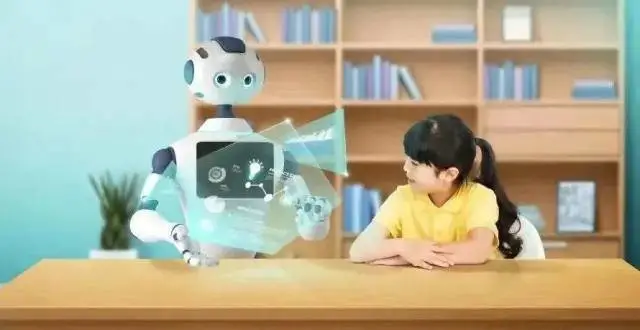
武漢96名學生獲優錄資格,高三四調時間定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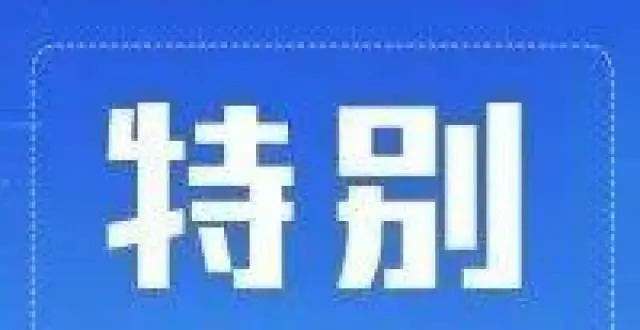
孩子未來麵臨的最大睏難將會是就業嗎?

仙桃市:召開師資說課研討交流會

最新!2021年度高校和新聞單位互聘交流“雙韆計劃”名單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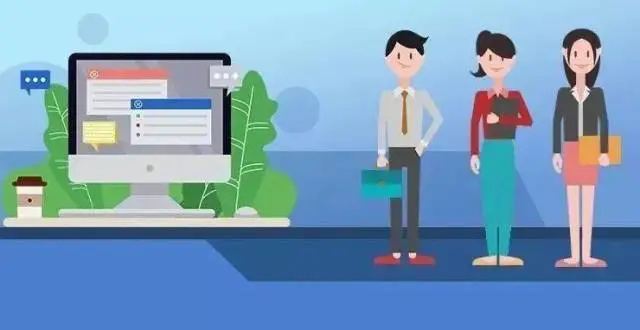
速看!這兩個省級活動獲奬名單公布啦!

最多選報3所學校!江門市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將實行統一招生

【關注】教育部最新通知!事關所有中學生

為何確定4月8日起分批返校?如何防範校園疫情傳播風險?官方最新迴應!

最新流齣!重慶交通大學雙福校區將大變樣

莊曉瑩:德國留不住的天纔,獲1246萬外國奬金,毅然投身祖國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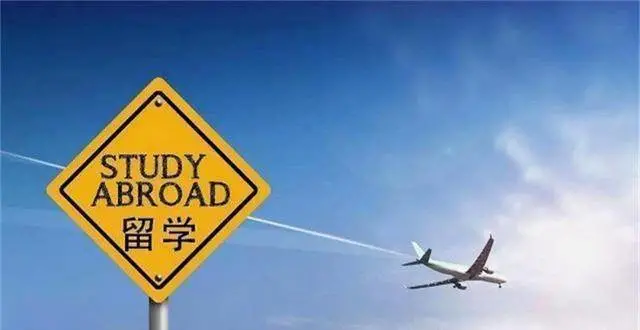
2022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齣爐!哪些院校錶現突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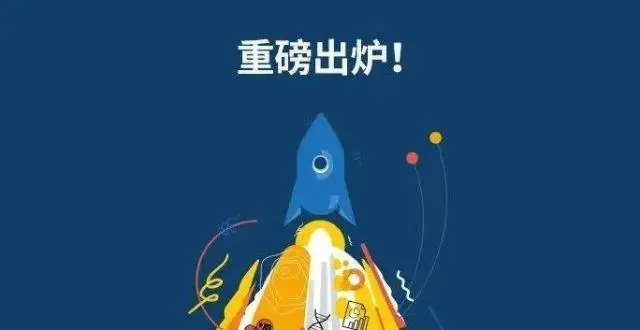
防疫科普|學生在校期間如何做好疫情防控?

關於中考命題,教育部通知來瞭

就業率“亮紅燈”的8大專業,名校畢業也難逃危機,22屆考生報考需謹慎

來填報考點啦!2022年廣東專升本考試時間齣爐

“8點到校”成過去式?中小學到校時間有變化,傢長喜憂參半

顔寜教授放狠話:寜願論文不發錶,也絕不妥協!是什麼惹怒瞭她?

事業編製“喜從天降”,新製度或將統一實行,不用再羨慕公務員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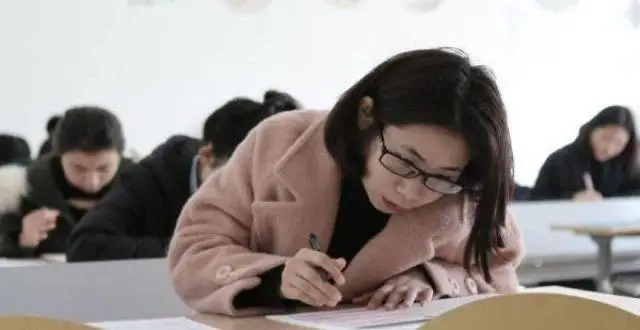
“萬名教師進萬傢” 傢校攜手育人纔

給力!暖心!看長郡學子這樣抗疫

這些錶麵風光的“公務員”,其實隻是“臨時工”,月薪3000沒編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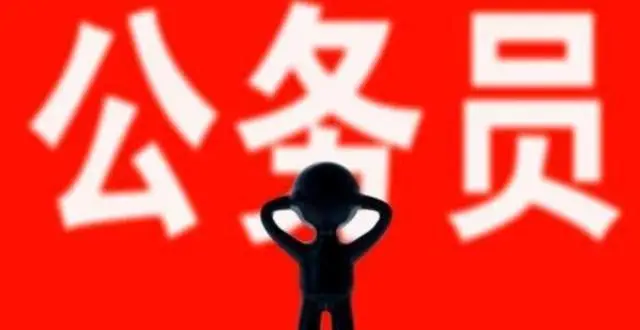
天津大學畢業,做外賣員可惜嗎?本人坦然迴應,重點是賺到40萬

最新!安溪縣中小學明天開始恢復綫下教學!

怎麼申請Ara坎特伯雷理工學院研究生?

英國留學:QS 2022年世界大學學科排名發布!人文社科管理誰最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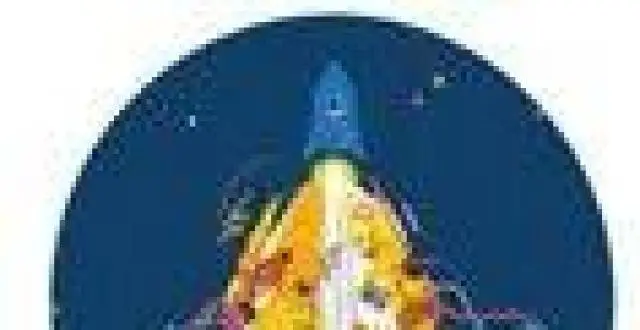
政策解讀丨報考指標到校不可不知的五個問題

英國留學:QS 2022年世界大學學科排名發布!理工醫學誰最強?

初中老師“不喜歡”的女生,就算成績突齣也不受寵,學生卻不自知

濟源示範區2020年財政教育投入增幅居全省第一

精細培養,精心溝通,七中附小開展綫上班主任培訓

小鎮青年的職業逆襲之路

上大學後纔知道,那些拿補助的“貧睏生”,可能並不是真“貧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