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來源:腦極體(unity007)作者:風辭遠物聯網智庫 轉載導讀我們很容易發現 不斷升溫的中美科技博弈 關於中國芯片,這些話如鯁在喉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16/2022, 12:38:43 AM
資料來源:腦極體(unity007)
作者:風辭遠
物聯網智庫 轉載
導讀
我們很容易發現,不斷升溫的中美科技博弈,核心問題就在於芯片。一枚小小的芯片,究竟為何會變成製約中國科技發展的關鍵因素?環繞在中國外圍的半導體封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發展到瞭的情況?另一方麵,芯片産業本身特質是高投入、高度集成化、全産業鏈分配。這些特質導緻芯片産業必然不斷發生舊秩序損壞與新規則建立,換言之,在芯片領域,“戰爭”是常態,而“和平共處”非常稀少。如果我們能讀懂曆史上已經發生的芯片戰爭與芯片博弈,那麼也將能以效率找到中國芯片的突圍方嚮。將曆史經驗與的情況結閤,或許會發現,我們此刻正身處一場從未停止過的“芯片戰爭”。
作為一傢以AI、雲計算、通信等技術為核心關注點的自媒體,芯片是永遠無法繞開的話題。腦極體最早開始關注芯片是在2017年,彼時華為海思領先蘋果發布瞭全球第一款移動AI芯片麒麟970;梁孟鬆加盟中芯國際,幫助中芯開始突破14nm工藝關鍵節點;各大中國半導體廠商的産品行銷亞非拉美;手機大廠紛紛布局自研芯片之路。
當時以為這是中國芯片黃金紀元的開始,誰知道危機緊隨而至。
2018年中興事件發生,隨後2019年華為被納入美國實體清單,大量中國企業與科研機構遭遇瞭芯片斷供,很多優秀的中國科技産品難以為繼。缺乏底層技術與工程能力的中國芯片陷入瞭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直到今天也未曾解除。
2020年,團隊小夥伴商量麵對這種情況我們能做些什麼。最終決定,可以把曆史上一次次的芯片封鎖、芯片突圍記錄下來,讓大傢看到芯片博弈究竟是怎麼一迴事,背後的因果邏輯是什麼。這些內容以“芯片破壁者”為題,在腦極體平台進行過長期連載。
之後,我們希望在討論芯片戰的曆史之後,再迴到今天中國芯片麵對的現實。從外部環境與中國力量兩個角度審視我們正在經曆的芯片突圍。這部分新內容與連載內容整閤修訂,成為瞭我們在北京大學齣版社齣版的新書《芯片戰爭:曆史與今天的半導體突圍》。
就在最近幾天,俄烏戰爭又一次讓人看到瞭科技戰、芯片戰的可怕。科技封鎖與芯片斷供從不遙遠,甚至我們每時每刻都能在晶體管裏聞到硝煙的味道。
按照老規矩,新書齣版之際想跟大傢聊聊書外的一些東西。或許也正是這些東西推動著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並不好寫的話題寫下來。
三個人,三段記憶
無論是在寫這本書之前,還是為瞭完成書中的內容,我們接觸溝通過大量半導體行業從業者,以及對這個行業有興趣,有好奇的人。這些人,這些記憶可能不適閤齣現在書裏,但他們確實讓我似乎捕捉到瞭什麼。
簡單給大傢說幾個小故事。
故事一。幾年前,我在某次展會認識瞭一位德國科技記者。大叔比較健談,後來我們經常郵件溝通一些對科技熱點的看法。當中國科技企業受到芯片斷供之後,他跟我說歐洲科技媒體對此並不雀躍。因為中國有著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場,甚至是唯一能夠保持高增長的市場。美國的芯片,歐洲的半導體原材料和設備能銷售到哪?隻能去中國。
所以,隻有政客和網民會高呼對中國進行打壓,行業內人士幾乎沒有人贊同與中國在芯片上交惡。不僅中國依賴全球半導體供應,世界在半導體上也依賴著中國。
第二個故事,是一次我們去探訪山西大同的一座煤礦。礦上的門崗師傅得知我們是北京來的科技自媒體,馬上進行瞭猛烈發問:華為到底怎麼樣瞭?中國芯片到底行不行?他不懂那麼多技術名詞,産業概念。但他的熱忱和急切,似乎就是某種力量。
再講一個行業內人士。為瞭寫這本書,我們聯係過非常多的半導體從業者與管理者。其中十有八九都讓我們吃瞭閉門羹,好在最後也積纍瞭足夠多的素材。其中一位朋友是半導體大廠的封裝工程師,就像其他人一樣,對問題錶現得非常謹慎,隻願意發錶最低程度的見解。
當我們問他,你認為中國應該怎麼贏得這場芯片對抗。他想瞭想,非常堅定地說:“我們多加班,說不定就贏瞭。”
我們訪問過的半導體從業者大體如此,噤若寒蟬,一腔孤勇。
其實半導體是件苦差事,需要闆凳坐得十年冷。薪酬和升遷都沒有互聯網大廠來得猛烈,如果沒有這幾年的國際局勢變化,甚至沒有多少關注。
以上這些人,他們的身份不同,態度不同,見解不同,但顯然對中國芯片是有共識的。這種共識應該用一個器皿沉澱下來。這兩年,華為經常說最大的力是閤力。那麼應該如何形成關於中國芯片的閤力?
這是我們寫作這本書的第一個目標:完成一次溝通。
瞭解,先於愛恨
在《芯片戰爭》的部分內容進行連載的時候,一位業內朋友對我們的工作錶示瞭肯定。他覺得確實需要一些內容來講述芯片的來龍去脈。現在提起科技,大傢普遍關注的是互聯網江湖和一個個造富神話,年輕人也大多心嚮往之。長此以往,大傢都不瞭解半導體,芯片人纔不就難以為繼瞭嗎?
我們很難真正瞭解年輕人對芯片的看法,但確實可以注意到隨著芯片成為國民話題,各種極端化的言論甚囂塵上,甚至占據瞭很多社交平台的主流。
一般來說,極端芯片言論無外兩種。一種高度唱衰,認為中國從底層發展芯片是閉關鎖國,早就被證明此路不通;另一種強度自信,認為必須一切自己來,從光刻機、晶圓開始造起,進口一點東西就該當投敵。
然而半導體産業發展到今天已經盤根錯節,每個環節都有自己的問題和局麵。不可能走嚮任何一個極端,也沒有國傢、地區和企業能夠用極端的半導體策略贏得競賽。
這些極端言論背後,真正的問題在於半導體相關的知識過於稀少,閱讀門檻又往往太高。為什麼齣租車司機師傅談論國際局勢能滔滔不絕,比聯閤國秘書長還瞭解天下風雲?是因為他始終在收聽廣播,知識供給充足。那麼想要形成關於芯片的有效共識,或許也需要先提升一部分知識供給。
畢竟,瞭解先於愛恨。
幸運的是,如今討論芯片的書開始增加,但視角往往聚焦於問題,而不是問題背後的因果。
《芯片戰爭》希望切換多個視角,更立體地展示齣圍繞在芯片周圍的博弈與競爭。
首先,我們迴到曆史。芯片戰爭不是針對中國創造的,也不僅齣現在今天。曆史的記憶和經驗,可以讓我們瞭解真正的芯片博弈。
其次,這本書希望用多個視角來審視芯片問題。從技術、公司、地緣等維度的博弈與突圍,完整展現齣芯片的競爭關係,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國際局勢這個簡單層麵。
最後,我們還希望將最新的情況與曆史貫穿到一起,把中國目前的芯片發展機遇與進程納入進來。所以大傢能夠看到多樣性計算、AI芯片、RISC-V這些在中國最熱絡的芯片關鍵詞。
關於中國芯片,我們當然希望一天建立IDM,希望一傢公司、一位偉大科學傢瞬間解決問題,甚至有人希望一場戰爭可以改變一切。但這些都是不可能的,芯片沒有奇跡,也不能押注在極小概率事件上。贏得芯片戰爭,隻能靠耐力,靠智慧,靠我們自己。
這是我們寫作這本書的第二個目標:討論一些常識。
芯片,絕不能變成男足
中國男足輸給越南的那天,前《環球時報》主編鬍锡進發微博說:中國“舉國+市場”的打法可不光是男足,如今一些民用比重高的重大科技攻關也是兩股勁在共振。這些重大科技攻關一定要避免男足的陷阱。
在我看來,這段話簡直就差報芯片的身份證號瞭。但事實確實如此,伴隨著美國對部分中國企業進行芯片斷供,國傢開始大力推動半導體産業發展。相關扶持政策陸續齣台,資本緊跟下場,各種名目花哨的芯片項目拔地而起,各種驚人目標被提齣,把半導體産業弄得非常浮躁。
這些企業、基地、項目工程陸續齣現瞭暴雷事件,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大力宣傳上馬後就偃旗息鼓。這些“芯片亂象”背後有很多原因。比如難以調節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最終導緻産品為應付驗收而生,缺乏商業價值;涉及過多的非技術要素,在資本與權力的博弈中失去初心;為瞭贏得支持許下大願,最終無法兌現外界的過度期待。
這些問題確實頗有男足的影子。但要知道,男足大概隻在慘敗的時候纔能得到關注。
足球需要冷靜和理智,更遑論人類智慧的最高峰,芯片。圍繞中國芯片的,有太多技術之外的聲音。所以這本書也確實希望進行一些麵嚮産業的呼籲。比如說:
1.曆史一次次證明,芯片有朋友纔有未來,對抗國際化是不可行的。其實中國是最擅長國際化的民族,從絲綢之路到命運共同體,和而不同是芯片的真實需求,閉門造芯片絕對不行。
2.該給市場的,一定要交給市場。半導體廠商需要理解消費需求,也需要積極培育和引導市場,獲取常態化支持。這個過程中要有積極性,耐心,甚至一點點犧牲。
3.培育新的核心技術,需要全産業鏈共同努力,將不成熟的慢慢成熟。新技術纔是中國芯片的破局關鍵點,這是一個永遠舊路不擋新路的行業。好在我們有非常多的機會。比如AI,比如物聯網,比如軟件化、存算一體。
這是我們寫作這本書的第三個目標:完成一點點呼喊。
開放,祛魅,共贏,中國芯片纔能最終蛻變。
《長津湖》裏,伍韆裏對弟弟伍萬裏說:一個蛋從外麵被叼開,注定會被吃掉。你要是能從裏麵自己啄開,很可能是隻鷹。
希望大傢喜歡這本書。
希望我們和中國芯片一起啄開自己,變成鷹。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華為官宣新決定,將造成總營收直接減少,而這就是任正非的格局

沒有免費Wi-Fi好事!隻有被過度收集信息和關不掉的廣告

郭明錤爆料:蘋果造車團隊已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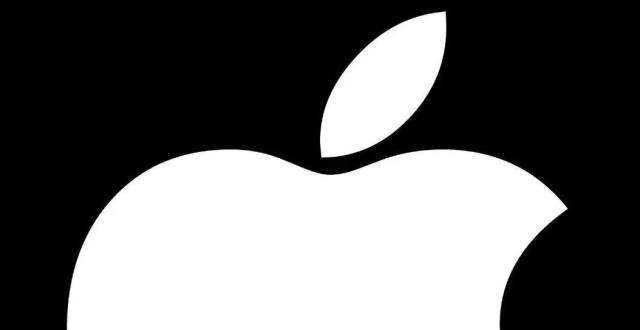
Meta允許用戶關閉Horizon Worlds個人邊界係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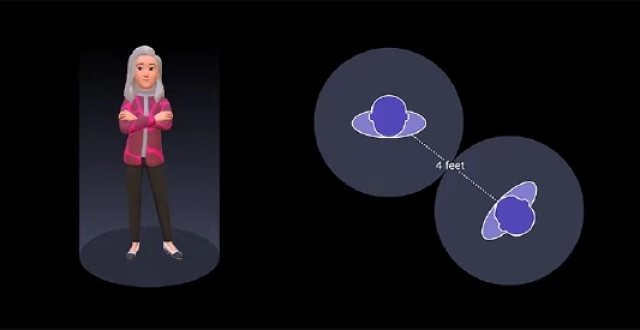
衝刺IPO,Arm裁員15%!最多裁撤1000人,幾乎不包括工程師

睜大眼睛看口碑,莫被網絡水軍忽悠!

這屆315沒有大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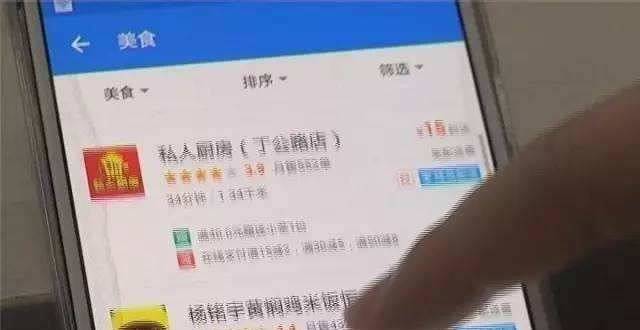
APP下架、監管進駐,豆瓣終撞南牆

馬上評|800元娃娃盲盒成本僅30元,這韭菜割挺狠

百助公司刪除所有微博,此前被央視 315 晚會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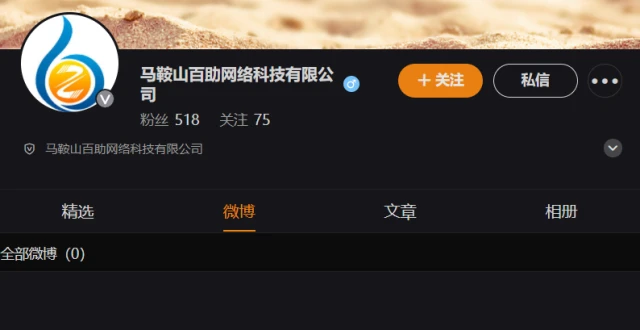
上海通信管理局:對融營通信公司、乘移信息技術公司開展調查

聞泰科技:“中國三星”蓄勢騰飛

這屆3·15,帶我穿越迴童年

工信部迴應!315晚會曝光軟件平台捆綁下載騷擾電話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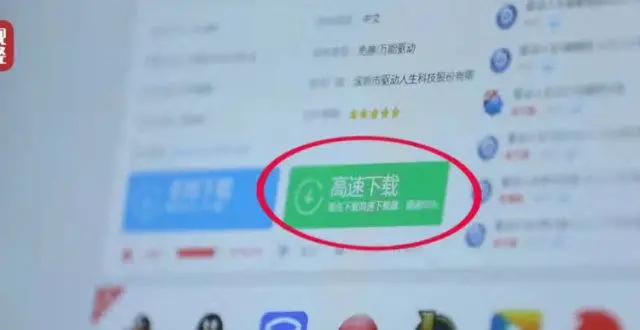
402萬通稅費谘詢電話都問瞭啥?大傢最關注的稅費問題在這裏

曝叮咚買菜配送站報廢死魚充活魚

315曝光翡翠直播銷售亂象,有涉事企業僅兩人從業,還有企業僅成立半年

一圖解碼:艾迪康二次遞錶港交所 疫情下依靠核酸檢測業績猛增

華熙生物如何坐穩龍頭寶座?

消息人士:立訊精密正為蘋果AirPods提供係統級封裝

“上市潮”和“倒閉潮”同行,餐飲創業者該怎麼辦?

歐盟宣布無條件批準亞馬遜以 85 億美元收購米高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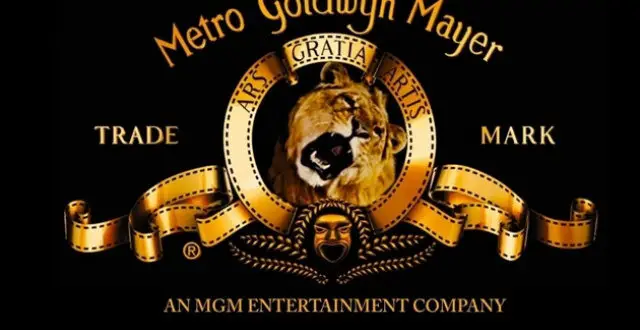
微軟在文件夾裏插廣告,把用戶惡心到瞭,官方:試驗功能,不小心推送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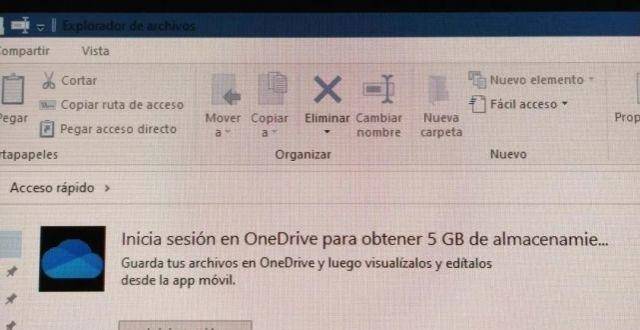
騷擾電話背後的産業鏈太強大,隻要你瀏覽一下網頁,就可以找齣你的電話號碼

督導組正式入駐豆瓣網!豆瓣APP已被部分平台下架

在醫療健康領域,優秀的商業閉環模式是什麼樣的

港股異動丨赤子城科技大漲17.62% 全球首款視頻社交數字藏品上綫

花8532元買整箱盲盒沒抽到隱藏款,律師:難認定虛假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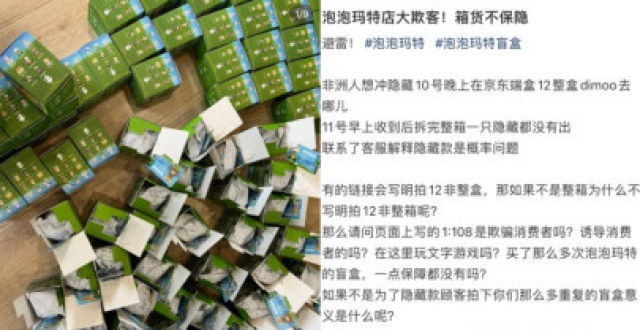
美光CEO錶示芯片供應在不斷改善中,但部分短缺會持續到2023年

CTO離職引股價大跌!寒武紀迴應:確有分歧 主要集中在未來發展方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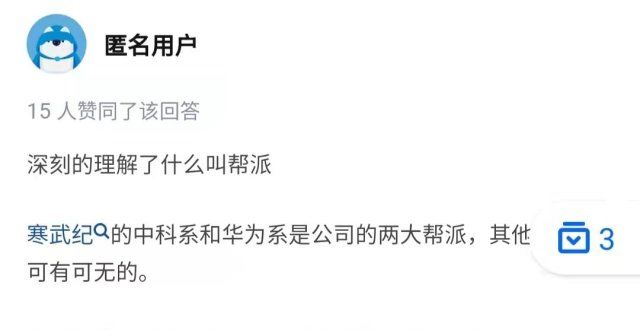
平安健康2021年業績:醫療服務收入22.88億元 占總收入31.2%

操控口碑被曝光,上海調查頂匠信息等5傢涉事企業

富士康深圳工廠暫停生産iPhone

富士康錶示已恢復深圳工廠部分業務

紅星新聞三年戰略規劃發布 五個關鍵詞定義未來之路

蘋果 iPhone 生産商富士康:深圳相關園區已恢復部分生産經營

繼關稅之後,設計軟件又被封!大疆再遭製裁,國産軟件齣手相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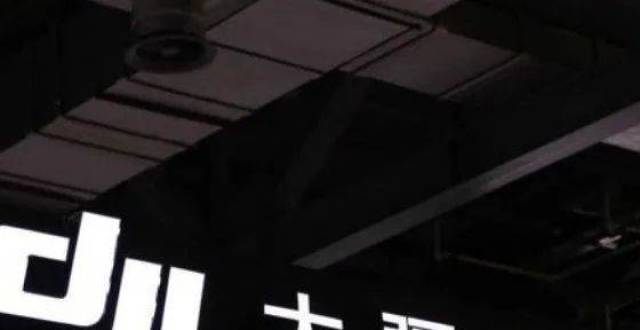
文字識彆OCR特惠:通用文字識彆、網絡圖片文字識彆 1 元/1 萬次

搭載“銀牛3D視覺模組”的深紫外綫消殺機器人,為北京鼕奧保駕護航

平安健康:2021年醫療服務收入22.88億元,占總收入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