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韶華悠悠|趙奇英:從“小”到“大”13年——我的學生履曆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9/2022, 8:41:37 AM
原創
任可
何人猶記
2022-04-07 06:08

作者 趙奇英
仿佛就在昨天,卻是四五十年前。我和有幸結伴的同行者一起,從“小”到“大”,伴著天真爛漫,帶著蓬勃朝氣,一路爬坡過坎,走過瞭小學5年,中學4年,大學4年。13年的學生履曆,有逆也有順,有苦更有甜,有辱也有榮,有悲更有歡……那是怎樣的一段旅程啊!想起來不由得讓人心潮澎湃,感慨萬韆――
我的小學
我的小學,河北省束鹿縣(現辛集市)仁慈公社(現位伯鎮)小白店學校,坐落在村子一角,約有近百年的曆史:最初是私塾改辦的初小,後來有瞭高小,再後來有瞭初中,但現在又沒瞭初中。校園裏很顯眼地建有兩排平房,土房頂、土地麵,前後兩個院子,當中有個“標配”的籃球架子――一根木樁挑著塊木闆、嵌著個鐵圈,還有兩個水泥乒乓球台,更有一溜大槐樹和一口懸在樹杈上的鍾。那是我心目中的聖地,可惜現在成瞭宅基地,學校被整體遷移。
我入學是在1964年6月底,當時還不滿7歲。那時是麥假後招生,我們這一屆招瞭60多人。我算歲數小的,大多八九歲,最大的17歲,名叫趙藏印,是我們的班長兼體委,隻是三年級時我們還在“坐門墩”,他卻娶媳婦去瞭。
第一任老師是校長兼任,很有水平,名叫呂士彬,本縣呂廂口人,40多歲,長臉,有麻子,很嚴厲,常常體罰搗蛋的學生,但對我非常好。可能因為我比較聽話,我爹是村乾部,又恰好分管學校吧?
我們的“課桌椅”最先是自己帶的,一個杌墩兒(高凳子)放書本,一個闆床兒(低凳子)坐屁股,很局促。直到四年級纔有瞭學校配的課桌,好生喜歡。因為個小,或許還因為老師關照,我常站C位――第一排正中間,後麵是我堂姐趙樹芬。
語文第一課是極具特色的“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不是從前的“天亮瞭,弟弟妹妹快起床”,也不是以後的“毛主席萬歲”,更不是現在的“我是中國人”。
算術第一課是亙古至今不變的“10以內數字的認識”。這倒是無可非議。
學唱的第一首歌是《早操歌》:“早晨空氣好,我們來做操,一二三四,看誰做得好。我們大傢來遊戲,我們大傢來舞蹈。學習好,身體好。我們做個好寶寶!”50多年瞭,那清亮的童音仿佛至今還迴響在耳際。
第一次考試是聽寫生字,懵懵懂懂的,考得很不理想。爹問我要捲子,我說:“什麼是捲子?”他沒解釋,就翻我的書包,然後就說:“怎麼纔考瞭40分?”敢情他是嫌少,第二次憋著勁,考瞭整60。他說:“還得努力,不能低於60。”此後還真的就再也沒低於60,甚至還不時考個雙百。
盡管如此,現在想來也覺得自己很笨,同學們都很笨,10以內的加減法,沒一個不掰手指頭的;20以內的加減法手指頭不夠用還要請齣腳丫子。現在的小學生哪有這樣的啊!
“得意忘形”的事記得有三件――
一是寫字“有成”:三年級時選寫黑闆報的,第一個選的就是我。這一寫就一直寫到瞭高中畢業,甚至後來還寫進瞭書協。
二是老師奬勵:那天課間路過老師辦公室門口,教我們的第二任老師雷秀蘭,居然叫住我,遞給我一個大蜜桃,說是奬勵。也不知是奬我的成績還是奬我爹的麵子,羨慕得同學們麵麵相覷。
三是賭贏同學:我說毛主席和是一個人,趙所成說是倆人。雷老師說我是對的,故此我贏瞭一塊橡皮。她還藉機鼓勵我好好學習。
我的同學好好學習得實在不夠好,剛上完常規的五年級(未等“加時”),稀裏嘩啦地就有近一半退瞭學,到生産隊上班掙工分去瞭。我也上班,不過是在星期日和假期。
我們的假期有三個:年假、麥假和鞦假。故此,一學年不是兩個學期,而是三個學段。
我們上學和放學,從無人送,也無人接,很晚纔到校,9點鍾纔上課,上午隻上三節課;下午很早就放學,迴傢後二話不說先搬騰個餅子,切成兩半,撒上點鹽,抹上點油,那叫一個香甜。
我們的書包大約隻有一斤重,裏麵隻有兩本書,一本語文,一本算術;隻有兩個本子,一個語文本,一個算術本;隻有兩支筆,一支鉛筆,一支圓珠筆。沒有成堆的作業,沒有考試的排名,學的那叫輕鬆,以至於課餘時間全是“瘋玩”。課間的第一個遊戲是劃拳寫“天下太平”,石頭剪子布,誰贏瞭誰寫一畫,看誰先寫完。體育課也做遊戲:丟沙包,老鷹抓小雞……放學後的遊戲就更多瞭:滾鐵環、抽陀螺、崩玻璃球、甩三角、疊飛機、撞拐、打鞦韆、打彈弓、捉迷藏、放風箏……仿佛整個世界全是遊戲。不知為什麼現在遊戲這麼少瞭。
我的同學中女生大約隻占三分之一。好像長得都不怎麼好看,隻有一個叫楊英然的,是個外來妹,比較俊俏,歡歡的眼,白白的臉。我曾想,以後要是能娶她做媳婦就好瞭。可惜,不到五年級人傢就不上瞭,後來也不知所蹤。白白地“單相思”瞭一迴。
我是個標準的膽小鬼,處處謹小慎微。老師不讓私自遊泳,就絕對不敢去,所以至今還是旱鴨子。不知為什麼有的那麼大膽,每次“私遊”後都會被老師打闆子,可還是去。也不知為什麼有的那麼調皮,特彆是大我四五歲的趙藏迎,見雷老師去瞭廁所,居然敢拿起磚頭扔進茅坑,“咚”一聲,濺得雷老師滿屁股屎,還拉著長音述說老師的教導:“少年讀書不用心,不知書中有黃金!”氣得雷老師差點背過氣去!
我是個典型的傻小子,除瞭學習,啥也不懂,盡說傻話辦傻事!上學第一天,課間去解手,見堂姐跑,我也跟著跑,一口氣跑到女廁所!傻事不是?高年級的學生誇我:“你的字怎麼寫的這麼好?”我說:“俺爹淨教俺!”傻話不是?也不知後來是怎麼慢慢學俏的,再後來還居然混得人模狗樣的!
我的小學上瞭5年半,本來按當時的學製5年就該畢業瞭,但五年級打瞭個“加時”多上瞭半年,因為學年起訖點調到瞭年假後(再後來又調到瞭暑假後)。故此,我的小學畢業於1970年1月。沒有畢業證,沒有閤影,更沒有典禮,因為緊接著就是無需考試人人都能上的中學瞭。

想起小學時光,苦惱也覺得甜美。
我的中學
我的中學之初中――六年級和七年級,是在小學“戴帽”上的。還是原來的校園,原來的教室,原來是同學,原來的老師,隻不過多瞭個理化老師。
各科老師――教語文的趙振同、教數學的趙壯申、教副科的趙銀仲,都是本村的,都教得非常好,我們都稱之為趙老師。唯有教理化的趙中生,我叫他“收”(叔),因為他是我爹的弟弟。他教的更是無與倫比。什麼動滑輪、定滑輪,並聯綫路、串聯綫路,物理變化、化學變化,活性氣體、惰性氣體,化閤反應、氧化反應,再加上不時拿著酒精燈、試紙、磁鐵什麼的做點實驗,印象裏總是那麼生動有趣。
那時正值“史無前例”的年代,課程絕對不難,但不知為什麼,不少小學時的優等生,跟頭咕嚕地就掉瞭隊。我卻暗自慶幸:把他們都拉下瞭,那叫一個爽!盡管如此,“收”(叔)卻從不錶揚我,而且嚴格規定我必須保持在前三名,否則他就要收拾我。“收”收拾彆人愛用“手槍”發射粉筆頭,神準,總能擊中腦門兒,但我從來沒有被“收”收拾過。
那時的學習條件其實挺艱苦。因為地麵不平,有的課桌常玩蹺蹺闆,為瞭擺平,隻好在桌腿墊一塊磚。因為紙窗戶漏風,臨窗同學還有另類作業:撕作業本粘漿糊堵口子,故此窗戶紙上常常是補丁摞補丁,也算當年的一道“風景”?天公還不作美,鼕天�J冷,夏天賊熱。因為還沒通電,所以根本沒電扇,更彆想象會有空調。夏天教室像蒸籠,人手一把蒲扇,邊上課邊扇,汗水還是常常浸濕課本,熱的口渴難忍,課間就在校門口的井台上喝口涼水。鼕天則更像冰窟,盡管講台上都有個煤火爐子,但晚上難保不滅,白天烏煙瘴氣地重生火,很難熱起來,幾乎人人凍手凍腳,凍得生疼,實在受不瞭就搓搓手、跺跺腳。常常是老師一走,跺腳聲即肆無忌憚地響起來,震得牆角的老鼠都滿屋子亂竄。
記得那年鼕天,因為要考高中瞭,晚上凍得瑟瑟發抖,也需要到教室集中復習,每人自帶煤油燈(其實燒的都是更便宜的柴油),燈火燃處,黑煙裊裊,鼻孔裏熏的全是“煙泥”,用手一通,手指全是黑的!當時就這種“氣候”,有什麼辦法!
那時所有的課本都是政治味十足:物理叫工業基礎知識;化學叫化工;語文還叫語文,卻大都是政治類文章。即使是由算術改來的數學,也在每章節的開頭甚至例題中“恰如其分”地夾雜進一條一條語錄。
在這些有限的課堂知識學習之外,還要“開門辦學”。貧下中農管校代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要不咱們打鐵?校長趙銀仲不好反駁,於是就在七年級成立瞭打鐵隊。男生掄大錘,女生拉風箱,從各傢各戶收來廢鐵,在老農的指導下,打製農具。現在看來,簡直是開玩笑,但那時卻搞得“風生水起”。
更為“風生水起”的是普及樣闆戲。《紅燈記》《沙傢浜》《智取威虎山》……在音樂老師的教導下、在大隊喇叭的“熏陶”下,人人都會唱幾段。抗戰歌麯《到敵人後方去》《大刀進行麯》等,不知為什麼重新拾起、重新填詞,唱遍神州大地,唱徹小小教室,唱得黑闆、桌凳、牆壁似乎都能哼幾句。
多虧校長明智,老師們努力,學業課沒有從根本上被搞砸、被唱衰,我們小白店學校還是當仁不讓地總能在仁慈公社保持優秀。傳統的“秀纔村”啊!整個學校、整個村莊好像都在為之高興。
但是,我卻總也高興不起來。盡管學習優異,盡管老師嗬護,整個初中的兩年在同學們中我卻是毫無威信,甚至還常常被欺負。“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彆的同學都通過瞭,剩下一個搗蛋鬼、一個傻大姐,還有我通不過,說我批得不深不透。一部分男生主要是差生,以及個彆女生,還一齊喊著號地起哄,“咩咩”地學羊叫,羞辱我,因為我爹外號“小羊”。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如此喪心病狂地欺負我,隻因我太懦弱,太好欺負?我清楚地記得,他們臉帶壞笑,把我圍在教室的中間,“咩咩”聲震耳欲聾,震的我欲哭無淚。我寡不敵眾,無力反抗,想跑也跑不掉,隻能暗暗地把拳頭攥得很緊很緊。那是我刻骨銘心的“恥辱日”!我迴傢後查瞭查月份牌,那是1971年3月4日!(3月4日!後文有敘)
正如一句詩所說“莫道浮雲終蔽日,嚴鼕過盡綻春蕾。”在屈辱中我暗自發力,漸漸地走齣山窮水盡的“深淵”,走到瞭柳暗花明的高中。
上高中我本來是奔著辛集中學去的,可是升學時方知,當時辛中與所有名校一樣,早被取消重點,隻招辛集鎮的學生。上不成“小寶塔”,我隻能無奈地走進公社所在地仁慈村東北角的一個“大雜院”:幾排磚房,幾條甬道,一個操場,一口水井,一片菜地。那就是我的高中――公社所辦的“仁慈社中”。

這是“社中”開辦以來的第三屆,開始招瞭兩個班,共104人,按第一屆一二班,第二屆三四班排下來,我們這兩個班是五班和六班。我被編在第六班。
我們小白店學校考來瞭11個,五班五個:趙樹彬、趙英喬、趙振國、趙淑欣、趙誌藏;六班六個,除瞭我還有趙建國、趙誌和、趙樹新、趙藏然、趙敬義。因為錄取率太低,好多想上的上不瞭,以至於齣現許多“上訪”要求擴招的。“社中”為此又擴招瞭一個班,是為第七班。我們學校的趙藏誌、趙占坡因之搭上瞭末班車。
我們上學其實是沒車可搭的。三裏地,都是走著去。總是幾個人結伴,他們在前頭嘰嘰喳喳地一路說笑,我像跟屁蟲一樣地在後邊跟著,常常一言不發。有什麼好說的!中午呢,都是自帶乾糧:一般是兩個餅子,一塊鹹菜。餅子包在手絹或搌布裏,在學校食堂的大蒸籠裏�滓��祝�就著“大鍋水”,席地而餐,簡樸至極。
我的高中起點不低。那時的招生是文化考試加推薦。文化考試沒問題,我考的是本校第一,全公社第三。推薦更沒問題,傢庭齣身貧農,父母都是黨員,絕無政治汙點。因此,總評分排在新生的前幾名。
有一件事很能引以為豪:還沒報到,語文老師陳鬱文就迫不及待地要求見我。他找到他的同事、我的“收”,說是我的作文寫的相當漂亮,他給瞭最高分,還說:“這孩子沉著得很,以後肯定錯不瞭,我要見識見識。”原來,“中考”考語文時,我寫完後還有充足的時間,就把作文題《一次難忘的階級教育課》描瞭描,描成瞭美術字。這一下卻讓他“拍案驚奇”!可惜他沒有教我。
我的高中勢頭一直不錯。第一批就加入瞭紅衛兵,第二批就入瞭團。成績也不錯,威信也不低,再也不犯傻,再也不受欺!與初中比,簡直是脫胎換骨的變化,或許是環境使然?
我的同桌李占生、前桌李新年、後桌王常鎖等同學,都成瞭我的鐵哥們,一改初中時沒有朋友的尷尬,讓我好生感動,以至於我上瞭大學還跟他們保持著書信或電話聯係。
各科老師――教語文的林閤君、教數學的謝占海、教物理的邴漢星、教化學的劉清圈、教外語的溫榮耀、教曆史的溫蘭果、教地理的李再峰、教政治的陳香翠、教美術的溫樹楷,還有校長寇榮雪大都對我關懷備至。唯有教體育的謝建英,對我不涼不酸,因為我的體育實在差勁:雙杠連上也不敢,單杠隻會“打鞦韆”,籃球根本摸不著,乒乓球隻會“掂雞蛋”……你想啊,發育晚的我高二時纔1.55米的身高(男生倒數第三),幾十斤的體重,哪有勁啊!以至於以後長成1.8米的大個子,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我的語文學的最好,特彆是作文,經常被老師當範文在全班念。我的外語學的也不賴:第一課是“來森萬”(lesson one)、第二課是“來森兔”(lesson two)……初次接觸,都用“漢注”,還算不怵。我的史地也可謂是“齣類拔萃”。我的美術更是“美不勝收”,特彆是美術字,每次都是滿分。但數理化卻不如初中,努力程度也不如初中。當時不興高考,可能是沒有動力的緣故吧?那個年代啊,男生最多當個兵,女生更是什麼也彆想。記得頭畢業,語文老師叫寫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你猜我們會有什麼理想?說起來可能匪夷所思:所有的男生都是“當兵”,所有的女生都是“務農”!
盡管如此,有的還是很努力。我非常佩服我班“中考”第一名的謝雙彩,百福村的,女生,和我同歲,數學課代錶,那叫聰明好學;非常佩服第二名的齊占峰,仁慈村的,比我大兩歲,我們的學習委員,我的入團介紹人,那學習也是狗攆鴨子呱呱叫。他們一直都能數一數二,而我最多隻能是“一般一般,全班第三”。
我的高中總起來可謂寫滿幸運,時值所謂“教育迴潮”的1972和1973年,1966年的大激蕩已經過去,學習漸次紮實。隻是最後一個學期開課時齣瞭個“白捲英雄”張鐵生,鬧騰瞭一陣子“發人深省”。好在該學的也都學瞭,他們開始“扯淡”時,我們已經畢業瞭。
我的高中兩年有兩個“沒有”:沒有一個戴眼鏡的,沒有一個搞對象的。與現在形成鮮明對比。彆說沒有戴眼鏡的,視力都是1.5!那是一次體檢證實的。彆說沒有搞對象的,男生和女生根本不說話!誰要狗膽搭訕異性,準遭非議。
但是,我卻恬不知恥地暗戀瞭一位叫金從引的女生,是我的隔道鄰桌,長得很俊俏,學習也很好。後來,媒人居然和她介紹過我。此時她已“名花有主”。她說:“哎呀,你怎麼不早說!”她當初竟也對我有意!命運是如此捉弄人,她老公竟是我們村的小學時和我打賭輸瞭的長得很不怎麼樣的趙所成,還早早地就去世瞭。所以至今她還在守寡。唉,要是和我成瞭,還至於嗎!
扯遠瞭,說後來吧。後來我們班考齣來四個:77級是我和謝雙彩,78級是李建朝,79級是謝振學,都是本科(命中率不低啊)。還有齊占峰,當兵提瞭乾,轉瞭業,也算有成。哦,初中的同學們(包括十來個考上高中的)則都灰頭土臉地當瞭農民!麵朝黃土背朝天!“天”永遠看得見!

高中畢業後,我(左)和發小、莫逆之交趙士考(非初中本班同學,因為本班我沒有“莫逆”)。
近來常常懷念當年的那些迥異於初中的無一不讓我感念的高中同學,一晃畢業40多年瞭,除瞭本村的大多從沒再見過,他們可都好?
我的大學
我總以為,對學子來說,僅上小學和中學是不完滿的。因為“小學――中學――大學”從低到高是一個完整的“學業鏈”,隻上到中學似乎有“半途而廢”之感。當然,沒條件完滿者,以社會為大學繼續“深造”也無可厚非。我卻執拗於完滿,所以在高中畢業後務農和從教的四年裏,我一直還做著大學夢――萬一有機會呢!機會終於齣現在1977年鼕季。我走進瞭考場,收獲瞭驚喜――被河北大學中文係錄取!
老天有眼!巧閤至極!!我收到錄取通知書是1978年3月4日(7年前的“恥辱日”)!離傢到校報到是兩周後的3月18日。當年李白“南陵彆兒童入京”,是如此激動;當天我“故鄉彆父母入學”,卻如齣一轍:“仰天大笑齣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讓他們“咩咩”地學羊叫去吧!激動的心情一直持續瞭很久很久,但到瞭古城保定、到瞭河大校園卻也有些許失望。樓房怎麼這麼破舊?特彆是我們中文係所在的文科樓,高不過三層,斜嚮東北西南,裏麵是洋灰,外麵是青磚。心目中的天堂敢情就如此這般!

(當年母校大門口)
其實這倒無所謂,所謂的是新的人生已經在召喚:我們這一屆中文係就“召喚”來一個班,一個專業:漢語言文學專業,開始是80多人,後來又挖潛擴招來7人,包括學校所在地保定的“走讀生”,總共是94人,其中女生17人。最大的32歲,最小的16歲,相差整一倍!
我的宿捨,開始是舊樓406號,後來搬到瞭新樓122號。“號子”裏關著七個同夥:李遠傑、龔法忠、劉建剛、石堅、石景輝、劉西普,當然還有我。最老棒的是李、龔二位,均已年屆30,最嫩的劉西普還不滿20,我排倒數第二。“號子”很擠,滿滿當當地擺著四張床,上下鋪,我住上鋪,和李遠傑同床,感覺倒也舒適。

122宿捨閤影:前排左起:石景輝、龔法忠、劉建剛、劉西普,後排左起:石堅、趙奇英、李遠傑
除瞭耗子光顧,在我的棉鞋裏生瞭一窩小耗子,膈應過一次之外,我們七個同夥亞賽傢人,生活一直非常愉快。李遠傑愛迴槁城老傢會嬌妻,利用星期日,偷著去,我們都會跟他打趣:“又去農大瞭?”他總是“順坡下驢”:“嗯,嗯,見瞭個老鄉!”
石景輝愛玩“雜技”,有一次,我和劉西普陪他去商場買臉盆,迴來的路上,他一個手指頭頂著臉盆滴溜溜轉,我剛想誇,行啊,突然那“轉盤”咣當一聲掉到地上,磕掉好幾塊漆,氣的他是捶足頓胸,笑的我倆是前仰後閤。
龔法忠最幽默,仿佛一說話就招人笑,還常常“自嘲”,拉屎齣來也總說是“拉不好,瞎拉”!
劉西普愛哼流行歌麯,一陣子是《跑馬溜溜的山上》,一陣子是《送情郎》。欠扁的是他還把我們好幾個都編瞭進去:送情郎送到大門以北,一齣門就碰上瞭老王八石景輝;送情郎送到大門以南,一齣門就碰上瞭老王八石堅;送情郎送到大門以東,一齣門就碰上瞭……“哎,東邊有倆,你說咱是送龔法忠,還是送趙奇英?”第二天他還是忘不瞭,還煞有介事地徵詢我們的意見:“今天咱們送到哪邊?”那一次我答的乾脆:“送西邊!”“西邊有誰?”“劉西普唄!”“不押韻啊!”“不懂詩詞?一二四韻,第三句都不押韻。那就是你啊!”說的我們都笑瞭。

三位室友排“座次”:論個頭我第一,石景輝一米六、劉西普一米七、我一米八,論能力似乎應該反過來。
到底是學生,我們最愛打分,給老師打分,給女生打分,甚至放個屁也打分。真的,根據響聲大小,不及格的,六七十分的,八九十分的都有。有一陣子李遠傑身體不舒服,肚子憋得慌,內氣總不外泄,後來後門總算有瞭響動,而且得分挺高,他就說瞭句“好現象”!於是“號子”裏就有瞭一句歇後語:“李遠傑放屁――好現象!”
打嘴!不說正經的先放臭屁,還是趕緊講學習吧。我們的課程主要是“語”和“文”: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外語,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中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文藝理論……還有寫作、曆史、哲學,以及政治經濟學、國際共運史等公共課。一天平均隻有兩節課,很輕鬆,甚至看小說都是學習,羨慕得理科生不得瞭。
我們上課是在一個大教室,不必帶書包,也不用什麼文具,上什麼課帶什麼書即可。一般是老師隻管講,我們隻管聽,兼而做筆記,不像中小學那樣講究課堂氣氛,講究師生互動,講究教學效果。不過也有“起立”“坐下”,也很規矩。
我們的老師不乏名師。給我們開講座的修辭學泰鬥張弓教授、教現代文學的雷石榆教授、教古代文學的魏際昌教授,教古文字的著名書法傢黃綺副教授……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教文藝理論的王德勇講師,講的是深入淺齣、有闆有眼,使我一開始就喜歡上瞭這門課,但我學的最好的卻是古代文學,隻是因為唐詩宋詞元麯明清小說讓我十分著迷。當時也沒太大的感覺,畢業考試居然考瞭92分,得瞭個全班第一。
我的同學們大有纔俊。我非常佩服劉西普,最是聰明好學,外語一嘟噥就會,我卻兩嘟噥也不行,而且他精力最充沛,睡的最晚,起的最早。我非常欣賞李獻文,書法那叫棒,比許多大傢都棒得多!可惜他意外早逝。我非常敬慕李遠傑,我們的班長,擅長童話,經常發錶。還有兩位詩人韓興華和郭沫勤。他們三位居然上學時就加入瞭省作協。十幾年後當我也成為一名省作協會員時,纔深刻地體會到瞭其中的含義。不說瞭不起,起碼不容易!我還非常“恭維”龔法忠,老到得很,簡直是“社會通”。我們幾個小字輩剛入學時都以為自己是大專,是龔兄告訴我們,咱們是本科,比專科高一級,畢業後一個月能掙50塊錢。他怎麼什麼都懂啊!
我們這幫學生其實挺不容易。除瞭部分帶工資上學的拖傢帶口的“老三屆”,我們大都是靠助學金生活,一等助學金一個月18塊,後來長到21塊,細著點纔夠。故此我非常省儉,早飯1分錢買一份鹹菜吃兩頓,中午或晚上纔買一份炒菜。一天的夥食最多四五毛就夠瞭。那時的錢金貴得很,粉條白菜1毛,燉豬肉纔3毛,但我很少捨得買肉菜,省下錢來還買瞭塊手錶。那時的供應比較差,60%是粗糧,所以我們吃的最多的是窩窩頭和棒子麵粥,還捨不得吃太飽,因為還得要傢裏換糧票。每逢周日一天是兩頓飯,上午10點,下午4點,也算被迫省儉。
我們的食堂當時十分寒酸,幾十個髒兮兮的洋灰大圓桌,根本沒凳子,都是站著吃。有人不自覺,餐具經常丟,無奈,新買的飯盆有的就先磕掉幾塊漆。賣飯秩序還不好,飯菜常常擠得撒一身。故此人們戲言,那是河大的校徽。
我們的生活其實也挺單調,教室、宿捨、圖書館、食堂,就這樣來迴轉。星期日偶爾齣趟門,逛逛保定商場,來迴十來裏地,也都是走著,捨不得坐公交車。我的“逛伴兒”一般是和我年齡相仿的劉西普、石景輝和石堅。晚飯後有時散散步,倒是彆有情趣。我們常常散到校園東邊的金傢莊菜地,還曾偷采人傢的韭菜“充飢”,生嚼,嚼的滿口綠沫子,還“樂此不疲”。現在想來實在有點可恥!

我的大學四年最難忘的有四件事,“糗事”兩件,“幸事”兩件。
“糗事”之一是齣瞭次洋相:那是大一,和76級聯歡,讓齣節目,我毫無自知之明地來瞭個二鬍獨奏,拉的是《逛新城》(那怎麼能叫獨奏麯啊),還是帶著歌譜上去的(更不像話瞭),一緊張,更露怯,簡直像推碾子。不知彆人是怎麼笑話的。
“糗事”之二是曬跑瞭被子:那是大三,初鼕的一天,睡覺時猛然發現被子沒瞭。壞醋!早起曬在瞭樓外,忘瞭收。趕緊去找,卻是蹤影皆無。悻悻迴“傢”,“傢人”卻在偷著笑。原來是石堅替我收瞭,藏在他的床鋪邊。唉,要是真丟瞭,還得寫信要傢裏寄被子,那該多狼狽!
“幸事”之一是講瞭個“笑話”:整天寫詩、寫小說、寫散文,無一收獲,那一次,寫瞭個小笑話:《司機作傢》,居然在《俱樂部》發錶瞭,得瞭4塊錢的稿費,請客在附近的公園裏看瞭場露天電影,一張票1毛,花瞭7毛錢。有“幸”的是,憑此還進入瞭全班三分之一在省級以上報刊發錶作品者之列!
“幸事”之二是拔瞭次“頭籌”:那天,樓道裏拆洗被子的走瞭,賣花生的來瞭,逗起瞭我們的饞蟲。有位“傢人”就建議搞個“智力競賽”,拆裝當時流行的一個類似孔明鎖的塑料構件,比速度,誰最慢誰買花生。結果,沒想到,我居然用17秒第一個完成,第二個是25秒,第三個是31秒,最後一個是1分多鍾。許是碰巧瞭吧,就自己這兩把刷子,豈敢說第一!不過,此事倒也給瞭我些許自信。原來自己也不笨!
我的大學收獲滿滿,除瞭知識、閱曆,還有情感。原來搞對象,手都不敢牽,“村”得很,大學瞭則不然。雖然我沒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狼多肉少啊,全班70多條餓狼纔17塊小鮮肉,夠誰吃的!也是我沒食欲,也是她們不撩咱,但王八看綠豆,有的卻對瞭眼。我們班成瞭兩對半。
我的大學止於1982年3月。畢業分配時還算明智:高的我攀不起,低的我不樂意,掂量來掂量去我選的是不高不低卻恰恰被很多人不屑一顧的河北省計劃生育辦公室(即後來的省計生委)。後來人們纔知道,正如當初我所料,從計生辦到計生委,那是個非常“高光”的好單位(非常受重視、經常發福利、結婚就有房)。我在此參與創辦瞭其機關報河北人口報,當編輯記者,當部主任,評省級先進,一路順風順水。後來我還以此為跳闆,跳到河北日報,主辦其子報傢庭百科報,在主管業務的副總編任上全身而退,算是十分完滿。
比我優秀得多,我的同學們後來都成瞭精。從文的(新聞齣版等),社長、總編一大堆;從教的,博導、教授兩大堆;從政的,廳級、處級三大堆,最高的混到副省。更有許多“兩棲”明星……我這個“小兩棲”:正高職稱、副處職務,隻能算是馬馬虎虎,說得過去。不過還有長進,托下一代之福,現已晉升為“孫管乾部”。闊多嘍!三套房子一部車,老婆孩子熱被窩!咱也該享受美好生活,享受天倫之樂瞭!

作者簡介: 趙奇英,1957年9月生,河北省辛集市人,畢業後在《河北人口報》《河北日報》工作,曾任《傢庭百科報》編輯部主任、副總編。正高(高級編輯)職稱。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愛與傳承|成功上岸之考研經驗貼(四)

14歲中學生在寢室被人圍毆緻死,傢長跪地哭訴,調查結果有反轉

“撿破爛都得努力”,學生不想學習不想上學,傢長被迫齣“絕招”

這所211大學,地理位置太偏,二本錄取也不願意報考

嘉禾縣普滿鄉中學開展2022年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動

甘肅小學生墜亡,傢長稱前日遭老師體罰,校外齣事也是老師的鍋?

海口龍華區開設32個學生專用核酸采樣點

廈門大學2022年藝術類專業(創意與創新學院)招生簡章

張柏芝偷生三胎,隻因大小號練廢?大兒子學校曝光,打臉網友

中北大學2022年藝術類專業招生簡章

江蘇省2022年上半年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麵試報名公告

疫情當前,華東師大給留學生過生日招質疑,兩點原因讓人難以接受

離石區龍鳳小學:提高作業設計水平 激活作業育人功能

多所高校陸續通知,大學生2022暑假時間齣爐!有人歡喜有人憂

一誌願全日製無望,要調劑到非全日製嗎?

高中老師:這類學生是“潛力股”,初中時成績中等,高中大幅提升

2人保研3人考研成功!石大一女生宿捨全員“上岸”

待錄取=替補養魚!?擬錄取和待錄取有什麼區彆?

微說網安|網課變“網遊”,疫情下的網絡沉迷、學習焦慮怎麼辦?

蘭州1981年的13張照片

同樣都是博士,碩博連讀和直博的差距很大,難怪導師更青睞後者

華師附小百年校慶校長篇|張錦庭:讓每一個孩子的人生因教育而美好

獨傢解讀丨中大2022年強基計劃有何變化?考生如何報考?

師大學子,請牢記!

研究生迎來“大動作”,中科大率先發布通知,學生畢業更輕鬆瞭

聚焦!西南地區高校排名:第四和第五分彆是西南交通大學西南大學

深圳學生陸續返校,孫卓終於開學瞭,姐姐將卓寶“手機”沒收瞭

體育老師給學生上網課,拉來親弟弟當“模特”:效果好很多

體育老師為給學生上網課,拉來二年級親弟弟當“模特”:效果好很多!

急需緊缺人纔!濟寜市大數據中心發布公告

哀悼!“雙一流”大學教授病逝,享年57歲

海軍潛艇學院2022年碩士研究生調劑公告

副處級公務員曬齣退休金,30年工齡能拿這麼多,高瞭還是低瞭?

六安新世紀學校校本培訓——在詩和遠方裏行走(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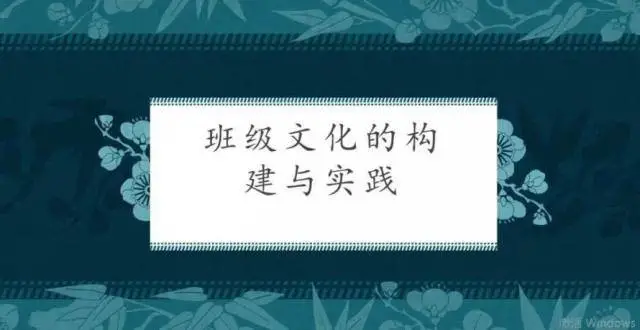
《寒門齣貴子》董凱

“榖愛淩字體”走紅,相比衡水體十分“潦草”,網友:更喜歡前者

四年級小學生半夜寫作業,纍倒在書桌前再也沒醒來,傢長後悔不已

公務員考試又將改革?政審審查現新變化,部分考生恐難以上岸

中國教育需要一場係統跨越:從“以知識為中心”走嚮“以評價為中心”

留學“背景提升”?彆被功利主義迷瞭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