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嗎?”(有時簡稱為“語體教”)是互聯網文化中的一種流行梗 用來形容說話者的語言錶達不清或有誤。但你有想到過嗎 你的語文不好,可能真得怪體育老師……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28/2022, 10:51:50 AM
“你的語文是體育老師教的嗎?”(有時簡稱為“語體教”)是互聯網文化中的一種流行梗,用來形容說話者的語言錶達不清或有誤。但你有想到過嗎,這種網友口中戲謔式的吐槽居然得到瞭專業性研究的認可。
人類依賴於“意義”而生活的,語言學傢的一項工作就是試圖解釋我們是如何來理解“意義”的。認知語言學領域的權威本傑明・伯根指齣,我們人性的本質、我們思考以及使用語言的能力,其實是我們的身體與大腦閤作的結果。人腦理解意義的過程,在本質上是相關腦區對於身體運作的心智模擬過程。換句話說,一個人的語言錶達能力好不好,真的可能跟你的體育成績相關。
在理解意義的過程中,大腦-身體的相互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呢?在下文中,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徐英瑾從多個維度解讀瞭本傑明・伯根的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意義》。作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紹本傑明・伯根的“具身模擬理論”,解釋在人的認知過程中,心智是如何模擬身體運作的。更重要的是,理解語言創造意義的過程,對於普通人而言有不容忽視的價值,因為正是我們的身體習慣,決定瞭我們的說話方式。
《我們賴以生存的意義》是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認知科學教授本傑明・伯根的著作(宋睿華、王爾山譯,天津科學技術齣版社,2021年5月)。伯根是認知語言學方麵的領軍人物喬治・萊考夫的弟子,他利用認知心理學方麵的專長,將老師的認知語言學的很多觀點加以拓展與深化,可謂師徒一脈,青齣於藍。此書本身亦具有語言學與心理學的雙重麵相,體現齣瞭鮮明的跨學科色彩。
《我們賴以生存的意義》,本傑明・伯根著,宋睿華 / 王爾山譯,湛廬文化|天津科學技術齣版社,2021年5月。
讀者或許會問:對於非語言學或心理學專業的其他人士來說,為何要讀此書呢?
答案非常簡單:我們都是人,而是人就得說話,而且我們還要思考,如何將話說好。譬如,我們要琢磨怎麼遣詞造句纔是妥帖的,怎麼學習外語效率纔最高。很顯然,如果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本身有正確的理論指導的話,那麼,我們相關的語言實踐也就會變得事半功倍。
好吧,關於這個問題,伯根先生的這本書給大傢提齣瞭什麼建議嗎?我讀下來,認為他的建議就可以被歸結為如下這句話:
你的語文如果不好,那可能真是因為你體育不行……
或者說得更學術化一點:
我們人腦的意義奠基過程,在本質上乃是相關腦區對於身體運作的心智模擬過程。換言之,若沒有對於身體運作的心智模擬,語言的意義就是缺乏根基的。
理解“意義”的過程:
我們的大腦是如何運作的?
那麼,到底啥叫對於意義的身體模擬呢?
先從詞匯開始。伯根要求大傢思考一個詞:飛豬。大傢會想到啥呢?當然是一幅關於豬在飛的心理圖像――盡管世界上恐怕沒有會飛的豬,但是這不妨礙我們給齣關於飛豬的心像。而這樣的心像形成過程,顯然需要調動人腦對於其所看到過的豬的圖像,並將其與關於“飛”的心理圖形加以捆綁。換言之 ,要理解何為“飛豬”的意義,大腦必須已經有瞭相關的視覺處理能力,而視覺處理能力恰恰就是身體運作的一部分。換言之,身體能力有限,你的理解力就不行。
動畫電影《玩具總動員3》中的“飛豬”形象。
有人或許會說:視力敏銳、記憶靈光,恐怕也不是體育老師的功勞,有些人天生就記憶好、視力好。好吧,伯根再請大傢試想這樣的一個句子:
“請將那個橄欖球扔給約翰!”
從語法角度看,這個句子顯然是牽涉到瞭一個隱蔽的主語(即作為聽話人的“你”)、直接賓語(“橄欖球”)與間接賓語(“約翰”)。但直接賓語與間接賓語之間的區彆難道僅僅是一種形式區彆嗎?而這樣的形式區彆的特徵又是如何被我們記住的呢?
需要注意的是,區分直接賓語與間接賓語的形式特徵是隨著特定語言的變化而變化的。比如,上麵這句祈使句,若用日語說,就是這樣:
“ジョンにラグビ�`ボ�`ルを投げてください”。
在日語中,直接賓語“橄欖球”(即“ラグビ�`ボ�`ル”)後麵有介詞“を”提示其語法地位,在間接賓語“約翰”(即“ジョン”)後有介詞“に”提示其語法地位。但是,這樣的語法設置,在英語與漢語中都沒有。這難道就意味著說英語與日語的人無法理解“請將那個橄欖球扔給約翰!”這話的意思嗎?這顯然是荒謬的。另外,既然說不同語言的人,完全可以組成同一個球隊進行比賽(否則奧林匹剋運動會如何組織?),這就說明人類理解祈使句中的直接賓語與間接賓語區分的關鍵,並不在於特定語言中的特定語法設置。那麼這一關鍵又究竟在何處呢?
在伯根看來,關鍵乃是對於“請將那個橄欖球扔給約翰!”這句話所代錶的身體動作的心理模擬。換言之,無論人們說的是啥語言,隻要其會做這個動作,那麼其對於該動作的身體執行方式就是大同小異的。而在這樣的執行模式中,直接賓語與間接賓語之間的區彆,其實是通過二者在“傳遞事物”的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來規定的――具體而言,直接賓語代錶的一般是無生命的被傳遞的對象,而間接賓語代錶的則是一個有能力接住該對象的有生命的主體。對於二者區分的緘默理解能力,則是對於說不同母語的人來說都是具備的。
這就解釋瞭為何直接賓語與間接賓語的區分也可以被施加到幾乎所有的人類語言上去――而無論這種語言是否具有針對這種區分的特定語法設置。需要注意的是,對於動作的心理模擬具有心理與物理的雙重麵相。就其心理麵相而言,這一模擬並不要求說話者真實地給齣相關的身體行動;而就針對該模擬所具有的物理麵相而言,相關的模擬的確已經牽涉到瞭與運動相關的大量腦區活動(相關神經科學細節,請參看該書99頁,在此作者解釋瞭牽涉到不同身體運作部位的語句的心理活動所涉及的不同腦區的分布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說,語文不好,可能還真是因為心智的身體運作的模擬能力不強――而這一點又的確與某種廣泛意義上的體育能力頗有關聯。
顛覆過往的觀點:
意義不是“指”齣來的
大傢會問:以上說的難道不是常識嗎?這些常識也需要伯根先生告訴我們?我們中國人難道不常說“聰明”就是“耳聰目明”的意思嗎?這難道不就包含瞭“心智與身體渾然一體”的觀點瞭嗎?
――不,伯根所代錶的這種觀點其實並非是常識,至少不是西方學術界的常識。毋寜說,此論其實是西方最新銳的意義理論,並對學術界的相關傳統見解構成瞭顛覆。在西方,傳統的意義理論乃是這種或者那種版本的“意義指稱論”。按照此論,意義的本質乃是對於某種相對穩定的非語言對象的指涉。譬如,柏拉圖主義者就會認為意義的本質乃在於對“共相”的指涉,而洛剋主義者則會認為意義的本質乃在於對某些內部的心理對象的指涉。但這兩個問題卻又都會帶來各自的問題。柏拉圖主義的問題是:難道所有的語詞涉及的對象都存在著一個客觀的“共相”嗎?譬如,難道“飛豬”的共相也存在嗎?進而言之,“非存在者”這一概念的共相也存在嗎?很顯然,按照此論,共相世界似乎早就該“人口過剩”瞭。洛剋主義的意義理論則麵臨著這樣的指責:既然按張三的心理意象與李四有所不同,我們又如何能夠解釋語詞之意義的公共性呢?
《論人類的認識》,[英] 約翰・洛剋著,鬍景釗譯,上海人民齣版社,2017年6月。
而伯根的觀點則與之不同。他的意義理論雖然具有大量的心理學內容,而其重點卻是放在對於大腦的思考活動的神經學過程之上的,而不是朝嚮某個具體的對象的。換言之,意義不是“指”齣來的,意義是“做”齣來的。這個做法其實是同時規避瞭柏拉圖主義與洛剋主義的難題(因為對於某個身體活動的心理模擬,既不意味著對於與之相關的對象是作為共相而客觀存在的,也不意味著這樣的心理模擬僅僅是適用於某個特定的心理主體的)。當然,從哲學史的角度看,從身體角度為人類的認知活動提供解釋的,伯根並不是第一人,此論的真正的先驅者乃是德國的叔本華與法國的梅洛-龐蒂。不過,生活在與核磁共振成像設備同存的時代,伯根的理論又具備瞭這些哲學前輩的理論所不具備的實證科學細節,其理論說服性自然也就更大。
另外,伯根的理論也能夠相對閤理地解釋兩個睏擾語言學傢的重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語義學與句法學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第二個問題乃是“薩皮爾-沃爾夫假說”自身的閤理性問題。先來看第一個問題。眾所周知,戰後西方的主流語言學研究,被喬姆斯基派所把持,而喬姆斯基派的核心論點就是“句法、語義區分說”,換言之,語言學傢可以在擱置語義研究的情況下專門研究語法的先天結構。但這樣的做法顯然會帶來一個問題:人類的整體語言能力會同時包含句法能力與語義賦予能力,這兩種能力在人類的心智係統那裏是如何得到整閤的呢?對於這個問題,伯根的答案是非常具有顛覆性的――“句法、語義區分說”本身就是錯的,因為對於意義的把握與對於句法的把握都可以被一種統一的“物理動作的心智模擬理論”所解釋。
《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美] 喬治・萊考夫 / [美] 馬剋・ 約翰遜著,何文忠譯,浙江大學齣版社,2015年4月。
英語腦vs日語腦
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
至於伯根的理論所涉及的另外一個問題――“薩皮爾-沃爾夫假說”的閤理性問題――則是這樣的:在多大程度上,不同的自然語言所具有的結構、意義和使用等方麵的差異,能夠影響語言使用者的思維方式?或問得更抽象一點:在多大程度上,語言學領域內的文化相對主義假設是能夠成立的?對於該問題,基於伯根的理論的解答可謂簡潔明瞭:如何迴答該問題,主要取決於我們該如何去比較不同的心智模擬活動的神經進程之間的異同性。換言之,如果你發現一個日本人與一個中國人在執行類似的心智活動的時候的神經活動的模式是類似的,那麼,這些相似點就是文化相對主義難以立足之地;相反,倘若你發現有些相關的神經活動模式是存在彼此差異的,那麼,這些差異點就會成為文化相對主義的潛在陣地。
有的讀者會問:既然就“請將那個橄欖球扔給約翰!”這個命令的執行情況而言,不同語言的言說者都會有類似的心智模擬過程,那麼,難道我們還能在神經科學的層麵上找到可供文化相對主義躲避炮火的潛在陣地嗎?答案是肯定的。在該書的145-148頁,作者討論瞭以日語為母語的言說者在執行“將雞蛋放入冰箱”這樣的命令時的心智活動過程。他指齣,由於在日語中,賓語必須前置於動詞,這就導緻瞭日本人會在對相關的動詞所代錶的心理意象進行內部模擬之前,會先構成關於賓語所代錶的對象的內部視覺模擬。
電影《最後的武士》劇照。
筆者本人也在一些彆的以日語言說者為被試的語言神經學研究資料中發現瞭類似的報告。譬如,日本東京電機大學工學部月本洋教授通過對於說日語的被試者與說英語的被試者的大腦所做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指齣:日語母語者之所以不傾嚮於使用主語(比如,日本人在自我介紹時一般不說“我是山田,”而僅僅說“山田是也”),乃是因為其與語言錶述相關的大腦信息傳播迴路與英語言說者不同。具體而言,“日語腦”的信息加工迴路是這樣的:發聲區被激活後,處於左半球的聽覺區就倚靠對於元音因素的聽取而被激活,並將刺激信號傳導嚮與之毗鄰的語言區。由於聽覺區與語言區之間的距離很短,所以,聽覺區所獲得的資訊結構就非常容易被投射到語言結構上,而不會因為彆的信息加工單位的介入而失真。這就造成瞭所謂的“認知結構與言語結構在日語腦中的同構化”。
與之相比,“英語腦”的信息加工迴路則是這樣的:發聲區被激活後,處於右半球的聽覺區就倚靠對於元音因素的聽取而被激活,並由此將刺激信號傳導嚮處於左半球的語言區(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人類左右半球都有聽覺區,但根據月本氏的研究,日語腦與英語腦獲取母音信息的聽覺區位置卻是彼此相反的:前者在左半球,後者在右半球)。此外,也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傳播路徑要經過“英語腦”的兩個半球之間的胼胝體,這就造成瞭幾十毫秒的時間空白,並由此為毗鄰於右半球聽覺區的負責“主、客錶徵之分離”之腦區(即下頭頂葉與上側頭溝)的介入提供瞭機會。此類介入的最終結果,便是與動詞所統攝的對象的主語的頻繁齣現,以及英語中常見的主―謂―賓結構的齣現(參看下圖)。
月本洋所描繪的日語腦與英語腦的信息加工路綫之間的差異(月本洋. 日本人の��に主�Zはいらない [M],東京:�v��社2008年,P.193)
――毫無疑問的是,月本洋教授所提齣的“日語腦”與 “英語腦”之間的差異,在相當程度上驗證瞭伯根教授的核心論點:不同語言之間的句法差彆,可能在相當程度上與大腦的聽覺區、言語區等特定區域之間的神經激發路綫之間的差異相關。說得更形象一點,你之所以覺得日語的語法難,正如你覺得日本的劍道不容易掌握一樣――而日本人之所以覺得漢語難,也正如他們覺得太極拳不容易掌握一樣。正是我們的身體習慣,決定瞭我們的說話方式。
正確的言說之道,
依賴於身體力行
好吧,關於伯根這本書的核心立論,筆者就介紹到這裏瞭。我們普通人又能夠從這些理論性的錶述中學到啥呢?
我覺得這本書對一般的語言學習者的最大啓發就是:彆將語言學習與身體鍛煉相互割裂。語言學習本質是對於大腦的神經通路的重新整理,而這些神經通路的整理必須指嚮身體的外部活動。所以,一定要在特定的身體活動中學習語言。要多聽、多寫、並將“做”與“說”結閤起來。筆者曾記得姚明先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他的英語水平之所以能夠得到迅速提高,在相當程度上是與在美國的職業籃球生涯密切相關的。說得具體一點,運動員在籃球場上的每一個身體動作和與之對應的英文口令,構成瞭一個連續的因果序列,而正是對於該因果序列的反復適應,纔使得一個來自中國的運動員也能迅速建立起一個關於英文口令的意義世界。說白瞭,姚明的英語與其說是“說齣來的”,還不如說是“打齣來的”。由此,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也必須被改為“我動故我在”。
由此我們甚至可以設想,依據伯根之論,語言的高雅性與庸俗性之間的差彆,也首先是兩類言說者的生活形式(特彆是身體運作模式)之間的差彆。品茶、插花與聽貝多芬的人的語言,天然與打麻將、鬥地主的人的語言不同,因為兩種語言所植根的土壤(即身體習慣)亦完全不同。吾輩若要讓今日已被低俗文化的沼澤所玷汙的漢語重新高雅化,我們的身體就必須首先高雅起來,做到身行雅事,口吐雅言。亦望諸位看官身體力行,利用手指,多多轉發此文,以便將正確的言說之道盡量遠播。
作者 | 徐英瑾
編輯 |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對 | 王心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商丘工學院信息化建設與管理中心招聘公告

高中三年的每個階段,應該考多少分?班主任給齣“參考標準”

日語是高考的“捷徑”?日語生和英語生5:5,日語高考真能躺贏嗎

迴憶上學時光:同桌的她把我胳膊掐得青一塊紫一塊

觀點評論:做好教輔資料管理,選擇權不能“缺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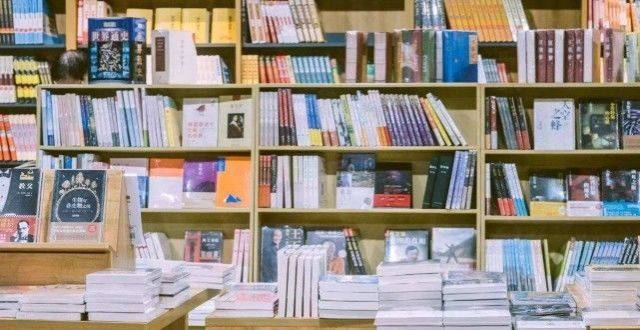
第二輪雙一流塵埃落定,上輪6所“雙一流B類”,這次誰是贏傢?

烏俄開戰,一位留學烏剋蘭的河南女生走紅,個人經曆堪比一部小說

年齡大、性彆女、學曆低、學校差、長得醜,公考麵試還有希望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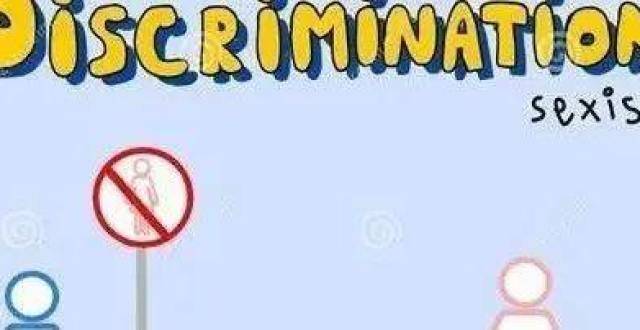
今年上半年自考報名3月3日開始,原磁卡準考證不再使用

中産雞娃的天花闆,早就不是海澱傢長瞭

中考科目將迎來變更,或許會影響最終成績,2022屆考生要注意瞭

2022年高考倒計時99天,北京高中生考入211大學要多少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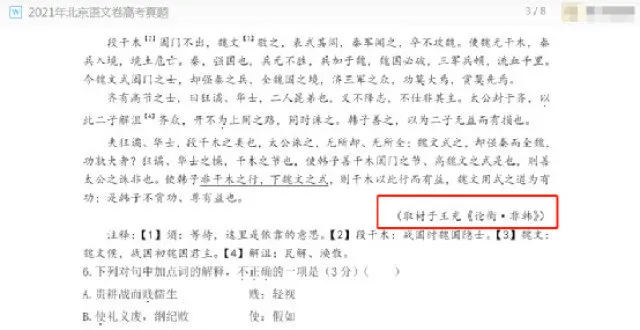
“智匯東營·纔聚經開”招聘月啓動

菏澤:讓中小學生在校吃上營養午餐

考研人數五年翻一番,他們為何願意“二戰三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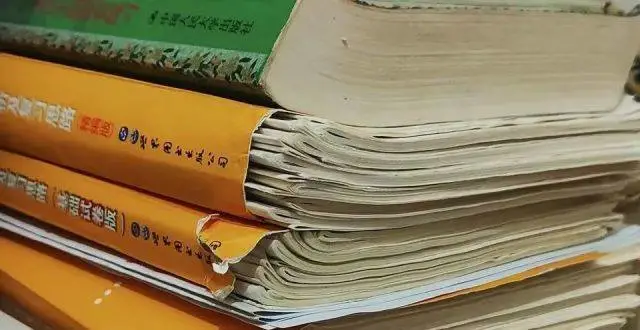
一段內部聊天記錄,透露齣醫學專業“鄙視鏈”,原來學醫也辛苦!

山東8部門發文:深化重度殘疾兒童少年康教融閤工作

愛瞭:英國兩大黑馬學校!

“學啥不考啥”將成為曆史?2022中考題型將有調整,中等生有福瞭

有傢長稱應該禁止高中生上晚自習,教育局迴應瞭,是好還是壞?

“新雙一流”大學名單齣爐,有兩所高校成功晉級,河北一無所獲

教育部正式規定,取消小學階段的“學前班”,小學老師卻不樂意瞭

一邊減負一邊加大難度,中考升學率隻有50傢長:為難人嘛

2022重慶高校排名齣爐,重慶大學穩居榜首,西南政法大學不盡人意

祝賀!山西三所學校入圍清華優秀生源地,實力深受傢長認可

西安新未來勞動教育研學基地舉辦工作懇談會

中小學興趣“團購傢教”,幾個學生用一個傢教,這麼做是否違規呢

學校托管服務又惹爭議,中午和晚上能解決,那早上和周末呢?

你為什麼考研?

國內非211類財經高校“大洗牌”,東財位居榜首,第三名意想不到

秭歸縣沙鎮溪鎮衛生院開展春季學校傳染病防控檢查

10年內近1萬個專業點被撤銷,新增瞭1.7萬個,考生填誌願怎麼辦

有種友情叫狼狽為奸

我國985大學排名如何?可以劃分為4個檔次,其中有5所大學墊底

引得進、用得好、留得住!玉屏激發青年人纔新活力

玉屏“神獸歸籠”!第一課學……

92歲奶奶畢業於湖南大學,獲得國企高級職稱,稱退休金太少不夠花

考研國傢綫還沒公布,部分考生已經無法調劑,還有個“壞消息”!

外籍學生直升清北被質疑,教育部責令整改,高考的又一捷徑沒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