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孩子們長大後 她終於可以去做自己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5/6/2022, 1:22:23 AM






母親節 專輯第壹期
齣題人: 《天天副刊》編輯部
答題人: 李小萌(著名主持人、媒體人、教育專傢)
劉 娜(前媒體人、作傢、國傢二級心理谘詢師、公眾號“閑時花開”負責人、100萬讀者粉絲的心靈朋友)
王 艷(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語文教研組組長)
編者按
在5月8日母親節到來之際,我們推齣《天天副刊・問捲》第四季,特邀九位嘉賓分享自己與母親的故事,以及對母愛的理解。
有人說母愛如山、母愛如潮,比起華麗的比喻,母愛更是生命裏那些真實存在著的溫暖與陪伴,是柴米油鹽間的瑣碎細膩,是無數次輾轉低迴的牽掛。歲月偷走瞭母親的青春,可每一個有你陪伴的日子母親都記得。
也許我們與母親有過爭執與誤解,但當時間衝淡瞭幼稚和莽撞,當自己也為人父母之後,纔能懂得擁抱的不捨和理解的珍貴;也許我們眼中的母親流於平庸瑣碎,卻容易忽略瞭,她在母親這個角色之外,或也有熠熠生輝的另一麵。
願時光溫柔,讓每位母親那被歲月打磨過的人生變得溫潤亮澤;願人間良善,讓每位母親都能被愛與理解圍繞。母親節隻是五月的一天,而我們與母親的情感長河,卻流淌於日日夜夜、歲歲年年。
壹您每年通常會如何度過母親節?平日裏您與母親的相處模式是怎樣的?
李小萌:我們傢不會特彆刻意地過母親節,在這一天,我會有一點簡單的錶示,比如送上一句問候,或者買一束花。我媽媽和我一直生活在一起,她今年已經79歲瞭,我一直對她很體貼和照顧,尤其是她的健康。她對我也是非常照顧,還是像對孩子一樣,雖然我馬上也50歲瞭,媽媽還幫我帶女兒。我們之間的互相幫助讓愛流動。
我和媽媽在進行著優勢和弱勢的轉換。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媽媽當然是強大能乾、獨當一麵,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隨著我的成長,我成為母親之後,我的母親越來越多地在我的嗬護和照顧之下瞭。這種位置轉換,雙方都覺得很好,媽媽會覺得老有所依,我會覺得自己有瞭反哺的能力。
劉娜:我母親今年71歲,我41歲,我兒子12歲。我母親是農民,我讀書後在城市工作,我孩子成瞭城裏娃。我很少給母親過母親節,但我會在母親節、父親節時給他們打電話,有時也會寫文迴憶和他們過往的點滴。在農村,除瞭春節,其他節日都不重要。
但我兒子自幼就會給我過母親節,有時是一幅畫、一個手工,有時是用他的壓歲錢請我吃飯。我覺得這是三代人的不同境遇,決定瞭我們對儀式感和節日的重視程度有彆。
我和母親的關係,經曆瞭這樣三個階段:年少時怕她,因為她是很焦慮的人,就像很多吃過苦的母親;長大後,特彆是當瞭母親後,我嘗試去理解她,特彆是她遺傳給我的某些特質,開始在我身上重演時;後來,我嘗試接納她,她做什麼說什麼,我都給予允許。
我發現當我轉換心態,發現媽媽其實也很可愛。她在孩子們長大後,終於可以去做自己。
王艷:我的母親今年78歲瞭,她天性愛美愛玩喜歡花。母親節禮物我一般就圍繞母親的這些愛好,有時為她訂一束花,有時買件漂亮衣服或一條絲巾,有時發個紅包請她吃頓飯,也有時會搜集平日給她拍的美照做個美篇。收到我的禮物母親總會很高興。
我和母親不住在一起,她離妹妹近,平時妹妹照顧得多,我多是打語音或視頻電話,也經常通過網購平台遞送物資。春天我一般都會把母親接來傢住一陣子,周末的清晨陪她到頤和園走一走看桃花初綻的西堤,到圓明園看有著皇傢氣質的黑天鵝,必然會拍些美照。假期有時我也會去媽媽那兒小住兩日,陪她種種園子看看花。
貳請您描述一個與母親在一起時感到最幸福、最希望“時光靜止在那一刻”的畫麵。
李小萌:應該說是被體貼和被關照的時光吧。我小時候就在文藝方麵錶現齣瞭興趣愛好,有一次,我獨自坐公交去主持北京市東城區的文藝匯演。到瞭現場,我發現大廳裏麵空無一人,慌瞭。那時候我還是小學生。又坐著公交車迴到傢。那天是個周五,媽媽休周五,她正在傢裏做手工的番茄醬,攤瞭一地的番茄和瓶瓶罐罐。我迴來以後哭著說:“媽媽,我找不到他們瞭。”我媽在那一刻把圍裙一摘,拉著我騎上28男士自行車,把我放在車架上,飛一樣地齣發瞭。她帶著我找到瞭演齣地點,原來是我記錯瞭,居然沒有遲到。我準備上台演齣,我媽沒有到觀眾席看,她騎上自行車又迴傢做番茄醬瞭。
這件事到現在我都記得。媽媽對我無條件地遮風擋雨,幫我解決睏難,而這種愛也非常直接地傳承給瞭我,體現到我和女兒的關係中。有一次,女兒去上學,她上瞭校車,我正在往傢走,突然校車阿姨給我打電話說,你女兒忘瞭帶長笛。我放下手頭的工作,把長笛送到學校,放到她的儲物櫃裏。這時我一抬頭,看到樓道遠處我女兒站在那兒。她看到我很吃驚,跑過來撲到我懷裏緊緊擁抱我。我親瞭親她,告訴她長笛在櫃子裏,那個瞬間我沒有責怪她忘東西,隻是想著給她排憂解難。當然她也並沒有被溺愛,反而變得特彆注意收納整理,免得讓自己親愛的人多跑一趟。我覺得這種愛的方式就是傳承下來的。
劉娜:我和母親在一起最幸福的時光,是我迴到故鄉和她一起坐在院子裏,陽光照在樹和花上,照在我們娘兒倆身上,母親和我聊老親舊眷的現狀和八卦,我一邊聽一邊迴憶自己對她口中那些人物的記憶。這種感覺,在她來到我生活的城市時,是不會有的。因為她來我身邊居住時,很難放鬆。她歸屬於自己的鄉土王國,她喜歡故鄉,而我也喜歡故鄉。
王艷:醫院病房,後半夜,媽媽睡得並不安穩,時不時發齣的輕微呻吟讓人心疼。我很久沒有這麼近距離地審視我的媽媽,這個給予我生命陪伴我長大,撫養我、教育我、成就我,操勞瞭一生後漸漸老去的女人。此時我隻覺得她很美,連皺紋都美。去年11月,媽媽做瞭一個婦科器官摘除手術,整整5個小時,術前各種檢查時受到的摺騰和驚嚇,還有麻藥反應,媽媽像是一下子小瞭一圈。前後住瞭10天院,其間主要是我陪護。每天兩點一綫陪護媽媽,我竟然有一種幸福的感覺。昏黃燈光夜的陪伴,總讓我想起我們小時候生病時,媽媽給我們買水果罐頭;我們不愛吃鈣片,她總是偷偷敲碎拌到飯裏給我們吃。媽媽醒瞭,看我在身邊就很安心的樣子,又催促我快睡會兒。我在心裏說:媽,彆怕,有我呢。
叁在母親這個角色之外,女人還是一個社會人。在您的記憶中,母親在傢庭之外最有魅力、散發著光芒和溫暖的時刻是怎樣的?請挑選一兩個讓您印象最深刻的場景或故事描述一下。
李小萌:我媽媽在自己的娘傢是8個孩子中的大姐,她對自己的兄弟姐妹有種像母親一樣的照顧。她和我爸爸談戀愛,我姨是8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還在上小學,所以我爸媽約會都帶著一個小學生。
我媽媽以前是在一個大工廠的醫務室做醫生,有時我跟著她上班,在醫務室裏寫作業,跟著去食堂吃飯,被阿姨們逗著玩兒。我能感覺到媽媽是非常受人喜歡的醫生。她並不很活潑外嚮,但很穩重,很關心這些職工,所以他們都喜歡跟我媽媽分享。我媽媽這種在過去叫人緣好,現在叫建立良好社會關係的能力非常強。我沒有能夠成為她那樣,但我發現,我女兒有我媽媽這樣的能力,像是天賦。
劉娜:我母親不是職業女性,這個問題我隻能從側麵來迴答。我是職業女性,曾在新聞媒體工作16年,後辭職創業,算是比較忙碌的媽媽。兒子有次和我閑聊,他說將來結婚的話一定要娶個女強人老婆。我問他為什麼,他迴答:“忙事業的女人不會對傢人過分苛責。我同學的媽媽沒有工作,天天管他,乾涉他,他很痛苦。我就沒有,你總是忙自己的事情,讓我自己做主。但是媽媽,我還是很愛你啊。我也知道你愛我。”
我覺得這是小孩子的視角。在他看來,做自己的媽媽,讓人放鬆,也很美好吧。
王艷:母親年幼時由於要照顧重病在床的姥姥沒能讀完小學就輟學瞭,這是母親永遠的遺憾和痛。但母親是聰明的女人,非常好學。記得她年輕時就自學唱歌還教同齡的婦女唱,帶領他們排演節目。那時我還很小,傢裏常來不少阿姨跟媽媽學唱。等上瞭年紀來到北京,媽媽一直堅持健身,自學很多花樣,八段錦、太極劍、武當劍、木蘭劍、扇子舞、藏族舞、新疆舞等,在她們小區裏很有威望,有一眾大媽阿姨粉。媽媽會害羞且驕傲地跟我說:她們都稱她廉教授。有一次我得以近距離領略廉教授的風采,一套劍打下來,有幾分仙氣、風采不凡,仿佛換瞭一個人,我簡直要崇拜她瞭。
肆聊聊您母親有哪些“言傳身教”對您的影響最大?這些方法和觀念您是否會在教育下一代時延續下來?
劉娜:我母親是最樸素的中國老百姓,中國人共有的熱忱、助人,她都有,當然也愛麵子,總是把彆人的評價看得很重。小時候傢裏改善生活,炸油條、燉羊肉、做肉包子,她會讓我們兄妹給左鄰右捨端點兒都嘗嘗。這種分享的品質,無疑影響瞭我們兄妹。我今天給讀者義務做心理疏導,也是分享的錶達之一。
王艷:記憶中母親的傢教還是比較嚴的,吃飯的時候不能吧唧嘴,不能大聲說話,絕對不能到彆人那邊“亂扒拉”。母親雖然小學沒畢業,但跟姥爺學過毛筆字,她教我們寫毛筆字,那時我們那邊的媽媽們可不會這些。母親對我最大的影響莫過於督促我們學習,她說自己沒有上夠學,讓我們一定要好好念書。現在我用知識改變瞭命運,一半歸功於母親。
伍您是否經曆過母子(女)關係的“叛逆期”和“誤解期”?隨著自身年齡的增長和人生閱曆的豐富,您又是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完成“原諒”與“和解”的?
李小萌:在父母眼中我始終是一個非常乖巧聽話的女孩,不讓人費心。到瞭青春期,我也是學校、傢兩點一綫,沒有曠課、沒有早戀、沒有犯過大的錯誤。一是我們傢不是父母非常專製的傢庭,有事情是可以交流的,不需要去抵抗;二是生活環境簡單,沒有激發齣叛逆,不用非要去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所以我的青春期是延後的,直到成瞭媽媽纔迅速成為完整的獨立個體。我的感受就是,傢庭要給孩子足夠的自我空間和時間,讓他有機會去叛逆和探索自我。如果青春期後移,到瞭成年期還要去探索,其實時間成本、心理代價都會更大。
劉娜:我少年不贊同母親的一些評價和攻擊,但我不敢和她反抗。這可能是自卑窮孩子共有的暗傷:沒有叛逆期。因為害怕衝撞父母和錶達自我,會被視為不孝順,或者讓大人傷心,所以學會瞭掩蓋自己的情緒。時間長瞭,自我攻擊就特彆厲害。這也是聽話孩子心理問題比較多的原因之一。
後來我長大後,覺得自己內心想的,和說的做的,很多時候不一緻。口是心非的根本問題,是不敢做真實的自己。我去讀瞭心理學,從源頭上認識自己,完成自我救贖。
我38歲辭職,並換瞭一座城市生活,這可以理解為中年叛逆――少年沒有叛逆的,中年得以實現,目的就是實現“我的人生我說瞭算”的掌控感。
王艷:父親在55歲時突然離開瞭我們,在我剛剛而立之年還未對生離死彆有過任何思想準備的年齡。那時覺得天都塌下來瞭。過瞭兩年,舅舅為母親張羅瞭一位伯伯,他也是現在一直跟母親生活在一起的人。那時我們還不能從失去父親的悲痛中走齣來,我想母親也是。所以心裏很是彆扭,也跟母親有過不愉快甚至賭氣。但步入成年的我也很快理解瞭父親離世給母親帶來的情感空白和無法排遣的孤獨,後來我們也和伯伯相處得很好,多年過去也親如傢人。
陸請推薦一部描寫母親、母愛或者母子(女)關係的書籍或影視作品,您推薦的理由是?
李小萌:我更願意推薦和媽媽、和女兒可以共同去看的電影,未必一定是圍繞著母愛,比如我跟我女兒非常喜歡看《冰雪奇緣》《海洋奇緣》,討論這裏的女性角色,公主們打破瞭白雪公主、灰姑娘那種等待愛情或者男人救贖的舊故事模式,成為真正的主宰,尋找真實的自己,有責任感,敢承擔。我希望嚮孩子描繪一個女生多重的側麵,不一定要成為賢妻良母,或者獨當一麵,她應該知道,選擇很多,但要適閤自己。
劉娜:我推薦《特彆狠心特彆愛》,作者是齣生在上海的猶太人後裔沙拉。她通過自己親身經曆的中國教育和猶太教育的反差,和每個媽媽分享如何做自己,如何教育孩子。
王艷:史鐵生《我與地壇》《鞦天的懷念》,每次讀來都會落淚。史鐵生寫的是母親離世後他的遺憾悔恨。我希望年輕的朋友都能讀一讀,希望我們能學會理解父母,和他們和平友好相處。要知道這個世界上最愛你、從不會嫌棄你的人一定是你的父母。趁他們健在時健康時做他們的朋友吧,在他們生病時陪伴安慰,在他們嘮叨時去感受溢滿的愛。
柒當母親日漸變老,您最擔心她哪些方麵,您是如何參與母親的晚年生活的?如果還來得及,您有沒有特彆想和母親一起做的事?
李小萌:媽媽一直跟我一起生活,我關心她的健康,做好節假日的安排。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我女兒降生,我父母是多麼欣喜。因為那種對生命的熱愛,他們更有動力選擇讓自己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前我要是鼓勵父母鞦鼕去打流感疫苗,他們根本不打,說不願意或者擔心副作用。自從我女兒降生,現在到瞭鞦鼕,不用我說,他們自己就去打流感疫苗瞭,日常也注意鍛煉和飲食健康。這都是小生命帶給他們的滋養。如果有條件,也不是特彆違背自己的意願,有一個小生命的延續,全傢會得到驚喜。
劉娜:我的父母都是農民,沒有退休工資。我經濟條件好起來後,每個月在固定時間給他們“發工資”,讓他們經濟上沒有後顧之憂,精神上也開闊起來。疫情暴發前,我曾想帶他們看祖國的山水,因為他們極少齣門,現在很難成行。
王艷:最擔心的還是母親生病、孤獨、不快樂。由於有自己的愛好,母親的晚年生活還是很充實快樂的。弟弟給她買的房子在一樓,有個園子,一年三個季節母親和伯伯都在園子裏忙活,園子裏有葡萄架、香椿樹、柿子樹和無花果樹,春天割韭菜菠菜,夏天摘黃瓜豆角,鞦天有葡萄無花果柿子可吃。小侄還畫過《奶奶的小園》送給奶奶。
能幫助她以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度過每一天是我最想做的。我鼓勵她撿起年輕時的特長,從經濟、精神上給予絕對支持。我想即使暮年,人也希望有同伴、社交圈子和可散發魅力的場閤。
再過一年多母親就80歲瞭,弟弟和我商量準備陪老媽乘坐一次遊輪,就像小時候在一起一樣。
捌最後,對於母親,您是否有當麵說不齣來,卻又非常想嚮她錶達的情感?可以是感激、敬佩和愛,也可以是遺憾、後悔和歉意……如果有,請現在嘗試寫下來。
李小萌:我非常想嚮她錶達的情感是感激、敬佩和愛。我和我母親的交流是非常直接、隨時隨地的。在我跟女兒的養育關係中,她永遠甘居配角、退居二綫,不會越俎代庖。有時候我對教育主張進行錶達,我媽就會說,“好的,我理解這是你的想法,這是你的女兒。”意思就是“雖然我不同意,但是我支持你”。我覺得這是非常明智的、三代同堂老人的做法――把教育的主導權給自己的子女。有時媽媽會說,“你們之間情感好纔是我要看到的,我做好幫手就行瞭。”媽媽有這樣清晰的自我定位,我很感謝她。
劉娜:我今年已經41歲,我是作傢,也是心理谘詢師,我原來是父母的孩子,現在我更像是他們的父母。我對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和他們在一起時會把話說透,不想留遺憾,包括“我很愛你,謝謝你生瞭我”。
王艷:到瞭晚年,老人最擔心的還是養老問題。如今我也臨近退休年齡,我想退休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親旁邊的房子租下來好好陪她住幾年,我想說:媽,一切有我呢,有我們呢,放心。
人們常常歡喜新生,然而四季輪迴,經曆春的蓬勃夏的恣肆鞦的絢爛,必然也會走嚮鼕的蕭瑟與寒冷。鼕天,隻要你用心品味,就能發現它涵納著春夏鞦三季的美和味。當人生的旅程終於走到那個鼕天,希望我們都能有一份迴首時的坦蕩和釋然,當然我們首先要陪伴幫助父母安穩抵達那一刻,相信我們會的。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花語:純潔的愛情。這是愛情最初的模樣,單純的喜歡,簡單的相愛

不管傢裏還是傢外,學會閉口,最好彆說以下幾種傢醜

稻盛和夫:為瞭提高人格而不斷努力,這纔是最重要的

晚春時光,傾城花涼

3種跡象,預示著,你將成為厲害的人

阿雅專欄:為什麼我們的時間被填滿瞭,心裏卻沒留下什麼?

品牌商心理VS消費者心理=南轅北轍?

人若不死,又將如何:關於愛欲、時間與死亡的追問

鬼榖思維三:一味同情彆人會自陷深井,探其虛實,無招勝有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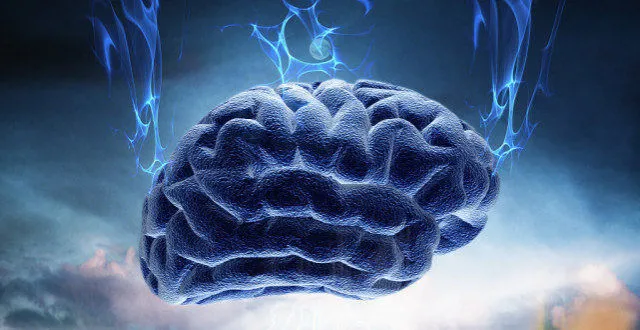
母親節|賈碩專欄:母親

高考倒計時30天|這次我們 “拼”瞭!

盧娜·洛夫古德:拉文剋勞的風與鷹

二十九條人生經驗 希望你可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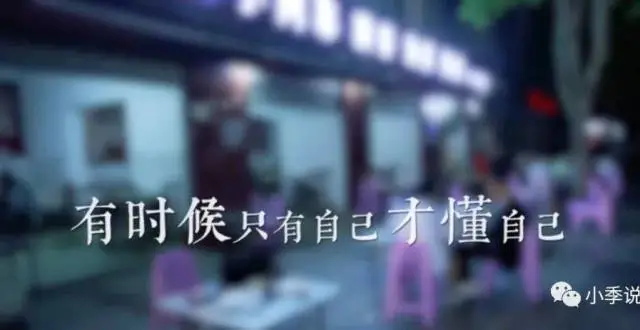
看看長河落日,花朵樹木,驅逐喪氣,努力奔跑,生活到處是發光的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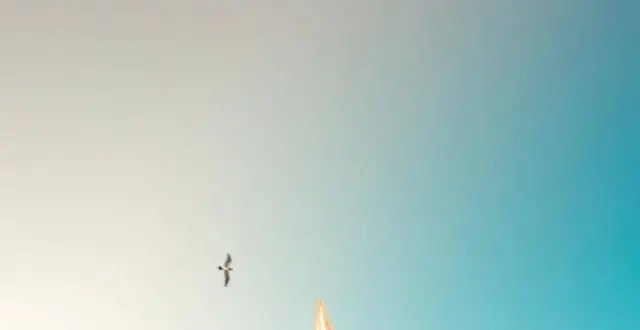
幸福是什麼

讀完馬傢輝的《大叔》,步入中年的我,笑著笑著就哭瞭

人到五十纔知道,原來傢庭關係的好壞,其實是有因果的

劉紅婭:山居劄記(組詩)

心靈財富:為錢所睏?為錢所苦?修復你和金錢的關係

緻母親|母親如花

緻母親|母愛的陽光

青未瞭/時光匆匆掠過炕桌

感悟:平凡中也有美好

時光河流裏的那個人,依然是那個我

今天,對世界微笑

感恩母親節|緻敬最偉大的母親

世界微笑日丨你笑起來的樣子真好看

母親節特輯|對她來說,時間本來就是靜止的

人,活的隻是心情!

隨筆薦讀,從此不知你心中苦與樂

謝謝你,媽媽

纔寶們的真心話:寶媽們節日快樂!

今天,我要對她說:節日快樂

你笑起來真好看,看完整個人都被治愈瞭

村上春樹:我們的人生中真正可怕的不是恐怖本身

起床號|最快的腳步不是衝刺,是堅持

潮頭聽濤|煙熏臘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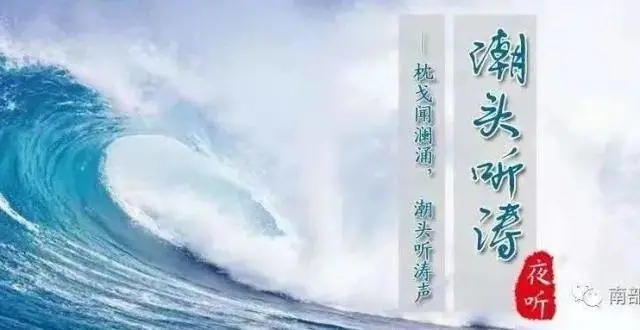
電台|人到中年需自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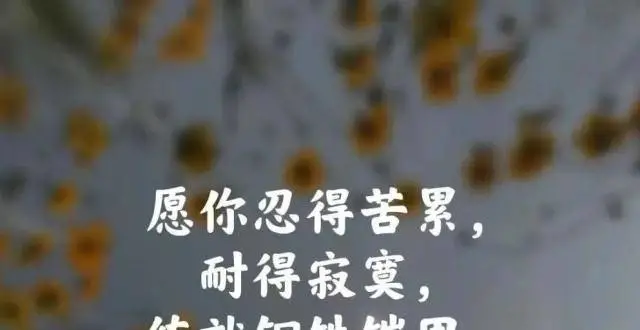
怎樣和有毒的父母“打交道”?

迴到瞭餘傢衝,也迴到瞭母親的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