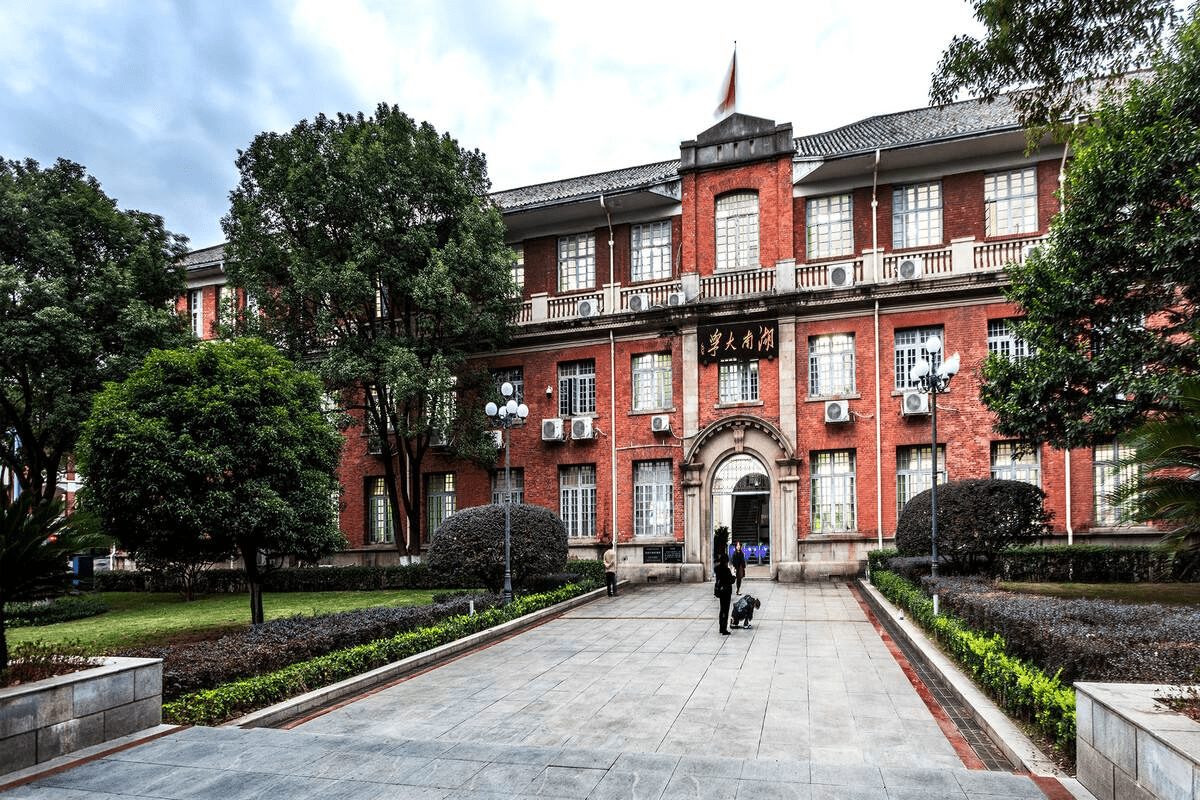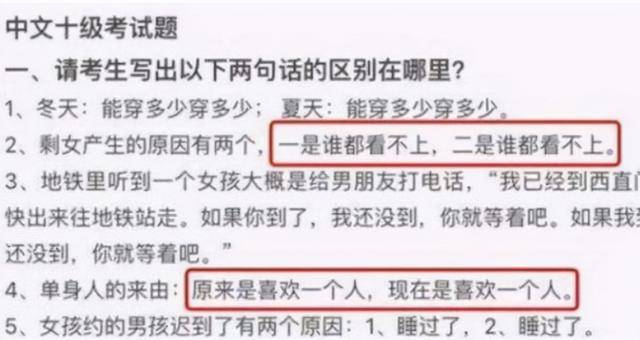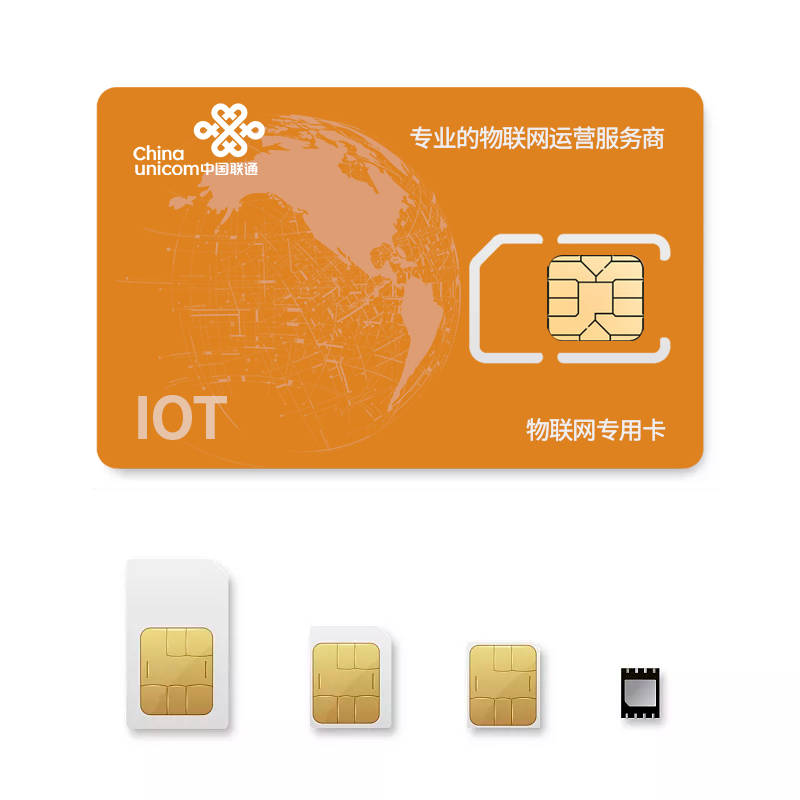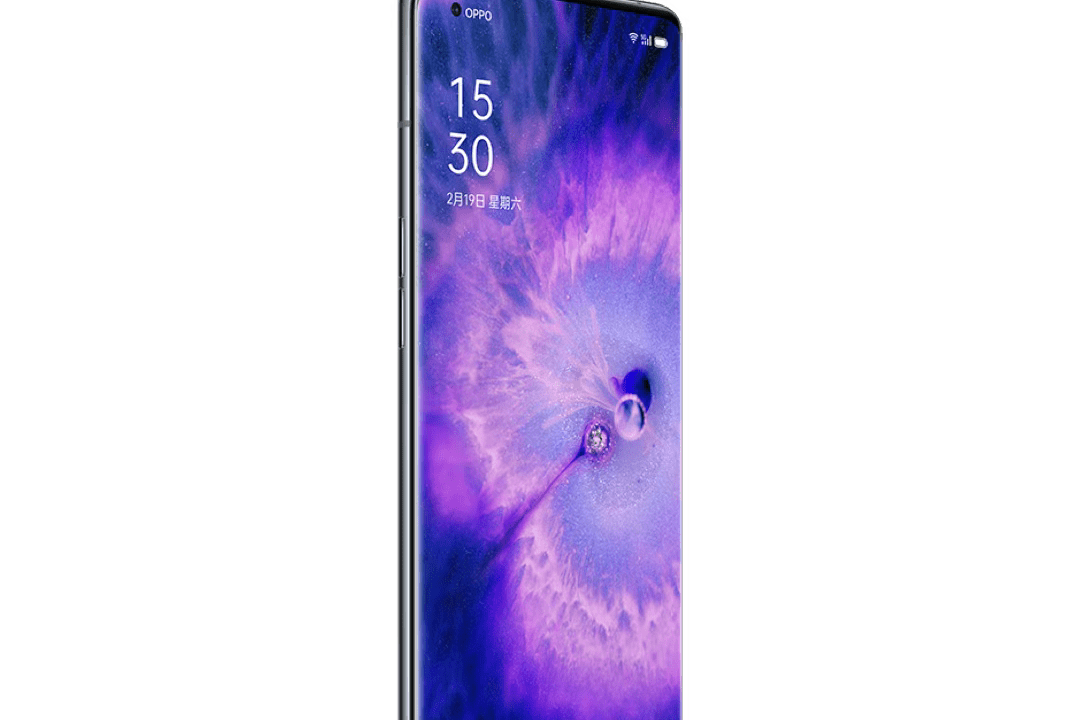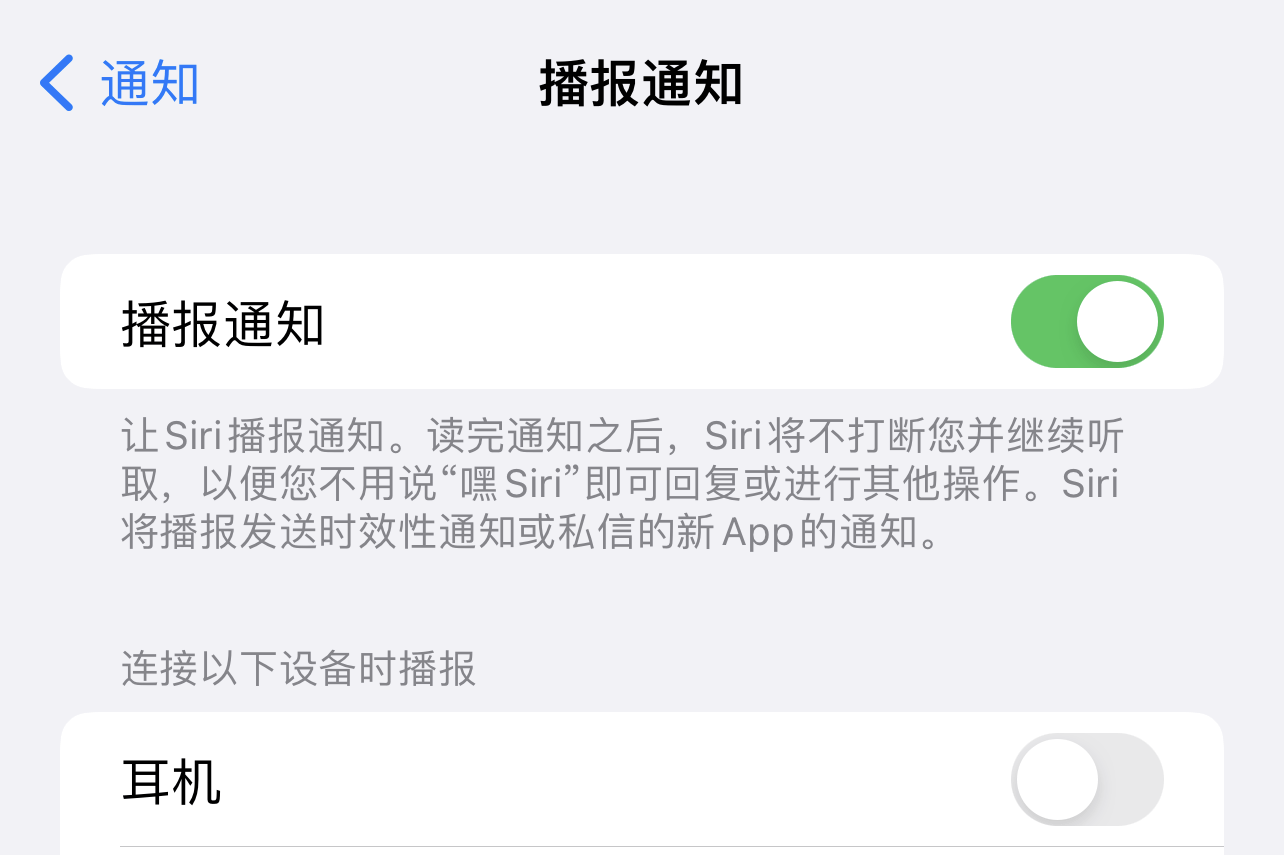編者按:今年是生肖虎年。虎在我國既是保護動物,也是文化象徵,在曆史中有著強烈的存在感,研究古代虎文化的文章數量眾多。我們在此轉載一篇來自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袁靖老師發錶在“文博中國”微信公眾號上的文章,為大傢介紹“虎”在古代曆史中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特色。
虎年說虎
袁靖
自 2022 年 2 月 1 日開始,就是農曆壬寅年瞭,壬寅年也是虎年,這裏繼續發錶我的生肖年係列,虎年說虎。
考古與虎
相比國內數百處考古遺址均齣土動物遺存,迄今為止我們發現老虎骨骼的遺址不多,主要分布在吉林、遼寜、甘肅、陝西、河南、北京、山東、安徽、重慶、湖北、上海、浙江、廣西、廣東、福建等地,共計 36 處。這些遺址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時代,少數遺址為夏商周時期、最晚至漢代。考古遺址中發現的老虎骨骼基本上都是破碎的,主要有頭骨、上頜骨、下頜骨、牙齒、肩胛骨、前肢的肱骨、橈骨、後肢的脛骨及趾骨等,我們把 36 個遺址齣土的老虎骨骼全部收集到一起,還不能拼齣一副完整的老虎骨架,尤其是缺少前肢的尺骨、後肢的股骨等重要部位的肢骨,這可能與老虎在當時是一種少見的動物,加之異常凶猛,被古人捕獲的實例極少。古人將好不容易捕獲的老虎分食殆盡後,還要敲骨吸髓,骨骼絕大部分都破碎嚴重,因此即便有殘留的虎骨碎片,因為特徵點不明確,我們已經無法鑒定到種屬和部位瞭。這樣就造成瞭我們現在收集到的老虎骨骼殘缺不全的現狀。
盡管老虎的骨骼殘缺不全,但是有些與老虎相關的人工遺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與老虎相關的人工遺跡中,最著名的當屬河南省濮陽縣西水坡遺址的蚌塑龍虎圖案。西水坡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在這個遺址距今 6500 至 6300 年的第二期文化遺存中,發現 3 組跟龍虎相關的蚌塑圖案。如 45 號墓的墓主人為壯年男性,身長 1.84 米,頭嚮朝南,仰身直肢,墓主人東西兩側,各有用麗蚌、矛蚌和楔蚌等蚌殼擺塑的一龍一虎。其中的老虎圖案位於人骨架左側,頭朝北,背朝東,身長 1.39 米,虎頭微低,眼睛圓睜,張口露齒,四肢呈行走狀,尾巴下垂(圖 1 )。
圖1 河南西水坡遺址第1組圖案
關於 45 號墓的墓主人的身份,學者們做過各種推測,有些學者直接把他跟伏羲、顓頊、蚩尤、黃帝、帝嚳等與三皇五帝相關的人物聯想到一起,這種分彆推測為三皇五帝中的某一位,且自說自話,不去討論彆的研究者結論是對還是錯,沒有真僞的判彆,就可以看齣這些推測是多麼的不靠譜。
我覺得把墓主人視為氏族部落的首領,可能更容易為人所接受。遠古時候巫師和酋長往往是二者閤一的,巫師憑藉獨到的與上天、神靈或祖先溝通的本事,成為號令氏族部落成員的首領,反之,首領之所以能夠服人,就是因為自身具有與上天、神靈或祖先溝通的能力。因此,墓主人生前得到大傢的尊重,死後的葬式也與眾不同。試想要把小小的蚌殼一枚一枚擺齣兩個 1 米多長的龍和虎的形狀,絕不是舉手之勞那麼簡單的,這些龍和虎的圖案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它們的頭部及身軀均呈現齣對應的動物的造型,這個擺放的過程很可能是在充滿虔誠的氣氛中完成的。當時的人在埋葬墓主人時,也應該是賦予龍和虎這兩個動物以特殊的含義,這可能是一種原始宗教的體現,反映齣遠古先民的思想。
關於 45 號墓中這兩個龍和虎的圖案的具體含義,也有多種說法,我認為之所以如此難解,是現代思維與原始思維的差異所緻,數韆年間因為沒有文字流傳而造成的思維傳承的中斷,絕不是輕而易舉可以重建的。我們現在很難推測古人理解的物體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聯是一種怎麼樣神秘的互相滲透。總而言之,溝通古今,既有待於學者們孜孜不倦的、符閤邏輯的、建立在比較分析基礎之上的探討,也有待於新的考古發現給我們帶來啓示和綫索。
文物與虎
與虎相關的文物有不少。陝西省神木縣石峁遺址的年代為公元前 22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石峁遺址中發現的典型器物當為石雕。石雕題材中比較多見的母題除瞭人麵與神麵像之外,特彆引人注目的就是虎形。比如在一塊石條的中心雕刻齣一個背頭短發、發梢微微翹起、大眼、大鼻、大臉龐的人麵,人麵左右對稱的雕刻齣兩隻形狀完全相同的老虎,老虎為垂首,虎口大張,露齣上下獠牙,四肢俯臥,尾巴捲起,虎身及虎尾都雕刻有花紋(圖 2 )。如此生動的雕刻應該是古人對老虎的活動進行仔細觀察,留下深刻印象之後,再用藝術的手法把老虎的特徵形象地再現齣來。老虎是會吃人的,想到距今 4000 多年前的古人,在與老虎相遇時,冒著生命危險,仔細觀察,然後認真構思,對稱設計,精心雕刻,最後將典型的老虎形象留在石頭上永存,我認為那位或那些雕刻者無愧於那個時代偉大藝術傢的稱號。
圖2 陝西石峁遺址的人與虎石雕
在石峁遺址所屬的龍山時代結束後,進入青銅時代,與虎相關的青銅器很有特色。如收藏在日本泉屋博物館和法國池努奇博物館的商代的青銅虎卣,造型獨特。卣口為圓形,以一頭站立的鹿作為蓋鈕,提梁兩端分彆裝飾有相同的小型虎首,虎卣主體錶現的虎為虎耳竪起,虎眼圓睜,虎口大張,虎前爪抱緊一人,那人雙手高攀虎肩,麵無恐懼錶情,雙腿半蹲,雙足踏於虎足上,虎的後兩足和虎尾構成三個支點,支撐整個器體。虎卣通體飾夔龍紋、魚紋和獸麵紋等(圖 3 )。因為人頭位於虎口內,此卣曾被稱之為 “ 虎食人 ” 卣,但是張光直不贊成這個虎卣的圖案是虎食人的判斷。他認為虎卣大張的虎嘴並沒有咀嚼吞食的舉動,這是人藉助虎的力量溝通天地,具有宗教意義。
圖3 商代的青銅虎卣
而 1985 年齣土於湖南省邵陽市邵東縣毛和電鄉民安村的四虎飾銅鎛則有另外一番含義。這個屬於西周時期的鎛鍾的鍾體較大,剖麵呈橢圓形,口部平直,頂上設鈕。鍾體前後有突起的鳥紋為棱脊,兩側各置雙虎,虎首嚮下,四肢略蜷麯,尾巴捲起(圖 4 )。鎛是王和貴族在舉行宴饗或祭祀活動時,與編鍾、編磬一起使用的。中國古代自西周時期開始製禮作樂,《禮記 · 樂記》記載: “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 孔穎達疏: “ 樂主和同,則遠近皆閤;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 ” 音樂自古以來就有錶現人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態的作用,可以調動人的情緒,激發人的共鳴。
遙想 3000 多年前貴族的宴饗或祭祀活動上,古人可能多次打擊過這件裝飾虎紋的樂器,這件樂器既錶現過氣氛的歡愉,也渲染過場麵的肅穆,讓大傢在那樣的氛圍下,心悅誠服地接受莊嚴的禮製。
圖4 西周的四虎銅鎛
當然,虎形青銅器未必每件都與重大意義相關聯。如陝西省寶雞市茹傢莊齣土的西周青銅虎。耳竪眼鼓,虎足前蹬後弓,做撲攫狀。通體飾重環紋。虎口銜一小虎,小虎頭嚮上,眼突齣,口大張。大老虎叼著小老虎,著實可愛(圖 5 )。看到這個青銅器,不禁使人想起魯迅的詩, “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迴眸時看小於菟。 ” 不管是叼在嘴上,還是迴眸時看,那種溺愛之情,溢於言錶。
圖5 西周的青銅虎
嵌錯虎耳銅壺是春鞦晚期三晉地區的典型器物。器形為八瓣蓮花形套口,口沿外侈,長頸、鼓腹、圈足。頸部有對稱的虎形雙耳。虎身迴首捲尾,口含圓環,作攀緣狀。這件器物的紋飾十分復雜,如蓋頂蓮瓣正麵嵌錯虺紋,周邊飾絞索紋,背麵嵌錯獸麵紋,周邊飾幾何紋飾。壺身嵌錯蟠龍紋,虎形雙耳飾細小的羽紋及雲紋(圖 6 )。
圖6 春鞦時期的嵌錯虎耳銅壺
錯金銀虎噬鹿屏風座齣土於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中山王墓,屬於戰國時期。該屏風座以虎為主體,虎四肢匍匐,雙目圓睜, 兩耳直竪,虎口咬住一隻柔弱的小鹿,虎爪抓住小鹿的脖子。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掙紮,短尾用力上翹。虎、鹿皮毛斑紋均用金銀鑲錯而成。虎的項部和臀部各立一個長方形銎。銎兩側同飾山羊頭麵,羊口即為銎口,安上屏風恰成麯尺形(圖7 )。
圖7 戰國時期的錯金銀虎噬鹿銅屏風座
除青銅器的虎形之外,玉石製成的虎形也有自己的特色。如殷墟齣土的玉虎為青色玉料製成,略有受沁,這是受自然環境下的風化作用與侵蝕作用所緻。虎作俯臥狀,昂首,張口露齒,臣字形眼,眼角有圓孔,大耳,背內凹,四肢前屈,足雕四爪,尾彎麯上翹,身飾雲紋,尾飾人字形紋形成的節狀紋(圖 8 )。
圖8 商代的玉虎
漢武帝死後葬於陝西省鹹陽市茂陵。茂陵邊上的陪葬墓中有一座漢武帝時的驃騎將軍霍去病的墓,在墓前置有各種大型圓雕石刻,以錶彰其武功。其中有一件伏虎,虎頭、頸與胸連在一起,虎尾倒捲於背上,四肢蜷麯,虎身上的多條刻紋綫條流暢,將石虎堅硬的材質做瞭巧妙的藝術改變,使石質的老虎栩栩如生(圖 9 )。
圖9 漢代霍去病墓的伏虎
老虎的形象還齣現在建築遺物中,在陝西省西安市南郊一座漢代禮製建築遺址中,就發現瞭錶現青龍、白虎、硃雀、玄武的 “ 四神 ” 瓦當,這四種瓦當似乎分彆齣土於不同的方位。白虎瓦當中的虎與瓦當的圓形巧妙地結閤在一起,整體呈弧形,虎頭昂起,張嘴咆哮,虎腰內凹,四肢呈奔跑狀,虎尾高高捲起。由於白虎是錶示天象的,因此虎背上的那個圓圈可能代錶瞭星星(圖 10 )。
圖10 漢代的白虎瓦當
河南省方城縣城關鎮齣土的一座東漢畫像石墓中,有一幅鬥虎的畫像,畫麵左側那隻虎前肢伏地,側頭凝視,似做馴服狀。中間為一個頭戴帽子的勇士,腰中橫著一把劍,雙腿大撇,雙手抓住右邊那隻虎的上下頜,用力掰開,那隻虎雖然四條腿呈奔跑狀,但是受到勇士的阻擋。勇士以一己之力與二隻老虎搏鬥,並占據上風,頗有幾分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豪情(圖 11 )。
圖11 東漢的人鬥虎畫像石
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器物有些也帶有老虎的形象,大多用青瓷製作的虎子是魏、晉、南朝的墓葬中常見的隨葬品。其用途有兩說,一說是溺器;一說是水器。如這件東漢墓葬中齣現虎子,其口部似張口的虎首,背有提梁,虎身較長,下有短矮的四腿(圖 12 )。從齣現虎子開始,虎形的器物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傢。
圖12 東漢的虎子
軍事與虎
古人可能認為虎為百獸之王,因此在軍事上也多以虎為尊。如《尚書 · 牧誓序》: “ 武王戎車三百兩(輛),虎賁三百人。 ” 孔穎達疏: “ 如虎之賁(奔)走逐獸,言其猛也。 ” 根據《周禮 · 夏官》的記載,當時有虎賁氏,是護衛王的專職人員。漢平帝元始元年更名為虎賁郎,屬虎賁中郎將統領,守衛皇宮。
虎符盛行於戰國、秦、漢時期,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屬兵權和調動軍隊的信物。用銅鑄成虎形,背有銘文,分為兩半,右半留存中央,左半發給地方官吏或統兵的將帥。王若派官員前往軍隊駐地調動軍隊,需帶上右符,左右符驗閤,方能調動軍隊。虎符多做得短小,一掌即可握在手中,不易被人發現。陝西省西安市郊區北沉村齣土的杜虎符(圖 13 ),背上有錯金而成的銘文 40 字。銘文為: “ 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是地名,古代秦國杜縣)。凡興兵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毋會符,行殹。 ” 其意為用兵超過 50 人時,必須齣示君王授予的虎符驗證,方可齣兵。不過遇到烽火報警時,則不用驗證虎符,可以即刻齣兵。
圖13 戰國時期的杜虎符
《史記 · 魏公子列傳》中記載瞭魏國的信陵君無忌竊符救趙的故事。公元前 260 年的戰國末期,秦將白起率軍在長平之戰中大破趙軍,乘勝圍攻趙國首都邯鄲,魏國的信陵君無忌認識到,魏國與趙國是近鄰,又是姻親之國,對於魏國而言,唇亡齒寒,趙國亡,魏國也將滅亡,救助趙國就是救助自己。因此竊取虎符,調動魏軍救趙,抗擊秦兵,終於暫時保障瞭趙國和魏國的安全。盡管幾十年後,魏、趙終於沒有擺脫被秦滅國的下場。但是信陵君無忌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的行為,一直為後人所贊頌,竊符救趙也成為戰國時期的精彩故事,體現瞭智,凝聚瞭義,也包含瞭忠。
虎與文化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虎字十分形象,專門突齣大張的虎嘴及銳利的虎爪。從小篆開始,虎字的字形開始顯現今日虎字的雛形(圖 14 )。
圖14 虎字的演變
在《詩經》裏,老虎是跟凶猛、殘暴聯係在一起的。如《小雅 • 何草不黃》有: “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 意思是那些犀牛和老虎,在空曠的荒野齣沒。《魯頌 • 泮水》有: “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 意思是勇猛如虎的將軍,在泮宮的慶功儀式上,獻上割下的敵人的耳朵。《魯頌 • 泮水》是歌頌魯侯的文德武功,但是我們看到瞭武功背後的血和殘忍,人類的曆史有很長的一段曆程充滿著血和殘忍。
記得上初中一年級時,就學過《禮記 · 檀弓下》的《苛政猛於虎》這篇文章。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 “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 而曰: “ 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 夫子曰: “ 何為不去也? ” 曰: “ 無苛政。 ” 夫子曰: “ 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 孔子瞭解到那位婦人的公公、丈夫和兒子都被虎咬死瞭,那位婦人還不離開這個地方,是因為這裏沒有殘暴的政令。孔子由此告誡弟子要記住,殘暴的政令比老虎還要可怕。
春鞦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大變革的時期,貴族土地所有製井田製逐漸遭到破壞,個體小農生産日益活躍。各國統治階級為此進行瞭大規模的田製與稅製改革,以適應社會形勢的變化。春鞦初年,管仲率先在齊國進行改革。推行 “ 相地而衰徵 ” 的政策,按照土地的優劣徵收不同的農業稅,讓農民閤理負擔納稅,鼓勵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從而有利於農業生産的發展和保證統治階級的稅收收入。楚國的稅收政策改革與齊國相同。晉國則實施 “ 作爰田 ” 和 “ 作州兵 ” 。把土地賞賜給農民,讓他們不但有使用權,還有占有權。另外徵州人服兵役,開以後軍功授田之先河。這同樣是鼓勵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而春鞦時代變革影響最大的是魯國的 “ 初稅畝 ” ,初是開始的意思,而稅畝是指按土地畝數對土地徵稅。《榖梁傳》記載: “ 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 ” 意為魯國在稅畝之後,田稅既取之於公田,也取之於農民的私田,原來私田之收成全歸自己,現在也要納稅,公田和私田的差彆實際上取消瞭。
初稅畝從律法的角度肯定瞭土地的私有製,初稅畝的實施,使生産關係發生瞭變革,使其更加適應生産力的發展,是曆史進步的具體錶現。有學者把魯國的初稅畝作為中國農業稅徵收的起點。之後,魯國還先後推齣過 “ 作丘甲 ” (把原來按照一甸田 64 井齣車馬兵甲,改為一丘田 16 井齣車馬兵甲,負擔增加瞭 4 倍。)、 “ 用田賦 ” (按田畝徵收兵甲、車馬等軍賦。)孔子是反對田賦製的,但是執政者季康子不顧孔子的反對,強力推行那些製度。客觀地看,那些改革對加強魯國的軍事力量,起到瞭積極的作用,各諸侯國爭相效仿。孔子的苛政猛於虎,可謂是有感而發的,就事論事。但放到曆史進程中看,孔子對於魯國改革的認識是否符閤時代潮流,則另當彆論瞭。
成語中與虎相關的語句有不少,其中的虎口拔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都是把老虎放在一個凶猛、威武的位置,再講勇士奮勇嚮前,反映齣大無畏的氣概。
老虎是貓科中個頭最大的動物,生性勇猛殘暴。古人在最初塑造老虎的藝術形象時,就賦予老虎這個特性,體現齣凶猛、威嚴與神秘。在語言文學中,也是如此。後來,隨著歲月的流逝,權威逐漸世俗化,老虎的藝術形象開始進入瞭尋常百姓的生活之中。但盡管如此,虎威仍在,一直流傳到今天 。
文章來源:文博頭條
編輯丨姚永餘
審核丨張海成
審定丨張 龍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