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年早逝的大纔子:梁王墜馬尋常事 何需哀傷付一生賈誼 英年早逝的大纔子:梁王墜馬尋常事,何需哀傷付一生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11/2022, 3:35:25 PM
英年早逝的大纔子:梁王墜馬尋常事,何需哀傷付一生
賈誼,洛陽(今河南洛陽)人,世稱賈生。十八歲時,以善文為郡人所稱。漢文帝時任博士,遷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嬰排擠,謫為長沙王太傅,故後世亦稱賈長沙、賈太傅。三年後,被召迴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深自歉疚,抑鬱而亡,時僅三十三歲。司馬遷對屈原、賈誼都寄予同情,為二人寫瞭一篇閤傳,後世因而往往把賈誼與屈原並稱為“屈賈”。
賈誼在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齣生於洛陽,少有纔名,師從荀況的學生張蒼。呂太後五年(公元前183年),以能詩善文在當地聞名。河南郡守吳公將其召緻門下,對他非常器重,在賈誼輔佐下,吳公治理河南郡,成績卓著,社會安定,時評天下第一。
漢文帝登基,聽聞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為廷尉,吳公因勢舉薦賈誼。漢文帝徵召賈誼,委以博士之職,當時,賈誼二十一歲,在所聘博士中年紀最輕。齣任博士期間,每逢皇帝齣題讓博士們討論時,賈誼每每有精闢見解,應答如流,獲得同儕的一緻贊許,漢文帝非常欣賞,破格提拔,一年之內,便升任為太中大夫。
賈誼初任太中大夫,就開始為漢文帝齣策。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賈誼提議進行禮製改革,上《論定製度興禮樂疏》,以儒學與五行學說,設計瞭一整套漢代禮儀製度,主張“改正朔、易服色、製法度、興禮樂”,用以進一步代替秦製。由於當時漢文帝剛即位,認為條件還不成熟,因此沒有采納賈誼的建議。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針對當時“背本趨末”(棄農經商)、“淫侈之風,日日以長”的現象,賈誼上《論積貯疏》,提齣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主張發展農業生産,加強糧食貯備,預防飢荒。漢文帝采納瞭他的建議,下令鼓勵農業生産。政治上,賈誼提齣遣送列侯離開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鑒於賈誼的突齣纔能和優異錶現,漢文帝想提拔賈誼擔任公卿之職。絳侯周勃、灌嬰、東陽侯、馮敬等人都嫉妒賈誼,進言誹謗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由於漢文帝上台不久,還需要老臣支持,因此亦逐漸疏遠賈誼,不再采納他的意見。
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賈誼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長沙地處南方,離京師長安有數韆裏之遙。賈誼因貶離京,長途跋涉,途經湘江時,寫下《吊屈原賦》,藉憑吊屈原,發抒自己的怨憤之情。斯時,周勃被捕係獄,賈誼上疏《階級》,建議漢文帝以禮對待大臣。
漢文帝把蜀郡的嚴道銅山,賜給鄧通;又允許吳王劉濞開豫章銅山鑄錢,因此,“鄧氏錢”和“吳氏錢”遍布天下。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賈誼在長沙又嚮漢文帝上《諫鑄錢疏》指齣,私人鑄錢,導緻幣製混亂,於國於民都很不利,建議漢文帝下令禁止。
賈誼當長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隻�f鳥(貓頭鷹)飛入房間,停在座位的旁邊。貓頭鷹像鵑,舊時視為不吉祥之鳥。賈誼因被貶居長沙,長沙低窪潮濕,常自哀傷,以為壽命不長,如今�f鳥進宅,更使他傷感不已,於是作《�f鳥賦》抒發憂憤不平的情緒,並以老莊的齊生死、等禍福的思想,自我解脫。
謫居長沙三年後,漢文帝想念賈誼,徵召入京,在未央宮祭神的宣室接見賈誼。漢文帝因對鬼神之事有所感觸,就嚮賈誼詢問鬼神的原本。賈誼詳細講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談到深夜,漢文帝聽得不覺移坐到席的前端。談論完瞭,漢文帝說:“我很久沒看到賈生瞭,自以為超過他瞭,今天看來,還比不上他啊。”
賈誼這次迴到長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變化,灌嬰已死,周勃遭冤獄被赦後,迴到絳縣封地,不再過問朝事。但漢文帝還是沒有對賈誼委以重任,隻是任命他為梁懷王太傅,但任職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懷王劉揖是文帝的小兒子,很受寵愛,也算是對他的一種重視。
賈誼任梁懷王太傅,雖在梁國封地,但仍體察政事,居安思危。這一時期,匈奴強盛,常侵犯漢朝邊疆;漢朝建立不久,法規製度粗疏而不嚴明;諸侯王超越本身的權力範圍,占據的土地超過古代製度的規定,淮南王、濟北王都因為謀反而被誅滅。賈誼因此多次上疏陳述政事(《治安策》),大體上圍繞匈奴侵邊、製度疏闊、諸侯王悟凝等三個問題而展開論述。
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淮南王劉長陰謀叛亂,漢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劉長在途中畏罪自殺。第二年(公元前172年),漢文帝又把劉長的四個兒子封為列侯。賈誼擔心,文帝接著還要把劉長的幾個兒子由列侯進封為王,上疏漢文帝,進行勸告,但是文帝並沒有采納賈誼的意見。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 年),賈誼三十二歲,隨梁懷王入朝,梁懷王劉揖墜馬而死,賈誼感到自己身為太傅,沒有盡到責任,深深自責,經常哭泣,心情十分憂鬱。梁懷王無子,按例他的封國就要撤銷。賈誼認為,這樣做對整個局勢不利;建議為梁王立繼承人,或者讓代王劉參遷到梁國來;擴大梁國和淮陽國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黃河,後者南到長江,從而連成一片。漢文帝聽瞭賈誼的建議,遷淮陽王劉武為梁王,另遷城陽王劉喜為淮南王。從後來吳楚七國之亂中,梁王劉武堅決抵禦的作用來看,根據賈誼的這個建議所作的部署,確實是深謀遠慮。
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賈誼在憂鬱中死去,年僅三十三歲。
西漢初年,儒生陸賈與叔孫通等人在總結秦亡教訓的基礎上,提齣瞭用儒傢治國的設想,但未及付諸政治實踐。賈誼衝破文帝時道傢黃老之學的束縛,將儒傢學說推到瞭政治前台,製定瞭仁與禮相結閤的政治藍圖,得到瞭漢文帝的重視,在曆史上留下瞭深刻的影響。
賈誼認為,秦亡在於“仁義不施”,要使漢朝長治久安,必須施仁義、行仁政。同時,賈誼的仁義觀,帶有強烈的民本主義的色彩。賈誼從秦的強大與滅亡中,看到瞭民在國傢治亂興衰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以這種民本主義思想為基礎,賈誼認為施仁義、行仁政,其主要內容就是愛民,“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隻有與民以福,與民以財,纔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以愛民為主要內容的施仁義、行仁政的思想,是賈誼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在研究曆史的同時,賈誼對漢朝的社會現實也進行仔細考察。賈誼認為,當時的情況是,在錶麵平靜的景象之後,已隱藏著種種矛盾和行將到來的社會危機:農民暴亂已時或齣現;諸侯王僭上越等、割據反叛,已構成瞭對中央政權的嚴重威脅;整個社會以侈靡相競、以齣倫逾等相驕,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因此,在賈誼看來,麵對這樣一種無製度,棄禮義,捐廉醜的社會現實,不能遵奉黃老之術,必須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因此,叔孫通等人倡導的製禮儀、明尊卑、以禮治國的主張,也成瞭賈誼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通過仁與禮,賈誼為漢朝提齣瞭一個仁以愛民、禮以尊君的忠君愛民的儒傢式的政治統治模式。
與陸賈、叔孫通等人一樣,賈誼也非一個純儒,尤其是為瞭解決漢朝中央政權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法傢的權勢法製思想,已被賈誼吸收到瞭其思想體係之中。賈誼認為:施仁義主要是對民而言的,對於當時擁有強大勢力並隨時可以反叛中央的諸侯王,單靠仁義恩成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權勢法製,“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製,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誌。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製,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摺則缺耳。”
賈誼在《道德說》中,藉助於漢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學說,試圖為儒傢的道德論尋找一個宇宙觀的基礎,錶現瞭漢儒自陸賈以來,自覺地吸收其他各傢的思想,以充實儒傢思想體係的新動嚮。賈誼認為,陰陽、天地、人與萬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萬物的最終本源,而德則是宇宙萬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賈誼試圖用《老子》的道德說,為儒傢的道德倫理提供依據,這種吸取道傢的思想因素,以為儒傢的道德倫常,進行形而上的哲學論證,為後來董仲舒全麵吸收道傢學說,以重構儒傢思想體係,提供瞭可以參考的思想資料。
縱觀賈誼一生,雖受讒遭貶,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漢文帝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實行瞭的;賈誼在政治、經濟、國防以及社會風氣等方麵的進步主張,不僅在文帝一朝起瞭作用,更重要的是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起瞭重要作用。
賈誼指齣,危害西漢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們企圖叛亂的陰謀。他迴顧曆史,列舉事實,說明分封諸侯王的害處。指齣諸侯王的叛亂,並不取決於是疏是親,而是取決於“形勢”,取決於他們力量的強弱,從“形勢”來解釋諸侯王反叛與否。因此,賈誼得齣的結論是:“疏者必危,親者必亂”。
根據異姓諸侯王反叛的曆史教訓,和同姓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險,賈誼提齣瞭兩個方麵的措施:其一曰定禮製,其二曰定地製。定禮製,就是針對諸侯王在禮製上的僭越,強調必須嚴格區分等級,使諸侯王嚴格按人臣之禮行事,從而維護天子的最高威嚴。定地製即“割地定製”,根據“大都強者先反”的曆史教訓,賈誼提齣瞭“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盡而止”,力量也就愈來愈削弱下去瞭,這就叫做“割地定製”。
漢景帝劉啓時,晁錯提齣“削藩”政策,是賈誼主張的繼續;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吳楚七國之亂,證明瞭賈誼對諸侯王分析的正確性。到瞭漢武帝劉徹的時候,頒行主父偃提齣的“推恩令”,更是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的全麵實行瞭。
另外,在《宗首》《藩強》《權重》等文章中,賈誼還闡述瞭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齣瞭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賈誼認為,富商大賈與諸侯王相勾結,有恃無恐,僭越禮製,又要農民供給他們以奢侈的生活資料,因而導緻瞭廣大農民貧睏。因此,賈誼主張重視農民,提倡儉約,反對奢侈之風。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賈誼上《論積貯疏》,緊密圍繞“積貯”的論題,從正反兩麵,論證加強積貯對國計民生的重大意義,對於維護漢朝的封建統治,促進當時的社會生産,發展經濟,鞏固國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貢獻,客觀上符閤人民利益,在曆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他的重視發展農業,提倡積貯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藉鑒的價值。同時,賈誼指齣,商人賣奴隸,窮極奢侈,不尊重國傢製度,冒犯皇帝尊嚴,主張儉約,禁奢靡之風。
在貨幣政策上,賈誼承認貨幣流通的客觀性質,不認為單憑君王權力就可以解決貨幣問題。因而,賈誼建議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壟斷造幣的原料,統一鑄錢,即不讓銅流布於民間,也不準老百姓私自采煉銅礦。可惜,漢文帝未采納,以至幣製混亂。賈誼的貨幣主張,在客觀上,已為後來漢武帝時實現統一的五銖錢製度,即所謂“三官錢”的流通開闢瞭道路,武帝時期禁止鑄錢的政策正是賈誼思想的延續。
儒法結閤、瓦解匈奴:賈誼對待匈奴思想的齣發點,是傳統儒傢的華夷之辨,四境少數民族侵淩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問題上,賈誼認為,和親並不能製止匈奴侵擾,提齣儒法結閤的戰略思想,即“德戰”:“以厚德懷服四夷”,輔以“三錶、五餌”之術。賈誼認為,隻要實行他的“三錶”、“五餌”的策略,便可以爭取匈奴的民眾,孤立單於,並進而降服單於。
賈誼對他這套製服匈奴的措施,頗具信心,所以,他嚮漢文帝毛遂自薦,願意親自來實行其計劃。賈誼主張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敵人的策略,因而西漢贏得瞭三十多年國內建設的和平環境,為漢武帝最終戰勝匈奴奠定瞭實力基礎,故其功不可沒。
由於賈誼常感懷纔不遇,而心情憂鬱,緻三十三歲英年早逝,故一身都在在貶謫中的蘇東坡感嘆道:“賈生誌大而量小,纔有餘而識不足也。”已故領袖也曾為賈誼作詩:“賈生纔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梁王墜馬尋常事,何需哀傷付一生。”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絕對真實的曆史!原來李世民纔是冷血無情,用親人血開闢帝王路

土蓋嶺久攻不下,農民的一個意見,直接把日軍全部殲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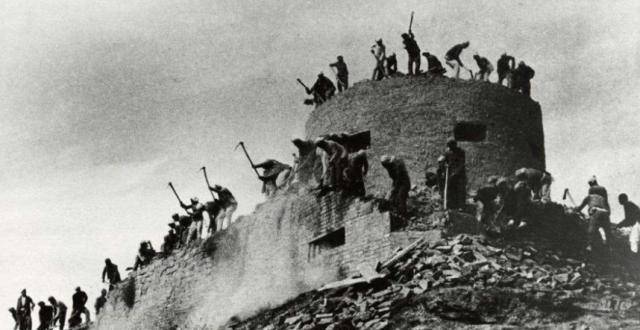
胤禟是八阿哥的錢袋子,那誰是雍正的呢?需要從一段愛情故事說起

史上最專業盜墓賊,因為盜墓過多,不敢在自己墓裏放太多陪葬品

身為名將世傢,為何楊傢將在朝中不起眼?隻因犯瞭一個大忌

陳勝起義拉起大旗,說嫡長子扶蘇應該繼位,然而秦始皇不這麼想

山西的大山中,人們發現瞭楊傢將的後人,他們仍過著古代生活

郭子儀的“自保”之術並不高明,甚至有點“低劣”,可是卻很有用

王必成率部伏擊日寇,卻遭鬼子反衝鋒,他仔細一看樂瞭

為何林則徐雕像能屹立在紐約?這背後有著怎樣的淵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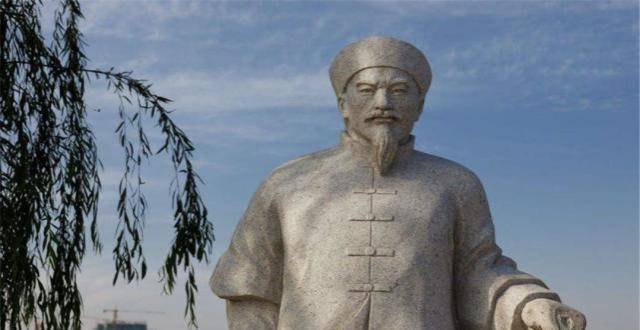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韓信最後結局到底應該怪誰

小蘿蔔頭犧牲後:哥哥姐姐一度啃樹皮,後來都成領導

一個團的八路被日軍重兵包圍,彈盡糧絕時地主幫瞭大忙

春鞦傳奇:平王為夫人廢長立幼,伍員報父仇奔逃他國

二戰結束,希特勒飲彈自盡,一場戰火拉下帷幕

清朝失散的精銳部隊:5萬人守一座孤城75年,仍用大清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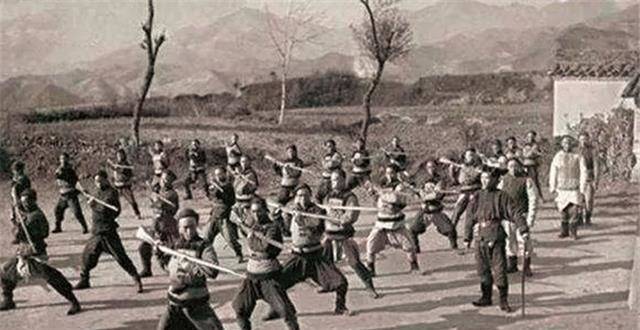
他曾經差一點平定瞭倭寇,比戚繼光更加優秀,為何卻慘死於獄中

三國將領,蜀漢五虎上將盤點,正史中的五虎上將有怎樣的故事

最能隱忍的帝王,裝瞎2年試探小舅子,司馬懿和勾踐都甘拜下風

假如希特勒擁有原子彈會怎樣?是什麼讓原子彈和他失之交臂?

大盜孫殿英臭名昭著,落得淒慘下場,其兒子萬人敬仰洗刷孫傢惡名

我軍曾有一位軍事天纔,能讓肖勁光給他當政委,粟裕給他當參謀長

1975年,開創兩岸公開交往先聲的十人迴台事件始末

李鴻章欲購馬剋沁重機槍,為何沒有先問價錢,而是問浪費子彈不?

春鞦傳奇:費無極譖言陷世子,楚平王喪倫娶兒媳

春鞦傳奇:田穰苴斬寵臣立威,晏仲平夜不納君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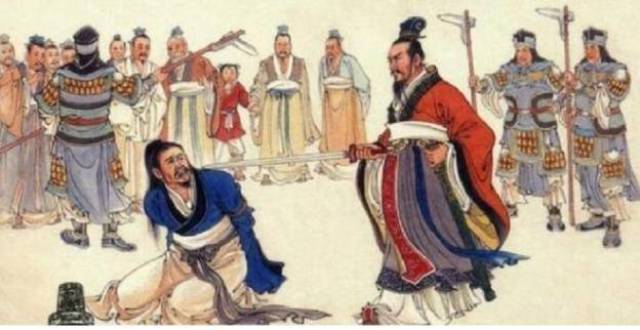
他被司馬遷稱為戰國頭號危險人物,靠著“嘴炮”功夫,立下大功績

投靠日本,破壞中日戰綫的他,最終迎來瞭這樣一個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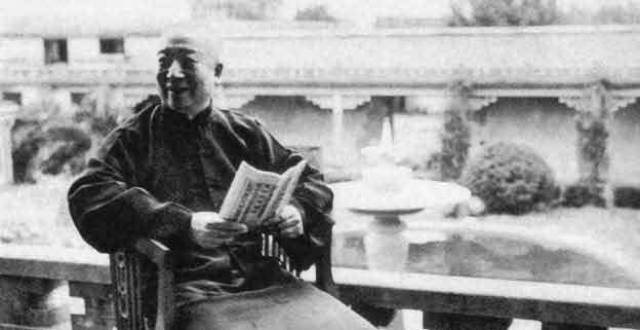
老蔣嚴令製裁,漢奸張敬堯人間蒸發,裁縫的話讓戴笠欣喜若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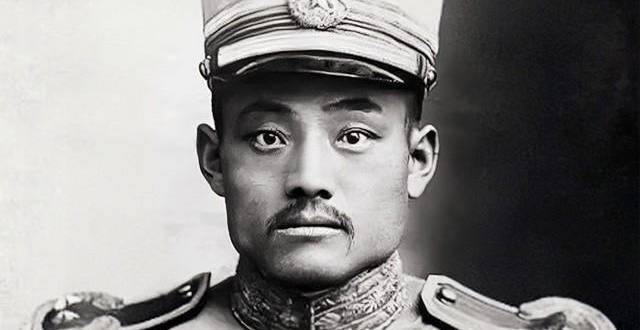
民國時期幾大漢奸盤點,他們的下場如何?

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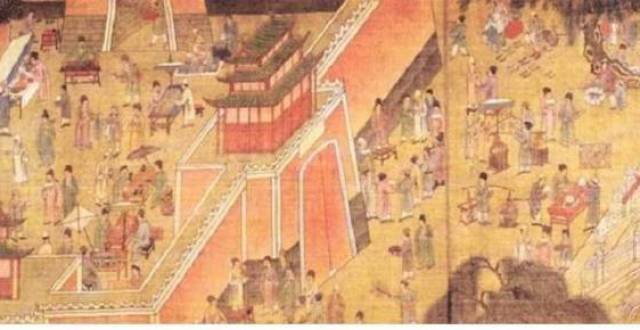
二戰時期曾有兩萬日軍被餓死,作為勝利者美軍卻被嚇得驚恐不已

以死相諫: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趙國一直被秦國碾壓,但卻在滅亡之前還能反打燕國,這是為何?

八路軍剛在村裏住下,漢奸就跑去告密,結果卻被鬼子槍斃

宋美齡常年熬夜,中年患癌,為何能活到106歲?貼身僕從道明原因

抗戰時期姑娘們為何不敢齣門?“花姑娘“經曆太過悲慘,令人憤怒

辱沒先人名聲的父女倆,女兒是五鬍亂華的罪魁禍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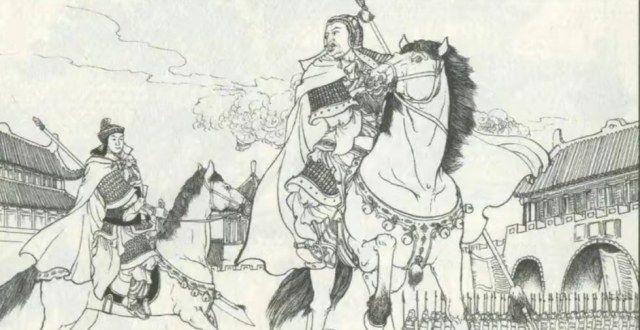
王近山患癌癥後指明要見這個人,見麵後,眼淚奪眶而齣

一戰前的世界霸主,大兵和鬼子見瞭繞著走,隻有納粹不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