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2021年1月25日在希臘雅典拍攝的法國國防部長帕利(右)。(新華社 馬裏奧斯・羅洛斯/圖)當人們提起“國防部長”這一職務 往往充滿瞭男性荷爾濛的味道。不過 歐洲國防部為何由越來越多女防長“掌舵”?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9/2022, 7:12:32 PM
這是2021年1月25日在希臘雅典拍攝的法國國防部長帕利(右)。(新華社 馬裏奧斯・羅洛斯/圖)
當人們提起“國防部長”這一職務,往往充滿瞭男性荷爾濛的味道。
不過,由女性擔任國防部長已不是新鮮事。英國、法國、瑞典等歐洲國傢,都曾由女性擔任過這一職務。
特彆在2008年,時任西班牙國防部長卡梅・查孔,就挺著大肚子進行閱兵,引發熱議,風頭一時無兩。
如今,在北約30個成員國中,就有四位現任女性國防部長,且比例正不斷擴大。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錶示,尤其是在國防部長這個職位上,無論北約還是歐洲,都想要刻意去強調性彆的無差異化。
“把握現代政治事務的能力,對外交協調溝通有豐富經驗。”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韓華認為,這對於一名稱職的國防部長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資質。
而就這些方麵,歐洲的女防長們顯然都有各自特點。
以歐洲現任的四位女防長為例,法國防長曾擔任希拉剋總統的預算國務秘書,西班牙防長則是一名法官,而奧地利防長畢業於維也納大學法學院,獲得過法學學位。
為何是“她”們?
2021年12月8日,在德國柏林非常寒冷的周三晚上,新任內閣走馬上任。國防部長由社民黨的剋裏斯蒂娜・蘭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擔任。
不過,她的就職儀式被德國媒體以“冷清”形容,不僅沒有恭賀的花束,就連前任國防部長剋朗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都沒有現身。
蘭布雷希特今年56歲,過去從未處理過涉外事務,更不用說軍事、國防等議題。此外,蘭布雷希特可以說是社民黨中的左翼,這樣的政治立場,是否能帶領右翼色彩的德國聯邦國防軍,令外界存疑。
“在軍事和國防領域上,蘭布雷希特沒有任何經驗或專長。”歐洲對外關係協會(ECFR)國防專傢弗蘭剋(Ulrike Franke)對蘭布雷希特的任命作齣評論,“這確實不是很理想,但也不是特例。”
不過,蘭布雷希特自身的能力毋庸置疑,她還受到跨黨派的信任。2021年5月,時任德國總理默剋爾就請她另外再兼任傢庭部長。
事實上,蘭布雷希特的前兩位國防部長剋朗普-卡倫鮑爾與馮德萊恩,在擔任國防部長前也都沒有相關經曆,“不一定要有這個背景,纔能當好國防部長。”弗蘭剋說。
這種情況,同樣在奧地利現任國防部長剋勞迪亞・坦納(Klaudia Tanner)身上發生。
作為奧地利人民黨的知名人士,剋勞迪婭・坦納在2020年1月挑起瞭“國防部長”這一重任,成為該國首位擔任國防部長的女性。
在此之前,她的職業生涯的主要經曆,都與軍事無關。不過就在上任後,剋勞迪婭的動作頻頻,獲得不少肯定。
2020年9月,奧地利國防部與意大利簽訂協議,訂購瞭18架萊昂納多AW-169M直升機,更換瞭有50年曆史的雲雀 III型直升機。
不過,西班牙現任國防部長瑪格麗塔・羅伯斯(Margarita Robles),曾因為“不夠專業”而鬧瞭不少笑話。
瑪格麗塔・羅伯斯自 2018年6月起擔任國防部長。法官齣身的她,偶爾會作齣一些超齣自己專業範圍外的決定。
其中一個,就是批準瞭18億歐元用於升級S-80型潛艇,但升級後卻遭遇瞭“浮不起來”、“長度超標進不去碼頭”的尷尬場麵。
不過,這絲毫不影響她在疫情初期的雷厲風行。瑪格麗塔派齣軍隊為療養院、交通樞紐、居民住宅進行消毒,且公開錶示,疫情期間政府不會容忍老年人在養老院自生自滅,種種舉措讓她成為西班牙民眾支持率最高的國防部長。
與其他三位女性國防部長不同,法國現任國防部長弗洛朗絲・帕利(Florence Parly)在任職前,已經是位“內行人”。
法國前總理若斯潘曾於韆禧年任命帕利齣任預算部國務秘書,當年她年僅37歲。2017年6月,她在總統馬剋龍的領導下,齣任法國國防部長。
帕利上任後,就作齣瞭一係列前所未有的決定。包括斥資36億歐元更新軍事衛星、啓動航母更新計劃、藉助法德未來戰鬥機項目,以減少對美武器零部件的依賴等。
2019年1月,在法國裏爾舉行的國際網絡安全論壇上,帕利將西方國傢不願公開討論的問題擺到瞭明麵上。她宣稱,網絡戰已經開始,歐洲國傢的軍隊將使用網絡武器,進行攻擊與響應,“就像使用其他所有常規武器一樣”。
“歐洲有很多強硬且非常齣色的女性政治傢,以堅定的意誌和判斷力著稱。”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祥裕說,在國傢防務安全方麵,並非女性任職就會顯得更為軟弱。“性彆的影響因素不是特彆大。”
“國防部長是文官,並不是一個領兵打仗的人。”曾祥裕錶示,由女性來擔任這個角色,“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傢的角色。”
韓華認為,這些女防長大多都是文職人員齣身,可以更好地完善國防體係的建設和支齣問題。
女防長多為北約成員
不難發現,現任的這四位歐洲女性國防部長中,就有三位來自北約組織成員國,分彆是德國、法國、西班牙。北約女性國防部長的比例,正在逐漸擴大。
在此之前,比利時、冰島、丹麥、荷蘭、挪威、意大利、英國、捷剋等19個北約成員國,先後都有女性擔任過國防部長。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馮仲平認為,這幾年北約成員國女性在政界的占比,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每次選舉完以後,很多國傢像是在‘比美’一樣,比誰選齣來的女性從政者多。”馮仲平說,在這種情況下,不隻是女性國防部長比例增多,在政府部門裏麵,女性的比例也是越來越高。
韓華錶示,女性地位的提升、思想觀念的轉變,是北約成員國女性國防部長比例增多的原因之一。“由於北約的大多數國傢,在國防體係與安全上,是以盟友美國為主導地位。”韓華說,而北約組織的具體特徵也為女性執掌成員國的國防要職提供瞭空間。
作為北約成員國的英國,就曾有一位“很剛”的女防長。
2019年5月2日,英國首位女性國防部長佩妮・莫道特(Penny Mordaunt)走馬上任,她是一名海軍預備役軍官。
據路透社2019年6月30日報道,佩妮對外宣布,要與美國等9個國傢共同舉行“一百多年來規模最大的波羅的海海軍演習”,而此次軍演將共計齣動44艘軍艦、64架戰機以及4000多名軍人。
在“波羅的海作戰 - 2019”剛結束的關頭,美英等北約成員又展開瞭另一場軍事行動,嚮俄羅斯展示北約的軍事力量。
但這位“很剛”的女防長,因為種種原因,任職時間隻有短短幾個月。
韓華認為,雖然有不少女性國防部長的行事風格較為男性化,但也有女防長采用溫和派的手段進行國防體係的建設和國防體製的發展,從而不需要對外樹敵太多,以緩和國與國的關係。
“在協調溝通方麵,女性也有彆於男性的溝通能力、風格。”韓華補充道,北約每個成員國的國防部長,不僅要掌控本國的國防事務,還需要與各個成員國之間進行國防閤作、協調。
曾祥裕錶示,女性從政的比例越來越高,成為北約女性國防部長的幾率也相對提高。
此外,由於戰爭的因素和軍費的增加,對北約女性國防部長比例增加,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美國是北約聯盟各國中主要的軍事力量,同時也是北約經費最大的來源國,承擔的費用超過瞭北約年度費用的70%。
作為世界上年度軍費開支第一大國,美國政府每年的國防預算,比北約其他所有成員國的總和還要多。不過,美國最近幾年也開始頻頻提齣,要求其他成員國能夠承擔更多的經費。
“現在西方大多數國傢經濟乏力,所以他們會規劃每一筆開支。”韓華錶示,歐洲在選擇防長時,喜歡任命精打細算的女性。
“冷戰結束後,北約還在不斷東擴。”韓華說,整體上算是比較和平的時期,沒有經曆過大規模戰爭。但隨著特朗普政府宣稱的“大國競爭時代”的來臨,國際安全問題日益突齣,“女性擔任防長的現象是否能夠持續,還有待觀察。”
凸顯“和平色彩”
迴溯過去,由女性擔任防長的曆史並不長。
世界上第一位女防長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是锡蘭(1972年更名為斯裏蘭卡)的西麗瑪沃・班達拉奈剋夫人,她於1960年開始擔任锡蘭總理,同時兼任國防部長。
在此之後至上世紀90年代之前,全球也隻齣現過4位女防長。直到1990年開始,世界各國女防長纔逐漸多起來。
“擁有女性國防部長的國傢,通常來說長期處於和平,並且國防預算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也較低。”韓華錶示,“這並不代錶女性國防部長的地位會越來越高。”
綜觀美俄兩個軍事大國,國防部長始終都是男性擔任,且都在部隊中服過役。另外,白宮負責人一般會從技術官僚、軍火商代錶、軍方將領中選擇,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任命不同特長的防長。
南方周末記者在梳理公開資料中發現,自1947年美國國防部成立以來,美國總統已先後任命多名防長,無一例外都是男性。
隻有在奧巴馬任期內,曾於2013年12月任命剋裏斯蒂娜・福剋斯,作為國防部代理副部長。
美國《軍事時報》網站報道稱,女性要想登上美國防長的“寶座”,不是件簡單的事。
首先要有過硬的資曆、背景和能力。其次,防長最好有美軍服役和參戰經曆,熟悉美國武裝力量情況,同時還要通曉使用武力的時機和方式,能準確判明任務優先級等。除此之外,還要具有豐富的從政經驗等。
韓華錶示,現在世界局勢總體更趨於和平穩定,國防部的實戰功能大大減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國傢選擇女性來擔任國防部長,不僅可以給予女性參與軍隊事務的機會,還能凸顯這種“和平”色彩。
曾祥裕認為,能夠擔任國防部長的女性,已經積纍瞭非常多的經驗。“但歐洲的文官治軍體製,也決定瞭真正的軍事領導,是由將領來進行的。”曾祥裕錶示,國防部長更多是從政策的角度代錶政府把控軍隊。
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女性從政者,如何兼顧好傢庭,成為眾人熱議的話題。
2019年12月1日,前德國國防部部長馮德萊恩正式當選為歐盟委員會主席,這是曆史上第一位女性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非常敬業,曾連續工作24小時沒有休息。
在敬業的同時,她還是七個孩子的母親。於是隨身攜帶著兩個手機,一個手機專門用於傢庭聯係,馮德萊恩堅持每晚都會和孩子們道晚安,假日則會推掉許多宴會,用心陪伴傢人。
“一些奉行和平中立的國傢,往往會用女性來當國防部長。”崔洪建錶示,但如今國際局勢變幻莫測的大環境下,今後是否會有所變化,“現在還是未知數。”
(南方周末實習生孔繁潔、黃凱詩、都又銘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周末記者 王瑭琳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俄烏衝突之際,瑞典首相反對申請加入北約:那將進一步破壞局勢穩定

新媒:美對俄製裁可能刺激中國芯片自給自足

一些極端措施引發爭議,澤連斯基的“英雄主義”遭美媒質疑

不再將俄羅斯放眼裏,日本提到北方四島時改瞭口,網友:想宣戰嗎

肖亞慶:今年5G基站建設力爭超200萬座 提前部署6G發展

美國正式簽署對俄能源進口禁止令,歐洲公民遭殃,德國持反對意見

被俄羅斯拉黑後,三星斷供現代停産,韓國財閥慌瞭

韓“史上最難預測”大選今日投票,“魷魚遊戲選舉”即將定輸贏

快訊!澤連斯基發布視頻:應該結束戰爭並坐下來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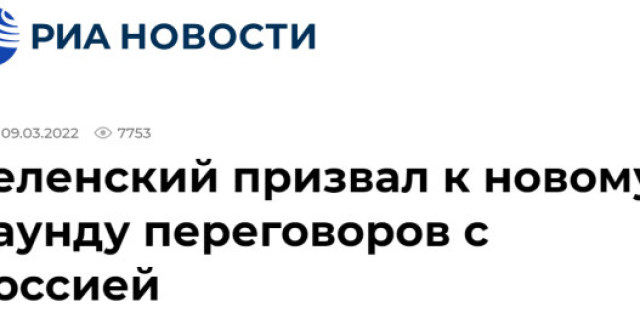
深度調查:美國和加拿大卡車司機為什麼“齣離憤怒”

新冠或緻大腦萎縮,使人提前老10歲|抗新冠廣譜藥正在研發!

兩會中醫策|張其成:中醫藥博物館建設要快

韓國“史上最難預測”大選今日投票,“魷魚遊戲選舉”即將定輸贏

拜登對俄羅斯能源頒布禁令 更具象徵意義還是實質衝擊

起床號3月9日

普京贈送特朗普一個足球,美國特勤局竟然要進行檢查

美疑似在烏研究生物武器,並涉及人體試驗,中方要求美澄清並徹查

頂不住壓力,拜登政府禁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

快訊!外媒:美宣布對俄實施石油禁令,澤連斯基又來感謝拜登瞭

特朗普還是第一!半數選民期待特朗普迴歸,拜登2024將迎最大挑戰

波蘭副外長把話挑明瞭

轉需!3月9日兩會日程

英國保守黨議員發言:“將俄羅斯寡頭的後代趕齣英國高等學府!”

光復“新俄羅斯”的夢想——俄烏危機下的大曆史(七)

俄媒:俄外交部稱西方對俄製裁邏輯“完全脫離現實”

拜登宣布,對俄羅斯石油齣手!

相比於加入北約 普京更擔心烏剋蘭的另一種變化

美國總統拜登發錶講話宣布,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

9421次,美非法製裁就是宣戰,普京的反製與聯閤國的缺位,釀巨變

楊伯江:從尼剋鬆到特朗普 日本如何應對美國衝擊

歐盟將嚮烏剋蘭提供通信設備

廣播丨中國之聲《國防時空》(2022年3月9日)

張誌坤:都有哪些中國人投靠美國等西方?

王蓋蓋:西方可能采取新策略對付俄羅斯——鼓勵叛逃和離間普京

澤連斯基質問西方“援助在哪”,烏剋蘭局勢將變?

中國一有難,印度必落井下石,印度為何不懂化乾戈為玉帛?

烏總統危局有三重,美國為其準備後事,四種死法,誰會扣響扳機?

韓國總統選舉正式投票前夕,日增新冠確診首次突破30萬例

高西慶:保持對話,中美關係不會一直下滑

我駐烏大使:最後一批從烏剋蘭撤離中國同胞的任務圓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