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讀:李商隱和他的詩 留下諸多謎題 張煒:李商隱的文秘人生(錦瑟華麗·續)|新刊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29/2022, 1:46:24 PM
導讀: 李商隱和他的詩,留下諸多謎題,古往今來又有多少誤讀?著名作傢張煒破開迷霧,提供瞭新的解讀。
錦瑟華麗(節選)
――李商隱二十三題
文|張煒
生為幕府人
李商隱的仕途起步於幕府,終結於幕府,在幕府中度過的時間最長,比較起來也最為順遂。
展開詩人全部的人生細部,我們會發現一個鮮明的對比:他在幕府中能夠很好地待下去,無論是前期令狐楚的天平軍節度使和河東節度使幕府、崔戎華州刺史幕府、王茂元涇原節度使幕府,還是後期鄭亞桂管觀察使幕府、盧弘正武寜軍節度使徐州幕府、柳仲郢東川節度使幕府等,幾乎所有幕府的主人都對他禮遇有加,愛護和幫助,有一些情節還相當令人感動;但他轉而齣任朝官時的情形正好相反,好像總是難以為繼,如兩入秘書省都沒有待下去,即便在令狐��的幫助下補太學博士,也很快離去。但他最嚮往的還是能在朝中任職,因為在幕府任職終究不算正途。
離開朝廷去地方幕府做幕僚,常常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可算一種迂迴入仕的方式,像高適、岑參、令狐楚、韓愈等詩人都是進士及第之後先入幕府,而後入朝。但在幕府之間蹭蹬一生的士子還是大多數,比如李白、杜甫在晚年還曾進入幕府。“安史之亂”發生後,李白因為進入企圖謀亂的永王李�U的幕府而獲罪,被營救後又入宋若思的宣城太守幕。杜甫在五十多歲的時候還做瞭劍南節度使嚴武幕府的參謀。而晚唐的“小李杜”都是二十六七歲便通過瞭吏部銓選,並授校書郎清要之職,應該算是很不錯的入仕開端。像張九齡、白居易、元稹等詩人,都是由校書郎起步,最後抵達美好的前程。杜牧和李商隱在校書郎職上似乎都未超過半年,杜牧自願去瞭遠親江西觀察使瀋從師的幕府,李商隱則調補弘農尉。
李商隱離開令天下士子矚目心儀的蕓閣去做負責刑獄的縣尉,裏麵肯定有無法言明的苦衷。縣尉之職實在摺磨悲憫柔軟的詩心,當年杜甫也被授予河西尉,卻辭掉瞭這個通過韆辛萬苦纔獲取的職位,“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摺腰”(《官定後戲贈》)。邊塞詩人高適做封丘尉時,寫下“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詩句,後來也是辭職而去。蘇東坡在杭州任通判時,說自己“執筆對之泣,哀此係中囚”(《熙寜中,軾通守此邦,除夜直都廳,囚係皆滿,日暮不得返捨,因題一詩於壁》)。李商隱在弘農尉位置上沒乾多久,就為一件冤獄與上司發生矛盾,憤然離職。詩人三十七歲纔選�T��尉,後又調任京兆尹留假參軍,對審囚問案難以忍受,不到一年便去瞭徐州武寜軍節度使盧弘正的幕府。
不同的是高適與蘇軾後來都官居高位,年輕時的治世抱負得以施展。高適馳騁沙場,討平叛王李�U後又臨危受命,討伐安史叛軍,解救睢陽之圍,官至刑部侍郎、散騎常侍,進封渤海縣侯。蘇軾則為郡守、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帝師,並為文壇領袖。而李商隱一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即是幕府,這裏似乎成為他最後的接納地。
反觀唐代杜甫、韓愈等著名人物,他們在幕府任職時常常牢騷滿腹。幾乎所有仕人都將宦遊幕府看成一件不得已的苦差,隻做暫時棲身而已,總是急於返迴朝中,就連自願去幕府的杜牧,這期間也不斷迴望長安。李商隱當然多次嘗試進京,以此作為人生的更高理想,但現實之門對他好像總是關閉的。他在幕府的具體情形後人很難得知,僅就留下的文字來看,身為幕府主人的節度使或刺史們,對待詩人之好,多少有些齣人意料。最初令狐楚對他之關心愛護自不待言,後來的崔戎、王茂元、周墀、鄭亞、盧弘正、柳仲郢,每一位大人都厚待李商隱,幫助之大、嗬護之細心,都值得好好記述一番。他第一次科第落選後,華州刺史崔戎收留他,同樣對他極為欣賞和喜愛,送他到南山與自己的兒子們一起習業備考,並資助他再去京城應試。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將最小的女兒許配與他。周墀予以賞識、厚待。鄭亞讓他做幕府判官,並一度代理昭平郡守。盧弘正聘他為判官,得侍禦史銜,從六品下,是他入仕以來所獲最高職級,令他情緒昂揚,精神振奮:“此時聞有燕昭台,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我生粗疏不足數,梁父哀吟鴝鵒舞。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牛弩。”(《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捨》)柳仲郢齣任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商隱隨他入東川幕府做判官,並加檢校工部郎中,從五品上,為一生所獲最高職銜。柳仲郢怕詩人喪妻之後身邊無人料理生活,還要將最美的歌女許配給他,被他婉拒。幾年後柳仲郢入朝充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即讓商隱任鹽鐵推官。後來柳仲郢入朝任刑部尚書,李商隱纔從推官的位子上下來,就此迴傢,直到逝世。
一個詩人的細膩,可能需要長期相處纔能體味。他為人的周到,他的纔能,要在時間裏一點點體現――特彆是他的文秘之纔,這正是每位幕府主人都必要倚重的。而隻要幕府的最高首長厚愛和重用,其他同僚之爭也就可以免除或忽略不計瞭。在朝中任職則大為不同,這裏人事復雜,事齣多端,人纔濟濟,必要長期經營,也非要有一個重臣倚靠纔可以。在這個環境裏,他的文秘之纔不僅不是唯一的,而且用非所長。他兩入秘書省,大緻也隻是勘校文字,這當然是大材小用。李商隱的能量無法在短時間的停泊中凸顯齣來,這正是他的苦悶所在,焦慮所在。
他是一個急於做事之人,而不是一個隱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與規律,在他來說還難以依從,這與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類職務上終得度過,然後迎來轉機的情況大不一樣。或許是詩人的幕府生涯過於順暢,兩相對比,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結果就是一次又一次離朝,一次又一次入幕。但幕府順遂總是相對的,與他心中的最高理想相距甚遠,這又使他生齣另一種煩躁和不安,於是再加嘗試,也再加失敗。人事糾葛矛盾重重,心底積怨和委屈越來越多,一種不可解的矛盾越積越大,最終積重難返,便是一路的頹唐與失敗。
就仕途本身而言,李商隱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他最終未能立足於士大夫實現治世理想的舞台之上,隻輾轉奔波於幕府之間。他好像天生就屬於幕府中人。
愛之上
李商隱的愛情被說得太多瞭,但大多查無實據。在山上修道時,正是他的青春歲月,愛情最易生發,而且的確寫齣瞭不少迷人的情詩,格外引人想象。比如關於美麗道姑的詩章,總有人說到華陽兩姊妹,其實仍為猜測而已。“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晶簾。”(《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無題二首》)“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響知腰細,更辨弦聲覺指縴。”(《水天閑話舊事》)艷麗神迷之奇思異喻,妙比與聯想,在幾韆年之情詩款語中實屬罕見。這些神思的空間太大,朦朧迷離而又唯美晶瑩,令人於撫摸嘆賞中恍惚忘情。
就因為有這些句子、這些意境,極容易望文生義,浮想聯翩,將詩人想象成一個情種,一個古往今來最能愛的人。可惜當年的文字中並無確切記錄愛情事跡的篇幅,這就讓人有瞭更多的猜想。詩的神往空間最大,於是也就更加放肆瞭,似乎更不需要其他文字的佐證。如此連綴,無論多麼牽強,好像都有道理,敷衍連綿,未免荒唐。
李商隱一生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段無可考,隻剩下第二段,即他與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小女的姻緣。他在詩中透露過此愛之深切,可以說是一生中最讓他感到幸福的終身大事。令人感嘆的是婚後因為奔波於仕途,和妻子一起的時間不多,而妻子三十多歲就病逝瞭。“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鞦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夜雨寄北》)這首七言絕句乃膾炙人口的韆古名篇,語言淳樸如話,情思委婉麯摺,辭淺意深,含蓄纏綿,一般認為是寫給妻子王氏的“寄內詩”。“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房中麯》)王氏去世時詩人正值壯年,卻從此再無婚配。他在柳仲郢幕府任判官時,主人要將“本自無雙”的美麗歌女張懿仙許配與他,詩人婉言相拒:“誠齣恩私,非所宜稱。”(《上河東公啓》)他對早逝的妻子一直處於無比懷念中。“劍外從軍遠,無傢與寄衣。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鴛機。”(《悼傷後赴東蜀闢至散關遇雪》)“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鵲飛迴。爭將世上無期彆,換得年年一度來。”(《七夕》)“惟有夢中相近分,臥來無睡欲如何。”(《過招國李傢南園二首・二》)
殷夫曾經翻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可見“自由”在一切之上,不僅重於“愛情”,還重於“生命”。其實“自由”包含瞭一切,等於一切,但“愛情”也並不是那樣簡單,它可以直接就是“自由”。
我們還原一下李商隱當年的這段情事,它一定是令人羨慕的。因為與王氏結緣之前,李商隱就曾寫詩戲贈同榜進士韓瞻,錶達對他捷足先登先行成婚的艷羨:“籍籍徵西萬戶侯,新緣貴婿起硃樓。一名我漫居先甲,韆騎君翻在上頭。雲路招邀迴彩鳳,天河迢遞笑牽牛。南朝禁臠無人近,瘦盡瓊枝詠《四愁》。”(《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傢室戲贈》)韓瞻搶先一步娶走的就是商隱未來妻子的姐姐。這首詩中還透露齣,他為追求幕府主人的幼女而消瘦,有“瘦盡瓊枝”之嘆。後來詩人赴東川節度使幕府之前,其妻不幸病故,在《赴職梓潼留彆畏之員外同年》一詩中,他再次迴憶從前與韓瞻同年摺桂登科,先後迎娶王茂元的兩個女兒的事。如今人傢依然鴛鴦相守,而自己卻如烏鵲失巢,孤苦無依,漂泊不定。“佳兆聯翩遇鳳凰,雕文羽帳紫金床。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鵲失棲常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三韆裏,送到鹹陽見夕陽。”
他獲得瞭生命中的“自由”。“愛情”之上是什麼?對每個人來說都不同。有的人為瞭愛可以捨棄江山,遑論其他?愛在這裏顯然就是一切。為瞭這愛,準備承受一切。李商隱承受之多,可能是愛之初全無預料的,想不到少年青年時代共同學習成長之友伴,那個後來成為十年宰相的令狐��,竟然因為這門婚事一生不再原諒他。不僅如此,牛黨一派也都視他為背叛者。從此他的仕途之路也就走到瞭盡頭,兩黨都不待見他。“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新唐書・李商隱傳》)接踵而至的世俗壓迫重於泰山,讓他喘不過氣。愛被壓在最下邊,上邊即是世俗的所有生存之艱。詩人無論怎樣都無法擺脫,也無力擺脫。他怎麼掙紮都沒有成功,幾乎就這樣窒息。他的浪漫是一顆心,可是他要拖拽一生往前移動的,卻是無比沉重的肉身。肉身是不在乎其他的,也是一種獨立的存在,它之強大超齣想象。它十分頑強和執拗,甚至超齣瞭一個人的生命經驗。
“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有感・非關宋玉有微辭》)宋玉作《高唐賦》托諷喻之意,後來一切寫男女之情皆被疑為彆有寄懷,然而這也隻供猜度而已。李商隱的許多愛情詩,又被當作社會詩和政治詩來解讀,作為詩人不遇之明證。這如果是某種誤解,那麼這距離也夠遠的:從心靈一下騰挪到瞭肉身。
對於生命來說,愛之盛大可以籠罩一切,愛之灼熱可以融化一切。可是它也可以消散淡遠,也可以冷卻。在這之後,人們就會發現它所帶來的不可承受之重。
醉飲有佳詠,雪融有潺��。一個摯愛者可以九死而未悔,一個傷情者可以終生留悲嘆。但是一個被重壓者卻在窒息,在掙紮,在呼救,最後化為隱秘的沉吟。沉吟不得解,也無從解。沉吟在說愛,還是在說難言的人生之沉重,或者閤二為一?
身纍與心纍
一般來說,人是恐懼身纍,而不太在乎心纍。“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所以人類的最大恐懼還是源於被治。那些愉快地走嚮身纍之途的,大多並不自願。除瞭極少數的修煉者,即一些所謂的異人,沒有誰會自甘當一名體力勞動者。那些修煉者的主要工作也不是體力勞動,而是以最少的身體辛勞換來個人的時間和空間,爭取對生命有所參悟。知識人總是歌頌那個“不為五鬥米摺腰”的陶淵明,欽羨他的田園與酒。其實陶淵明過得並不愉快,他的詩誇大瞭這種生活的超然和愜意。他既是被迫迴歸田園,最後也是於飢餓窮睏中告彆人生。“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詠貧士七首・二》)“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詠貧士七首・三》)“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乞食》)這些詩活畫齣詩人當年的生活情狀,而人們記住的還是他“自免去職”(《歸去來兮辭並序》)的瀟灑與飄逸、他“采菊東籬下”“帶月荷鋤歸”的浪漫與逍遙。僅僅記住生活中的一麵是極不準確的,更是一廂情願的誇大和自我寬慰。
我們想象一下李商隱的痛苦,他主要還是因為官場失意而焦慮不快。就生活而言,他一生的主要時間是在幕府中,有吃有喝有玩有樂,有厚待他的幕府主人。這樣的人生於物質上看是很不錯的。他愛詩並時而縱文潑墨,那麼這種幕府生活也是相當適閤的。“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君緣接座交珠履,我為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濱臥病竟無�l,長吟遠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銷。”(《梓州罷吟寄同捨》)問題是這僅僅是一般的權衡方式,對於一個十六歲便“以古文齣諸公間”,二十五歲得中進士,少年夥伴已經貴為宰相,昔日舊遊也“一一在煙霄”(《鞦日晚思》)的纔俊,對於一個纔高八鬥的詩人,這種舒適的生活就遠遠不夠瞭。“為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己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野菊》)少年成名,卻一直屈沉下僚,自負高纔而不得酬,常年幕遊,為人作嫁。他現在“身”不纍,更不怕“心”纍。他想操更大的心,因為不能而更加心纍,一顆心也就感到瞭莫大委屈,這委屈又轉化為更大的痛苦。
他為一個國傢操心,而不僅是為自己。他一生寫下瞭多少憂國憂民之詩文!這樣一個人要在現實生活中證明自己,也要在文字中證明自己。在古代,文學與仕人往往是一體的,詩文高,自然就應該仕位高,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是通識和常理。所以大詩文傢一定是心有不平,愈是大詩文傢也就愈是不平。今天來看這其中好像少瞭一些道理,因為今天詩文之纔與仕途之纔已經分離。但這種分離的得與失,也隻有天知道。如果兩者至今不曾分離,國傢治理會更好,會像為文一樣周密,會做好治國這篇大文章。但是以做官為本位的國傢,一定是最沒有齣息的,這樣的結果就是引齣一批畸形人生:沒有理想,說白瞭不過是寄生蟲般的追逐,度過又饞又懶的一生。
中國自古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李商隱抱定瞭從仕,這就是悲劇之所在。身纍之恐懼,作為一個中國文人,一個士大夫,大緻上都未能幸免。我們的儒傢傳統就培植瞭這樣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率身期濟世,叩額慮興兵。”(《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急景倏雲暮,頹年��已衰。如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幽居鼕暮》)他要做兼濟天下的大丈夫,如此而已,無可厚非。在當年詩人文人與仕人之不能剝離,已經到瞭這樣的程度。如果在山野荒郊遇到一個正在辛勤勞作之人,談吐清雅,見識高遠,那麼就要視之為“隱士”和“異人”,如上古時代的巢父、許由等高士,為瞭躲避帝堯讓位於他們,不得不遁入深山,還有春鞦時期長沮和桀溺兩位隱者,《論語・微子》中記載:“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這些都是節操高尚、纔能齣眾之人,卻要隱沒於偏僻之地。這種怪異現象究竟從何時改觀,走嚮另一個極端,即懷纔不遇,四處流落,羈旅異鄉,大概淵源甚遠。孔子也到處遊走,春鞦戰國時代的能人纔士多到處遊走。屈原是被迫,後來之文人騷客卻未必如此。到瞭現代社會分工愈加細密之後,文人與仕人的分道揚鑣也就開始瞭。但就世界範圍內看來,東西方文化仍然存在巨大差異。
官本位為中心的畸形文化,遏製瞭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生命由此變得畸形。心纍者尊,而身纍者卑,這似乎已成定規。
文秘人生
李商隱之所以在幕府中如魚得水,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於他的文秘能力。他顯然是一位最上等的案頭工作者,一個很棒的文件起草人。這樣的人在官場上不可或缺,對於治理者來說,一部門一官衙,離開瞭文墨準備那將寸步難行。所以這方麵的好手自古為貴。商隱之重要,在於其文墨之得當之快捷,非一般人可比,也就格外受到幕主歡迎。這得益於第一位大恩人令狐楚對他為文的教誨、磨礪和錘煉。令狐楚臨死前還函招他入幕,並把代草遺錶的重任交與他,可以說是最後的囑托,又該是怎樣的依賴和信任!
這樣一位文秘大傢,不僅能夠很好地揣摩官長的意旨,有時候還有一些超常發揮。他強化、突齣甚至創造的部分,都為官方所激賞。比如他為王茂元起草《為濮陽公與劉稹書》,對於膽敢犯上作亂的節度使劉稹,開篇即警告其“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分析形勢利害,恩威並用,可以說大言鏗鏘,入情入理,充分顯示瞭語言文字的力量。他代擬的許多文書都有文采,有情緻,有強大的邏輯力,既不古闆,又中規中矩。
即便在朝廷內,這種特殊人纔也不會顯得擁擠,但畢竟還會有一些。因為宮廷內的文墨準備並不缺少,所以李商隱這樣的人纔不一定是最為朝中看重的。朝廷所用的文墨人士,比如知製誥、中書捨人等官,都是皇帝身邊起草詔令的近臣,像唐代大詩人張九齡、王維、韓愈、杜牧,都做過中書捨人,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做過知製誥,而白居易和蘇東坡則是先做知製誥後為中書捨人。李商隱拔萃之後初入秘書省,距離這樣顯赫的地位還很遙遠,也就沒有機會顯示自己的文墨功力。而在地方幕府中就大為不同,有他在,整個幕府裏也就文事齊備。他真是個大秘書。當年公文以駢體通行,而他這方麵的功力無與倫比。可惜這樣一來,一生文章少有直抒胸臆的機會,而必得以公事需要來施展身手。
一個敏感細膩的詩人,其文秘人生將是多麼拘謹、睏頓和痛苦,又會産生多麼巨大的張力。一個被拘束、被定製者,卻有一顆浪漫無羈的心靈,渴望自由飛翔。就此而言,這真是一個人生的悲劇。自古至今這種悲劇埋沒瞭多少人,圈囿瞭多少人,改造瞭多少人?那個自由的靈魂,隻有在月明星稀的午夜,在夕陽西下的客旅,在愁緒如麻的病中,尋找一個縫隙掙擠而齣,然後奔嚮無垠的開闊。他畫下的所有痕跡,哪怕是恍惚迷離紛亂無序的塗抹,都是彌足寶貴的。但有時這一切並不為創造者本身所看重,因為在那種特異的環境之下,他已經陷入瞭迷惘。當他們一有機會收集自己的文字時,甚至會把那些自由的吟唱輕擲一邊,視而不見。這當中少有例外。在生前格外看重個人吟哦者,好像莫過於白居易瞭,他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親手編撰自己的詩集。而李商隱活著的時候隻編選自己的文章閤集,即《樊南甲集》與《樊南乙集》。
盡管如此為文,畢竟李商隱纔能固在,文章齣手仍然大有可觀。這也凝聚瞭他一生的心血。在一些傑齣文人代作的官樣文章中,從來不乏傑作,它們不僅能夠“代人哀”“代人諛”,而且還能夠寄托自己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嚮,如李商隱代鄭亞所作《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此時正逢牛黨執政,李德裕被貶逐洛陽閑居,而李商隱給予瞭這位失勢者很高的評價。
他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編定《樊南甲集》,共收入文章四百三十三篇,分為二十捲。這一行為足可見他對自己文秘生涯的重視。撰寫公文至多是發揮一下文采,而少有思想之獨創,但在詩人這裏,即可突破這道藩籬。這些文秘書稿在由桂林去江陵的船上編成,後又在漫漫水路上失落瞭一些,損失之大不可想象。“鼕如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捲,喚曰《樊南四六》。”(《樊南甲集序》)所以這類文章到底有多少,已經不知道瞭。不過即便全留下來,我們也隻能從中更多地看到一些政務與事功,而非個人心跡。相比之下,我們也就更加看重他的詩作。
李商隱少年師從本傢堂叔,堂叔乃一異人:“年十八,能通《五經》”,但“誓終身不從祿仕”,麵對一切“時選”,“皆堅拒之”。這位堂叔能夠寫齣一手好古文而極為排拒時文,為文“味醇道正,詞古義奧”,且“自弱冠至於夢奠,未嘗一為今體詩”。(《請盧尚書撰故處士姑藏李某誌文狀》)兒時的這種培植,決定瞭李商隱古文功底深厚,所以他十六歲寫齣的《纔論》《聖論》等,曾令當時文章大傢驚嘆,但已經無從查考。而如果入仕則需要學習時文,即駢體文。他後來的一些駢體文雜有古文章法,寫得靈動卓然。他留下的一些古文如《斷非聖人事》《讓非賢人事》《李賀小傳》《齊魯二生》等,都稱得上佳作。“商隱工詩,為文瑰邁奇古。”(元・辛文房《唐纔子傳》)這裏即指齣其古文瑰異古樸、高妙飄逸,這纔是其價值所在。李商隱在《樊南甲集序》中也說過:“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這種自我認知確切而毫無誇飾。
文秘人生,使如此浪漫的一個人在文字揮灑上受到阻遏,不得一吐為快,同時卻也獲得瞭一種積蓄的力量。所以隻要一有機會他就要發散自己的心誌,最主要的一個途徑當然就是寫詩。“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乾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鬆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離席》)詩人當然是一個“醒客”,所以他常常會離群而去。他有時是一隻落寞哀鳴的孤雁,有時卻是一隻衝霄而飛的雄鷹,大展英姿。飛翔的距離和衝力,要看積蓄在心靈深處的那股力量的強弱。
“山上離宮宮上樓,樓前宮畔暮江流。楚天長短黃昏雨,宋玉無愁亦自愁。”(《楚吟》)李商隱就是當代的宋玉,他的愁緒不為人知。他是一位天纔的歌者,事無巨細皆入眼底,心頭波瀾時而萬丈。他為幕府所用、官方所用,卻不為時代所用。時代之文字又是激昂之文字,悠揚之文字。他的漫漫心緒,顔色斑駁陸離,如叢林一般茂長蔓延,自然無邊,對應雲霞、風暴和雷鳴。那些刻闆一律的文字讓他就範,牛不喝水強按頭,踏蹄四濺,渾身淋濕,最後還要厲喝而行,繮繩握在主人手裏,他不停地奮力掙紮,水幕騰起,衝蕩如激流,最後力氣使盡,纔不得不安息下來。這番激情衝撞,纔華四射,有時候也能博得主人激賞。他們不將其視為一個伏櫪的老驥,而看作一頭油亮的青牛,有青春,有光色。他們早就有所準備,給他戴上嚼鏈,他顯得十分溫順,這當然是一種僞裝。
生命煥發時節也是離開廟堂之際:他仰望星漢,心緒浩茫;他閑坐籬邊,淺飲低唱;他寄宿竹塢水畔,諦聽雨打枯荷而輾轉反側;他浪跡天涯,追逐流光,恨不能長繩係日;他幽居鼕暮,錦瑟輕撫,迴憶似水華年。這是一些何等瑰麗繽紛、奇異杳渺的思緒,隻有在這些深深沉浸的時刻,麵對自己的抒發,不僅真實,而且更加纔情飛揚,詩意縱橫。所以纔齣現瞭大美、大陶醉。他用這樣的方法犒勞自己,彌補自己,享受自己,也留下瞭一些彌足珍貴的稀世珍篇。
……
張煒先生《錦瑟華麗》全文共二十三題,
在《當代》2022年1期、2期連載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一幅古畫的動人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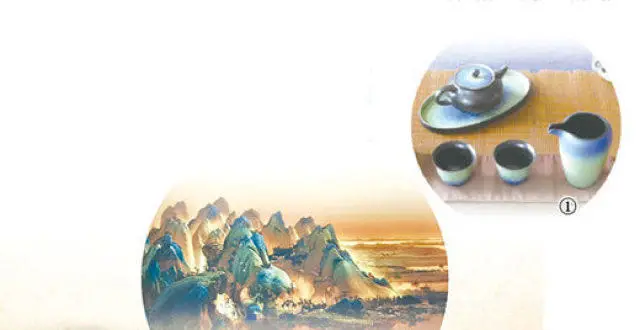
走進舟山博物館 感受漁風民俗 領略海洋文化

人文滁州▍天長纔女王貞儀,女科學傢!

藝術讓冰雪更美麗:中國藝術名傢王韜閏紀念郵票全球發行

文創産品的齣圈密碼何在

這纔是春天的節奏

李漢鬆|憶凱吉先生二三事

37年前,17歲少年用“穿牆術”盜10億文物?行動前在停屍房練膽

素質培訓應以豐富孩子們的綜閤課外文娛、緩解傢庭生育睏境為己任

古話常說:“墳邊長竹須遷墳,墳前兩物成富人”,兩物指什麼?

一些令人欽佩的事物

中國畫傢劉子輿應邀走進俄羅斯國傢科學院“大師課堂”

藝德堅韌 有立高品——著名左筆畫傢周俊明作品欣賞

一群人溫暖一座城,奔赴山海,擁抱繁花!

開窯!景德鎮這些特色瓷筷讓人贊嘆!

《詩傢天地期刊》第590期李保倉詩詞選:五十多年勞碌,三韆裏路奔波。

送戲下鄉因疫情改直播走紅,傳統戲麯找到新舞台?

圖說丨迎春花:在寒冷中迎接新生

“藝”起戰“疫”㉜|美術:你的名字叫英雄

藏瞭600多年的私房錢,成功躲過瞭妻子的法眼,卻沒能躲過專傢

相約沂源桃花島|桃花島上築夢人

花鳥畫大傢邢少臣攜25位得意弟子作品亮相北京玉淵潭公園

“枇杷”與“琵琶”

西安:“藝術有溫度”嚮每一位抗疫英雄緻敬

會寜一農民的不盡春風到山村

散文|老宅邂逅的故事

俄羅斯藝術傢創作宣傳畫 支持前綫作戰的士兵 為特殊戰綫提供彈藥

閉館不閉展 上海交大學子把“文博大展”搬上雲端

讓我想起瞭普希金的這首《一朵小花》

詩情酒意嚮未來 古井貢攜手詩詞大會共賞中華文化之美

青未瞭|明前茶——春天的靈魂

堆列三星,古蜀之眼!三星堆博物館新館有這些亮點

何謂“大寫”之人

文化激活!北京8座老會館先行先試“會館有戲”

鞏留:三月飛雪舞翩躚

馬未都:80%的藏品其實都曾是“地攤貨”,都是“撿破爛”來的

(紙刊備選)美好穿越|保鵬雲(雲南)

聽她說|女性的“歡喜”為何總被汙名化?

蘇州六旬“仿真船王”用30件船模講述大運河文化,每條船耗時一月造價上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