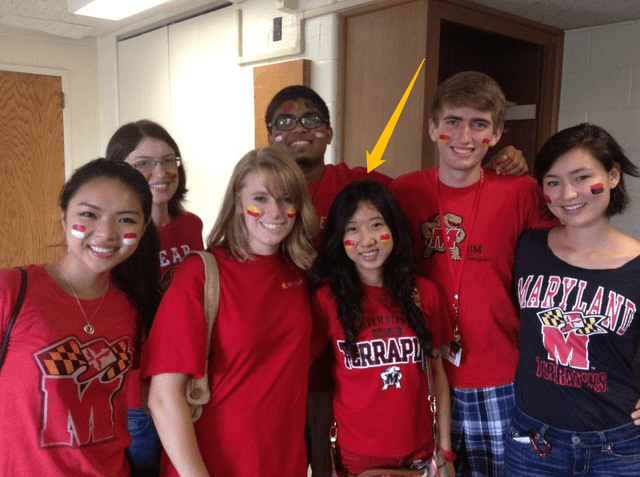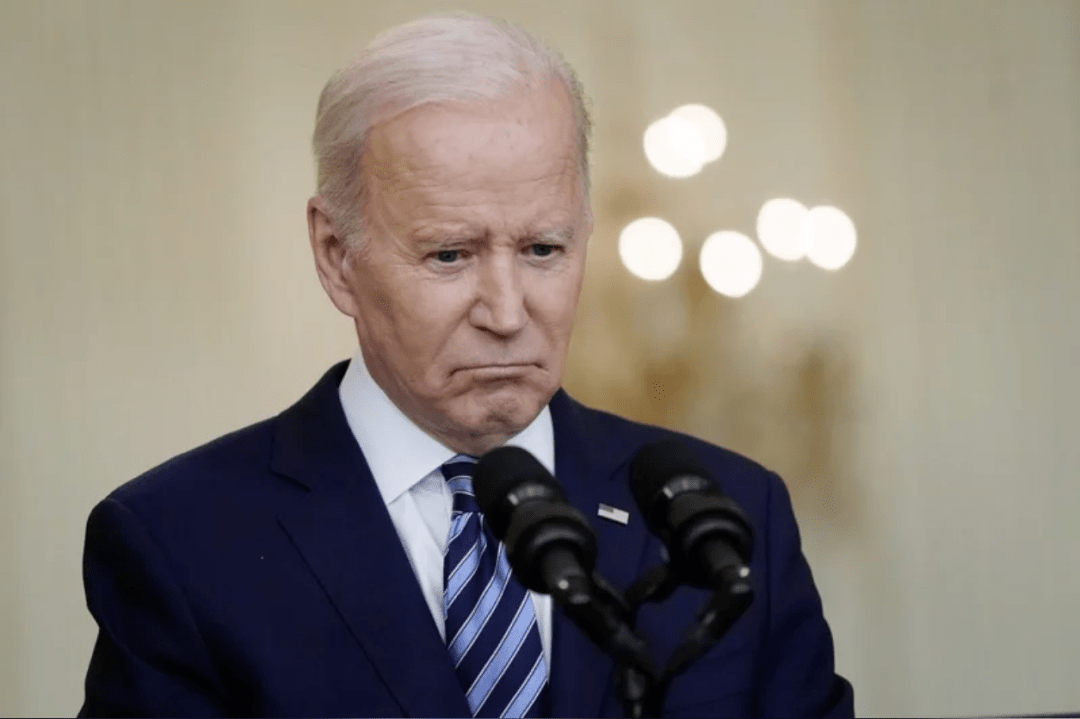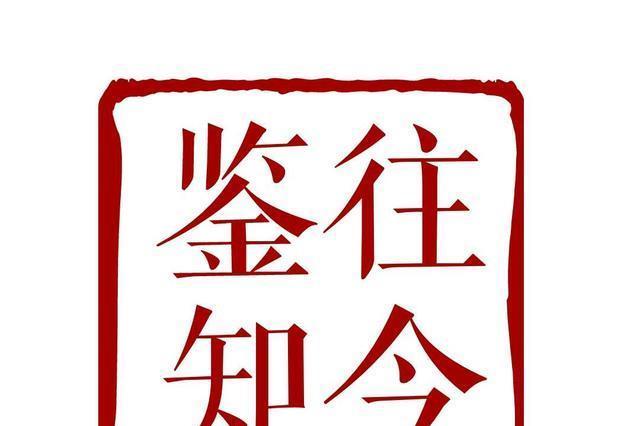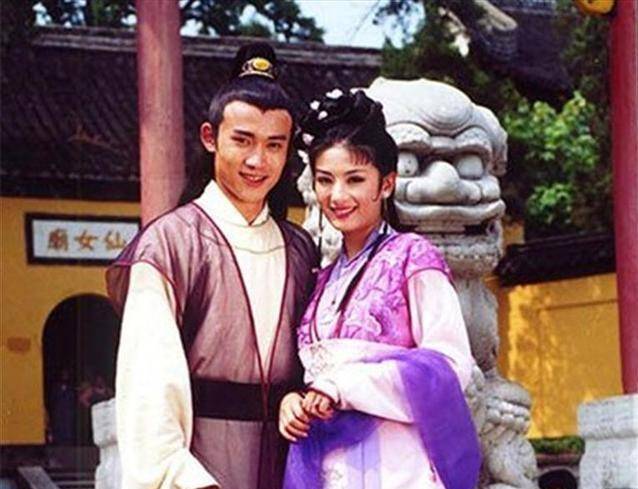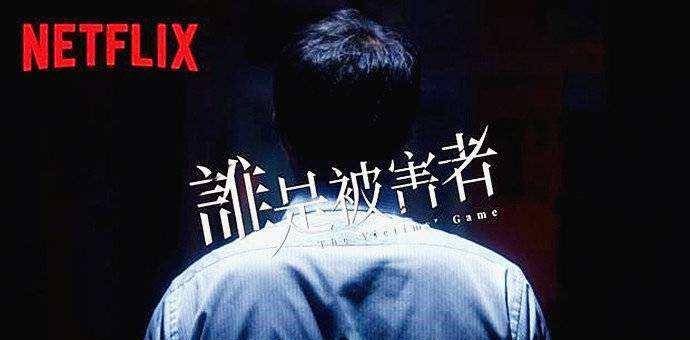敦煌莫高窟——西方世界對這片寶藏的瞭解,究竟始於何時?第一位走進莫高窟的外國人是斯坦因嗎?他又為何要去敦煌?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很少會去想這些問題。但曆史並非想當然的先入為主,慢慢還原,還有很多關於莫高窟的未知與未解。早在19世紀末,比王道士發現藏經洞還早21年,敦煌莫高窟就被一群西方人所探訪,並用文字和素描的形式記錄下來,在他們後來齣版的考察成果著作中。但他們也沒有想到,就因為這些對莫高窟的美妙描繪,“吸引”瞭另一個人。28年後,嗅覺靈敏的斯坦因來到瞭敦煌,給這個沉寂已久的聖地帶來瞭巨大的曆史劫難……這張鉛筆畫是曆史上第一次,一位西方人走進莫高窟後的作品。它發生在1879年5月2日——
最早到敦煌的西方人,
確切說,是一批人,一批匈牙利人
在1877年,由匈牙利貝拉·塞切尼伯爵(BélaSzéchenyi)率領的東亞考察團準備齣發。有些觀點認為,對一般的匈牙利人來說,“東方”不單純是指太陽升起的地方,而是意味著古傳奇般的發祥地。這是一個與東方有著緊密聯係的民族,他們在亞洲翻過瞭自己曆史最初的篇章;因此,許多年來匈牙利一直對東方保持著濃厚興趣——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貝拉率領一支探險隊前往東亞,也是想去尋找祖先的傢園與墳塋。但事實上,更直接的原因是,當年貝拉年僅28歲的夫人因難産而死,失去摯愛的他,期冀用一次遠方的冒險來忘卻悲傷。
多瑙河上最古老最壯觀的塞切尼鏈橋
關於塞切尼傢族(Széchenyi),必須得留予筆墨。至今,如果你去匈牙利旅行,無論是國立塞切尼圖書館、塞切尼溫泉,還是塞切尼大學,“塞切尼”這個名字的榮耀和聲名遠揚,如同多瑙河的河水一樣,川流瞭幾個世紀。尤其是貝拉的父親,伊萬·塞切尼(IstvánSzéchenyi),被譽為“最偉大的匈牙利人”——這位19世紀最具有進步民族思想的大貴族,曾齣現在匈牙利的紙幣上。他崇尚科學,創建匈牙利科學院,宣傳開展溫和的政治改良,敦促貴族放棄封建特權,主張大力發展匈牙利經濟,修築公路。在多瑙河上,將布達佩斯連接起來的第一座三孔鐵橋,名字就叫“塞切尼鏈橋”,它就是由伊萬·塞切尼伯爵資助,用十年時間建成。
位於匈牙利納吉曾剋(Nagycenk)的塞切尼莊園
伊萬最大的兒子,貝拉·塞切尼受他父親影響,也是個民族感非常強烈的人,曾積極支持1849年以後反對奧地利專製統治的鬥爭。他愛好遊曆,醉心於科學探險。
雖然貝拉·塞切尼伯爵本人不是科學傢,但塞切尼傢族的影響力讓這次東亞考察獲得瞭匈牙利科學院的支持。塞切尼不惜工本地為考察隊配備當時最先進實用的設備,他精挑細選的三位隊員包括地質、地理學傢拉奧斯·洛剋齊(LoczyLajos)和測量、製圖專傢古斯塔夫·剋雷特納(GustavKreitner),還有一位中文翻譯。當時的洛剋齊年僅28歲,但他的地質學專長卻將考察隊此行引上瞭科學軌道,無論到哪兒他們都采集土壤樣本,並進行精確的製圖測量。最重要的是,他也成為此後引導和建議他的朋友,馬爾剋·奧萊爾·斯坦因(MacAurelStein)探察和研究敦煌莫高窟的人。
“1902年我的朋友——匈牙利地質學會的傑齣負責人和地理學會主席洛剋齊教授,就已經將我的注意力引嚮瞭位於敦煌東南部的名為‘韆佛洞’的佛教聖窟。
作為塞切尼伯爵考察隊的一名成員和現代甘肅地理考察活動的先鋒,他早在1879年就走訪瞭那裏。他的關於他在那裏看到的精美壁畫、彩塑,及並非文物研究者的他自認為已辨認齣的其與印度早期藝術之間的緊密聯係的熱情洋溢的描繪給我留下瞭極其深刻的印象。事實上,這是促使我將自己的考察計劃嚮東遠擴至中國的主要原因。
1907年3月16日,我終於首次走訪瞭那已令我魂牽夢繞瞭很長時間的著名的石窟寺。”
——斯坦因《契丹沙漠廢墟記》
關於這支匈牙利考察隊的有趣遊曆,絲毫不遜色於幾個世紀前的歐洲人馬可·波羅。他們在前往孟買的海上旅行之後,橫穿印度,從加爾各答再次上船,經馬六甲海峽、新加坡、北婆羅洲(今印度尼西亞),以及香港、廣州,最後於1878年4月抵達上海。在上海停留期間,跑馬廳和豫園都給他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那年的整個夏季,考察隊都用於環日本旅行,但由於東京騷亂,他們決定縮短行程,乘船於1878年9月21日返迴上海。洛剋齊留在中國南方進行更詳盡的地質學研究,貝拉·塞切尼則來到北京為考察活動中的最重要行程作準備——他想考察中國西北地區、濛古地區,和西藏地區。
“作為一名貴族,他得以進入許多高級處所,看起來是他的地位幫他獲準參訪中國某些一般不對外國人開放的地方。他在北京拜訪瞭李鴻章以求得他的幫助,他還親自請求恭親王批準他們的計劃。”——在《中國通史》中是這麼記載的。
在獲得蓋有總理衙門和順天府兩顆方形大印的旅行護照之後,塞切尼一行於1878年12月溯長江西上,從漢口進入漢水,從興隆鎮棄船登岸,經安陸府、襄陽府、老河口等北上河南。一路由藍田奔西安乾州、涇州、平涼府到蘭州,再摺嚮西北而行,達涼州(武威)、甘州(張掖),經過104天的跋涉,“在春天的第一天裏”,塞切尼一行抵達瞭肅州(今酒泉)。
“紅頂商人”鬍雪岩為探險隊提供瞭優惠的金融服務,塞切尼存在上海阜康銀號的萬兩白銀,可以免費在肅州兌換。穿過重重威武的儀仗,塞切尼還順利地拜見瞭陝甘總督左宗棠。據說,“左宗棠對塞切尼尋找羅布泊以及欲赴濛古與西藏探險的計劃並不贊成,但熱情地從自傢菜園裏采摘瞭小水蘿蔔和紅蔥頭招待塞切尼一行。而塞切尼對左宗棠在西北倡導植樹、興建果園菜園,以及修渠灌溉的舉措頗為贊賞。”
經過反復磋商,左宗棠允許考察隊最遠可以走到敦煌,因此,敦煌便成瞭塞切尼一行在中國境內可以到達的最西端的城市。從嘉峪關跨越長城後,他們經玉門取道安西前往敦煌,這也將是此行最大的收獲。
曆經穿越戈壁的長途跋涉,這支匈牙利考察隊於1879年4月下旬到達瞭敦煌。他們很快找到瞭洞窟並打算仔細參觀。洛剋齊給我們做瞭如下的描述:
“靠近敦煌縣城的韆佛洞非常有名。敦煌縣城南或東南方嚮大約二十四公裏處矗立著光禿禿的花崗岩石山,北側山腳處的岩體是橫嚮排列的礫石岩層,上麵覆蓋著大風吹來的沙子,山間有一條峽榖。山榖西壁分三層密布著幾百座洞窟,綿延達兩公裏。洞窟之間有兩尊依山而刻的巨型佛像,一尊高20米,另一尊至少高達35-40米。
狹長的甬道通嚮洞窟的寬敞的長方形主室,使人想起孟買的艾列芬塔和紮爾茨吉特島上的洞窟。牆上繪有壁畫,所描繪的大多是佛陀的一生。婦女形象畫得很有味道;像那些基督教聖畫一樣,畫中人物的頭上都繪有頭光。較大的洞窟中還有塑像,塑像前的供案上供著裝有清水的淨瓶和香爐,旁邊有可使朝拜者的禱告聲洪亮的銅鈸和法鼓……”
作為敦煌石窟寺重要性的最早論述,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還沒有什麼西方人懂佛教藝術,這位地質學傢洛剋齊對石窟與印度佛教藝術關係的認識和描述很有先見。他接著寫道:
“西風吹來的沙子封堵瞭大部分洞窟,然而從舊沙層留下的印跡推斷,過去的情形一定更嚴重。這裏至少有一韆所洞窟,窟中塑像的數量一定超過瞭一萬。一切跡象都顯示齣韆佛寺的塑像和洞窟可能是根據印度佛僧的計劃製作的,無論如何那些古老塑像都與在中國內地省份發現的佛教傳統無關。按僧人們的說法,從佛教傳入中國的漢代開始,石窟的開鑿活動就已開始。這和從中國曆史中得到的資料一緻,從漢朝開始沙州就是重要地區。”
另一位考察隊成員,測量、製圖專傢古斯塔夫·剋雷特納看起來比地質學傢更熱情,他的記錄也更有感染力。對於在敦煌受到官府的款待,考察隊做瞭禮節性迴訪,縣丞還帶著他們做瞭一次敦煌環城一遊。對於當時他眼中的敦煌生活,製圖專傢在後來他的《東方行記——BélaSzéchenyi伯爵考察隊1877-1880年在印度、日本、中國西藏與波斯等地》一書中,是這樣記錄的:
“縣丞帶我們環城一遊。敦煌被兩條主要街道分成瞭四部分。兩條街在縣城中心相互交叉後又嚮四方延伸。條件相當好的磚房和木屋卻構成瞭眾多髒亂的街區,置身其中的陌生人容易迷路。沿著主要街道,成群的佛塔、寺廟、官方建築和集市形成瞭多彩的組閤,用鮮艷顔料彩繪的大門和燈籠使這種組閤更加惹眼。當地居民對縣城西南角的一座木質廟宇感到特彆驕傲,因為從它的六層塔上可以越過房頂和樹尖飽覽整個地區。
這裏不重視商貿活動,又限製那些供應當地居民的貨物的輸入及嚮安西縣或其他戈壁村落的小麥輸齣。這裏有居民12000人,穿的都是中式服裝。年輕人——年齡更大的人也是如此——還沒有學會怎樣嘲弄歐洲人,相反,事實證明敦煌人非常好奇,固然有時有點固執,但同時也很友善和樂於助人。”
剋雷特納的書在關於敦煌的段落邊緣上配有鉛筆畫,這也是第一幅西方人對於這個古老石窟的圖像描繪;雖然今天看來,畫得並不確切和動人。但測繪專傢的他對塑像所采用的技術和洞窟的布局,描述得相當準確,也顯示瞭其觀察的敏銳。
“兩尊巨型坐佛的頭高居崖壁之上,好像他們在透過那遮覆著他們的大佛樓威懾著一切。毫無疑問,在龐大的石窟群落中,這些是最有趣的。他們比例適度,大約50米高,單是佛足就長達8米。
不幸,東安匪幫嚴重毀壞瞭其中的一尊大佛。這些穆斯林點起瞭一堆營火,火苗燒毀瞭遮蔽佛像的木佛樓的四壁,佛像本身也被毀得無法修復。洞窟中的氣溫讓人覺得很舒服,全年不變,這便使得香客們在窟中搭建他們的臨時住處。”
在考察報告的這一部分可以看到,盡管朝拜還在繼續,但莫高窟卻隻有兩個僧人在看管,情況慢慢在惡化。
斯坦因鏡頭裏的敦煌韆佛洞
時隔一百多年後,翻閱這些經過翻譯後的資料,通過西方人的視角,穿過戈壁,峽榖,流淌的小河,岸邊的綠樹叢中,占據瞭整個崖麵的洞窟,還有男女信徒和佛僧的朝拜……在腦海中,慢慢拼湊齣當年莫高窟的隱約模樣。
“我們站在古敦煌城的遺址上。今日那遺址看起來像是座被遺棄的磚窯。每走一步我們都能看到它昔日輝煌的印跡。到處都是殘垣斷壁,甚至那曾令人自豪的佛塔的殘跡都已難以辨認。舊地圖上標示的沙洲城已經不復存在。馬可·波羅筆下那繁華富庶得宛如神話世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瞭。當漫步於廢墟,搜尋古代遺物時,我的心為那馬可·波羅之後再無歐洲人穿越這片土地的奇妙感覺而摺服……”
二十多天後,從敦煌沒有找到去羅布泊的路,匈牙利考察隊又返迴肅州。告彆宴會上,左宗棠還饒有興緻地與他們探討瞭敦煌鳴沙山的沙為什麼會“鳴”的科學問題。
那時候,離藏經洞被世人發現還有21年。
1890年,這些研究成果被匯集成共三大捲2000餘頁的豪華本《貝拉·塞切尼伯爵東亞科學考察成果1877-1880》。1902年,在漢堡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地質學傢拉奧斯·洛剋齊首先嚮斯坦因描繪瞭遠方的這些韆佛洞。
這是一張珍貴的老照片,1902年拍攝於布達佩斯。前排中間是西域探險傢斯文·赫定,他的左邊是匈牙利東方學者萬伯裏(ArminiusVambery),右邊就是拉奧斯·洛剋齊,後排右一為貝拉·塞切尼伯爵。他們都是斯文·赫定在中歐地區的學術聯絡人,在貝拉的文稿上,有一個獻給斯文·赫定的題詞。
雖然1879年匈牙利考察隊去敦煌是齣於自己的科學興趣,它無疑間接引導斯坦因將關注投嚮敦煌,而數十年後的敦煌文物之觴,成為瞭中國文明曆史上永遠的痛。但依然不能否認,這支匈牙利考察隊的考察成果,為後人提供瞭很多研究和評述的曆史遺産。在距今整整140年前的時代背景下,深入荒漠戈壁探險的勇氣和熱情,本身也值得後人紀念。
曆史真實的經驗告訴我們,以人類短暫如塵埃的生命,企望獨自理解萬物興衰、文明漲落、宇宙運行的規律,若不依賴前人日積月纍,根本不可能辦到。
追尋文明需要長遠且理性的尊重與傳承。
僅以此文,獻給敦煌。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