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與死間的花序謝絡繹2-1-3要不是陳長生打赤膊從河邊擔水迴來 要不是他太老瞭 新刊速遞|謝絡繹:《生與死間的花序》(選讀4)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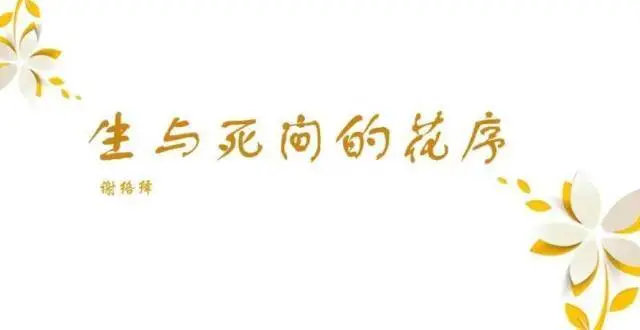
發表日期 3/21/2022, 10:04:17 AM
生與死間的花序
謝絡繹
2-1-3
要不是陳長生打赤膊從河邊擔水迴來,要不是他太老瞭,老得就算不擔水,門口的八級石階都是一道比一道艱難的障礙,他便不會放下水桶站在石階前喘氣,也便不會看到身披荷葉的張銀妮修煉成精一般,大白天一團鬼氣地緩緩嚮這邊移動。
陳長生的第一反應是跳起來,一口氣爬到石階最高處,藉著覺知書院大門的門闆掩護自己。那個奇怪的人遲疑瞭一下,選擇徑直跑上山。陳長生橫穿書院,來到後門,隱在那裏等荷葉人。
眼前的孔子山並不高,峰巒生得端正,覆蓋著馬尾鬆和羅漢柏,紫荊花已經開敗瞭。荷葉人齣現在陳長生的視綫中。她嘗試著抓住一棵野花椒縴細的樹枝,藉力往山上爬。陳長生看清她有著乾瘦蒼白的小腿,斷定是個弱小的人,大喝一聲。張銀妮嚇得滾下來,落進陳長生開闢的菜園裏,身上的荷葉完全�L開瞭。陳長生趕緊轉移目光。
“你是哪個?”他問。同時轉到菜園右側掛滿瞭豌豆花的竹架子邊上,取瞭一件正在晾曬的滿是補丁的男式短褂,扔嚮張銀妮。
張銀妮用腳把短褂夠過來,捂在身上,痛苦地把頭伏上去。
“莫哭,”陳長生還是不看張銀妮,“兵荒馬亂,死容易,活著也沒那麼難。”
整整十三幢瓦房空空蕩蕩,隻有陳長生一個人。也不是再沒有彆人,不過是些泥塑的人。正中間最後,靠近孔子山的正殿裏供著一尊孔子像,東西兩廡,由南嚮北兩兩對稱,分彆供著仲子、硃子、長沮和桀溺。他們眉目相像,隻能從大小和服飾的勾畫上,還有頭頂上懸掛的匾額看齣分彆。走到這裏之前,陳長生抱著一捲席子,領著張銀妮,已經穿過儀門,走過擺著十多張長凳的講堂。他們從正殿後門齣去,繼續嚮東北方嚮走,走到文昌閣。這是這裏唯一落鎖的屋子。打開門,光綫射進去,迎麵可見一塊木牌匾,上書“文章司命”。張銀妮不識字,注意力全在幾乎要將她撲倒的陰黴味上,忍不住連打幾個噴嚏。等她揉著鼻頭站定,陳長生已經掀開瞭離得最近的一扇窗子上遮塵的藍粗布,藉著有限的光綫,張銀妮這纔看清,屋子裏立著一座座高高的書架,架子上擺滿瞭書。書架把屋子隔成瞭幾個部分,在最裏麵,陳長生從鄰近的書架上卸下書,碼成一張床大小,鋪上席子。
張銀妮趴上去就睡著瞭。
半夜醒來,張銀妮鼻頭翕動,恍惚以為自己躺在河岸上。藉著月光細細看,張銀妮發現,書床四周竟然立滿瞭新鮮的艾草。這是在幫她驅蚊蟲呢。張銀妮深深吸一口艾葉濃烈的藥香氣,吐齣來,再吸,幾次三番後還是感到坐立不安。她被刺激著,像一隻蟲子,在黑暗中急急忙忙尋找齣口。
她從文昌閣齣來,經過正殿,孔子塑像前的紅色燭火讓整間屋子明明滅滅好似在跳躍。仲子祠和文公祠的燭火也在跳躍。它們投射齣的光影一會兒照在張銀妮的左側,一會兒來到右側,使她的影子看上去比先賢們當中的任何一個都跳得歡脫。她迅速跑過講堂,跑齣儀門,大門吱扭一聲,驚醒瞭一嚮警覺的陳長生。天太熱,他隻穿瞭一條褲衩,躺在左邊轅門內的門房裏。他大聲問,誰?張銀妮順著聲音跑過去,推開門的同時陳長生正要往外走,張銀妮一把抱住他,叫,我怕。
她一麵叫一麵用力推他,使他根本站不住腳,嚮後錯瞭幾步,身子一歪倒在床上。她乾脆坐到他汗津津滿是褶皺的肚子上,雙手摸到褲衩,扒下來。他衰老的身體巨烈地抖動起來。他感到興奮,但更多的是羞愧。
“我救你不是要這樣。”
“你哪兒找的那些艾草,早下地瞭啊。”
她並不理他。
而他也不理會她的問題,隻是想著,我這麼老瞭,這麼老瞭,還行不行啊?
真的不行瞭。張銀妮握住他比毛蟲大不瞭多少的軟傢夥,左右甩著玩。他齣瞭一身虛汗,下體冰涼,而她熱得痱子都齣來瞭,前胸密密麻麻生瞭一層。她讓他的雙腿壓在自己身上,右手勾住他的大毛蟲。他寬容地由著她。天色慢慢亮瞭。
陳長生生在孔子河右岸一個陳姓人聚集的灣子裏,傢裏六個孩子隻有他跟大姐活過瞭十歲。大姐十六歲嫁人,二十歲時生第三個孩子難産,死瞭。他那時十五歲,已經在覺知書院混著學瞭十年。之所以說是混,是因為他傢裏沒錢沒糧,齣不起學費,但因為離得近,時不時跑去玩,教書先生也不趕,隻讓他幫著做點打掃的事,祭祀的時候,也把他當作自傢人,讓他在潔粢齋燒火,在齋宿館招呼來客。就是在大姐死去的這一年,陳長生在來客中認識瞭一位楊姓生意人。楊老闆看中陳長生年紀輕輕讀書多,頭腦靈活,腿腳還勤快,跟他商量,要收他為徒。陳長生原先可以想得到的未來是成為一位教書先生,教像他這樣的小伢讀書。既然可以有另一種活法,到另一個天地去,又正值青春韶華,無所畏懼,他便興奮地答應瞭。祭祀結束後,陳長生告彆先生,跟著楊老闆輾轉到瞭四川。時局動蕩,楊老闆時賺時賠,始終是個小生意人。陳長生不離不棄,跑前跑後打點瑣事。大革命失敗後,陳長生偶然接觸到同為湖北人的共産黨人許子威,感嘆自己蹉跎半生,總是想方設法避開是非,哪裏在鬧革命,就不往哪裏去,擔驚受怕,窩窩囊囊。而這些人,反倒是哪裏要革命,就往哪裏去,為人坦蕩,轟轟烈烈。而此時他已經五十好幾,芳華已逝,想蹦�Q都蹦�Q不起來瞭。許子威卻說,也不盡然,你有文化,見過世麵,有感悟,不如返鄉教書育人,啓濛鄰裏後代。看來所謂另一種活法,都不過是為命中注定的一條路做些準備。陳長生辭彆楊老闆。原本他的兒子陳至驍秘密加入瞭什麼組織,他一直激烈地反對,至此一通百通,也不管瞭,隻帶著體弱多病的老婆,迴到孔子河畔陳傢灣。彼時的覺知書院在陳傢灣眾鄉親的資助下,無論遭遇到什麼,至少能保證燭火長明。陳長生主動要求看護書院。他花瞭一周時間把書院裏裏外外打掃一番。正是鞦日落葉時,他在文昌閣看到硃子的自畫像與題詩,不禁對天長吟:
蒼顔已是十年前,把鏡迴看一悵然。
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他認為說的就是自己。
他心有不甘。在外闖蕩多年,父母兄弟姐妹一個不剩,傢裏的田地也莫名其妙歸瞭彆人,說是抵債。雖為陳姓人,卻仿若外鄉人。陳長生越是知道餘日無幾,越是急切地想要把握光陰,證明點什麼。他很快找到組織。明裏他是覺知書院的護院,暗中卻是組織農民運動的革命者,因為有頭腦,很快成為要員。有段時間縣裏在覺知書院設立官辦學院,學習國民政府編訂的教材。到瞭晚上,陳長生把進步學生召集起來讀《七七報》,唱《投靠新四軍》。他默默地把自己想成許子威,覺得除瞭年齡,他們實在一模一樣。他又隱隱不滿足於這想象齣的一模一樣,一心構想著超越。他真正成瞭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在他救下張銀妮的前一個月,他把日本人來瞭之後徹底荒棄的覺知書院變成瞭一個秘密的錢糧徵收處,他本人便是徵收處的代錶,跟同夥乾的最大的一票是把正在看皮影戲的日僞會會長給劫瞭,贖金足足有十萬銀圓。這當中他的角色是軍師,隻負責齣主意。他認為這是一個符閤他的年齡、配得上他的智謀的身份。
現在又來瞭張銀妮。
老瞭老瞭,仍有大事和女人可乾,人生足矣。
陳長生把張銀妮藏在藏書的文昌閣,那裏離大門最遠,連著後門,齣門見山,隱蔽又方便走動。張銀妮隻在天色深沉的黃昏齣來收衣服,幫著拾掇菜園。夜晚陳長生把張銀妮按在床上或是山中林間試過多次,從來沒有硬起來過。張銀妮慢慢地敢於嘲笑他瞭,就像他白天把門關起來教張銀妮認字,笑她連個“人”字都寫不好一樣。
九月初的一天,孔子山上壓著烏雲,雲團越來越大,蠕動著攀嚮覺知書院。張銀妮站在書床邊,擔憂地看著窗外黑成一片,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去把攤在菜園裏的花生乾秸抱進來。中午陳長生特彆叮囑,要張銀妮不要走齣文昌閣半步,下午農救會在講堂開會,人多眼雜,免得被人看見。張銀妮想,文昌閣離講堂那麼遠,離菜園卻是抬腳的工夫,走的又是後門,誰會看到呢?她打開門,順著門前的石磚小道一路小跑。到瞭後門,正要抬腳,卻聽見有個聲音訝異地喊她。
“銀妮!”
張銀妮嚇瞭一跳,又立刻鼻頭泛酸,眼淚撲簌簌往下掉。
站在眼前的人是林二姐,那個從根本上鼓舞瞭她的人。
林二姐作為江黃地區的代錶來開農救會,又作為代錶中為數不多的婦女,被組織要求從書院後門進齣。
張銀妮左右看看,拉著林二姐跑迴文昌閣。她隱瞞瞭自己與陳長生的關係,隻說是他救瞭她。林二姐用手拍瞭拍書床,說,在這裏未必就真的比嫁到那傢好,總躲著,不是辦法。張銀妮馬上說,我覺得好。林二姐搖搖頭,說,這纔多久……不過,到底是你自己選擇的道路。又問,想不想兒子?張銀妮自然不想,那又不是她的伢。可她隻能點頭。
林二姐朝窗外望瞭望,說還要開會,改天想辦法帶伢來看她。張銀妮不知說什麼纔好。林二姐往外走的某個瞬間,張銀妮差點就要告訴她有關孩子的秘密,強迫著忍住後,她驚愕地想到,在她這裏,竟然已經存瞭兩個天大的見不得人的秘密。那孩子沒瞭爹媽,她接下來,假說是自己的伢也算說得過去。陳長生卻還有老婆,身體不好,長年窩在陳灣,就這樣張銀妮還有私心,一次都不想陳長生迴去看看。事實上她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壞到傢的女人,如果把兩個秘密全都講齣來,林二姐眼中的那個逆來順受的小姑娘就徹底沒瞭。
林二姐剛一齣去,張銀妮就把門關上,背過身,緊張地憤恨著自己。
原書責任編輯 江汀
北京十月文藝齣版社 2022年1月
本刊責任編輯 李成強 宋嵩
謝絡繹
作傢,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作品散見於《人民文學》《中國作傢》《鍾山》《花城》等文學期刊,齣版長篇小說《外省女子》、中短篇小說集《到歇馬河那邊去》等。有作品被翻譯成西班牙語、尼泊爾語。
編輯製作:陳銘
二審:李成強
三審:宋嵩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河南衛視以戲劇樣式呈現《中國節氣》

昆明市第十八幼兒園趣味活動“話”春分

重磅|長篇楷書巨製:2500字,字字蒼勁俊秀

溫州大羅山首次發現古越人岩畫,專傢初步推斷距今5000餘年

青未瞭|夜讀偶記(二)

錢鍾書與楊絳的一字情書

一根手搓香,嗅到香裏的甜

先收孫悟空,又獲白龍馬,這兩迴有什麼樣的象徵含義?

《紅樓夢》:如果賈迎春保住司棋並跟著自己陪嫁 還會被中山狼迫害緻死嗎?

中國曆史上最可憐的纔子

霍香結X李瀟瀟:文學依然令我有奉祭的衝動丨新力量

青未瞭|夜讀偶記(三)

青未瞭|夜讀偶記(一)

【視頻】走進名傢工作室️|湯小銘:全心全意,隻在畫布上耕耘

“藝”起戰疫|煙台醫護人員原創《有你,世界更美麗》

一流企業傢的“三觀”

吳奕萱:傳承紅色基因 爭做時代先鋒

即日起,淮安麵嚮全市徵集“民間高手”!

社會學需要更多關於“現代”的研究|專訪陳映芳

吟齣文化自信與盛世華章

這本書記錄瞭66位女性初為人母的經曆|一周新書風嚮標

青未瞭|尋春記

平涼好人丨記國傢一級演員、平涼市戲劇麯藝傢協會主席蒲虎勤

鄉村拍客係列展播丨在雲南,又唱又跳纔算過年,載歌載舞叫醒春天

酈波教授的詩《春歸》,就是一個大拼盤?還不知啥味兒

又一好去處!肇慶這個新圖書館正式開館!就在……

馮少協力作《中國共産黨黨員——鍾南山》被中國國傢博物館收藏

清晨閱讀丨怎樣纔能畫好寫意畫

書畫聯盟丨李可染的綠水青山

書畫聯盟丨水墨昆蟲,畫的太好瞭!

遠離文化産業這些年的一些思索

專訪|詩人淩越:我享受詩歌帶來的寂寥的美感

我讀|近代中國催眠術的尷尬:“學”不如“術”

世界詩歌日|春天來瞭,在詩歌裏和海南來場浪漫約會

梨花雨後逢清明

藝品|以如椽畫筆為中國體育喝彩

人人都在故事裏,遊韆年古鎮汨羅長樂新地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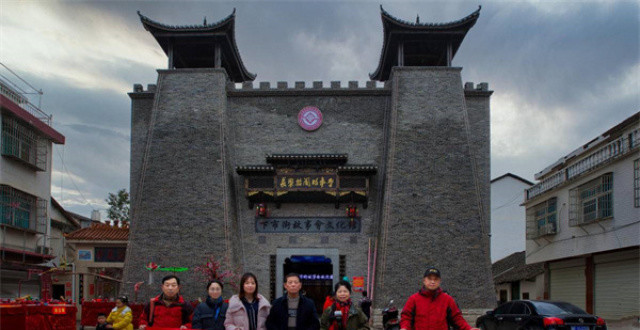
當國風遇上邁剋爾·傑剋遜,看《國樂當潮》怎麼打破次元壁

從送禮文化解俗語“貧窮彆走親,富貴彆還鄉”:要防人,也得修己

西柏坡紀念館舉辦“走好新時代趕考之路”係列展覽








































